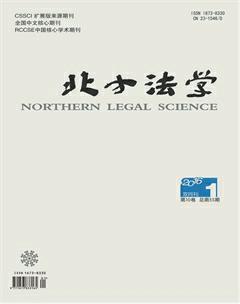程序正義的社會心理學及在糾紛解決中的運用
程波
摘要:法律權威需要尋找一些方法,以解決沖突并增進和協調人際和群體之間的關系。在這種考察中,社會心理學領域中圍繞“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以實驗方法展開的研究成果顯示:程序和程序正義在解決糾紛方面存在巨大的潛能。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程序正義的社會心理學及其在美國社會的沖突衡量與評價、沖突轉型的治療分析以及沖突解決策略的可行性認識等方面,均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也有助于我們分析美國替代性糾紛解決方法(ADR)適用的各種情境。
關鍵詞:程序正義社會心理學治療性法學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1-0016-09
社會心理學(social psychology)是研究人與人相互作用的一門現代社會科學。每天我們自身的行為與周圍人(父母、朋友、老板、老師、陌生人——事實上,在整個社會情境中)的行為之間都在相互影響。這種相互影響不只停留在人的行為層面,還包括人們的思想、情感和外在的行動。有時候這些相互影響會彼此起沖突。社會心理學家對于當各種不同的影響在個人內心彼此發生沖突時會產生何種結果,也特別感興趣。在戴維·邁爾斯(David G Myers)看來,社會心理學家就是通過科學地探索人們彼此之間如何思考、如何影響以及如何聯系來研究這些關聯的。 ①與上述社會心理學的定義相關,在社會內部和組織群體內部,由于人際和群體間的沖突仍然持續不斷,人們日益求助于法律和法律權威以解決這些沖突。因此,法律權威需要尋找一些方法,以解決沖突并增進和協調人際和群體之間的關系。一種理想的糾紛解決方式是:有關各方都能夠接受法律的決定,彼此保持協調的關系,對于處理有關糾紛的法律權威以及更一般的法律和法律權威感到滿意。②在這種考察中,社會心理學領域中圍繞“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以實驗方法展開的研究成果顯示:程序和程序正義在解決糾紛方面存在巨大的潛能。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3頁。
一、審視程序正義的社會心理學
20世紀法學學習開始跨學科化,這個傳統始于社會學和經濟學,但是后來擴展到了政治科學和心理分析,并且最后開始包括文學理論和哲學。這種法學學術轉向也為“司法裁決的替代性方式”、“從制度分析轉向過程分析”(即把審判視為程序參加者的相互作用的過程)提供了“從法律以外尋找客觀性標準的科學化主張”。至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調解、仲裁和其他相關糾紛解決方法——替代性糾紛解決方法(ADR),作為控制訟案激增從而減少庭審遲延、節約司法成本、提升公眾對司法滿意度的手段,對法人類學和法社會學領域關于糾紛與糾紛處理的研究成果,包括社會心理學關于程序正義的研究成果的有益利用是相當顯著的。例如,在一些被正式組織稱為“模范(extrarole)”行為的社會心理學研究中發現,當群體內部的某些成員從事有益于該群體的合作行為時,為了合作而實施懲罰的威脅或激勵機制,可以促使人們接受某些決定。但是,如果群體成員自愿實施某些行為,且這些行為有助于群體形成內在的認同感和忠誠感,那么這些行為就有益于該群體。如果人們認為群體的決定公正,他們就會自愿地與群體合作。因此,公正的決策程序會產生一般性效應,有助于激勵人們自愿地維護他們所屬的群體。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9頁。這種訴諸于心理學上對于程序公正的理解,有助于不同群體間借助共同的正義概念實現社會協調。美國和其他地方的社會心理學家不僅“通過試驗科學地證明程序公正加強了有關個人對法律和司法決定的服從”,[日]谷口安平:《程序公正》,載宋冰編:《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演講錄》,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頁。而且顯示出令人樂觀的結論:“人們的正義或公正觀是一種社會協調機制,通過這種機制,人際和群體之間才得以維持互動。正義的價值就在于使得人際和群體維持互動,消除沖突和防止社會解體。沖突和敵對可以導致社會互動關系的解體,一旦面臨這種威脅,人們便不得不求助于權威。程序正義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這種解體,并有助于維持人們之間建設性的長期互動關系。”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4頁。
人們關注自己所從屬的群體,實際上更多地是關注該群體做出裁決時適用了什么樣的程序。對于人們的這種程序性取向,社會心理學者的研究表明,人們關注程序正義問題,會影響他們對司法機關和有關機構的看法。[美]湯姆·R.泰勒:《人們為什么遵守法律》,黃永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94頁。根據社會交換和社會依賴的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理論,人們之所以要加入一個群體并且愿意留在這個群體中,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可以從群體中獲得利益,或者說,人們之所以要與他人交往,其目的在于努力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因此,如果程序是公正的,即使他們短期內無法獲得自己期望的利益,也可能合理期望自己能夠獲得長期的收益。這一以人的自利性假設為基礎進行的研究,為美國學者約翰·蒂伯(John Thibaut)和勞倫斯·沃克(Laurens Walker)早期關于程序正義的研究提供了最基本的前提。蒂伯和沃克的研究直接以法律糾紛解決程序為對象。他們通過實驗研究證明,結果(outcomes)并不是唯一決定人們事后感受的因素,無論獲得什么樣的結果,一個被認為公平的程序本身都能增加人們對法律制度的滿意程度。也就是說,只要決定的程序符合正義(程序正義),結果就更具可接受性。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8頁。這種圍繞“法律權威富有成效地解決糾紛和實施規則的能力”展開的研究,其關注點是權威行使的方式,即重視過程的公正而不是結果的公正。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8頁。根據這一理論,他們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即一旦人們發現自己陷入與他人的糾紛,而且通過雙方的自我協商無法成功地解決問題,就會轉而求助于第三方來解決這些糾紛。他們會努力向第三方提出自己的證據和意見,通過這種方式實現對處理結果的最大化控制。前引⑦,第291—292頁。通過進一步的問卷設計,還發現對抗制(adversary)的訴訟結構比糾問制(inquisitorial)讓人感到更公平(fairness)。按照他們的理論設想,權威借助程序正義的機制解決沖突。結果,法律權威關心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預防、抑制和終止社會沖突。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4頁。
針對蒂伯和沃克旨在揭示程序正義效果的實驗所表明的基本論點:即人們對于第三方所采取程序公正性的認可程度,影響著他們對于該結果的滿意程度。在著有《程序正義的社會心理學》(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cedural Justice,與Allen Lind合著,1988)的紐約大學心理學與法律教授湯姆·R.泰勒(Tom Tyler)看來,蒂伯和沃克的研究結論“得到了廣泛的驗證” 。泰勒認為,蒂伯和沃克關于程序正義實驗最值得關注之處在于,這些程序正義效果在對真實糾紛的研究中得到了驗證,這些真實糾紛所涉及的是真實的當事人。參見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8—479頁。泰勒在1984年“芝加哥研究(Chicago Studies)”的基礎上,曾于1990年發表了著名的論文《人們為什么遵守法律》(Why People Obey the Law),他通過控制變量證明程序正義對人們主觀感受的影響不但獨立于程序適用的結果,而且也獨立于所謂的掌控感。泰勒指出,程序的重要意義在于它影響了人們對于權威合法性(legitimacy of authority)的態度,而這一態度決定了人們是否主動服從法律(compliance)。在泰勒等法律心理學研究者的成果中,通過社會心理實驗證明了人們的正義感在很大程度上與所屬群體的身份感有關,程序正義有助于實現人們在社會地位方面的自我認知和滿足。在隨后關于正式和非正式糾紛解決方法的研究中,泰勒還發現,那些利用調解這樣的非正式糾紛解決機制解決問題的人,一般都覺得這種程序是公正的。前引⑦,第269頁。這是因為,“這些非正式的法律程序比審判更能讓人們從直覺上產生公正的感覺。比如,這些非正式程序能夠提供給當事人更多的機會,讓他們直接參與糾紛的處理。如果所要處理的事情涉及的是人際關系方面的問題,這種程序也能使裁決者有更大的靈活性。而這些優勢是審判等正式的糾紛處理程序所沒有的” 。前引⑦,第270頁。有趣的是,人們顯然把自己是否應當服從當局與當局是否使用了公正的程序聯系在一起,而不是將其與自己是否獲得了公正結果聯系在一起。前引⑦,第295頁。另外一些研究者發現,人們關于程序正義的判斷在影響人們在特定時間內遵守協議方面,尤其具有重要作用。特別是社會心理學家普魯特(DGPruitt)及其合作者,通過研究那些促使糾紛者遵守終止糾紛的調解協議的因素發現,當事人在6個月后是否遵守協議,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調解程序是否公正。轉引自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79頁。
在日本學者谷口安平看來,蒂伯和沃克、林德和泰勒等法律心理學家一系列“有趣的實際研究”,不僅“提供了一種沖突雙方可以更容易接受最終結果的方式”,而且在評估公眾強烈關注法庭作出決定的程序公正方面,涉及以下四個決定性因素:它們是“參與”、“可信”、“中立”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前引⑤,第376—377頁。其中,參與就是指發生沖突或出現問題時,人們如果能參與糾紛或問題的解決過程,就解決方案提出建議,那么他們就會感到受到了較公正的對待。這樣的機會涉及對過程的控制和意見表達。對于參與所具有的積極效果,在美國司法實踐有關辯訴交易、審判聽證以及調解的研究中,都發現了這種效果。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3頁。社會心理學有關研究發現,“在人們認為他們的意見對于結果的影響微乎其微或根本沒有影響的情況下,他們仍然看重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例如,受害人不管自己的主張對于刑事被告的判決是否會產生影響,他們在審判聽證時都會重視發表意見的機會”。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3頁。“有關研究發現,人們看重參與機會,從而表達自己的意見和陳述有關案件,這種研究結論有助于解釋為何人們偏好訴諸調解。人們通常認為,與正式審判相比,調解提供了更多的參與機會”。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3頁。而“人與人之間的尊重”,就是社會心理學關于“人們希望自己在社會中的權利和地位得到他人的尊重。人們十分在意的是,在與權威接觸的過程中,他們作為人和社會成員的尊嚴應得到承認和認可。當人們與權威接觸時,禮貌和尊重與他們獲得的結果并無實質關聯,而人們地位得到認可的重要性卻與沖突解決存在特殊的關聯。比其他問題更重要的是,尊重與尊嚴是權威能夠給予每個與之接觸之人的東西” 。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5頁。基于此,谷口安平指出,“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作為程序正義的因素是法律心理學家提出的重要因素,既“符合我們的常識”,又“可以被認為是參與不可分割的部分” 。前引⑤,第377頁。諸如良好的法律教育、嚴格的測試和資格認證制度、完善的培訓、優厚的待遇(薪水、任期等)、良好的過去紀錄(沒有腐敗記錄)等等“可信”因素,“對人們和訴訟人對程序公正的看法的心理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前引⑤,第377頁。“中立”作為程序公正的獨立價值“也得到了心理研究的印證”,前引⑤,第378頁。這一因素被單列出來并且重點放在了決策者的中立性或程序的主觀看法,“包括誠實、公正的評價和決策過程中運用事實而非個人意見” 。前引⑤,第377—378頁。根據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的意見,所有這些(因素)都加強了人們對司法決定的自愿服從,是一個了不起的優勢。前引⑤,第378頁。
二、沖突解決的個人理性策略與治療性法學
社會心理學在程序正義效果驗證上的研究成果顯示,在所有類型的社會情境下,程序(正義)問題都至關重要。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1頁。對于創建和維護內在價值來說,“公正的決策程序會促使人們自愿地與群體合作,因為這種程序有助于保持人們對群體的認同、忠誠和歸屬。相似地,程序正義有助于促使人們服從社會規則,因為它會增強人們對于權威合法性的信念” 。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1頁。受此啟發,美國社會科學家逐漸認識到命令和控制在解決沖突方面的限制,進而“把個人視為算計得失的行動者,認為他們在具體環境下根據成本與收益來思考、感受和行為”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1頁。作為個人理性選擇模式主導下的社會控制策略。這種沖突解決策略也就是近幾十年來總稱為“可替代解紛程序”參見MacCoun,Lind,and Tyler,Altern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in Trial and Appellate Courts,in DKageheiro,Psychology and Law(New York:Springer,1992)轉引自[美]杰弗里·C哈澤德、米歇爾·塔魯伊:《美國民事訴訟法導論》,張茂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和“因地制宜調解”方式,GCormick,Resolving Environmental Conflicts through Mediation Experience,Process and Potentials(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San Francisco,Sept7,1978)轉引自[意]M.卡佩萊蒂、B.加斯:《緒論:福利國家的接近正義》,載[意]莫諾·卡佩萊蒂編:《福利國家與接近正義》,劉俊祥等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頁。引導人們自愿地實施合作行為以更有效地解決糾紛在美國呈日漸上升趨勢的主要原因。表現為:對當事人自治的提倡和重視;鼓勵當事人通過利益衡量及協商妥協解決糾紛;贊成并積極試驗和推行各種新型的調解程序,以替代訴訟和審判。例如,1987年韋克斯勒(Wexler)在美國國家精神衛生研究所舉辦的關于法律與精神衛生的研討會上,首次提出了治療性法學(Therapeutic Jurisprudence)的概念。[英]詹妮弗·M布朗、伊麗莎白·A坎貝爾主編:《劍橋司法心理學手冊》,馬皚、劉建波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頁。在於興中教授看來,愈療法理學(即治療性法學)這一概念的起源也歸功于邁阿密大學法學院已故教授布魯斯·威尼克(Bruce Winick)。韋克斯勒和威尼克這兩位愈療法理學的創始人認為,有必要提出愈療法理學這一全新概念,研究實體規則、法律程序,還有法律工作者、主要包括律師和法官,在對牽涉于法律程序中的個人,在何種程序上產生心理創傷愈療方面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影響。參見於興中:《法理學前沿》,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55—166頁。隨后這一概念很快被定義為主要是探討法律、法律程序、法律制度以及法律工作者對個體福利所產生的影響,也是解決社會沖突問題的最佳途徑之一。由于它強調人的福利,強調治療性價值,因此治療性法學自然會與其他途徑存在交集,比如恢復性司法、調解以及程序正義。前引B32詹妮弗·M布朗、伊麗莎白·A坎貝爾主編書,第79頁。
美國社會心理學家普魯特(D·GPruitt)也認為,無論是在個體間還是群際間,只要關系發生問題,關系治療都有效。[美]狄恩·普魯特、金盛熙:《社會沖突——升級、僵局及解決》,王凡妹譯,人民郵電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頁。由于沖突常常植根于社會結構或體系當中,而那些政治的、法律的、社會的、經濟的結構體系又制造出利益分歧和扭曲的關系,因此,關系治療可能還要結合其他干預措施,以改變發生故障的社會體系。除了最常見的第三方調解外,普魯特還特別介紹了關系治療師和沖突管理培訓師等類別的第三方角色。其中,婚姻治療是關系治療中最古老的一種治療方法。很久之前,婚姻治療師就像調解者一樣,試圖幫助夫妻訂立一項合約,約束雙方行為,以改善夫妻關系。現代的婚姻治療師試圖幫助夫妻解決自己的問題,教給他們聯合解決問題的技能,并幫助他們掌控和克服雙方長期緊張的交往方式。類似的治療方法也適合長期緊張的親子沖突,以及同事沖突。前引B34,第299—300頁。在普魯特看來,美國近年來治療方法和教育干預項目越來越多,以便促進沖突雙方的寬恕與和解。舉例來說,有一種治療方法能幫助夫妻雙方原諒對方的背叛行為。治療師先協助夫妻評估背叛行為帶來的所有后果,之后再幫助他們想出應對負面感情的方法。治療師還會幫助雙方探究導致背叛行為的各種原因,并且培養他們的共情,最后,他們會協助夫妻雙方評估和解的可行性。前引B34,第300頁。這其實是對治療性法學作為一種治療的動因以及其所具有的巨大的療愈潛能的一種回應。
在於興中教授看來,治療性法學關注傳統法學研究中不受重視的法律在人的感情生活和精神健康方面的影響,它的目標是創造性地使法律在不違背和影響其他原則的情況下具有最大的愈療效果,其潛在的問題是法律制度如何運行并且影響在其中生活的人。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57—158頁。針對美國越來越將治療性法學視為一種可應用于提高司法制度的結果(如沖突解決、罪犯矯治以及家庭治療)的關系性研究,范愉教授也介紹了美國家事調解與“治療”理念。在她看來,“治療型調解”與其說是法律上的糾紛解決方式,毋寧說是一種心理治療。范愉:《非訴訟程序(ADR)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頁。由于美國家事調解更多地考慮人際關系而不是法律方面的爭點,因而擔任家事調解的人多具有心理學方面的素養,遂將“治療(therapeutic)”理念帶入了調解之中。具體而言,就是促進當事人正面認識糾紛的根源在于感情上的爭點,在調解人認為適當的場合,鼓勵當事人繼續維持雙方的關系。前引B38,第72頁。
在過去,美國人曾將法院視為解決糾紛的主要途徑,盡管他們可能在這一過程中輸掉案子和損失金錢,如美國最高法院前任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Warren EBurger)所說:“越來越多地訴諸法院尋求救濟個人怨憤,使這個國家遭受浮夸言辭的病痛和由此產生的訴訟爆炸的威脅” 。From David Trubeck,Turning Away From Law?轉引自[美]博西格諾等:《法律之門》,鄧子濱譯,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637頁。許多法律學者、律師和法官表達了他們對“訴訟爆炸”的憂慮,例如,曾經是法律職業者、后來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德里克·博克(Derek Bok)在1983年春發表了一份報告,也同樣反對司法裁判,并建議法學院教給他們的學生“妥協與適應的溫和化藝術(for the gentler arts of reconciliation and accommodation)”,把注意力從法院轉向一種解決爭議的“新的自發機制(new voluntary mechanisms)”。Owen Fiss:《反對和解制度》,載[美]歐文·費斯:《如法所能》,師帥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頁。一些評論家甚至指出,司法的作用就是實施轉型。比如朱迪恩·麗絲奈克(Judifh Resnick)聲稱:“許多法官已經背離他們先前的態度……法官越來越多地……與當事人面談,鼓勵解決糾紛并監督為案件的審理所做的準備……作為管理者,法官比以前更多地了解案件,他們與當事人談判庭審前后案件的進程、時間和范圍……”Judifh Resnick,23JudgesJournal,8—11(Winter 1984) 轉引自前引B40博西格諾等書,第636頁。許多研究者甚至一直在檢視當事人為什么要訴諸法院這一社會心理現象。例如,維勒姆·奧伯特(Vilhelm Aubert)認為:為什么沖突的雙方背離“理智的”行為,甘冒劇增的、讓一方受損的風險而訴諸法院?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們都傾向于過高估計自己的獲勝機會……為什么人們傾向于高估自己勝訴的機會呢?原因之一是有利于本方的論點更容易得到,也更容易被接受。有理由說,人們缺乏對案件全面的洞察,積極的方面更容易被體察到。訴訟案件有著道德標簽,預料在法庭上的失敗通常意味著懷疑己方的道德正確性。個人對這種道德疑惑的抗拒,自然而然使實際的預見不甚可靠,甚至需要保持一種對另一方的道德攻擊態勢。法律案件代表的生活領域中,人們很難完全理智,很難不偏不倚地以實證為根據預見未來。加之其他原因,這一領域通常在“技術上”難以作出預見。Vilhelm Aubert,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umeXII,No1,1967,p51 轉引自前引B40博西格諾等書,第636頁。
也許正是有了上述美國社會的沖突衡量與評價、沖突轉型的治療分析以及沖突解決策略的可行性認識,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留學于美國的棚瀨孝雄在日本法學界以“頗有兼容并包的胸襟”,提出了一種作為對“法的邊界”反動的“法的擴散”的構想,即要把社會性評價視角帶入到法律中來,使在關系性中得到定位的個人,能以自己的語言來言說法律。在他看來,“糾紛解決的過程分析意味著研究焦點集中于現實中卷入糾紛的個人身上,主要探究規定他們進行行為選擇的各種因素”。[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與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7頁。基于此,棚瀨教授自覺地把人類學、社會學、社會心理學等社會科學為了分析過程而精心構成的分析工具(行為科學、意思決定模型、網絡分析、象征互動等)“積極地導入糾紛解決過程的研究領域” 。前引B44,第6—7頁。他從個人行為的經驗層次,研究了“當事人也因實質上參加了程序能夠獲得更高的心理滿足感” ,前引B44,第259頁。并對美國最早從心理治療的角度來考察糾紛解決的初步理論化的文獻加以整理,提出一種“治療型調解”模式。在他看來,治療型調解的基本前提是把糾紛視為人際關系的一種病理現象,解決糾紛意味著人際關系恢復正常。James Gibbs,Two Forms of Dispute Settlement among the Kpelle of West Africa,轉引自前引B44,第66—72頁。無獨有偶,美國紐約大學人類學及法律社會學教授薩利·安格爾·梅麗(Sally Engle Merry)在其《訴訟的話語——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人的法律意識》一書中,描述了美國初等法院在庭審和調解中最常使用的法律、道德和治療性三種話語及話語轉換的互動過程。在她看來,人們是在文化和自覺的層次上行使法律權力的。法律的語言和實踐,不僅對那些受過法律訓練的人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于普通的民眾來說也是如此。因此,“在話語中嵌入文化支配是一個十分微妙的過程” ,[美]薩利·安格爾·梅麗:《訴訟的話語——生活在美國社會底層人的法律意識》,郭星華、王曉蓓、王平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頁。“將法律訴訟轉換為道德話語和治療性話語”,“這被很多倡導者看作是調解的目的。人們倡導的是這樣一個過程,這一過程關注的是問題中動態的人際關系,并將問題界定為‘不適合由法庭解決而應該采用更‘適合的解決方式,這一過程關注的是感受和關系”。前引B48,第181頁。
這種關注“感受和關系”的糾紛解決實踐的研究,不僅把焦點對準糾紛過程中的個人,而且將他們置身于其中的社會狀況、他們的利益所在、與其他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制約著人們行為的各種社會規范以及所涉及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fication)等等,都納入到了訴訟外糾紛解決過程的分析框架,日漸成為英語學術圈近些年來的學術新動向。例如,美國Geordgetown大學的Carrie Menkel Meadow教授,在2003年美國《糾紛解決雜志》(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第2輯發表的論文中,以及隨后發表的另一篇論文中,重點介紹了糾紛解決理論跨越從法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到國際關系等多領域的特點,討論了有關糾紛解決的一般理論與種種不同的具體語境(contexts)之間的關聯問題。Carrie Menkel-Meadow,Correspondence and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s Conflict Resolution:Lessons fron General Theory and Varied Contexts;From legal Dispute to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Human Problem Solving:Legal Dispute Resolution in A Multidisciplinary Context,參見王亞新:《〈法律程序運作的實證分析〉序》,載王亞新、傅郁林、范愉等:《法律程序運作的實證分析》,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對此,有學者指出,雖然Meadow教授的論文顯示了有關糾紛解決的理論在“跨學科”這方面具有相當高的普遍性和一般化程度,但其基調卻是對這種植根于歐美社會的理論究竟能否有效適用于“跨文化”的不同語境表現出一種強烈的懷疑。他的結論是在研究糾紛及糾紛處理的領域,當前需要的是對具體情境更加敏感(more sentiment to contexts)的理論。前引B50王亞新文。
在今天的美國學術界,法律和其他相關學科,主要是心理學、社會工作、犯罪學和精神科學形成了很好的合作關系。由于治療性法學提出一個更加符合人性的法律作為治療手段的觀點,“創造了一個以權利為導向的”,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58頁。“全新的令人興奮的”,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59頁。“真正跨學科的”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59頁。方法,并能夠設計出“減少法律以及法律程序對心理療愈進程所造成負面影響的一些嘗試”,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64頁。因此,律師和法官應該始終注意精神衛生法的起源、正當程序的保障作用,以及從具體案件吸取的經驗;但是同時,律師和法官也不應回避行為科學。參見前引B32於興中書,第159頁。
三、程序正義與社會化的心理學理論
許多心理學理論的發展——例如社會知覺與認知,歸因理論、偏見,以及群體行為等,都可以通過對考察糾紛解決過程的“具體情境”的研究得以驗證。社會心理學研究者發現,當人們在所屬群體內部發生沖突,且負責解決沖突的權威也屬于該群體時,人們可能更依賴正義的共識。但是,如果糾紛是通過調解而不是通過審判解決的,人們如何判斷調解程序是否更為公正?在泰勒等法律心理學家看來,影響這種判斷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社會化。也就是說,一個社會或者組織是通過社會化的方法在其群體內部交流,并形成關于“公正”程序和“公正”結果的共同信念。群體新成員則需要通過向老成員學習來形成自己對程序價值觀念的認識。前引⑦,第302—303頁。對這種“社會化”在個人信念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社會心理學研究者伊斯頓和丹尼斯進行了研究驗證。前引⑦,第303頁。伊斯頓的理論還討論了擴散性支持如何從具體支持中分離出來的問題。他提出,如果當局能讓人們覺得為了自己的長期收益他們有必要建立對法律制度的擴散性支持,這對當局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他認為,如果政治或法律制度總是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或者總是不能為其成員提供有利的結果,其終將喪失人們的擴散性支持。人們通過社會化過程所建立起來的對當局的情感依戀,為維持這種支持提供了緩沖。但如果人們總是不斷經歷不平等的事情,他們這種對當局的情感上的忠誠終究會消弱甚至煙消云散。前引⑦,第303—304頁。與伊斯頓的理論一樣,有關社會化的心理學理論則強調,社會化過程對建立這種基本價值觀念非常重要(霍夫曼1977年)。這種理論認為,一個文化群體的成員在童年時期會學習這個社會的基本共同價值觀,這些價值會制約他們成年后的行為。前引⑦,第304頁。所有這些信念的社會化理論其實也提出了一種策略,即我們需要重視建構人們對社會和社會制度的認同。如果人們深度認同權威,那么,他們就會更重視自己是否受到公正對待,而較少關注是否獲得有利的結果。如何才能建構積極的認同?重要的一點就是以程序公正的方式對待群體內部成員。有關研究揭示,程序正義有助于建立人們對群體的依賴和認同,以及服從權威和群體規則的情感。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6頁。
就解決沖突而言,基于正義策略有效性的范圍存在一些限制。這些限制或許是潛在的,因為社會性質的不同可能對于社會沖突解決的影響也不同。例如,潛在的文化背景可能改變人們對程序正義的接受程度或改變人們界定程序公正的標準。然而,正如社會心理學研究者所注意到的,“在看待程序正義的重要性上,不同種族成員之間的差異很小。無論是白人還是少數民族群體,在訴諸第三方解決沖突時,更重視的是他們所經歷的程序是否公正,而不是他們所接受的結果是否公正”。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5頁。一些研究還發現,程序也具有強勁的穿越意識形態的能力。就是說,持不同社會價值觀和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們,常常會就特定程序是否公正這一問題達成一致意見。這一發現特別重要,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對于人們關于何謂結果公正的觀點會有強烈影響,在這方面,程序正義比分配正義可以成為穿越不同社會和意識形態的更好橋梁。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5頁。當然,這些研究結論并不意味著,存在某種適合一切情境的普適的公正程序。相反,即便在特定的情境中,人們在界定程序公正時,也會強調不同程序要素的重要性。例如,人們在發生沖突時,會把陳述自己觀點的機會看作是公正程序的核心。然而在其他情況下,獲得參與機會對判斷程序是否公正則不那么重要。人們會區分不同的境況,并根據不同的境況適用不同的關于程序是否公正的判斷。由此我們可以得知,人們并不會以簡單的方式對待程序公正問題。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7頁。
泰勒等人的程序正義理論在方法和進路上是心理學的,但是其理論層次已經超越了基本的實證研究,具有一般社會理論色彩并被引入到法律理論的研究中。他在2006年《人們為什么遵守法律》一書中,不僅檢視了人們在評價程序正義是否公正時所依據的心理學基礎,而且提出了合法性的規范主義觀點:
人們之所以遵守法律,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做是正確的,他們在評價自己的個人經歷時,實際上就是看自己的這些經歷是公正的還是不公正的。而且,他們在做出這種評價時,考慮的也是那些與結果是否有利于自己無關的因素,比如他們是否獲得了陳述自己意見的機會,是否受到了有尊嚴的對待等。對于所有這些問題,都是人們的規范性觀念起了決定性作用,會對他們如何看待這些問題以及如何行動產生影響。通過總結我們的研究結論,可以這樣說:一個人的社會價值觀,也就是他們認為什么是正確的,什么是適當的,決定了他們對當局的看法,也決定了他們如何行動。法律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和組織學理論認為,自利是影響人們對當局的看法和決定人們的行為的基礎,與我們的觀點有很大的差距……人們并不像法律當局通常所想象的那樣,實際上他們更愿意從規范性的角度來評判法律當局,來提出自己的訴求。前引⑦,第305—306頁。
盡管美國法律學者已經指出,在美國的法律制度中,無論是訴訟或調解或其他ADR方法,都是個人當事人在評估證據、提出案件和達成解決方案上承擔主要責任。因此,即使是美國最激進的調解倡導者也強調私人秩序和個人選擇。但無論如何,選擇都必須是有意識的,并且是對優先性加以衡量而其在沖突的目標之間達到適當平衡的選擇——解決私人糾紛或者設定公共規范標準,規范的程序正義或自由裁量的個別正義,效率或公平。當然,至少每個社會都必須認識并懂得其所選擇的糾紛解決方法如何能夠發揮作用,如何禁止或促進那些目標。[美]史蒂文·蘇本、瑪格瑞特(綺劍)·伍:《美國民事訴訟的真諦——從歷史、文化、實務的視角》,蔡彥敏、徐卉譯,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26—227頁。在社會心理學家看來,法律學者關于“人們有意識的選擇”,可能也意味著他們并不僅僅關注結果,相反,他們更可能關注人們的情感和行為包含重要的倫理和道德的要素,這些要素或許比結果更重要。因此,在社會情境中,人們如何對待他人問題上所表現的倫理或道德之維,可以成為建設性地解決社會沖突的一種途徑。前引②湯姆·R.泰勒文,第487頁。這一途徑還進一步表明,要想使人們自愿服從當局的裁決,程序正義是問題的關鍵。它對于人們如何評價司法機關的裁決、如何才能消除對司法程序的不滿情緒、如何評價法律制度、如何評價當局的政策等等,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由于人們已經認識到程序正義的重要性,因此法律當局不斷調整其糾紛解決體系,努力使人們更愿意使用調解的方式來解決糾紛,這就是美國糾紛解決替代運動(ADR)興起的重要原因。
總之,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證角度,社會心理學為審視程序正義問題提供了豐富的資源,也有助于我們分析“應用在很多新領域之中”的美國調解適用的情境。作為一種非正式的糾紛解決方式,最受關注的美國調解制度或許已經存在一種超越了法律本身學科界限的社會科學和心理學的話語空間。因此,作為法律人的我們,就需要努力把社會科學知識轉化為法律話語,盡管有時這種努力與本文的寫作一樣可能仍有明顯的缺陷,但是,我們的態度是積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