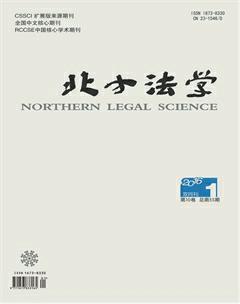“問題豆芽”案的刑事法治報告
歐錦雄
摘要:近一年多來,全國審理判決的“問題豆芽”案件近千件,被判刑人數愈千人,大多數案件是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的。然而,有些行業人士和法律專家認為,無根劑(主要成分為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等植物激素)不屬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產、銷售使用無根劑的豆芽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應一律認定無罪,并主張為這些案件翻案。但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是低毒農藥,是豆芽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的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而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為犯和行政犯(法定犯),因此,無論將豆芽制發過程理解為種植過程或食品加工過程,在豆芽制發過程中添加“無根劑”的行為,都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關鍵詞:問題豆芽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行為犯行政犯
中圖分類號:DF6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1-0122-11
一、“問題豆芽”案引起的法治論爭
近年來,我國惡性食品安全事件層出不窮,食品安全已成為國家和人民關注的焦點問題。
豆芽本是我國老百姓餐桌上的營養美味食品,但是,一些豆芽生產企業和個人為了縮短生產周期和提高產量,在豆芽制發過程中大量添加植物生長激素(如: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乙烯利)和多菌靈、百菌清、福美雙、諾氟沙星、青霉素等藥物。為了改變變色發黃的豆芽外觀又使用漂白劑、連二亞硫酸鈉等物質。 ①添加了植物生長激素的豆芽可在3—5天內長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這些“問題豆芽”曾充斥全國各地市場。由于豆芽很容易清洗,節約人力和成本,“問題豆芽”成為中小學、大學以及單位食堂很喜歡采購的菜種,食用人群眾多。
由于長期食用這些違法制發的豆芽將會逐漸損害人體健康,在媒體大量曝光“毒豆芽”案件后,“問題豆芽”牽動了全國人民的神經,并引起國家重視。因此,各相關執法部門在全國范圍內打擊生產銷售“問題豆芽”違法犯罪,摧毀了大批制售“問題豆芽”的窩點,抓獲了一大批涉案人員,嚴懲了一批犯罪分子。
在懲罰“問題豆芽”的犯罪行為時,大多數法院是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的。現在,全國各地的“問題豆芽”已基本銷聲匿跡。
然而,有些行業人士和法律專家對我國懲治“問題豆芽”犯罪分子的司法活動提出了批評。2015年2月6日,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組織召開了“無根豆芽案件法律問題學術研討會”(以下簡稱“研討會”)。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中國食品工業協會豆制品專業委員會、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中心、中國法學會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等單位的有關人員參加了會議,該研討會經廣泛討論后初步形成以下共識:(1)無根劑(主要成分為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不屬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2)生產、銷售使用無根劑豆芽的行為,不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也不構成生產、銷售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罪。(3)建議人民法院對生產、銷售使用了無根劑豆芽的行為不追究刑事責任。對正在刑事訴訟追訴中的上述行為,應當依法撤銷案件,或不起訴,或終止審理,或宣告無罪,原刑罰已執行的,受害人(即原審被告人)可依《國家賠償法》的規定享有取得賠償的權利。(4)建議媒體報道時對生產、銷售使用了無根劑的豆芽不再使用“毒豆芽”一詞,以免給人們造成這種豆芽就是有毒豆芽的感覺,過度造成人們的恐慌。《“無根豆芽案件法律問題學術研討會”成功舉行》,資料來源于中國刑事法律網:http://wwwcrimina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13503,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4月10日。
由于這一研討會有許多重要國家機關、機構和大學專家、學者參與,研討結論引起了各相關部門和人員的關注。
2015年3月,中國法學會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專職研究員王偉國等人在澎湃網發布了《203份“毒豆芽”案判決的初步統計分析報告》,對“問題豆芽”案全面提出質疑,主張對生產、銷售“問題豆芽”的行為以無罪論處。王偉國、姚國艷、強梅梅:《203份“毒豆芽”案判決的初步統計分析報告》,資料來源于澎湃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11880,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4月23日。自此,網上和傳統媒體為“問題豆芽”刑事案件翻案的聲音一浪高于一浪。
因生產、銷售“問題豆芽”而被定罪判刑或即將被定罪判刑的人員燃起了被無罪釋放的希望,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對于嚴厲打擊此類行為的信心受到沖擊。2015年6月16日,遼寧省葫蘆島市連山區人民法院對此前(2014年12月11日)該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刑的“問題豆芽案”被告人農某和魯某改判無罪。符向軍:《“毒豆芽案”無罪判決是尊重科學》,載《法制日報》2015年7月29日第7版。若因生產、銷售“問題豆芽”而被定罪判刑的案件全部翻案,“問題豆芽”將死灰復燃,并堂而皇之大肆占領市場。難道我國公安司法機關大力打擊生產、銷售“問題豆芽”行為的活動違背了法律規定?他們真的錯了嗎?
一年多來,全國處理的“問題豆芽”刑事案件近千起,被人民法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刑的犯罪人有1000多人,前引③。如果這些案件全部翻案,那么國家必須向涉案有關人員支付數以千萬元計的國家賠償款項。有人甚至預測這可能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集體被判有罪但又集體翻案的例子” 。黃芳:《兩高叫停“毒豆芽”案件審理》,載《東方日報》2015年4月15日。
二、“問題豆芽”法治治理的對與錯
我國司法機關在打擊“問題豆芽”犯罪的斗爭中,對違法添加“無根劑”的生產、銷售豆芽行為一般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主要打擊添加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這兩種物質的行為)。這一定性受到“研討會”專家和參與人員的普遍質疑,他們認為,這一定性是錯誤的,添加“無根劑”生產、銷售豆芽行為是無罪的。
至于這種行為是否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應以《刑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為準。我國《刑法》第144條規定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即構成該罪。刑法明文規定該罪為行為犯。所謂行為犯,是指只要實施了刑法規定的行為就構成犯罪既遂的犯罪。行為犯不需要考慮危害結果是否發生,只要行為人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就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不要求一定要造成人員傷亡的危害結果才構成犯罪。
該罪也是行政犯(法定犯),即指刑法規定的、違反了行政法中的禁止性規定而構成的犯罪。只要違反行政法中的禁止性規定,符合犯罪構成,即構成犯罪,即使其客觀上并沒有造成實際危害。行政犯的規定是為了更好地維護法秩序和更好地保護社會的需要而做出的規定。因此,行為人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為,即使最終鑒定結論認為這一批食品總體上無毒無害,也可認定其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于2013年4月28日頒布了《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運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法釋[2013]12號),其第9條和第20條對如何認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作出了具體解釋,這是當前辦理“問題豆芽”刑事案件的重要依據。
“問題豆芽”刑事案件的法治論爭聚焦于幾個方面:
(一)添加“無根劑”制發豆芽的行為是“種植”行為還是“食品加工”行為
《解釋》第9條第1款規定:在食品加工、銷售、運輸、貯存等過程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的,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第9條第2款則規定:在食用農產品種植、養植、銷售、運輸、貯存等過程中,使用禁用農藥、獸藥等禁用物質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的,也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
主張為“問題豆芽”案平反的人士認為,豆芽屬于食用農產品,無根豆芽制發過程屬于食用農產品種植過程,由于“無根劑”主要指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植物生長激素,這些植物生長激素屬于低毒農藥范疇,不屬于禁用農藥,因此,在無根豆芽制發過程中添加“無根劑”的行為,不能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參見前引②;云無心:《“毒豆芽”是樁“冤案”》,載《農村·農業·農民》2014年11月(B)期,第1頁。
由于豆芽制發具有一定的生物生長特性同時又具有農產品加工特性,因此,人們對豆芽的屬性在認識上有較大分歧。在制定相關文件或有關標準時,有的國家機關將豆芽歸類于蔬菜,將其作為初級農產品,有的國家機關則將豆芽作為初級農產品的加工品。關于豆芽制發是種植過程還是食品加工,原衛生部在2004年曾給北京市衛生局復函(衛監督發[2004]212號)指出:豆芽的制發屬于種植生產過程,不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衛生法》調整的食品生產經營活動。但是,農業部在《關于豆芽制發有關問題的函》(農辦函[2014]13號)(復函中國食品工業協會制品專業委員會)明確指出:豆芽屬于豆制品,其制發過程不同于一般農作物的種植活動,生產經營應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關規定。同時,農業部明確表示:“關于豆芽制發中農藥登記問題。目前尚無農藥產品在豆芽上登記使用,我部不受理植物生長調節劑在豆芽制發中登記。”這說明農業部對豆芽制發使用植物激素持反對的態度。此外,在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發布〈享受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的農產品初加工范圍(試行)〉的通知》(財稅[2008]149號)里,對大多數農產品的初級加工進行了界定,其中“食用豆類初加工”規定,對大豆、綠豆、紅小豆食用豆類進行清洗去雜、浸洗、晾曬、分級、包裝簡單加工處理而制成豆面粉、黃豆芽、綠豆芽行為,屬于農產品初級加工行為。
筆者認為,從豆芽制發目的、方式、過程和時間等方面看,豆芽制發不是種植過程而是初級農產品加工過程,豆芽不是初級農產品,而是初級農產品的加工品。在豆芽制發中添加“無根劑”的行為就是在食品加工過程中添加國家機關禁止在加工中使用的物質(低毒農藥)的行為。
根據常識,種植是指把植物種子或幼苗埋在泥土里使其生長。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新華字典》,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第631頁。 但是,隨著豆芽制發技術和方式的變化,豆芽機已發明并廣泛使用,工廠化制作已普遍化,目前,大多數商業化的豆芽制發過程已沒有使用一塊泥土或一粒沙,而是以泡發方式制發豆芽,這些豆芽制發行為顯然不是種植行為。
豆芽制發過程一般包括選豆、泡豆、孵化、采收、清洗幾個階段,在不添加植物激素的情況下,每個生產周期一般為7—10天。參見郝凌峰:《傳統生產工藝仍有大市場》,載《農民日報》2014年12月16日第7版。在豆芽制發過程中,由于豆芽種泡發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豆芽,其制發方式是將食用豆類泡浸孵化,且制發時間很短,因此,豆芽制發實際上是對初級農產品黃豆、綠豆等豆類的加工過程,而不是豆類的種植過程,若出于種植黃豆或綠豆等豆類的目的,而將豆種埋在泥土上讓其生長,其過程才是種植過程。如果將豆芽制發過程看作農作物種植過程,并按種植農作物來立法管理,那么,行為人在豆芽生產中可能會廣泛施加各種農藥、化肥或別的藥物,甚至施用殺蟲農藥,只要其殘留量不超標即可。但是,由于豆芽制發時間非常短,各種農藥、化肥或別的藥物缺乏使用的安全間隔期或休藥期,這些農藥、化肥和別的藥物極易被豆芽吸收或轉化成其它可檢測或不可檢測的有毒有害物質,從而造成具體的或潛在的危害后果。無根豆芽生長期非常短,僅僅3—5天即可長成,其危害更大。因此,我國絕不能將豆芽制發看成是農作物種植過程,并按農作物種植來立法管理。豆芽制發其實就是初級農產品的加工過程,而且是一種特殊的加工過程。豆芽則屬于初級農產品的加工產品。
(二)“無根劑”有毒有害抑或無毒無害
目前,一些行業內人士或法律專家認為,“無根劑”不屬于有毒、有害物質,經過負責風險評估部門的評估,在豆芽制發中添加使用是安全的,甚至認為,“無根劑”是無毒無害的,“毒豆芽”是樁冤案。參見呂明合:《毒豆芽冤不冤?近千芽農為之獲刑,是否有毒違法依舊存疑》,載《南方周末》2014年11月6日;前引⑦云無心文;前引③。一些專家還認為,“無根劑”按急性毒性分級屬無毒,未發現致癌、致畸、致突變的可靠證據,不會對人造成“催熟”效果。至于媒體報道說添加了“無根劑”的豆芽會致癌、致畸、致兒童早熟,他們認為,這是謠言。參見黃芳:《香港認定 “毒豆芽”不影響健康,“五毒俱全說”上了謠言榜》,資料來源于澎湃網: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4384,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1月15日。
“無根劑”真的無毒無害嗎?前述人士認為“無根劑”無毒無害的重要依據是三份風險評估報告。這三份風險評估報告的全文,我們無法從網上或圖書館找到,但是,從有關人士論述的材料看,其得出“無根劑”無毒無害的結論是有重大疑問的。
2013年9月12日,農業部農產品質量安全風險評估實驗室(杭州)發布了《豆芽中6-芐基腺嘌呤殘留的膳食風險評估報告》,該報告以豆芽中6-芐基腺嘌呤殘留量為依據,對消費者食用添加有6-芐基腺嘌呤的豆芽的膳食風險進行了評估,其結論是:“即使按照最大風險原則進行評估,各類人群的6-芐基腺嘌呤攝入量也遠低于每日允許攝入量,風險完全可以接受。”周浩:《豆芽中添加6-芐基腺嘌呤的行為定性》,載《中國檢察官》2015年第2期,第42—43頁。2013年9月13日,浙江省農業科學院農產品質量標準研究所發布了《關于豆芽中6-芐基腺嘌呤殘留對消費者健康影響的評估意見》,該報告以個例為研究對象,認為“6-芐基腺嘌呤在豆芽生產中的規范使用,是安全的”。前引③;前引B12。中國農業大學研究課題《關于6-芐基腺嘌呤和赤霉酸在豆芽工廠化生產中使用后殘留量變化及其膳食風險評估》的研究成果顯示:芐氨基嘌呤(即6-芐基腺嘌呤)在黃豆芽上按照低濃度施用2次,3天后其殘留最高值為014mg/kg,在綠豆芽上的殘留試驗最高值為013mg/kg,而6-芐基腺嘌呤的ADI值為005mg/(kgbwd) (ADI是FAO/WHO農藥殘留聯合專家委員會確定的每日允許攝入量,該單位表示每kg人體每天允許攝入多少mg )。其結論是:“豆芽中芐氨基嘌呤,其慢性風險商(RQC)低于01%,急性風險商(RQa)低于7%,表明膳食攝入風險是很低的”(注:風險商>100%,表示有不可接受的風險,風險商越小越安全)。前引③;前引B12。這三份風險評估報告均以豆芽中6-芐基腺嘌呤殘留量為依據,說明在豆芽制發中添加低濃度或合理濃度6-芐基腺嘌呤時,這些豆芽是安全的,即這些豆芽不是有毒、有害的。這三份風險評估報告是以現有一些機構確定的6-芐基腺嘌呤殘留限量標準為依據而得出的結論,其實驗方式、方法、過程等問題在此不予評論。但是,這三份風險評估報告并不能得出6-芐基腺嘌呤和其它“無根劑”物質屬于無毒無害物質的結論。
“無根劑是否是有毒有害物質”與“添加無根劑的豆芽是否是有毒有害物質”是兩個不同的問題。由于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為犯和行政犯,因此,只要在生產加工食品中違反行政法規范(如《食品安全法》《農藥管理條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加入有毒有害物質,就可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即使最終鑒定整個或整批食品的量化指標未達到有毒有害程度。例如,白酒廠商在白酒裝瓶前,在酒缸里加入少量劇毒殺蟲劑敵敵畏,即便最終檢測不出敵敵畏物質的量,也應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關于犯罪的本質,刑法學界有“法益侵害說”和“規范違反說”之爭。一般地,行為無價值論贊同“規范違反說”,結果無價值論贊同“法益侵害說”。在風險社會里,筆者支持行為無價值論,所以,筆者得出這一結論。)其實,根據《刑法》第144條的規定,該罪最準確的罪名應是“生產、銷售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物質罪”。因此,對于“問題豆芽”案,我們應關注的焦點是“無根劑是否是有毒有害物質”,而不是“添加無根劑的豆芽是否是有毒有害物質”。由于前面已論證豆芽制發是初級農產品的加工過程,而不是種植過程,因此,一旦證明“無根劑”是有毒有害物質,并且國務院有關部門禁止其在食品加工中添加使用,那么,只要在豆芽食品加工過程中添加了“無根劑”,就可認定其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無根劑”中的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屬于植物生長調節劑(植物激素),“無根劑”是人們根據植物激素結構,利用一定的方法生產出來的類似植物激素活性的化學物質。植物生長調節劑并非無毒無害物質,它是低毒農藥,這是農業和林業的行業內常識。國內外研究表明,盲目、超量使用植物生長調節劑,可能引起人畜的急慢性中毒,導致疾病發生,甚至影響下一代健康。曹洪恩、夏慧、楊益眾:《植物生長調節劑的毒理學研究進展》,載《毒理學雜志》2011年第5期,第383頁。
研究表明,6-芐基腺嘌呤的急性毒性和刺激性較高,人體攝入過多能刺激皮膚黏膜,并出現食道和胃黏膜損傷、惡心、嘔吐等現象。前引B15,第384頁。Doleala通過研究細胞分裂素6-BA(6-芐基腺嘌呤)及其衍生物的生物活性,發現它的一些衍生物通過抑制細胞周期蛋白依賴性激酶(CDK)的活性而對動物細胞產生毒性。前引B15,第384頁;Doleala K, Popa I, Krytof V,et al.,Preparation and Biological Activity of 6-benzylamino- purine Derivatives in Plant and Human Cancer Cells,Bioorganic&Medicinal Chemistry,2006,14 (3),pp875—884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關于化學品急性毒性分級標準,6-芐基腺嘌呤應歸在“有害(harmful)”這一檔(200-2000mg/kg)。沈建華:《為豆芽靈“正名”,有必要嗎?》,載《文匯報》2015年1月9日第5版。有學者對25種常用植物生長調節劑的毒性和半衰期進行了比較研究,其結論是:6-芐基腺嘌呤(別名芐氨基嘌呤)為低毒。鄭先福、文雨婷、鄭昊、萬翠: 《植物生長調節劑使用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和解決方法》,載《現代農藥》2014年第5期,第17頁。
4-氯苯氧乙酸鈉(別名:對氯苯氧乙酸鈉)為苯氧乙酸類化合物,是一種植物生長調節劑。其急性毒性實驗表明,小鼠經口半數致死量為794 mg/kg,屬于低毒物質。4-氯苯氧乙酸鈉酸化后生成4-氯苯氧乙酸(又名對氯苯氧乙酸),國內商品名為防落素、番茄靈,是植物生長調節劑。防落素的雄性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為850 mg/kg,比殺蟲劑乙酰甲胺磷(雄性大白鼠急性口服LD50為900 mg/kg)的急性毒性還要高。前引①;前引B19;前引B15,第384頁。
赤霉素被認為是最安全的植物生長調節劑之一。赤霉素最初的急性、亞急性毒理學研究顯示屬微毒甚至無毒,但近年來對其進行慢性毒性毒理學的研究發現其存在一些明顯的慢性毒性。Celik等研究發現,赤霉素能改變大鼠不同組織中的抗氧化能力,使組織中的脂質更加容易氧化。氧化應激是指體內氧化與抗氧化作用失衡,并被認為是導致衰老和疾病的一個重要因素。前引B15,第384頁;Celik I, Turker M,Tuluce Y,Abcisic Acid and Gibberellic Acid Cause increased Lipid Peroxidation and Fluctuated Antioxidant Defense Systems of Various Tissues in Rats,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07,148 (2),pp623—629慢性炎癥具有促使氧化應激和癌癥的作用, Erin等發現赤霉素能引起皮膚和膀胱的慢性炎癥,并提出要對赤霉素進行明確的監控。赤霉素還能引發雌性大鼠及其子代肝臟組織的病變和肝臟毒性。前引B15,第384頁;Erin N,Afacan B,Ersoy Y, et al ,Gibberellic Acid, a P1ant Groth Regulators, Increases Mast Cell Recruitment and Alters Substance Levels,Toxicology,2008,254 (2),pp75—81; Troudi A,SameL AM,Zeghal N,Hepatotoxicity induced by Gibberellic Acid in Adult Rats and Their Progeny,Experimental and Oxicologic Pathology,2009,48(2),pp1—6此外,有關研究成果表明:赤霉素濃度0 0625 g /kg 增加了動物的生長速度,增加了甲狀腺、卵巢和腎上腺及血鈣水平。結果發現:赤霉素染毒組仔鼠耳闊分離、牙齒萌出、長毛、開眼時間及陰道開口和睪丸下降時間均明顯縮短,仔鼠的體重、體長、尾長與對照組動物相應指標比較明顯增加,說明赤霉素具有促進仔鼠出生后生長發育作用。鄭寶珠等: 《環境中的植物激素與人體健康》,載《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07年第4期,第252頁。
綜上所述,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是低毒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在日常生活中,對于這幾種低毒農藥,我們是絕對不能將它們倒入開水后立即飲用的,也不能將其倒入橙汁中直接飲用。若人體過量攝入這三種低毒農藥,健康將受到損害,其潛在的各種危險有多大尚需進一步研究。所謂“有毒、有害”,是指經過毒理學實驗研究證明確實對人體有毒、有害,同時,也包括通過對動物實驗預知,其對人體潛在的可能危害。
可見,“無根劑”主要成分是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其屬于有毒、有害物質,是有科學依據的。從前述材料看,人體長期過量攝入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確實有致使兒童早熟、生育障礙、過早衰老、致癌以及致使其他疾病發生的潛在可能。以前媒體報道“無根劑”可能產生的各種危害并非危言聳聽,更不是什么赤裸裸的謠言。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曾被衛生部批準為食品生產中使用的加工助劑,豆芽生產可以添加使用。但是,2011年9月30日,原衛生部在《關于〈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GB2760-2011)有關問題的復函》(衛辦監督函〔2011〕919號)中明確對39個原標準[《食品添加劑使用標準》(GB2760-2011)]允許使用的食品添加劑品種進行了調整,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被刪除,不得作為食品用加工助劑生產經營和使用。據此,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頒布了《關于食品添加劑對羥基苯甲酸丙酯等33種產品監管工作的公告》(2011年第156號公告),禁止食品添加劑生產企業生產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33種產品,企業已生產的上述產品禁止作為食品添加劑出廠銷售,食品生產企業禁止使用這些產品,撤回并注銷已批準的上述食品添加劑生產企業的生產許可證書。原衛生部復函中提到,刪除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23種產品的理由是:“缺乏食品添加劑工藝必要性”。一些主張為“問題豆芽”案平反的人士就認為,這一復函說明衛生部認為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既無毒也無害,也不存在“安全性風險”,只是無“食品添加劑工藝必要性”。前引⑩呂明合文;Cssysrz:《豆芽使用6-芐基腺嘌呤和赤霉酸犯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嗎?》,資料來源于百度貼吧:http://tiebabaiducom/p/2704629992,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4月25日。
筆者認為,原衛生部以“缺乏食品添加劑工藝必要性”為由,將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23種物質從允許使用名單中刪除,并不當然得出這23種物質是無毒無害物質的結論。通過查閱這23種物質資料可知,它們大多數是化學產品,個別是金屬物質。這些物質曾可作為消毒劑、防腐劑、增塑劑、保鮮劑等,從毒理學實驗看,其中許多物質被證明是有毒性的,或有害的,這些物質若不限量攝入將會損害人體。但是,原衛生部當時尚無法對這23種物質一一進行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因此,其刪除這23種添加劑的實質原因是擔心這些物質添加到食品加工中存在風險。因為沒有進行風險評估的數據,若以安全為由刪除這23種物質是不合適的,所以以“缺乏食品添加劑工藝必要性”為由是一個兜底的理由。甲醛也是這23種物質中的一種,它也是以“缺乏食品添加劑工藝必要性”為由而被刪除的。它可作農藥和防腐劑, 毒理學實驗證明,其急性毒性:LD50:800mg/kg(大鼠經口),人經口吸入10—20ml可致死,經實驗,這種物質可致多種疾病,可致癌,對生育有影響。參見“甲醛”的詞條,資料來源于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jxgTucEQ3RN26oK9xHAhyd8PrUakduMo6Ye AmAvpavkfp63bnQ1VGwWGBwURAluDnLja8-sR8iu3VYc5EvqZq。對于甲醛,難道能說其無毒無害嗎?
從前文論證資料看,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實屬低毒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使用不當很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由于添加了這兩種植物類激素后豆芽在3—5天即可長成,而豆芽是無法貯存的,這導致使用這一植物激素類農藥無安全間隔期,此外,目前我國對豆芽添加農藥后的安全檢測技術仍存在各種難題,允許在豆芽加工中添加植物激素類農藥,其安全性堪憂。
2015年4月13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農業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頒布了《關于豆芽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6-芐基腺嘌呤等物質的公告(2015年第11號)》,該公告明確規定:“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等物質作為低毒農藥登記管理并限定了使用范圍,豆芽生產不在可使用范圍之列,且目前豆芽生產過程中使用上述物質的安全性尚無結論。為確保豆芽食用安全,現重申:生產者不得在豆芽生產過程中使用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等物質,豆芽經營者不得經營含有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等物質的豆芽。……”這一公告進一步明確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等物質是在豆芽生產上禁止使用的低毒農藥,而低毒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
(三)如何看待一些國家或地區食品中農藥殘留限量標準或免訂殘留限量
反對對“問題豆芽”案定罪的人士認為,6-芐基腺嘌呤(6-BA)、4-氯苯氧乙酸鈉(4-CPA)和赤霉素(GA)是世界許多地區允許在生產農產品過程中使用的農藥,他們還制定了農藥殘留限量或免訂殘留限量,前引⑩呂明合文;前引B12。這說明在生產農產品中使用這些農藥(植物激素)是安全的,這些農藥是無毒無害的。
筆者認為,這幾種激素農藥是低毒農藥,其屬性是有毒有害的物質,這是常識。世界許多國家或地區對這幾種農藥允許在農產品中使用并制定殘留限量或免訂殘留限量的做法,并不能得出這幾種農藥是無毒無害物質的結論。根據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制定的農藥最大殘留量標準,在普通農產品正常種植過程中,如果科學合理運用這幾種農藥,在種植果樹和種植黃豆等生長期較長的植物時,免訂這幾種農藥殘留量或限制殘留量,這可能是安全的,但是,豆芽制發是一種特殊的初級農產品加工過程,使用這種激素農藥后制發時間非常短,豆芽又不宜貯存,其沒有農藥降解的安全間隔期,豆類在這幾種激素類農藥泡發中的發芽過程是一種異常復雜的生物、化學反應過程,其生成的各種物質是否有毒有害,對人體健康有多大風險,尚有待實驗驗證。這幾種激素農藥的過量使用極有可能危害人體健康,因此,在尚未獲得科學確鑿的、經反復實驗確證的安全數據前,我國不應允許在豆芽的加工制作中添加這幾種激素類農藥。
一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具有高水平的檢測工具和檢測方法,且能在各市場廣泛地隨意檢測上市的各農產品的農藥殘留量,因此,允許個別激素類農藥用于豆芽生產中并規定殘留限量,但是,我國臺灣地區禁止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用于豆芽生產,甚至禁止4-氯苯氧乙酸鈉用于農產品生產。鐘凱:《 “毒”豆芽到底毒不毒?》,資料來源于中國食品安全法治網: http://wwwfoodlawcn/lawhtml/spaqfxjl/rdjj/7100s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4月25日。上述情況說明,發達國家或地區對這幾種激素農藥的安全性是有爭議的。
我們不能因為某些發達國家或地區允許個別激素類農藥用于豆芽生產而盲目效仿。發達國家在食品或藥品生產上也發生過因生產、實驗和管理不當而造成的危害公共人群安全的悲劇。例如,德國的科學技術發達,其藥品和食品生產、實驗和管理嚴格。但是,德國20世紀70年代發生了“擦里刀米德案”。在那一時期,許多婦女在懷孕期間服用了“擦里刀米德”品牌的安眠藥,生下了畸形的嬰兒。而這一安眠藥品已經德國嚴格的審查程序才用于臨床使用,但其仍可能出現藥品的安全隱患。參見謝治東:《“疫學因果關系”與我國刑法理論的借鑒》,載《湖北社會科學》2005年第9期,第118—120頁。這一案件說明發達國家或地區在藥品食品生產、實驗和管理上也會有漏洞。因此,豆芽制發中添加植物激素類農藥可能會帶來哪些危害,這依然是值得研究的,我國應有自己的實驗數據。 長期以來,人們對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的毒理研究還很不夠,尤其不重視其慢性毒性研究。我們必須加強對這幾種激素農藥的急性毒理研究,也要加強研究這幾種激素農藥對生殖、生長發育、遺傳、基因、致癌性及其他潛在人體危害等方面的毒理性研究。我們應對這幾種激素農藥適用于豆芽制發中的各種食品安全問題(包括對其衍生物、殘留量等)進行研究,在無科學的、穩定的、可信的結論情況下,堅決不能將其添加到豆芽制發過程中。
(四)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是否正確
全國審理的“問題豆芽” 案件中,大多數是添加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這兩種物質的案件,對行為人主要是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難道如此多的法官高度一致地犯了同樣的定罪錯誤?
如前文所述,我國《刑法》第144條規定:“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即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從這一規定可知,該罪是行為犯。由于生產和銷售食品是受我國行政機關管理的,我國制定了許多行政法律法規和法令來調整生產和銷售食品行為,《刑法》第144條規定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的行為形態,我國行政法也是禁止的。因此,該罪也屬于行政犯(法定犯)。同時,從《刑法》第144條規定也可看出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構成:(1)本罪的客體是國家對食品衛生的管理秩序和人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2)本罪的客觀要件表現為,違反國家食品衛生法律法規和法令,在生產、銷售的食品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為,或者銷售明知摻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為。(3)本罪的主體為一般主體。(4)本罪的主觀要件表現為故意。參見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279—282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12號)第20條規定,對于法律、法規禁止在食品生產經營活動中添加、使用的物質,國務院有關部門公布的《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名單》《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質名單》上的物質,國務院有關部門公告禁止使用的農藥、獸藥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質,應當認定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據此,只要在生產、銷售食品中添加上述法律、法規和法令禁止的物質,就可構成該罪,即便若干年后證明行為人添加上述禁止的物質為無毒無害物質,根據行為無價值論的觀點,該行為也違反了刑法規范,符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構成。這一規定說明最高司法機關明確了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為行政犯。因此,筆者認為,對于豆芽制發中添加“無根劑”的“問題豆芽”案件,人民法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是符合刑法規定的。
在“問題豆芽”案中,“無根劑”中的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屬于低毒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如果這些物質在食品加工中添加使用,其屬性可歸為非法添加的化學物質。由于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關于食品添加劑對羥基苯甲酸丙酯等33種產品監管工作的公告》明確禁止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這兩種農藥作為食品添加劑生產和使用,因此,這兩種物質屬于《關于辦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0條第3項規定的“國務院有關部門公告禁止使用的有毒有害物質(農藥)”。可見,這兩種激素類農藥在食品加工中均屬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前文筆者已論證豆芽制發過程不是種植過程,而是初級農產品加工過程,因此,在豆芽制發過程中添加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的行為,就是在生產食品過程中摻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行為,違反了《食品安全法》第3、28、45和46條的規定,破壞了國家對食品衛生的管理秩序,威脅了廣大消費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符合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構成,應以該罪論處。因此,在辦理“問題豆芽”案時,只要檢測出豆芽中有這兩種物質,即使沒有檢測其殘留量的具體數值,也可定罪。
主張為“問題豆芽”案平反的人士的基本思路是:豆芽是農產品,豆芽制發過程是種植過程,而不是初級農產品加工過程。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是農藥,但不是禁用農藥,添加了這兩種物質的豆芽是無毒無害的,因此,對添加“無根劑”豆芽的案件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是錯誤的。
筆者認為,即使將豆芽看成是農產品、將豆芽制發過程看成是種植過程,在豆芽生產中添加“無根劑”的行為也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解釋》第9條規定,在食用農產品種植、養殖、銷售、運輸、貯存等過程中,使用禁用農藥、獸藥等禁用物質或者其他有毒、有害物質的,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處罰。據此,判斷行為人在豆芽生產中添加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的行為是否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前提是: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是禁止使用的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
對此,國務院2001年修訂頒布的《農藥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生產、經營、進口或者使用未取得農藥登記證或者農藥臨時登記證的農藥”。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第25條規定:禁止在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使用國家明令禁止使用的農業投入品(包括農藥和化肥等)。由此可見,國家已明令禁止使用未取得農藥登記證或者農藥臨時登記證的農藥。而農業部在《關于豆芽制發有關問題的函》中明確指出:“關于豆芽制發中農藥登記問題。目前尚無農藥產品在豆芽上登記使用,我部不受理植物生長調節劑在豆芽制發中登記。”也就是說,至今還沒有任何一種農藥在豆芽生產上獲得登記,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等植物生長調節劑(激素類農藥)同樣沒有獲得登記。那么其就屬于《農藥管理條例》第30條規定的禁止使用的農藥。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農業部、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聯合頒布的《關于豆芽生產過程中禁止使用6-芐基腺嘌呤等物質的公告》(2015年第11號)進一步明確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赤霉素等物質是在豆芽生產上禁止使用的低毒農藥。因此,若將豆芽制發過程看成是種植過程,其在豆芽生產中添加的6-芐基腺嘌呤和4-氯苯氧乙酸鈉行為,屬于添加禁用農藥的行為 ,同樣可構成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通過前述分析,在豆芽制發中添加“無根劑”的案件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是符合刑法規定的,是正確的。公安機關對有關犯罪嫌疑人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立案偵查沒有錯,檢察機關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起訴沒有錯,人民法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判刑同樣也沒有錯。掀起“問題豆芽”案翻案聲浪的行業人士和法律人士的主張不應得到支持,因“問題豆芽”案而被人民法院以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的犯罪人不能無罪釋放,更不能要求國家賠償。
三、“問題豆芽”未來法治之路
“問題豆芽”案的翻案聲浪并非無緣無故地掀起。自從國家執法部門嚴厲打擊“問題豆芽”的生產者和銷售者后,“問題豆芽”在全國各地的市場上逐漸銷聲匿跡,老百姓可以吃到安全的放心豆芽了。但是曾經的“問題豆芽”生產和銷售企業以及個人在生產豆芽時不能再添加農藥“無根劑”了,其豆芽的生產周期增加,利潤大幅度減少,為此,曾經的“問題豆芽”生產群體(尤其是大型的豆芽生產企業)反對國家執法部門在豆芽制發領域取締激素類農藥“無根劑”。有關行業協會似乎成了豆芽生產和銷售企業的“娘家”,他們搖旗助其吶喊,或上書國家領導人,或致函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或通過其他方式去渲染“無根劑”無毒無害和論證已判案件是錯誤的。目前,在網絡上或傳統媒體上為“問題豆芽”案翻案的聲音一浪高于一浪。全國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和行政執法機關面臨著巨大壓力。
當前,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食品安全標準與監測評估司正委托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下屬的委員會制定《食品安全國家標準(豆芽)(草案)》,并向社會征求意見,該標準(草案)將6-芐基腺嘌呤、赤霉素、4-氯苯氧乙酸鈉和乙烯利定性為植物生長調節劑(即植物激素類農藥),允許在豆芽生產中使用,并制定了殘留標準。然而,該標準(草案)所委托的制定主體是中國食品工業協會豆制品委員會,前引③。而該豆制品委員會的負責人與各種豆芽生產企業關系密切。近一段時間,該豆制品委員會的秘書長正在為豆芽制發中使用的激素類農藥“無根劑”正名而奔走,她向國務院上書,或向最高人民法院致函,極力為“問題豆芽”案鳴冤。為了給“無根劑”去污名,該機構的其他人員也正在利用各種方式進行一系列密集攻關活動。由此判定,制定該標準(草案)的起草單位已失去了公正人的資格,其制定的豆芽標準的科學性豈不大打折扣?
而“無根劑”等激素類農藥是有毒有害物質。在豆芽制發中添加激素類農藥后,豆芽中會產生多少對人體有害的衍生物尚需研究,在我國現在的科技發展水平下,農藥檢驗設備、檢測方法及全面推廣能力均有限。在國人守法意識不強的法治環境下,若立法上允許在豆芽制發中添加激素類農藥,豆芽生產者必將大行其是,從而使“問題豆芽”更多更廣,甚至泛濫成災。筆者認為,制定豆芽的安全標準應以保障公民身體健康為根本宗旨,決不能以豆芽生產者利益至上為指導思想!豆芽制發過程中根本沒有必要添加“無根劑”,其并未增加任何營養成分,徒增人們的不安全感。有的生產者無度使用“無根劑”,添加“無根劑”豆芽4個小時就可長5厘米。韋輝:《“毒豆芽”4小時長5公分 商販稱不攙毒賣不動》,資料來源于大眾網(濟南):http://sddzwwwcom/sdnews/201407/t20140722_10698758htm, 最后訪問時間: 2015年4月20日。“問題豆芽”生產者知道其豆芽是添加了“無根劑”的產品,因顧忌豆芽的毒副作用,他們往往從不吃自己生產的豆芽。馬超:《白凈豆芽竟是農藥浸泡60萬斤毒豆芽流向餐桌》,資料來源于鳳凰網財經:http://financeifengcom/a/20130806/10359805_0shtml,最后訪問時間: 2015年4月20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國社會生活的基本道德準則,正在為“無根劑”正名和正在為“問題豆芽”案翻案的各行業人士和法律專家,又作何考慮?
豆芽是廣大老百姓餐桌上常見的食品。為了人民的健康,在未來,我國應在立法上完善各種法律規范讓豆芽的生產、銷售、管理更加科學,同時,應依法嚴厲打擊“問題豆芽”的生產、銷售活動。豆芽制發的目的是為了獲取豆芽,其制發的時間較短,以泡發方式制作,它無疑是一種特殊的食品加工過程,因此,立法上應進一步明確其食品加工的性質,并應嚴格按食品加工來管理。我們不能將豆芽制發作為種植來看待,更不能像種植水果和普通疏菜一樣,來管理豆芽制發,否則,許多“問題豆芽”案件將難以嚴厲懲處,從而導致各種各樣的激素類農藥和殺蟲劑以及各種各樣抗生素、避孕藥等藥物在豆芽制發中被廣泛添加。我國臺灣地區禁止6-芐基腺嘌呤、4-氯苯氧乙酸鈉和赤霉素用于豆芽生產,甚至禁止4-氯苯氧乙酸鈉用于農產品生產。前引B27。在這一問題上,為我們作出了好榜樣。國家司法機關具有獨立的職責,在辦案中應忠于法律,堅持司法獨立,摒棄各種外界不良干擾。當前,我國正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各級領導干部應成為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模范,為各地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創造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可以說,“問題豆芽”案是一塊檢驗“全面依法治國”能否實現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