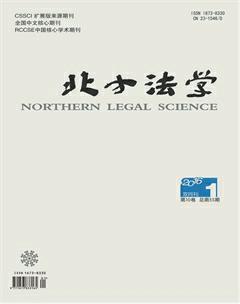后果主義論辯的證成與具體適用
張順

摘要:后果主義論辯是法律論證的一種重要的形式,其存在的目的就是從后果論的角度為規(guī)范適用提供“二次證明”。盡管后果主義論辯受到諸多批判,如以損害形式邏輯為代價、引入法官動機破壞法律的確定性、以法律工具主義作為價值預設等,但是后果主義論辯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其作為重要的論證方法,是法官思維的組成部分,也是協(xié)調規(guī)則安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矛盾、解決權利相對性困境的重要方法。基于不同類型的后果,可以將后果主義論辯區(qū)分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這四種類型的后果主義論辯都有獨特的適用領域和適用限制。在個案裁判中,后果主義論辯以“顯性”和“隱性”的方式存在,作為一種輔助性依據(jù),它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將法律問題還原為事實問題。然而,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法官的價值偏好,后果主義論辯在適用時需要就個案事實與邏輯后果的相關性進行論證,必要時輔之以其他的論證形式,并對適用的推理過程展開細致的說理。
關鍵詞:后果論后果主義論辯輔助性依據(jù)相關性形式法治
中圖分類號:DF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330(2016)01-0133-15
引言
司法裁判的合法性、合理性與可接受性是判斷司法裁判優(yōu)劣的重要標準,也是法律論證理論得以建構的理論預設。無論在實踐中遇到怎樣的案件——簡易抑或疑難,法官都有義務跨越規(guī)范與事實的縫隙,為司法裁判提供充分而細致的論證。“人們想知道,某個坐在裁判席上或帶有徽章的人憑借什么權利去行使剝奪他人生命、自由或財產的國家權力……在施行法治時,法律推理應該揭示法律和特定行為之間的聯(lián)系”。 ①質言之,法律論證的目的不是單純地展現(xiàn)法律人的推理技術,而是向社會大眾闡明判決得以產生的脈絡,并最終回歸“法律是什么”這一基本的法哲學問題,即法律體系的構成要素。探討法律體系的構成理論不僅僅是一個知識學的問題,也是一個受法官的實踐理性所支配的經(jīng)驗命題。
法律人在為個案判決提供論證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前理解、直覺、經(jīng)驗以及理性的影響。在面對具體的個案時,法官一般借由“潛意識、直覺和經(jīng)驗得出一個初步法律結論”,②然后再根據(jù)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檢驗這一初步法律結論,在必要時不斷修正法律結論,循環(huán)往復之后才能最終實現(xiàn)應然與實然之間的等置。毋庸置疑,為判決提供充分的理由是法律論證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裁判的理由可能源于明確、具體的規(guī)則體系,也可能受制于包容性強但過于抽象的法律原則,抑或是法學家學說、習慣等次要的法律淵源。然而,這些裁判理由在為判決提供支撐的同時,自身的缺陷也暴露無遺:剛性的規(guī)則體系容易陷入僵化、原則需要權衡才能具體化、法學家學說也是流派紛呈等。因此,裁判理由在適用時又需要獲得“二次證明”,即為裁判依據(jù)本身提供正當性論證。在這些正當性論證中,后果主義論辯就是一種重要的論證工具。
顧名思義,后果主義論辯就是從后果論的角度為規(guī)范適用提供“二次證明”。“大致說,后果論是這樣一種理論:一種特定的選擇是不是一個行動者已經(jīng)做出的正確選擇,這要看這種決策的相關后果,要看這種決策對世界的相關影響”。[印]阿馬蒂亞·森:《后果評價與實踐理性》,應奇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頁。 而“后果是事務的一種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來自我們關注的所有影響決策的因素,例如行為、規(guī)則或傾向。……對于事務狀態(tài)的基本認識卻可以包含豐富的信息,并注意到我們認為重要的所有特征”。[印]阿馬蒂亞·森:《正義的理念》,王磊等譯,劉民權校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01頁。 作為一種論證方式的后果論,就是將任何行動者的決策所產生的對行為、規(guī)則或傾向等因素的影響展現(xiàn)出來,從而更為深刻地認知決策所產生的“事務狀態(tài)”。對于法律論證來說,后果主義論辯就是在個案裁判中考量規(guī)則、原則等適用時所帶來的后果,并通過對這些后果的衡量,證成或者證偽個案裁判。這種看似“本末倒置”的思維模式,受到來自義務論和反工具論者的批判。誠然,后果主義論辯的適用的確受制于人的有限理性、個人價值偏好等因素,但是這并不表明后果主義論辯沒有展現(xiàn)自身價值的空間。基于后果主義論辯所面臨的批評意見,本文首先從方法論、法官思維、法律品性等四個維度為后果主義論辯提供正當性論證;同時,基于后果的不同類型,將后果主義論辯細分為制度型、目的型、道德型和政策型等四種類型,并結合具體實踐中的個案,具體分析這些類型的后果主義論辯所存在的優(yōu)勢、劣勢以及相應的適用限制;最后將探討后果主義論辯的法律地位以及適用時所應當注意的事項。
一、后果主義論辯的批判及其辯護
現(xiàn)有批判后果主義論辯的理論主要可以區(qū)分為兩種進路:一是義務論(deontology),二是工具化。前者認為判定一個行為(對于案件來說就是被訴法律行為)的正當性的依據(jù)是行為本身的性質或者特征,即使某類行為是否最大限度地促進了善;而后者認為由于后果主義沉迷于計算與衡量行為的善與惡,進而受制于此,使得人類退變?yōu)樽非笊频墓ぞ摺⒁?Judith Lichtenberg, The Right, The All Right, And The Good,Yale Law Journal, 1983, pp545—547 具體而言,可以區(qū)分為下述四種情形予以討論。
(一)后果主義損害形式邏輯
對于推崇形式邏輯的學者來說,后果主義論辯破壞了“法官僅服從于法律”的司法準則,將除法律規(guī)則和個案事實之外的其他不可控甚至非理性的因素引入形式主義法律推理過程,進而破壞了規(guī)則的確定性和裁判結果的可預見性。“規(guī)則是盲目的,不受個人情感的影響;它們能夠促進平等待遇,減少偏見和武斷的可能性。規(guī)則總是和公正聯(lián)系在一起的,它們的公正性體現(xiàn)在自由女神的公正是盲目的這種思想中。規(guī)則對案件的許多本來可能起到相關作業(yè)的特征、也對在某些社會情境中——宗教、社會階層、相貌、身高等——的相關特征一視同仁,還對人們很難就其關聯(lián)性達成一致的事情一視同仁”。[美]凱斯·R.孫斯坦:《法律推理與政治沖突》,金朝武等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4—135頁。 換言之,形式主義法律推理將裁判的正當性僅僅與法律規(guī)則相關聯(lián),而經(jīng)由規(guī)則所邏輯推導出來的結果也就保證了裁判結論的權威性,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實現(xiàn)了“同案同判”。一旦判決逾越現(xiàn)有的法律體系,并運用“強意義的裁量”(德沃金所反對),法律外的理由被納入裁判之中,法律體系的剛性穩(wěn)定就會被侵蝕。
后果論者意識到形式邏輯建立在一個錯誤的假定之上,即將法律視為自給自足的體系,且能自我證立。形式邏輯固然具有其獨特的優(yōu)勢,但其權威的樹立并不以排斥其他合理的論證形式為依托,反而正是由于其他論證形式的引入,使得形式邏輯的地位得以鞏固。以阿列克西所推崇的“外部證成”與“內部證成”理論為例,“外部證成的對象是對在內部證成所使用的各個前提的證立”;而這些前提大致包括實在法規(guī)則、經(jīng)驗命題,以及既非經(jīng)驗命題、亦非實在法規(guī)則的前提。參見[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舒國瀅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85頁。 同理,結果主義論辯適用的目的并不在于消解形式邏輯的權威地位,“后果主義論辯就是法官在現(xiàn)行法律體系的支持下,全面考慮各種裁決可能產生的不同影響,從諸多相互競爭的具體利益中作出選擇,通過審慎評估所有規(guī)范性行為模式的現(xiàn)實意義,發(fā)現(xiàn)最令人滿意的裁判規(guī)范,從而得出最合乎情理的判決結果”。曹晟旻:《社會學解釋方法論的運作過程》,載《廣西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2年第1期。 經(jīng)由后果主義論辯檢驗所形成的裁判規(guī)范,由于既契合了法律體系的內在精神,同時又能符合法律發(fā)展的內在邏輯,因而可以作為演繹推理的大前提,直接適用于待決個案,從而產生最令人滿意的法律結果。
(二)后果主義引入法官動機,導致裁判結果的不確定性
波斯納認為,類似案件的前后處理出現(xiàn)不一致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因為“塑造法官前理解并因此塑造他對論證和證據(jù)之回應的個人背景、氣質、訓練、經(jīng)驗和意識形態(tài)不同。不同法官對后果權衡也會不同”,而且因為“基于同樣的上述理由,不同法官看到的后果也不同”。[美]理查德·波斯納:《法官如何思考》,蘇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26頁。 換言之,后果權衡及其結果由于受到法官的背景、氣質、訓練、經(jīng)驗等方面因素的影響,即在客觀的規(guī)范體系之外,引入了不受控制的、主觀的法官的個人動機,因而損害裁判結果的確定性,進而對規(guī)范體系的確定性和明確性造成一定的沖擊。
基于法官的內在動機而批判后果主義論辯的學者其實秉持了一種極端理性主義的立場,其主觀預設了兩個前提條件:一是法官是理性的動物,只受理性法律思維的支配;二是通過解釋和推理可以建立客觀、有效的法律體系。問題的癥結在于,即使法官受到背景、氣質、訓練等因素的影響,是否意味著法官就不受理性思維的支配?是否意味著個案裁判必然不正義?臺灣地區(qū)學者黃舒芃認為,“在落實法官受法律拘束要求的過程當中,法官的主觀意志如何,或者用何種方式影響了裁判結果,其實都不是應該或者必須被追究的對象。重要在裁判論證中,法官能證明其判決結果擁有法律上的根據(jù),能夠成為這個抽象規(guī)范所容許的具體選項之一,此時的司法便已能通過法律拘束的檢驗,亦即被認為是一次遵守法律框限的權力發(fā)動”。黃舒芃:《變遷社會中的法學方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6頁。 直白地說,即使法官受到所謂非理性的影響,也要受到現(xiàn)有法律體系的約束,即法官需要將其個人偏好轉化為法律上的根據(jù),然后才能根據(jù)法律上的理由作出裁判。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波斯納認為,德沃金提出的“建構性解釋”理論的正確之處在于,其意識到如果把道德和政治價值帶入決策之時,法官仍然具有守法的動機。參見[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理學問題》,蘇力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0頁。
(三)后果主義與功利主義系“一丘之貉”
后果主義論辯之所以受到批判,在很大程度上與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相關。由于后果主義論辯在適用時需要對相關后果進行權衡,權衡又必須基于一定的標準或方法,因而功利原則被視為后果主義論辯得以適用的基本前提和理論預設。正因如此,功利原則所受到的批判自然也就成為后果主義論辯無法逃脫的桎梏。若要消解這一桎梏,就需要回歸到有關功利原則的討論上來。所謂功利原則,即對于共同體(政府)的每一項措施或者行動而言,如果其“增大共同體幸福的傾向大于它減少這一幸福的傾向”,這項措施就是符合功利原則的。參見[英]邊沁:《道德與立法原理導論》,時殷弘譯,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57—59頁。 也就是說,如果一項措施或者行動所引發(fā)的后果,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個體的快樂或者減少個體的痛苦,那么其就符合“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這一功利原則。將這一理論運用于后果論,則意味著要在尊重比例原則的基礎之上,最大限度地增加與案件相關的有利后果、減少有害后果,從而優(yōu)化個案裁判所帶來的收益。
通說認為,功利主義一般存在兩個“致命的”缺陷:一是快樂和痛苦主要體現(xiàn)為一種主觀感受,無法有效衡量一項制度或者行為所引起的快樂和痛苦的總量,即無法實現(xiàn)帕累托最優(yōu)。二是少數(shù)人成為“最大多數(shù)人的最大幸福”的犧牲品,因為只要某項措施或某個裁判使得最大多數(shù)人的快樂得以增加,那么就可以以對少數(shù)人造成痛苦作為代價。當然,盡管功利主義存在種種缺陷,但并不是邊沁創(chuàng)立功利原則的初衷。邊沁雖然推崇功利原則,但并不主張以犧牲個人利益作為代價——“不理解什么是個人利益,談論共同體的利益便毫無意義”。前引B12,第58頁。 質言之,邊沁所推崇的功利原則并不是以犧牲個人利益為代價的,只是當功利原則被付諸實施時,制度操作所產生的消極后果遠遠超出了預期。更為重要的是,即便將少數(shù)人權利的犧牲視為適用功利原則的必然后果,也不能把后果主義論辯單純視為一種“功利主義”的論辯方式,因為沒有理由認為后果主義論辯只是在借助單一的指標進行評價。參見[英]尼爾·麥考密克:《法律推理與法律理論》,姜峰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頁。 除了功利主義,正義、社會公共價值等都是重要的指標。
(四)后果主義蘊涵著法律工具主義的預設
在反工具主義論者的視域下,后果主義還潛藏著一個巨大的風險,就是一旦將法律體系之外的因素引入個案裁判,甚至作為法官裁決的正當理由,那么除了法律體系的自治性受到?jīng)_擊外,法律自身所蘊涵的正義、公平、倫理等傳統(tǒng)觀念就有被架空的危險。在最為根本的意義上說,就是后果論將法律視為實現(xiàn)某種特定后果的工具,進而為了這些特定后果,可以置法律體系、傳統(tǒng)觀念于不顧。在反工具主義論者看來,法律工具主義的最大危害就是不斷地侵蝕法治,使得高級法理論崩潰、公共利益惡化,并對合法性構成威脅。參見 Brian Z Tamanaha, Law as a Means to an E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215—245 而在我國的語境下,法律工具主義是“刀把子”的同義語,其負面效應就是不斷侵蝕民眾對于法律的信仰,使得法律成為強者壓制弱者的工具。
事實上,將后果論視為導致法律工具主義的原因之一,使得后果論遭受了過多不合理的指責,因為真正促使法律被“工具化”的,并不是后果主義。法律的工具化是法律的神圣性被褫奪之后的必然結果,法律不再被視為上帝的理性或者自然法的體現(xiàn),而是被視為實現(xiàn)人類抑或是某個階層意志的手段或者方式。在規(guī)則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等思想潮流的沖擊下,法律工具化的趨勢在當代更是有增無減。當然,也需要承認,當對判決的任何可能后果進行評估時,似乎的確有將法律僅僅作為實現(xiàn)某種社會效果與效益的工具的傾向,以至于損害法律的權威性。當下我國司法實踐中,有的地方法院一味將地方利益、經(jīng)濟效益等“扭曲”的后果作為正當理由,進而損害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導致累訟或案件久拖不決。因此,后果主義論辯在適用時,一方面要受制于規(guī)則體系本身所提供的衡量標準,如憲法價值、法律原則等;另一方面也要排除考量與案件裁判不具有邏輯關系的后果因素。
二、后果主義論辯的理論證成
(一)后果論是一種重要的法學理論的論證方法
盡管后果論受到諸多的批判,但其作為一種重要的社會科學的論證方法的事實卻是毋庸置疑的。在傳統(tǒng)的法學理論中,我們也可以發(fā)現(xiàn)大量運用后果主義論證法律規(guī)則、政策等正當性的典型例子。例如,我國的刑法學通說一般認為,刑罰的目的具體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一是特殊預防,即根據(jù)罪犯罪行的輕重科以相應的刑事處罰,并對罪犯予以改造;二是一般預防,即防止社會成員實施犯罪行為。上述刑罰目的,無論是對犯罪分子的改造使其成為社會人,還是針對一般人的各種預防犯罪的機制,其背后的理論邏輯都是后果論,因為“它關注未來和社會的秩序,而不是罪犯或犯罪行為的邪惡或應受懲罰性”。[美]布賴恩·比克斯:《法理學:理論與語境》,邱昭繼譯,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頁。 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刑罰理論都將一般預防視為刑罰的根本目的。再如,為了批判美國各州所進行的法官的連任選舉(retention election)制度,批判者即從后果論角度提出理由支持廢除這一制度的主張,即與司法公正、獨立的法制原則相沖突,向其他法官傳遞不良信號,阻礙法官作出公正判決等。參見Todd E Pettys,Judicial Retention Elections,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Rhetorical Weaknesses of Consequentialism,60 Buff L Rev 69, pp93—99
之所以后果主義論辯在受到批判的同時,還有諸多的理論都試圖從后果論角度尋求正當性依據(jù),原因無非在于法律本身所具有的雙重屬性:一方面,相對于應然的自然法學說,法律是實現(xiàn)自然理性或人類理性的實然法;另一方面,相對于法律在社會生活中所發(fā)生的實際效果,法律則是規(guī)范“可能生活事實”的應然規(guī)范。正因為法律具有上述三個主要的面向,因而我們在為法律的正當性提供理由時,自然也會訴諸自然法、法律體系(如基礎規(guī)范)或者法律實效。那么怎么判斷法律的實踐符合理性、體系等標準的要求?其中的重要路徑就是求助于后果論。后果論為法律實踐提供了較為客觀、真實的現(xiàn)實反映,一定程度上擺脫了相對主義和懷疑論的羈絆,即不再受制于何謂正義、何謂公平的爭論,而是將規(guī)則實踐的結果還原為可以加以操作和辨識的客觀真實,并以類型化的方式得以展現(xiàn)。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后果論為法律的正當性論證提供了形式化的理由。
(二)后果主義論辯是法官思維的組成部分
在一份合格的判決書中,不能僅僅陳列事實、設定規(guī)則、給出結論,法官還必須為規(guī)則、事實與結論之間的邏輯給出適當?shù)恼撟C,這就是法官的釋明義務。法官為了闡明裁判結論背后所蘊涵的裁判理由,必須求助于各種解釋方法與論證技巧。以社會學解釋方法為例,其“偏重于社會效果的預測及其目的之考量”。楊仁壽:《法學方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頁。 對于社會學解釋方法的適用過程,梁慧星教授描述如下:“首先,假定按照第一種解釋進行判決,并預測將在社會上產生的結果,所產生的結果是好的,還是壞的。然后,再假定按照第二種解釋進行判決,并預測所產生的結果是好是壞。對兩種結果`進行對比評價,所謂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大。最后采納所預測的結果較好的那種解釋,放棄預測結果不好的那一種解釋。”梁慧星:《裁判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頁。 由此可見,社會學解釋方法在運用時,就需要權衡各種解釋方法所引起的各種后果,并根據(jù)相應的衡量標準進行判斷,最后選擇一種“利大害小”的解釋方法,從而也就發(fā)現(xiàn)了最佳的裁判規(guī)則。同理,目的解釋、合憲解釋、利益衡量等法律方法在適用時,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其中隱含后果主義論辯的影子。
法官之所以會有意無意地運用后果主義論辯處理案件,主要源于法律推理的本質不是僵化的三段論邏輯,不是“按照證成、法律尋找、解釋、規(guī)則適用、評價、闡述這樣的思維路線運行的,而可能是從結論到前提的反向運動”。張保生:《法律推理中的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載《法學研究》2006年第6期。 法官思維的特質其實是根據(jù)預設的結論,尋求相應的權威規(guī)則予以支撐,一旦出現(xiàn)規(guī)則空缺、規(guī)則悖反、規(guī)則沖突等情形時,法官就需要尋找法律體系以外的正當理由,來創(chuàng)制新的裁判規(guī)則或者消除規(guī)則與規(guī)則、規(guī)則與原則之間的沖突。法律體系外的正當理由并不是寬泛地等同于平等、公正、公平等抽象的道德原則,而是需要建立起正當理由、法律理由與個案法律事實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特別是明確所擬制的新規(guī)則對今后裁判的指引作用,以及裁判規(guī)則對社會大眾行為的指引功能。也就是說,體系外的正當理由需要內化于法律制度本身的一致性與協(xié)調性、法律制度與其他社會制度的銜接、社會大眾對規(guī)則的合理預期,而這些因素恰恰是后果主義論辯使用時要予以特別考量的。
法律實務中所發(fā)生的諸多典型個案都可以探尋到后果主義論辯的蛛絲馬跡。如在廣西“驢友”案中,裁判法官就采用了如下理由作為裁判依據(jù),即我國尚未建立戶外探險的責任機制,一旦免除行為人的責任,受害人的損失無法得到補償;同時也會造成戶外探險活動的輕率化和盲目化。參見南寧市青秀區(qū)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2006)青民一初字第1428號];陳坤:《疑難案件、司法判決與實質權衡》,載《法律科學》2012年第1期。 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第7號指導案例中,為了論證再審期間當事人達成和解協(xié)議后申請撤訴的正當性,法院將“為了尊重和保障當事人在法定范圍內對本人合法權利的自由處分權,實現(xiàn)訴訟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促進社會和諧”作為裁判理由;而在第10號指導性案例中,法院提出在審理公司決議撤銷糾紛案件中,應當將“尊重公司自治,公司內部法律關系原則上由公司自治機構調整,司法機關原則上不介入公司內部事務”作為審查的重要標準。在上述個案判決中,防止“探險活動的輕率化和盲目化”、“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等理由背后都暗含后果論邏輯;而“尊重和保障……自由處分權”、“尊重公司自治”等理由則兼有權利論和后果論的色彩。
(三)法律的品性與后果主義論辯
法律作為具有強制約束力的社會規(guī)范,必然與政治、道德、經(jīng)濟、宗教等社會因素發(fā)生關聯(lián),進而呈現(xiàn)出政治性、道德性、經(jīng)濟性等屬性,這些屬性既約束著立法行為,同時也影響著執(zhí)法行為(行政與司法)。在此以法律的政治性和經(jīng)濟性作為分析樣本。法律的政治性具有多個面向,對于后果主義論辯來說,則意味著維護分權體制,即尊重立法機關對“政治問題”的判斷、尊重立法者和執(zhí)法者自主的決策空間。協(xié)調公正與效率的沖突是法律經(jīng)濟性的內在要求,即司法在維護個案公正的同時,同樣需要兼顧實現(xiàn)公正的成本和方式,特別是實現(xiàn)公正所獲得的收益應當高于所投入的成本。例如,司法者在作出個案裁判時,應當考慮執(zhí)行個案裁判所需要的公共資源,特別是執(zhí)行刑罰所需要的公共懲罰資源,一旦公共資源的投入遠小于產出,法律的實效就會大打折扣。比如,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就出臺了整治淫穢色情手機短信的司法解釋,但是時至今日,這一司法解釋也并未發(fā)揮實質性的效力,主要原因就在于整治色情短信需投入公共資源用于監(jiān)控信息往來,但是產出卻不理想。
從立法技術上看,為了安置這些法律的品性,不得不寄望于在剛性規(guī)則(即完全法條)之外,還有意無意地通過一般條款、不確定法律概念等方式為法律的發(fā)展預留空間。這種品性促使法律形成一定意義上“封閉完美的體系”,從而可以從容應對來自實踐的挑戰(zhàn)的同時,也會使法律被架空、濫用、虛置的危險加大。因而,在遇到規(guī)則的“開放結構”時,就需要借助后果論對規(guī)則所牽涉到的實質要素進行衡量。例如,我國《刑法》中大量充斥著“數(shù)額巨大”、“數(shù)額特別巨大”、“情節(jié)特別嚴重”等語詞,在對這些標準進行具體化操作時,除了需要考量犯罪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外,還需要注意所確定的標準可能造成的后果,如對未來判決的引導意義、各地區(qū)之間的差異等。在變革現(xiàn)有規(guī)則、創(chuàng)制新規(guī)則的場合,就可以根據(jù)革新后的規(guī)則、新規(guī)則所產生的一般后果和邏輯后果檢驗新規(guī)則的正當性,如檢驗規(guī)則與其他社會制度、社會政策等之間是否存在沖突。例如,在侵權責任法領域,無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一方面壓縮了過錯責任原則的適用范圍,另一方面也對舉證責任、證明標準、保險政策等制度或政策產生了方方面面的影響。
(四)權利沖突的解決需要后果論
對于義務論的批判意見,后果主義論辯可以將權利沖突作為“擋箭牌”——即便我們將“視權利為王牌”的權利理論視為后果主義論辯中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衡量原則,即只要任何措施與權利發(fā)生沖突就應當被視為非法或者違法,權利理論還是需要面對由于權利沖突所引發(fā)的衡量問題。美國政治哲學學者索薩所設想的例子就可以用來解釋權利理論在適用中可能遇到的困境:一位父親站在碼頭上,突然發(fā)現(xiàn)兩個小孩溺水,更糟糕的是,其中一個是他的兒子;他意識到自己無法將兩個孩子都救出來。索薩同時假設兩個小孩彼此相像:他們的年齡和健康狀態(tài)相同,他們之間的關系同樣密切等。參見[美]戴維·索薩:《后果主義的后果》,解本遠譯,載徐向東編:《后果主義與義務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頁。 在此情境下,“視權利為王牌”難以發(fā)揮作用。同樣,實踐中大量的個案也可以還原為權利之間的沖突。例如,“瀘州遺贈案”可以被視為法定繼承權與遺囑繼承權之間的沖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導案例1號“上海中原物業(yè)顧問有限公司訴陶德華居間合同糾紛案”也可以理解為陶德華的合同自由權利與中原物業(yè)顧問有限公司的債權(履行)之間的沖突。
為了妥善解決權利沖突,有必要將權利規(guī)范視為一種規(guī)則與原則相結合的結構。徐繼強:《憲法權利規(guī)范的結構及其推理方式》,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4期。 即當權利規(guī)范視為規(guī)則存在時,這一規(guī)則具有強制適用性,如我國《憲法》第34條所規(guī)定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除了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外)就是一種典型的不能加以衡量的權利;而當權利規(guī)范被視為原則時,就要求審慎地運用衡量的方法,以最大程度地予以實現(xiàn),參見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lated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7 并確定今后處理這類權利沖突的相對固定的規(guī)則。在具體的衡量過程中,權利論者或者義務論者無法再次訴諸權利本身的位階,只能轉而衡量權利背后所蘊含的法益,進而基于法益的重要性與特殊性,明確如果某一權利得到優(yōu)先保護時所可能產生的收益和損失,最后在合法性原則、比例原則的約束下作出最終的裁決。因此,“權利不是反結果主義的道德論的組成部分,因為在許多情境下權利被一般政策考慮所壓倒”。前引B23。
三、后果主義論辯適用的類型學分析
具體而言,不妨基于不同類型的后果,將后果主義論辯區(qū)分為以下四種類型:
(一)制度型后果主義論辯
制度型后果主義即是將制度性因素作為衡量標準納入個案的審判過程,謀求個案裁判所產生的邏輯、一般后果可以獲得制度實踐的支持。具言之,制度性后果的衡量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是后果論將某一特定的制度性因素作為后果因素予以考量時,相類似的其他制度性因素是否同樣需要受到合理的對待,特別是根據(jù)這一制度性因素對既有的規(guī)則作出調整時,如發(fā)生在英國的British Transport Commission v Gourley案。二是法官作為被動的、中立的、客觀的職業(yè)群體,無法預知判決的結果是否為當事人、法律人共同體和社會大眾所認可,同時由于法院手中并無財政權和強制執(zhí)行權,個案判決的執(zhí)行有時還倚賴其他權力機構的配合,如布朗訴教育局案。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雷耶認為,“最高法院解釋法律時,如果能尊重憲法賦予其他機構的不同權力、職責和地位,效果可能會錦上添花”。具體而言,最高法院應當充分考慮以下要素:適用憲法的目標及后果;不同機構的職能分工及彼此關聯(lián);分工協(xié)作下蘊涵的價值觀;承認憲法局限性之必要。參見[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為民主做什么》,何帆譯,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114頁。 固然布雷耶的觀點立足于美國最高法院解釋法律的活動,但對于各級法院來說同樣具有詮釋力,因為法院審級的高低并不影響后果主義論辯的適用。
在British Transport Commission v Gourley案中,雙方爭議的焦點是Gourley所獲得的人身損害賠償是否需要繳納稅收。上議院的6位大法官認為人身損害賠償應當納稅,他們的基本理由就是各國憲法所普遍規(guī)定的公民的納稅義務。Reid法官即認為,納稅這項義務由國會的法案所確定,并適用于所有人。納稅義務是每個人無法逃避的公共性事務。如果受害人所獲得的賠償無須支付稅收部分,那么受害人無異于獲得了一份意外的收入,因為其實際的損失并沒有那么多,特別是當受害人并未完全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1956] 2 W LR 41, pp214—215 反對考量納稅因素的Keith of Avonholm法官即認為,在確定損害時,評估未來的稅收情況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稅收義務的確定具有立法性質,當法官在評估納稅因素時,便有僭越司法權力的嫌疑。[1956] 2 W LR 41, pp217—218 之后,加拿大馬尼托巴王座法院在處理同類型的Soltys v Middup Moving & Storage Ltd案時,針對Gourley案的判決意見,Nitikman法官認為,如果確立人身損害賠償需要繳納稅收這一規(guī)則,那么與人身損害賠償性質相類似的退休金、失業(yè)保險等補償是否也應當承擔納稅義務?Nitikman法官的言外之意即一旦確立人身損害賠償部分需要繳納賦稅,那么也就意味著退休金、失業(yè)保險等制度就同樣需要承擔納稅義務,否則制度之間就會出現(xiàn)失衡,從而衍生出更多的矛盾和沖突。1963 CarswellMan 64, 44 WWR 522, 41 DLR (2d) 576 從Gourley案所采用的論證邏輯可以看出,制度型后果主義論辯的優(yōu)勢在于將論證的邏輯提升到實踐理性的高度,充分重視規(guī)則背后所蘊涵的制度性因素,但是缺陷也恰恰源于此,即法官容易忽視對類似的制度性因素的考察。
(二)目標型后果主義論辯
目標型后果主義所考量的就是判決預期所產生的良好的社會效果,即是否促成良好的社會目標的實現(xiàn)。目的型后果主義所力圖促進的目標,不能簡單地等同于立法目的或者統(tǒng)治階級的目的,而是指法律體系所蘊涵的價值追求。例如,現(xiàn)代民法的核心價值已不再是純粹的保護物權,而是通過契約促進物的流動,進而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刑罰的目的也已擺脫以懲罰罪犯為目的,而是轉化為積極矯正罪犯,使其再社會化。當然,這里的價值追求不是籠統(tǒng)意義上的“平等”、“正義”等形而上的目標,這些目標往往內化于規(guī)則之中,可加以具體認知和操作(即一般對此不會產生爭議),并且事后可以通過實證科學的方式予以檢驗。
Barbara Grutter v Bollinger案涉及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所采取的一項糾偏(平權)行動——將種族因素作為一種錄取標準,傾斜保護少數(shù)族群的受教育權。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為了論證這一糾偏行為并不違背美國憲法所規(guī)定的平等保護條款,即從法律所追求的目標展開了論證:“大量的研究表明,學生主體的多元化會促進學習效果,以及‘讓學生可以更好地準備日趨多元化的工作場所和社會,更好地準備成為職業(yè)人士。……這些收益是實實在在的,而不停留于理論層面。美國的主要商業(yè)發(fā)展業(yè)已表明,在現(xiàn)如今日益全球化的市場所需要的技能,只有在多元化的民族、文化、理念與立場中才能得到發(fā)展。”539 US 306,p330 支持奧康納大法官作出這一裁決的,正是法律促進社會團結、兄弟友愛的目的。除了在糾偏行為所引發(fā)的爭議中,我們還可以在其他類型的案件中發(fā)現(xiàn)目的型后果主義的身影。例如,法院在處理涉及安樂死的爭端時,一般會認可立法或行政機關所出臺的禁止或限制安樂死的措施,因為一旦將安樂死合法化,除了被濫用的風險外,也與保護人的生命的目的存在一定的沖突。當然,社會目的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發(fā)生顯著的變化,目的型后果主義在適用時也需要作出相應的調整。
(三)道德型后果主義論辯
道德型后果主義意味著判決的正當性并非來源于制度抑或是目標,而是源于判決的證立方式,即“判決與適用于當事人行為及其行為造成的事物狀態(tài)的正義的社會道德規(guī)范相一致”。[美]羅伯特·S薩默斯:《美國實用工具主義法學》,柯華慶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頁。 換言之,道德型后果主義需要側重于考量以下后果因素:一是當法官運用現(xiàn)有的規(guī)則進行裁判時,是否與社會大眾的預期判斷產生沖突,而這些預期判斷往往源于其普通的倫理觀念或者常識。例如在瀘州遺贈案中,法官將“夫妻之間的忠誠義務”、“公序良俗”、“社會公德”、“社會秩序”等作為裁判的理由,即是將道德型后果論納入實質推理的典型表現(xiàn)。二是在法官革新規(guī)則、創(chuàng)制新規(guī)則的場合,考量新規(guī)則與社會道德規(guī)范的契合度,進而考量新規(guī)則是否可能導致“公民的不服從”。三是個案裁判對大眾行為的指引作用,即如嫖娼、通奸等行為的非罪化本身也會對公民的道德觀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影響,進而直接作用于日常的言行舉止。
與此同時,在適用道德型后果主義論辯時也應當注意,“社會道德”、“社會共同價值”極有可能成為壓制個人自由、少數(shù)人權利的理由。臺灣地區(qū)學者黃舒芃就對臺灣地區(qū)大法官解釋第617號我國臺灣地區(qū)“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617號所涉及的是,臺灣地區(qū)“刑法”第235條有關“猥褻出版品”的處罰規(guī)定是否違背憲法所認可的言論自由。參見《大法官解釋匯編》(增訂九版),三民書局2011年版,第717—721頁。 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大法官以所謂的“社會多數(shù)共通價值”作為理解價值的出發(fā)點,并借此具體化憲法規(guī)范的內涵;但是大法官在第617號解釋中透過現(xiàn)實導向的價值宣示,一再強化“憲法旨在保障社會共通價值秩序”的論點,扭曲了憲法保護“少數(shù)”族群自由的全面性;不難認定,在第617號解釋中,“社會多數(shù)共通價值”只是大法官個人的價值觀而已。前引B10,第104—107頁。 基于此種不足,道德型后果主義論辯的適用應當受到合理的限制:其一,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將過高的道德標準引入后果論,那么道德標準就會成為“帝王條款”,進而排斥規(guī)范體系和其他后果論的適用。其二,在處理一些特定的案件時,如墮胎、同性戀婚姻、宗教教育等引發(fā)的訴訟,法官應當盡量避免運用沒有達成社會共識的所謂的道德標準,特別是以社會公德或公序良俗掩飾法官的個人道德偏見,才能避免使案件陷入訴訟危機。
(四)政策型后果主義論辯
顧名思義,政策型后果主義就是指將規(guī)則和個案判決的證立方式與政策性因素聯(lián)結起來,著力探討政策在后果主義論辯適用過程中所產生的兩個作用機制:其一,判決的邏輯后果對社會政策所產生的消極或者積極的影響;其二,政策性因素對后果論適用所產生的制約作用。正如美國學者庫克所言,“若法官在一個新的案件遇到邏輯問題時……(他)可以自由選擇以何種方式裁判案件,所以他的選擇將是基于對社會或經(jīng)濟政策的考慮而分析出來的。作出一個明智選擇唯一的途徑是,對各種判決的任何可能后果進行評估。”Walter Wheeler Cook, Scientific Method and the Law, 13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1927, p308 嚴格來說,政策型后果主義與目標型后果主義相涉,但是考慮到政策與社會目標之間不能完全等同,尤其是政策因素在我國法律淵源中的獨特地位,故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類型予以分析。
對于政策型后果主義的適用,則必須回歸政策的法源地位。傳統(tǒng)的法學理論一直將其作為次要的法律淵源予以看待,其作用是彌補主要法律淵源之不足或缺陷。但在我國,在處理某些特定類型的案件(如土地征收、房屋拆遷、計劃生育等)時,政策因素有成為主要法律淵源之趨勢,有時甚至完全排除主要法律淵源的適用。例如,在劉某訴通州市姜灶鎮(zhèn)人民政府案中,政府工作人員于凌晨4點至劉某家作計劃生育工作,劉某一時情急從二樓跳下導致全身癱瘓。劉某訴請國家賠償,法院在以行政行為符合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以及行政行為與劉某的癱瘓之間并無因果關系為由,判決劉某敗訴。參見江蘇省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2003)通中行終字第46號。 同樣在另一起由于計劃生育所引發(fā)的行政訴訟中,黃某因為生育四胎而違反計生政策,被南安市豐州鎮(zhèn)政府以學習計劃生育國策為由,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前后達到166天;此后法院雖然確認被訴具體行政行為違法,但是對于黃某所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要求,則以沒有法律依據(jù)、事實不清為由駁回。參見黃煌輝訴南安市豐州鎮(zhèn)人民政府限制人身自由并要求賠償案,載北大法寶。 毋庸置疑,由于在這些案件中法院將基本國策作為獨斷性理由,直接排除了憲法和民法所確立的權利規(guī)范體系的適用,因而難以通過合理性原則特別是比例原則的審查。
有關上述四種類型后果主義的進一步歸納和總結,可參見下表:
制度型后果主義論辯目的型后果主義論辯道德型后果主義論辯政策型后果主義論辯
考量的因素相類似的其他制度性因素;權力機構之間的分工與合作等判決預期所產生的良好的社會效果社會道德、社會共同價值對個案裁判的制約作用以及裁判對道德因素的影響調整政治、經(jīng)濟、文化目標而設定的指導準則,如計劃生育、土地征收等
典型個案Gourley案等Barbara Grutter v Bollinger案等瀘州遺贈案等劉某訴通州市姜灶鎮(zhèn)人民政府案等
優(yōu)勢將論證的邏輯提升到實踐理性的高度,充分重視規(guī)則背后所蘊涵的制度因素在抽象的法律體系中獲得支撐;容易得到其他法官或者社會大眾的普遍的認同具體化不確定法律概念;注重規(guī)則的實效;提高法律的可預測性,引導社會大眾調整個人行為彌補法律的漏洞與不足;促進法律的變革與與時俱進;消解規(guī)則的滯后性
劣勢容易忽視對類似的制度性因素的考察等為追求效果而忽視規(guī)范權威;事后才能得到檢驗等法官的價值偏好;道德的法律強制等對人權保障產生消極影響;與行政合理原則相沖突
適用限制不同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不得違背基本的法律原則,如法律保留合理對待差別;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支撐,如統(tǒng)計數(shù)據(jù)等基于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識;在特定類型的案件中避免使用,如墮胎等審慎的衡量;接受比例原則的審查;在處理特定案件時才會予以考慮
四、后果主義論辯的作用機制
(一)后果主義論辯是否只能適用于疑難案件
麥考密克認為,只有在演繹推理的局限性顯現(xiàn)出來(無法對理由作出解釋、規(guī)則的模糊性限制),需要對備選的裁判規(guī)則進行權衡時,后果主義論辯才會成為法律論證的一個關鍵因素,“如果被認為負載著那種合理的目標,那么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那些無法根據(jù)明確的強制性規(guī)則得出判決結論的場合,或者規(guī)則本身語焉不詳?shù)膱龊希揽繉蠊目剂孔龀雠袥Q實乃必要之舉”。前引B14,第147頁。 質言之,麥考密克所推崇的后果主義論證只能適用于規(guī)則模糊和規(guī)則缺失的情形,也就是只能在疑難案件中適用后果主義論辯。當然,這一立場還獲得了其他學者的支持。例如,美國著名批判法學者肯尼迪就認為,政策論證不同于演繹論證,因而主要適用于以下兩個場域:一是在法律被“用盡”的場域,“破天荒案件”或“疑難案件”;二是有效的形式規(guī)定需要進入政策考量的場合。美國學者肯尼迪認為,政策論證不同于演繹論證,主要表現(xiàn)在三個關鍵的方面:一是有效規(guī)范作演繹不能解決法律問題,或者說,適用于案件的有效規(guī)范要求法官考慮非演繹理由來支持選擇這樣那樣的亞規(guī)則;二是政策主張的內容就是根據(jù)某套社會價值或法律制度的價值證明亞規(guī)則的可欲性;三是政策主張預設判決過程有個“力場”模式。參見[美]鄧肯·肯尼迪:《判決的批判》,王家園譯,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 比如,我國《民法通則》第4條規(guī)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愿、公平、等價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在此,“公平”、“等價”和“誠實”等不確定法律概念的詮釋既要依賴于社會公認的價值觀,也要考量這些標準所牽涉的政策因素。
通過適用范圍來限制后果主義論辯的適用,其實預設了兩個邏輯前提:一是將法官所處理的案件截然區(qū)分為“簡易案件”和“疑難案件”兩個相對獨立的類型,并根據(jù)不同的類型限制法官所擬采用的論證方法。事實上,在“簡易案件”和“疑難案件”之間存在著一個“過渡區(qū)域”,在這個“過渡區(qū)域”,純粹采用演繹邏輯還是需要其他論證方法(包括后果主義論辯),會受到社會公認價值、常識、法官的主觀動機等因素的影響,因而難以作出一個截然的劃分。二是將規(guī)則的適用過程區(qū)分為“規(guī)則選擇”和“規(guī)則論證”兩個完全獨立的思維過程,前者僅僅在于羅列待決案件所牽涉的規(guī)則體系,后者則是在這些規(guī)則體系中依據(jù)一定的標準選擇恰當?shù)呐袥Q理由。在法律適用的過程中,到底是根據(jù)規(guī)則闡釋特定規(guī)則所產生的后果,還是根據(jù)后果的預設選擇相應的規(guī)則作為裁判理由,本身就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事情。綜觀之,這兩個邏輯前提其實犯了機械主義的錯誤,即試圖對法官思維的過程進行理性的劃分,然后再根據(jù)思維階段的不同,輔之以不同的法律論證方法。
實際上,后果主義論辯其實以“隱性”或者“顯性”的方式存在于法律適用與法律論證過程之中。根據(jù)案件性質的不同,后果論的存在方式也有所差異:
一是在簡易案件中,后果主義論辯一般以“隱性”的方式存在,除非法律規(guī)則以明確方式要求考慮后果。所謂“隱性”,其實就是說,法官已然對規(guī)則的適用作出了后果主義性質的判斷,只是法官認為,這一后果主義的判斷無須在裁判文書中予以體現(xiàn),原因在于,規(guī)則體系本身已經(jīng)可以為裁判提出充足的理由,即規(guī)則適用本身并不會引發(fā)爭議,也能順利通過后果論的檢驗。
二是在簡易案件和疑難案件的“過渡區(qū)域”,后果主義論辯需要為現(xiàn)行法律的適用提供“顯性”論辯。例如,當實體法遭遇違背正義之質疑,只是由于違反程度尚未達到“難以容忍”的地步,故而仍適用現(xiàn)行規(guī)則的場合就需要后果論的支撐。以交通肇事案件為例。由于近年來交通肇事發(fā)案率居高不下、危害程度的加劇,我國《刑法》第133條所規(guī)定的交通肇事罪受到諸多質疑,其中最大爭議便是最高刑過低,難以發(fā)揮刑罰的威懾作用,以至于不少地方的法院甚至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過失殺人罪等罪名處罰交通肇事行為。但從后果論的角度看,如果為了增加處罰力度而規(guī)避第133條的適用,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包括:破壞了我國刑法所設定的罪刑體系(制度型后果主義)、損害了刑罰目的的預設(目的型后果主義)、違背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政策型后果主義)等。因此,法官在適用第133條處理案件時,就可以運用后果主義論辯予以佐證。
三是在疑難案件中,后果主義論辯以“顯性”方式存在。所謂“顯性”,是法官將其后果主義論辯的思考直接在裁判文本中予以細致、明確地寫明,抑或是在附隨意見、異議意見中予以體現(xiàn)。在“顯性”適用的場合,也是現(xiàn)行規(guī)則體系無法明確為個案裁判提供明確、具體法律理由的場合,需要借助其他法律理由和正當性理由為個案裁判提供支持。即在規(guī)則模糊、規(guī)則沖突、規(guī)則空白和規(guī)則悖反的情形下,后果主義論辯的功能就是直接作為論證個案判決的正當理由,為類推適用原有規(guī)則、適用法律原則或者創(chuàng)制的新規(guī)則提供“二次證明”。圍繞裁判所可能引發(fā)的各種后果,持不同立場的法官可能對是否會引發(fā)特定后果、某一后果的重要性、后果的衡量標準等問題進行爭論,但可以確定的是,法官對于后果主義論辯本身并不持排斥態(tài)度,在Gourley案、Barbara Grutter v Bollinger案等案件的判決書中可以得到清晰的體現(xiàn)。
(二)后果主義論辯一般作為輔助性依據(jù)
在常態(tài)的司法環(huán)境下,適用后果主義論辯的直接目的不是直接推導出個案判決,而是論證裁判規(guī)則的正當性與可接受性,即為運作性依據(jù)提供正當性證明。有關運作性依據(jù)和輔助性依據(jù)的劃分,參見陳林林:《公眾意見在裁判結構中的地位》,載《法學研究》2012年第1期。 針對不同的情形,后果主義論辯所論證的對象也是有所差異的:在規(guī)則空缺的情形下,后果論需要為所擬制的新規(guī)則提供論證,當然,所證成的規(guī)則非源于法官的主觀臆斷,而是需要在法律體系內找到相應的依托,如原則的具體化、擬類推適用的準用規(guī)則;在規(guī)則模糊的情形,后果論為“可能語義”范圍內的諸種解釋提供論證,并將規(guī)則的目的、常識等作為評價標準,以此將規(guī)則的邊緣意義具體化;在規(guī)則沖突的情形下,后果論為相互沖突的規(guī)則各自提供論證,從而選擇最佳的規(guī)則,限定相互沖突的規(guī)則各自的適用領域;在規(guī)則悖反的情形下,結果論為通過“目的論限縮”所產生的規(guī)則或創(chuàng)制的例外規(guī)則提供實質性依據(jù),并將法律目的轉化為目的型后果主義論辯的依據(jù)。
在處理特殊的個案時,后果主義論辯也可以直接作為運作性依據(jù)。這里的特殊個案是指同性戀婚姻、墮胎、安樂死等在道德上具有高度爭議、沒有形成社會共識的案件類型。對于這類案件,美國學者桑斯坦主張法官的最佳選擇就是運用“司法最低限度主義”,其基本特征就是“窄”(不制定寬泛的規(guī)則)和“淺”(避免提出一些基礎性原則)。參見[美]凱斯·R.桑斯坦:《就事論事》,泮偉江、周武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3頁。 例如,我國臺灣地區(qū)司法院針對“特殊重婚是否得撤銷”所作的第242號解釋就屬于這一類型。該案的事實具有特殊性又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甲男與乙女于1940年在福建締結婚姻,后甲男于1949年只身前往臺灣,于1960年與丙女結婚;兩岸恢復交流后,乙女以甲男的行為違背臺灣地區(qū)“民法”第985、992條的規(guī)定為由,依法申請撤銷甲男與丙女的婚姻關系。相關案件事實參見前引B39陳林林文。 在第242號解釋中,臺灣地區(qū)司法院認為,本案與一般重婚案件有所不同,如果撤銷此種有長期實際共同生活事實之后婚姻關系,“其結果將致人民不得享有正常婚姻生活,嚴重影響后婚姻當事人及其親屬之家庭生活及人倫關系,反足以妨害社會秩序”。前引B32《大法官解釋匯編》,第119—120頁。 針對這一特殊個案,臺灣地區(qū)司法院并沒有創(chuàng)制相應的規(guī)則,原因在于這類案件畢竟是由于特殊的歷史事實所造成,適用范圍有限,因而主要采用了道德型后果主義論辯(家庭生活及人倫關系)、目的型后果主義論辯(社會穩(wěn)定)。
(三)后果主義論辯的本質:法律維度轉變?yōu)槭聦嵕S度
之所以后果主義論辯可以為個案裁判或規(guī)則適用提供“二次證明”,原因在于后果論為法律爭議的處理提供了獨特的事實維度——將法律問題作為事實問題加以處理,美國學者薩默斯認為,對后果的關注反映出工具性價值具有經(jīng)驗主義的色彩,而工具主義論者主張,在制定和實施法律過程中,所遇到的價值問題基本都可以轉化為事實問題。參見前引B31,第41頁。 即將那些難以具體化的不確定法律概念、規(guī)范性概念、一般條款在一定程度上還原為事實問題,進而根據(jù)這些被還原的客觀事實或合理預設的事實進行衡量,那么法官或者法律共同體也就可以清晰地認知不同類型的法律理由所可能牽涉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換言之,后果論的適用轉變了法律論證的思維方式,即從如何尋找法律理由和正當理由,轉變?yōu)橛懻搨€案裁判會引發(fā)哪些后果、這些后果具體的表現(xiàn)形式、這些后果之間的邏輯關系、這些后果之間的評價標準等問題。個案裁判所爭論的焦點也從如何解釋規(guī)則、如何實現(xiàn)規(guī)則與案件事實的關聯(lián),轉化為規(guī)則的適用會產生怎樣的后果、如何處理和認識這些后果;如何積極規(guī)避消極后果、如何擴大積極后果。
之所以需要將法律問題還原為事實問題,原因在于,“如果沒有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同質,那么無論是在法律文化內部,還是參照道德的或其他法律之外的規(guī)范(還是傳統(tǒng)的自然法的領域),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就某個疑難法律問題得出一個明顯正確的答案,甚至得不出一個令法律職業(yè)人士信服的答案”。前引B11。 與其花費大量的筆墨爭論何謂“正義”、“公平”等形而上的概念,以及如何在個案裁判中體現(xiàn)這些形而上的觀念,還不如從確定的、具體的后果論角度為裁判提供理由。正如桑斯坦提出的“未完全理論化協(xié)議”理論所揭示的那樣,固然我們無法在宏觀上對高層次的原則達成共識,但是卻可以在“范圍狹窄的或低層次的原則上達成的協(xié)議來解釋有關特定結果”。前引⑥,第41頁。 對于個案裁判,“未完全理論化協(xié)議”的指導意義在于:與其糾結于高層次的原則與理念,不如從低層次原則與制度上尋求共識,特別是適用低層次原則所產生的相關后果。
五、后果主義論辯適用的限制
從整體上看,后果主義論辯的優(yōu)勢是遵循實踐理性的要求,揭示規(guī)則適用與個案裁判所可能引發(fā)的系統(tǒng)性影響,從而積極推動法律的現(xiàn)代性變革。但是,其內在的缺陷也不容忽視:一是受人的有限理性的約束,法官可能無法全面預見所有的相關后果,特別是難以以實效佐證相關后果是否必然發(fā)生,以及相關后果的影響范圍、方式與程度;二是無法避免個人價值偏好的影響,即后果論在引導規(guī)則的選擇與規(guī)則的具體化時,憲法價值、常識、公共利益等評價標準之間無法形成固定的位階關系;三是基于不同的思維進路,各種類型的后果論之間有時難以實現(xiàn)溝通對話。基于此,就需要從后果主義論辯的具體適用過程提出相應的限制性舉措。
(一)所論辯的后果:待決事實與法律后果之間具有相關性
麥考密克反對兩種極端的后果主義思維,即要么將裁判所引起的所有的各種類型的后果作為論證理由,要么將裁判論證過程中排除后果主義論辯,其秉持一種折中主義的立場——后果主義論辯之考量與裁判的正當理由相關的類型和系列的后果。參見Neil MacCormick, On Legal Decision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rom Dewey to Dworkin,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1983, pp239—240 同時,麥氏將對后果的思辨回歸于法律推理本身,并提出相關后果就是“邏輯的后果”或“蘊含的后果”,而不是判決的行為的后果或其他較長期的可能的結果。參見[英]尼爾·麥考密克、奧塔·魏因貝格爾:《制度法論》,周葉謙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頁。 當然,麥氏并未對“邏輯的后果”作進一步的類型劃分,實乃裁判所引發(fā)的后果千差萬別,不同類型的案件所考量的后果具有典型的差異。但可以肯定的是,在確定相關后果時,需要確定兩個基礎標準:一是后果的普遍性;二是后果以行為指引作為核心。
所謂普遍性,即適用后果主義論辯時所考量的后果應當具有一般性,而不僅僅針對個案而無法對同類案件形成拘束力。普遍性意味著論辯過程可以經(jīng)受時間的檢驗。經(jīng)后果主義論辯所形成的規(guī)則自然無法輕易獲得法律共同體的認可,在今后遇到類似的案件時,其他的法官一方面會驗證之前所使用的論辯方式是否也能在當前案件中運用;另一方面也會檢討論辯方式所運用的后果是否實際發(fā)生或者尚未發(fā)生,從而進一步支持或者消解適用后果主義論辯的正當性。之所以要強調后果的普遍性,原因在于經(jīng)后果論辯所形成的規(guī)范能夠作為未來案件的大前提,并積極引導社會大眾的行為,即社會大眾根據(jù)法律安排自己的行為,預測行為可能引發(fā)的法律后果。特別是在創(chuàng)制規(guī)則或者變更規(guī)則的情況下,需要評估人的行為發(fā)生變化的可能性。法律不能強人所難,不能違背理性人對法律的期待。當適用后果主義論辯時,法官所思辨的所有后果最后都會落腳于人的行為,并依靠人的實踐活動去證明或者證偽法官所設想的種種可能的后果。例如,引發(fā)訴訟爆炸就是法官在處理人身損害賠償?shù)劝讣r經(jīng)常考慮的一類后果,在Gourley案中也不例外,而是否真正會引發(fā)訴訟爆炸,實際上取決于個人的理性衡量。正因為如此,在確定相關性后果時,需要圍繞人的選擇和實踐觀念,從而確定后果主義論辯發(fā)生作用的場域。
(二)論證缺陷:后果主義論辯與其他論證形式的配合使用
實踐中,后果主義論辯適用的困境主要有二:一是如何辨識適用不同規(guī)則、原則、政策等法律理由之下產生的各種類型的后果。由于法官并不天然擁有除法律知識以外的社會科學知識,因而法官極有可能無法全面意識到適用某個法律理由所引發(fā)的全部后果。二是似乎難以確定一個可行的衡量標準,對已識別的后果進行衡量,并根據(jù)優(yōu)位關系確定適用的具體規(guī)則、原則或其他裁判理由。質言之,法官們通常可以借助“正義”、“功利原則”、“權利理論”(德沃金)、“公共政策”、“常識”、“憲法所確立的價值”、“法律體系”等標準或者價值進行衡量,但這些標準和價值之間并沒有優(yōu)先關系。因此,后果主義論辯有時并不具有終局性,還需要與其他論證形式相互配合。麥考密克認為,雖然后果主義論證能夠安排和構建一個從相關后果出發(fā)權衡裁判的圖景,能夠為司法裁判的制作和論證提供合理的依據(jù),但其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是不容忽視的:法官的個人偏好對于特定結論的影響是無法規(guī)避的;法官容易受民意等非理性因素的影響;法官容易迷失于各種類型后果的爭辯,無法作出獨立的裁判,等等。正是基于這樣的思考,麥考密克在后果主義論辯之外,還提出了一致性和協(xié)調性論辯:“在論證裁判結論時……相關的論證必須是一個可讓人接受的、結果精確闡釋的論證,要達到這一要求,其所要遵循的條件是,一方面不能與既定的法律原則相沖突,另一方面要找到某種支持性的類比、原則或者其他法律上的理由來使判決結論正當化。”前引B14,第118頁。 換言之,法官適用后果主義論辯的目的不是要架空法律體系,而是要為規(guī)則、原則、政策或者其他法律上的理由的適用提供“二次證明”,以保證法律體系形式上的融貫性。
(三)論證義務:法官就論證過程展開詳細的說理
對于法官來說,后果主義論辯的適用需要法官履行充分的說理義務。“司法的權威來源于其具有的專門技能,而不是其特殊的人員構成”。[美]基思·E.惠廷頓:《憲法解釋》,杜強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40頁。 這項特殊的專門技能其實就是法律人所特有的法律思維。法官運用法律思維解決個案糾紛,將推理過程詳細記錄于判決書中,并輔助之以裁判理由——規(guī)則、原則、政策等。給出裁判理由是法官的基本義務,其既能約束法官審慎行使裁判權,也能促使公眾特別是案件當事人產生對司法解決糾紛能力的信賴。職是之故,在運用后果主義論辯之時,法官需要著墨于以下內容:(1)司法裁判引入后果主義論辯的緣由,即為何需要在傳統(tǒng)的論證模式之外,輔助以后果論的考量;(2)個案裁判所需要考量的邏輯后果與一般后果的類型和范圍;(3)這些邏輯后果、一般后果與個案事實、裁判標準的相關性,特別是運用普遍性和行為指引兩項重要標準,具體闡釋后果對同類型案件的影響,以及對人的行為的指引作用;(4)當事人及其律師提出后果論意義上的理由作為訴訟或者抗辯理由時,無論是支持還是反對,抑或是提出其他后果論理由,法官都有義務對這些理由作出回應,并給出相應的論據(jù)。
結語
有關后果主義論辯的爭論,本質上反映了司法克制主義與司法能動主義之間的方法論分歧。崇尚文本主義、原旨主義的司法克制主義者認為,“一旦法官開始習慣于通過引證真實世界內的效果來證成法律的結論,法官將經(jīng)常性地主觀、不民主地行動,以精英所理解的良好政策取代合理的法律”。[美]斯蒂芬·布雷耶:《積極自由——美國憲法的民主解釋論》,田雷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頁。 對于克制論者的這一立場,能動論者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作出辯護:一是司法克制主義者的觀點也暗含后果主義論辯的邏輯:他們之所以希望法官合理約束、控制司法的主觀性,是因為運用文本、體系、歷史等解釋方法就已經(jīng)能妥善處理個案;他們得出這一結論的前提,就是司法實踐所反映出來的經(jīng)驗與效果。也就是說,司法克制主義者也是站在后果論的立場反駁能動主義的。二是后果本身也在約束法官的能動性,因為后果主義論辯所考量的后果具有普遍性和邏輯性,同時還要經(jīng)受法律共同體的檢驗。更為重要的是,任何信奉后果主義論辯的法官將后果主義思維運用到各種類型的案件中時,其必然堅持一種特定的立場,一旦放棄或者改變這一立場,其無可避免地要回應理論界和實務界的質疑。
蘇力主張,“法律人應以一種追求系統(tǒng)好結果的實用主義態(tài)度,充分利用各種相關信息,基于社會科學的縝密思維”。蘇力:《法條主義、民意與難辦案件》,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1期。 對此,波斯納曾對后果論與實用主義之間的關系作過梳理,一方面他承認實用主義主張通過對命題所產生的后果來對命題進行檢驗,即具有后果論的理論預設,但另一方面,“實用主義審判體系中肯定具有形式主義的成分,特別是按照規(guī)則而不是按照標準裁判”。[美]理查德·A.波斯納:《法律、實用主義與民主》,凌斌、李國慶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4頁。 其實,波斯納努力撇清后果論與實用主義之間的內在關系實無必要,因為法律方法理論的發(fā)展趨勢表明,我們不可能再回到僅僅崇尚概念法學的形式法治時代,同時也可能完全拋棄形式邏輯從而創(chuàng)設出一套全新的論證體系。固然在形式邏輯之外,學者們提出多種論證理論用以彌補形式邏輯本身的缺陷,如“弱意義的裁量”(德沃金)、“二次證明”(麥考密克)、“理性法律論辯理論”(阿列克西),但形式邏輯始終是法官作出裁判的最終依據(jù)。因此,后果論無論在何種意義上與形式邏輯、義務論相沖突,都不可能以減損形式法治的方式樹立自身的權威,因為后果主義論辯的最終目的是促進法律體系的融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