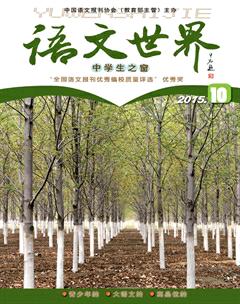青島啊,青島
劉兆亮
青島是一個很美麗的城市。我那時認為它恰如其分的美麗是因為父親去了那里。
自從父親去了青島,這個離我800里的地方突然有了親和力和感召力。父親是去青島干建筑小工的,抬水泥,搬石塊,挑磚頭是他的工作。但這是次要的,父親在青島生活和工作了,這是讓人興奮的事。
那時我正上高三,父親帶著家中最破的被子和那頂漏雨的安全帽到縣城坐火車。因為還有40分鐘的空閑,父親就到學校去看我。但他并沒有見到我,他的腳剛好踩到上課鈴聲。父親就給看門師傅留了一張字條,寫道:“兒,我去青島干活兒了。青島好啊,包吃包住一天20塊錢。你好好念書,爭取考到青島去。”署名是“父親親筆”。
這是父親寫給我的第一封書信,是寫在隨手撿起的煙盒上的,煙盒上腳印清晰可辨,比父親的字還工整。但父親的字比它精神多了,撇撇捺捺都有把持不住的去青島的激動之情。
青島好啊!父親這個贊美詩般的感嘆也是聽別人陳述來的。父親沒去過青島,甚至他連比縣城更大點兒的城市都沒去過,但父親那時去青島了。看到父親的留言,我很高興。從此以后,我的學習和生活便有了“青島特色”。地理課本上的膠東半島成了我的維多利亞港,歷史課本上德國強占青島的章節讓我深刻銘記,青島頤中足球隊成了我心中的巴西隊。而我的高考志愿上,打頭陣的都是青島的大學。
父親在一個叫觀海山的山上建花園。山不太高,但站在屋頂上可以看到海,下雨天不上工,父親就上山頂去看海。看海是父親最高級的精神生活。他的物質生活,也讓他津津樂道,隔三差五能吃到兩塊五一斤的肥肉膘。父親說,青島就是青島啊!但青島沒有及時給他發工資,這是堵心窩兒的事。父親說,肥肉很香,但一想到錢就咽不下去了。
父親走時只準備了25塊錢生活費,他花了40天。之后,他摸口袋時,兜里只剩下五個手指頭了。
青島怎么不發工資呢?老板解釋說臨時有點兒困難,讓父親等人頂一頂。父親覺得那個李老板說的話不虛。以前李老板讓父親下山替他買的煙都是十多塊錢一包的,現在下降到四塊多錢一包了。
給李老板買煙是父親難忘青島的另外一個原因。起初,父親買煙買得一肚子得意,覺得老板還挺把自己當回事。等父親戒煙了——實際是沒有閑錢買煙了,他才感覺到買煙成了一種煎熬和痛苦。
父親經常把煙包放在鼻子下使勁地聞一聞。聞一聞煙又不會少,沒事的。有幾次他甚至就想把手中的煙往腰里一別,一口氣跑回家,坐在田頭再一口氣抽光。邊抽煙邊看玉米生長,多美的事兒啊!但父親是個老實巴交的人。有一次,李老板客氣地說,剩下的三毛錢硬幣不要了,看你累的,頭上的汗珠子比雨點兒還大!父親不收,兩個人互相推讓,干活兒的人都把手中的活兒停下來看他們。李老板生氣了,大喝一聲后又把聲音壓得低低的,拿著,對,拿著。父親的兜里就多了三毛錢。父親想等下次再多出三毛,還有再下次,再再下次……
但李老板已經好幾天沒讓父親買煙了,也就是說李老板已經很少過來了。慢慢地,父親感覺到李老板可能跑掉了!工程沒完,老板就跑了,碰上這樣的事,算是倒霉了。
父親和工友們有的拆開了內衣,有的翻起鞋子,有的把被子里的棉花團弄開……那是事先準備好的路費。這是家鄉的習慣,路費多少就縫多少。
父親跟我講他在青島的這些經歷時,我還在等大學通知書。青島與我的關系還八字沒一撇。但青島朝我走來了。我被青島一所重點大學的土木工程系錄取了。
那天父親抽煙抽得很興奮,滿眼亮光,比畫著青島寬闊的馬路怎么走,還一個勁兒說,青島好啊!青島好啊!
我不知道,當父親贊美詩一樣地感嘆青島好的時候,他的右手在口袋里把從青島帶回來的那三毛錢都攥出了汗!到了學校后我才發現,那三枚硬幣,被父親打進了我的背包——那是父親在青島賺取到的財富,兒子應當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