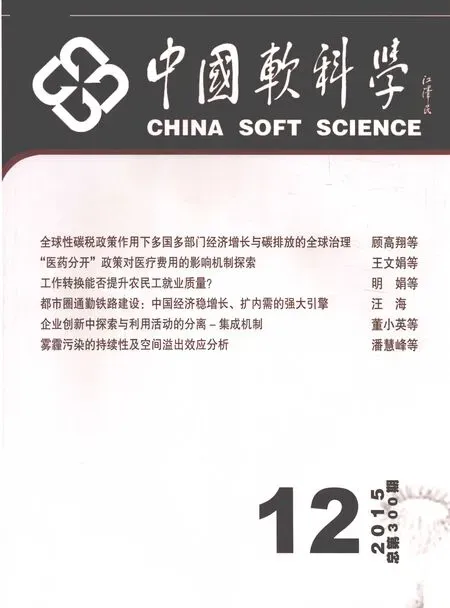都市圈通勤鐵路建設:中國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
汪 海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江蘇 南京 210003)
?
都市圈通勤鐵路建設:中國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
汪海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江蘇南京210003)
摘要:世界城市化經驗表明,一國城市化進程是人口空間集聚度持續提高的過程。以單體大城市為核心、以發達交通網為基礎、與周邊中小城市實現同城化發展的大都市圈,是城市化向高級階段發展后出現的人口空間集聚形態,目前發達國家大部分城市人口都已聚集在大都市圈。我國城鎮化率已超過50%,進入“大都市圈化”發展階段。大都市圈建設的關鍵性基礎設施,是核心大城市緊密聯系周邊中小城市的通勤鐵路網。我國到2030年需建3萬公里通勤鐵路,相當于全國現有鐵路長度1/3。以低成本通勤鐵路替代過度擴張的城市地鐵,可節省上萬億元投資。城市化是我國最大內需所在,但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的真實城市化進程滯緩,是造成內需不足、增長乏力的主要原因。通勤鐵路引領的同城化大都市圈建設,能化解城市新移民“大城市進不去、小城市不愿去”兩難困境,有效推進真實城市化進程,有力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極大提升我國城市集聚力、輻射力、創新力和競爭力,是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是塑造國家競爭優勢的利器和重器。當前需及早制定主要都市圈通勤鐵路規劃,盡快列為我國“十三五”時期建設重點。
關鍵詞:都市圈;通勤鐵路;城市化
世界城市化經驗表明,一國城市化進程是城市人口空間集聚度持續提高的過程,城市規模由小到大、城市數量由少到多、城市體系由簡單到復雜、城市形態由單體城市向多中心城市密集區發展。在一國城市化率不足50%時,以農村人口向單體城市集聚為主,制造業快速增長,取代農業成為主導產業。城市化率超過50%后,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地位下降,服務業成為新的主導產業,城市空間發展的主要標志是形成“大都市區”(即“大都市圈”)[1],人口會進一步向以服務業發達的大城市為極核、由眾多大中小城市組成的大都市區(大都市圈)集聚。大城市作為經濟、科技、文化中心,帶動周邊中小城市發展,形成同城化的大都市區(大都市圈),既能發揮大城市的集聚效應和規模優勢,又可避免單體城市的擁擠弊病。以美國為例,1920年城市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50%,成為一個城市化國家;1940年大都市區(metropolitan area)人口接近全國人口的50%,進入“大都市區時代”;1990年超過50%人口居住在百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區;到2000年更有30%人口居住在500萬人口以上的大都市區[2]。隨著城市化水平提升,多個地理鄰接的大都市區(大都市圈)還進一步朝連綿化方向發展,共同組成大都市帶(megalopolis)。如美國東北部大都市帶就是由紐約—北新澤西—長島、華盛頓—巴爾的摩、波士頓—伍斯特—勞倫斯等多個大都市區構成的空間聯合體[2]。目前發達國家大部分城市人口都已集聚在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在世界范圍大都市圈也正快速發展。從1900年到1980年全球城市人口增長8倍,50萬以下的城市人口只增長5倍,而500萬以上的城市人口增長了20倍[3]。1900年世界上還沒有1000萬人口的超大城市,目前已有23個城市人口在1000萬以上[4]。20世紀初世界首位城市倫敦只有650萬人,21世紀初全球最大城市東京都市圈人口已超過3600萬[5]。當代世界超大城市多數都不是單體城市,而已成為像東京那樣的大都市圈。
目前世界城市化率已超過50%,有越來越多的人口向城市以至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城市密集區集聚。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等人創立的空間經濟學認為,要素流動和規模報酬遞增的累積性導致人口和產業集聚的不斷自我強化,從而形成空間上的“中心—外圍結構”,系統闡釋了工業化與城市化相互依存、產業和人口空間集聚度持續提升、城市和城市密集區規模越來越大的基本原理[6]。世界銀行《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基于空間經濟學理論,依據大量數據和實例,指出隨著經濟增長產業和人口在空間上高度集聚是世界各國發展的普遍規律,而規模經濟可以解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產業和人口持續集中現象。“在公司追求規模經濟的過程中,農業生產趨于分散,而制造業趨于集中”,“服務業的集中程度高于制造業”。“隨著國家從農業生產轉向工業再轉向服務業生產,公司和工人拋開的不僅是農村和農業工作,而且是一個規模無關緊要的世界。他們越來越多地移居規模較大、人口稠密、而且規模至關重要的地區,那里,生產與分配實現了規模經濟效應”[7]。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大規模城市密集區,正是這種因人口、產業集聚而實現資源高效配置的“規模至關重要的地區”。
在全球化背景下,國家競爭優勢集中體現為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城市密集區的規模優勢和創新優勢。發達國家的世界級大都市圈、大都市帶集聚著大量人口、創新人才和多樣化產業,具有遠勝于單體城市的超強規模,是發展與創新的強大引擎,也是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科技活動中樞。擁有世界級大都市圈、大都市帶,就擁有參與國際競爭的雄厚實力。美、日、歐大國崛起的重要標志,就是擁有世界級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我國要發揮大國優勢,提升國家核心競爭力,關鍵在構建自己的世界級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引領全國發展。
一、大都市圈:中國城市化新階段的發展重點
都市圈概念源于美國的大都市區(metropolitan area),隨著城市化推進,中心城市人口和產業不斷向郊區擴散。基于城市人口統計需要,1910 年美國最早提出了大都市區的定義,它是一個大的人口核心以及與這個核心具有高度社會經濟一體化傾向的鄰接社區的組合。其統計標準是以非農業活動占絕對優勢的城市中心區與外圍地區之間勞動力聯系的規模和密切程度,以人口通勤率為核心指標[8]。由于大都市區是城市化向高級階段發展的必然產物,隨著各國城市化的推進,美國“大都市區”的概念被許多國家引用。1960年日本行政管理部門參照美國大都市區定義,提出“大都市圈”概念:中心城市為中央指定市,或人口規模在100萬人以上,并且鄰近有50萬人以上的城市,外圍地區到中心城市的通勤率不小于本身人口的15%[9]。根據美國、日本等國的嚴格定義,都市圈以通勤率為主要統計指標,以都市核心區與外圍區之間的當日往返通勤范圍為界限。通常最大單向通勤時距在1小時左右能為通勤者普遍接受,都市圈遠郊居民與中心城居民可在生活質量與心理感受上大致相同,形成同城效應。按照通勤率的界定標準,都市圈的實質是同城化的“1小時通勤圈”。
中國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展開世界上規模空前的城市化進程。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預測,中國城市人口在2030年將增加到10億,城市化水平也將達到70%左右。但中國是人多地少的國家,未來10多年如何在有限的城市空間內“迎接10億城市大軍”,形成可持續發展的城市體系和空間結構?麥肯錫研究報告將中國可能的城市化道路分為四種:超大城市、中心輻射、分布式增長、小城鎮主導。前兩種是集中式城市化,后兩種是分散式城市化。報告認為,由于規模經濟的原因,集中式的城市化無論在人均產出、單位能耗、占用耕地、大眾交通、控制污染、人才集聚等方面都更有效率[10]。而從各國城市化經驗看,過度發展單體“超大城市”會產生嚴重負面的“擁擠效應”,最可取的是“中心輻射”的集中城市化模式,即重點發展以大城市為核心的包括眾多大中小城市在內的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
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很不平衡,94%人口集中在從黑龍江黑河到云南騰沖一線的東南半壁,其土地面積僅占全國43%[11],人口密度與日本、韓國相近,沿海地帶人口密度更遠高于日本、韓國。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占全國51%,而土地面積僅占日本9%[12]。中國只能像日本和韓國那樣,重點發展人口和產業密集、高度集約利用土地的大都市圈以至大都市帶。中國人口是日本的10倍,在進入城市化成熟期后,將會形成10個人口7000萬像日本太平洋沿岸那樣的大都市帶,30個人口1000萬~3600萬像東京、大阪、名古屋那樣的大都市圈,還會有50個人口200萬~500萬像札幌、仙臺、靜岡、廣島、北九州等那樣的都市圈,2/3的人口將居住在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13]。
2014年中國城市化率達54.8%,服務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8.2%,超過制造業成為新的主導產業,中國開始向以服務產品生產與消費為主的后工業化時期過渡。大都市圈也是經濟發展向后工業化階段轉型升級的產物。中心地理論認為,服務業有明顯等級體系,其空間分布與城市等級體系一致,服務業等級越高,所在城市規模也就越大[14]。由于大多數服務產品不像制造業產品那樣便于運輸,因而服務貿易特別是高端服務業要求供需雙方在時空上高度接近,進行交易效率最高的面對面交易,只有消費者大量集聚達到一定的市場規模才能盈利,所以現代服務業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和大都市圈。多樣化生產性服務業在核心大都市集聚,還有助于提高制造業的生產率,會吸引制造業大規模聚集在核心大都市周圍形成許多專業化城市,與核心城市組成大都市圈。從需求角度看,由于消費者具有多樣化的消費需求偏好,大都市圈擁有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和強大的先進制造業,能夠提供豐富多彩的消費產品和多種多樣的就業機會,吸引人口大規模集聚,從而擴展大都市圈的“本地市場”。市場的擴張又促使大都市圈產業規模擴大、分工深化、就業增加,提供更多樣化的產品并吸引更多消費者和廠商集聚。亞當·斯密認為勞動分工是一國財富增長的源泉,分工的深化取決于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市場規模又受運輸能力的限制[15]。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人口和產業密集區能夠最大化降低運輸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最大化擴張本地市場,從而促進勞動分工深化。在斯密-楊格定理揭示的“勞動分工深化促使市場規模擴大,而市場規模擴大又推進勞動分工深化”的自我強化機制作用下[15][16],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等城市密集區的人口和產業集聚規模也就越來越大。
由于“服務業的集聚程度遠高于制造業”[7],而生產性服務業和高端消費性服務業的集聚程度更高,當前我國城市化已開始轉變到中小城市人口向大都市圈、大都市帶集聚的發展新階段。2013年在我國290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206個城市常住人口少于戶籍人口,為離散力大于集聚力的人口凈遷出城市;只有84個城市常住人口多于戶籍人口,是有不同程度集聚力的人口凈遷入城市。84個城市共有常住人口45451萬人,戶籍人口36179萬人,非本地戶籍常住人口為9272萬人。其中,有44個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在50萬人以下,為低集聚力城市,共計凈遷入813萬人,平均每個城市僅遷入18萬人;有10個城市凈遷入人口在200萬以上,為強集聚力城市,共計凈遷入5282萬人,相當于全部84個凈遷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總和的57%[17],城均遷入高達528萬人。10大強集聚力城市按非戶籍常住人口規模由高到低排序為:上海、北京、深圳、東莞、天津、廣州、蘇州、佛山、成都、武漢,其中上海市最高達983萬人,超過44個低集聚力城市凈遷入人口的總和。10大強集聚力城市有8個分布在沿海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城市密集區,反映這些地區已初步向多中心大都市帶發展。深圳、東莞、蘇州、佛山并非區域核心城市,而人口集聚規模接近甚至超過一些區域核心城市,主要原因是其鄰近某些集聚力更強的區域核心城市。如蘇州鄰近上海、佛山鄰近廣州,深圳、東莞則鄰近香港。正如日本第二大城市橫濱緊鄰東京,并與東京組成多中心大都市圈一樣,上海—蘇州、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正在形成多中心大都市圈,這三大都市圈集聚的非戶籍常住人口總量高達3578萬,相當于全部84個凈遷入城市非戶籍常住人口總和的1/3強,實際上大都市圈而非單體城市已成為吸引流動人口的主體。10大強集聚力城市還有2個是中西部大都市成都和武漢,而這兩大城市也在構建各自的大都市圈,顯示全國人口聚集的大趨勢已不再單一流向沿海,而是向各地的大城市和城市密集區集中,我國開始邁向重點發展大都市圈、大都市帶的城市化高級階段。
從國際經驗看,美國分別于1910年、1920年進入大都市區[8]和大都市帶發展的起步階段[18],同期美國的城市化率分別為45.7%和50.9%[19];而到1940年和1950年已處于大都市區[2]和大都市帶發展成熟階段[18],同期美國城市化率分別為56.3%和63.6%[19]。預計到2030年代我國城市化率達70%,進入城市化高級階段后,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的發展也將基本成熟。因此,未來10多年我國處于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快速發展時期。中國是人口和經濟大國,在城市化發展新階段,重點建設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對提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有重大意義,能有力引領全國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
二、借鑒國際大都市經驗,構建基于通勤鐵路的多中心大都市圈
發達國家大都市隨著人口增長,無一例外都經歷了城市空間大規模擴張的“郊區化”發展階段,城市建成區向周邊郊區不斷擴展,中心城人口、產業和部分功能向郊區轉移擴散,許多新城在郊區崛起,并通過現代化交通走廊與中心城實現一體化發展。城市“郊區化”的實質是郊區的城市化,更確切地說是“大都市區化”[2]或“大都市圈化”,中心城與眾多郊區新城和外圍城市共同組成多中心大都市圈。
從單體大都市向多中心大都市圈擴展的郊區化進程中,有“汽車交通引導郊區化”和“軌道交通引導郊區化”兩種模式。在“汽車交通引導郊區化”模式下,中心城與郊區聯系以高速公路為主,郊區無序蔓延,大量占用土地,中心城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大都市的人口規模與密度都會受到限制。而東京、香港等“緊湊型”國際大都市是“軌道交通引導郊區化”的典范,中心城與郊區聯系以占地少、能耗低、運量大、效率高的通勤鐵路為主。東京人口規模和香港人口密度遠超過世界其他大都市,之所以能保持城市的有序營運,一是有多中心、開放型的城市空間結構,二是有高度發達和高效準時的軌道交通體系,優先建設眾多放射性軌道交通走廊直接把市中心與郊區城鎮無障礙緊密聯系起來,形成多中心一體化大都市圈,既可共享同城化規模優勢,又能減少單體大都市的擁擠弊病。中國是人多地少的國家,只能走以軌道交通建設引領大都市圈發展的道路。
東京都市圈包括東京都及鄰近神奈川縣、埼玉縣、千葉縣,土地面積1.34萬平方公里,2010年人口3562萬(日本總務省統計局用通勤率指標統計人口為3692萬人)[12]。東京都市圈從1958年起實施了5次空間發展規劃,引導都市圈從單中心圈層結構向多中心網絡結構演變[20]。目前已形成由都心(以東京火車站為核心包括丸之內、銀座等商務中心區)—副都心(新宿、池袋、澀谷等)—郊區衛星城(立川、八王子、多摩新城等)—鄰縣城市(橫濱、川崎、埼玉等)構成的多中心、多層次都市圈空間結構。在東京大都市圈內,橫濱人口達360萬,川崎、埼玉人口也超過100萬,還有千葉等50多個大中城市。這些城市人口總和近2000萬,相當于東京都中心23區800萬人的2倍多,不僅疏解了人口壓力,而且分擔了主城的工業、交通、科研、教育等城市功能。東京是隨著軌道交通網絡成長的大都市(圖1),優先建設鐵路。東京都市圈50 公里半徑范圍內軌道交通線總長2305 公里,承擔56%的交通運量[21]。其中地鐵292 公里,主要分布在東京都23區內,以市區交通為主;在其外圍,有20多條國家鐵路(JR)及私營鐵路放射線從市區通向郊區腹地(圖2),主要承擔大都市圈的通勤交通。都市圈通勤鐵路網總長2013公里,是市區地鐵網長度的7倍[22]。東京所有城市商業中心和副中心,都是依托都市圈軌道交通主軸——JR鐵路山手環行線上的東京、新宿、池袋、澀谷、上野等火車站發展起來的,形成環狀“交通樞紐—商業中心”復合體系(圖3),其中每個“交通樞紐—商業中心”復合體都有多條通勤鐵路向外放射聯系市郊衛星城,構成東京大都市圈多中心一體化空間結構的主框架。軌道交通運量大、時間準、效率高,保障了城市活動有序營運和內外聯系通達順暢,全國居民都可通過發達軌道交通網準時快捷往返東京市中心,同時也減輕了人口向東京集聚的壓力。東京都市圈汽車保有量超過1000萬輛[23],是北京、上海的2~4倍,既不實行汽車限行限購,也不收擁堵費,而城市交通卻高效有序,還多次被評為世界宜居城市[24]。擁有發達軌道公交體系,出行十分便利是其重要因素。

圖1 東京都市圈基于通勤鐵路網的空間擴展資料來源:資料來源:劉賢騰.東京的軌道交通發展與大都市區空間結構的變遷[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10(11).

圖2 東京都市圈以山手線為核心的通勤鐵路網(路網中心橢圓形環線為山手線)資料來源:高木清晴.日本城市軌道交通概況[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04(4).

圖3 東京沿山手環線分布的都心和副都心 資料來源:鄭明遠.軌道交通時代的城市開發[M].中國鐵道出版社,2006.
不單是東京,紐約、倫敦、巴黎等國際大都市也都有兩類不同的軌道交通系統,即市區地鐵等軌道交通網和都市圈通勤鐵路網。地鐵、輕軌等市區軌道交通網大多分布在距市中心15公里半徑范圍內,具有線路短、站點多、運力大等特點,但市區軌交線一般建在地下,造價高,運速慢,主要為大都市的中心城內部提供短途客運服務;而通勤鐵路又稱市郊鐵路,利用既有鐵路線改造發展而來,通常建于地面或高架,具有線路長、站點少、站距遠、運速快等特點,造價僅為地鐵的1/2~1/3[25],其實際運營時速可達50~60公里,比地鐵要快1倍[26],主要提供市中心與郊區新城間中長距離通勤服務。都市圈通勤鐵路與市區軌道交通服務對象和運行方式不同,不能互相替代,卻可互為補充。國際大都市都是先建都市圈通勤鐵路,然后再修市區地鐵。在郊區城市化初期就利用國家鐵路既有線改建發達的通勤鐵路網,由于其覆蓋面廣,長度是市區地鐵網的4~9倍。紐約有地鐵368 公里,而通勤鐵路長1632公里;巴黎有地鐵214公里,通勤鐵路1883公里;大倫敦有地鐵415 公里,通勤鐵路長達3071公里[22]。
我國大城市軌道交通體系的建設時序與國際大都市相反,先建市區地鐵,而都市圈通勤鐵路只有少數超大城市才剛起步建設,與國際大都市相比這是最大差距所在。如上海地鐵等市區軌交線長達567 公里,已居世界城市首位;但市域鐵路包括國家干線在內僅456 公里,而通勤鐵路只有1條56公里長的金山線。我國由于缺少發達通勤鐵路網,許多大城市都試圖建設市區地鐵的長距離延伸線到遠郊區,以加強城郊聯系(圖4)。在各類軌道交通方式中地鐵投資最大、速度最慢。按照市區地鐵制式建設到郊區的長距離延伸線需要巨額投資,但市中心區地鐵站點多、運速慢、運力飽和,即使花費巨資建成長距離延伸線也無法滿足市郊新城與中心城之間“1小時通勤圈”的快速直達客運需求。如上海以人民廣場為中心,軌道交通平均“1小時通勤半徑”只有20多公里(圖5),僅能覆蓋上海市域約1/4的空間。松江、嘉定等主要新城居民到市中心的軌交出行時間大多超過1小時,與私家車相比明顯缺乏競爭力[27]。

圖4 上海市域軌道交通規劃
因都市圈通勤鐵路建設嚴重滯后,目前我國大城市與郊區交通主要依賴高速公路。國際大都市的市中心區都建有發達的對外放射性通道,與郊區腹地保持緊密聯系。而我國大城市一般為“單中心+環形道路”的圈層式空間結構,城市道路網又以棋盤方格狀為主,由市中心直通郊區的放射性干道原本就不多,卻又高標準建設了多重包圍中心城的封閉性環行線,力圖用環行道路和環城綠帶等限制城市對外擴展。在重重環線阻礙下,城郊聯系的放射線難以直達暢通,大量次要通道都成為“斷頭路”,以致進出城壓力疊加在為數不多的主要放射性干道上,造成嚴重交通擁堵。北京、上海都建成長約1000公里的高速公路,但狹小擁擠的中心城卻不能承受郊區高速公路網導入的大量車流,只能限制私人汽車發展。而城郊聯系受阻又使得我國大都市人口、產業和城市功能高度集聚在中心城難以向外疏解,郊區城市化無法有效推進。如土地面積660平方公里的上海中心城2010年常住人口1132萬,在占全市1/10的土地上集聚了近一半的人口,人口密度達1.71萬人/平方公里[28],遠高于1萬人/平方公里的國際宜居城市標準。內環以內核心區人口密度更達2.99萬人/平方公里,明顯高于東京、巴黎等國際城市[29]。而在土地面積占全市一半以上的遠郊區,2010年常住人口只有520萬,人口密度僅1400人,還不到中心城的1/10(圖6)。北京也同樣如此,五環路以內中心城面積670平方公里,2010年常住人口968萬,在占全市僅4%的土地上集聚了北京近一半的人口。而六環以外土地面積14500平方公里,占全市86%;人口497萬,僅占全市25%;人口密度343人,只有中心城的2.4%[30]。

圖5 上海市現狀以人民廣場站為中心的軌道交通出行時耗等時圈分布資料來源:陸錫明,王祥.上海市快速軌道交通規劃研究[J].城市交通,2012(4).

圖6 201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密度三維分布圖資料來源:葛巖.上海市中心城現狀發展評價及規劃策略探討[J].上海城市規劃,2014(3).
在人口剛性增長壓力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建成區沿著一圈圈環行線向外圍邊緣區“攤大餅”式近域蔓延,而在蔓延到一定程度后又要建設新的環線。這種單中心城市空間結構的圈層越多,核心圈層的封閉性和內聚性就越強,市中心對外聯系就越發不便,其人口、產業和城市功能也就越難外遷,反而引致人流、車流向眾多城市功能集聚的中心城強烈聚焦,造成中心城人口密集、交通擁堵、房價高企、環境惡化等各種“城市病”。實際上這種“城市病”并不是“大城市病”,而是城郊二元結構顯著、人口和產業空間分布失衡的“封閉式單一中心城病”。東京人口規模遠超過北京、上海,卻能保持城市的高效運營,說明城市人口規模大并不必然導致“大城市病”。根治北京、上海等國內大城市“封閉式單一中心城病”的對策,只有借鑒東京等國際大都市發展的成功經驗,對城市的空間結構、交通網絡等進行脫胎換骨的全面改造,構建以放射性通勤鐵路為骨干基于現代化軌道交通體系的開放型、多中心、同城化大都市圈。大都市圈中心城的人口、產業和部分城市功能,可沿著發達軌道交通走廊疏解分散到各個城市副中心、郊區新城和都市圈其他城市,有寬松空間和優良環境能從容應對未來城市人口增長和服務功能提升的多方面挑戰。
三、都市圈通勤鐵路建設:中國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
目前我國正進入“大都市圈化”發展階段,到城市化成熟期有可能類似日本形成近百個200萬以上人口的大都市圈,其中30個大都市圈像東京、大阪、名古屋那樣人口可達1000萬~3600萬。大都市圈建設的關鍵性基礎設施,是構建核心城市緊密聯系周邊中小城市的通勤鐵路網。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通勤鐵路(不包括地鐵)總長4152公里[31]。以此計算,僅30個人口1000萬以上的大都市圈就需擁有長達4萬公里的通勤鐵路。扣除1萬公里可改造為通勤鐵路的既有鐵路(其長度已占全國既有鐵路1/10),到2030年城市化成熟期,我國至少需新建3萬公里通勤鐵路,這相當于全國現有鐵路網長度的1/3、城市軌道交通線網長度的10多倍。如從現在就開始建設通勤鐵路,到2030年每年需新建2000公里,約為近年鐵路建設規模的1/3多。我國城市地鐵建設造價每公里7億元,通勤鐵路造價在市區高架段每公里 3 億元左右、郊區 1 億元左右[32]。目前全國許多大城市都在大規模興建地鐵,并規劃建設到郊區的眾多長距離地鐵延伸線網以加強城郊聯系,投資大、效益低。目前北京、上海單個城市的地鐵長度,都已與日本東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的地鐵長度總和570公里[31]相當,而且還在繼續大規模擴建地鐵線網。我國建設3萬公里都市圈通勤鐵路網,可大量替代過度擴張、成本高昂的地鐵郊區延伸線,節省上萬億元巨額投資。
為適應我國進入“大都市圈化”發展階段的要求,未來10多年需大規模建設都市圈通勤鐵路。如北京已規劃建設1000 公里市郊鐵路,但“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表示,北京未來的城市圈一定會擴展到六環之外,市郊鐵路才是支撐這種發展的骨架。根據東京、紐約的經驗,規劃的市郊鐵路里程,應當從目前1000 公里擴展到 3000 公里至4000 公里”[33]。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有多方面綜合效益,是中國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
——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能大規模容納城市新增人口,高效推動我國城市化進程。2013年我國城鎮化率按常住人口計算為53.73%,城鎮常住人口7.3億;而以非農業戶籍人口占戶籍總人口比重衡量的真實城鎮化率只有35.93%,非農業戶籍人口僅為4.9億[34],有2.4億城鎮常住人口并未真正融入城市、享受市民待遇。這2.4億并未享受市民待遇的城鎮常住人口大體可分為兩類:約1.5億城鎮常住人口持有農業人口戶籍,在本地城鎮行政轄區范圍內由農村移居到城鎮;另一類是沒有本地戶籍的異地城市新移民,這部分非戶籍城鎮常住人口有9272萬人。2014年我國實行戶籍制度改革,取消農業與非農業戶口劃分,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較嚴控制大城市落戶規模,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戶籍改革后,一部分本地戶籍農業人口的城市化問題有望得到解決。然而在我國城鎮化率超過50%后進入大都市圈發展階段,遠離城市密集區的分散、孤立小城鎮以至中小城市人口增長有限,城市新移民的主流是遷入現代服務業發達、就業機會更多的大城市及其周邊城市密集區,9000多萬異地城市新移民的絕大部分就是如此,以后其數量還會持續增長。目前一、二線城市與三、四線城市房價兩極分化顯著,也反映了今后人口城市化的這一大趨勢。
由于我國大城市實行嚴格戶籍控制而且市區房價高企,大量城市新移民雖在大城市就業,卻難以購房入戶、融入城市,成為我國推進真實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難題。通勤鐵路引領的以大城市為核心、包括周邊眾多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大都市圈建設,能化解城市新移民“大城市進不去、小城市不愿去”的兩難困境,他們可在核心大城市就業,而在戶籍和房價門檻較低的周邊中小城市購房入戶。2015年中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一線城市房價都已超過30000元/平方米,而其鄰近的廊坊、蘇州、嘉興、東莞房價只有7000~12000元/平方米[35],戶籍門檻又遠低于一線城市。構建基于發達通勤鐵路網的北京—廊坊、上海—蘇州—嘉興、香港—深圳—東莞大都市圈,就有寬廣空間和優良環境不僅能讓數百萬非戶籍常住人口順利融入城市,而且有條件建成集聚效應可于東京相比的世界級大都市圈。都市圈中心城與遠郊區之間如果依賴地鐵和汽車交通,交通高峰期1小時有效通勤半徑不及30公里,則都市圈面積只有2800平方公里,如北京六環路以內面積僅為2282平方公里,2010人口1465萬[30]。而像東京都市圈那樣建設發達通勤鐵路網,可把中心城1小時有效通勤半徑延伸到50~60公里(紐約通勤鐵路服務半徑更高達80公里[36]),發達軌道交通主導的同城化大都市圈面積能達到8000~11000平方公里,要比基于地鐵和汽車交通的都市圈擴大3~4倍,可大量增加一、二線大都市中低價住宅供給,大幅降低限制人口城市化的“房價門檻”,其意義不亞于大規模保障房建設,都市圈容納人口也可成倍增長。北京—廊坊、上海—蘇州—嘉興、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四大都市圈現有1.1億人,今后人口如增長30%,就可容納全國1/10人口。未來城市化成熟期我國如果建成80個200萬~3600萬人口類似日本的大都市圈,可以容納8億人,占全國人口一半以上,高效推進城市化進程。加上發展其他各類城市,就可順利進入城市人口超過70%的城市化高級階段。
——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將有力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是今后相當長時期我國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城市化是我國最大內需所在,但農民工為主體的外來人口融入城市的真實城市化進程滯緩,他們以工人的生產方式在城市工作,他們的家庭卻以農民的生活方式在農村消費。農村分散化的居住和消費模式使得消費基礎設施遠落后于城市,以致億萬農民大量卻分散的消費需求難以得到充分滿足,最終只能將打工收入用于在家鄉建房,而農民工及其子女還要離家外出打工,這必然加大他們未來融入城市的成本,固化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和“三農困境”。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數億農民工及其家屬融入城市的真實城市化進程更嚴重滯后,他們不能充分消費其生產的產品,是造成我國長期以來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
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可以大幅擴張我國城市人口和產業集聚規模,高效推進城市化進程,有力拉動投資和消費需求。首先,我國到2030年新建3萬公里通勤鐵路,需投資6萬億元。而這6萬億元僅是撬動未來城市化巨大投資和消費需求的“杠桿”。“羅馬不是一日建成的”,我國如建設近百個人口200萬~3600萬人基于軌道交通的大都市圈,未來數十年就需巨額投資,并且有高效回報。大都市圈基于發達軌道交通網形成的多中心空間結構,能以低成本大幅度增加城市中心高端商務樓和郊區中低價住宅供給,大幅擴張產業和人口容量,根本遏制因人口過度集中于中心城造成的房價、地價不合理上漲,顯著降低營商和生活成本,吸引國內外企業和人才投資創業,都市圈中心城交通擁擠、房價高企等“城市病”都能得到根本治理。今后十多年我國最大宗的國內需求,是數以億計的大中城市新移民對中低價住房的消費需求。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能大幅度擴張大中城市中低價住房的有效供給。而億萬城市新移民的住房需求一旦得到實現,將對各類建材、汽車、電腦、手機、家電、日用消費品以及城市金融、商貿、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產生一系列關聯性消費需求,國內大量過剩產品和產能可以充分消化利用,因城市化發展長期滯后被抑制的巨大投資和消費需求將會得到充分釋放,從而促使中國經濟在未來相當長時期保持穩定增長。
——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可高度集約利用資源,顯著優化生態環境。人口集聚可以極大節約運輸成本。東京大都市圈人口規模與加拿大相當,盡管加拿大人口也集中在為數不多的幾個大都市圈,但其分布在從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的數千公里廣闊地帶,運輸成本和能源消耗遠高于東京大都市圈。人口集聚可以集約利用資源。我國200萬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人均用地要比20萬以下人口的小城市少120平方米[37]。與建設3000個分散的萬人小城鎮相比,1個3000萬人的大都市圈無論土地、能源或其他資源都可以得到高效利用。“東京大城市圈的總人口高達3000多萬人,這是以汽車為交通工具的城市所不能企及的人口高密度”[38]。只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圈,才能支持大運量軌道交通網的低成本建設和高效率運營。如果我國分散發展小城鎮以至中小城市,只能過度依賴耗能高、占地多、污染大、交通堵的汽車交通,建設連接眾多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密集高速公路網,不僅大量占用土地,更會強化能源、耕地、環境瓶頸對國家發展的緊約束。而基于軌道交通的多中心大都市圈,比依賴汽車交通的城市能夠顯著優化城市生態環境,是低碳環保、集約高效的城市化發展路徑。
大都市圈人口和產業集聚,現代服務業高度發達,可容納大量勞動力就業,有利扭轉我國因城市化滯后造成第三產業發育不良、非農勞動力過度集中在制造業以致產能嚴重過剩的結構失衡局面。相對制造業而言,現代服務業低消耗、低排放。如京津冀地區建成北京、天津、石家莊等以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產業的大都市圈,就可以大幅壓縮河北畸形發展的鋼鐵、建材、能源等高消耗、高排放制造業,根治嚴重霧霾痼疾,還可大量節省工業用水。城市的承載力只是科技進步的函數,大都市圈有強大科技實力,隨著科技的進步,約束城市發展的“城市病”和資源瓶頸都可不斷得到治理,包括京津冀面臨的水資源短缺問題,也能通過產業結構調整、降低海水淡化成本和實施水價改革而得到根本解決。
——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可以極大提升我國城市的集聚力、輻射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強力帶動全國經濟轉型升級。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是國家經濟增長極、創新發展引擎,然而近年來發展動力明顯不足,經濟增速落后于大多數省區和中心城市,GDP占全國比重持續下降。上海是長三角以至長江經濟帶的“龍頭”,2000年上海GDP所占比重分別為20.5%、11.2%,到2013年已降至15.7%和8.3%。大都市以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等知識、技術密集產業為主,人才是首要資源。北京、上海增長乏力,根源在創新力不強,實質是人才集聚力和吸納力不足。北京是國家科教中心,“985”和“211”高校均居全國首位。但1999年大學擴招以來,全國在校生人數增加了5.5倍,北京只增長1.8倍[17]。擴招前北京高校在校生人數居全國各省市第2位,到2013年已降至第20位,甚至落后于多個中西部省區及二線城市,一流科教資源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而戶籍準入門檻過高,又限制了高校畢業生及其他各類人才落戶北京、上海。上海創新中心張江國家高科技區13萬科技人員中,一半以上都沒有上海戶口,以致人才流失嚴重[39],優質創新資源未能得到優化配置。北京要建設“世界城市”,上海要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首先要大規模集聚創新創業人才。我國每年已有700萬大學生畢業,原有的“人口紅利”已轉化為“人才紅利”,他們將成為今后城市新移民的主體,也是創新創業的主力。我國建設近百個大都市圈可以大量集聚國內外創新資源和創業人才,也可分流北京、上海等一線大都市過大的人口集中壓力,逐步創造條件取消對人才流動的戶籍制度限制,讓創新創業者能夠安居樂業,讓經濟增長的最寶貴資源——人才資源得到優化配置,促進大都市圈創新發展。
東京都市圈是世界經濟實力最強的大都市,但東京都的GDP僅占東京都市圈“一都三縣”的1/2。東京都正是與周邊橫濱、川崎、千葉等眾多城市構建了同城化大都市圈,其GDP占日本比重高達1/3。上海如與鄰近蘇州、嘉興構建同城化大都市圈,目前GDP已達3.8萬億元,是上海單體城市的1.7倍,占長三角和長江經濟帶比重可上升到27.5%和14.6%[17],遠高于浦東開發以來“單體上海”的占比峰值。升級版的“大上海”將大幅提升區域經濟輻射力,有力引領長江經濟帶發展。位于長三角平原的滬蘇嘉大都市圈發展條件優于東京都市圈,現有土地面積18700 平方公里,人口3900萬,規模大于東京都市圈,而人口密度卻低于東京都市圈,且高鐵、城鐵和地鐵系統均不亞于東京都市圈,再補齊通勤鐵路“短板”,發展潛力將優于后者。如果滬蘇嘉大都市圈人口密度達到東京都市圈水平,到2030年后我國城市化成熟期就可承載約5000萬人口,比現在增長近30%,大體相當于過去10多年的人口增幅,成為世界最大都市圈。目前滬蘇嘉大都市圈人均GDP已近2萬美元,未來人口規模如達到5000萬人,經濟實力有可能接近甚至超過現居全球首位的東京大都市圈。全球化時代的國際競爭聚焦于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帶,東京都市圈人口占日本1/4,卻集中了全國最重要的經濟實力與核心競爭力。中國未來如能建設10個類似東京的世界級大都市圈,必將極大提升國際競爭力和全球影響力。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方向是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大都市圈是現代服務業和高科技產業的大規模集聚地,建設大都市圈能大幅提升現代服務業和高技術產業占GDP比重,強力帶動全國經濟轉型升級。
目前我國正處在從城市化中級階段向高級階段過渡時期,也處于從傳統工業化經濟向以現代服務業和高新科技產業為主導的創新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通勤鐵路引領的大都市圈建設,能大規模集聚國內外創新資源和創業人才,從供給側優化配置我國經濟轉方式、調結構最急需的高端生產要素,極大提升我國城市的集聚力、輻射力、創新力,有力促進現代服務業和高新科技產業發展,是經濟穩增長、擴內需的強大引擎,是塑造國家競爭優勢的利器和重器。為重塑國家競爭優勢,近年我國出臺多個經濟區規劃、城市群規劃,但未明確提出構建經濟區資源配置樞紐和城市群發展核心——大都市圈的基本目標,往往難以找到抓手、取得突破。如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協同發展的基礎是交通一體化,而重心就在構建基于通勤鐵路網的北京(中心城)—通州-廊坊、上海—蘇州—嘉興、香港—深圳—東莞、廣州—佛山等跨行政區大都市圈,以通勤鐵路為載體的人員交流引導都市圈同城化經濟社會整合,進而引領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要求:“特大城市要推進中心城區功能向 1 小時交通圈地區擴散,培育形成通勤高效、一體發展的都市圈”,但尚未明確提出都市圈建設的發展目標與總體規劃。鑒于大都市圈建設對我國未來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而國內大都市圈理論研究與實際建設均嚴重滯后,因此需明確界定大都市圈的概念內涵,完善大都市圈人口和經濟社會統計體系,確立大都市圈建設在全國城鎮體系發展中的重心地位與核心作用,提出我國城市化新階段發展大都市圈的長遠目標、總體規劃和實施對策。當前,亟待制定主要大都市圈規劃和通勤鐵路網規劃,盡快列入我國“十三五”發展規劃,并列為“十三五”時期的建設重點,不失時機邁向經濟轉型升級和城市化發展的新階段。
參考文獻:
[1]李璐穎.城市化率50%的拐點迷局——典型國家快速城市化階段發展特征的比較研究[J].城市規劃學刊,2013(3):43- 49.
[2]王旭.美國城市發展模式: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區化[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3]謝文蕙等.城市經濟學[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6.
[4]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1 Re-vision[EB/OL].http://esa.un.org/ unpd/wup/ind-ex.htm.
[5]《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編委會.2001~2002中國城市發展報告[M].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
[6]Paul R.Krugman.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99(3):483- 499
[7]世界銀行,胡光宇等譯.2009年世界發展報告:重塑世界經濟地理[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
[8]許學強等.城市地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9]韋偉等.日本都市圈模式研究綜述[J].現代日本經濟,2005(2):40- 45.
[10]MGI.Preparing for China’s Urban Billion [EB/OL].http://www.mckinsey.com/insights/mgi/ research/urbaniz-ation/preparing_for urban_billion in_china.
[11]張善余.中國人口地理[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1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平成22年國勢調查.日本の人口[EB/OL].http:// www.stat.go.jp/data/kokusei/2010/pdf/ waga2.pdf.
[13]汪海.構建以京滬港渝為核心的中國城市體系[J].城市發展研究,2006(2):118-122.
[14]克里斯塔勒.德國南部中心地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15]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
[16]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2):52-57.
[17]國家統計局.2014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5.
[18]史育龍等.戈特曼關于大都市帶的學術思想評介[J].經濟地理,1996(3):32-36.
[19]何志揚.城市化道路國際比較研究[D].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20]張良等.日本首都圈規劃的主要進程及其歷史經驗[J].城市發展研究,2009(12):5-11.
[21]馬述林.東京城市快速軌道交通發展模式及啟示[J].綜合運輸,2009(3):78- 84.
[22]陳孟喬等.國外主要城市市郊鐵路發展現狀分析及啟示[J].綜合運輸,2010(3):77- 81.
[23]陸錫明等.上海交通戰略規劃研究[M].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12.
[24]彭純.2014年世界十大宜居都市排名日本3城獲選[EB/OL].新華網http://japan.xinhuanet.com/2015-05/19/c_134251094.htm
[25]周詡民等.城市軌道交通市郊線的功能及技術特征[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07(8):1-5.
[26]楊朗等.日本東京都市圈的交通發展戰略[J].綜合運輸,2005(10):75-78.
[27]陸錫明等.上海市快速軌道交通規劃研究[J].城市交通,2012(4):1- 8.
[28]馮經明.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實施評估若干問題的戰略思考[J].上海城市規劃,2013(3):6-10.
[29]葛巖.上海市中心城現狀發展評價及規劃策略探討[J].上海城市規劃,2014(3):118-122.
[30]趙暉等.北京城市職住空間重構及其通勤模式演化研究[J].城市規劃,2013(8):33-39.
[31]高木清晴.日本城市軌道交通概況[J].城市軌道交通研究,2004(4):61- 64.
[32]秦永平.我國市郊鐵路規劃和建設中的主要問題與建議[J].鐵道工程學報,2014(3):6-13.
[33]耿諾等.代表建議市郊鐵路規模需擴至3000公里[N].北京日報,2014-01-18.
[34]國家統計局.2014中國人口和就業經濟統計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4.
[35]中國指數研究院.2015年6月中國房地產指數系統百城價格指數報告[EB/OL].中國指數研究院網站http://fdc.fang.com/report/9316.htm
[36]魯永辰.市郊鐵路主要技術標準的選擇[J].鐵道勘察,2014(6):77- 80.
[37]王放.中國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
[38]中國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地區經濟司,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城市化:中國現代化的主旋律[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
[39]魏一平、徐木子.為了一個上海戶口[J].三聯生活周刊,2009(10):91-95.
(本文責編:王延芳)
Construction of Commuter Rails in Metropolitan Areas:A Powerful Engine for Stable Growth and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of China’s Economy
WANG Hai
(JiangsuProvincialAcademyofSocialSciences,InstituteofEconomicResearch,Nanjing210003,China)
Abstract:As indicated by international urbanization experience,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of a country is a process in which the spatial aggregation of population increases continuously.Most urban residen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aggregated in metropolitan areas where single metropolises develop synchronously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surrounding cities on the basis of developed traffic networks.With an urbanization rate of over 50%,China has entered a development phase of “metropolitan areas”.The key infrastructur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is commuter rail networks closely connecting metropolises with small and medium-sized surrounding cities.The integrated construction of metropolitan areas guided by commuter rail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real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vigorously trigger investment and consumer demands,as a powerful engine for the growth stabilization and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of Chinese economy.
Key words:metropolitan area;commuter rail;urbanization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9753(2015)12-0075-13
作者簡介:汪海(1955-),男,江蘇南京人,江蘇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區域和城市經濟。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大都市帶建設與中國經濟發展的空間非均衡戰略研究”(13BJL097)。
收稿日期:2015-07-05修回日期:2015-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