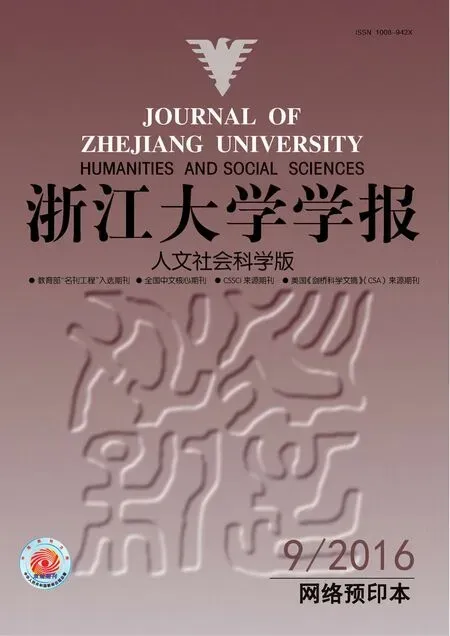從現象學到生活藝術哲學
王 俊
(浙江大學 哲學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從現象學到生活藝術哲學
王 俊
(浙江大學 哲學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作為生活藝術的哲學”已成為當代歐洲思想界的一個熱點,對哲學的這種理解和實踐與20世紀的現象學運動密不可分。無論是胡塞爾的生活世界,還是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都是以關懷人類生存、合理安頓人與世界的關系為根本動機的。現象學對理論和實踐關系的倒置、對在場和缺席關系的倒置、對確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為生活藝術哲學做了充分的理論奠基,由此出發,生活藝術哲學在哲學實踐、審美泛化等向度上得到了發展。現象學的“小零錢”精神、“前科學”立場、關注意義構建、重回古典哲學的精神和實踐,都成為生活藝術哲學的基本立場。
現象學; 生活藝術哲學; 生活世界; 哲學實踐; 補償; 審美泛化
一、 現象學的根本動機
在現代哲學中,面對傳統唯心論體系的崩潰和自然科學的蓬勃興起,尼采、柏格森、狄爾泰等哲學家把哲思的目光轉移到生命/生活這個主題上。胡塞爾的老師弗朗茨·布倫塔諾就明確提出,哲學的任務就在于回復到生活本身,通過諸如“內觀”和“明見性”這樣的生命實踐和情感性體驗為當代生活、認識論和倫理學重新建立統一的形而上學基礎。這個基本的哲學理念在胡塞爾那里得到了延續。
在胡塞爾看來,現象學所要面對和亟須克服的乃是現代化文明的危機,這種危機是由自然科學意識形態所帶來的。在認識論的層面上,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的確立有賴于一種極端的還原論和客觀主義,即將世界置于一種客觀化、均質化的解釋框架之中,并且將人類生活的意義和質感從這個客觀的解釋框架中徹底排除,以便對客觀世界局部事實性進行實證性研究,或者消除主觀視域,實現一種抽象的客觀主義普遍理論形式。這種科學主義的做法導致了“生活意味的喪失”或者“意義的空乏”,因而無法從一種人性化角度為人類文明提供一種可延續的、和諧的思想基礎。
胡塞爾認為,現代自然科學的意識形態化實際上是理性的僭越,以消除主體質感和割斷主體生活關聯為代價最終獲得的并不是一勞永逸的嚴格科學世界,而只是背離人性并將導致人類生活危機和文明沒落的科學意識形態。隨著對前科學生活經驗的排除和對經驗世界主體相關性的抽離,自然科學的客觀主義抽象形式逐漸被絕對化,占據了普遍真理的位置,進而規定了人類的一切生活和認知方式,這導致了客體存在的有效性被必然化和普遍化,客觀的自然世界被賦予認識上的特權,心靈和主體的意義世界則被矮化和遺忘。自然科學的客觀主義意味著絕對知識客觀性的現代性理想:“科學有效的東西應當擺脫任何在各自的主觀的被給予性方面的相對性”,“科學可認識的世界的自在存在被理解為一種與主觀經驗視域的徹底無關性”[1]38。對客觀性知識的追求意味著一個獨立的、割斷主觀視域聯系的認識過程。
現象學的創始人憂心忡忡地看到,現代化危機造成根源層次上的主體相關性和意義構建被遺忘了,這就是現代歐洲人的危機或“病癥”:一種原本植根于生活世界和生活經驗的科學、哲學和生活的統一意義喪失了。自然科學意識形態化,技術科學成了解釋世界的唯一普遍方式,而人的主體性在面對世界時本應具有的奠基地位則相應地消失了,人與世界的關系被倒置,這是現代人類精神世界空虛和責任匱乏的最重要根源,是人類理想生活方式不斷墮落的根源。如何恢復人與主體的尊嚴,從而恢復哲學在當代的意義,為重建和諧的人類生活進行指導,這恰是胡塞爾思想道路最初的出發點。
克服意義的空乏并恢復生活意義是胡塞爾現象學的基本動機。在這里,意義首先被理解為一種普遍化、發生性的指引關聯,胡塞爾現象學中最為核心和源初的指引關聯類型就是意向性。意向性結構和意向性構建先于主體-客體二元關系的構建過程,恢復了心靈的豐富維度以及心靈與世界的平等關系。通過意向性及其構建分析,胡塞爾將哲學理解成一門“發生現象學”,不再將哲學理念看作柏拉圖式的無時間之物,而是嵌在生活世界之中的可再造的精神過程。在發生學視角下,指導生活實踐的規范性或者倫理學也被引入了生活世界的歷史維度,規范的建立并非與其產生的歷史毫無關系*正如Ferdinand Fellmann所指出的:“生活世界的明見性……不僅對對象化的認識,而且對道德感受都扮演了一個建設性的角色。它被感受為生活的定位模式,這一模式在生活的展開結構中形成并且為道德行為訂立規則。”見F.Fellmann, Philosophie der Lebenskunst zur 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Verlag, 2009, p.31。。置身于時間性和世界性中的指引關聯最終指向一個普全的視域,也就是生活世界,視域總是以非課題的形式為對象化的認識奠基,并以發生的方式決定了我們生活中一切課題化的行為和抉擇。在胡塞爾看來,作為關聯域的生活世界具有的這種在先的奠基性、包含的可能性及現實性轉化才是現象學所要關注的話題。
換句話說,胡塞爾設想現象學所要把握的乃是以下內容:將對一個對象的存在設定把握為在指引關聯的境域中的設定、在關系中的設定,或者說,通過課題化的行為(意向性結構)把握隱含在其背后的非課題化境域乃至生活世界*對此胡塞爾說道:“人們也可以說:一切存在物都是關聯的,它只處于與他者的關系之中。或者從設定的方面說:一切存在設定同時就是‘設定于關系之中’。在這里,‘設定于關系之中’……是說:對確定的或不確定的對象性而言,潛在的共同設定以境域的形式進行,并且由此出發,這種共同設定通過意向相關項的意義在意識中被擁有,這種意義就是:在判斷背后能夠展現境域,能夠預先找到關聯體和關系。”見E.Husserl, Die Lebenswelt: Auslegungen der Vorgegebenen Welt Und Ihrer Konstitution: Texte Aus Dem Nachlass(1916-1937), edited by R.Sowa,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p.5。。因此胡塞爾斷言,“存在的世界無外乎就是存在有效性的關聯性(Relativit?t)”[2]724。他在這里強調的是存在者之間的關聯性、相關性,沒有一個絕對的、與其他存在者無關的存在者,存在的意義就意味著關聯性,生活世界就是關聯域的大全——這就是現象學最終要揭示的東西。舉例來說,意識現象學就不能僅局限于理論化的自我反思,還應包含實踐的自身狀況,意識的建構只有基于主體和交互主體的實踐和價值感受這一關聯域才有可能實現。
更進一步地,這種關聯域的承擔者則是時間中的個別實體,對這種“自然關聯域”的研究是區域存在論的任務*胡塞爾說:“顯然人與人之間的每一精神關系,以及在較高層階個人的精神性中賦予此精神性以自然界時空存在者所構成的一切,都可還原為心理物理層次上思考的彼此之間的自然關聯域。純粹意義上的主體間精神性在世界經驗中不是自為的,而是世界性的,因此通過其個別的移情作用,借助于個別實在軀體內一定的基礎,而成為自然時間性的。”見[德]埃德蒙德·胡塞爾《現象學的構成研究——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2卷,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19頁。。因此胡塞爾指出,無論是在普遍存在論還是在區域存在論中,人與物、人與人、物與物之間的關聯構成了世界本身,而且兩個領域之間是統一的。現象學要關注的生活世界領域是一個介于經驗科學(心理學)和邏輯學之間的領域,可以以結構-功能的方式被描述,胡塞爾稱之為“超越論的經驗”或者“生活世界的科學”,人們也可稱之為“前科學”,這個第一人稱視角的領域是一切規范性、客觀認識和自我認識的源泉。在這個領域內,發生性、可能性和偶然性既未被排斥,其被說明的方式也有異于經驗科學。這個“元-實踐領域”也是生活藝術(Lebenskunst)作為一種哲學形式被定位于其間的領域。
海德格爾的生存論現象學始終是以人的生存實踐為關注焦點的。在《存在與時間》中,他的初衷就是用生存取代傳統哲學中實體化的、現成的“主體性”,實現對傳統形而上學的“翻轉”。海德格爾將發生性的生存實踐看作存在的基礎,在《存在與時間》中,此在的本質是生存、是“去存在”,因此要把握人是什么,必須從人的存在即生存活動來把握。由此,基于人在世界內的生存經驗,海德格爾對真理進行了存在論的闡釋,他認為“揭示”(Entdecken)的“生存論存在論基礎”指向“最源始的真理現象”,即“作為此在的展開狀態(Erschlie?endsein des Daseins),而此在的展開狀態中包含有世內存在者的揭示狀態”[4]256。也就是說,“真理本質上就具有此在式的存在方式,由于這種存在方式,一切真理都同此在的存在相關聯”[4]261。真理與世內存在的關聯性并不意味著真理的虛無或主觀相對性不是純粹經驗層面上的,恰好相反,“只因為‘真理’作為揭示乃是此在的一種存在方式,才可能把真理從此在的任意性那里取走。真理的‘普遍有效性’也僅僅植根于此在能夠揭示和開放自在的存在者”[4]261。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完全是以發生現象學的形式探討“元-實踐”層面上的世內生存經驗。
盡管海德格爾本人謹慎地用Dasein(此在)和Existenz(生存)取代Leben(生活、生命)這樣的術語,以避免人類學和日常化的嫌疑,但是他并不排斥一種作為生活藝術的哲學。在《關于人道主義的通信》中他說道,并不存在普遍的規則可以指導“經歷了從生存到存在的人應當如何合乎命運地生活”[5]353,在這里我們找不到一種指導生活的普遍先天規則,而是只有與實踐密不可分的技藝,古典意義上的技藝。在1928年題為《以萊布尼茲為起點的邏輯學的形而上學基礎知識》的講稿中,海德格爾提到了“生存藝術”(Existierkunst),亦即在人生有限性的條件下生活行為的展開過程[6]201。這里所涉及的不是盲目的實踐行動,也不是純粹理論的自我反思,而是既與生存經驗纏繞在一起,又能指導生活的生活藝術。
在海德格爾看來,理論乃是實踐活動的一種形式,因此,“理解”也應當首先被把握為一種行為模式,人的此在就是“在其存在中圍繞此存在自身進行的”存在過程。即便海德格爾有意識地將基礎存在論與人類學區別開來,但在《存在與時間》所勾勒的與傳統的實體形而上學針鋒相對的動態化存在模式中,存在總是在“操心”(Sorge)、“能存在”和“自身領會”等語詞描述的狀態中獲得其經驗化-實踐化的現實化過程。因此總的來看,海德格爾的此在分析最終導向的是更本源、更貼切的自我認識,是開啟存在意義的實踐路徑,在生活藝術的意義上可以被解釋為“自我操心”。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并非要得出任何無涉于具體生存過程的絕對律令,也不關注純粹形式的理論體系或者道德規范性,甚至他對實踐生活過程的關注也不是康德意義上的實踐理性優先,而是對世內生存經驗領域的重視和回歸。
在傳統的主體形而上學中,人在本質上被看作表象著的理性主體,客體的存在只有通過主體的表象才被確定,而數學和計算方法加強了主體的這種自我確信(Ichgewissheit),從而造成了理性統治的假象和存在者的抽象確定性。這種普遍化的計算理性在海德格爾那里被活生生的此在經驗、真理的世內發生特別是時間性和歷史性的引入所解構,晚期海德格爾尤其注重存有的非現成性和歷史性,以消解傳統哲學中習慣談論的存在的必然性。他說:“作為本-有(Er-reignis)的存有(Seyn)本身首先承荷著每一種歷史,并且因此是絕不能得到計算的。”[7]253存在者進入存有之中,“在其中非本質作為某個本質之物而起支配作用”,“并且把歷史帶入其固有的基礎之中”[7]254。歷史性如此通透地貫徹到存有之中,以至于“基礎存在論”的論述本身都充滿了偶然。“存在問題唯一地只關乎我們的歷史的這個準備者的實行。《存在與時間》之初步嘗試的全部特殊‘內容’、‘意見’和‘道路’都是偶然的、可能消失的。”[7]253-254
順應19世紀以來整個歐陸哲學對生命實踐話題的興趣,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構想特別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論現象學在多個向度上重塑了當代的哲學形態,扭轉了傳統形而上學對世界和存在的理解,比如對理論和實踐關系的倒置,對在場和缺席關系的倒置,對主題化和非主題化的倒置,對確定性和可能性的倒置,對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倒置,等等。對存在過程的關注,重視動態化、時機化、具體的世內生存,反對教條化和抽象化,恢復人之生存本然意義,將世界和人的生存視為一種蘊含了普遍和個別的關聯域,這些都是現象學哲學所追求的目標。現象學哲學讓我們回到事實和生活本身,回到實踐本身,生活中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因此得到了捍衛,實踐層面上的生活常識因此得到了捍衛。由此,曾經在弗萊堡跟隨胡塞爾和海德格爾學習的九鬼周造(Kuki Syuzou)就明確地把他自己的思想稱為“偶然性哲學”,就絕非是偶然的。
二、 從捍衛偶然性到哲學實踐以及生活藝術的美學擴展
當然不是只有非歐洲傳統的九鬼周造透過現象學看到了偶然性在當代哲學中的價值,從梅洛-龐蒂到奧多·馬奎德(Odo Marquard)都致力于在哲學上捍衛偶然性。從現象學對傳統哲學理念的倒置到捍衛生活領域的偶然性,再到哲學實踐的嘗試,這是生活藝術哲學極為重要的思想路徑和來源之一。
現象學的基本動機和思路在梅洛-龐蒂那里從“身體場”的角度得到了強化。他從身體切入,試圖由此更加準確地描述意識與不可窮盡的世界之間的關系。在梅洛-龐蒂看來,正是知覺這種前意識現象將自我與世界聯結在一起,知覺使一切對象化構建活動成為可能,它構成了對象化認識活動的意義基礎。這一想法的基本驅動力來自于胡塞爾的生活世界和視域理論,以及海德格爾對存在域、操勞(Besorgen)、上手狀態(zuhanden)等的表達。
梅洛-龐蒂秉承了胡塞爾對意向性的構想,將知覺與世界之間的聯系(意向性關聯)闡釋為意義的本質所在:意義不是一個主體有意識地賦予其對象的現成之物,而是一種關系性的呈現,事物正是在關系之網中顯現出其本真的意義。被知覺之物與知覺主體之間有一種前邏輯和前主題化的統一性,這正是現象學要討論的話題。這種在先的統一性在胡塞爾那里是生活世界和視域,在海德格爾那里是存在的時機化、動態化表述,而梅洛-龐蒂則通過身體對之進行了巧妙的說明:知覺和意識基于身體,因而對象物也是基于身體的,“物體是在我的身體對它的把握中形成的”,因此“物體不可能與感知它的某個人分離,物體實際上不可能是自在的”[8]405。與之對應的,主體同樣“應該首先有一個世界,或在世界上存在,也就是在自己的周圍應該有一個意義系統,其對應、關系和分享不需要被闡明就能被使用”[8]173。
與胡塞爾一致,梅洛-龐蒂也認為意義就是世界之中的關聯關系,而且是在不斷建構中的關聯關系,人就是“關系的扭結”*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的結尾引用了圣·埃克絮佩里的話:“你寓于你的行為本身中……人只不過是關系的扭結,關系僅僅對人來說是重要的。”見[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71頁。。所以意義是不斷生成的,而非絕對的,“存在”同樣也不可避免地只能作為事件歷史性地存在。在此,梅洛-龐蒂同樣將現象學討論引入歷史性的維度,意義作為關系不斷地被構建,處于生成之中。因此,存在和真理都是歷史性的,意義的本真到場也是歷史性的,沒有絕對的真理,也沒有絕對的存在。存在的歷史性和非絕對性并不是存在的缺陷,因為世界在存在論層面上就是偶然的,正是這種偶然性而非必然性才是我們認知和生活的基礎——這是梅洛-龐蒂從現象學方法中得出的重要結論。他說:
世界的偶然性不應該被理解為一種微不足道的存在,一種在必然存在的結構中的缺陷,一種對合理性的威脅,也不應該被理解為應通過發現某種更深刻的必然性而應盡早解決的問題。這就是在世界之內的實體化的偶然性。存在論的偶然性、世界本身的偶然性是根本的,是最初作為我們真理概念的基礎的東西。[8]499-500
在生活意義的層面上對偶然性的捍衛源自現象學,而在漢堡的哲學家奧多·馬奎德那里,偶然性則成了他整個哲學的核心話題。馬奎德接受了海德格爾的存在分析,在對德國唯心論尤其是黑格爾的哲學進行反思批判的基礎上,將哲學和真理的根基置于歷史性的生活經驗之上,在哲學上為生活的偶然性辯護。他說,偶然性并非“一個不幸事件”,而是“我們歷史的規范性所在”[9]131,我們基于偶然而存在。由此他提醒人們不要受到傳統的本質哲學或絕對化哲學的迷惑,以及獨斷論和哲學烏托邦的迷惑,他的偶然性哲學為技術時代的現代人生活提供了一幅樂觀的圖景。現代人要重塑人性的生活,就要逆轉自亞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學傳統。他說:“誰尋求開端,誰就要做開端;誰要做開端,誰就不想做人,而是想做絕對。因此,現代人為了人性考慮,在拒絕成為絕對的地方與原則性、始基告別。”[9]77在馬奎德那里,生活的偶然性和可能性、人的有限性、世界的歷史性都構成了我們無可回避的現實,由此他反對對世界、存在和自我的絕對設定,反對“人的絕對化計劃”。從理念上,他秉承了整個現象學傳統特別是海德格爾在這一論題上的基本思路,并將之推向一個極端。
馬奎德的偶然性哲學深刻洞察到了人生和世界的有限,甚至連那種致力于破除絕對設定的懷疑本身也是有限的,普遍懷疑是非人性的,所以他主張一種“有限的懷疑論”,基于一種日常性贊同的懷疑。懷疑只是告別脫離生活的原則性,而不是摧毀一切生活的根基,懷疑論者“知道,在那里,人們知道什么——在通常情形和習以為常的狀態下。懷疑論者甚至也不是那些根本無知的人,這些人只知道非原則性的東西:懷疑論并非無可節制地神化,而是和原則性告別”[9]17。
他對偶然性和有限性的關注使他的哲學不像胡塞爾那樣追求普遍和嚴格,也不像海德格爾那樣在存在論層面上激情洋溢,馬奎德的思想更多的是嘗試在實踐和人類學層面上為我們的生活提供具體的指導。在他看來,今天精神科學的作用并非如胡塞爾所說的是為一切科學奠基,也不是海德格爾所熱衷的對傳統形而上學的批判,而是補償現代技術給我們的生活世界造成的損失。他以樂觀的態度面對生活的偶然性,與之相一致地,他也并沒有對現代技術的飛速發展表現出深切的憂慮和極端的批判,相反,他甚至認為恰好是現代技術使我們的生活更加可靠,大部分對技術的恐懼都是人類夸張的幻覺而已*1986年12月馬奎德在《時代》周刊上發表了一篇題為《失業的恐懼》的文章,討論切爾諾貝利核泄漏事件。他認為,對核戰爭和生態危機與日俱增的恐懼并沒有現實根據,或者說,只是恐懼的幻覺。現代科技使人們的生活更加可靠,因而釋放了人基本的人類學恐懼。這種類似于失業的恐懼通過幻想任意發展,引發人們對災難的神往。此文當時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參見I.Breuer, P.Leusch & D.Mersch, Welten im Kopf, Hamburg: Rotbuch Verlag, 1996, p.181。。因此,現代性并不意味著人類命運的災難性深淵,反而是相對可靠的生存條件和無危機狀態。
以補償(均衡)為目的的哲學實踐及溫和樂觀的基調使馬奎德的哲學介于后現代的多元相對主義和傳統的普遍主義之間,他追求現代世界中的“多元化平衡”,并且將這種補償的嘗試視為指導個體的實踐策略,指導人們在當下如何應對技術時代令人目眩的變化以及如何抉擇陷于決定論和反決定論之斗爭的社會政治形態,由此將哲學從理論引入現實層面的生活實踐。因此,他將哲學首要地理解為一種與生活密切相關的哲學實踐,甚至直言哲學就是一種“定位服務職業”。在某種意義上他恢復了哲學的古典意義,在古代“生活咨詢很容易就屬于哲學,而哲學學園首先肯定不是學院式研究機構,而是生活藝術的練習場所”。在馬奎德看來,“哲學思維并不意味著建立一座理論大廈,而毋寧是遵守倫理-實踐的準則”,因此,“哲學思維對他而言,就是訓練自己和他人如何生活的藝術”[10]193。
馬奎德的學生阿亨巴赫(Gerd B.Achenbach)進一步踐行了哲學實踐的概念,并于1981年創立了“哲學實踐學院”,將哲學實踐定位為職業化的哲學的生活咨商,強調了作為思考著的人的哲學家的角色。他說,“在哲學實踐中我們并非被要求作為哲學的教師,而是作為哲學家”[11]65。“哲學的集體架構就是哲學家,并且哲學家作為一種情境中的指導行動,就是哲學實踐。”[11]14與海德格爾和馬奎德一樣,阿亨巴赫同樣強調哲學的首要任務是實踐,而非理論。“哲學實踐是一個自由的對話。它……并不規定哲學命題……不給出哲學洞見,而是將思想設定在活動之中:哲思著。”[11]32與治療對象一同哲思,并不是將接受治療者的情況歸入某一類預先給定的問題或解決范式,而是深入到作為個體的人之中,尋找他精神生活中的阻滯并且給出哲學上明智的生活定位建議。當代的哲學咨商實踐力圖成為幫助現代人擺脫生活困境的一種矯正方式,亦即“哲學治療”。哲學實踐的嘗試一方面重拾了哲學的古典形態,亦即哲學在蘇格拉底、智者學派和斯多亞派哲學中的形態,在那里哲學是作為生活藝術被傳授的;另一方面,其重要思想來源之一則是現象學哲學,哲學實踐從現象學出發從而重視生存和實踐,重視偶然性和可能性,把哲學理解為指導生存實踐的技藝。
進入21世紀,作為生活藝術的哲學在歐洲有了全新的拓展。首先,作為哲學實踐的哲學咨商或哲學治療仍然在不斷發展,除了阿亨巴赫,達姆施塔特的現象學家伯梅(Gernot B?hme)也開設了哲學實踐學院,開展哲學治療,為現代生活中個體的心理迷失、精神壓力和抉擇困境提供幫助。除了作為心理疏導方式的哲學治療或哲學咨商之外,當代生活藝術哲學開始廣泛地與美學聯系在一起,通過生活美學或者審美生活化擴展了生活藝術哲學的內涵和外延。生活藝術哲學不僅是治療和糾正活動,同時也是圍繞人類生存的富有建設性的意義建構活動。這種美學嘗試中極為重要的切入話題就是身體,身體哲學與修煉實踐成為當下生活藝術哲學的重要論題,特別是引入非歐洲的冥想或修煉方式,使之更具有多元化、全球化的特征。
當代生活藝術哲學通過“生活美學”或者“審美生活化(審美泛化)”的概念,將美學作為切入點。耶拿的韋爾施(Wolfgang Welsch)提出了“審美泛化”的概念,他說我們現代社會正在經歷一場美學復興,把都市的、工業的和自然的環境整個改造成一個超級的審美世界。首先,在物質層面發生了錦上添花式的日常生活表層的審美化,享樂、娛樂和廣告美學深刻影響了整體的文化形式和我們的生存方式;其次,在非物質層面,則是更深一層的技術和傳媒對我們物質和社會現實的審美化:技術改變材料,新材料廣泛運用,通過傳媒對現實進行重構,這種審美構建能力深刻影響到當下的人類生活;再次,倫理道德審美化,主體形式和生活方式的美學甚至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道德的缺失;最后,彼此關聯的認識論的審美化[12]。如果說哲學治療的定位服務致力于在認識論和價值論的層面上幫助人們獲取更加完善的知識和自我知識,進而對人生實踐和自我發展做出明智的定位和選擇,對世界和生活進行整體性理解和解釋,彌合自我與世界的裂痕,那么在審美泛化的趨勢下,生活藝術哲學及其美學實踐則是以指導審美、指導藝術營造的方式介入現代生活,為“美學人”(homo aestheticus)的消費、健身、自我包裝、日常消遣、藝術追求等生活過程提供指導,形塑現代人健康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自信,塑造完美的個體生活。
我們也可以將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的身體美學理解成審美泛化的一個角度。身體美學以身體的修煉為基點,將美學生活化、可操作化。身體美學包含了向內和向外的兩個向度。向外的向度包括運動、化妝、流行裝飾與服飾、整容;向內的向度包括冥想術、亞歷山大氣術、水療、瑜伽等跨文化背景下的精神和身體的修煉方式等。在這個意義上的生活藝術哲學涵蓋的范圍被極大地擴展了,不僅是一種職業化的哲學治療,而且是以實踐主體為中心在身體和精神上實現自我提升的一種技能,施洛德代克(Peter Sloterdijk)將之稱為“人類技藝”,在他看來,整個人類思想史和宗教史都是這種人類自我提升的修煉體系[13]。
三、 現象學與生活藝術哲學
我們熟知的當代哲學的實踐轉向在不同的哲學論域中有著不同的面向,除了政治哲學和倫理學的勃興、語言學轉向和分析哲學的濫觴之外,關切現代境域中個體生存問題的生活藝術哲學也是實踐轉向的面向之一。在某些思想路向中,生活藝術哲學甚至被視為政治哲學討論特別是資本主義批判的最終歸宿,這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法國后現代主義思潮中尤為明顯,比如馬克思主義者和情境主義者居伊·波德(Guy Debord)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景觀批判,最后就以日常生活藝術化為解決之途,并且提出了“易軌”、“漂移”等具體的哲學式實踐策略。另一位情境主義者、“日常生活批判理論”創立者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的巨著《日常生活批判》同樣主張將后馬克思的政治和經濟批判融貫到日常生活的藝術實踐之中。
現象學則秉持著關注“小零錢”的精神,在更為基礎的層面為生活藝術哲學和生活化美學開辟可能性。當代哲學被看作一種生活藝術,在恢復生活意義、合乎本源存在、捍衛偶然性以及認同常識的方式下,生活藝術哲學旨在指導個體在技術時代優雅地生活、保持健全的人性以及建立與自然的和諧關系,彌合個體與時代、人文與技術、自然與科學之間的裂痕,開辟鮮活的生命境界,實現理想的生活狀態。哲學家不僅要關注學院化的專業哲學和理論體系的建構,而且也應當通過哲學實踐為個體的心理迷失、精神壓力提供幫助,為商品社會與高尚藝術的協調提供指導,為城市中產階級提升生活品位、完善自我修養提供捷徑,為教育和培養現代社會中的完善個體提供理論依據。當代德語哲學界涌現出了一批致力于此的哲學家,比如馬奎德、阿亨巴赫、韋爾施、施洛德代克、伯梅、威廉·施密德(Wilhelm Schmid)、薩弗蘭斯基(Rüdiger Safranski)、費迪南德·菲曼(Ferdinand Fellmann)等,他們都從不同的方向為作為生活藝術的哲學和哲學實踐做出了貢獻。其中伯梅、薩弗蘭斯基、菲曼本身就是出色的現象學家,在現象學研究領域做過不少杰出的工作,而馬奎德、威廉·施密德、施洛德代克等人則在思想方法上受到現象學尤其是海德格爾存在哲學的重大影響。
生活藝術哲學將自身定位于現象學所開辟的立場,即位于規范科學(邏輯學、數學)與經驗科學之間的前科學。在這個領域中,生活藝術作為一種展開形式將經驗立場與規范立場關聯到一起,在這里這兩種立場是同樣原初的。而在古代,作為生活藝術的哲學乃是哲學的基本形態,蘇格拉底的助產術式哲學對話,斯托亞派的人生智慧,畢達哥拉斯的神秘修煉,都是生活藝術的具體形式,更日常的看法則把生活藝術等同于美德倫理學,即一門在具體生活中不斷反思辯詰的學問。而近代道德哲學更專注于為高于具體生活的規范奠基,因此生活藝術逐漸脫離了道德哲學的范疇,在20世紀逐漸接近于心理治療和心靈疏導。隨著現象學的介入,生活藝術哲學作為哲學咨商和生活化美學才有了更為明確的自我定位,它將作為經驗的生活技藝和倫理學規范以發生學的方式結合到一起:一方面將生活藝術的人生經驗哲學化,另一方面則通過發生學解讀將倫理規范和先驗哲學現象學化。因此,當代生活藝術哲學所涉及的范圍更為寬廣,比如“對人的自身關系、自我賦義(Selbstbesinnung)、自我規定的描述,就像從第一人稱視角所感受和體驗到的那樣”,“人們也可以談及自身境象(Selbstbildern),在其中不同知識形式的規范性得到統一”[14]24-25。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生活藝術的哲學領域被描述為對康德先驗主義現象學化的同時,也是人生哲學化的轉型”[14]37。
現象學關于生活世界以及此在是在世存在的構想,是當代生活藝術哲學的重要思想根基*比如施密德就說道:“無論如何,生活世界的概念都被證明是成果豐富的,它對一門生活藝術的哲學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參見W.Schmid, Philosophie der Lebenskunst, Eine Grundlegung, Frankfurt a.M.: Suhrkampf, 1999, p.43。。它以一種全新的哲學眼光告訴我們何為世界:世界是以身體和體驗的方式展開生活的過程并且是以感官的方式去經驗之物。個體生活于世界的關聯之網中,而這個生活世界之網并非一蹴而就地被給予,它必須不斷地被重新設計和編織,不斷地融入其中生活。“生活世界蘊含了生活藝術的問題”[15]200,它要求創造性,根本上需要生活藝術的創造活動。
如果說當代生活藝術哲學將哲學生活化、反哲學專業化的姿態是對古典哲學形態的一種重溫,那么,這種姿態與現象學哲學的古典氣質恰好吻合。換句話說,現象學在此充當了當代生活藝術哲學重新發現古希臘哲學資源的媒介,由此,生活藝術哲學家們重新發現古希臘哲學資源中與人生哲學密切相關的部分:通過現象學視角恢復生活世界、恢復人與世界樸素和諧的交往經驗、恢復對人之存在經驗偶然性的重視、恢復哲學生活化而非專業化的本然面貌,最終彌合古典與現代的裂痕。
最后,現象學與生活藝術哲學都是基于對現代科學技術的批判性反思,思考在技術時代個體如何更好地生活。現象學家的技術批判并非主張徹底地摒棄技術,而是在接受日常生活常識的基礎上警惕自然科學技術的僭越。這種溫和的批判立場與生活藝術哲學中對技術的批判所蘊含的樂觀態度相契合:現代人無須一味地憂慮和拒斥科學,我們要做的只是通過補償達到生活的均衡。
[1][德]埃德蒙德·胡塞爾: 《生活世界現象學》,[德]克勞斯·黑爾德編,倪梁康、張廷國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E.Husserl,Ph?nomenologiederLebenswelt:Ausgew?hlteTexteⅡ(PhenomenologyofLife-world:SelectedTextsⅡ), edited by K.Held, edited by Ni Liangkang & Zhang Tingguo,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02.]
[2]E.Husserl,DieLebenswelt:AuslegungenderVorgegebenenWeltUndIhrerKonstitution—TexteAusDemNachlass(1916-1937), edited by R.Sowa, Dordrecht: Springer, 2008.[E.Husserl,TheLife-world:InterpretationsoftheBefore-givenWorldandtheirConstitution—TextsfromtheManuscript(1916-1937), edited by R.Sowa, Dordrecht: Springer, 2008.]
[3][德]埃德蒙德·胡塞爾: 《現象學的構成研究——純粹現象學和現象學哲學的觀念》第2卷,李幼蒸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E.Husserl,IdeenⅡ:Ph?nomenologischeUntersuchungenzurKonstitution(IdeasⅡ:PhenomenologicalInvestigationsonConstitution), trans. by Li Youzheng, Beijing: Chian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3.]
[4][德]馬丁·海德格爾: 《存在與時間》,陳嘉映、王慶節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社,2006年。[M.Heidegger,BeingandTime, trans. by Chen Jiaying &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5]M.Heidegger,Wegmarken, edited by F.-W.von Herrmann, Frankfurt a.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M.Heidegger,RouteSigns, edited by F.-W.von Herrmann, Frankfurt a.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6.][6]M.Heidegger,MetaphysischeAnfangsgründederLogikimAusgangvonLeibniz(Sommersemester1928), edited by K.Held, Frankfurt a.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8.[M.Heidegger,TheMetaphysicalBasisofLogicfromtheOriginofLeibniz(SummerSemester1928), edited by K.Held, Frankfurt a.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8.]
[7][德]馬丁·海德格爾: 《哲學論稿(從本有而來)》,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年。[M.Heidegger,Beitr?gezurPhilosophie:VomEreignis(ContributionstoPhilosophy:OnEreignis), trans. by Sun Zhoux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8][法]莫里斯·梅洛-龐蒂: 《知覺現象學》,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M.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delaPerception(PhenomenologyofPerception), trans. by Jiang Zhihui,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1.]
[9]O.Marquard,AbschiedvomPrinzipiellen:PhilosophischeStudien, Stuttgart: Reclam, 1981.[O.Marquard,PartingfromthePrinciple:PhilosophicalStudies, Stuttgart: Reclam, 1981.] [10]I.Breuer, P.Leusch & D.Mersch,WeltenimKopf:ProfilederGegenwartsphilosophie, Hamburg: Rotbuch Verlag, 1996.[I.Breuer, P.Leusch & D.Mersch,WorldsintheHead:ProfilesoftheContemporaryPhilosophy, Hamburg: Rotbuch Publishing House, 1996.]
[11]G.B.Achenbach,PhilosophischePraxis:Vortr?geundAufs?tze, K?ln: Dinter, 1984.[G.B.Achenbach,PhilosophicalPractice:LecturesandEssays, K?ln: Dinter, 1984.]
[12]W.Welsch,UndoingAesthetic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7.
[13]P.Sloterdijk,Dumu?tdeinLeben?ndern, überAnthropotechnik,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9.[P.Sloterdijk,YouMustChangeYourLifeaboutAhthropotechnology, Frankfurt a.M.: Suhrkamp, 2009.]
[14]F.Fellmann,PhilosophiederLebenskunstzurEinführung, Hamburg: Junius Verlag, 2009.[F.Fellmann,IntroductiontoPhilosophyofArtofLife, Hamburg: Junius Publishing House, 2009.]
[15]P.Kiwitz,LebensweltundLebenskunst:PerspektiveneinerkritischenTheoriedessozialenLebens,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86.[P.Kiwitz,Life-worldandArtofLife:ProspectsofaCriticalTheoryofSocialLife, Munich: Wilhelm Fink, 1986.]
From Phenomenology to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Wang Jun
(DepartmentofPhilosophy,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8,China)
A notable tendency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s academicism and specialization, which result in alienation and estrangement from life.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Philosophie als Lebenskunst) has been one of the reactions among intellectuals to this tendency. At present,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is intensely debated among contemporary European thinkers. This new style of philosophical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mund Husserl’s conception of life-world (Lebenswelt) as a source of meaning relating to non-topicalization und pre-science and the corresponding genetic constitutions based on life-world are the original field of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Martin Heidegger’s Daseins-analysis has subverted the understanding of essence of Being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s and is focused on the experiences of existence in the world in the dimension of ″meta-practice″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central theoretical basis for further discussions of the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Using descriptions of body and its field, and defending contingency as a foundation for truth, Maurice Merleau-Ponty has interpreted ego and world as a unity. The philosophical views and motivations guiding the above-mentioned topics, which belong to the field of classical phenomenology, involve inversions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esence and absence, uncertainty and possibility, inevitability and contingency, and have laid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Based on this,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which centers on human existence and sensi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the world as its fundamental motivation, has been fully develop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one example being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and aestheticization. Odo Marquard treated philosophy as contemporary art of life for ″Orientierungsdienstleistungsgewerbe″ by his defense of contingency. Marquard’s concept of compensation,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and the 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 by Gerd Achenbach and Gernot B?hme, have attempted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living dilemma of modern humans, while Wolfgang Welsch’s aestheticization interpreted the whole world as a huge aesthetic system involving the life of modern human in terms of aesthetic guidance and artistic creations; Richard Shusterman’s Somaesthetics aimed at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self-promotion in two directions, inward and outward. All these are variations on the theme of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based on phenomenology. The phenomenological spirit of ″small change,″ the position against the tendency of theorizing, specialization and academicism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the position of ″pre-science,″ i. e. of philosophy preceding empirical science and normal science, the defense of life-world and contingency, the focusing on the genetic constitution of meanings, the return to classical philosophy and the practice of philosophy, the attitude of mild criticism of moder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affirmation of everyday life — all these have become the starting point and standpoint of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Research into the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phenomenology and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has therefore become indispensible to comprehending the values of and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y, as well as to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as art of life; life-world; philosophical practice; compensation; aestheticization
10.3785/j.issn.1008-942X.CN33-6000/C.2015.11.221
2015-11-22
[本刊網址·在線雜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線優先出版日期] 2016-09-30 [網絡連續型出版物號] CN33-6000/C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3&ZD069); 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
王俊(http://orcid.org/0000-0002-5140-0288),男,浙江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哲學博士,主要從事當代歐陸哲學、現象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