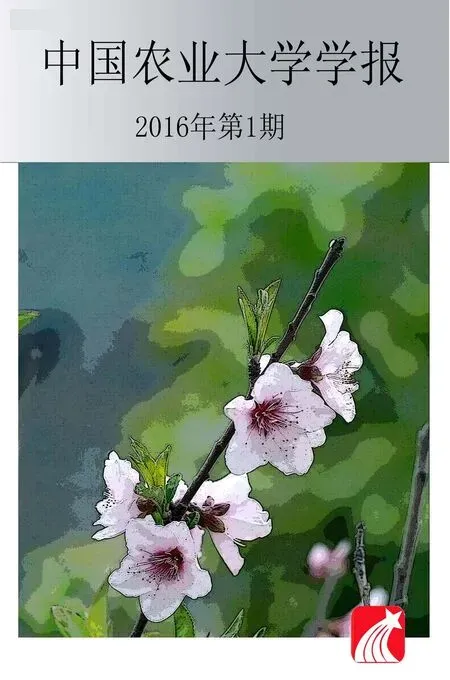生計與生存:集體化時代的村莊經濟與農民日常生活——以山西平遙雙口村為考察中心①
馬維強 鄧宏琴
?
生計與生存:集體化時代的村莊經濟與農民日常生活
——以山西平遙雙口村為考察中心①
馬維強鄧宏琴
[摘要]在集體化時代,為保障農業集體經濟體制的有效運轉并實現工業化的戰略目標,國家通過經濟制度安排的約束、政治意識形態的引導以及社會流動上的限制等手段使農民投身于農業生產,但勞動安排和工分管理的不足使集體生產產生困境。一些農民往往跨越國家政策規定的界限進行手工業勞作和倒買倒賣,這些手段被賦予了政治含義,受到約束限制,有些人甚至因此而被戴上“帽子”,成為“階級敵人”。不過,村民依然通過非農業勞動甚至偷盜來獲得生存所需。農民的生存理性和村莊傳統對于農民的生計觀念和謀生手段發揮著重要作用,革命的現代性邏輯遭遇到農民日常生活邏輯的抵抗,使看似無可辯駁、無法更改的人民公社體制機體受到村民雖然微弱但卻是日積月累的侵蝕。
[關鍵詞]集體化時代; 農民; 生計; 生存; 日常生活
集體化時代,國家農業集體經濟制度的安排首先是基于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發展定位。國家希望通過戶籍制度、統購統銷制度、票證制度、口糧工分制等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村莊黨政組織及生產隊的組織管理,以及政治運動、政策宣傳和階級話語工具等的思想意識改造使農民投身于集體農業生產,勞動成為鄉村農民的主要謀生手段。
農業生產對于1949年后社會經濟發展作出的貢獻不言而喻。但從農業勞動的管理和組織運轉來看,作為中樞的工分體制存在不足。由于對勞動數量和質量的信息收集和監督的成本高、難度大,難以將其與勞動報酬緊密對應,勞動者的動力不足;同時,國家直接領導和計劃農業生產,并進行統一規定、管理、分配,這樣就幾乎完全控制了農業生產,包括剩余權支配。作為政策直接實施者的鄉村干部尤其是生產(小)隊干部升遷無望,也享受不到農業剩余收益,得到的對集體勞動監督和管理的激勵同樣不足[1]。無論是村干部還是普通農民,都沒有足夠積極性進行集體農業生產,致使偷懶、欺哄、磨洋工、搭便車現象普遍發生。集體勞動陷入困境和惡性循環中,并形成了所謂的“檸檬市場”效應②檸檬市場效應指的是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好的商品遭受淘汰,劣等商品取而代之,致使劣等品充斥市場。。不過,也有學者認為,農業生產中集體收益下降并造成了過密化的傾向[2],但農民的勞動量卻是飽滿的,某一家戶的勞動邊際收益仍有可能增加,工分體制在某種程度上能夠相當有效地激勵勞動者的積極性[3]。
盡管農民不能自由流動,卻存在著一定的相對自主空間,如農民利用自留地和經營家庭副業謀生,被稱為是對集體體制的“隱性退出”[4];作為管理者的村干部盡管不能享有剩余收益權,但能夠利用“因控制著農村經濟剩余的生產和初級分配而掌握的、以腐敗形式存在的‘剩余控制權’來分享剩余”。而且,“鄉村七十年代發展起來的社隊企業沖破了國家對加工工業高利潤的獨占,由集體來組織并占有剩余”[1]。這些可以視為國家治理在鄉村的積極調整和對于鄉村社會的靈活適應,其結果是為農民構建了一定的自主空間。
與上述研究成果從制度性的、結構性的視角對農業生產效率和工分體制的運作困境進行探求不同,本文以村莊檔案為資料基礎,從日常生活即農民謀生的具體實踐和過程的微觀視角進行實證性的探討,論述在國家嚴格控制管理下的農民群體是如何生存的,他們對于集體勞動有著怎樣的體驗和感受,除了農業勞動外是否還存在著其他的生計方式,形成了怎樣的生存策略,處于怎樣的生存狀況和境遇中,并揭示農民在點點滴滴的日常行為選擇中如何形成了應對不同于國家意志的主體性建構,成為解構國家制度安排和形塑社會發展路徑的重要因素。
一、“勞動最光榮”
基于社會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以及對農業勞動力的投入即約等于農業產出的邏輯推論和防止產生剝削、不勞而獲的意識形態評判,國家認為農村的勞動力必須要占到農村人口的40%左右,這些勞動力中的95%左右要固定歸生產隊支配,這樣能使農業有好的收成,就能緩和城市消費品供應緊張的狀況,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工作效率,就不會形成“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局面[5]。人民公社內的每一個社員被要求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完成應該做的基本勞動日[6]。不僅是農村的農民,凡是具有勞動能力的人如機關工作人員、在校學生、知識分子幾乎都被動員加入農業勞動的行列。許多的市鎮非生產人員也回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這被認為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表現,符合人人勞動、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原則[7]。
為了保障集體經濟體制的運作,需要從思想意識和行為選擇上形塑村民的勞動態度與勞動觀念。為農業建設和社會主義發展貢獻力量是國家對村民的勞動及勞動觀念的要求。國家通過下發政令、發動各種運動,加強農業第一位、生產勞動第一位的思想意識宣傳。是否積極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成為是否遵守國家政策法令、是否跟著黨走、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否與貧下中農站在一起的標準,成為影響個人社會形象和社會地位的因素。在公共空間的話語表述中,勞動是崇高的,勞動人民是偉大的,不勞動依賴別人生活是剝削、是可恥的。地主和富農正是由于自己不勞動,“壓迫和剝削勞動人民”而成為被專政的對象。勞動似乎成為衡量村民的政治立場、個人品質、個人能力的重要標準,從而具有了政治意義。
農業勞動重要的意識形態逐漸形成并散播在村莊經濟、行政組織管理和社會管理的運作機制中,成為改造民眾的思想觀念、日常生活和謀生方式的重要因素。作為干部和黨團員,首先要在勞動中起到領導帶頭作用,勞動成為評價黨員干部的重要標準。作為一名普通社員,也應該在干部的指揮下好好勞動。許多因不安心于生產勞動而犯了“錯誤”的社員常用“好好勞動”的一套話語來表示自己的“決心”。因倒販屠宰羊被逮住的呂廣才在檢查中寫下了自己的保證:“我再不做與人民不利之事,在隊里好好勞動,聽從各級領導干部的指揮,把自己投入到三大革命運動之中,為了今年農業的大豐收而大干特干加油干,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呂廣才檢查書.1971-1-25.雙口村莊檔案.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藏(下同).XYJ-2-6-6。。
同時,農業生產勞動還是一個改造人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的大熔爐。四類分子作為“階級敵人”的被專政和管制的過程,就是在人民監督下從勞動中“改造”自己的過程。劉清媛在個人檢查中寫道:“我要老老實實,規規矩矩的參加集體勞動,接受黨和人民對自己的監督改造,使自己脫胎換骨,重新做人。……大打農業翻身戰,支援戰備,支援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劉清媛的個人檢查.1971-9-15.XYJ-3-1-2。。能否積極地參加集體勞動是評判他們現實表現的重要依據。作為青年學生同樣應該放下知識分子的臭架子,在勞動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觀*杜松莊公社中學第一屆高中畢業生個人總結——吳小濤.1972-1-31.XYJ-2-28-5。。
農業生產勞動在當時確乎成為了村莊一切事務的中心。對于農民而言,當時除了勞動之外似乎也沒有更多選擇,而且在集體體制之下被組織起來,初期不僅會因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變化而產生新奇感,同時其分散和不善于創新的特點也使農民在一定程度上樂于參與集體勞動并接受干部管理。農業勞動管理體制有利于勞力多的家庭,而人口多、勞力少的家庭在生活上就會發生困難,但最基本的口糧能夠得到保障。盡管農業勞動的邊際效益相對低下,但為每個人都提供了就業機會,相對于農民個體和家庭而言勞動力的投入仍然能帶來收益的絕對增加。
在村莊的勞動管理中,工分是連接村民投入勞動與取得報酬的中介,是村莊的勞動管理以及公共生活得以運轉的中樞,其高低直接關系著村民的收入,拿到高工分、獲得高收益的經濟理性而非政治覺悟是支配他們日常勞動的主要動力。柳春生在檢討班上交代自己掙工分的思想:“近幾年來我愿意做大隊工,原因是在大隊做木活,每天能掙工分15分,在本隊才12分。從去年開始,在大隊勞動減少了工分,每天成了13分,我思想上就背了包袱,心想以前做的時候一天還給15分,現在做的時間也長了,技術也高了,工分反而給我減少了,以后我永不在大隊做活,在我隊做一天木活還給我記14分,以后大隊叫我去做我就不去,如果再叫我去的時候我在勞動中等就是了。10天的工總要多做一兩天”*柳春生的檢查.1970-6-25.XYJ-2-63-3。。盡管柳對自己的此種行為做出批判,但獲取更多工分始終是他的目標,這也是大多數村民不斷投入勞動的目的。工分的高低雖不能與實際的經濟利益直接掛鉤,但由于集體單位不能解雇過剩的勞動力,村民也沒有更多的生存途徑,所以只要邊際產品大于零,勞動力的繼續投入就合乎村民的經濟邏輯[2]201。
工分體制對村民的經濟生活至關重要,但卻存在著不足,既不能與勞動報酬直接掛鉤,也難以與勞動質量相對應。村民為了多掙工分,常常不能保證農活質量,無論是干部還是普通群眾,都存在偷懶、瞞哄現象。古秀堂檢討自己當共青團員,不能給沒砍好地的社員們提出建議,自己反而也不能夠按照隊內所要求和規定的質量做到砍好,只想砍得快些,多砍一些,多掙些工分*古秀堂自我檢查書.XYJ-2-19-1。。同時,工分記錄也存在問題,工分登記不嚴格,多記、少記、漏記的情況時有發生。一些記工員承認自己有時會給社員誤記,也不能及時記、及時清,常出錯誤*呂榮磊的檢查書.1965-10-21.XYJ-2-10-3;柳翠蓮的自我檢查書.1965-12-18.XYJ-2-57-1。。吳翠蘭檢討自己有時正在記賬或打工分時,孩子哭,心一急,就不可避免地要打錯或記錯工分*吳翠蘭的檢查書.XYJ-9-4-12。。而且,由于復雜的勞動安排,工分的記錄有時并不局限于記工員,多人負責、隨人而變容易造成工分錯記,農民干部相沿成習的生活和思維方式難以與村莊公共管理對責任義務觀念和工作素養的要求相適應。而且,究竟如何確定某一種農活的工分數量,村莊并沒有統一的標準和明確的規定,對于一些公共事務是否應記工分也會隨人、隨事而定*雙口村干部座談會記錄.1976-1-1.XYJ-7-12-17。。
干部的工分登記問題相對較多,一些干部有時無論勞動與否都要登記工分,有的在城里、公社開會等也要記工分,在村莊里做社務和行政工作也記工分,記工員、保管的工分有時超過了普通全勞力的分數*杜松莊公社雙口工作組工作匯報.1963-4-13. XYJ-8-6-12;各隊隊長自覺甩包袱開始.1964-12-10.XYJ-9-4-1;10隊全體隊員會議,干部甩包袱材料.1965-1-5.XYJ-9-4-4。。這樣的記工實際已經模糊了干部正常補貼與非勞動所得之間的界限,使干部能以辦理公共事務為借口賺高工分,并躲避勞動。團支書柳武斌就在支部揭蓋子會議上說:“大部分干部不勞動,懶,有的連補助賺下成萬分,但還是不勞動”*黨員學習班會談記錄.1975-12-28.XYJ-7-12-11。。何魏質問劉嵐溫:“從今年勞動多少天數,工分掙了6 000多分,是地里一天天掙下的,還是游手好閑(得來的)?”*解決雙口支部問題座談會.1977-1-29.XYJ-7-12-3。事實上國家對于干部的補貼工分有明確規定,即不得超過全大隊總工分的2%,但干部的補貼工分實際遠遠超出了這一比例。一些干部認為參加勞動會影響工作,只要把工作做好多補貼些工分算不了什么,只要增了產,哪還在乎幾個干部的補貼工分呢?*工作組關于十二隊的問題分析.1963-5-30.XYJ-8-6-10。這樣的思想在村莊干部中普遍存在,使干部的補貼工分登記往往超出規定。此外,干部還庇護親戚朋友得高工分,對于要好的就多記工分,不要好的就亂扣少記,甚至給干部私人干活也在生產隊里記工分*對古建民的揭發材料.XYJ-1-1-3;對梁新發的揭發材料.時間不詳.XYJ-2-76-7;杜松莊公社雙口大隊關于給與陳海亮撤職處分的決定.1962-2-20.XYJ-1-25-4;向工作隊反映王鐵林的問題.1965.XYJ-9-4-10。。
由于農業勞動難以分解為環環相扣的規范流程,難以形成職責明確的分工并進行較為客觀的計時或計件取酬,管理、組織成本高昂。在這種背景下,勞動者所得工分與其勞動質量并不能直接掛鉤,無論是干部的監督管理還是群眾的相互監督,都無法與監督收益的公共性產生直接聯系,欺哄難以避免,由此會挫傷村民勞動的積極性和責任感。更何況村莊傳統的經濟理性、人情面子始終在公共管理體系和管理事務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干部的工作業務素質也尚需較大的提升。不過,不可忽視的是,農民可在集體勞動之外將自身的勞力投入到自留地中。雙口村民時常將肥料、將自身的勞力更多地投入到自留地中,并且會私自擴大自留地,占用集體耕地。有學者將其稱為隱性退出,而正是因為這種隱性退出部分地使僵化的公社體制有了一定的彈性,使人民公社體制得以維持下來[4]。
二、“自由職業者”
“集體化的效果并不優于以前的市場經濟。盡管國家政權銳意進取,農業并未沖破過密化的老路。到1970年代末,農村勞動力的報酬仍只夠維持生存,與解放前數百年一樣”[2]317。農業集體經濟使村民通過勞動獲得報酬的空間有限,許多村民因此通過非農業勞動來謀取賴以生存的資源。他們或一邊勞動、一邊利用閑暇時間搞副業生產,或干脆放棄農業勞動通過其他手段謀生。生存的渴望使村民對于經濟利益產生追逐,不僅在觀念上與國家意識形態相互矛盾,而且在日常的行為實踐中也常常突破國家政策的界限。這會使安心于勞動的村民產生心理失衡,并威脅到村莊集體勞動的生產秩序,因此受到國家的嚴格管理。
國家強化農業生產重要、勞動光榮的觀念意識,認為社會物質財富的增加靠生產不靠商業,要求農民不熱心于做生意,不棄農經商[21]662,但有的村民卻認為勞動是“死受”,眼界狹窄且效益低下,是無能的表現,通過其他手段獲得經濟資源、不用“下苦”就能賺到錢的那些村民是“能人”[22]。柳春生就認為自己在大隊做木活,工具拿上一大堆,說起來還是個有技術的,而不是只干農活的“受苦人”[11]。在柳看來,擺脫“農業勞動者”的身份,通過自身更具有技術含量的方式謀生,能夠得到更多的社會認可。這也是其他一些村民所具有的觀念,他們認為能勞動而不勞動,進行倒買倒賣賺錢是腦袋活、能力強的體現。有的村莊干部甚至因為自身沒有這樣的“能力”和“本事”而自慚形穢。謝炳坤在生產隊里當干部,但他認為自己沒有說服社員特別是那些因投機倒把而發家的社員的資格。謝炳坤說:自己看到呂清文與葛大偉在隊里勞動時歇單身,但在自留地里卻挺盡心。常有人夸他們是能人,搞投機倒把,個人勢力發達,人人羨慕個個稱,而自己死鉆在農業社,死勞動挺無能,哪有臉面能說服人。又認為呂清文的母親更是個能人,本來能勞動而不勞動,還說多勞動僅夠生活,活不成”[23]。經營副業與農業勞動不同,可以得到更多的現金,獲取利益相對更為直接和迅速,數量也更大,這常常吸引著一些村民放棄勞動去賺現錢。朱玉鳳對當時村民的“小動作”記憶猶新,她說:“那時社員有的請了假說去看病,實際是出去做買賣了,人們偷得賣油,去火柴廠拿火柴去太原賣。有的是因為孩子多,不夠吃,不這樣就活不了”*訪談對象:朱玉鳳,女,65歲,平遙縣雙口村人。訪談時間:2009年5月2日。。爭取生存資源“鬧紅塵”是村民生活的主要目標,經濟理性支配著他們利用村莊集體經濟體制和勞動管理的漏洞來謀取利益,緩解對于貧困的焦慮和在集體勞動中受束縛的壓抑。
國家對于村民的家庭副業持鼓勵發展的態度,認為其是社會主義經濟不可缺少的補充部分,不是資本主義,生產隊應該鼓勵和領導社員積極發展各項副業生產。只要不投機倒把和棄農經商,不影響集體生產和集體勞動,不損害公共利益,不破壞國家資源,就應當看作是正當的,就不應亂加干涉和限制[24]。對于半工半農的手工業勞動者,國家規定生產隊要同他們協商,確定全年應做的勞動工分,以及交多少錢,記多少工分,對于他們所得的收入,除了經過全社群眾協議,認為有必要交付少量公積金和公益金的以外,其余的全部歸個人,由自己支配[25]。村民的家庭副業雖被明確定性為非資本主義,但實踐中的個體副業常常處于尷尬境地。
村莊對于個體副業的管理處于模糊狀態,沒有明晰具體的辦法,而且變動不居。以同一時段的村莊管理為例,大隊在1961年11月—1962年1月規定平車在太原搞副業,拉大隊平車的人每月交大隊150元,拉個人車每月90元。在1962年3月下旬-4月上旬期間大隊規定,拉大隊車每月交大隊125元,個人車80元*古云海交代材料.1965-11-15.XYJ-2-21-1。。但是劉洪富在1961年6月28號至1962年2月底在太原搞皮車運輸時,卻是每天交大隊1元算作一個勞動日的10分即可*談話記錄.1965-5-24.XYJ-4-1-1。。梁步魁搞泥活,每月貼16元,楊福生剃頭每年貼隊80元,口糧錢不計在內,吃糧花錢買。韓全虎補牙及賣戒指等,每年貼小隊200元錢。賈文寶、李治富(木匠)在大隊里干,每月交45元,其中16元交給隊作收入,29元記工分*柳紹軍檢查.1964-12-12.XYJ-9-4-2。。木匠白偉佳在太原拉木活,每月貼16元,給分口糧*各隊隊長自覺甩包袱開始——四隊白平江檢查.1964-12-10.XYJ-9-4-1。。由于各類副業的利潤和收益不同,村民個體的勞動能力大小不同,村莊的管理亦理應隨之體現出其間的差異,但這樣的差異應該怎樣管理,公積金、公益金和口糧錢應該如何交納,國家并無具體的管理辦法,村莊對此也無明確統一的規定,多因人因事而異。
無論是村干部還是從事副業的村民,在實踐中都偏向于個人單干,即向大隊交納了基本的費用后自負盈虧。但一些村民由于工作習慣或者是利潤的吸引,難以兼顧農業勞動,常常違反政策行事,加之階級斗爭被強化,副業單干受到更多約束,個人手工業往往被要求納入集體經濟的范圍,個人謀取利益進行單干的空間有限。不過,謀求生計生存的愿望使村民有著各種因應策略,以集體的名義搞個人單干成為許多村民搞副業生產的隱蔽方式,如韓全虎補牙、賣戒指,許成在外修理裁縫機等,白偉佳在太原拉木活、呂榮閎當水泥工等,都是以生產隊的集體名義做個人私活*柳紹軍檢查.1964-12-12.XYJ-9-4-2;何巍代表支部檢查.1976-1-20.XYJ-7-12-13;相關問題的揭發.XYJ-8-5-13。。雙口村的副業生產“成風”雖是因村民對利益的追逐引發,但與村莊干部不無關系。作為公共管理者的干部在國家政策與村民利益、自身利益之間進行搖擺,在運動來臨之際面對政治壓力限制村民的謀利活動,在運動過后又會持遷就和寬容的態度。很多干部自身就被搞副業生產的利益所吸引,因而對個人的單干也放任自流,甚至與普通村民進行“合謀”,成為村民副業生產的庇護者和合作人。
對于沒有技術的村民而言,倒買倒賣是他們在農業勞動以外獲取經濟利益的重要手段。國家對于投機倒把的定義及對其處理規定了詳細的標準,如倒販統購物資、長途運輸等,并明確提出將投機倒把與小商小販區分開來, 投機倒把是“資本主義勢力的復辟罪行”,投機倒把者是“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們的同盟軍”,小商販則是除供銷合作社和集市貿易之外的鄉村商品計劃與自由流通的重要補充[13]。但是,“國家對于投機倒把的界定含義籠統,內容損益不定,邊界模糊,尺度盈縮無償”[14]。這使村莊干部在管理中沒有明確的執行標準,因而籠統地加以限制。村莊里村民的倒販活動大多屬于村民的日常經濟交往,規模小,而且倒販的商品有的并不屬于統購物資,但都受到嚴格管理,尤其當運動來臨時,只要與集體經濟和農業勞動無關的謀生活動都有可能被定性為投機倒把。呂廣才因屠殺牲畜、賣肉、販賣羊和花椒樹苗,但未交割頭稅和營業稅而被定性為走資本主義道路、搞投機倒把。他被迫參加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班來檢討自己的錯誤思想,交代自己的錯誤行為,并在訊問中將自身販賣和屠宰羊的時間、地點、數量、使用的交通工具、涉及的人、獲利多少都一一交代清楚*柳紹軍檢查.1964-12-12.XYJ-9-4-2;何巍代表支部檢查.1976-1-20.XYJ-7-12-13;相關問題的揭發.XYJ-8-5-13。。村民倒賣燈泡、肥田粉、鍋蓋、偷殺牲畜賣肉等涉及金額雖相對較少,但也都被定性為“投機倒把”,被要求寫檢查交代錯誤,并且受到補稅、退賠、罰款、沒收工具等的處罰,如果是四類分子搞投機倒把,除了一般處罰外,個人管制也被延期*專政對象登記表——許滿金.1966-4-12.XYJ-4-14-8。。有的甚至為此而遭到大會批斗,并定性為投機倒把罪*許瑞庭個人材料.XYJ-3-12-1至XYJ-3-12-7。。
副業經營由于利潤相對較高并且脫離勞動管理而對農業集體生產構成威脅,因此受到較大限制。在“自謀職業”的村民看來,集體并不代表著個人的利益,反而是對個人生活的一種制約,他們因此要掙脫這種牽制而獲得自由,并努力利用“集體”的政治、經濟資源來謀取個人利益,通過非農業勞動來謀取生存所需的資源。在吃飯是第一需要的時代背景下,無論是黨員干部還是普通群眾,無論是四類分子還是貧下中農,都在生存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艱難掙扎,難以放棄對利益的追求和索取,也難以完全契合國家意識形態的要求并保證“規規矩矩”地站在政策規定的界限內。雙口村靈活的手工業生產和倒買倒賣活動雖然受到約束限制,但卻可以滿足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因而屢禁不止,“會過日子”的生活理性對“革命”的邏輯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力。
三、村莊里的“賊”
除了進行農業勞動和副業生產外,村民偷盜也是他們用以維持生存的手段,“這些或大或小的偷盜行為具有一種銘刻在村莊社會結構中的模式”[15]。斯科特認為:鄉下的偷竊行為很平常,它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幾乎都是農業生活的持久特點,并且國家及其代理人也無力控制。而當偷竊涉及有爭議的財產權時,偷竊就并不僅僅是一種必須的生存選擇,而且還被視作自然權利的實現。革命致力于改造鄉村傳統,不僅用集體經濟體制取代分散的家戶小農生產,而且對村民生產生活的思想觀念和行為選擇,尤其在村莊公共生活領域中的行為進行規范,如要求無論干部還是群眾都應大公無私、勇于奉獻,積極主動地維護集體利益,不偷不盜等。但是,村民的偷盜,特別是對集體糧食和財產的偷盜現象卻并不容易消逝。偷盜雖與革命現代性的邏輯相去甚遠,卻具有維持村民生存的功能,尤其在生存型經濟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以及國家以政策規定和體制性約束要求村民將土地、財產入股到村莊集體經濟繼而造成財產權爭議的背景下,村莊的偷盜行為更加難以避免。
1949年以后,農業集體經濟制度使村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有所改善,但維持在較低水平,農村依然貧困,且仍有部分村民的基本生活無法得到保障*雙口生產大隊關于訪貧問寒的情況報告.1964-1-31.XYJ-8-6-6。。村莊流行著“不偷不挖,社會主義難爬”的俗語。對于部分村民而言,爭取生存是本能,也是正當的,盡管有被捉、被罰的危險,但不偷就有可能無法生活下去,經濟上的窮困成為偷盜行為發生的重要根源。三年困難時期村莊的偷盜現象最為嚴重。當時村民偷的方法多樣,許多人穿的衣服里外都是口袋,有的扎住褲管放糧食*訪談對象:陳中智,男,73歲,平遙縣雙口村人。訪談時間:2009年4月29日。。有的去地里吃玉米,就在桿子上吃,吃完再將外皮包好,乍眼一看看不出來。有的偷糧食,光偷中間不偷兩邊,以免讓人看出來。“偷盜沒仇,得便就偷”,人們碰上哪偷哪*訪談對象:朱玉鳳,女,65歲,平遙縣雙口村人。訪談時間:2009年5月2日。。這樣的偷盜在當時比較普遍。在面臨生存威脅的情形下,能否填飽肚子的底線似乎已經超越了是否道德的社會輿論約束,更何況之前農民是在國家意識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引導和要求之下將自己的土地、財產作價入社,這種被剝奪感也會在某種程度上緩釋可能因偷盜而產生的道德負罪感。
村民偷盜的對象以集體財產為主,有的村民不僅在自身所在的生產隊、其他生產隊和生產大隊,而且還到鄰村進行偷盜,其中有個體行為也有集體行動。雙口村的村民既偷過鄰村的,也被鄰村偷過,偷盜及互相偷盜似乎成為一股蔓延在雙口及附近周圍村莊的隱而不絕、禁而不絕的風潮。村莊中因偷盜而被判刑的村民屬于個例,而且都是因偷盜村民的私人現金和財產*關于蘇淑梅的個人材料. XYJ-3-16-1;梁岱盛的個人檢查.XYJ-7-16-1,XYJ-3-20-1。。村莊中幾乎沒有因偷盜集體財產而被判刑的個案,偷竊集體的糧食在道義上與偷竊個人財產相比更容易為村莊的社會輿論和公共管理所寬容和接受。
捉賊要捉贓,偷盜者都抱有可以逃脫的僥幸心理,村莊里的一些偷盜現象常由于缺乏確鑿證據而無法得到處理。偷盜雖能僥幸逃脫,但需要冒很大風險,有時會危及自身安全。王鐵山在1963年夏收之際的一天趁黑夜寧靜無人到九隊場里偷小麥,當時場里有100瓦的一盞燈,他怕別人看見,便先去扭燈泡,孰料因手忙腳亂而觸電,將手粘在燈泡口上。看守麥場的人看見后,急忙過去用木棍打下來,王鐵山得以逃脫,看場者并未看清偷糧食的賊到底是誰。后來邱增寶到太原賣香瓜時在王的妻姐家找到了他,王對邱說:“那天晚上我在北廟后偷糧被電拉住,手上沾了一塊肉,胳膊上也沾了一塊,強強地(方言,非常費力地)爬回家,你回去以后可別告訴其他人。”可以想象王當時的疼痛及對于偷盜被逮的擔憂,事后王的家人曾派人去問看場者是否看清楚被電打的人是誰*關于王鐵山偷糧的證明材料.1970-4-3.XYJ-2-32-6。。面對與自己一樣經常偷盜的邱增寶,王鐵山幾乎毫無顧忌地談論自己的偷盜經歷。在王看來,偷盜似乎并非難以啟齒或罪無可恕,做賊心虛的心理壓力可以承受,存在的安全隱患也可以掌控。受傷的經歷并未讓他放棄偷盜的念頭,他甚至與人結伴行竊*王鐵山的個人檢查書.1965-11-21.XYJ-2-32-5。。
對于偷盜者而言,如果不被逮住就能獲利;如果被逮住,需要退出偷盜的東西,有時可能再挨一頓揍,或者被加倍罰款,但常常不能兌現,因為已經很窮,干部有時無法追究,這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偷盜現象的屢禁不止。針對村民的偷盜行為,尤其是收獲季節的“捎帶”糧食行為,村莊一般只稍作處理,如保衛、巡田員會在道口檢查、搜身,如果搜到就會看拿了多少,在哪里拿得,把偷下的東西全部沒收,再打上兩棍子,或者把工分扣掉,不給記工分*訪談對象:王昌勇,男,65歲,平遙縣雙口村人。訪談時間:2009年5月2日。。
除了經濟和精神被處罰外,有些偷竊者還會以挨打的形式受罰。1958年陰歷8月,呂向成因家里沒吃的,偷了20來穗將要成熟的玉茭,因牙口咬不動,便想馱到平遙城內賣了換現金再買別的吃,不料剛走到鄰村就被那里的保衛抓住了,并被“押送”回雙口村,正巧在村供銷社門口碰上了支書王鋼毅。王質問呂“又偷了玉茭穗到城內去?”在聽到呂“活不了,偷了幾穗”的回答后,王從供銷社內拿了一條水車上用的鐵繩拴在呂的脖子上,接著用一把鐵鎖鎖住,并把呂拉到供銷社南面的大隊,將呂向成脖子上的鐵繩的另一頭栓在大隊門口的明柱上,呂求饒無果。王鋼毅在其他干部勸說后覺得公開懲罰不妥,便把呂拉到村北大橋上,用洋鎬打了一頓,然后給呂解掉鐵繩,放他回了家*關于干部毆打群眾柳尚喜一事的證明材料. XYJ-1-6-2;關于支書懲罰呂向成的證明材料.XYJ-5-4-4;關于支書打人的檢舉材料.1965-12-11.XYJ-5-4-5。。村支書王剛毅在此將公共關系置于村莊私人關系之上,用“打”來治理村莊的偷盜行為,穩定村莊秩序。除了王之外,保衛股長和保衛組的成員也都曾用“打”來懲罰竊賊。在鄉村社會中,“打”是處理鄰里之間和鄉村社會關系中產生的沖突和糾紛的常見方式。由于鄉村習性與文化的延續性,“打”的方式也往往被運用于鄉村對于偷盜的治理中。
為了減少或消除偷盜行為,村莊干部有時也通過加倍(糧食或金錢)處罰來加大懲處力度,但這種不當的方式往往會引發村民的心理反彈,導致更多的偷盜行為。杜富強有一次因偷了17穗玉茭而被要求交罰款10元,最后他交了170穗玉茭。如此嚴重的懲罰讓杜無法接受,他在檢討書中寫道:“這樣處理后,我自己更產生了一種惡劣的思想,認為自己為偷點菜食糊口,但反而使自己的生活更加困難了,我更得去偷。當時是初秋,社員開始上地勞動,我的思想就打下了底子,若偷不多少也得偷點,于是我經常在回家的路上捎帶個一斤三斤,這是很多次的”*杜富強的檢討書.1964-1-15.XYJ-2-48-6。。耿睿智同樣遭受到不公正的處罰。1974年9月下旬的一天夜間,耿與其他村民共五人在沙河以內偷割樤子被發現。當時按公定價是5分錢1斤,負責人尹杰和柳武金按私價1角錢1斤的十倍罰錢,耿共割了31斤,因而被罰31元整。由于耿當時沒錢交這筆“巨”款,尹、柳二人便把耿的一輛自行車派人拿走,并且未等耿交款,也未征得其同意就將自行車以31元的價錢私自出賣,耿也未收到罰款收據。耿辯駁道:“我偷樤則不對,但不是慣偷,干部應該按黨的政策加強教育,(讓我)賠償損失,以觀后效,但干部們卻是用一棒子把人打死的手段加倍罰款,把我全家唯一的一輛自行車拿走出賣了”*耿睿智對自己被懲罰過重的問題的申述.1979-3-8.XYJ-5-5-31。。
公共治理方式的失當無益于對偷盜行為的治理,更何況有的村莊干部也會利用自身身份的便利而變相“行竊”。雙口村的一些村干部利用職務、權力之便從生產隊占取、占用糧食、蔬菜、布票、食油、現金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其他日用品,白用、白拿集體的各種生產工具和日常用具等。何魏就質問柳武金“社員拿紫樹槐樤子和木業社木料就是偷,而你柳武金是有權明拿”*黨員學習班上揭發問題記錄.1975-12-25.XYJ-7-12-11。。有的干部還以管理偷盜為名義將罰款及贓物據為己有。如雙口村有人偷了鄰村的條則,被罰一斤一塊錢,干部把罰下的錢買了煙然后分掉*揭公社黨委蓋子會議記錄.1977-1-28.XYJ-7-12-2。。保衛扣下村民所偷的糧食后給所有保衛人員均分*柳尚云的個人檢查.1965-11-16,XYJ-1-16-1。。保衛股長韓銀富看到村民在田地里拿糧時不管,而是在道口設卡,再扣下私分*保衛韓銀富第二次群眾會檢查.XYJ-1-21-1。。這實際也是一種變相的“偷盜行為”。干部的偷由于包裹了一層權力的保護膜而具有了安全性,而且彼此之間能進行合謀,與村民的偷盜相比更“安全”,更容易成功,而且很少被抓住*關于白平江偷竊甜菜的證明材料.1965-11-1.XYJ-1-26-3;梁新發的個人檢查.1965-12-9.XYJ-2-76-15。。許多干部的偷盜行為是在四清、整風等運動中受到別人揭發和進行自我交代中才暴露出來并被予以處理。
在集體化時代,偷盜在鄉村社會具有復雜的意涵。生活貧困是導致村民偷盜的重要原因,因此偷盜是他們不偷活不成的逼不得已,也是別人偷、自己不偷會吃虧的心理驅使,還是爭取生存權利的一種努力掙扎。同時,由于存在財產權爭議,村民以偷盜來平衡自身由加入集體經濟體制而產生的被剝奪感,并借以實現利益彌補。干部自身的盜竊行為以及對于村民偷盜的失當治理招致他們對干部管理行為的合理、合法性的質疑,并引發更多的偷盜,以此來彌補自身對于干部利用職務謀利的利益缺失。因此,偷盜不是一種單純的違背鄉村道德規則的行為,或是因超越村莊公共管理規范而受到約束限制的行為,而是隱匿和內化在鄉村社會關系中的結構性因素,也是對村民糊口型經濟和生存方式的重要補充。
四、結語
集體化時代的農業經濟為國家工業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成為改革開放后經濟飛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但是無論對于國家,還是對于鄉村農民,在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都面臨著巨大挑戰,如何在制度安排與個體行為選擇之間形成平衡點,如何協調國家意志與個體意愿之間的利益和矛盾沖突,都需要付諸努力。國家對社會主義社會的建構理念及對其實現途徑的預設未能與小農的經濟理性及村莊的公共管理體制實現有效融合,使國家的革命邏輯相對于復雜的鄉村社會顯得理想化和簡單化,導致農民與國家進行的只是有限的合作和部分的接受,除此而外還有不合作和隱秘的反抗,他們對于國家管理的應對是“風聲”來了緊一陣,“風聲”過后仍照舊,“運動”式治理的效能有限。
生存型經濟的威脅對于村民而言始終存在,他們謀求生計、生存的愿望更為凸顯,而不是政治性的“階級斗爭”,其對于政治資源的爭取更多地也是為了獲得經濟資源。無論是干部還是普通村民,都依然為了生計而奔波忙碌,只不過干部相對于普通村民而言受到更多行政管理體制的約束。生存的渴望使他們對于經濟利益產生追逐,干部與干部、干部與群眾之間也因此而形成庇護或共謀關系。這使農民通過其自身的文化和日常實踐形成了不同于國家意志的意愿和行為選擇,由此形成占據了一定的自主生存空間。從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些違背國家政策行為顯然是一種“反行為”,與以革命的邏輯、公共關系和階級關系超越代替生活邏輯和姻親、血緣的村莊傳統的制度安排和國家意識形態不相契合,但以“反行為”呈現出來的生活狀貌正是集體化時代村民對生活需求的表達和他們真實生活的體現,是他們對自身的自由流動和多樣謀生方式的權利爭取。
可以說,革命邏輯雖然主導了村莊的政治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但村民的生存理性和村莊傳統仍堅韌地嵌入革命的枝蔓脈絡中。國家全面覆蓋而非嵌入式的覆蓋并沒有完全替代了以道義和人情來維系的鄉村社會關系[16],農民的生活邏輯及由此而形成的村莊人際關系并未消失,農民并不完全聽從于國家的制度安排,他們努力掙脫體制的束縛和意識形態規訓,以自己擅長的方式經營自身的生活,于此求得生存和主體性的建構。村民的這些脫離制度軌道、爭取自身權益的行為雖然是分散的,但威脅著集體經濟和村莊秩序,在某種程度上不僅對集體經濟體制構成威脅,也對國家向鄉村傳播的以社會主義思想為核心的、具有排他性的政治文化形成解構,并成為經濟體制創新和“創造性政治”的潛在因素[17],推動社會向新的方向發展。
[參考文獻]
[1]周其仁.中國農村改革.國家和所有權關系的變化(上)——一個經濟制度變遷史的回顧.管理世界,1995(4):178-189
[2]黃宗智.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1368—1988).北京:中華書局,2000
[3]張江華.工分制下的勞動激勵與集體行動的效率.社會學研究,2007(5):1-19
[4]羅必良.限制退出、偷懶與勞動力檸檬市場——人民公社的制度特征及其低效率的根源.中國農業經濟評論,2007(1):95-104
[5]中共中央轉發五人小組《關于調整農村勞動力和精簡下放職工問題的報告》.1961-4-9//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6]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1961-6∥《當代中國農業合作化》編輯室編.建國以來農業合作化史料匯編.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2
[7]山西省人民委員會財糧貿辦公室關于壓縮市鎮非生產人員回鄉參加生產的報告.1958-1-16.山西政報.1958(4):30-33
[8]中共中央關于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1961-11-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4冊).1997
[9]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決定.1962-11-22∥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匯編(第1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0]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農村副業生產的指示.1965-9-5∥建國以來重要文獻匯編(第20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11]當前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一些問題.1971-2-14∥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12]國務院關于統一管理農村副業生產的通知.1957-10-22∥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上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
[1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6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14]張學兵.當代中國史上“投機倒把罪”的興廢——以經濟體制的變遷為視角.中共黨史研究,2011(5):35-46
[15]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鄭廣還,張敏,何江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1
[16]董磊明.從覆蓋到嵌入:國家與鄉村1949-2011.戰略與管理,2014(3/4)
[17]徐勇.農民改變中國.基層社會與創造性政治——對農民政治行為經典模式的超越.學術月刊,2009(5): 5-14
Livelihoods and Survival: the Village Economy and the Daily Life of Farmers 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A Case Study of ShuangkouVillage in Pingyao County, Shanxi Province
Ma WeiqiangDeng Hongqin
AbstractIn 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the state had farmers being engag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hrough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guiding political ideology and restrictions on social mobility, which protected the effective functioning agricult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system and achieving the strategic objectives of industrialization. But less labor arrangements and work-point management enabled collective production to be difficulties. Some farmers often transcended the boundaries of policies to be hand labor or profiteering, which had been given political meaning to be constrained. Some people even were put on the hat as the class enemies. However, the villagers still survived through non-agricultural labor or theft. The survival of farmers and villages tradition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Modern revolutionary logic encountered peasant resistance logic of everyday life, which made the irrefutable and unchangeable people's commune system be cumulative erosion by the villagers.
Key wordsThe collectivization era; Farmers; Livelihoods; Survival; Daily life
(責任編輯:陳世棟)
[作者簡介]馬維強,山西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生導師,郵編:030006;
[基金項目]200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09YJC770047)和2012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項目批準號:12&ZD147)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7-26
鄧宏琴,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①為了尊重當事人的隱私權,文中隱去了真實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