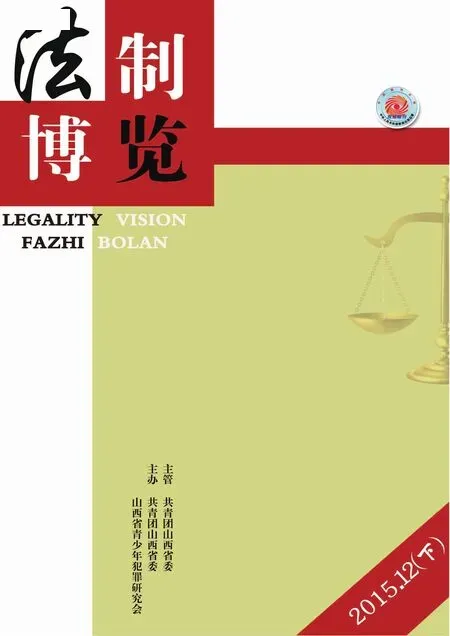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研究的概念、問題和方向
張雯晴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研究的概念、問題和方向
張雯晴
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政治參與是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訴求,其深度與廣度也是衡量我國社會發展的重要標準之一。以往的農民工政治參與問題研究主要為描述農民工群體政治參與現狀、分析農民工群體參政對社會的利弊與計算其參政成本幾類。本文試圖通過回顧和總結已有的文獻資料,闡述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政治參與的概念,存在的主要問題與未來的發展方向。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綜述
中圖分類號:D4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5)36-0005-04
作者簡介:張文晴,女,漢族,遼寧葫蘆島人,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學。

一、概念厘定: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及其特征
新生代農民工的概念要與老一代農民工相比較著理解。王春光于2001年首次提出這個概念,其后的研究中,對這一概念的描述大致包括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以下幾個特征:其一,新生代農民工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平均年齡在23歲左右,于90年代外出務工;其二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戶籍仍在農村,本質上是農民,但幾乎沒有農村的生活技能。
(一)新生性:新生代農民工幾乎都年輕人
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是由年齡在16歲以上、80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輕人組成的。許向東在《大眾傳媒中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分析與思考》中說:“新生代農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①在鄭永蘭和丁曉虎的文章中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們認為新生代農民工是“年齡在18-35周歲,具有農村戶籍而主要從事非農就業的人群”。②
(二)工人與農民性:他們的戶籍在農村
胡紹元、鐘純真和田波在其發表的《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理性思考》一文中,將新生代農民工定義為“80、90后,年齡在18-25歲之間身在城市從事非農經歷”的人,他們中的“多數未婚,受教育程度較高,與農村生活日漸脫離,而與城市生活日漸密切的群體”。③胡樞也在研究中說“我們將外出從業6個月以上、并且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農村勞動力稱為新生代農民工”。④
(三)城市化傾向:價值觀的城市化變革
長時間的城市生活,使新生代農民工在外表、生活習慣、利益訴求等方面更像城市人,他們的價值觀也發生了改變。張永剛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一文中說“所謂新生代農民工,是指改革開放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在城市中打工的農民。同他們的同輩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受多元化的現代文明影響,逐漸形成幾個突出特質:一是價值取向多元化;二是維權意識較強;三是渴望融入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新’在年輕,他們憧憬城市生活,期盼得到社會認可和尊重,利益訴求比較明確。”⑤
二、參政現狀: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轉變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以及政治制度的逐步完善,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政治參與從很多方面發生了改變,在眾多對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研究文章中,可以總結出以下幾點明顯的變化。
(一)從被動參與到主動參與的轉變
相比老一代農民工的權益受到侵害時的冷漠、委曲求全等無意識的解決方式,新生代農民工的解決方式更直接,方式也更為先進。通過使用新生的媒介比如網絡、電視等,來發表看法,參與政治,維護權益。新媒體的產生和發展也間接提高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主動性。與印度,農民工也存在相類似的進步,新一代的農民工提高了通過運用新媒體解決其家鄉和個人問題的積極性。⑥
在一些學者的著作中,對于農民工網絡政治參與下了明確的定義。例如,《政治學概論》一書中是這樣定義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政治參與的概念的:“新生代農民工網絡政治參與是指新生代農民工以虛擬的網民身份或者以網絡社區的形式發表政治主張、政治意愿,影響和推動政治決策過程、監督行政管理的活動,是一種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府決定和與政府活動相關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參政行為”。⑦換言之,網絡的誕生不但提高了參政的積極性,也為新生代農民工提供更多參政機會。
可見,隨著網絡等新媒體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角色在無形中發生改變,利用網絡自由言論的便利,新生代農民工群體通過高科技媒體參與政治已經成為一種家常便飯,推動了新生代農民工自覺參與政治的腳步。
(二)從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到制度化政治參與的轉變
公民的政治參與可以按照參與者的參與方式是否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可以將其分為制度化政治參與和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兩類。其中,制度化參與是公民在法律規定的框架內按照其所確定的一系列具體操作規則進行的政治參與活動;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是有悖于法律規定而采取的政治參與活動。
一般情況下的非制度化參與都含有經濟目的性與被迫性。方軍、李宗錄在《政府治理制度化中農民工非制度政治參與探析——兼論馬克思主義參與式民主》中將農民工的非制度參與概括了三個特點,首先,很多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是以討回薪資等經濟權益,也就是說,很多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發生的主要是以維護自身的經濟利益為目的;其次,由于制度與維權機構的缺失,很多農民工維權無門、求助無路,非制度化參與出于無奈;最后,非制度政治參與常常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地區和行業也相對集中,發生地點多集中于政府機構門口、主要干道路口等,并具有一定的爆發性、多發性與反復性。
徐志達在文章中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導致新生代農民工選擇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方式:其一是制度化參與的物質基礎不充實: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收入相對較低;其二是制度化參與的制度保障不力:新生代農民工參與渠道的虛置與缺失;其三是制度化參與的文化內涵不深;新生代農民工政治文化落后;其四是制度化參與的社會認同感不強;城市居民對新生代農民工的排斥。⑧
除上述原因外,城市有限的資源和地區保護導致的城鎮市民排斥農民工的現狀,也是造成農民工行為偏激的原因。隨著經濟的發展,文化水平的提高,制度的逐步健全,各種組織機構的完善以及城市對農民工包容性的增加,有效的減少了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逐步提高參政頻率時,政治參與的質量也在慢慢提高。
(三)從無組織個體化參政到有組織群體化參政的轉變
新生代農民工之所以會傾向與選擇非制度化的政治參與,與沒有代表他們表達觀點、維護權益的非政府組織有關。也可以說,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非制度化和零散性,與當前缺少組織依托,缺少合理的平臺有很大關系。
楊莉蕓在《突破與創新:構建農民工城市政治參與的長效機制》中指出“農民工要獲得同等國民的待遇,獲得‘話語自由權’,不僅要依靠政策制定和執行,還要依靠成立和加入自己的組織來提高在城市的博弈權,通過組織為其政治參與提供支撐,以獲得同等國民待遇。”⑨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現代化社會組織體制,農民工非政府組織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和空間。
三、參政障礙:分析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中存在的問題
(一)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經濟水平是主要引用
在楊莉蕓2013的調查中,她發放了600份問卷,統計得到這樣的結果,“41%的新生代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600至1200元,47%的農民工月收入在1200元至1500元,12%的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1500元以上。“在潘清2015的調查中顯示,新生代農民工中從事建筑行業的平均月收入為1747.87元,而從事制造業的農民工的平均工資在2000-3000元。相比較2013年的數據可見,農民工群體的工資水平依然很低。
由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情況雖然較老一代農民工有所改善,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平均經濟水平相對落后,即使他們有參政的愿望,但沒有機會和條件來實現。農民工政治參與無法提高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農民工群體的平均經濟水平沒有得到提高。
增加新生代農民工的經濟收入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要發展經濟,提高平均工資水平,二是要建立起合理的工資保障制度,確保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能夠準時、準確的拿到勞動報酬。
(二)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邊緣化狀態
道格拉斯曾說,“制度是社會的游戲規則。更嚴謹的說,制度是人為制定的限制,用以約束人類的互動行為。”不合理的制度迫使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游移在城市與鄉村之間,也成為了束縛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政治參與行為的枷鎖。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長和合理發放國家補貼,戶籍制度在農村和城市之間建造了一堵無形的墻。現在二元戶籍制度仍然存在,這也成為了制約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最大障礙。
新生代農民工在二元戶籍制度的限制下,即使擁有平等的選舉權,卻沒有可以行使權利的機會和空間。鄉村與城市之間的界限是橫亙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的溝渠。戶籍政策與很多城市的人口保護政策阻擋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融入城市的進程,同時,遠離家鄉的他們被排斥鄉村的范圍之外,也無法受到家鄉政府的保護,無法享受到家鄉的優惠利民政策。左珂、何紹輝在文章中說,“新生代農民工因受到戶籍制度、城市化政策以及個人能力等的影響,新生代農民工既無法完全融入城市,成為真正的城里人,從而參加務工地的政治生活;又遠離鄉村社會,被排斥于鄉村社會之外,無法實現戶籍所在地的政治權利,這使得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呈現出雙重邊緣化的特征。”
(三)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缺少組織依托
“政治參與渠道是公民進行政治參與的平臺和基礎。”農民工的信息渠道和正式的權力機構不足,但是組織可以彌補這方面存在的缺陷。
張彪認為“中國還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多元利益表達和決策機制,在政府決策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的依然是權力精英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愿望需要得到權力精英的確認和重視后才有機會得以實現。”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是一個年輕的社會階層,無論是在經濟資源還是政治資源、文化資源的占有上都處于社會分層的底層,在城市中,如果既沒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又缺乏表達利益訴求的組織,沒有利益代言人,他們心底的需求無法表達,他們的訴求很難被政策制定者所知。
相比老一輩農民工,新生代農民工更會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當前,在利益表達的障礙除了有些偏遠地區缺少專門的管理部門以外、還有很多已經設立的信訪部門形同虛設。農民工的表達渠道不通暢,又缺少制度保障,久而久之便會出問題。
(四)新生代農民工的平均文化素質較低
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群比老一輩農民工文化水平更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強,但是相比城市中同齡人,他們的平均文化水平較低。
鄧秀華2012年的調查數據顯示:57.3%的外出務工的農民工文化為初中水平,僅有4.8%的大專及以上學歷和8.0%的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偏低的文化水平讓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深度和廣度都受到了極大的限制。農民工認為當前影響其政治參與的障礙最主要的是自身素質與知識文化水平有限,占總署的38.4%;其次是無人受理和重視占總數的23.9%,最后是渠道不通暢,占總調查人數的16.9%。可見,新生代農民工的自身素質是影響其政治參與的最重要的主觀因素。
四、發展方向:推進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路徑
現階段,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現狀的改善和推進,要從兩方面著手,其一是改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外在環境,其中包括社會環境和制度環境,其二是要改善新生代農民工的參政基礎,包括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基礎、文化基礎、經濟基礎與社會保障基礎。
(一)打破政治參與的制度屏障
現存的不合理制度制約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發展速度,其中對其造成的影響最大的是二元戶籍制度。按農村與農村的戶籍劃分將社會分為兩層,亨廷頓說過,分成的社會是不穩定的,分層的社會結構也是造成農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各個方面被不平等對待直接原因。因此優化戶籍制度,推進戶籍制度的改革,各級政府要認真貫徹落實廢除二元戶籍制度政策,為改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環境提供政策保障,打好基礎。
首先要從提高維護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認識、建立統一的戶籍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使農民工政治參與制度化、程序化三個方面有所作為,徹底破除二元城鄉體制,要統籌城鄉社會綜合發展,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工作的首要位置,努力建立和完善城鄉一體化的政治、經濟和社會體制,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其次,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政治格局、樹立保護農民工利益政治表達的重要觀念,從而完善農民工利益政治表達機制。用制度安排來反映農民工的利益訴求,不斷培養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意識,不斷提高政治參與能力;緊密團結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在基層建立咨詢與幫助機制,提高農民工政治參與的有組織化程度。
徹底清除制度障礙,除了要改革不合理制度,還要建立健全新生代農民工利益表達機制,建立利益表達機構,并為其提供更多的利益表達渠道。
楊桂宏、王偉的比較研究“在推進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建議”中認為,首先由于原有的二元社會體制不僅形成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路徑依賴,而且也成為一種文化惰距。這對服從和適應社會政策的農民工群體來講,其束縛更為明顯。改革要著眼于社會體制的變革,建立健全相關機制,為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獲取正當的維權渠道;其次要鼓勵和支持農民工群體建立自治組織,最后是提高農民工的參政意識。
(二)建設人人平等的社會環境,使新生代農民工能夠平等生活、平等參政
2006年國務院發布《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指出:對農民工要“公平對待,一視同仁。尊重和維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消除對農民進城務工的歧視性規定和體制性障礙,使他們和城市職工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十七大報告指出:公民政治參與要有序擴大。2007年全國人大五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決定草案決定:“來自一線的工人和農民代表人數應高于上一屆”,而且“在農民工比較集中的省、直轄市,應有農民工代表”。在十八大上,農民工代表的人數有所增加。
政府提高對農民工生活的重視才能更切制定出更加有利于改善農民工生活的政策,提高農民工對政治參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政治參與。還有很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
(三)推進農村義務教育建設,提高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文化水平
在農村繼續推進義務教育的宣傳與教育基礎設施建設,為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提供主觀基礎,要在提升文化知識水平、提高修養素質的同時加強對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工作技能的培養,讓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得到整體上的提升。
對于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要采取多種多樣的方式提高他們身邊的文化氛圍,多方法,多地點,多種類的為新生代農民工營造學習、進修的機會。
近日來,多地圖書館施行公平讀書的政策,無論社會地位與身份,對所有想讀書的人敞開大門,這一舉動有利于提高全民的文化素養,更為新生代農民工群體提供了進修于提高自己的機會。龔超曾在其文章中指出可以“通過社區、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公園等教育載體,向農民工群體開放,吸納農民工融入到社區政治經濟文化的建設中來,在參與中獲得科學文化知識和信息,增加知識儲備,提高文化素養,陶冶情操,轉變或更新價值觀念。”同時,各用人單位要加強尊重農民工人格的教育和政治素養的培育,要著力營造合宜的企業文化,提高尊老愛幼、誠實守信、舍利取義等傳統美德的熏染作用的重視程度,加強傳統節日的內涵宣傳給予外來務工人員更多的人文關懷。
(四)落實合同制度,保障新生代農民工群體的人身和財產安全
目前在城市務工的農民工一半以上沒有簽訂勞務合同。勞動合同既能有效的降低農民工的流動頻率,也能保障勞務合同簽訂期間,農民工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簽訂同時也是對用工方按時、按量的履行責任的有效監督辦法。除了簽訂勞務合同,用工方和社區應為進程務工的農民工提供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保障農民工能夠在城市中享受同等的待遇。
在鄧秀華對廣東和湖南兩地的農民工調查結果顯示,2010年,廣東湖南兩地的農民工中分別有54.6%和43.8%的新生代農民工沒有和用工單位簽訂書面合同,而在有勞動合同的農民工中,廣東和湖南兩省分別有占73.4%和55.4%的有書面合同,仍有26.3%和44.6%的農民工僅有口頭合同。且在他的調查中也顯示出當前新生代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狀況也不樂觀。在調查的廣東和湖南兩省的農民工中,他們的醫療、失業、工傷等基本保險都有嚴重的缺失。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無法做到一步將全部的農民工納入社會保障范疇,只能一步步完成。首先,要著力普及農民工的工傷保險。新生代農民工主要以從事建筑、煤炭等高危行業為主,因此要建立強有力的法律制度,用法律武器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其次,要認證落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每年清查領取保障的人群是否符合標準,要把保障給予到需要的家庭,用最低生活保障去挽救生活困難的迫切需要幫助的家庭。在各個社區要加強對外來務工人員的關注與幫助,使其獲得與城鎮居民同等的待遇。最后,要健全新生代農民工的養老保險制度。新生代農民工群體大多數都把自己的年輕時代奉獻給了整個城市建設,所以我們要建立健全針對他們的養老保險制度,讓他們老有所依。養老保險價格的制定一定要考慮農民的經濟承受能力,逐漸完成從自愿投保向強制投保的過渡。
[注釋]
①許向東.對大眾傳媒中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分析與思考[J].國際新聞界,2012(03):56.
②鄭永蘭,丁曉虎.基于區域合作治理視角下的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考量[J].統計與決策,2012(23):102.
③胡紹元,鐘純真,田波.我國“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理性思考[J].湖南社會科學,2011(5):70.
④鐘樞.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對策[J].探索與爭鳴,2013(09):29.
⑤張永剛.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J].中州學刊,2011(04):32.
⑥Aajeevika Bureau(Udaipur):Political Inclusion of Seasonal Migrant Workers in India:Perceptions,Realities and Challenges,2012.
⑦<政治學概論>編寫組編.政治學概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⑧徐志達.論新生代農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原因及走向制度化的路徑[J].玉林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011(03).
⑨楊莉蕓.突破與創新:構建農民工城市政治參與的長效機制[J].求實,2013(0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