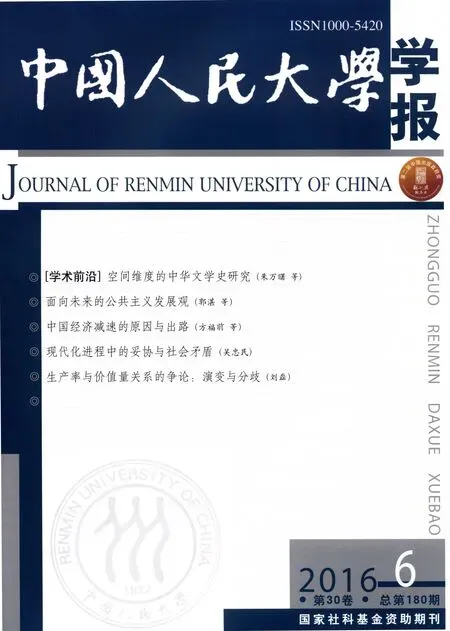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演變與分歧
劉 磊
?
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演變與分歧
劉 磊
梳理國內(nèi)學(xué)界就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的演變歷程,以及爭論各階段的主要分歧,我們可以看到:早期的爭論集中于同一時期不同主體間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共時性關(guān)系;隨著“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這一論證思路的建立,爭論逐漸轉(zhuǎn)向同一主體在不同時期中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歷時性關(guān)系。早期爭論的主要分歧在于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邏輯先在性;“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論證思路引出了有關(guān)勞動量的衡量尺度的分歧。在爭論發(fā)生轉(zhuǎn)向之后,分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成正比和成反比的關(guān)系是什么;其二,如何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chǔ)認(rèn)識社會經(jīng)濟(jì)增長。
勞動生產(chǎn)率;價值量;超額剩余價值;復(fù)雜勞動;社會總勞動
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國內(nèi)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就勞動生產(chǎn)率和價值量的關(guān)系問題展開了廣泛的爭論。這一爭論來源于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有關(guān)表述。
在《資本論》第一章,馬克思兩次提到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變動關(guān)系:(1)“商品的價值量與實(shí)現(xiàn)在商品中的勞動的量成正比地變動,與這一勞動的生產(chǎn)力成反比地變動”[1](P53-54)。(2)“不管生產(chǎn)力發(fā)生了什么變化,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nèi)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2](P60)。這兩處文本表達(dá)了兩個相互等價的命題,即勞動生產(chǎn)率與給定勞動時間內(nèi)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總量無關(guān),與單位商品的價值量成反比。馬克思的文本中還有多處直接或間接地表達(dá)了相同的觀點(diǎn)。
在談到超額剩余價值問題時,馬克思提出了另外一種含義不同的表述:“生產(chǎn)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nèi),它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3](P370)這一表述體現(xiàn)了這樣一種邏輯:與給定的社會平均勞動時間相比,生產(chǎn)率越高的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越大。這意味著,在同一部門內(nèi)部,就勞動生產(chǎn)率各不相同的企業(yè)來說,企業(yè)的勞動生產(chǎn)率與企業(yè)產(chǎn)出的價值總量成正比。
除了同一部門內(nèi)部不同企業(yè)的生產(chǎn)率與其產(chǎn)出價值量成正比之外,馬克思還把這一邏輯應(yīng)用于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在談及“工資的國民差異”時,馬克思提到,“強(qiáng)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qiáng)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nèi)生產(chǎn)出更多的價值”,并且“生產(chǎn)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qiáng)度較大的勞動”。[4](P645)
在上述所引的文本中,馬克思所論及的成反比和成正比這兩個規(guī)律涉及的是兩個不同的理論問題。成反比規(guī)律描述的是同一生產(chǎn)主體在不同時期(生產(chǎn)率提高前后)的勞動生產(chǎn)率與單位商品價值量之間的歷時性關(guān)系。例如,同一企業(yè)在其生產(chǎn)率提高前后單位產(chǎn)品的個別價值量與其生產(chǎn)率成反比;同一部門在部門平均生產(chǎn)率提高前后單位商品價值量與該部門平均勞動生產(chǎn)率成反比。成正比規(guī)律描述的是同一時期不同生產(chǎn)主體的勞動生產(chǎn)率與其產(chǎn)出價值總量之間的共時性關(guān)系。例如,同一部門內(nèi)部具有不同勞動生產(chǎn)率的企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越高,則其產(chǎn)出價值量越大;就不同國家之間的比較而言,勞動生產(chǎn)率越高的國家,其產(chǎn)出的國際價值越大。
關(guān)于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的爭論,早期多集中于超額剩余價值來源問題,體現(xiàn)為在同一部門不同企業(yè)之間勞動生產(chǎn)率與其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是否成正比。早期爭論的主要分歧在于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邏輯先在性,即在勞動價值論的理論邏輯中,價值這一范疇?wèi)?yīng)當(dāng)首先被理解為個別價值還是社會價值。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對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自創(chuàng)論的論證逐漸集中在“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這一思路上。這一論證思路表明,由于諸如勞動復(fù)雜程度、勞動強(qiáng)度等生產(chǎn)率主觀因素的不同,等量勞動時間中可以包含不等量的形成價值的勞動量。這就隱含著對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歷時性關(guān)系也成正比的判斷。隨著布寧提出的世紀(jì)之謎[5]引起學(xué)界對社會價值總量問題的關(guān)注,上述自創(chuàng)論的論證思路逐漸轉(zhuǎn)變?yōu)檎撟C社會價值總量隨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而增長的一個主要思路。成正比與成反比的爭論開始涉及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之間的歷時性關(guān)系。
本文將考察爭論在上述三個方面的演變歷程以及爭論中各方的主要分歧。
一、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
關(guān)于超額剩余價值來源問題的爭論,自20世紀(jì)60年代起一直延續(xù)至今。自創(chuàng)論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同一部門內(nèi)生產(chǎn)率較高的企業(yè),其所獲得的超額剩余價值(或超額價值)是由本企業(yè)的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轉(zhuǎn)移論的觀點(diǎn)則認(rèn)為,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所獲得的超額價值是由生產(chǎn)率較低的企業(yè)付出的但并未由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實(shí)現(xiàn)的勞動轉(zhuǎn)移而來的。在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這一問題上,自創(chuàng)論與轉(zhuǎn)移論這兩種觀點(diǎn)蘊(yùn)含著相互對立的推論。如果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所獲得的超額價值是由其自身勞動創(chuàng)造出來的,那就表明企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越高,其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就越大。反之,如果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所獲得的超額價值來源于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勞動的轉(zhuǎn)移,那就意味著,盡管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產(chǎn)品的價值總量較大,但其自身勞動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并沒有增加。
早期爭論的一個主要分歧是對價值這一范疇的不同認(rèn)識,即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在勞動價值論中何者邏輯在先。轉(zhuǎn)移論者把商品的價值量即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理解為個別勞動時間從而個別價值的加權(quán)平均,這意味著個別價值這一概念在邏輯上是先于社會價值的。自創(chuàng)論者盡管也承認(rèn)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個別勞動時間的加權(quán)平均值,但他們通常認(rèn)為價值這一范疇正是在這個加權(quán)平均的實(shí)現(xiàn)過程中得到?jīng)Q定的,因此價值只能被理解為社會價值,而個別價值只是由社會價值引申出來的附屬概念。也就是說,在自創(chuàng)論者看來,社會價值在邏輯上是先于個別價值的。
王積業(yè)較早提出了轉(zhuǎn)移論的觀點(diǎn)。在他看來,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耗費(fèi)較少的個別勞動,生產(chǎn)出較多的產(chǎn)品,這些產(chǎn)品在市場上表現(xiàn)為較多的價值,是一個“所創(chuàng)造的使用價值的社會估價問題,是個別價值均衡為社會價值的問題”[6](P27),因而是一個價值實(shí)現(xiàn)的問題。從價值創(chuàng)造的角度來說,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并不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它在等量個別勞動時間中只創(chuàng)造出等量的價值;它所獲得的超額價值是它占有的、由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付出的勞動。
衛(wèi)興華對轉(zhuǎn)移論觀點(diǎn)提出了商榷意見。他認(rèn)為,成反比的規(guī)律“從時間的繼起性方面”來考察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而成正比則是“從同一部門內(nèi)的不同企業(yè)之間的關(guān)系出發(fā)的”[7](P34),不能將這兩者各自適用的理論問題相混淆。就超額剩余價值來源而言,要討論的問題是“勞動生產(chǎn)率互不相同的各個企業(yè),在相同的個別勞動時間內(nèi),是否會創(chuàng)造出等量的社會價值”[8](P35)。衛(wèi)興華強(qiáng)調(diào),商品的價值不是個別價值,而是社會價值,“在商品價值量的決定上,被計(jì)算的只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不是實(shí)際耗費(fèi)的個別勞動時間”[9](P15)。這就是說,無論單個企業(yè)在實(shí)際生產(chǎn)中付出多少個別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量的都只能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較多的社會價值量,是因?yàn)槠鋭趧拥摹吧a(chǎn)性較高,在價值關(guān)系中,同量的個別勞動可以‘形成’或‘創(chuàng)造’出較多的社會價值來”[10](P35)。吳宣恭也提出了相似的觀點(diǎn):“勞動生產(chǎn)率較高的企業(yè)之所以能夠?qū)崿F(xiàn)較多的價值,是由于它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價值;反之,勞動生產(chǎn)率較低的企業(yè)之所以有一部分個別價值不能實(shí)現(xiàn),則是因?yàn)樗囊徊糠謧€別勞動沒有得到社會承認(rèn),不形成為價值”[11](P32)。
其他自創(chuàng)論者[12]在此問題上往往也持類似的觀點(diǎn)。在自創(chuàng)論者看來,由于商品的價值這一范疇只能被理解為商品內(nèi)含的社會勞動,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所得到的超額價值,只能用其個別勞動所包含的較多的社會勞動來解釋。生產(chǎn)者在直接生產(chǎn)中付出個別勞動,但在商品體系中,個別勞動并不形成價值,它只有轉(zhuǎn)化為社會勞動才形成價值。換句話說,產(chǎn)品的價值決定指的只能是商品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的決定。因此,較少的個別勞動之所以能夠轉(zhuǎn)化為較多的社會勞動,在自創(chuàng)論者看來,本身就意味著較少的個別勞動中包含著較多的社會勞動。
轉(zhuǎn)移論者對此具有完全不同的認(rèn)識。何安強(qiáng)調(diào)個別價值在價值決定中具有基礎(chǔ)性地位:“個別價值是社會價值賴以確立的基礎(chǔ),并沒有一個獨(dú)立于個別價值以外的社會價值”[13](P8)。單個企業(yè)在生產(chǎn)中直接付出的是個別勞動時間,其產(chǎn)品中包含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社會價值,是“通過各種競爭力量的均衡造成的”[14](P9)。段進(jìn)朋認(rèn)為,“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實(shí)質(zhì)上是把企業(yè)已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值依生產(chǎn)條件的不同在企業(yè)間進(jìn)行再分配”[15](P37)。唐國增也強(qiáng)調(diào)了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這種關(guān)系:“社會價值是作為個別價值的一種加權(quán)平均值而存在的價值,它來源于個別價值”[16](P51)。丁堡駿則認(rèn)為,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存在著價值—市場價值—生產(chǎn)價格依次轉(zhuǎn)化的邏輯結(jié)構(gòu)。在這個邏輯結(jié)構(gòu)中,價值指的就是商品的個別價值即個別勞動時間,市場價值則是商品的社會價值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17]崔戰(zhàn)利提出,馬克思對超額剩余價值的分析是分為兩個層次的:其一,個別生產(chǎn)率提高導(dǎo)致個別價值降低;其二,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差額形成超額剩余價值。這一邏輯思路表明“馬克思是通過‘個別價值’這個中介來研究個別生產(chǎn)力與社會價值量的關(guān)系的”[18](P54)。
就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轉(zhuǎn)移論者描繪了這樣一幅理論圖景: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付出較少的個別勞動時間,但通過商品交換和市場競爭,它們從社會總勞動中取得了一個較大的勞動量。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在獲得與付出之間的差額,就是由低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付出的但并未由低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獲得的那部分個別勞動時間或個別價值。
影響勞動生產(chǎn)率的因素可以被分為兩類:一類是主觀因素,即包括諸如勞動者技能、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qiáng)度等勞動者方面的因素;另一類是客觀因素,即包括諸如技術(shù)裝備水平、原材料的質(zhì)量等生產(chǎn)資料方面的因素。爭論各方均注意到了這兩類因素的區(qū)別,但就這兩種因素對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影響,不同的學(xué)者有不同的認(rèn)識。
孫連成強(qiáng)調(diào)了生產(chǎn)率的主、客觀因素的區(qū)分問題。他認(rèn)為:主觀因素改變帶來的企業(yè)生產(chǎn)率的提高,意味著企業(yè)在同樣的時間內(nèi)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因而由此帶來的超額價值量是由企業(yè)自身勞動創(chuàng)造的;客觀因素改變導(dǎo)致生產(chǎn)率提高所帶來的超額價值,則來自于低生產(chǎn)率企業(yè)勞動的轉(zhuǎn)移。就是說,在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問題上,孫連成提出了某種自創(chuàng)論與轉(zhuǎn)移論的綜合觀點(diǎn);與此相對應(yīng),在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問題上,他也提出了某種形式的正比論與反比論相綜合的觀點(diǎn)。[19]80年代后,一些學(xué)者[20]重新提出了綜合論的觀點(diǎn),其論證邏輯大致與孫連成相同。
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綜合論觀點(diǎn),事實(shí)上是以個別價值為基礎(chǔ)的一種觀點(diǎn)。這種觀點(diǎn)部分地接受了轉(zhuǎn)移論觀點(diǎn),即企業(yè)產(chǎn)品的價值可以不由自身創(chuàng)造,而來源于其他企業(yè)勞動轉(zhuǎn)移的觀點(diǎn)。如果把這種勞動轉(zhuǎn)移看做是價值的轉(zhuǎn)移,那就意味著接受了個別勞動時間即個別價值的邏輯先在性。
在自創(chuàng)論者看來,綜合論所隱含的這一觀念無疑是有問題的。吳宣恭在同孫連成的商榷中提出,“價值形成過程是一個個別勞動折合或還原為社會必要勞動的過程”[21](P30)。無論生產(chǎn)率提高的原因是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因素,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的個別勞動都應(yīng)當(dāng)首先“折合”成社會勞動,才能夠形成價值。這也就意味著,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的產(chǎn)出中所包含的超額價值,無論它是由主觀因素還是客觀因素的變動造成的,都只能來自于該企業(yè)自身勞動的創(chuàng)造。在這一問題上,衛(wèi)興華持類似的觀點(diǎn)。他說:“即使勞動者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強(qiáng)度不變,他們只要利用較好的生產(chǎn)資料,提高了勞動生產(chǎn)率,他們的勞動就成為更生產(chǎn)的……可以生產(chǎn)出更多的價值”。[22](P15)
何安曾對自創(chuàng)論提出質(zhì)疑。他認(rèn)為,自創(chuàng)論的觀點(diǎn)“對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何以和怎樣創(chuàng)造出較多的價值,并沒有論證清楚”[23](P9)。勞動生產(chǎn)率各不相同的生產(chǎn)者付出等量的個別勞動時間,按照自創(chuàng)論的觀點(diǎn),這些生產(chǎn)者被看做是付出了不等量的社會勞動時間。那么,個別生產(chǎn)者究竟怎樣在等量個別勞動時間中付出了不等量的被計(jì)為價值的社會勞動時間呢?
綜合論中來自于自創(chuàng)論的那一部分,即主觀因素改變帶來的超額價值來源于自創(chuàng)的觀點(diǎn),包含著這樣一種認(rèn)識:主觀因素變動帶來的生產(chǎn)率的提高,意味著等量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增加。這種認(rèn)識隱含著對何安的質(zhì)疑的一個回應(yīng):由于生產(chǎn)率較高的原因是勞動復(fù)雜程度較高或勞動強(qiáng)度較大等主觀因素帶來的,因此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付出的等量個別勞動時間中包含有較多的社會勞動量,因而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社會價值。何安考察了這種解釋思路。在他看來,超額剩余價值來源問題討論的本來就是由客觀因素變動導(dǎo)致生產(chǎn)率提高所帶來的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這是因?yàn)椋瑒趧訌?qiáng)度或復(fù)雜程度等主觀因素的變動,本身就意味著在等量“自然尺度的時間”內(nèi)所付出的“社會經(jīng)濟(jì)意義上的勞動時間”變得更多。盡管主觀因素的變動使得在等量“自然尺度的時間”內(nèi)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更大,但這只是表明“因?yàn)橛昧溯^多的勞動時間,所以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價值”[24](P34),并不是提高勞動生產(chǎn)率這一問題的本意。衛(wèi)興華同樣反對綜合論的這一認(rèn)識。他認(rèn)為,生產(chǎn)率高低與勞動復(fù)雜程度高低是兩回事,生產(chǎn)率的提高并不意味著復(fù)雜程度的提高,還可能帶來復(fù)雜程度的降低。在他看來,無論勞動復(fù)雜程度如何,只要生產(chǎn)率得到了提高,勞動就代表著更多的社會勞動,從而能夠創(chuàng)造更多的價值。[25]
二、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
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許多學(xué)者沿著綜合論中隱含的“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這一思路來論證超額剩余價值的自創(chuàng)論觀點(diǎn)及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的關(guān)系。這些論證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基于復(fù)雜勞動還原為簡單勞動的論證*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學(xué)界對生產(chǎn)率主觀因素的討論多集中在復(fù)雜勞動上,因此在本節(jié)及之后的分析中,當(dāng)談到勞動復(fù)雜程度時,根據(jù)上下文環(huán)境,可以指代各種影響生產(chǎn)的主觀因素。;其二是通過區(qū)分實(shí)際耗費(fèi)的勞動和其中所包含的有效勞動的論證。
基于復(fù)雜勞動還原為簡單勞動的論證,其主要邏輯如下:由于復(fù)雜勞動等價于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只要高生產(chǎn)率的勞動被認(rèn)定為復(fù)雜勞動,那就可以把由此帶來的超額價值解釋為由復(fù)雜勞動自身所創(chuàng)造的,同時也就可以表明高生產(chǎn)率勞動在等量時間內(nèi)創(chuàng)造出了較多的價值。一般而言,說復(fù)雜勞動是高生產(chǎn)率勞動是容易的。但基于復(fù)雜勞動對自創(chuàng)論和成正比的論證,要求把生產(chǎn)率提高的原因全部歸結(jié)為勞動復(fù)雜程度的提高,否則論證就是不充分的。這是因?yàn)椋浩湟唬荒芘懦陀^因素對生產(chǎn)率提高的影響,因而就不能排除轉(zhuǎn)移論的觀點(diǎn);其二,它與馬克思有關(guān)技能退化的理論相違背。
要論證生產(chǎn)率提高將導(dǎo)致勞動復(fù)雜程度提高,就需要排除客觀因素對生產(chǎn)率提高的影響。正比論者通過如下幾個步驟來實(shí)現(xiàn)這一目標(biāo)。
首先,正比論者提出了“同一勞動”假設(shè),認(rèn)為馬克思對成反比規(guī)律的表述,即“同一勞動在同樣的時間內(nèi)提供的價值量總是相同的”[26](P60)。這一命題隱含著勞動的復(fù)雜程度等生產(chǎn)率的主觀因素不變這一假定條件,因而成反比的規(guī)律是一個在特定假設(shè)條件下才能夠成立的結(jié)果。
葛偉民較早明確了這一觀點(diǎn),提出成反比的規(guī)律是以“同一勞動”假設(shè)為前提的:“如果生產(chǎn)力變化是因?yàn)閯趧硬辉偈峭粍趧樱瑒趧拥膹?qiáng)度或復(fù)雜程度起了變化,那么同樣時間內(nèi)的勞動就不再提供相同的價值量”[27](P65)。朱富強(qiáng)認(rèn)為馬克思對成反比規(guī)律的闡述,是在假定所有勞動都是簡單勞動的情況下做出的,因而馬克思所說的同一勞動,指的是同質(zhì)化的簡單勞動。[28]馬艷和程恩富提出,馬克思在闡述成反比規(guī)律時,“絲毫沒有考慮勞動生產(chǎn)率與勞動主觀因素復(fù)雜化之間的變量關(guān)系”[29](P45)。孟捷提出,同一勞動“既可以解讀為生產(chǎn)同種使用價值的勞動,也可以解讀為,勞動的復(fù)雜程度不受技術(shù)變革的影響,仍然和先前的勞動在復(fù)雜性上保持同一”。在他看來,如果考慮到后一種含義,那么“同一勞動”就成為一個假定條件。在此條件下,馬克思有關(guān)成反比的論述“就不能用來批評‘成正比’的觀點(diǎn)”。[30](P9)
其次,認(rèn)定生產(chǎn)率的變動總是伴隨著主觀因素的改變。熊躍平提出,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一方面體現(xiàn)著生產(chǎn)技術(shù)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則要求工人具備更高的技能,因而“生產(chǎn)力特別高的勞動……是……‘倍加’的或者‘自乘’的勞動,在同類生產(chǎn)中具有加強(qiáng)勞動和復(fù)雜勞動的性質(zhì)”[31](P52)。李澤南提出,雖然客觀因素的變動會帶來生產(chǎn)率提高,但“要發(fā)揮客觀因素的作用也必須通過主觀因素來實(shí)現(xiàn)”[32](P2)。馬艷和程恩富認(rèn)為,“就現(xiàn)實(shí)而言,勞動客觀條件的任何變化都不可避免地引起勞動的主觀條件的變化”[33](P46)。
我們注意到,說在客觀條件變化導(dǎo)致生產(chǎn)率變化的同時主觀因素也會隨之發(fā)生改變,并不意味著生產(chǎn)率提高時勞動復(fù)雜程度也提高。例如,當(dāng)機(jī)器的應(yīng)用帶來生產(chǎn)率提高時,有可能伴隨著生產(chǎn)工人的勞動復(fù)雜程度的降低,即技能退化的問題。因此,正比論者進(jìn)一步引入了總體工人的概念。
再次,利用馬克思有關(guān)總體工人的理論,將管理、科技等勞動納入到形成價值的勞動中去,突出科技進(jìn)步提高總體勞動復(fù)雜程度的作用。葛偉民認(rèn)為,“盡管分工協(xié)作簡化了生產(chǎn)過程的個別環(huán)節(jié),但社會生產(chǎn)的總過程相對歷史上存在的總過程來說,復(fù)雜程度提高了”[34](P76)。劉解龍認(rèn)為,科技進(jìn)步是“創(chuàng)造性勞動……其復(fù)雜度是極高的”[35](P16)。馬艷和程恩富認(rèn)為,“就‘總體工人’的勞動而言,其勞動的強(qiáng)度和復(fù)雜化都有提高的趨勢”[36](P46)。
孟捷試圖將上述以復(fù)雜勞動為基礎(chǔ)對自創(chuàng)論的論證,建立在對馬克思文本進(jìn)行考察的基礎(chǔ)上。孟捷對比了馬克思《經(jīng)濟(jì)學(xué)手稿(1861—1863年)》和《資本論》的文本,認(rèn)為馬克思本人存在著自創(chuàng)論和轉(zhuǎn)移論這兩種相互矛盾的觀點(diǎn)。他認(rèn)為馬克思在《手稿》中利用復(fù)雜勞動闡述了自創(chuàng)論的觀點(diǎn):隨著技術(shù)的變革,勞動成為復(fù)雜勞動,因而在相同的時間內(nèi)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價值。就為什么技術(shù)變革使勞動成為復(fù)雜勞動,孟捷認(rèn)為馬克思有三種解釋:其一,復(fù)雜勞動是“濃縮了勞動時間的”勞動;其二,復(fù)雜勞動是經(jīng)過培訓(xùn)的勞動;其三,將管理、科技等方面的勞動納入到形成價值的勞動范疇中。但是到了《資本論》中,馬克思提出了轉(zhuǎn)移論觀點(diǎn)。在孟捷看來,這是馬克思對自創(chuàng)論的偏離,而“馬克思本人此時尚未意識到自己的理論立場已經(jīng)悄然轉(zhuǎn)變”。通過考察,孟捷提出了一個自創(chuàng)論和經(jīng)過改造的轉(zhuǎn)移論的混合版本:若商品的售賣價值超出了商品的價值,則超出部分來自于其他部門商品價值的轉(zhuǎn)移;除此之外,超額價值只能來自于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自身勞動的創(chuàng)造。[37]
基于有效勞動的論證,其要點(diǎn)在于區(qū)分生產(chǎn)過程中耗費(fèi)的勞動與形成價值的勞動。由于高生產(chǎn)率勞動能夠在等量勞動時間中包含較多的形成價值的勞動,因而能夠創(chuàng)造較多的價值。這一論證的關(guān)鍵在于說明現(xiàn)實(shí)勞動過程中何種勞動是形成價值的勞動。
何干強(qiáng)提出了有用勞動的概念。他認(rèn)為,馬克思使用具體勞動這一概念注重的是其有用性,即有用勞動。如果具體勞動是有用的,那么它就形成價值;如果具體勞動是無用的,那么它就不形成價值。這意味著,具體勞動中包含的有用勞動的多少,決定了它被計(jì)算為的抽象勞動有多少,或形成了多少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付出了較少的個別勞動時間,但由于其包含有較多的有用勞動,因而形成了較多的社會勞動或價值量。[38]鄭怡然提出實(shí)際耗費(fèi)的勞動時間并不等同于凝結(jié)為價值的勞動時間。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在等量勞動時間的耗費(fèi)中,有效凝結(jié)為價值的勞動時間增加,因而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39]朱富強(qiáng)同樣提出了有效勞動的概念,來論證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的觀點(diǎn)。[40]
無論是基于復(fù)雜勞動的論證,還是基于有效勞動的論證,這些論證思路都在試圖表明,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等量勞動時間內(nèi)所包含的形成價值的勞動量增加,因而創(chuàng)造了更多的價值量。對這種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論證思路,許多學(xué)者提出了批評意見。這些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不能等同于勞動復(fù)雜程度的提高。曹子勤認(rèn)為,勞動復(fù)雜程度不是影響勞動生產(chǎn)率的因素。[41]肖毅敏強(qiáng)調(diào),生產(chǎn)率的提高并不一定伴隨勞動復(fù)雜程度的上升,相反有可能使勞動復(fù)雜程度下降,因而不能用勞動的復(fù)雜化來論證超額剩余價值的自創(chuàng)論。[42]崔朝棟提出,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的標(biāo)志之一就是生產(chǎn)所耗費(fèi)的勞動量的減少,而勞動復(fù)雜程度的提高,指的是在生產(chǎn)中耗費(fèi)了多倍的因而是較多的勞動量。這就意味著,把高生產(chǎn)率勞動看做是復(fù)雜勞動,本身就可能是自相矛盾的。[43]
其二,由勞動復(fù)雜程度提高帶來的價值量的增加,不能用來解釋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也不能用來解釋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一方面,由于復(fù)雜勞動被理解為多倍的簡單勞動,因而由勞動復(fù)雜程度提高帶來的價值量的增加,只能被理解為因?yàn)楦冻隽溯^多的勞動量,所以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價值。另一方面,馬克思將超額剩余價值界定為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由于復(fù)雜勞動的本質(zhì)是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勞動復(fù)雜程度的提高,將減少而不是增加個別價值與社會價值之間的差額。[44]
其三,總體勞動復(fù)雜程度的增加,不能用來解釋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在肖毅敏看來,總體勞動復(fù)雜化的觀點(diǎn)事實(shí)上是一種誤用。一方面,如果使直接生產(chǎn)勞動簡化的科技產(chǎn)品來自于企業(yè)之外,那么其價值本身就已經(jīng)得到實(shí)現(xiàn),因而在生產(chǎn)中只能轉(zhuǎn)移價值而不會創(chuàng)造價值;另一方面,即使新的科技和管理勞動是企業(yè)自身所付出的,在產(chǎn)出達(dá)到一定規(guī)模之后,它也有可能在單位產(chǎn)品價值量中只占有較小的比例,不足以解釋產(chǎn)出價值總量的增加。[45]
其四,馮金華認(rèn)為,以有用勞動來論證的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成正比的思路,“混淆了社會必要勞動和有效勞動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46](P31)。這是因?yàn)椋鐣匾獎趧邮且粋€平均意義上的概念,而有用勞動則是一個生產(chǎn)工藝角度的概念。即使某些勞動時間在生產(chǎn)工藝上是無效的,但只要它是在社會平均意義上必要的,它也應(yīng)被計(jì)算在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從而形成價值。
本文認(rèn)為,上述這些批評意見,并沒有真正把握“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這一論證思路的關(guān)鍵。這一論證思路中真正重要的問題在于:它提出了一個有別于勞動時間的勞動量概念。本文將在下一節(jié)中對此進(jìn)行闡述。
三、成正比與成反比之爭及社會價值總量的增長
根據(jù)孟捷[47]、余斌和沈尤佳[48]的考察,葉航在一個未定稿中提出成正比與成反比之間存在矛盾。葉航認(rèn)為,隨著勞動復(fù)雜程度從而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等量勞動時間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將與勞動生產(chǎn)率成正比。[49]這意味著,除非勞動生產(chǎn)率與勞動的復(fù)雜程度無關(guān),否則成反比的規(guī)律將不再成立。正比論者提出的“同一勞動”假設(shè),正是在這一觀點(diǎn)下形成的。在“同一勞動”假設(shè)下,成反比規(guī)律喪失了其作為勞動價值論的一個一般性結(jié)論的地位。
布寧提出,20世紀(jì)20年代以后,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社會產(chǎn)出價格總量在扣除了通貨膨脹等貨幣因素以后仍在不斷增長。如果把商品價格看做是商品價值量的表現(xiàn),那么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與社會產(chǎn)出的不變價格總量正相關(guān)這一現(xiàn)象就意味著勞動生產(chǎn)率與社會價值總量也存在著正相關(guān)的關(guān)系。布寧把這一現(xiàn)象稱作“世紀(jì)之謎”。[50]由于這一現(xiàn)象涉及的是社會經(jīng)濟(jì)增長與社會價值總量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谷書堂把這一現(xiàn)象稱作價值總量之謎。[51]
在這兩個理論背景下,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發(fā)生了明顯的轉(zhuǎn)向。20世紀(jì)60年代的爭論集中在同一部門內(nèi)部生產(chǎn)率各不相同的生產(chǎn)者之間,個別勞動生產(chǎn)率是否與其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成正比。它涉及的是不同生產(chǎn)主體就其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之間的共時性關(guān)系。正如何安所說,在那時的爭論中,“價值與勞動生產(chǎn)率成正比這一點(diǎn)并非不同看法的分歧之點(diǎn)。分歧在于:這些價值是實(shí)現(xiàn)中所轉(zhuǎn)移的,還是各自在直接生產(chǎn)過程中創(chuàng)造的”[52](P11注3)。但是,自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爭論逐漸延伸到同一主體在不同時期的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之間的歷時性關(guān)系。在這一問題上,爭論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成正比與成反比這兩個命題的關(guān)系;其二,社會價值總量是否隨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而增長。
由于成正比與成反比這兩個命題的關(guān)系問題涉及多個不同的理論問題,而爭論各方在這一名目下往往各自闡述不同的理論問題,并且常常沒有加以清晰的界定,一些觀點(diǎn)甚至?xí)巡煌睦碚搯栴}混雜在一起,因此爭論顯得十分復(fù)雜。
大體上看,關(guān)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中存在著否定論和統(tǒng)一論兩類觀點(diǎn)。否定論者往往接受其中之一而否定另一個。例如,一方面,把“同一勞動”看做是一個假設(shè)條件的觀點(diǎn),往往就意味著否定成反比規(guī)律的一般性,把成反比規(guī)律看做是特殊假設(shè)條件下的結(jié)論;如果同時還接受了隨生產(chǎn)率的提高勞動復(fù)雜程度也總會提高的觀點(diǎn),那就完全否定了成反比規(guī)律。[53]另一方面,在超額剩余價值來源問題上,如果考慮的是高生產(chǎn)率勞動是否創(chuàng)造了較多的價值,而不是高生產(chǎn)率企業(yè)的生產(chǎn)率與其產(chǎn)品的價值總量的關(guān)系,那么轉(zhuǎn)移論者就否定了成正比的命題。[54]統(tǒng)一論者同時承認(rèn)這兩個命題,認(rèn)為它們之間并不矛盾,但不同的學(xué)者對這兩者統(tǒng)一的方式有不同的理解。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成正比與成反比這兩個命題涉及不同的理論問題,兩者并不矛盾。[55]白暴力[56]和林崗[57]基于馬克思對勞動價值論的闡述,為成正比與成反比的關(guān)系建立了數(shù)理形式的分析。分析的結(jié)果表明,這兩個規(guī)律可以并存于勞動價值理論中。基于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綜合論的觀點(diǎn)則認(rèn)為,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取決于引起生產(chǎn)率變動的主客觀因素的區(qū)分:主觀因素變動將帶來兩者成正比變動,而客觀因素變動將帶來兩者成反比變動。[58]孟捷認(rèn)為,即使就超額剩余價值來源這一涉及共時性關(guān)系的問題而言,成正比和成反比仍然可以同時存在,這表明它們是“由同一些原因帶來的兩個具有互補(bǔ)性的規(guī)律”[59](P11)。
在社會價值總量問題上,許多正比論者表現(xiàn)出一個共同的疑慮:如果社會價值總量不隨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而增加,那就難以解釋現(xiàn)實(shí)的經(jīng)濟(jì)增長。例如,馬艷和程恩富認(rèn)為,成反比的理論“無法完整地解釋……社會價值總量與勞動生產(chǎn)率一般會產(chǎn)生正向變動的事實(shí)。如美國直接生產(chǎn)過程中的勞動量自上個世紀(jì)30年代以來一直呈不斷下降的趨勢,但是,美國的國民生產(chǎn)總值卻一直呈不斷上升的趨勢”[60](P43)。嚴(yán)金強(qiáng)和馬一飛認(rèn)為,成反比的理論“無法解釋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社會出現(xiàn)的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不僅社會財(cái)富總量增加了,而且價值總量也在增加的現(xiàn)象”[61](P23)。
以“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為基礎(chǔ)來論證超額剩余價值自創(chuàng)論的觀點(diǎn),可以很方便地移植到價值總量增長問題上。只要接受了在社會總體層面上等量勞動時間可以包含不等量的形成價值的勞動量,那就可以得到隨著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一個社會能夠在等量總勞動時間內(nèi)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社會價值總量的結(jié)論。在這一移植過程中,關(guān)鍵是要說明為什么社會總體層面上等量勞動時間可以包含不同的勞動量。
在上一節(jié)末尾筆者提出,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論證思路的關(guān)鍵在于:它提出了一個有別于勞動時間的勞動量概念。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勞動本身的量是用勞動的持續(xù)時間來計(jì)量”[62](P51)的,形成商品價值量的勞動量由生產(chǎn)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jì)量。就超額剩余價值來源問題而言,盡管高生產(chǎn)率生產(chǎn)者產(chǎn)品的價值量可以被理解為生產(chǎn)者付出的個別勞動時間中所包含的社會勞動量(時間),但是這個社會勞動量本身是由個別勞動時間的加權(quán)平均計(jì)算得到的。換句話說,在從個別勞動時間向社會勞動時間的轉(zhuǎn)化中存在著一個總量約束條件:個別勞動時間的加總必然恒等于社會總勞動時間。對形成價值的勞動量的衡量,則受到這一總量約束條件的限制。
然而,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解釋存在著忽視這一總量約束的可能。一旦在解釋中放棄了這一總量約束,那就必須要為形成價值的勞動量另尋衡量尺度。例如,唐元明確區(qū)分了勞動時間和勞動量,提出“勞動量是勞動者體力和腦力的消耗”,在不同的生產(chǎn)率條件下,勞動過程中“消耗的體力和腦力勞動量也是不同的”[63](P64)。這顯然就是在為勞動量尋求一種生理耗費(fèi)意義上的衡量尺度。
為勞動量另尋衡量尺度的做法會產(chǎn)生兩個理論后果。其一,如果現(xiàn)實(shí)所耗費(fèi)的勞動時間不再構(gòu)成形成價值的勞動量的衡量基礎(chǔ),那么在勞動量衡量尺度的選擇上就會產(chǎn)生較大的隨意性。這就削弱了基于這一思路的理論解釋的效力。其二,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之間成正比的關(guān)系,將不再被限制在不同生產(chǎn)主體之間進(jìn)行比較的共時性關(guān)系上:它現(xiàn)在具備了被應(yīng)用于同一主體在不同時期之間的歷時性關(guān)系上的可能。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延伸至社會價值總量問題上,反映出的正是這種理論上的轉(zhuǎn)向。
上一節(jié)已經(jīng)說明,在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論證思路中,一個重要的邏輯環(huán)節(jié)是利用總體工人的概念來說明,為什么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的復(fù)雜程度也較高。這里的總體工人,通常被界定為“較直接地或者較間接地作用于勞動對象”[64](P582)的全部工人。換句話說,在社會總體層面上,總體工人的勞動就是社會總勞動。于是,說因?yàn)榭傮w勞動復(fù)雜程度提高,所以等量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增加,就等同于說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不變的條件下,形成價值的社會總勞動量增加,因而社會價值總量增長。如前所述,這就打破了勞動量衡量中的總量約束條件。也就是說,在社會價值總量問題上,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論證思路,必須在勞動時間以外另尋勞動量的衡量尺度。
正比論者對此的解決思路,是從作為價值尺度的簡單勞動入手。馬克思曾指出,“簡單平均勞動本身雖然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具有不同的性質(zhì),但在一定的社會里是一定的。”[65](P58)一些學(xué)者由此認(rèn)為,隨著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作為價值衡量尺度的簡單平均勞動的性質(zhì)也會發(fā)生變化。現(xiàn)在的簡單勞動可能是過去的復(fù)雜勞動,從而現(xiàn)在的單位時間內(nèi)形成價值的勞動量等于過去多倍的形成價值的勞動量。如果不是采用在“不同的國家和不同的文化時代”性質(zhì)各不相同的簡單勞動作為衡量價值量的尺度,而是采用某個在各歷史時期都相同的絕對尺度來衡量價值量,那就能夠得到結(jié)論說:隨著勞動生產(chǎn)率的發(fā)展,一個社會在等量勞動時間內(nèi)可以付出更多勞動量,從而創(chuàng)造出更多價值量。
胡秀花較早明確地表達(dá)了這一觀點(diǎn):“從整個社會看,過去的復(fù)雜勞動現(xiàn)在可能是簡單勞動。”[66](P36)唐元認(rèn)為,馬克思在區(qū)分簡單勞動和復(fù)雜勞動時,是就同一時期進(jìn)行比較的,而不同時期等量時間的勞動也應(yīng)當(dāng)以這種形式做出區(qū)分。[67]劉解龍?zhí)岢觯煌瑫r期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不可比較的,要對它們進(jìn)行比較,“就必須選擇確定一個‘同度量因素’——用來進(jìn)行比較和換算的‘基期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或‘不變價值’”[68](P17)。劉平提出,“在一定社會里被簡化為平均簡單無差別的抽象勞動,在歷史的發(fā)展中實(shí)際上存在著結(jié)構(gòu)變化,存在著不同時期和同一時期的不同局部的平均簡單勞動的變化”[69](P97)。馬艷和程恩富提出了密度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概念來表達(dá)這一觀點(diǎn)。他們認(rèn)為,由主觀因素帶來的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將會使等量以鐘表計(jì)量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包含較多的形成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說,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密度增加了。[70]
張忠任把簡單勞動尺度的變動這一現(xiàn)象稱作價值的期差性。這個概念說的是,由于簡單勞動的性質(zhì)在不同時期之間存在著差異,因而以各時期簡單勞動尺度衡量的同一商品的各期價值量也就各不相等。在張忠任看來,由于各時期簡單勞動尺度是不一致的,因此各時期社會產(chǎn)出的價值總量不能直接進(jìn)行比較。但是,如果以某個時期的簡單勞動尺度來衡量各個不同時期的社會產(chǎn)出的價值總量,那就可以得到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總量之間的成正比關(guān)系。[71]
對于上述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來論證社會價值總量增長的思路,孟捷提出了批評:“成正比賴以存在的價值關(guān)系是不同商品之間互相比較的共時性關(guān)系,而不是歷時性關(guān)系。在這個問題上不能陷入錯覺,以為當(dāng)勞動生產(chǎn)率普遍提高后,無須和其他部門或其他國家相比較,單位時間在今年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即可高于往年”[72](P45-46)。盡管孟捷力圖將自己對成正比的分析限制在共時性關(guān)系之上,但上面所引的這段文字恰恰表明他也受到了上述思路的影響。這段文字中后一句話的意思是:要想對不同年份中單位時間所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進(jìn)行比較,那就必須要“和其他部門或其他國家相比較”。換句話說,“和其他部門或其他國家相比較”是對本部門或本國不同年份之間進(jìn)行比較的必要條件。但是,同一部門或同一國家在生產(chǎn)率提高前后的比較是一個歷時性的縱向比較,部門之間或國家之間的比較則是同一時期的橫向比較。要想通過橫向比較得到一個縱向比較的結(jié)果,必然隱含著這樣一個前提,即在橫向比較中用來作為比較標(biāo)準(zhǔn)的那個“其他部門或其他國家”,本身“無須和其他部門或其他國家相比較”,就可以直接進(jìn)行歷時性的縱向比較。也就是說,這句話所隱含的前提,恰恰和這句話本身所表達(dá)的含義相矛盾。
反比論者反對上述利用成正比關(guān)系來解釋布寧的世紀(jì)之謎的思路。在反比論者看來,布寧的世紀(jì)之謎涉及的是馬克思關(guān)于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之間的歷時性關(guān)系,因此能夠在成反比規(guī)律的基礎(chǔ)上得到解釋。基于成反比的解釋思路是:社會價值總量取決于社會勞動總量;以不變價格衡量的社會價格總量衡量的是社會所生產(chǎn)的使用價值總量;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意味著,一個社會能夠以較少的價值總量生產(chǎn)出較多的使用價值總量。因此,在成反比規(guī)律的視角下,布寧的世紀(jì)之謎并不是一個謎,而是商品二因素的矛盾在社會總量上的具體表現(xiàn)。
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一些學(xué)者在論述中涉及這一解釋思路。衛(wèi)興華提出,由于價格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因此在商品價值隨生產(chǎn)率的提高而降低時,價格不一定隨之降低。[73]郝玉柱強(qiáng)調(diào)了紙幣與金屬貨幣體系的差異。在金屬貨幣體系下,金屬貨幣的價值量決定著金屬貨幣的流通量;在紙幣體系下,紙幣發(fā)行量由國家掌握,以紙幣面額表示的價格總水平受到紙幣發(fā)行量從而國家政策的影響。因此,在紙幣體系下,隨著社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社會產(chǎn)出的價格與價值將呈現(xiàn)不一致的變動。[74]白瑞雪和白暴力基于這一思路對布寧的世紀(jì)之謎給出了一個數(shù)理形式的描述,其結(jié)論是:當(dāng)貨幣所代表的價值量與商品價值量兩者的變動不一致時,商品的價值與價格就會發(fā)生不一致的變動。[75]
四、結(jié)語
本文考察了國內(nèi)學(xué)界就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的演變歷程,以及在各發(fā)展階段中爭論各方的主要分歧。
國內(nèi)學(xué)界就這一問題的爭論,自20世紀(jì)60年代提出后一直延續(xù)至今。早期的爭論集中在同一時期不同主體之間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共時性關(guān)系之上,爭論的一個基礎(chǔ)性的理論分歧在于爭論各方對價值這一范疇的理解不同。
20世紀(jì)80年代以后,對超額剩余價值來源自創(chuàng)論的論證思路,逐漸建立在“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這一邏輯基礎(chǔ)之上。由此引出的一個主要分歧在于:什么是形成價值的勞動量?它的衡量尺度是什么?
基于“勞動時間中包含的勞動量”的邏輯思路,打破了勞動價值論的總量約束條件,這導(dǎo)致爭論轉(zhuǎn)向同一主體不同時期的歷時性關(guān)系。在這一階段,爭論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成正比和成反比的關(guān)系是什么;其二,如何以勞動價值論為基礎(chǔ)認(rèn)識社會經(jīng)濟(jì)增長。
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的關(guān)系問題,既是一個理論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數(shù)量關(guān)系的問題,對這一問題建立恰當(dāng)?shù)臄?shù)理表述,將有助于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理解。20世紀(jì)90年代以前,對這一問題的分析雖然也使用了一些數(shù)理分析方法,但很少建立相應(yīng)的具有一般性的數(shù)理模型。90年代以后,一些學(xué)者開始嘗試為它建立數(shù)理模型。唐國增[76]、丁堡駿[77]較早做出了這種嘗試。進(jìn)入21世紀(jì),在這方面的嘗試變得更加普遍。白暴力[78]、林崗[79]、張忠任[80]、朱殊洋[81]、馬艷[82]、張銜[83]、馮金華[84]等對構(gòu)建數(shù)理表述做出了貢獻(xiàn)。
[1][2][3][4][26][62][64][65]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50] 布寧:《科學(xué)技術(shù)革命與世界價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82。
[6] 王積業(yè):《關(guān)于社會主義制度下價值量計(jì)算問題的初步探討》,載《經(jīng)濟(jì)研究》,1962(11)。
[7][8][10] 衛(wèi)興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問題》,載《經(jīng)濟(jì)研究》,1962(12)。
[9][22][73] 衛(wèi)興華:《價值決定規(guī)律的作用會引起部門內(nèi)部剩余勞動的再分配嗎》,載《學(xué)術(shù)月刊》,1963(4)。
[11][21] 吳宣恭:《個別企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與商品價值量的關(guān)系——與孫連成同志商榷》,載《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1964(9)。
[12] 熊躍平:《對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管見——與洪遠(yuǎn)朋同志商榷》,載《財(cái)經(jīng)理論與實(shí)踐》,1983(6);李澤南:《關(guān)于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載《吉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84(1);張理智:《也論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創(chuàng)造——與佐牧同志商榷》,載《經(jīng)濟(jì)研究》,1984(3)。
[13][14][23][52] 何安:《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能否創(chuàng)造較多的價值》,載《學(xué)術(shù)月刊》,1963(9)。
[15] 段進(jìn)朋:《生產(chǎn)力特別高的勞動能創(chuàng)造更多價值嗎?》,載《復(fù)旦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82(4)。
[16][76] 唐國增:《論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載《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94(1)。
[17][77] 丁堡駿:《揭開勞動生產(chǎn)力和商品價值量之間關(guān)系之謎》,載《稅務(wù)與經(jīng)濟(jì)(長春稅務(w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94(3)。
[18] 崔戰(zhàn)利:《論超額價值的源泉——關(guān)于價值決定若干問題的新解,兼與衛(wèi)興華同志商榷》,載《南京政治學(xué)院學(xué)報(bào)》,1988(2)。
[19] 孫連成:《略論勞動生產(chǎn)率與商品價值量的關(guān)系》,載《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1963(11)。
[20] 佐牧:《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創(chuàng)造》,載《經(jīng)濟(jì)研究》,1983(8);潘永強(qiáng):《論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兼評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幾種觀點(diǎn)》,載《長白學(xué)刊》,1995(6);馬艷:《關(guān)于“價值創(chuàng)造”與“價值轉(zhuǎn)移”之爭的探討》,載《學(xué)術(shù)月刊》,2002(6)。
[24] 何安:《再論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能否創(chuàng)造較多的價值》,載《江漢學(xué)報(bào)》,1964(6)。
[25] 衛(wèi)興華:《馬克思關(guān)于勞動生產(chǎn)力同價值關(guān)系的三個原理和社會主義經(jīng)濟(jì)實(shí)踐》,載《教學(xué)與研究》,1983(2)。
[27][34] 葛偉民:《淺論勞動生產(chǎn)力與價值創(chuàng)造》,載《經(jīng)濟(jì)研究》,1984(11)。
[28][40] 朱富強(qiáng):《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力成反比嗎——兼論傳統(tǒng)勞動價值論中的一個“悖論”》,載《社會科學(xué)研究》,2002(3)。
[29][33][36][58][60][70] 馬艷、程恩富:《馬克思“商品價值與勞動生產(chǎn)率變動規(guī)律”新探——對勞動價值論的一種發(fā)展》,載《財(cái)經(jīng)研究》,2002(10)。
[30][37][59] 孟捷:《技術(shù)創(chuàng)新與超額利潤的來源——基于勞動價值論的各種解釋》,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2005(5)。
[31] 熊躍平:《對超額剩余價值來源的管見——與洪遠(yuǎn)朋同志商榷》,載《財(cái)經(jīng)理論與實(shí)踐》,1983(6)。
[32] 李澤南:《關(guān)于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載《吉首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84(1)。
[35] 劉解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率的關(guān)系新探》,載《經(jīng)濟(jì)問題》,1992(6)。
[38] 何干強(qiáng):《論有用勞動是價值創(chuàng)造的前提》,載《南京師大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86(2)。
[39] 鄭怡然:《有效勞動價值論——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新解釋》,載《江漢論壇》,2000(2)。
[41] 曹子勤:《也談馬克思“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率變動規(guī)律”——與程恩富教授、馬艷副教授商榷》,載《內(nèi)蒙古財(cái)經(jīng)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4(4)。
[42][45] 肖毅敏:《略論勞動生產(chǎn)力、復(fù)雜勞動與價值創(chuàng)造》,載《求索》,1990(3)。
[43] 崔朝棟:《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載《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09(10)。
[44] 唐國增:《論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載《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94(1);崔朝棟:《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載《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09(10);馮金華:《商品價值量的變化和某些“成正比”觀點(diǎn)的誤區(qū)》,載《教學(xué)與研究》,2012(5)。
[46] 馮金華:《商品價值量的變化和某些“成正比”觀點(diǎn)的誤區(qū)》,載《教學(xué)與研究》,2012(5)。
[47][72] 孟捷:《勞動生產(chǎn)率與單位時間創(chuàng)造的價值量成正比的理論:一個簡史》,載《經(jīng)濟(jì)學(xué)動態(tài)》,2011(6)。
[48] 余斌、沈尤佳:《論單位商品價值量下降規(guī)律——回應(yīng)“成正比”爭議的第2個命題》,載《教學(xué)與研究》,2012(3)。
[49] 葉航:《試論價值的測量和精神生產(chǎn)對價值量的影響》,載《中國社會科學(xué)》(未定稿),1980(33)。
[51] 谷書堂:《求解價值總量之“謎”兩條思路的比較》,載《南開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2(1)。
[53] 劉平:《勞動價值論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經(jīng)濟(jì)哲學(xué)蘊(yùn)涵——社會變遷的一種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S1);朱富強(qiáng):《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力成反比嗎——兼論傳統(tǒng)勞動價值論中的一個“悖論”》,載《社會科學(xué)研究》,2002(3)。
[54] 何安:《生產(chǎn)率較高的勞動能否創(chuàng)造較多的價值》,載《學(xué)術(shù)月刊》,1963(9);唐國增:《論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載《河北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1994(1);崔朝棟:《超額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載《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09(10)。
[55] 衛(wèi)興華:《價值決定規(guī)律的作用會引起部門內(nèi)部剩余勞動的再分配嗎》,載《學(xué)術(shù)月刊》,1963(4);徐素環(huán):《全面考察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率的關(guān)系——兼評谷書堂與蘇星“勞動價值論一元論”之爭論》,載《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1997(5)。
[56][78] 白暴力:《勞動生產(chǎn)率與商品價值量變化關(guān)系的分析》,載《當(dāng)代經(jīng)濟(jì)研究》,2002(3)。
[57][79] 林崗:《關(guān)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及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問題的探討》,載《教學(xué)與研究》,2005(7)。
[61] 嚴(yán)金強(qiáng)、馬一飛:《關(guān)于“成正比”理論的發(fā)展脈絡(luò)》,載《海派經(jīng)濟(jì)學(xué)》,2011(2)。
[63][67] 唐元:《勞動生產(chǎn)率同商品價值量的關(guān)系之我見》,載《寧夏社會科學(xué)》,1985(5)。
[66] 胡秀花:《勞動生產(chǎn)力與商品價值總量的關(guān)系》,載《經(jīng)濟(jì)科學(xué)》,1984(10)。
[68] 劉解龍:《全面認(rèn)識勞動生產(chǎn)率對商品價值量的影響》,載《當(dāng)代財(cái)經(jīng)》,1996(12)。
[69] 劉平:《勞動價值論的內(nèi)在邏輯及其經(jīng)濟(jì)哲學(xué)蘊(yùn)涵——社會變遷的一種經(jīng)濟(jì)學(xué)視角》,載《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0(S1)。
[71][80] 張忠任:《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微觀法則與宏觀特征》,載《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評論》,2011(2)。
[74] 郝玉柱:《論勞動生產(chǎn)率與價格總水平的關(guān)系》,載《生產(chǎn)力研究》,1995(9)。
[75] 白瑞雪、白暴力:《勞動生產(chǎn)率與使用價值、價值和價格變化的辯證關(guān)系》,載《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評論》,2012(7)。
[81] 朱殊洋:《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率的關(guān)系——對程恩富、馬艷理論的數(shù)理分析與評述》,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5)。
[82] 馬艷:《勞動生產(chǎn)率與商品價值量變動關(guān)系的理論界定及探索》,載《教學(xué)與研究》,2011(7)。
[83] 張銜:《勞動生產(chǎn)率與商品價值量關(guān)系的思考》,載《教學(xué)與研究》,2011(7)。
[84] 馮金華:《單位商品價值量與勞動生產(chǎn)力不可能成正比》,載《財(cái)經(jīng)研究》,2013(8)。
(責(zé)任編輯 武京閩)
《中國人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6年總目錄
(括號內(nèi)數(shù)字前者為期數(shù),后者為頁碼)
第一期
企業(yè)發(fā)展和養(yǎng)老保險(xiǎn)制度變革
第三支柱商業(yè)養(yǎng)老保險(xiǎn)頂層設(shè)計(jì):稅收的作用 及其深遠(yuǎn)意義
鄭秉文(1,2)
養(yǎng)老保險(xiǎn)中的市場力量:中國企業(yè)年金的發(fā)展
韓克慶(1,12)
基本養(yǎng)老保險(xiǎn)費(fèi)率:國際比較、現(xiàn)實(shí)困境與改革方向
蘇中興(1,20)
企業(yè)年金對員工工作搜尋和任期的影響——基于雇主—雇員匹配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徐長杰 曾湘泉(1,28)
企業(yè)年金參與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雇主—雇員匹配數(shù)據(jù)的實(shí)證研究
郭 瑜 田 墨(1,37)
政治正當(dāng)性、合法性與正義
楊偉清(1,44)
論內(nèi)在的政治自由主義
惠春壽(1,54)
儒家會如何看待同性婚姻的合法化?
張祥龍(1,62)
“陰陽”新釋——從梅洛-龐蒂的“身體間性”出發(fā)
張?jiān)倭?王建華(1,71)
論從經(jīng)驗(yàn)理性出發(fā)的社會治理
張康之(1,81)
回應(yīng)性監(jiān)管理論及其本土適用性分析
劉 鵬 王 力(1,91)
漢末魏晉以“清”為美探源
袁濟(jì)喜(1,102)
將“癥候解讀”引入文學(xué)批評——馬舍雷的文學(xué)生產(chǎn)理論
姚文放(1,112)
19世紀(jì)中國茶葉與鴉片經(jīng)濟(jì)之比較
仲偉民(1,119)
二十等爵確立與秦漢爵制分層的發(fā)展
孫聞博(1,131)
人類學(xué)視野下的商品生產(chǎn)與消費(fèi)——從西方工商人類學(xué)的發(fā)展談起
劉 謙 張銀鋒(1,138)
論中國傳統(tǒng)術(shù)治主義
彭新武(1,147)
“平等主義與優(yōu)先論”學(xué)術(shù)研討會綜述
胡業(yè)成(1,155)
第二期
環(huán)境公益訴訟的基本原理與制度適用
論檢察機(jī)關(guān)在環(huán)境公益訴訟中的角色與定位——兼評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機(jī)關(guān)提起公益訴訟改革試點(diǎn)方案》
李艷芳 吳凱杰(2,2)
利益交錯中的環(huán)境公益訴訟原理
肖建國(2,14)
論環(huán)境民事公益訴訟救濟(jì)的實(shí)體公益
竺 效(2,23)
環(huán)境公益訴訟制度擴(kuò)張解釋論
黃忠順(2,32)
道德歷史人類學(xué)視域中我國多民族道德生活的歷史變遷
李 偉 陳文江(2,43)
規(guī)范判斷的特征與功能
徐夢秋 楊 松(2,51)
工業(yè)化、人口轉(zhuǎn)型與長期農(nóng)業(yè)增長的差異化路徑
郭劍雄(2,58)
我國稅制演變影響因素分析——以稅種結(jié)構(gòu)變動為視角
劉振亞 李 偉(2,69)
經(jīng)濟(jì)發(fā)展、環(huán)境污染與公眾環(huán)保行為——基于中國CGSS2013數(shù)據(jù)的多層分析
王玉君 韓冬臨(2,79)
我國新醫(yī)改背景下的醫(yī)療服務(wù)公平研究
王文娟(2,93)
從權(quán)力改變處境的功能區(qū)分權(quán)力的不同類型
張乾友(2,101)
“儒家式權(quán)利”建構(gòu)的可能及嘗試
臧豪杰(2,110)
軒轅譜系與中國“四方”治法之雛形
杜文忠(2,118)
清代督撫在清理“錢糧虧空”中的權(quán)力、責(zé)任與利益
劉鳳云(2,130)
金融危機(jī)后產(chǎn)出缺口理論的回顧、反思與最新進(jìn)展
劉元春 楊丹丹(2,142)
大道至簡說華為——讀《華為你學(xué)不會》有感
張玉梅(2,155)
第三期
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守正與創(chuàng)新
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的前史形態(tài)——試論馬克思恩格斯1833—1844年的批評理論
張永清(3,2)
論馬克思主義文學(xué)批評中國形態(tài)的民族之維
胡亞敏(3,12)
馬克思主義批評視域中的文學(xué)事件論
張 進(jìn)(3,21)
論東歐新馬克思主義戲劇批評
傅其林(3,31)
權(quán)力與權(quán)威:新的解釋
俞可平(3,40)
馬克思早期批判思路的形成路徑——自由與平等、公平與正義:理念與現(xiàn)實(shí)的悖論
魏小萍(3,50)
易受傷害性:女性主義倫理學(xué)的闡釋
肖 巍(3,56)
工業(yè)革命中生產(chǎn)組織方式變革的歷史考察與展望——基于康德拉季耶夫長波的分析
黃陽華(3,66)
城鎮(zhèn)化的古典模式與新古典模式
吳 垠(3,78)
繼承人社會資本對代際傳承中企業(yè)創(chuàng)新的影響
趙 晶 孟維烜(3,91)
質(zhì)量控制與成本管理的變革阻力是否會倒逼企業(yè)的戰(zhàn)略變革?——基于案例調(diào)查的研究
戴 璐 羅曉蕾 支曉強(qiáng)(3,106)
反思企業(yè)社會責(zé)任的康德主義辯護(hù)
文躍然 解本遠(yuǎn)(3,120)
民主與專業(yè)的平衡:稅收法定原則的中國進(jìn)路
徐陽光(3,126)
我國律師辯護(hù)保障體系的完善——以審判中心主義為視角
陳衛(wèi)東 亢晶晶(3,136)
國外政治學(xué)實(shí)驗(yàn)研究的發(fā)展及其對于中國政治學(xué)研究的價值
王金水 胡華杰(3,147)
第四期
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及其支持體系
我國當(dāng)前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新形態(tài)、新趨勢與新問題
金元浦(4,2)
文化與科技融合創(chuàng)新:演進(jìn)機(jī)理與歷史語境
李鳳亮 宗祖盼(4,11)
新常態(tài)下中國文化產(chǎn)業(yè)金融支持體系的學(xué)理探討
魏鵬舉(4,20)
亞里士多德論德性的四重統(tǒng)一
劉 瑋(4,26)
參與者視角與旁觀者視角——黑格爾論任性與自我決定判準(zhǔn)的適用性
陳 浩(4,38)
普雷維什—辛格新假說與新李斯特主義的政策建議
賈根良 沈梓鑫(4,46)
論搭售的反壟斷爭議
吳漢洪 鐘 洲(4,55)
政治審慎:重申作為一種智慧的政治學(xué)
陳華文(4,66)
探索中國政治傳播的新境界
荊學(xué)民(4,74)
論政府與公眾間距離的形成
劉小燕(4,82)
重建公共行政的道德秩序
張成福 馬子博(4,90)
傳統(tǒng)忠德在現(xiàn)代行政倫理中的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
鄯愛紅(4,101)
公眾環(huán)境知識測量:一個本土量表的提出與檢驗(yàn)
洪大用 范葉超(4,110)
大眾媒介對我國城鄉(xiāng)居民環(huán)保行為的影響——基于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diào)查數(shù)據(jù)
張 萍 晉英杰(4,122)
感性整體——麥克盧漢的媒介研究與文學(xué)研究
金惠敏(4,130)
形式主義文論中的唯科學(xué)主義批判
黃念然(4,140)
“由舊入新”與“無中生有”:民國初年的文史之學(xué)
姜 萌(4,148)
第五期
中國宏觀經(jīng)濟(jì)發(fā)展與經(jīng)濟(jì)政策轉(zhuǎn)型
中國經(jīng)濟(jì)增長進(jìn)程中的動能切換與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
劉鳳良 章瀟萌(5,2)
中國宏觀經(jīng)濟(jì)政策體系面臨的困境與改革方向
陳彥斌 劉哲希(5,12)
近年來中國宏觀調(diào)控和經(jīng)濟(jì)政策的特征分析
毛振華 張英杰 袁海霞(5,21)
中國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轉(zhuǎn)型升級中的障礙、困局與改革展望
張 杰(5,29)
先秦秦漢“性”字的多義性及其解釋框架
方朝暉(5,38)
從“物·事論”看和辻倫理學(xué)的“間柄”結(jié)構(gòu)
林美茂(5,48)
《神圣家族》對思想政治教育理論的啟示
張 智 劉建軍(5,57)
自然哲學(xué)的研究傳統(tǒng)與當(dāng)代定位
劉勁楊 李健民(5,65)
中國城市創(chuàng)業(yè)指數(shù)編制與測算研究
袁 衛(wèi) 吳翌琳 張延松 唐麗娜(5,73)
從反應(yīng)式治理到參與式治理:地方政府危機(jī)治理轉(zhuǎn)型的趨向
張緊跟(5,86)
供應(yīng)鏈金融的演進(jìn)與互聯(lián)網(wǎng)供應(yīng)鏈金融:一個理論框架
宋 華 陳思潔(5,95)
當(dāng)代中國糾紛解決機(jī)制的轉(zhuǎn)型
郭星華(5,105)
國際環(huán)境法造法機(jī)制研究
曹 煒(5,113)
跨學(xué)科跨文化的現(xiàn)代斯拉夫文論
周啟超(5,122)
韓禮德與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系統(tǒng)功能語言學(xué)的范式設(shè)計(jì)溯源
彭宣維(5,130)
關(guān)于《被竊的信》:德里達(dá)對拉康
馬元龍(5,139)
社會科學(xué)研究中實(shí)驗(yàn)方法的應(yīng)用與反思——以政治學(xué)科為例
臧雷振(5,150)
第六期
空間維度的中華文學(xué)史研究
唐宋詩歌版圖的空間分布與位移
王兆鵬(6,2)
湖畔水濱:清代江南文學(xué)社團(tuán)的創(chuàng)作現(xiàn)場
羅時進(jìn)(6,10)
小玲瓏山館:一個“有意味”的文學(xué)空間
朱萬曙(6,20)
面向未來的公共主義發(fā)展觀
郭 湛 桑明旭(6,30)
正義的解構(gòu)與馬克思主義正義原則的建構(gòu)
林育川(6,38)
儒家孝道中的性別難題——以匡章事件為中心的討論
陳繼紅(6,46)
約翰·塞爾論集體意向
田 潔(6,57)
中國經(jīng)濟(jì)減速的原因與出路
方福前 馬學(xué)俊(6,64)
稅收腐敗的動因與治理:基于征納行為的理論考察
谷 成 斯旺都·西雷特 曲紅寶(6,76)
基于門限自回歸模型的中國財(cái)政風(fēng)險(xiǎn)預(yù)警系統(tǒng)
孟慶斌 楊俊華(6,86)
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的妥協(xié)與社會矛盾
吳忠民(6,95)
全面兩孩政策執(zhí)行中生育成本的分擔(dān)——基于國家、家庭和用人單位三方視角
宋 健 周宇香(6,107)
技術(shù)治理的邏輯
劉永謀(6,118)
信息哲學(xué)對哲學(xué)的根本變革
鄔 焜(6,128)
西漢海昏侯國的租稅收入蠡測
溫樂平(6,136)
生產(chǎn)率與價值量關(guān)系的爭論:演變與分歧
劉 磊(6,143)
The Debat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ductivity and Magnitude of Value: Evolution and Divergence
LIU Lei
(School of Economics,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Henan 450046)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ontroversy in China over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magnitude of value, and explores the key points of the disagreement in each period of the controversy. Early debates focused on the simultaneous relationship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magnitude of value between the economic agents in the same period. It changed onto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of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magnitude of value betwee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same agent, with development of the approach of “the labor amount in labor time”. The essential disagreement in early debates was which one possesses the priority between the individual value and the social value. The approach of “the labor amount in labor time” brought about the difference o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amount of labor. There are two major differences at the present time. On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oposition that the magnitude of value is direct proportion to the productivity and the proposition of inverse proportion. The other is how to perceive the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labor theory of value.Key words: productivity; magnitude of value; excess surplus value; complex labor; aggregate social labor
劉磊:法學(xué)博士,河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經(jīng)濟(jì)學(xué)院講師(河南 鄭州 45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