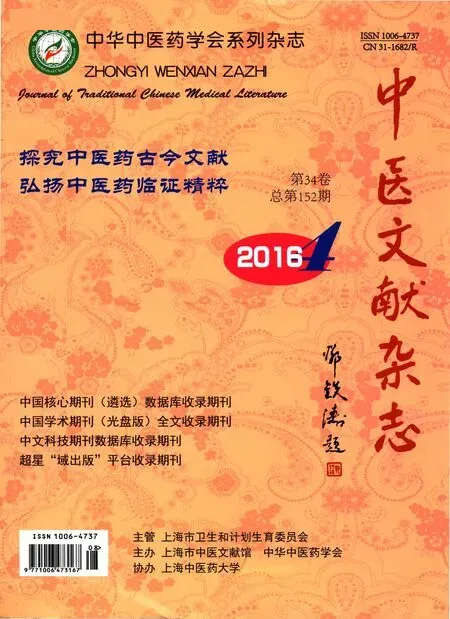古代中醫“腦”范疇自宋代以來的流變研究*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100029)
秦曉慧 張寧怡 牛一焯 王林云 段曉華△
?
·學術探討·
古代中醫“腦”范疇自宋代以來的流變研究*
北京中醫藥大學(北京,100029)
秦曉慧張寧怡牛一焯王林云段曉華△
中醫早在《黃帝內經》中便已對“腦”有所認識,隨著醫學的發展,中醫對“腦”的認識也不斷加深,在經歷了宋元科學技術發展及明清西方科技傳入的影響之后,古代中醫對腦的認識有了巨大的發展。本文即從宋、元、明、清等歷史角度,探討了宋以來不同社會思潮對中醫腦范疇研究的影響,以及宋以來古代中醫腦范疇的流變過程。
中醫腦沿革
中醫對“腦”這一概念的認識由來已久,早在《黃帝內經》當中,就已有關于心與腦孰主神明的論述。《素問·靈蘭秘典論》篇有:“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這里說心是神明的主宰。而《素問·脈要精微論》中說:“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 則精神將奪也。”《靈樞·海論》中有:“人始生,先成精, 精成而腦髓生。”然而《內經》當中構建的是以五臟為中心的理論體系,腦雖也被列為奇恒之腑之一,但腦與神明相關的認識并不是藏象學說的核心內容。此后的醫家在對孰主神明這一問題的探討上,大多數秉持了《內經》心主神明的觀點,但還有一些醫家對腦及其功能、腦與神明的關系有所思考,尤其是宋明理學的興盛,促使一批醫家對中醫腦范疇進行了深入的理性思考。本文通過梳理宋代至清代中晚期社會因素與文化思潮的發展變化,探索其對中醫腦范疇認識的內在影響,以及古代中醫腦范疇自宋以來的流變過程。
宋元時期
1.時代背景
宋元時期社會經濟較為發達,在此基礎上,此時期的科學技術也保持著持續發展,其中即包括了醫學。宋金元時期,政府十分注重醫學的發展,積極發展醫學教育,培養了大批醫學人才,此舉為基礎理論的創新奠定了基礎。此外,戰爭及社會需求、醫學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也對醫學基礎理論的創新產生了積極影響。
宋元時期出現的理學與新學等具有革新思想的學術流派,其學風亦促進了醫學界的學術爭鳴,在寬松的學術氛圍中,宋金元醫家敢于疑古,在繼承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紛紛提出新的學術觀點[1]。
2.“腦”概念范疇的流變
宋元時期的醫家大多還是秉持《內經》中“心主神明”的觀點,但有部分醫家對于腦的認識已不再拘泥于《內經》時的內容,開始認識到“腦主神明”的功能,在臨床治療中對腦病的證治經驗也更為豐富。
北宋政府編撰的《圣濟總錄》謂: “五臟六腑之精華,皆見于目,上注于頭。”“論曰凡腦為物所擊, 傷破而髓出者, 治療宜速。蓋頭者諸陽所會, 囟者物有所受命, 若腦破髓出, 稽于救治, 斃不旋踵, 宜速以藥封裹, 勿為外邪所中, 調養榮衛, 安定精神, 庶幾可活, 其證戴眼直視不能語者, 不可治。”《普濟方》亦有:“蓋頭者諸陽所會, 腦者物所受命。”此時便已認識到,任物者謂之囟(腦),這是對《內經》中“所以任物者謂之心”的創新與變革,并且強調了腦部受傷時急救的重要性[2]。宋代陳無擇也在《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一書中論述了腦與神的密切關系:“頭者,諸陽之會,上丹產于泥丸宮,百神所集。”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東垣在《脾胃論》中載張元素之說:“視聽明而清涼,香臭辨而溫暖,此內受腦之氣而外利九竅者也。”則明確寫到了腦對視覺、嗅覺的支配作用[3]。
在對有關腦的生理功能的認識有所加深的同時,宋元時期對于腦病的證治亦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圣濟總錄》中有專題討論“諸風”的辨證論治,說明對“風證”的治療頗為重視。該書還首先提出健忘的名稱,一直沿用至今,書中強調心虛、血氣虛衰的影響,列安神定志人參湯、養神湯、開心丸等方治療。金元四大家對腦病的闡述也多有新意,對中風、厥證的論治更為詳細深入。劉河間《素問病機氣宜保命集·瘡瘍論》:“從腦而出,初覺腦痛不可忍,且欲生瘡也。腦者,髓之海,當灸刺絕骨,以泄邪氣。”強調腦者髓之海[3]6- 9。
3.小結
由上可知,宋元時期的醫家對腦主神明有了初步的認識,雖對《內經》中“心主神明”之說有所突破,但在理論上對于腦的生理功能的認識還是處于一種零散且不甚具體的階段,更多的還是注重腦病的臨床證治方面。對腦中風、癲證、狂證等腦病的病因學有了更加深入的發展,并提出治療方法;至寶丹、蘇合香丸等著名方劑亦被創制。
明 朝
1.時代背景
明朝是我國古代科技發展的一個高峰,尤其是晚明時期,一方面各種社會矛盾的加劇激發了有志學者經世致用、發展科學技術以解救危機的熱情,一方面經濟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萌芽也伴隨著人們思想上的激變,在對逐漸變得空疏無用的的理學進行批判時,出現了主張實行實用的實學思潮。除了明朝內部自身的劇烈變化之外,因中西方交流的加深,西方傳入的知識也給明朝的學者以思想和科技上的強烈沖擊,而西方科學知識所倡導的注重實測的方法也對晚明的學者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理學“格物致知”和實學注重實踐的影響下,明朝的醫家更為注重實踐觀察,不盲從經典所言,而是從臨床實踐中觀察歸納總結以得出結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晚明時期西方來華傳教士傳入的一些西醫知識也引起了一些醫家和學者的重視,這些西醫知識對晚明中醫的發展也起到了推動作用。
2.“腦”概念范疇的流變
在繼承和發揚前人對腦的認知的基礎上,明代醫家又從臨床實踐中總結發展出新的腦理論,獨立創新之余,也學習吸納西方解剖學知識,使得此時期的腦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明永樂年間成書的《普濟方》中寫有:“腦為髓之海也,頭者諸陽之會,上丹產于泥丸,內則百神之所聚,為一身之元首也。”強調了腦總統眾神。李梴在《醫學入門·臟腑》中說:“有血肉之心,形如未開蓮花,居肺下膈上也。有神明之心,神者,氣血所化,生之本也……主宰萬事萬物。”這里所說的形如未開蓮花的“血肉之心”即是指位于胸中的心臟;而主宰萬事萬物的“神明之心”顯然不同于前者,說明李梴已經意識到主宰神明的并不是解剖學上的心,而是另有所在[4]。李梴還明確指出腦與脊髓的關系,其云:“腦者髓之海,諸髓皆屬于腦,故上至腦,下至尾骶,髓責腎主之。”
此時期在腦理論上最為突出的成就當屬李時珍提出的“腦為元神之府”的觀點。李時珍所著《本草綱目》的“辛夷”篇中寫有:“鼻氣通于天。天者,頭也,肺也。肺開竅于鼻,而陽明胃脈環鼻而上行。腦為元神之府,而鼻為命門之竅。人之中氣不足,清陽不升,則頭為之傾,九竅為之不利。”這是我國醫學史上首次明確地提出腦主神明的觀點。李時珍“腦為元神之府”的理論是在繼承總結前人關于“頭”和“泥丸”的認識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這一見解突破了長期以來“心主神明”的說法。這較之“腦為髓之海”(《靈樞·海論》)的認識有了極大的升華[5]。
晚明時期,西方傳教士傳入了一些西方醫學知識,其中利瑪竇所著《西國記法·原本篇》簡要講述了西方對腦的結構和功能的認識,即腦與記憶的關系:“記含有所在腦囊,蓋顱囟后、枕骨下為記含之室。故人追憶所記之事驟不可得,其手不覺搔腦后, 若索物令之出者,雖兒童亦如是。或人腦后有患則多遺忘。”此“腦囊記憶說”全新于中醫對腦的傳統認知,故被當時的一些學者和醫家所學習與接受。晚明的金正希曾接受西說,在其《尚志堂文集·見聞錄》中云:“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善忘者,腦未滿也,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凡是一形,必有一形留于腦中。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腦之意也。”這里明確指出了人的記憶功能在于腦。
還有其他醫家對腦的生理功能也有深入的認識,如王慧源在《醫學原始》中說:“五官居身上,為知覺之具。耳目口鼻聚于首,最顯最高,便于接物。耳目口鼻之所導入,最近于腦,必以腦先受其象而覺之,而寄之,而存之也。”“腦顱居百體之首,為五官四司所賴,以攝百肢,為運動知覺之德。”指出了腦對五官感覺、肢體運動等的支配作用[3]11,28。
在腦髓病變辨證治療方面,明朝醫家在生理病理、病機證候、治療方藥方面均有所發揮,研究得更為深入,經驗更為豐富。從所運用的方藥來看,不僅有立足整體觀念從臟從腑、從氣從血治腦病者,而且出現了大量治療腦病的專方[6]。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宋元到明代各醫家有關腦的論述中,常可見到“泥丸”一詞。“泥丸”源于道家,道家把腦分為九宮,其最為重要者稱為泥丸,泥丸為元神所居之宮,如《金丹正理》曰:“ 頭有九宮, 上應九天, 中間一宮, 謂之泥丸, 又曰黃庭, 又名昆侖, 又名天谷, 其名頗多, 乃元神所住之宮, 其空如谷, 而神居之, 故謂之谷神。神存則生, 神去則死, 日則接于物, 夜則接于夢。”道家對于腦有其獨特的認識,而中醫與道家醫學有很深的淵源,中醫對腦的認識也受到了道家的影響[7]。
3.小結
將明朝與宋元時期的中醫對腦的認識進行對比,可以看出宋元時期對腦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臨床證治等各方面的認知都顯得相對簡略,特別是腦理論上的內容更多的還是處于一種萌芽的狀態,而明朝時則以李時珍明確提出的“腦為元神之府”之觀點為代表,突破了《內經》的局限,創立腦理論新說。“腦為元神之府”雖未論及腦的思維、記憶等生理功能,但其強調了腦的重要性,為后代醫家逐漸把“心主神明”更正為“腦主記憶”,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8]。而后傳入的西醫“腦囊記憶說”被部分學者醫家接受,其中所言“腦主記憶”亦逐漸被吸收到中醫腦范疇當中,為傳統中醫理論注入了新的思想。
清朝(1644- 1840年)
1.時代背景
清朝初年延續了晚明時期的學術氛圍與學風,清朝中期社會開始顯出衰落之勢,到晚清時,社會因內憂外患而動蕩不安,思想文化因此而發生變革,實學中經世致用之精神再一次受到重視,實用的西方文化在帶來沖擊的同時也被不斷吸收接納,學者的研究也更多了幾分科學實證的精神。
明朝李時珍、金正希等醫家將腦的研究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此基礎上也激發了新一代學者對中醫腦科的探索。
2.“腦”概念范疇的流變
清朝時期對中醫腦學說有深入研究者眾多,而在本文所探討的歷史時段里,最為有代表性的醫家當屬汪昂和王清任。
汪昂為明末清初人,其繼承李時珍“腦為元神之府”之說,又經金正希傳西方“腦囊記憶說”,形成了新的腦理論。其著作《本草備要》中載有:“吾鄉金正希先生嘗語余曰: 人之記性皆在腦中。小兒善忘者, 腦未滿也; 老人健忘者腦漸空也。凡人外見一物, 必有一形影留于腦中。昂思今人每記憶往事, 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 此即凝神于腦之意也。不經先生道破, 人皆習焉不察焉。李時珍曰: 腦為元神之府。其于此義殆暗符欽! ”可見汪昂認同李時珍之論,并將之與西方腦學說相結合,指出腦主記憶。
及至王清任,他積極吸取明清腦學說的成就,結合自己親手解剖尸體臟腑、實地觀察實驗所得的結果,創造性地提出了“腦髓說”,認為“靈機記性不在心而在腦”,并從多方面進行了論證。第一,王清任從解剖學的角度論述“腦髓”的概念:“靈機記性在腦者,因飲食生氣血,長肌肉,精汁之清者,化而為髓,由脊骨上行入腦,名曰腦髓。盛腦髓者,名曰髓海,其上之骨,名曰天靈蓋。”明確指出了腦與脊髓的解剖部位。同時還論述了腦與五官的解剖及功能之關聯:“兩耳通腦,所聽之聲歸于腦。……兩目系如錢,長于腦,所見之物歸于腦,……鼻通于腦,所聞香臭歸于腦。”說明了腦能接收其他器官傳來的信息,能支配人體的感覺功能。第二,王清任通過仔細觀察兒童腦髓發育狀況,精細闡述小兒顱腦和神經系統發育過程:“小兒初生時,腦未全,囟門軟,目不靈動,耳不知聽,鼻不知聞,舌不言。至周歲,腦漸生,囟門漸長,耳稍知聽,目稍有靈動,鼻微知香臭,舌能言一二字。至三四歲,腦髓漸滿,囟門長全,耳能聽,目有靈動,鼻知香臭,言語成句。”小兒能具有初步的意識活動有賴于腦的發育,這進一步論證了人腦具有產生感覺,主管語言、思維的功能。第三,王清任認為腦主記憶:“小兒無記性者,腦髓未滿;高年無記性者,腦髓漸空。”并引汪讱庵之語:“今人每記憶往事,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這說明腦具有主記憶的功能,而且腦髓充足與否決定著記憶功能的強弱,髓海充足則記憶牢固,不足則反之。第四,王清任通過觀察中風病人口眼喎斜之狀,發現“凡病左半身不遂者,喎斜多半在右;病右半身不遂者,喎斜多半在左”, 因此推斷腦有交叉支配運動的特點:“人左半身經絡,上頭面,從右行;右半身經絡,上頭面,從左行,有左右交互之義。”說明經絡左右交叉循行,因而腦交叉支配軀體運動[9]。
在臨床病癥方面,王清任對腦病的認識亦有其獨到之處。如《醫林改錯》中記錄了34種中風前驅癥狀,觀察入微。“有云偶爾一陣頭暈者,……有耳內無故一陣風響者, ……有無故一陣眼睛發直者, ……有睡臥口流涎沫者, 有平素聰明忽然無記性者, ……”王清任主張, 認識這些癥狀, 有效防止中風[10]。
王清任“腦髓說”是我國古代中醫腦學說發展到一個較為成熟階段的成果,其繼承了諸多醫家的學說,在《醫林改錯》中,王清任就清楚地寫道:“李時珍曰:‘腦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記性皆在腦中。’汪讱庵曰:‘今人每記憶往事, 必閉目上瞪而思索之。’”說明他繼承并發展了李時珍、金正希和汪昂的學術思想,也通過金正希和汪昂間接接受了西醫學說,并加入自己的新認識,才形成了較為完備而系統的“腦髓說”。
3.小結
清朝(1644- 1840年)時對腦的認識以《醫林改錯》為代表,已基本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理論系統,王清任不僅在解剖學上觀察到腦的定位,還觀察到腦系神經系統的走行,從大量臨床案例中詳細總結出諸多腦系病癥的癥狀并創立相應的治療方劑。相較前朝稍顯單純的研究腦的生理功能、病理變化、臨床證治等內容,此時期將“腦”的范疇發展成了一個立體的系統,其中除了上述所言內容外,還探討了腦與人體五官肢節、生長發育、言語思維記憶等之間的緊密聯系,明確了腦對于人的精神的重要性,形成了完全異于《內經》“心主神明”的理論,是中醫腦學說發展的一次質的飛躍。
總 結
自《內經》以來,“心主神明”之說便占據了統治地位,腦之功能多被分散至心甚者其余臟腑之中,此后的醫家雖多秉持《內經》中的觀點,但臨床的實踐依舊會令人們開始認識并思考腦的重要性,并不斷加深對腦的研究。縱觀宋代至清代前中期這段歷史,可以看出社會的實際需求、思想的交匯碰撞、醫學自身發展的需求等因素都是推動中醫學發展的積極動力,這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實踐,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結論,而古代中醫對腦范疇的研究,從“腦者物所受命”到“靈機記性不在心而在腦”,也正是在實踐中不斷思考與總結,在西學的沖擊下不斷探索與創新,從而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登上了新的歷史高度。
[1]李成文,司富春.宋金元時期中醫基礎理論創新研究[J]. 中華中醫藥雜志(原中國醫藥學報), 2010,25(7):985- 989.
[2]鄭國慶.論《圣濟總錄》腦者物有所受命[J]. 浙江中醫藥大學學報,2008,32(4):430- 431.
[3]王永炎,張伯禮.中醫腦病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6- 9,6- 9,11,28.
[4]許沛虎.中醫腦病學[M].北京: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1998:7- 9.
[5]吳運泉,吳懿,季波,等.《本草綱目》對腦科的貢獻[J]. 亞太傳統醫藥,2006,(9):34- 37.
[6]金香蘭.中醫腦髓學說源流考[J].中國醫藥學報,1997,12(5):21- 24,64.
[7]張俊龍.中醫腦理論演進軌跡[J].山西中醫學院學報,2001,3(2):43- 47.
[8]童良康.李時珍“腦為元神之府”并未論及腦主思維和記憶的功能[J].醫古文知識,1996,(3):36- 37.
[9]何玉德.再談王清任是中國近代“腦髓說”的真正創立者——兼評方以智對“腦髓”的認識[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4):53- 60.
[10]徐瑛,張云鵬.明清時期腦的學說發展舉要[J].遼寧中醫雜志,2004,31(12):990- 991.
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Brai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ince the Song Dynasty
QIN Xiao-hui, ZHANG Ning-yi, NIU Yi-zhuo, WANG Lin-yun, DUAN Xiao-hua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Beijing 100029,China)
As early as in The Medical Classic of theHuangDiNeiJ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has already recognized the concept of “brai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edical science, TCM also has deepened its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 of “brain”. Ancient TCM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 of “brain” by the influen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as well as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ties. From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ranging from Song to Qing Dynasty, the thesis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social thoughts on the concept of “brain” in TC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brain” in TCM since the Song Dynas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Brain; evolution
北京市共建項目“探討中國社會發展對中醫‘腦’概念之變遷的影響”
R223.1+3
A
1006- 4737(2016)04- 0027- 05
2016- 01-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