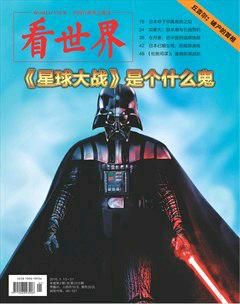沙特:美國的盟友還是敵人?
李明波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沙特是國際舞臺上的幕后角色。普通中國人對沙特的認識更多地停留在經濟層面,比如說沙特是世界第一大產油國。見識再豐富一點的人,會知道沙特女性的社會地位非常低。實際上,習慣隱藏在幕后的沙特,其實一直是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強國之一。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一直非常看重沙特在中東的角色,并將沙特視為美國在中東第二重要的盟友,僅次于以色列。曾兩次出任小布什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波斯灣事務主管的肯尼斯·波拉克這樣描述美國中東政策的基石:“美國在中東的首要利益是石油,其次就是維護以色列、沙特等盟友國家的關系。”沙特之所以能成為中東地區最重要的強國之一,除了自身擁有驚人儲量的石油資源外,伊斯蘭教的兩大圣地麥加和麥地那都位于沙特境內,沙特王室以“圣地守護者”的身份出現在伊斯蘭世界中,增加了其權威性。
不過進入2015年以來,沙特已經不甘居于國際舞臺的幕后,也因此惹出不少麻煩,甚至是笑話。比如沙特宣布將組建一個有34個國家參加的伊斯蘭軍事聯盟以打擊恐怖主義,但這個反恐聯盟中包含的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卻一臉無辜地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有這個聯盟,更沒有參加這個聯盟。此外,去年早些時候,沙特曾聯合多個阿拉伯國家出兵也門,試圖彈壓也門境內的胡賽武裝,但戰果平平,甚至將戰火引入自己邊境線。
沙特外交政策的悄然轉變是有著復雜的戰略背景。沙特雖為富裕的石油王國,但軍力薄弱。身處動蕩不已的中東和海灣,面對伊朗等地區強國的威脅,沙特不得不尋求美國的安全庇護。然而,頁巖油革命和新能源崛起,不僅使沙特賴以生存的石油大幅貶值,還導致其戰略地位顯著下降。美國減少進口沙特石油,使沙美關系的根基遭到動搖。在沙特看來,2015年伊朗核問題的解決,便反映了沙美關系的根本性變化。沙特戰略地位下降,導致其重大安全利益被美國“出賣”。
確實如沙特王室自己感受到的一樣,美國與沙特的關系正在發生某種變化。這一點可以從西方報紙上讀出來,從西方政治家們口中聽出來,從西方外交政策轉變中看出來。對沙特懷有敵意的文章如今已成為西方媒體的標配。德國副總理西格馬爾·加布里爾公開指責沙特為在西方活動的伊斯蘭極端主義分子提供資金,并補充稱:“我們必須讓沙特明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的日子已經結束。”
西方對沙特突然激增的擔憂很大程度上是由“伊斯蘭國”崛起帶來的。西方政策制定者在尋找“伊斯蘭國”世界觀的根源時,他們越來越多地追溯到了沙特宗教機構所倡導的瓦哈比主義。事實上,“伊斯蘭國”的意識形態——薩拉菲主義與沙特的瓦哈比主義同宗同源,“伊斯蘭國”還在其控制區內的學校使用沙特教科書作為教材,讓沙特百口莫辯。自建國以來,沙特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廣瓦哈比主義。令奧巴馬政府感到憤怒的是,沙特政府不肯出一兵一卒打擊“伊斯蘭國”,但卻強行出兵干涉其南部鄰國也門的內政。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對沙特的不信任感由來已久。比如“9·11”事件中19名劫機者有15名沙特公民,其策劃者本·拉丹更是與沙特王室關系密切。盡管沙特政府一直試圖撇清和基地組織的關系,但沙特始終無法拿出讓人心服口服的證據。只不過,西方對沙特的石油依賴讓這種不信任感只能停留在桌底下。不過,近年來美國的“頁巖革命”使西方國家減少了對沙特石油的依賴,美國與沙特的不睦也逐漸公開化。美國對沙特的防范在過去一年確實在升級。外界普遍認為,原本不被看好的伊朗核談判之所以能在2015年取得大突破,關鍵在于美國希望改善與伊朗的關系,以什葉派的伊朗制衡遜尼派的沙特,甚至不排除在未來用伊朗取代沙特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