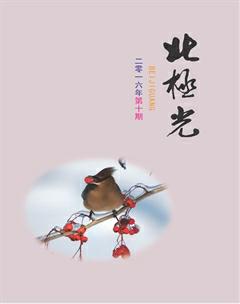高管人員勞動管理的現實困境與對策思考
文/謝慧婷
高管人員勞動管理的現實困境與對策思考
文/謝慧婷
法律對勞動者的分類管理沒有明確規定,高管作為特殊的勞動者,具有其特殊性:監督管理、占據優勢、享有決定,因而兼具有管理者與決策者雙重身份。高管引發的勞動爭議在勞動管理中經常面臨法律適用難題,分析其在勞動管理中現實困境對界定其勞動者的身份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高管人員;勞動者;勞動爭議;路徑選擇
一、高管人員勞動者身份問題的理論探究
近年來理論界和實務界有論者主張“高管不應屬于勞動者,受到勞動法傾斜保護”。比如有學者認為“董事或總經理能夠作出經營決策,傳遞雇主意志。”[1]從中可以看出把高管人員排除在“勞動者”的范疇,而黃越欽教授把服從指示、提供勞務作為認定勞動者的重要因素![2]根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公司章程也沒有明文規定不得將董事列入高管人員的范疇,可以推斷公司章程將董事列入高管人員是合法的。
從“勞動者”這個概念出發:廣義上的勞動者是具有外在資格與內心要素相結合的自然人;狹義上的勞動者就是勞動法上的勞動者。王全興教授認為明顯把“民事法律主體”中自然人的概念引入到勞動法學中來模糊了勞動者的本質特征。[3]造成司法實踐中諸如高管人員、飛行員等是否屬于勞動者的范疇產生爭議。為了有效避免社會較低階層“勞動者”被邊緣化、較高階層“勞動者”被排斥化,細化勞動者身份的認定標準在保護勞動者合法勞動權益方面顯得尤為重要。
從“勞動者”界定的相關學說來考察:大陸法系通說為從屬性,強調勞動關系的依附性,從屬性標準有利于界定勞動者概念的明確性與統一性,但是具體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英美法系以“控制說”理論為主,對勞動者是以雇員來代替,擴張雇傭關系的范圍,甚有學者指出對雇員的控制過于嚴苛極易發生罷工事件。高管人員身份的雙重性決定了其勞動關系的特殊性:一方面高管在勞動關系的博弈之間占據優勢地位,另一方面也擔負著譬如競業禁止等的法定義務。
從勞動關系中的主體定位來分析:學界對此形成了勞動關系肯定說與否定說,有學者認為高管人員不是勞動者。[4]這種看法否定了高管人員與公司之間具有隸屬性,《公司法》中關于董事會解任高管人員的規定為應對突發事件賦予的單方解除權提供了依據,而且企業對高管人員的不當之處可以以無權代理進行追償。明顯高管在現實中還是要受用人單位的組織與管理,對高管人員在勞動關系中的主體適用問題,本文認為要以身份關聯性、勞動從屬性、勞動有償性為核心標準來確定高管人員與公司之間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以控制權的大小來對高級管理人員進行分層化處理。
二、高管人員適用勞動法之現實困境
(一)高管薪酬問題
企業高管的高薪報酬關系勞動者個人收入問題,關系社會財富的分配。高管人員擁有較大的自主權,要求實行嚴格的工時制度在目前的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勞動法》第44條延長工作時間的工資支付就是為了防止公司惡意剝奪勞動者而定的。高管本身享有譬如巨額安置費、享有公司期權等經濟激勵。[5]作為管理者的公司高管極有可能利用職務便利故意不與自己簽訂勞動合同,要求公司就支付兩倍工資的情形。因此,高管身份的特殊性顯然不適用《勞動合同法》的上述規定。
(二)高管與工會的關系問題
工會是勞動者利益的代表者,不參與企業的內部管理。在我國,不少企業高管在工會中身居工會主席要職,依照我國《工會法》工會是群眾組織的規定,高管自然成為工會的會員,難免作為管理方的代表與企業職工同屬于一個工會。同時肩負者企業管理者的利益與企業職工利益,這種矛盾與尷尬的局面不但在工會中起不到任何作用,反而抑制工會的發展,間接損害勞動者的工會權益。為了防止工會制度趨于形式化,有必要參照國外立法,提高高管加入工會組織的門檻。
(三)高管離職糾紛問題
高管一旦離職,所引發的勞動爭議主要體現在:解除合同時相關規定的適用問題、禁業限制和經濟補償金的適用問題等。根據《勞動合同法》關于違約金制度的規定,現只存在服務期和競業限制這兩種情況中,高管人員在勞動期間的禁業限制就是法定義務,在離職后才是約定義務。依據《勞動合同法》第47 條的關于經濟補償金的限制額度規定,體現了勞動法對一般勞動者的傾斜保護,可是實踐中由于高管人員年薪數額巨大,所得到的經濟補償金往往是普通勞動者的好幾倍,明顯有違立法初衷。
三、高管人員勞動管理的對策探究
(一)確立“勞動者分層”管理的立法思路
分層保護的理論依據來源于《勞動合同法》適當傾斜保護這一立法宗旨,譬如美國法律針對20歲以下的雇員就特別規定了培訓工資或者青少年最低工資標準,針對高管人員其稅法明確規定了不得超過100萬美元。[6]限薪問題明顯區分了高管和普通勞動者,而且《德國商法典》第74條明確規定了高管經濟補償金標準問題“企業支付的補償金額不得低于勞動者離職前一年收入的二分之一”,為解決我國高管法律適用問題提供了思路。
(二)強化法律對高管的契約自由
法律事務中,高管拿著蘊含勞動者權利義務內容的經營目標責任書訴至仲裁機構請求雙倍工資,那么此種經營目標責任書能否視為勞動合同呢?個人認為:隨著電子化的普及,勞動合同形式多元化,不能僅從形式上對簽訂勞動合同進行文理解釋,更應當考慮雙方締約的載體是否包含權利義務、工資崗位、績效獎金等方面的約定,實質上具備這些約定,就足以認定簽訂了書面勞動合同。高管人員是否適用“雙倍工資罰則”,應綜合考量高管人員的崗位職責與職權范圍、有無過錯等情況,視具體情形而定。[7]
(三)協調勞動法與公司法
高管對勞動者享有基本權利義務應當完全適用,但是在《勞動法》與《公司法》之間的沖突應當區分合理對待。主要從立法和法律適用方面進行協調:首先高管實現優勝劣汰制,一旦滿足簽約條件就有法定義務簽訂此合同,只是在操作層面可實施調崗;其次在用人單位單方解除合同時應限制適用《勞動合同法》第39條,如果高管失職給公司造成損失,企業依據《公司法》的相關規定對其進行解聘。董事會決議有權解除總經理職務,勞動合同內容的變更并不影響繼續履行合同。[8]最后在違約金條款適用的問題上,高管掌握企業的商業秘密,從長遠來看,事先防范機制遠比事后訴訟更節約成本,故而應當尊重高管與企業之間的意思自治。
[1][德]沃爾夫岡.多伊普勒:《德國勞動法》(第11版),王倩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頁。
[2]參見黃越欽:《勞動法新論》(第5版),翰蘆圖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162—163頁。
[3]王全興:《勞動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8—80頁。
[4]參見問清泓:《論高級管理人員勞動關系調整》,《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0年第8期,第82—86頁。
[5]參見譚艷,余偉:《公司高級管理人員勞動權利義務的特殊性研究》,《企業家天地.理論前沿》,2005年第4期,第12頁。
[6]姚曙明,陳依婷:《論勞動者分層保護的法律規制》,《法學論壇》,2015年第6期,第109頁。
[7]參見曹文兵,林靜寂:《高層管理人員勞動合同的認定與“雙倍工資罰則”的適用》,載《人民法院報》,2014年3月20日。
[8]參見劉繼承:《解聘高管,遵照<公司法>還是<勞動法>》,《人力資源》,2015年第1期,第62頁。
(作者單位:西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