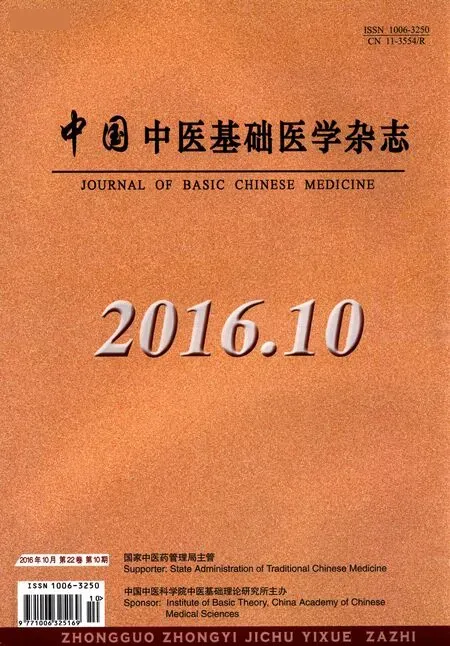對“肝病實脾”相關問題的思考
祝建材,蘇新民
(山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山東煙臺 265200)
對“肝病實脾”相關問題的思考
祝建材,蘇新民
(山東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山東煙臺 265200)
“肝病實脾”最早見于《難經》,是根據中醫五行理論提出的重要治法,體現了中醫治未病的思想。肝脾在生理上關系密切,故病理上肝實也好、肝虛也罷常易傳脾。領會“肝病傳脾”與“肝病實脾”的涵義,對于掌握肝病的傳變規律,推測疾病的轉歸意義甚大。但歷代醫家對于“肝病傳脾”與“肝病實脾”的認識仁智互見,故筆者不揣淺陋提出自己的一管之見,以期提高肝病的治療效果,更好地領會中醫治未病的精髓。
肝病;實脾;治未病;臨床應用
“治未病”首見于《黃帝內經》“不治已病治未病”,奠定了中醫預防醫學的基礎。所謂治未病,包括未病先防和既病防變兩方面,“肝病實脾”當屬于后者。“肝病實脾”首見于《難經·七十七難》:“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之于脾,故先實其脾氣。”《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云:“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補之。”并將“肝病實脾”謂之上工之舉,一直以來“肝病實脾”被視為治未病的典范。因此對“肝病實脾”之治未病思想深加探究,對提高肝病的治療效果、領會中醫治未病的精髓有著重大意義。
1 肝(膽)與脾(胃)的生理關系
肝為剛臟,主疏泄,調暢氣機;脾為濕土,主運化,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肝(膽)與脾(胃)生理上關系密切,一方面“土得木而達之”,即肝的疏泄有助于脾的運化,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一是調暢全身氣機。肝氣疏泄,暢達全身氣機,促進和協調脾胃之氣的升降協調,只有脾升胃降協調,脾的運化功能才能正常,從而促進飲食物的消化、水谷精微的吸收和糟粕的排泄。《血證論·臟腑病機論》云:“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氣入胃,全賴肝木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設肝之清陽不升,則不能疏泄水谷,滲泄中滿之癥,在所不免。”二是促進膽汁的分泌與排泄。膽汁乃肝之余氣所化,其分泌和排泄受肝氣疏泄功能的影響。肝氣疏泄,全身氣機條暢,膽汁化生正常,排出通暢,從而有助于飲食物的消化吸收。三是助脾運化水液。肝之疏泄,既能疏泄脾土助其運化水液,又能使三焦疏利,水道通調。
另一方面“木賴土以培之”,即脾的運化有助于肝的疏泄。脾胃主運化水谷精微,為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脾運強健,化源充足,氣血充盈,則肝血充足而肝有所藏,肝體得養,肝氣沖和條達,疏泄正常。
2 肝實、肝虛皆易傳脾
“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后世很多醫家認為此處肝病乃肝實一證,只有肝實一證才會傳脾,需實脾。尤在涇在《金匱要略心典》中即云:“蓋臟病,惟虛者受之,而實則不受;臟邪,惟實則能傳,而虛則不傳。”《醫宗金鑒》云:“上工不但知肝實必傳,脾虛之病,而且知肝虛不傳脾,虛反受肺邪之病。”臨床上肝氣郁滯之肝實證,即可影響脾氣升清,致脾失健運、清氣不升,可見胸脅脹滿、腹脹腹痛、腸鳴、腹瀉等癥;又可影響胃氣降濁,致胃失和降、胃氣上逆,出現納呆、胸脅脘腹脹滿或疼痛,甚則出現惡心、嘔吐、噯氣、泛酸等癥。
筆者認為,不僅肝實易傳脾,肝虛亦可傳脾。這在《金匱要略》中早有論述。《金匱要略·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云:“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趺陽脈候脾胃,今見微弦,乃肝失疏泄,肝氣乘脾胃之征,脾失健運,故當腹滿;若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乃胃失和降,肝之“虛寒”從下焦上逆所致。《金匱要略·嘔吐噦下利病脈證并治》云:“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干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以方測知,此嘔、干嘔均系肝陽不足、疏泄不及,加之胃虛致胃氣上逆而成。方中吳茱萸暖肝散寒,人參、大棗補胃之虛,生姜溫胃散寒可證。《金匱要略·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云:“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厥陰之寒犯胃,胃失和降,胃不納食,故食則吐。
因此,不管是肝實也好,肝虛也罷,只要肝的疏泄功能失調都會影響脾,導致肝脾同病。需要指出的是“肝病傳脾”亦并非絕對,如肝陽上亢的病人癥見急躁易怒、頭目脹痛、眩暈耳鳴、面色潮紅、失眠多夢、口苦咽干,常因情志不遂而諸癥加重,舌紅少津、脈弦等,卻飲食如常,亦無腹脹、腹瀉等脾失健運之象。所以說肝病容易傳脾,但并非都傳脾。
3 “肝病實脾”的理論基礎
肝病“實脾”,既可使脾(胃)得調,又能使肝病早愈,事半功倍。其理論基于以下三點:一是“實脾”可使脾氣得升,中州氣機升降有常,則肝氣不郁;可使脾氣健旺,水濕得運,膽汁得以輸送、排泄,則濕邪無以郁阻肝膽。二是“實脾”使脾氣健運,體內水濕之邪易除,有利于三焦水道的通利,恢復肝臟調節水液代謝的作用,從而加快肝病康復。三是“實脾”使脾胃強健,氣血化源充足,血液運行有力,使瘀血輕者可祛甚者可緩,有助于肝病的康復[1]。
同時脾屬五行中的土行,生理上脾(胃)主運化,化生水谷精微,為全身臟腑提供營養,是后天之本,氣血生化之源。病理上脾失健運、氣血虧虛、臟腑難和則人體易病,“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治療上“治其肝、心、肺、腎,有余不足,或補或瀉,惟益脾胃為切”;“上下交損,當治其中”。因此,“不理脾則諸疾續起”“理脾則百病不生”[2],上述觀點充分體現了中醫五臟一體觀的學術思想。因此,確保脾運健旺是防治疾病的關鍵所在,對于肝病的治療亦不例外。
4 “實脾”之“實”并非“補”之意
關于肝病“實脾”之法歷代醫家觀點不一。如《臨證指南醫案》云:“夫木郁土位,古人制肝補脾,升陽散邪,皆理偏就和為治。”《金匱要略方論本義》說:“四時之氣始于春,五臟之氣始于肝,故先引肝以為之準。五臟之氣旺,則資其所生,病則侮其所克。所以肝病必傳于脾。”《金匱要略論注》說:“假如見肝之氣病,肝木勝脾土,故知必傳脾,而先務實脾,脾未病而先實之。”《醫宗金鑒》說:“良醫知肝病傳脾,見人病肝,先審天時衰旺,次審脾土虛實”。結合歷代醫家觀點,筆者認為“實脾”并非一味補脾,而是兼顧脾胃,以護脾、醒脾、運脾為要,使之運化功能健全。肝病初期未及于脾時,治肝同時要兼調脾胃,“調其中氣,使之和平”可用醒脾、運脾等法,使脾胃升降有序,脾運健旺,可防肝木來乘,又可使肝木得養,而遂其疏泄條達之性;用藥要以胃氣下行為順,既不能補,也不可過于寒涼,以防傷及脾胃,藥用枳術丸以防土郁。若肝病傳脾,出現木不疏土、脾氣壅滯,癥見脘腹脹滿、大便秘結或有濕熱征象者,此時若選用甘溫補中之法,如黃芪、大棗、炙甘草等補之,則脾氣更加壅滯,肝膽濕熱之邪難以祛除,勢必造成“實實”之戒。此時要采用行氣導滯、運脾降胃之法,選用厚樸、木香、枳殼、檳榔、雞內金、陳皮、焦山楂等,使中樞運轉、脾氣得實,也使濕熱之邪亦從下而去[3]。
5 肝病實脾的臨床運用
5.1 《金匱要略》中肝虛用甘的啟示
《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云:“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這是《金匱要略》提出的肝虛治法。酸入肝,肝虛當補之以本味,故補用酸。焦苦入心,子(心)能令母(肝)實,且肝虛易受肺金來乘,助心火可制約肺金,所以助用焦苦。甘藥能夠調和中氣,補土制水,水弱則火旺,從而制金以防其乘肝木,且肝苦急,急食甘味藥物以緩之;另外,酸甘化陰以養肝體。后世根據酸甘焦苦合用的原則,選用芍藥、當歸、五味子、丹參、地黃等藥,配以炙甘草、淮小麥、大棗之屬來治療頭暈目眩、失眠多夢、舌紅少苔、脈弦細之肝虛證,療效確切。
5.2 方藥配伍中體現肝病實脾
《景岳全書》中解肝煎(白芍、蘇葉、砂仁、半夏、陳皮、厚樸)方名為解肝,但方中除蘇葉理氣、白芍養肝外,均屬調理脾胃、化濕行滯之品,適用于肝郁脾壅的證候。因濕困脾胃導致肝氣不疏,須注重中焦治本,故方中用蘇葉疏肝而不用柴胡,取其既能舒肝解郁又能調和脾胃,脾胃健運則肝氣自暢。臨床遇到肝病引起的脘悶、納呆、腹脹等脾胃癥狀比較嚴重者,此方具有很好的和中作用。再如逍遙散主治肝郁血虛、脅痛、頭痛、納少、女性月經不調、脈象虛弦等。方中柴胡疏肝解郁,白芍、當歸養肝,以遂其條達之性;因肝木為病,易乘脾土,所以配伍茯苓、白術、炙甘草等益氣健脾之品來實土,以防木乘;加煨姜、薄荷少許同煎,有助于舒肝和中,諸藥合用共奏疏肝解郁、健脾益氣之功。再如白術芍藥散主治肝旺脾弱的腹瀉,方中白術健脾,白芍斂肝,佐以陳皮理氣和中,防風疏肝理脾,諸藥合用疏肝木而補脾土,氣機調則痛瀉止。柴胡疏肝散主治肝氣郁滯,蒲氏益氣補肝湯主治肝氣虛弱,都是常用的疏肝顧脾與益肝顧脾的方劑,充分體現了“肝病實脾”的治未病思想[4]。
5.3 治療方法中體現肝病實脾
肝病實脾之法在肝病的不同時期可分為直接法和間接法。直接實脾法包括清熱利濕、益氣健脾、溫中健脾等,間接實脾法包括疏肝理氣、祛瘀通絡、養陰柔肝、清肝利膽等。但在臨床具體運用時,往往相互結合,如肝病及脾、土虛濕困、濕熱內蘊或外感濕熱之邪,肝脾氣機不暢,癥見頭暈乏力、四肢困重、納呆泛惡、脘悶腹脹、口干欲飲或不欲飲、小便短少、大便溏薄或秘結,或目睛、肌膚色黃、舌紅邊有齒痕、苔白膩或黃厚、脈濡數或弦滑,治宜健脾化濕、清利濕熱,方用甘露消毒丹合茵陳蒿湯或茵陳胃苓湯。
肝病中晚期肝木乘土、土不制水、水濕泛濫,癥見腹大有水、按之柔軟,下肢浮腫,納少腹脹,小便短少,大便溏薄或干結,形體消瘦,舌淡胖苔白膩或白厚、脈弦緩或滑緩,治宜益氣健脾、化氣行水,方用實脾飲合五苓散。
肝失疏泄、脾失健運、氣滯濕停、瘀血阻絡之虛實夾雜證,癥見脅下刺痛拒按、形瘦神疲、面色青紫、頭暈、納差腹脹、舌質紫暗或有瘀點瘀斑、苔白膩或花剝、脈細澀或沉細,治宜益氣健脾、活血化瘀,方用歸芍六君子湯合失笑散或金鈴子散,或用膈下逐瘀湯加減[5]。
6 小結
本文主要對“肝病傳脾”與“肝病實脾”相關的理論作了深入探討,肝脾在生理上關系密切,病理上肝實、肝虛皆可傳脾,充分體現了中醫五臟一體觀的重要思想,而“實脾”不能望文生義,去1味補脾,而應全面綜合分析,權衡虛實偏頗,補其不足損其有余,注重脾胃功能的調理,以固“后天之本”,這也充分體現了中醫治未病的學術思想。
[1] 張玉慶.“肝病實脾”的臨證應用[J].陜西中醫函授,1994,14(2):25?26.
[2] 彭相華.“肝病實脾”淺識[J].江西中醫藥,1992,23(8):30.
[3] 田林忠.“肝病實脾”探[J].河南中醫,1992,12(12):30.
[4] 李富旺.“肝病實脾”的探討與應用[J].中華中醫藥雜志,2006,21(8):510?511.
[5] 陳文照.“肝病傳脾”與“肝病實脾”芻議[J].陜西中醫,1987,8(5):221?222.
R222.15
:A
:1006?3250(2016)10?1308?02
2016?02?23
祝建材(1976?),男,山東文登人,副教授,醫學碩士,從事中醫基礎理論的教學與臨床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