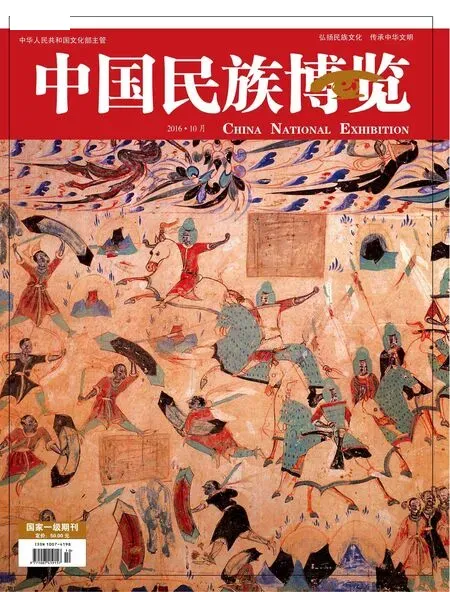文化變遷理論與民族節日研究
何馬玉涓
(云南藝術學院文華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文化變遷理論與民族節日研究
何馬玉涓
(云南藝術學院文華學院,云南 昆明 650000)
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關于民族節日現代化演變的研究不甚枚舉,文化變遷理論被廣泛運用。本文旨在對文化變遷視域下的民族節日進行研究,打破對節日現代特征深描的慣例,而將研究重心放到刀桿節成型過程中,通過追朔、推演,以更為廣闊的歷史視角把握民族節日文化的發展規律。
文化變遷;民族節日;溯源
在人類學界,“文化變遷”和“社會變遷”兩個概念經常混同使用。有時又混為“社會和文化變遷”或“社會文化變遷”。從嚴格意義上來作區分,社會變遷的使用范圍更為寬泛,可以指整體性的社會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更替過程,也可以具體到社會形態或文化模式某一方面發生的任何有意義的變化,諸如食物、服裝、工藝、技術以及習慣、價值觀和社會關系方面的變化。克萊德·伍茲就認為“文化變遷和社會變遷都是同一過程的重要部分,但在必要的時候,在概念上也可以區分,倘若文化可以理解為生活上的多種規則,社會就是指遵循這些規則的人們的有組織的聚合體。”[1]
研究之初,關于文化變遷的研究是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而前行。早期古典進化學派著力于說明文化變遷與發展的普遍作用,較少關注地域差異性和民族接觸及其文化交流。傳播學派的研究則將研究重心放在了文化的地理環境、空間變化和地方性演變,強調文化的散布。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進化學派的不足,但也忽視了內部因素,忽略了人類創造文化主觀能動性,對文化變遷過程或傳播時間順序的解釋缺乏說服力。功能學派強調文化變遷是以適應社會生存發展的需要為目的而發生的。在討論文化變遷的動因上,人類學家通常把創新、傳播、進化、涵化、沖突、適應、同化、融合和整合等都歸在文化變遷這一動態的過程中予以分析和研究。[2]由歷史學派發展的“文化區”理論,認為一個特定的文化區域是由相似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叢構成,此區域內存在著文化中心,文化的變遷過程就是文化特質、文化叢由中心向外擴散的歷史,“占主導地位的模式被吸收、重造和向外輻射這個變遷的首要源泉,被稱為文化頂峰或文化焦點。”[3]史徒華在《文化變遷的理論》中提到,關于文化演進的研究可以視為一種特殊的歷史重建或是一種特殊的方法與取向。他提出“對環境的適應”是文化生態的核心理念,借用了生物學上生態的意義,即有機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強調文化生態的適應才是文化變遷的動力。文化核心即是與生產和經濟活動最為關聯的各項特質的集合,與經濟活動有密切關聯的社會、政治,與宗教模式皆包括在文化核心之內。其他更多的特質則可能具備非常高的變異性。這些特質稱為次要特質,主要受純粹的文化-歷史因素所決定的,如傳播或無意的創新。正是這些次要特質使具備相同核心的文化顯出各自的獨特性。當然文化的確傾向于保持不變,人們的文化態度的確能夠使得變遷的速度緩慢下來。但是在過去的數千年內,在不同環境中的各文化都發生過或正在發生著極為劇烈的變遷,這些變遷基本上可歸因于新舊技術交替與生產方式變化引發的新適應。即使偶爾有文化性的障礙出現,也阻礙不了因為需要、適應的步伐。[4]國內學者也傾向于文化變遷的動力研究。在王海龍、何勇的著作《文化人類學歷史導引》中對文化變遷動力因素做了詳細表述:如果文化的供應不能適應當時社會的要求;如果洞察到了,并且掌握了新的、進步的工具;如果能夠作出必要的反應;如果新的事物比舊的事物看起來更令人滿意;其他因素。如“中樞導向”或“強制文明”。[5]黃淑聘和龔佩華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是研究社會文化變遷的要點,社會發展的合力可以看作文化變遷的根本動力。[6]
現代化進程的加速,使得少數民族節日變遷研究成為了熱點。學者們將目光聚焦于近30年民族節日的變化,而事實上,漫長的節日成型過程更加不容忽視的。在此,我以西南地區傈僳族刀桿節為個案,不難看出,文化變遷理論在民族節日溯源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當傈僳族刀桿節的研究放置于文化變遷背景之下,需要討論的便不僅僅是現代社會近三十年內出現的問題。有關節日的一切因素,文化歷史、民族發展、地理環境、社會適應等都受到文化變遷的影響。因此,濃墨重彩地從明代開始進行歷史梳理才是研究刀桿節的文化演變過程的基礎。
現在,學界對于社會變遷的動因達成一項共識,即社會文化變遷的具體動因在于新要素的產生。一般情況下,社會變遷新要素的出現的因素分為兩種情況,一是以積累為基礎,從社會內部產生。二是從外部導入,從而對原來的社會產生強烈的沖擊和影響,導入的外部要素與社會內因共同作用,推動社會變革的發生。
騰沖刀桿節的傳說體系依附于明代三征麓川的將領王驥,而明代正是影響騰沖、乃至云南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而這個時期,大量的漢族移民進入云南成為影響云南社會變遷的明顯的外部新要素。從根本上改變了云南人口的民族構成。來自不同時期、不同階層與不同地區的漢族移民,完成著他們自身的土著化轉變,在與當地各民族的相互交融中,帶入了新的社會、經濟、文化因子,為云南社會注入新的活力,逐漸影響和改變云南社會的發展面貌及民族關系,通過民族融合完成社會文化的變遷。民族融合是一個討論起來比較復雜的問題,涉及到諸多因素共同作用。相互融合的民族先要擁有共同的生活地域。在其中,他們共同生產生活、文化交流、相互影響、逐漸融合。因此,民族雜居形成的共同地域是民族融合重要前提。從局部區域看,漢族移民的分布具有城鎮、壩區、干線、要沖和開發新區相對聚居的特點,但是從全局看,漢族移民實際散處于云南各民族人民的汪洋大海之中,呈現出在滇中、滇東、滇西和滇南等廣大地區與當地民族雜居的局面。漢族移民的散居分布,打破了云南當地民族原本存在的較為固定和完整的民族地域,切割了傳統的民族聚居區,將在千百年歷史中云南各民族相對穩定的地域,分離為一個個互有聯系卻分散的、較小的民族聚居區,使諸多民族失去了單獨的領域,逐漸變成了漢夷雜居,推動了各民族大雜居趨勢的發展。[7]民族融合與地主經濟發展則是明代云南社會變遷最重要的內在動因。漢族移民在土著化過程中與云南各民族的不斷融合,反過來推進了少數民族社會的變遷。
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8月),朱元璋做好準備,“先給以布帛鈔錠為衣裝之具,凡二十四萬九千一百人”,欲平定西南[8]。穎川侯傅友德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為征南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為征南右副將軍。根據朱元璋的部署,傅友德等率兵先至湖廣,征集兵馬,增加兵力,沿途又招引地方軍伍,使征南大軍人數達到了30萬。九月,30萬兵馬的征南大軍自南京出發,分兵兩路,從北、從東兩方大舉向云南挺進北路,傅友德分遣都督郭英、胡海洋等領兵萬由四川南下,從永寧四川敘永縣直趨烏撒云南鎮雄縣。東路,由傅友德、藍玉和沐英等主將親率主力從湖廣西進,經辰沉(今沉陵)、芷江入普定(今安順),進逼曲靖,據其要害。[9]之后,曲靖被明軍攻下,奠定了全面攻取云南的基礎。洪武十五年三月,明王朝“更置云南布政司所屬府州縣”,設云南、大理、永昌、姚安、楚雄、武定、騰沖、等五十余府,下轄州、縣、千戶所、蠻部等。[10]
正統元年(公元1436年)前后,麓川路“白夷”土官思任侵奪了南甸的羅卜思莊等村寨后,又“攻陷騰沖衛,云南震動”,更進一步“侵及金齒(今保山)”而“勢甚猖撅”[11]。明王朝于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正統八年(公元1443年)、正統十三年(公元1448年)三次派王驥發兵征討麓川,即為歷史上的“三征麓川”。在這三次軍事行動中,騰沖成為了王驥軍隊征討百夷土官的主要戰場之一。第一次征討,王驥與蔣貴一隊,率軍攻上江入騰沖。十一月初,王驥攻破上江寨,率兵渡下江,通高黎貢山道路,入騰沖,再由南甸(今梁河縣東北九保)至羅卜思莊(今梁河西南之芒東)。與此同時,思任發率眾二萬于沙木籠(在今隴川縣東北部)“據高山,立硬寨,連環七營”,抵御王驥軍隊,被王驥擊敗。第二次征討,王驥派人前往緬甸宣慰司,檄緬甸宣慰司縛思任發父子來獻,進兵騰沖。至騰沖,分兵兩路,截斷思機發逃往孟養(今緬甸克欽邦)的退路。[12]
明景泰《云南圖經》載,騰沖疆域幅員東至瀘江安撫司一百四十里,南至南甸宣撫司七十里,西至里麻長官司四百九十里,北至大理府云龍州三百五十里,東北至金齒軍民指揮使司二百七十五里,東南至南甸巡撫司大蒲窩寨一百里,西南至干崖宣撫司一百八十里,西北至茶山長官司五百里。《州志》載“吳志”云:“(騰越)諸夷接境,為遠邇之喉襟,作西南之保障,邊關要地,山河寸金,申畫不嚴即為棄土。”[13]“騰沖處極邊,緬甸撣人之所叩關而入貢者也,威弧不弦,乃無寧歲。”[14]騰沖地處滇西極邊,為云南西出緬甸、印度的對外交通要沖。“三征麓川”之后,邊患仍然存在,在滇西建立牢固的防衛體系,增兵鎮守顯得尤為重要。騰沖的地理位置,使其成為屯重兵的據點,修城池加以固守,是確保滇西的重要措施。正統十年(公元1445年),將原來的騰沖千戶所改設為騰沖軍民指揮使司,騰沖筑城置衛成為明代中葉增兵云南,進行軍事移民屯戍的重要契機。明王朝調重兵修筑了騰沖衛城。隨后,調軍騰沖,組織軍衛,屯田固守。
正是這樣特殊的疆域,影響著騰沖歷史進程以及民族融合中本土文化的形成。明代收復西南邊境的過程中,多有收編少數民族以補充兵力的情況。騰沖作為“江山阻絕,孤立西陲,四封之外,群夷猥集。”之地,少數民族被收編以制夷是征邊的重要手段。明代吳宗堯作《騰越山川封土形勢道里論》對收夷有專門記載:“永昌之上江十五喧,皆瘴區也,皆夷氓也,編之里甲,役之驛傳,律以國法、官儀,不聞有違戾者。”[15]同時,列舉了民族融合的成功案例,強調了少數民族融合的可行性,并大力推行:“為潞之計,雖夷其人,漸變其俗,……侵馴侵狎,潛消而默奪之。”[16]這些史料對應了騰沖傈僳族對其遷徙至騰的解釋(隨軍駐守邊關),古永(今猴橋鎮)、滇灘均是騰沖地區傈僳族聚居區,也是歷史上邊境關隘。
騰沖自三征麓川設衛之后,大批漢人進入屯田鎮戍,增加了人口,帶來了先進技術,墾殖發展,成為滇西少數民族包圍之中的文華薈萃、經濟繁榮的特區,對當地社會經濟發展起著積極帶動作用。正因為騰沖豐饒的物資和“諸夷接境”的地理位置,清朝之后多有“緬人”、“野匪”來犯,“乾隆三十一年,緬人犯邊”、“嘉慶十八年,野匪沿邊焚掠”、“道光十七年,野匪余小老燒殺滇灘等處”……面對這些邊亂,朝廷多次派兵征討、剿辦。在滇灘調查中,發現當地騰沖傈僳族的民族記憶雖然有零亂、重組的表現,但是主要歷史線索與上述歷史記載有諸多重合之處。當地50歲以上的傈僳族都認為他們是從北方遷徙而來,經過石月亮,再到騰沖。他們強調過去這里常有外族侵犯,搶奪物資,其先人因為有射弩的本事,被漢族征用,駐扎此地,抵御外敵。關于王驥的傳說中,有騰沖建造石城的情節,也與史上明王朝調重兵修筑騰沖衛城相吻合。服從社會變遷大背景的騰沖戍邊歷史與傈僳族民族融合記憶的梳理為我們推演刀桿節演變過程的重要前提。
生計方式(戍邊)在每一個環境中可以有不同的利用方式,因而也導致不同社會性后果。環境不只是對生計方式有許可性與抑制性影響,地方性的環境特色甚至可能決定了某些有巨大影響的社會性適應。歷史演進過程中,騰沖傈僳族與漢族等其他少數民族建立日常的接觸,使得彼此能夠有機會接受對方的文化,民族相互融合,即使存在積極吸收或被動接受的情況。因此,同樣是狩獵、刀耕火種的生產方式,騰沖傈僳族卻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民族文化交融而形成獨特的意識,包括審美與精神。正如上文說述,極邊的地理位置使其“蓋自麓川之役(緬甸撣人)而還,干戈未戢,弓矢斯張,中朝分閫之心,亦勤至矣。”又“騰越徼外多野夷,素無管轄,自立頭目,常為邊患。”[17]長期邊境內外的對峙關系使得傈僳族邊民生出戍守邊關的使命感,從而造成“軍事”意象和“國家意識”在傈僳族刀桿節中的體現,展現出“尚武”、“愛國”的民族精神。
得出了傈僳族刀桿節中“軍事化”特征之后,不妨再大膽地推測一下史上刀桿節的發展過程,那就是刀桿節和“軍儺”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據《騰沖縣志稿》記載:“騰沖隘地尚有巫教之香僮,其術無師傳,信之以為神附之,能跣足于熾炭之中,燒鐵練纏于脖頸,空中借火,赤足履利刃,咬瓷瓦如嚼餅餌,所奉為三崇之神,每年二月八日演刀桿之劇,相傳此種巫教乃明正統間王驥征麓川時設之以威服諸夷也。否歟?”[18]文中記載的刀桿儀式與傈僳族刀桿節核心儀式基本相同,并提出了刀桿儀式與“王驥三征麓川”的關聯問題。這就不得不讓人聯想到明代的軍儺。
軍儺是在古代軍隊歲終或誓師等祭祀儀式中,戴面具的群體儺舞,兼具祭祀、實戰、訓練、娛樂的功能。軍儺一詞,在南宋周去非的《嶺外代答》一書中首先出現,“桂林儺隊,自承平時名聞京師,曰:靜江諸軍儺。”隨著明代大軍出征云南,軍儺也就隨著帶來,并與當地民族文化交融,逐漸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儺戲。較為著名,并與明軍出征云南相關聯的當數安順地戲。它的形成可以推演到明代邊屯時期。“明朝初年,朱元璋的軍隊出征云南,曾在安順建城屯兵,屯田的士兵和南遷的移民帶來了古老的儺戲,并逐代流傳”、[19]。
刀桿節中重要的的核心儀式是“上刀山”、“下火海”,其間香通們經過神授過程,完成蹬、跳、翻、騰空等動作;地戲的表演招式有拋槍、梭槍、架槍、壓槍、挑槍、殺轉槍、耍刀、順刀、提刀、夾刀、飛刀、理三刀、圍城刀、打黃金棍、打背板等刀、槍、棍技藝,以及徒手對打的空拳對、扭脖勁、雞打架、左右栽花,等等。這些招式具備大量民間武術成分,也有對現實生產生活動作的模擬。[20]相比較而言,兩者都有著強烈的軍事化特征。
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騰沖是“西南之保障,邊關要地”,而安順也是“黔之腹,滇之喉”,兩者都屬于軍事要地。另外,明初的安順,居住的主要是布依族、苗族、仡佬族居民。隨著南征軍屯居貴州,漢族人口大量南遷,改變了貴州歷來“民夷雜處而夷居十八九”的居住情況和“溪洞山箐、內外隔離”的閉塞交通。為防范“諸蠻”叛亂,明王朝擇地建城,在修建城池的同時,明軍在安順、平壩一帶,設置屯、堡、衛、所駐扎人馬。這也與騰沖的兵屯過程相類似。明軍里盛行的融祭祀、操練、娛樂為一體的軍儺隨南征軍進入貴州,與當地民俗風情結合,逐漸形成了以安順為中心的貴州地戲。貴州地戲的傳承路線,是沿著南征軍的行軍路線及屯田駐軍分布的,呈現出明顯的帶狀構架,其中心是貴州安順,并一直延伸到云南澄江縣陽宗小屯一帶。[21]
安順軍儺演變可被借鑒,以來回答《騰沖縣志稿》中“相傳此種巫教乃明正統間王驥征麓川時設之以威服諸夷也。否歟?” 通過上述對騰沖社會變遷的梳理,軍儺演變為刀桿節確實有相對應的歷史條件。而且,由軍儺轉為刀桿節的演變過程一直延續到清代才逐漸固化為現代所呈現出的核心程式。刀桿架所設刀桿數量有明確要求并有所指,香通所要求的72把鋼刀代表王驥三征麓川時候設立的72道關卡。騰沖72道關卡在歷史上確有記載,但已經是清代之后的事情。“(胡啟榮)嘉慶二十五年任騰越廳同知,在任六年,洞悉夷患,依苗疆案例,請于大吏,奏準擇險要建石雕,筑堅堡。自古永隘美古、尖高山、蠻旦、檳榔江源,沿江扼設碉堡七十二卡,置買練田,收租給養練丁,以嚴防堵,邊境肅然者六十余年。”[22]這明顯受到后世文化的影響,將多個人的英雄事跡疊加在同一個人的身上,構建出現存的刀桿節口頭敘事系統。
刀桿節的演變過程是整個社會文化變遷背景下的產物,因為軍事政治的需要帶來的軍儺被從軍的民族運用,成為民族“軍事歷史”的符號化表現。由最初的軍事操演、祭祀行為轉變為占卜、祈福手段;由歷史事件的復演轉變為尚武精神的推崇。但核心沒有改變,就是傈僳族文化適應下對自身民族精神與民族記憶的表達,關乎其堅毅品格、健碩體格和維護國家統一、服從總體利益的意識形態。當然,現代社會處于“全球一體化”的發展態勢,文化自新、文化傳播的速度加快,近30年刀桿節的復興使節日本身發生了適應時代需求的演變,區域性的節日逐漸演變為整個民族的盛大節日,并得到了周邊民族認同,迅速地產生出新的內涵與意義。
注釋:
[1][美]克萊德·伍茲.文化變遷[M].何端福,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2-6.
[2]劉明.環境變遷與文化適應研究述要[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9(2):56.
[3][美]克萊德·伍茲.文化變遷[M].何端福,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4.
[4][美]朱利安·史徒華.文化變遷的理論[M].張恭啟,譯.臺北: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40-45.
[5]王海龍,何勇.文化人類學歷史導引[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234.
[6]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38.
7]陸韌.變遷與交融—明代云南漢族移民研究[D].云南大學,1999:317.
[8]《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一三八.
[9]《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一三九、卷一四二.
[10]《明太祖洪武實錄》卷一四三.
[11]《明史·麓川土司傳》.
[12]尤中.明朝三征麓川敘論[J].思想戰線,1987(4):61.
[13]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87.
[14]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491.
[15]傈僳族民歌中有《上江姑娘我領走》,與此地應該相同。
[16][明]陳宗海.騰越廳志(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3:471.
[17]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43.
[18]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443.
[19]沈福馨.貴州安順地戲和地戲臉子[J].貴州大學大學報,2003(1):1-9.
[20]桂梅.安順地戲表演藝術探析[M].民族藝術,1990(1):36.
[21]庹修明.中國軍儺——貴州地戲[J].民族藝術研究,2001(4):3-4.
[22]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484.
[1][美]克萊德·伍茲.文化變遷[M].何端福,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2]劉明.環境變遷與文化適應研究述要[J].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09(2).
[3][美]克萊德·伍茲.文化變遷[M].何端福,譯.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4][美]利安·史徒華.文化變遷的理論[M].張恭啟,譯.臺北:臺灣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5]王海龍,何勇.文化人類學歷史導引[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2.
[6]黃淑娉,龔佩華.文化人類學理論方法研究[M].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7]李根源,劉楚湘.民國騰沖縣志稿(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4.
[8][明]陳宗海.騰越廳志(點校本)[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2003.
[9]沈福馨.貴州安順地戲和地戲臉子[J].貴州大學大學報,2003(1).
[10]庹修明.中國軍儺——貴州地戲[J].民族藝術研究,2001(4).
G03
A
何馬玉涓,副教授,現任教于云南藝術學院文華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