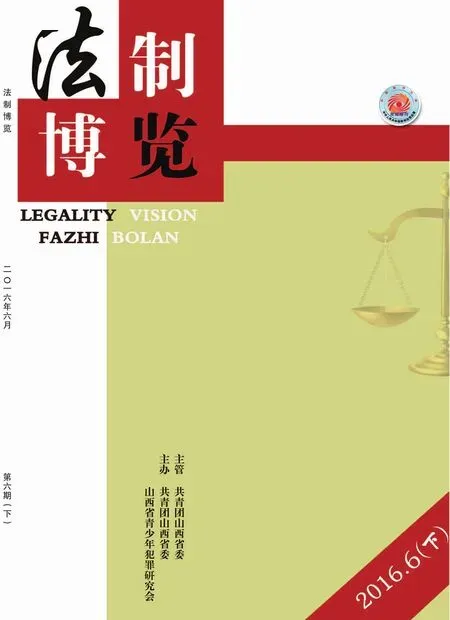家族成員特有財產:同居共財的例外?
姜曉雨
中山大學,廣東 廣州 510275
家族成員特有財產:同居共財的例外?
姜曉雨
中山大學,廣東廣州510275
摘要:近年,網絡上掀起了一股“宮斗”、“宅斗”小說的熱潮,其中不少甚至被改編成影視劇,導致人們對古代家庭生活也產生了一些刻板印象,比如說,男子不涉內宅之事,父權家長制,一妻多妾,嫡庶之爭等等。文藝作品畢竟會有夸張和虛構歷史的成分在,有一些是事實,而許多內容和歷史相去甚遠。
關鍵詞:家族;家產
一、“家長制”和同居共財的關系?
在中國的家庭中,“家長”即“家主”,“家的主人”,處在“家的主人”的地位的某一個人,他同時是父親或者兄長①。作為家長的長者掌握經濟大權,在家庭中,他被賦予日常性支出之權和管理權,也就是說,他可以實際上處分家產,管理家務。簡單舉例,處分家產最常見的形式就是把蓄積的金錢轉化為不動產,進行生產、經營甚至投資。而管理家務則是一般的日常性收支事務的處理。
何謂家產?家產是家庭成員所共同擁有的財產,也稱產業、家業、家當。家產一般掌握在家長手中,家庭成員人人有份,這也是同居共財一詞中的“財”的來源。同居共財主要包括幾個要素。第一,每個人的勞動所得全部放進為了全體成員利益的單一共同的會計即家計中的形態,此為同居共財的核心;第二,同居的每個人的生活中必要的消費全面性地由共同的會計來供給;第三,以上的剩余,被當作為了全體乘員的共同資產即家產加以蓄積②。
二、家族成員特有財產包含什么?
家庭紀律的松弛,導致私產被秘密的儲存起來時有發生,這是事實問題,暫且不論。另外,還有一些財產,是作為特有財產被公認的,也就是說,法律允許這些財產供個人支配。
男性可以個人私有的,是官俸及其他特別的勞動所得;而女性可以個人私有的,有自己的隨嫁財產,通常稱之為“陪嫁”或“嫁妝”,還有少部分純個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以及金銀首飾等。
中國的民事法律絕大部分來源于習慣,就家規中的習慣來看,既有官俸應該屬于家產的規定,也有非強制性的規定。官俸至少不是由家產提供資本而從事經營的盈利,所做的工作本質上也與通常的勞動相差懸殊,因此特殊對待。不過,為官者,置父母、兄弟于貧寒之狀況而不顧,也是不顧臉面違反孝道的。另外,如果有人空手出門,多年后擁有大筆產業歸鄉,那么除去一部分給兄弟們的適當補貼,其余的默認為自己本人的財產來保有也被承認。
原則的例外還是原則的補充?
中國古代的“家”是具有很大的伸縮性,又由于古人好“枝繁葉茂”、“五代同堂”,故古代的家庭有往往具有“生活堡壘”的規模。而在這個繁雜的家族中,若所有成年人都有權處置家產,則很可能出現不事先知會家人而私自出賣家產,甚至出現“一地二賣”的情況。這種交易對于一個典型的小農家庭的生計是十分要害的。于是就產生了“家長”作為一切事務代表的制度,以保證“同居共財”下的全家所有人的生計不受侵害。
但是,個人特有財產同樣在事實上廣泛存在,這并不意味著家庭成員試圖挑戰根本的原則和家族倫理,也不意味著人們先進到開始反思同居共財的劣勢,社會逐漸向私有制過渡。然而,人性中不可抵抗的私欲的存在,人與人之間獲得收入的不平等,也讓很多人難以接受與自己不親近的人分享自己的所得。譬如,為官者事實上并不靠那少量官俸生活,把這部分錢財放進公中,既能為自己博得美名,亦不會影響自己小家庭的個人生活。所以,實際上,逐漸被制度默認的其實指的是所有不因傳統勞作所得的收入,在明清以后,商品經濟逐漸發展,商人輾轉各地經營,官員也用盡各種手段斂財,這些收入當然地不計入家族財產,而是夫妻這個最簡單的生活體的特有財產。而婦女,因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特性,在料理后宅事務是,同樣需要一部分個人財產來周轉。妻妾地位的巨大差異,使得妾往往需要更多的私產來維持自己和庶子女的生活。這些不被制度承認的私有財產,如同地下暗河一樣靜靜地流淌。
因此,筆者認為,與其將所有的這些家族成員的特有財產視之為同居共財原則的例外,不如視為原則的補充。它們并不獨立地和同居共財相對抗,而是在此之外,更靈活地調整人與人之間的財產關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影響身份關系。小農社會的本質不變,社會生產和生活資料就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這里的特有財產,不能和現代意義上的個人私有財產相等同,嚴格上來講,它們并不是法定的,不是天然的,而是隨之社會關系的變化,人們生產生活習慣的改變而形成,并被制度或者說法律逐漸認可的。家族成員特有財產的問題,更傾向于是事實問題而非理論問題。
雖然中國的古代(甚至到現代)一直因其強烈的“暴君式專制”而為人所詬病,但在作為古代小農經濟下的中國家庭卻是一個十分穩定且精致的系統,依靠人們腦中根深蒂固的“家法”有序而安逸的運作著。“在中國的家庭生活之中,如此明確的區別自己的與他人的、公共的于個人的,即這種法師存在著的。類似所謂家父、家長權威,由于僅強調權利支配的方法論,家庭生活的真實狀態并沒有被抓住”。中國古代的家族法并不是以一個權威含糊霸道的概括掉的,而是細致的訂立下來的,彷如刺繡一般,每一種情況都依照那個基本的原則精確無誤的訂立著,大氣而不失細節。這樣精致的家族法,使得在那個生產力比較低的農業社會下的基本單位——“家”能夠最大限度地生存下來。
[注釋]
①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234.
②滋賀秀三.中國家族法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57-62.
中圖分類號:D923.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379-(2016)18-0255-01
作者簡介:姜曉雨(1995-),女,漢族,江蘇無錫人,中山大學,本科在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