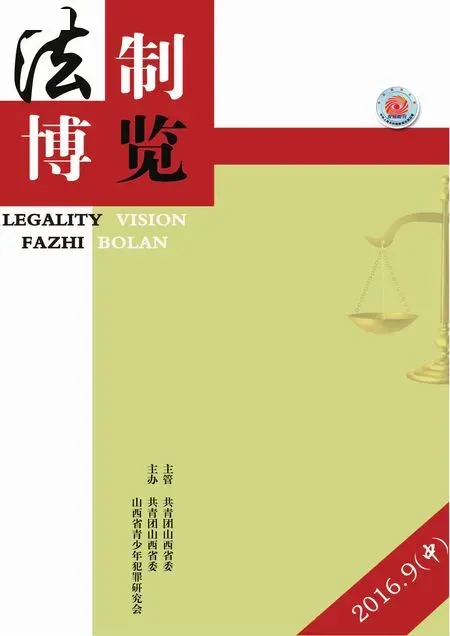淺談犯罪現場心理痕跡的開發利用
劉 涵
甘肅警察職業學院,甘肅 蘭州 730046
?
淺談犯罪現場心理痕跡的開發利用
劉涵
甘肅警察職業學院,甘肅蘭州730046
犯罪心理痕跡是犯罪分子在犯罪現場實施犯罪行為的過程中外顯出來的某些帶有犯罪意向的、穩定的、典型的心理特點。它具有一致性、個性性和可知性三個特征。認識、理解以及利用犯罪心理痕跡的關鍵在于對其予以正確合理地分析推斷,可以從現場損失物品、現場遺留人體排泄物、案犯足跡、命案中的附加性加害行為、裸露尸體覆蓋物、無明顯動機系列殺人案件、現場遺留特殊物品七個方面來分析推斷作案人犯罪心理痕跡,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科學合理的偵查對策,以便極大提高偵查破案工作的效率。
現場勘驗;心理痕跡;分析利用
任何犯罪現場的客觀物質痕跡都有其特定的心理屬性,都間接地反映著犯罪人在實施犯罪的過程中所具有的動機目的、心理狀態和個性心理特征等心理痕跡。犯罪現場心理痕跡是相對于物質痕跡而言的。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現場實施犯罪行為的過程中外顯出來的某些帶有犯罪意向的、穩定的、典型的心理特點,這些心理特點通過犯罪行為間接地反映在犯罪現場的遺留物以及痕跡之中。[1]這種犯罪現場中隱含的犯罪分子的心理痕跡如同物質痕跡一樣,如果能夠正確分析、刻畫并加以利用,將會極大地拓展偵查的思路和途徑,極大地提高偵查工作的效率。在現場分析的實踐中,偵查人員往往對物質痕跡研究極為重視,而對心理痕跡研究的少,甚至有時還忽視。因此,有的案件現場分析出現偏差,使偵查工作走了彎路,甚至陷入困境;反之,重視對現場心理痕跡的研究和利用,就能全面正確地認識犯罪現象,拓展現場分析的思路,為偵查工作的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在當前犯罪現場遺留的可作為偵查線索利用的物質痕跡越來越少的情況下,充分分析研究和利用犯罪現場心理痕跡就顯得越來越重要。
一、犯罪現場心理痕跡的特征
(一)一致性特征
心理痕跡與物質痕跡是相互印證的,在犯罪現場上出現什么樣的物質痕跡,必然會反映出犯罪分子在實施犯罪過程中與之相適應的心理狀態。作案人在意識正常的狀態下,現場的物質痕跡會按一般常態下物質運動的規律排列組合;而在異常意識狀態下,現場的物質痕跡會表現出不規則現象。心理因素,在一定的條件下必然會在行動中表露出來,也就是內因通過外部行動造成了一定的結果,這就說明心理痕跡和物質痕跡之間存在著一致性的特征。只要能夠抓住這個特征進行分析,對案件就能作出正確的判斷。
(二)個性性特征
個性是指一個人具有一定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總和。個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個性心理傾向性,是在社會實踐活動中逐漸形成的,比如動機、需要、興趣等。二是個性心理特征,它是通過自身的行為表現出來的,比如能力、氣質、性格等。[2]由于個人的興趣、愛好、認識能力、價值觀念、職業特點、生活閱歷以及知識結構的不同,導致了人與人在個性方面存在絕對的區別性,就象指紋、DNA各人不同一樣。當他(她)在實施犯罪行為時,其個性特征也就會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表現在整個犯罪活動過程中。這一特征正是我們在偵查破案中需要運用心理痕跡的科學依據。
(三)可知性特征
心理痕跡雖然是看不見、摸不著的十分抽象的現象,但它卻是可以被人們的大腦所認識和理解的。心理學有關理論表明,個體的心理活動與其行為反應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通過對行為的直接觀察與科學分析,可以間接地推斷人的心理活動的性質與水平。[3]雖然偵查人員沒有直接目睹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但是通過勘驗、檢查與調查訪問,利用自身的感覺器官,有時借助于某些專門器材,就能夠感知到犯罪現場中的物質痕跡以及由該物質痕跡反映出的犯罪行為,從而可以進一步推斷出罪犯的心理痕跡。[4]
二、犯罪現場心理痕跡的開發利用途徑
(一)利用現場損失物品折射出的心理痕跡來分析案犯作案的特殊動機和目的
凡是引起和推動某人去從事某種活動以滿足其一定需要的愿望和意識,就是這種活動的動機。一般來說,犯罪行為是有目的的、自覺的活動,是由犯罪動機所驅使的。不同的犯罪動機,常常引發不同的犯罪行為。動機取決于需要,犯罪分子作案是以滿足其某種需要為目的的。所謂作案目的是指犯罪分子所希望達到的結果。案犯在實施其行為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留下一些反映其需要的客觀“痕跡”,從而為我們分析其心理動機和行為目的提供了依據。通過其侵犯的不同客體,可以反映出一些不同的心理特點。比如2015年3月,某市發生一起盜竊案,一新婚夫婦家中被盜,犯罪分子將4床緞子被面仔細拆下來偷走,這與獲取目的物心切、急于逃離現場有矛盾,說明其行竊與結婚需求有關。以此特殊動機為條件排查作案人,很快破獲了案件。破案后結果證明了偵查人員的推斷完全正確。
(二)利用現場遺留人體排泄物折射出的心理痕跡來分析案犯的心理素質
案犯在作案中的一般規律是盡量避免在現場遺留痕跡物證,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時間達到作案的目的,所以在現場是不會遺留人體排泄物的。如果在現場發現了案犯遺留的排泄物,那么就不符合作案的一般規律。然而,案犯的這一現場行為恰恰折射出了其非常特殊的心理痕跡,那就是心理素質極差。比如有的作案人,在作案過程中由于高度恐懼緊張引起肌體內的內分泌腺功能失調,大小便失禁,在現場排泄糞便、尿液,而且有的已成為習慣。它不是犯罪分子膽大妄為的表現,而恰恰是萬分恐懼的特殊生理反映。案犯的這一典型心理特點為以后的摸排工作提供了便利條件。
(三)利用案犯足跡中的心理痕跡確定追捕方向
在追捕正在逃跑的案犯過程中,如何確保追緝的正確方向是追捕成敗的關鍵。實踐中我們常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步法追蹤,即根據案犯逃跑中遺留的足跡來追蹤,由于案犯在逃跑時是非常恐慌不安的,總是懷疑警察正在后面追趕他,這種心理決定了其在逃跑中留下的足跡明顯不同于正常人在行進中留下的足跡。
比如,2016年2月某地發生一起殺人案件,案犯作案后逃進了留有積雪的山里,當偵查人員順腳印追到山下時,發現雪地上有多趟足跡,不知那行足跡是罪犯所留。這時有人提出罪犯的足跡應有以下特征:1、只走山溝,不走山梁;2、該足跡有走一走就有一只腳打橫,或者在遇到大樹等能遮掩身體的物體時,就有停頓、腳尖朝后的跡象。于是就尋找具有這種特征的足跡,并沿此足跡追蹤將案犯抓獲。這就是利用了案犯在逃跑時,害怕被人發現而只走山溝以及在行走中不時地向后觀望的心理狀態在足跡上的必然反映,從而為追捕逃犯指明了正確的方向。
(四)利用命案中的附加性加害行為來分析案犯的心理痕跡
命案中的附加性加害行為是指犯罪分子在實施殺人過程中,由于某種心理動因的需要,在被害人處于瀕死期間或死亡之后,又附加實施的侵害行為。[5]在殺人案件偵查實踐中,此類實施殺人且伴有對受害人的附加性加害行為的情形出現機率較高,而這種加害行為總是在一定的犯罪心理影響與支配下發生的,必然反映出犯罪分子的心理痕跡和個性特點。比如有一起一家五口被殺的案件,現場勘驗發現五具尸體的眼睛都被銳器刺破,分析作案人可能因不懂醫學知識或者信奉迷信,認為人死后會在其眼睛里留下作案人的影像。據此分析犯罪分子應是比較偏僻,文化落后、愚昧且交通、通訊極不便利的農村人作案的可能性較大,破案后證明這一分析是正確的。對于命案中的附加性加害行為,我們既要分析常態心理痕跡,如泄憤報復、圖財害命等,又要深入研究分析其特殊的個性心理痕跡。只有這樣,偵查工作才不會出現重大偏差、失誤和遺漏。
(五)利用裸露尸體覆蓋物狀況折射出的心理痕跡分析確定案犯與死者的關系
殺人案件現場一般都有尸體存在,尸體的位置、姿勢、尸體損傷程度、尸體胃內容、尸斑、尸僵、尸體的穿著打扮以及尸體上面的覆蓋物等等,這些與尸體有關的痕跡物質以及尸體所在環境等都是非常重要的證據,也是非常關鍵的線索,其中也包含了大量相關的犯罪心理痕跡,歷來是偵破殺人案件現場勘驗的重中之重。這里突出強調尸體的覆蓋物狀況,因為這一現場細節常常容易被偵查人員所忽視。但是偵查實踐表明,深入分析研究尸體覆蓋物及其包含的心理痕跡是非常重要的,常常能反映出作案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某種特定關系,有利于正確劃定偵查范圍,極大提高破案效率。
比如,在一塊油菜地里發現一具女尸,現場及尸體表明有強奸殺人跡象,女尸下身赤裸,陰部十分明顯的被人有意放了一把油菜。偵查人員沒有輕易地放過這一把很不起眼的油菜,對其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犯罪分子為什么要在女尸陰部放一把油菜?出于什么心理?一名有經驗的偵察員判斷:放油菜是出于遮羞心理,可能是被害者的親人或熟人作案。破案后證明犯罪分子正是被害者的公公,其將兒媳在家中趁無人之機強奸殺害后,拋尸于油菜地,轉身臨走時看了一眼,覺得兒媳赤身裸體太難看,于是順手拔了一把油菜將陰部遮蓋。
(六)從無明顯動機系列殺人案件來推斷案犯的變態反社會心理痕跡
心理活動的變態是與常態相對而言的,它既不是精神病患者,又不是精神健全的正常人,醫學上稱之為“心理障礙”。這種人的行為呈現出固定行為的異常反映,其精神發泄往往超越正常規范。一旦確認了案犯的變態心理,則可以大大縮小偵查的范圍。比如,2001年5月至2002年5月,在徐州市及其周邊地區相繼發生20余起盲流癡呆等弱智者被殺案件。通過作案手段分析案件為同一人作案,案犯針對的是特定弱勢群體的不特定個體目標,其侵害手段均為下半夜就地取材用石塊或水泥混凝土塊來砸擊露宿街頭的盲流癡呆者頭面部,同時伴有多次銳器捅刺,并有個別焚尸行為。在偵查階段分析罪犯的心理痕跡,認為很可能有心理障礙、反社會偏執型人格。破案后證實,貴州籍犯罪分子劉明武,本人即是盲流,具有偏執型人格障礙(有刑事責任能力),因被公安、民政部門多次遣送產生極度反感情緒,因而遷怒于同類,報復心理泛化,進而連續殺害無辜。[5]如果不按照此思路開展偵查,而是按照常規殺人案件展開偵查,那么偵查工作將會走很多的彎路。
(七)利用現場遺留特殊物品來分析推斷案犯的迷信、風俗習慣心理痕跡
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域都有其源遠流長的不同的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也有相互不同的封建迷信習俗,共同構成了有鮮明差別的地域心理和民族心理。這種心理根深蒂固,習慣成自然,必然會有意或無意地表現在案犯作案的行為過程之中,形成包涵此心理的各種痕跡物質。在偵查中如果能夠認識到這一點,并能夠善于透過物質痕跡現象,提取出案犯的這種心理,則非常有利于劃定偵查范圍,刻畫作案人的個性特點,從而為制定科學合理的偵查措施提供科學合理的依據。
例如,上海盧灣區曾發生一起兇殺案件,在勘驗女被害人的尸體時,警方發現在死者的右腳襪子筒里塞有一張折疊成小方塊的一元面值的人民幣紙幣,一時讓人不得其解。后在案件的調查中發現,嫌疑對象吳某是江蘇吳江人,在吳某的家鄉有在死亡者尸體腳邊放置紙元寶或冥錢,送死者上路的風俗習慣。據此,再結合吳某有重大犯罪嫌疑,案件的偵查范圍和方向變得較為明確。[6]
綜上所述,心理痕跡是受人的心理發展、變化的規律所制約的,再狡猾的犯罪分子都不會抹去自己的心理痕跡。只要我們能夠加強和重視對現場犯罪心理痕跡的開發利用,就必然會極大提高偵查破案的效率,也必將會把偵查破案帶入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1]高士藝.偵查心理科學應用技術的若干進展[J].中國刑事警察,1999(4):55.
[2]北京師范大學等.普通心理學[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2.96.
[3]伍新春.高等教育心理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7-8.
[4]張玉鑲.犯罪信息的概念分析[J].北京刑偵研究,1999(1):7.
[5]王鐵兵.命案中伴有附加性加害行為的犯罪心理分析[J].中國刑事警察,2002(4):29-30.
[6]張平.試論刑事現場的犯罪信息[J].上海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3):39.
D917.2
A
2095-4379-(2016)26-0212-03
劉涵(1966-),男,漢族,甘肅會寧人,甘肅警察職業學院基礎教學部,講師,研究發現:刑事法律文書、犯罪心理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