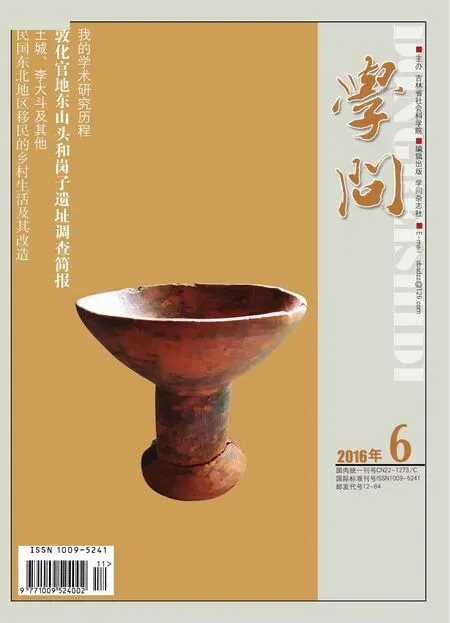高句麗后期相權擴張原因探析
董健
高句麗后期相權擴張原因探析
董健
[內容提要]相權在高句麗社會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尤其是在高句麗社會后期,相權不斷擴張,更顯重要。通過分析高句麗后期的相職可以看——高句麗相權擴張既是消除內訌、應對周邊關系的迫切之需,亦是個人實力彰顯的結果。
相權擴張 大對盧 莫離支
相權與王權自古便是國家權力的兩大核心力量,是外朝與內廷得以統治的中流砥柱,國家維穩的重要標桿。其中,相權關乎國本,而在高句麗社會中,王權、相權和貴族權三權并存。①本該作為王與貴族間潤滑劑的相權何以會在高句麗后期權力陡增呢?筆者擬對此加以分析,以期得出導致相權擴張的諸多因素。
一、高句麗后期之相職
隨著時代的變化,相職的名稱及職權亦有所不同。對此,劉炬先生根據其權力的發展將相權劃分為三個階段,分別為左右輔時代、國相時代與大對盧時代。②本文所要研究的正是高句麗相權發展的第三階段。在這個階段的相職應為大對盧和莫離支。大對盧為相職的說法目前已成為學界共識,而對于莫離支是否為相職尚存爭議。
不同觀點主要有日本學者武田幸男的“太大兄說”及韓國學者李文基的“中里太大兄說”③,可見兩者都將莫離支看成了已有的官職。那么,究竟莫離支一職是早已有之,還是始于蓋蘇文自創呢?首先,若莫離支為太大兄、中里太大兄,那此時已將大對盧一職世襲的蓋蘇文為何要自降其官職呢?這顯然有悖常理。其次,韓國學者李文基在文章中認為莫離支為“中里太大兄”,但在之后發表的文章中又指出“蓋蘇文是為了應對664年唐朝的討伐而設置了莫離支一職,并自任其職”④,可見,其學術觀點已發生轉變,對莫離支為新立之職已給予了認可。朝鮮學者權勝安亦有“在高句麗末期的6世紀中葉,莫離支取代了最高官職國相”的論述。⑤再者,筆者認為之所以有上述不同觀點,主要是受《唐代海東藩閥志存·泉男生墓志》中“曾祖子游,祖大祚,并任莫離支”的影響而認為莫離支并非始自蓋蘇文,基于此,對其職進行一系列推測類比。而這極可能是當時的唐人認為莫離支即為相職,而將過去的相職稱謂大對盧寫為莫離支,由此帶給了今人概念上的混淆。實際上,在中國正史中有關莫離支一職的記載都集中在唐麗戰爭期間,而在蓋蘇文弒君之前則史無所載。并且常將莫離支以借代的手法,借指宰相蓋蘇文。史載中常有“莫離支蓋金”、“莫離支蓋蘇文”的記載,亦有大量省去名字而直稱“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⑥、“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⑦的記載。這些記載都將莫離支作為蓋蘇文的代稱,可見蓋蘇文與莫離支可互為所指。所以筆者認為,欲知“莫離支”之職能,其實考察任其職者的職權即可,故只需考察蓋蘇文的所作所為便可知莫離支之職能。蓋蘇文舍棄相職大對盧,從其后的作為來看,其職權有增無減,故莫離支一職理應屬于相職研究的范圍。高句麗后期,大對盧與莫離支皆可以相職視之。以下將詳述高句麗后期大對盧與莫離支作為相職其職權的演進與擴張。
二、高句麗后期的相權擴張
相權擴張非朝夕之變,若考察高句麗后期的相權擴張,自然要對前此時期一并進行探究。如此方能對高句麗相權有一整體把握,對相權之漸變有一綜合認識。
左右輔時期,“以沛者穆度婁為左輔,高福章為右輔”⑧,“拜貫那沛者彌儒為左輔”……左右輔由王任命,是王的屬官,王的附庸;從“拜乙豆智為右輔,委以軍國之事”⑩之句可知其職權為軍國之事,而從后來的“乙豆智鯉魚退漢兵”?及“高福章上奏‘遂成將叛’”?之事可見王對左右輔的意見很是重視。左右輔正如其官名一般,是對王權的輔佐;從“立王子無恤為太子,委以軍國之事”可見此時的皇室亦是政府,兩者的權力并未完全分離,此時的左右輔只是皇權的附庸。
國相時期,從“國相乙巴素卒…以高優婁為國相”,“國相高優婁卒,以于臺明臨于漱為國相”,“國相明臨于漱卒,以沸流沛者陰友為國相”,“國相陰友卒。九月,以尚婁為國相”,“國相尚婁卒,以南部大使者倉助利為國相”?等記載可見國相曾不間斷地存在于一段歷史時期,且都是前任國相卒而后任國相立,未有被輕易罷免的情形,此亦可見相職在國家中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乙巴素“以至誠奉國,明政教,慎賞罰,人民以安,內外無事”,“王謂群臣曰:‘慕容氏兵馬精強,屢犯我疆場,為之奈何?’國相倉助利對曰:‘北部大兄高奴子賢且勇,大王若御寇安民,非高奴子無可用者。’王以高奴子為新城太守”?等相關記載可知國相之職權為明政教,慎賞罰,知政事,掌行政之權。同左右輔時期一樣,其提議一般都會得到王的采納;而從“于是,四部共舉東部晏留。王征之,委以國政”?之句可看出此時期與左右輔時期的不同之處在于:此時的國相人選并非是由王一人所決定,而是由貴族推薦,王最終任命,既然選任由王與貴族共同完成,可知此時的相權同時代表了兩者的利益,是兩者利益的平衡點。此外,《三國史記》中的另一條史料也需要加以關注:“拜達賈為安國君,知內外兵馬事,兼統梁貊、肅慎諸部落”?,當時,恰值西川王在位,尚婁為國相,而達賈卻以“知內外兵馬事”一職與之并存,足見國相一職只有行政之權,并無軍事權力。
以上是前兩個階段的相職,對于大對盧一職,《周書·高麗傳》有載:“其大對盧,以強弱相凌奪”,這是大對盧一詞初見于史書。而在其后的《舊唐書·高麗傳》中亦有載:“其官大者,號大對盧,比一品,總知國事。三年一代,若稱職者,不拘年限。交替之日,或不相祗服,皆勒兵相功。其王但閉宮自守,不能制御”。由“總知國事”可知大對盧一職負責全面管理國家事務;由“不相祗服,皆勒兵相功,勝者為之”可知大對盧手中必有兵權,且必為軍事實力最強者。但從另一方面講,既然有人能領軍與大對盧相爭,足見大對盧未能統全國之兵。這說明大對盧應為本部之軍事首領,而不是全國的軍事統帥。最后,從各路人馬用如此野蠻的手段爭奪大對盧一職時,王只能采取“閉宮自守”的自保行為來看,大對盧之權已然凌駕于王權之上,此時的相權已有王權化之傾向。而后期任大對盧一職的蓋蘇文弒主而另立新王之舉亦可佐證相權之重。由此可見,大對盧一職掌全國行政之權,亦有本部的軍權,但并不能執掌整個王國的軍事權力。
那么權傾朝野的蓋蘇文為何又要自立為莫離支呢?這還要回到大對盧一職所固有的職權制約上來分析。時任大對盧的蓋蘇文雖然能夠掌控全國的行政,但卻無法自由征調全國之兵。而從莫離支“猶中國兵部尚書兼中書令職”?及“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尚書”?的記載可知,莫離支一職已不僅執掌全國之政務,而且已開始獨掌王國的軍事事務。這一點,從隋麗、唐麗戰爭這兩次重要的戰爭中參戰的高句麗兵力上亦可得到見證。在隋麗戰爭的歷次戰役中,各史籍均未見有高句麗各城協同作戰、相互應援的只言片語,也未提及高句麗在歷次戰役中的參戰人數,即使是在決定雙方命運的薩水之戰中,也未見有關于高句麗一方參戰人數的記載。這顯然是因其人數較少,不值一提。而有關唐麗戰爭的記載則與此迥然不同。在唐太宗親征之戰時竟然能讓“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耨薩高惠貞率高麗、靺鞨之眾十五萬來援安市城”?的記載。須知,當時高句麗全國之軍不過有“強兵三十余萬”?。這也就是說,蓋蘇文將全國一半的兵力用于一次戰役之中,足見其掌控力之強。此外,在這場戰爭中,各城之間已不再孤立作戰,從“莫離支以加尸人七百戍蓋牟”?,“高麗發新城、國內城騎四萬救遼東”?,“烏骨城遣兵萬馀為白巖聲援”?等記載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高句麗軍隊協同作戰能力的加強。這充分說明,蓋蘇文不僅掌控著王畿一帶的兵權,而且對政治對手掌握的軍隊也能調動自如。凡此種種,都能清楚地發現,在蓋蘇文設立莫離支一職之后的巨大變化。進而亦可知蓋蘇文自設莫離支的目的,就在于讓自己獨掌全國軍權。
當然,雖然此時的高句麗已處于蓋蘇文的獨裁統治之下,但不得不說,高句麗社會相較大對盧時期要好很多。大對盧時期各部各統其兵,可以說隨時存有內亂的隱患,是一個混亂無序的時期。莫離支的產生,促進了各部的統一與協調,并且在蓋蘇文的專政下,其行動能夠高度一致,指令能夠迅速執行。
通過對高句麗三個時期相權的考察,不難發現,高句麗相權從皇權的附庸,到掌全國行政之權,直到獨掌全國軍政大權,最終將相權王權化,相權擴張趨勢顯而易見。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得高句麗后期相權會如此一路擴張呢?
三、高句麗后期相權擴張原因
高句麗后期相權之擴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來自消除內訌和應對周邊危局的客觀需要,亦是英雄主義伸張及個人實力彰顯的結果。
其一,消除內訌之需要。高句麗自建國始,王權與貴族權便同時存在,當兩者有矛盾沖突之時,貴族權一般也會聽令于王權。但在高句麗后期,各部爭雄,內訌時有發生,而王權卻無法制止各部貴族之爭。據史載:“六年,高句麗大亂,被誅者眾。七年,是歲凡斗死者二千余。(中夫人子為王,年八歲。貊王有三夫人,正夫人無子,中夫人生世子,其舅氏鹿群也,小夫人生子,其舅氏細群也。及貊王疾篤,細群、鹿群各欲立其夫人子,故細群死者二千余人也。)”?由此可見貴族間斗爭之慘烈。而貴族權之復興,足見王權之衰落。王權既衰,便不復有統領各部之力,而所謂“國不可一日無君”說的正是統一領導的重要所在。因為若無統一領導,各部各自為政,則必然導致分裂,國將不國。如此則極易發生人心的渙散。可見,結束內訌已迫在眉睫,故統一軍權,從而相權王權化實屬必然。
其二,應對周邊關系之需。高句麗相權急劇擴張之際,恰值公元6世紀后期,而此前高句麗的周邊形勢可謂每況愈下。當時,高句麗西北面臨著來自中原王朝的巨大壓力,據史載:“天保三年,文宣至營州,使博陵崔柳使于高麗,求魏末流人。敕柳曰:‘若不從者,以便宜從事。’及至,不見許。柳張目叱之,拳擊成墜于床下,成左右雀息不敢動,乃謝服,柳以五千戶反命”?。高句麗地廣人稀,人口一直未曾飽和。故高句麗每當攻城略地之后,必將虜掠當地大批人口前往內地。而此時竟然允許崔柳一次帶走5千戶,其所承受的壓力,可謂不言而喻。在其南面,高句麗在新羅和百濟的猛烈攻勢下,領地大量喪失。551年“百濟圣明王親率眾及二國兵(原書注:二國,謂新羅、任那也。)往伐高麗,獲漢城之地,并進軍討平壤凡六郡之地,遂復故地”?。與此同時,新羅大將“居柒夫等乘勝取竹嶺以外高峴以內十郡”?。在北面,則有勿吉—靺鞨人對高句麗侵擾不斷,尤其是粟末靺鞨,更是“每寇高麗中”?。由此可見,當時高句麗周邊是何等嚴峻。而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邊境危機,擺脫周邊關系的不利局面,實為高句麗朝野上下不得不考慮的問題。而要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盡快結束高句麗貴族集團的內訌,早日實現王國內部的統一與團結,這就必須要加強政治集權。此時高句麗正處于貴族集團執政階段,要想重振王權,簡直勢比登天,而將權力集中于作為貴族集團代表的大對盧之手乃是唯一的選擇。因此,擴大相權,并使相權王權化勢在必行。
其三,英雄主義的伸張與個人實力的彰顯。任何一項重大的社會改革都是客觀與主觀相互作用的產物。高句麗相權的擴張也同樣如此。在危機四伏之時,高句麗權力集中,但是,要實現這一目標,還必須有一位鐵腕領導人來推動這一偉大的事業。泉氏家族的泉子游和蓋蘇文正是這種應運而生的英雄。泉子游,史籍無載,其名僅見于《泉男生墓志》。但種種跡象表明,他就是結束高句麗統治階層內訌,實現重振高句麗國威的領袖。泉子游雄才大略,帶領高句麗軍民在戰爭中屢戰屢勝,即使是強大的隋朝對其也束手無策,從而為大對盧一職一家世襲及其職權范圍不斷擴張奠定了堅實基礎。?蓋蘇文則同其祖父泉子游一樣,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實權人物,史稱其“儀表雄偉,意氣豪逸……甚有威嚴,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這種專斷果敢的品行同樣是相權擴張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因此說,高句麗后期相權的擴張,是與泉子游、蓋蘇文祖孫二人品性、能力及其所建樹的赫赫功勛是分不開的。
綜上所述,高句麗后期社會形勢的發展與鐵腕領袖泉子游、蓋蘇文個人品格乃是導致高句麗后期相權得以不斷擴張的主要原因。
[注釋]
① 參見劉炬《高句麗三權并存制研究》,《北方文物》2009年第1期。文中指出:高句麗是王權、相權、貴族權三權并存制。
② 劉炬:《高句麗相權考》,《北方文物》2003年第3期。
③ [韓]李文基:《高句麗莫離支的官制性質與職能》,《白山學報》55,白山學會,2000年,第93頁。
④ [韓]李文基:《高句麗滅亡期政治運營的變化及其滅亡的內因》,《韓國古代史研究》50,2008年,第69、76頁。
⑤ [朝]權勝安(音譯):《檀君朝鮮的政治制度對古代、中世國家政治制度的影響》,《歷史科學》(2015)第3號,5第1頁。
⑥ 王欽若:《冊府元龜》卷991,《外臣部·備御四》,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2012年,第11639頁。
⑦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8,唐太宗貞觀十九年條,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228頁。
⑧?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太祖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3頁,195頁。
⑨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次大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96頁。
⑩?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大武神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84頁,185頁。
? 分別引自《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之《山上王》《東川王》《中川王》《西川王》《烽上王》。
?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烽上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214頁。
?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故國川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201頁。
?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西川王》,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212頁。
?? 劉昫:《舊唐書》卷199上,《東夷·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3621頁,第3622頁。
?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6,唐太宗貞觀十六年條,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8162頁。
? 劉昫:《舊唐書》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3647頁。
?? 歐陽修:《新唐書》卷220,《東夷·高麗傳》,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第4703頁,第4702頁。
? 司馬光:《資治通鑒》卷197,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221頁。
? 田溶新譯:《日本書紀》卷19,《欽明天皇》六年、七年條,一志社1964年,第332頁。
? 李延壽:《北史》卷94,《高麗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3115頁。
? 田溶新譯:《日本書紀》卷19,《欽明天皇》,一志社,1964年,第335頁。
?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居柒夫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07頁。
? 魏征、令狐德棻:《隋書》卷81,《東夷·靺鞨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1821頁。
? 劉炬:《蓋蘇文家世考》,《東北史地》2009年第5期。
? 金富軾著,孫文范等校勘:《三國史記·蓋蘇文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549頁。
責任編輯:趙欣
K242.1
A
1009-5241(2016)06-0074-04
董健 吉林省高句麗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吉林 長春 13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