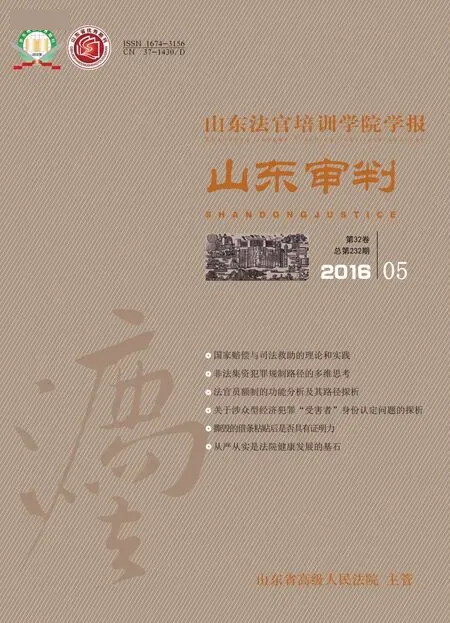從規則之治到多元共治
●鄭家泰
從規則之治到多元共治
●鄭家泰
山東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山東省多元化解紛促進條例》將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實施,這是山東省乃至全國法制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對于在新形勢下動員各方面力量共同化解矛盾糾紛、構建穩定和諧社會作出了具體規定,對于建立健全國家治理體系、不斷提高國家與社會治理能力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義。
一是條例規定了國家機關、政府部門和社會組織在促進糾紛多元化解方面的法律地位及法律職責,是解決社會內部沖突、促進社會整合、形成穩定和諧局面的重要法律保障。回顧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的歷程,經濟與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國家自身建設面臨現代化與“后現代化”的多重挑戰。一方面,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到30年的時間,經濟發展形態經歷了幾個重大模式的遞進式轉換。反映到上層建筑,要求國家法律體系的加快建立健全及司法、執法、守法層面的嚴格、規范運作,達到依法治國的理想狀態;另一方面,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使得各領域的糾紛迅猛增多,依靠國家正式法律的干預緩不濟急,遇到了與法治成熟國家相似的訴訟“爆炸”、治理“失靈”等困境,不得不在國家正式法律治理之外,同時開辟多元化解紛、社會化治理的另一條路徑。上一世紀9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應用ADR(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建立起以仲裁和調解為主要內容的、由法院以外第三方主持化解紛爭的制度體系,取得了提高解紛效率,降低訴訟成本、節省司法資源等方面的顯著效果。據理論研究,ADR這種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源自“東方經驗”,與中華文明的“和”文化存在一定淵源或是“暗合”。在長達幾千年的中華政治文明史中,基于對“無訟”、“和諧”的追求,基層鄉村自治、宗族管理、行業管理等等領域都把調解、和解作為解紛的基本手段和目標;即便是在建國后不同的歷史時期,行業、單位、鄉村管理等也一直存在著人民調解、行業調解等非國家法律解紛方式。只不過,在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過程中,這些傳統性的社會解紛理念和手段跟不上化解紛爭的需求,遠不如正式法律運作的權威與成效,導致大量的矛盾糾紛都以訴訟形式涌入法院,呈現出與發達國家等量齊觀的訴訟“爆炸”等“后現代”樣態,對社會穩定和諧構成嚴峻挑戰。因此,當前我們國家的法治建設面臨雙重任務:既要加快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司法體制機制,實現以法治國;又要建立健全社會化、多元化解紛體系,動員全社會各機關、團體、組織都參與到社會矛盾的化解與預防中來,形成多元共治的國家與社會治理格局;實踐中,很多地方將預防、化解糾紛上升到當地黨、政機關維護社會穩定第一責任的政治高度,紛紛成立各種類型的糾紛多元化解機制,收到了矛盾排查、多元化解、源頭預防等標本兼治的良好效果。這些理論上的研究成果與社會實踐的成效證成了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可行性與必要性。基于理論與實踐探索的多樣性和一定程度上的無序性,迫切需要以立法進行規范。山東省十二屆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山東省多元化解紛促進條例》,是國內第一部關于多元化解紛機制的地方性法律規范,首次以法規的形式賦予多元化解紛機制的法律地位與功用。條例明確規定各級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人民團體、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和其他社會組織,應當按照各自職責建立健全重大決策風險評估、糾紛排查調解處理等制度,推進糾紛多元化解機制建設,共同做好糾紛化解工作。明確了構建多元化解紛機制乃是上述機關、部門、單位、組織的法律義務和法律責任,是必須履行的法定職責;同時,條例對上述機關、部門、單位、組織的職責分工進行了細化,明確了各個組成部分在多元化解紛機制中的定位和具體職能,防止出現職能交叉、職責越位、推諉扯皮等問題;條例特別指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將多元化解紛機制建設納入當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預防和化解矛盾糾紛能力建設,提供必要的公共財政保障,支持各類糾紛化解組織發展。為多元化解紛機制建設提供財力上的支持,在山東省范圍內成為各級人民政府的法定職責,這就為該機制的建設解除了后顧之憂,也保證了多元解紛機制建設的內在活力和發展動力。
二是通過法律形式明確規定了多元解紛形式的法律地位和法律后果,使得多元解紛手段上升到與國家解紛手段并立運行、相互銜接的高度,為多元解紛機制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持。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的傳統“義利觀”,“德”、“義”等道德范疇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規制力趨減,傳統的、基于道德倫理勸教、輿論施壓的調解、和解功能隨之弱化。法權時代,一個基于利益的糾紛要想得到徹底解決,就必須給當事人講清楚法律對此是怎樣規定的,“分”不定則“爭”不止。在法律職業化、精英化的今天,司法者講法、用法解決糾紛獨享職業優勢,一般社會管理人員則力有不逮;同時,傳統的人民調解、民間和解之履行缺乏必要的強制力,只要一方違約即告調解無效;再是效率過低、成本過高。在“時間就是金錢”的物質時代,效率是權威的重要來源,無效率則無權威。這就是有些地方社會化解紛、人民調解、民間和解有心無力、日漸式微的重要原因。多元化解紛機制要實現健康發展,一是要不斷提高從業人員的業務技能,使其兼備道德與法律的雙重素養;在化解工作中,既會講道德理念,也會講法律規范,從而變舊劣勢為新優勢;二是要賦予人民調解、民間和解一定的法律效力,使其產生對當事人的足夠強制力。要么是通過在正式訴訟中對某些領域糾紛設置必須的調解前置程序(如勞動爭議、離婚調解),要么直接規定某些調解、和解的法律執行力;三是要使人民調解、民間和解等解紛方式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面具備比較優勢。對此,《山東省多元化解紛促進條例》中均設定了法律對策,比如,對于提高從業人員的技能和素養,既明確要求人民法院加強對人民調解、和解等解紛機制的指導和監督,又從組織建設上鼓勵和支持律師階層建立調解員隊伍、參與糾紛化解;還從業務培訓、理論研討、人才培養、信息共享等角度為多元化解紛機制建設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在賦予多元化解紛法律效力方面,明確規定了調解、和解協議可以分別通過申請辦理公證債權文書、申請仲裁確認、申請司法確認來獲得法律效力、執行力的途徑;在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面,條例體現了“調解自愿、不得強制”的精神,對于調解不成的,要及時轉入其他規范程序;為降低當事人解紛成本,條例規定通過上述途徑化解糾紛的,“不得向當事人收取任何費用”,國家機關、人民團體可以通過購買社會服務方式,將適合的糾紛化解工作委托社會力量辦理;對符合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的,有關機關和機構負有提供救濟義務。實踐中,有的地方(如日照市、莒縣)社會化矛盾調處中心打出了“你有矛盾糾紛,我來免費調解”的行業品牌,對當事人產生了足夠的吸引力,吸附了大量的矛盾糾紛,等等。這些規定和舉措,取得了相對于正式訴訟的比較優勢,實現了與正式訴訟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協同解紛的良好態勢。
三是通過法律形式規定了參與多元解紛的社會組織建設,促進形成國家與社會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伴隨“從身份到契約”的社會轉型,人們逐漸解除對原單位的人身依附,獲得了自由參與社會活動的權利,大量的、非官方、平權型的社會組織成為接納“原子式”公民、序化其社會活動的基本單元,也使社會組織成為承接政府釋放管理職能的重要載體。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既需要政府自上而下發揮好管控職能,也需要社會組織以自治方式參與社會治理,解決那些政府管不到、管不了、管不好的社會問題。業內矛盾糾紛的發生率、化解率成為衡量某個社會組織是否健全完善、有無生機活力的重要指標,也是對其社會治理功能是否得到有效發揮的重要評價標準。社會組織要通過及時化解矛盾糾紛來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彌補缺漏,從而實現自我治理、自我完善、自我發展。因此,完善社會組織的解紛功能,促成大量的矛盾糾紛在社會內部消化,就不僅僅是一個消解“訴訟爆炸”、緩解穩定壓力的權宜之計,而是一個推進國家與社會多元共治的長效之策。社會組織的解紛功能要得到充分發揮,一方面要充分認識到解決業內發生的矛盾糾紛是其應盡義務、基本職責,不能將化解矛盾的責任外推;另一方面解紛堅持的指導思想和基本遵循必須契合法律的精神和原則,解紛的過程和結果不能觸碰法律的底線,要接受司法的審查和監督。條例對于基層村、居人民調解組織、行業性調解組織、勞動人事爭議調解組織、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婚姻家庭人民調解組織、殘疾人法律救助組織等的建設及解紛職責作出了明確規定,化解糾紛成為這些組織的法律責任;同時,為保證社會組織解紛合乎法律要求,條例賦予人民法院對社會化解紛的指導、審查、監督之責,對違反法律法規的和解、調解協議、仲裁等不予確認和執行,以此保證社會化解紛與司法解紛指導思想、價值原則、程序方法上的一致性,實現以規則之治引導多元共治、規則之治與多元共治并存共興的良法善治格局。
可以預見,《山東省多元化解紛促進條例》的實施,必將推動全省多元化解紛機制建設乃至國家與社會治理工作開創一個嶄新的局面。
(作者單位:莒縣人民法院)
責任編校:范岱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