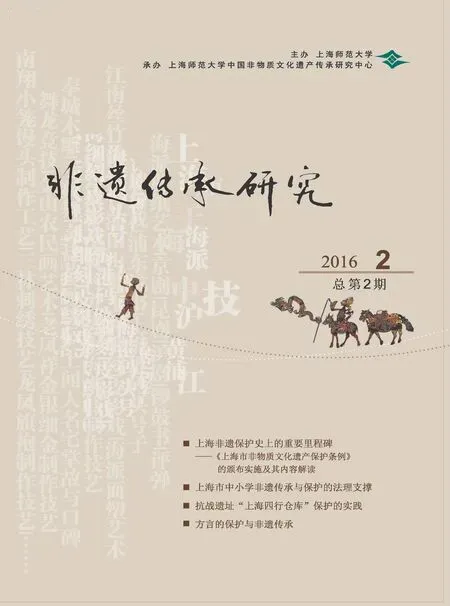吳宗錫與新中國評彈(上)
吳宗錫口述 王其康 毛信軍整理
吳宗錫,詩人、作家、戲曲曲藝理論家。中國曲藝牡丹獎終身成就獎和上海文藝家終身榮譽獎獲得者。曾任上海評彈團團長,中國曲協副主席,上海市曲協主席,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常務副主席。江浙滬評彈領導小組組長。日前,筆者就上海評彈團的前世今生,對吳宗錫老先生作了專訪。以下是采訪整理稿。
一、新中國評彈開拓者和建設者的由來
講新中國評彈開拓者最早是原國務委員、外交部長唐家璇提出的。有一次唐家璇同志到上海評彈團一起吃飯時,邀請我參加,過去我從未與他碰過面。唐家璇同志向我敬酒時說:“你是評彈的開拓者和建設者。”我聽了嚇一跳,覺得評彈開拓者應是過去清朝的事情。我說不、不、不……。他補了一句:“你是新中國評彈開拓者和建設者。”
二、為什么能接受新中國評彈開拓者和建設者的講法
我后來想了想,這個開拓者我是能接受的。講到開拓者,有些情況可能大家不太了解。1949年前,我沒有接觸過評彈藝人。后來聽中國戲劇家協會原副主席劉厚生同志講,周恩來同志在國共和談破裂離開上海前交代給上海地下黨一個任務:派一些作風正派的同志到舊日的戲曲界去。像劉厚生搞話劇的,后來派到越劇界去。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上海文委也就是上海地下黨根據周恩來的指示,決定上海當時地下黨搞文藝工作的同志,到戲曲界去。當時的看法是北方南下干部不一定了解上海的戲曲界,上海的同志進去后工作比較方便。當時我在地下黨是搞文藝的,做夢也沒有想到,領導找我談,要我轉為搞戲曲。找我談的地方是現在的靜安公園,當時是靜安外國公墓。那時地下黨碰頭,要么找非常熱鬧的地方,要么找非常冷靜的地方。那時的外國公墓誰都能走進去的,但是沒有人進去的。約我在公墓里面一邊散步一邊談,希望我去搞戲曲。當時我不大愿意,因為那時看不起戲曲,總覺得滬劇、越劇要比文藝界低一些。但這是黨的任務,只好接受。接受后,劉厚生同志來聯系我們這批人,我與另外三位同志成立了一個小組,討論如何去搞地方戲曲。要開始分工了,我當時不愿去搞滬劇、越劇,那時還有維揚戲。我想我是蘇州人,而評彈比其它戲曲文學性要強一些,比較高雅一些,還是去搞評彈吧。所以,我主動提出來,我去搞評彈。其他同志就分工搞滬劇、滑稽戲等。1949年初,上級就確定了我去搞評彈。這個階段一直到上海解放,除去地下黨給我的其它任務,包括發信要求文藝界人士留在上海等工作之外,我就是對評彈進行調查研究。那時候去跑書場、收集資料,包括評彈的報紙、書場陣容表,演員不認識,我就通過評彈小報的一個作者去認識評彈演員。1949年初,我就開始接觸評彈了,所以可以說我是開拓者。
三、1949年5月28日首次接觸評彈界人士
我接觸評彈人士是哪一天?上海市是5月25日南部地區解放,5月27日全市解放。5月28日,我代表領導去參加上海演藝協會評彈分會在泥城橋大中華大陸電臺做的特別節目。這個特別節目宣傳解放軍進城,老百姓歡迎,解放軍是不擾民的,以穩定人心。所以上海一解放,第二天電臺就有特別節目,有戲曲、評彈、滑稽戲等。那時,評彈在電臺做特別節目很多,因為評彈主要是聽的,電臺都有評彈節目。5月28日上午,我就到大中華大陸電臺,電臺有地下黨同志來組織和安排節目。我帶了些宣傳材料去,那時我是不大聽評彈的,也不知寫出來的東西是否像評彈,總的都是一些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擾民,解放軍是為人民的等。我記得來的評彈演員很多,都比較有名。我印象比較深的,第一個見到的是趙稼秋。那時我是沒有單位的,就說我是上面派下來的,要你們宣傳,他們也心照不宣,你是上面派下來的,是代表共產黨來的。隨后我就把開篇給趙稼秋,說你們可以唱嗎?趙稼秋善于唱白話開篇,連說“好唱,好唱,我好唱”。所以,我接觸評彈演員是上海解放第二天的5月28日。自此之后,地下黨通知我到市委組織部去報到,以后就到軍管會文藝處,作為軍管會文藝處的干部。我原來搞評彈就仍然搞評彈。
四、初期怎樣開展評彈工作
那時的工作倒不是領導與被領導,跑進去是聯絡、交朋友、去組織他們學習等工作。我后來就到現在的壽寧路民生里評彈協會去了。著名評話演員金聲伯最近還講起過我去報到的情景。他說,你進來時(那時有一個工會干部陪我進去),你們兩人年紀很輕,穿了套西裝。金聲伯那時17歲,坐在門口,他說看見你們進來的。開始工作還是照地下黨聯系群眾的辦法,一是聯系年紀輕的,當時認為年紀輕的比較好,思想進步;還有是發現比較正派、積極的一些演員。所以最早我聯系的、把他選擇作為骨干的是潘伯英,后來他到蘇州評彈團去了。接著還組織所有演員學習,那時主要是學習“工人讀本”。那時沒有什么學習材料,“工人讀本”是比較淺顯的,里面講勞動創造世界等內容。當時幫助他們成立了許多小組,婦女有婦女組,年紀輕的叫青年組。有人對我說響檔他們喜歡睡懶覺,不大肯來,每個星期有一次在南京路成都路有個叫大觀園的地方,那兒是個商場,有個可喝喝茶、布置得蠻好的地方,那些響檔在那里唱京戲,每周有一天像票友那樣,學唱京戲。你這時候去,就能見到這些響檔。于是,我就找了個時間去大觀園,到了后也不去打擾他們唱京戲,唱好京戲再請他們坐下來學習。后來就比較正規了,婦女組擺在滄州書場,我就去和他們一起學習,那時就這樣領導的。潘伯英也有個小組,他們在福建路匯泉樓。潘伯英與我關系比較好,向我表示擁護共產黨。我覺得他人比較熱情,也比較正派。他對我說,我們組織一個小組在匯泉樓,你可以過來。我就去了。那時匯泉樓有朱慧珍、唐耿良等人,與潘伯英一個圈子的。那時我一是組織他們學習,二是推動他們說新書。那時認為評彈是舊的封建文藝,要改造。我就與潘伯英商量著要說新書。有這么多藝人,這么多拼檔,你叫他們說新書,他們又沒有新書。這時潘伯英出的點子,我們來組織一出書戲。書戲是化裝上臺的,可以把上海比較有名的藝人全部都包括在內。那么說什么內容呢?研究下來決定說新書《小二黑結婚》,是從解放區來的。于是,由潘伯英執筆,寫了《小二黑結婚》這出書戲。演出在南京大戲院(后改為上海音樂廳)進行,演出的劇照資料評彈團內應該還有保存,評彈詞典上也有一張劇照。蔣月泉演小二黑。那時最紅的是范雪君,她演小芹。劉天韻、朱耀祥、張鑒庭、張鴻聲等當時在上海的(嚴雪亭當時不在上海,有些人出去了)全部都上臺了。當時的影響是蠻大的。這等于全體評彈響檔亮相,表示他們是擁護共產黨的,是要說新書的,就像是個宣言似的。這大概是1949年6、7月份的事。接下來再聯系他們,推動他們學習,這的確是新中國評彈的開拓工作。
五、從創建評彈改進協會到領導上海曲藝家協會
在國民黨時期有一個評彈界協會,到解放后全部要接受改造,我幫助他們籌建了評彈改進協會。開會就在軍管會文藝處大禮堂,就在同孚路(現石門一路),現在的民立中學隔壁。后來因為評彈屬于曲藝,中央成立曲藝協會,上海就成立了分會。當時分會主席是劉天韻,我是副主席兼秘書長,實際上分會是我籌備開始的。到1979、1980年“文革”后,分會都改成協會了,開始叫曲藝工作者協會,后來改成曲藝家協會。這些協會的成立都是我經手的。后來上海評彈團黨支部實際上是領導上海評彈界的。我也做了很多評彈界的工作,評彈團當時認為我們是整個上海評彈界的核心,上海評彈界歸我們支部領導。我們搞過中青年演員培訓班,很多工作都是由評彈團出面。所以,現在評彈界一些年歲老一點的演員都和我關系很好。
六、評彈團成立和赴治淮工地
我最早是寫詩歌的,那時要題個筆名,我父親啟發我,他說用“弦”。詩歌古時叫“弦誦”,后來我題了個筆名叫“左弦”,左當時表示進步、革命,所以我是革命的詩人。后來我搞評彈了,有人問你是否早就搞評彈了,筆名中用“弦”字。其實不是的,但很奇怪,我像是命中注定要搞評彈工作的。“文革”后一次開會時,見到讀大學時的一位教授對我說,我們大學里沒有“評彈”這一課程,你怎么會搞“評彈”的。后來軍管會文藝處改成上海市文化局,我在文化局文藝處工作,聯系評彈少了。有一段時間我在編審科工作,管戲曲劇本,聯系戲曲編劇和導演,與評彈的聯系比較少,所以成立評彈團時,派的干部不是我,是一個叫何慢的同志兼的,他是創作室主任。實際上他也沒有去評彈團。團長是演員劉天韻。所以有人講我是第一任團長,其實是訛傳。但是事情也是蠻巧的,那一年搞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要派知識分子干部去參加土改,我原來是被派去參加四川土改的,后來毛主席提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治淮委員會說上海文藝界應該派些人去參加治淮工作,這也是接觸工農改造思想的好機會。所以1951年下半年就派我去參加文聯的治淮工作隊。文聯治淮工作隊有三個隊長,一個叫楊村彬,話劇編導,寫《清宮外史》的。還有一個是搞音樂的司徒漢,再有一個就是我。三個人中司徒漢是搞音樂的,他管美術、音樂、新文藝界,一個是管話劇,我當時分管戲曲,那時有很多戲曲編劇和導演。這時正好成立了評彈團。評彈團成立第二天,領導就決定評彈團也去參加治淮學習。這一決定現在看起來是非常好的。過去評彈藝人都是單干從未參加過集體生活,下去參加治淮接觸工農,為評彈團打下了很堅實的思想基礎。評彈團11月20日成立,上面決定第二天就參加治淮學習,11月23日就參加治淮工作隊,我們一起出發,由我分管領導評彈團。所以評彈團成立我沒有參加,但實際上評彈團成立第二天起,我就帶他們這個團了,一起到治淮工地去了三個月又二十多天。這時與評彈演員的關系又進了一步。原來與他們熟悉的,現在又進一步聯系和熟悉了。那時的生活比較艱苦,與民工及團員同吃同住同勞動。從治淮工地回來,當時上海在搞三反、五反運動,我被調到戲改整風領導小組。
七、被派往上海評彈團工作
1952年3月從治淮工地回來后,5月份上級領導考慮到評彈團當時沒有駐團干部,原來的何慢是兼任的,但他有自己的本職工作。我記得有一次與劉厚生一起吃飯時講起這件事,當時我就自告奮勇說我去。因為那時在機關里工作,每天上班下班較枯燥。到評彈團去,可出去巡回演出,到外面跑跑。我對劉厚生同志說,評彈團要人,我去吧。就這樣,組織決定派我去評彈團了。那時的評彈團團長是藝人劉天韻,駐會的干部也不能叫黨代表,叫政委好像又太高了,所以最早叫教導員。起初我是教導員,劉天韻是團長。后來覺得藝人當團長,分散他的精力,他還是搞藝術比較好,所以后來是我做團長。我不是評彈團第一任團長,但評彈團干部當團長,我是第一個。
八、年輕人怎樣當評彈團團長
我到評彈團28歲,上海解放時我25歲,當時評彈演員年齡都在35歲以上,年紀較大的都是40好幾歲了。我28歲,大學畢業,其它社會經歷不多,后來做軍管會干部。而他們年齡比我大,甚至要大一倍,都是社會經歷豐富的。以前講起來叫跑江湖,評彈藝人比一般跑江湖層次要高一些,但實際上也是在江湖上生活的。我與他們有一個極大的反差,我年紀很輕就進去了,所以后來陳云同志說,他們是五顏六色都見過的,鑒貌辨色的。陳云同志說,吳團長啊,我替你想想,你這個團長不好當啊。我那時去評彈團也有點糊里糊涂,沒有覺得一點怕。而且在治淮時與他們打成一片,建立了深厚友誼。這些評彈演員待我都比較好,當然后來也有各種矛盾和意見,但他們總有個思想你是黨派來的,是與我們一起為搞好評彈來的。所以就這樣來到評彈團,一直干到1984年,搞了三十幾年。
九、五四新文化對舊文藝的改造
我覺得當時周恩來同志的指示是正確的,派我們地下黨一些懂文藝的同志去文藝界,與一般派個行政干部去不一樣。解放后,黨的方針政策是要為人民服務、推陳出新。說我是新中國評彈的開拓者和建設者,那么什么是新中國的評彈呢?我總結了兩條,一條是演員懂得了為人民服務,當然也是為國家、為社會作貢獻。舊中國的演員是為自己個人名利、為生活、為衣食。新中國的評彈藝人,就是要懂得為人民服務,特別是國家劇團、人民評彈團。第二條是對書目要推陳出新,進行整舊和創新。老的書目中工農大眾做主人翁是沒有的,都是太太小姐老爺少爺。新社會既有整舊,也有創新,有了以工農大眾為主人翁的新書目。我現在想一想,當初我們進入戲曲界,也是做了這方面的工作。當時搞評彈團,要改人、改書、改戲,要推陳出新,評彈團有一個宗旨就是要實驗示范。實驗是在書目中、藝術上要創新實踐。示范就是要推動其他團,帶動其他團。這一點,應該說我們是做到了。比如說,評彈團搞中篇。現在有人講以中篇為主是不對的,評彈應該演長篇。其實評彈團從未講過以中篇為主,但是評彈團創作出中篇適應了當時人民的需要,現在群眾仍然蠻歡迎中篇的。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一公演,聽眾反應極其強烈,而且吸引了新的聽眾。于是,整個評彈界成立了八九個小組都演中篇。中篇順應了時代和人民的需要,示了范,結果推廣出去了。所以上海曲協副主席周介安講我是根據黨的戰略要求,用五四新文化和黨的文藝政策來推動評彈的傳承和創新。所以說建設者應該體現在這些方面。
十、與評彈演員的關系
一個搞新文藝的青年,結果打入當時所謂的舊藝人里面去,且一些當時還是響檔。這是因為當時我是黨員的身份,他們比較尊重。此外,我也的確是虛心向他們學習的。后來到團里工作也有好處,與他們完全打成一片。很多演員對我有非常感人的事情,甚至于我不在評彈團后也這樣。去年我90歲,他們一批演員要為我祝壽,一道吃頓飯。我說倘然一般人請我過90歲生日,我是會拒絕的。我們是幾十年的老朋友了,不是為了奉承拍馬,而真正是一種感情,一份情意,這份情意我要領的。結果大家買了蛋糕,還為我唱了生日歌,我非常感動。我覺得人與人的感情,沒有無緣無故的愛,我們的感情是建立在評彈基礎上的。他們覺得我對評彈藝術是一心一意的,是在幫助他們搞評彈藝術。
十一、進行評彈藝術的研究
我搞評彈理論研究的第一個階段是到評彈團后,當時覺得評彈要宣傳,要讓更多的人喜歡評彈。所以寫了《怎樣欣賞評彈》等,目的是要讓更多聽眾理解評彈,不是要做什么理論家。后來文化大革命把評彈說得一文不值。當時我想,評彈不好,怎么能吸引這么多的聽眾。我就想評彈為什么這么美,到再后來想許多老藝人的經驗,包括我的經驗能夠對下一代演員的創作演出作些參考。所以,我就寫了這些東西。我覺得理論一定要從實踐出來的。我到了評彈團,開始改編了幾出短篇,就是按毛主席說的若要知道梨子是啥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我不會唱,我唱出來不入調,但我會寫,我開始學著創作。后來做了藝術指導,幫助他們改進藝術。我覺得真正的理論必須來自實踐,是實踐經驗的提升。當然,這個實踐不是我一個人的實踐,是與演員們共同的藝術實踐、創作實踐。所以,周介安同志說:“整舊的過程是吳宗錫所代表的新文藝思想對傳統評彈藝術實行滲透的過程,是令評彈藝術清新化、去俗化、趨雅化的過程,是上海評彈團整體風格逐漸成熟的過程。而吳宗錫本人也在整舊的過程中對評彈的藝術規律有了更深刻的領悟和把握。”我是接受的。
有關上海評彈團的群體風格,文藝戲劇理論家沈鴻鑫等同志也是肯定我的。也有人現在提出來,這是“左”的東西。怎么可以有“群體風格”,“個人風格”發揮怎么會有“群體風格”,這是他們沒有理解。過去,上海評彈團跑出去無論到碼頭演出或書場演出,老聽客都講他們聽得出這是上海評彈團,那不是上海評彈團。為什么呢?因為我們追求一個藝術的格調,藝術的品味,而且在臺上不濫放噱頭、不庸俗化,這就是上海評彈團的風格。這些藝人有自己的風格,像蔣月泉有蔣月泉的風格,張鑒庭有張鑒庭的風格,楊振雄有楊振雄的風格,嚴雪亭有嚴雪亭的風格,不是把他們抹殺了,而是在他們的個性中有一個共性,那就是追求藝術不要庸俗,要高雅,也就是藝術的目標是為人民服務,不是在臺上我要賣噱頭吸引聽客。所以,這就是群體風格。這個群體風格不是很容易培養出來的,是大家在實踐中互相切磋,互相展開批評,逐步達到的。
十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評彈大發展得益于天時地利人和
有人說:“你做團長時我們要聽評彈,你現在不做團長了,我們評彈也不聽了。”這當然是說笑話。但是我講這不是吳宗錫的功勞,主要還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來講,最主要是新中國。地利是上海的環境。人和當然有很多的好演員。對評彈的發展,有人講評彈發源地是蘇州,發祥地是上海。這種說法可能與評彈的兩次繁榮有關。一次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如果不到上海來,評彈不會有這樣的興旺。那時好多藝人來到上海,一個是上海有許多唱片公司和電臺,那時上海有五十多家電臺,沒有一家電臺沒有評彈節目。還有一個是海派的藝術環境,評彈很善于吸收,吸收了很多戲曲甚至電影的精華,蔣月泉曾說他的唱還是學的平克勞斯貝的發聲。現在說起來是吸收了戲曲的先進一面,包括各種文藝。如果不是新中國,不是在上海,不是上海評彈團,就不會有今天的評彈,這是第二次繁榮。所以我講是天時地利人和。我看到一些資料,評彈剛進上海時,上海沒有評彈聽眾。因為上海人說浦東話,不習慣聽評彈。評彈進上海,是與滑稽、雜技等節目放在一起演的。所以說對聽眾一個是要適應,一個是要培養,再有一個是要爭取。起初評彈在上海是沒有人要聽的,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評彈聽眾多得不得了。解放以后,也是順應了時代,發展了評彈。既是培養了聽眾,又是爭取了聽眾,也是適應了聽眾。這個適應包括像在交易所等工作的每天來聽的老聽眾,但新聽眾沒有時間每天來聽,對這部分聽眾他如不聽中篇,他更沒有時間聽長篇。后來我們到北京去演晚會,都是一段一段的書,人家要來聽。一段一段的都是精品。所以說,我們不是一定要搞中篇,不搞長篇。長篇也搞的,在一般老的書場內照樣說長篇。但是沒有中篇,就沒有這么多新聽眾,包括現在的一些六七十歲的干部,當時的中學生、大學生歡喜聽評彈,就是我們順應了聽眾,適應了聽眾要求,所以評彈得以興旺。評彈最早的書場都是茶樓書場,如上海城隍廟的茶樓書場,是茶館店改的。到解放后是舞廳書場,舞廳都改成書場,可以容納一二千人。那時的西藏書場,最早叫米高梅舞廳。還有新成書場、大滬書場等都是千把人的。一直到評彈進入到文化廣場,我看到有資料講一共演了13場。現在講評彈團到文化廣場似乎是輕而易舉的,六七千人的座位客滿,都是外面排隊買票的,且上臺演出時下面凝神靜聽。這樣六七千人的一個文化廣場要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這應該講是評彈的一種興旺。這是評彈藝術適應了上海的聽眾,上海聽眾需要這樣的藝術,而且很多聽眾是我們培養的,我們培養了一批我要聽評彈、我愿意聽評彈的聽眾。所以說沒有上海就沒有上海評彈團,沒有上海評彈團也就沒有中篇等形式。這是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個共同結晶。最近上海評彈團演了一出中篇《林徽因》,聽說票買到五場了。我們那時演中篇《一定要把淮河修好》,那時叫“放票板”的,開始想能演五天就蠻好了。到第五天,還有不少人來買票,于是再放。包括后來的中篇《王孝和》,我記得我有一本臺歷,在上面記數字的,票務組每隔兩天要對我講,現在賣掉多少了,數字不斷地增長。有幾出中篇賣了三個多月。最長的一出中篇是《蘆葦青青》,那時是“四清”期間,許多演員下鄉了,不是主要演員演的,演了七八個月。我們的演出在藝術上適應了這些沒有時間每天來聽的聽眾,反過來聽眾也支持了評彈的許多改革。所以說不是不要長篇,而是有許多新的東西是適應了時代,得到了聽眾的支持。我覺得藝術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深入群眾,還要跟上時代。
十三、搞評彈的人必須懂文學、戲劇和音樂
我再補充一點我的認識:評彈有文學性、音樂性、戲劇性;搞評彈必須要懂文學、懂戲劇和懂音樂。一般的行政人員和懂文藝的人看似是一樣的,實際上是完全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