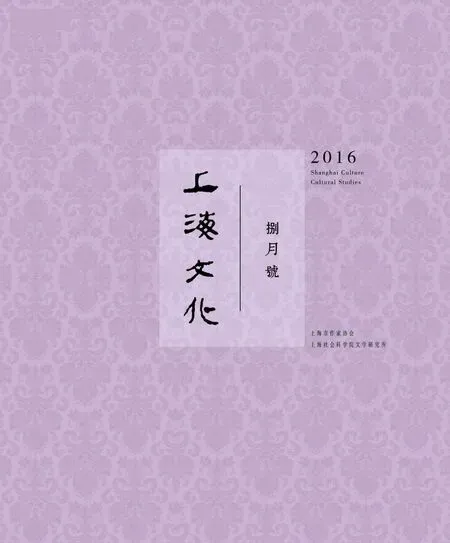略論蔣孔陽美學的性質、意義及其他
——兼向閻國忠先生請教
劉陽軍
略論蔣孔陽美學的性質、意義及其他
——兼向閻國忠先生請教
劉陽軍*
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這一本質地關涉其自身之理解和闡釋取向的問題,是蔣孔陽美學思想研究的基礎性問題。蔣孔陽美學奠立在唯物史觀這一革命性哲學根基之上,并由此獲得和確立了基本取向甚至定向。由此哲學根基來透視和評估,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大致可從如下三個基本點來澄清和闡明:一、以馬克思“存在論革命”即“感性的活動”(或實踐)或“對象性的活動”,而非某種抽象的、天真的假設或假定為基礎,來進行美學思考和探索;二、實質地擊穿了形而上學美學“意識的內在性”封閉建制,直面和貫穿“對象領域”;三、在思想路徑上不再沿襲形而上學美學的“知識論路向”,而走上“生存論路向”。這為實踐美學一脈的探索和發展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蔣孔陽美學 唯物史觀 形而上學美學 存在論革命 意識的內在性 生存論路向
蔣孔陽先生是享有卓越聲譽的當代著名美學家,其美學被譽為中國美學界獨樹一幟的“第五派”。①朱立元:《中國美學界獨樹一幟的“第五派”》,《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2期。關于蔣孔陽美學,學界探討和研究頗多,而且成果非常突出。綜觀這些探討、研究,大致來說視野廣闊,幾近涉及了蔣孔陽美學的方方面面。不過同時,我們也發現,有關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這一基礎性問題,過往研究涉及不多,更鮮見系統的專題探究。知名學者閻國忠先生在蔣孔陽美學研究方面撰寫了視角獨特、水平很高,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可以說是蔣孔陽美學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獻。但是,若從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這個高度來審視,其中委實也存在一些有待深入之處。因此,在這里,我將嘗試以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問題為中心,同時兼及閻先生一些論斷或觀點,談一點粗淺理解和看法,以求教于閻先生以及學界其他方家。
一、蔣孔陽美學的哲學根基:哲學革命與唯物史觀
蔣孔陽美學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觀這一堅實哲學基礎之上的。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因為其時特殊思想語境和時代背景使然,另一方面則主要是蔣孔陽自身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及其思想道路的自覺遵循、堅守和實踐。從早期《德國古典美學》到晚期《美學新論》,可以說自始至終都堅持以此為思想引領和實踐指向,不僅直接援引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以及論點和核心命題為憑據,而展開創造性闡釋和發揮,更關鍵的是切切實實地自覺貫徹和實踐了這一革命性的哲學觀。因此,若要全面而準確地領會和把握蔣孔陽美學思想,首先就需要透徹領會和把握其哲學基礎,即唯物史觀。閻先生對蔣孔陽美學思想的理解、論釋與評價,雖然論及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及其思想對蔣孔陽美學思想建構和形成的積極影響,但對唯物史觀在蔣孔陽美學思想中的基礎性位置和革命性影響的關注和認識仍然有待深化。大致說來,這一方面是受唯物史觀的意識形態化以及簡單化、機械化理解等時代氛圍影響,另一方面則可能是由于閻先生自身囿于長期以來學界關于唯物史觀的成見和定見,而造成對唯物史觀的革命性及其意義的懸置和忽視。這很可能是閻先生難以真正洞穿和參透蔣孔陽美學思想之核心奧秘的根本所在。
唯物史觀對于中國學界來說早已是耳熟能詳的了。在過去較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受國際上費爾巴哈化馬克思主義、黑格爾化馬克思主義、斯大林化馬克思主義,①參見俞吾金:《被遮蔽的馬克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以及國內極左馬克思主義等多重影響和遮蔽,關于唯物史觀的理解和闡釋呈現出較大程度的“正統化”、庸俗化、激進化傾向,譬如把唯物史觀與辯證唯物主義進行拆分而作對立、分離的對待和理解,②這種觀點并非肇始于我國,早在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部正統馬克思主義經典中就有較為集中的體現。在“蘇聯熱”驅動下,這種觀點逐漸成為主流觀點,并在我國較長一段時期內都占據了主流位置。認為前者集中于社會歷史領域,后者聚焦于自然觀上,對此已有學者提出了嚴肅批判。③參見朱立元:《實踐美學哲學基礎新論》,《人文雜志》1996年第2期;楊耕:《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實踐唯物主義的內涵——基于概念史的考察與審視》,《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正是因為這樣一種傾向和狀況,唯物史觀所蘊藏著的一些原初的、根本的意義由于長期的耽擱以及陷于晦黯狀態而得不到解蔽以及應然地昭示、顯現。這原初的、根本的意義,本質上講就是唯物史觀的革命性。這種革命性不是“武裝革命”,而是徑直本質地關聯到馬克思的“哲學革命”。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種革命性雖然曾以諸種形式被不同程度地認識、關注和認可過,但是極大多數的認識、關注和認可仍然不同程度地囿于現代形而上學的基本框架和建制,因而是不充分、不徹底、不真確的。
唯物史觀的革命性,最根本地說來關涉如下三方面:首先,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由存在論(Ontology)④朱立元:《對Ontology與唯心、唯物之關系的考察》,朱立元主編:《第一、二屆中德雙邊國際美學研討會論文集》,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62-177頁。基礎或根基處發動的“哲學革命”,并且是這種革命的必然的決定性成果。這種革命的核心或樞軸,是“感性的活動”(或實踐)或“對象性的活動”。⑤吳曉明:《試論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基礎》,《學術月刊》2001年第9期。僅由此來看,唯物史觀首要本質地指向并敞開為“實踐論”①鄒詩鵬在《“實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的相通性——基于〈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與〈德意志意識形態〉的探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5年第4期)中深刻指出,“實踐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是本質相通的,須要避免和防止對兩者進行疏離的、激進的理解和把握。筆者也認為唯物史觀與實踐的唯物主義是本質相通、內部鞏固的,整體的、一體的復雜關聯在一起。或“實踐的唯物主義”。②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73頁。存在論基礎的這種最徹底澄清和革命性變動,最關本質地奠定、確保并呈示了馬克思哲學的存在論基礎。其次,這種存在論革命,徹底地、實質地擊穿和瓦解了現代形而上學的基本建制,這種基本建制大體說來就是“意識的內在性”。由此可以判定,這不僅“整個地改變了存在論設定存在者整體的基本結構”,而且意味著并標志著“超感性世界神話學的破產”、③吳曉明:《馬克思的存在論革命與超感性世界神話學的破產》,《江蘇社會科學》2009年第6期。整個柏拉圖主義的顛覆以及全部形而上學的終結。④吳曉明:《馬克思的哲學革命與全部形而上學的終結》,《江蘇社會科學》2000年第6期。最后,這種存在論革命要求根本地揭示并訴諸“前概念、前邏輯和前反思”的世界(或“生活世界”),而非“概念的、邏輯的和反思的世界”,呈現了人與自然的原初關聯,從而在存在論基礎上決定性地超越了“知識論(或范疇論)路向”,而開啟并敞開為“生存論路向”。⑤吳曉明:《重估馬克思哲學革命的性質與意義》,《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4期。由此,我們對“Ontology”的領會和把握,不能再憑借其傳統語義,而應當是“生存論”。⑥鄒詩鵬:《馬克思實踐哲學的生存論基礎》,《學術月刊》2003年第7期。上述三個方面共同鑄成了唯物史觀的原則高度與全新地平線。
前面所述,唯物史觀是蔣孔陽美學思想之哲學基礎的論斷,歸根到底正是在此意義上說的。過去對唯物史觀的這種革命性的有意或無意的忽視和遮蔽,嚴重影響了這一原初要義的徹底澄明和真確顯現,從而造成唯物史觀對我國當代美學,尤其是實踐美學一脈的奠基性作用和革命性影響較長時期以來沒于晦暗狀態而得不到應然的彰顯。因此,我們的這種強調絕非可有可無、無足輕重,而是具有根本性的、決定性的意義。
正是如此這般的唯物史觀,真正構成了蔣孔陽美學思想的哲學根基。這具體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和把握:首先從文獻學上看,蔣孔陽重視并大量引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馬克思主義原典。這一點顯著地凸顯了其美學思想的馬克思主義淵源。關于這一點,可從其眾多著述中得到有力、客觀印證,在此無需贅言。當然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蔣孔陽之所以如此這般重視馬克思主義原典,不是因為外部因素的刺激、干擾和強制,抑或一廂情愿、盲目崇拜,根因在于馬克思主義原典的唯物史觀根基及其美學意蘊。譬如,蔣孔陽尤為關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其中的奧秘恐怕就在于這部經典是“馬克思新的世界觀和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體系”的誕生、孕育之地。⑦參見蔣孔陽為朱立元《歷史與美學之謎的求解——論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美學問題》一書所作的“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頁。
其次,從撰述的指導精神和思想原則上看,蔣孔陽始終不渝地堅持和貫徹唯物史觀及其辯證法。這既是其高度自覺的馬克思主義意識、境界的重要體現,也是其撰述精神和原則的真實寫照。譬如,即使蔣孔陽早期的著述《德國古典美學》,根據相關研究成果,也可稱得上是這一方面的優秀之作。①朱立元:《西方美學斷代史研究的經典之作——重讀蔣孔陽〈德國古典美學〉》,《江西社會科學》2015年第4期。
再次,進一步,由存在論(Ontology)根基來看,蔣孔陽美學無疑是建立在“感性的活動”(或實踐)或“對象性的活動”這一根基之上的,而非某種抽象的、天真的假設或假定之上。更簡約地講,就是建立在馬克思的實踐論這一哲學基礎之上的,②蔣孔陽:《蔣孔陽全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50頁。而為突出“存在論”意義,以朱立元先生為代表的一些重要學者直接采用“實踐存在論”這一具有重大突破性和創造性的表述。③參見朱立元:《尋找存在論的根基——蔣孔陽美學思想新論探之二》,《學術月刊》2003年第12期。在此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樣一個論斷絕非我們對其進行“強制闡釋”④參見張江、朱立元、王寧、周憲等先生關于“強制闡釋”的系列探討文章。如張江《強制闡釋論》、朱立元《關于“強制闡釋”概念的幾點補充意見》,以及拙文《“強制闡釋”現象及其批判——兼反思百年中國文論現代化道路》(《文藝評論》雜志即將刊出)等。的結果,而確確實實是對其美學思想的根本透視和客觀總結。譬如,作為其立論的主要憑據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自然的人化”等馬克思主義思想,與“感性的活動”(或實踐)或“對象性的活動”不僅都誕生、孕育于《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⑤巴日特諾夫在《哲學中革命變革的起源》(劉丕坤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中就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是馬克思“哲學中革命變革的起源”。并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態》等經典中得到進一步發展和完善,更為關鍵的是它們是一脈相通、本質一致、意涵根本契合的,正是在此基礎上,“人是世界的美”、“美在創造”、“多層壘突創”等系列美學論點得以誕生。可以說,正是這樣的堅實基礎,奠定了蔣孔陽美學的高起點、高格調、高境界等非凡品格,拉開了與一般美學的距離。一方面,蔣孔陽不僅從對國外尤其是德國古典美學的深厚研究中大體上已經體會到了西方形而上學美學的諸多不足和弊病,而且其馬克思主義態度和立場使其對之保持了高度清醒、批判的認識和把握。另一方面,或許正是因為這一點,蔣孔陽美學徑直訴諸鮮活的、現實的審美關系或審美活動本身,而且這種美學探索和建構自覺地否定并躍出了西方形而上學美學的固有觀念論建制之怪圈,即不再憑靠抽象的、虛假的“意識內在性”來構筑和夯實人類美學。由此看來,這種美學思考和探索,在基本建制上已突破并本質地迥異于西方形而上學美學傳統,也與現當代中國眾美學流派不盡一樣。
最后,正是因為對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透徹領會和把握,以及由此而對西方形而上學美學、國內諸路美學展開的深刻洞悉和反思,蔣孔陽美學較為自覺地擺脫或脫離了西方形而上學美學的知識論或范疇論路向,而走上了生存論路向。更確切地說,蔣孔陽否棄了先行地訴諸抽象世界、超感性世界等來展開美學探索和建構的道路,而積極選擇并實踐著首先本質地揭示和訴諸“生活世界”本身的美學探索和構筑之道路。這里需要強調的是,這種抉擇絕非無關緊要,因為這種抉擇原則高度地、內在鞏固地堅守并貫徹了唯物史觀及其實踐指向和要求,進一步講,它本質地關涉“感性活動”或“對象性活動”本身對美學事業的開啟、敞開和開放這一道路定向。
由此看來,蔣孔陽美學是對唯物史觀深刻領會和把握的思想結晶,而且就是扎扎實實地建筑在唯物史觀這一堅固基礎之上的。由此,欲真正徹底、根本地洞悉和把握蔣孔陽美學,我們就必須而且應當進入其哲學根基處。
二、蔣孔陽美學的性質與意義——兼評閻國忠先生的觀點
之所以如此重要地強調唯物史觀這一哲學根基,根本原因在于它決定性地關涉蔣孔陽美學的基本性質和意義,或美學道路之定向。正是因為不少學者未能充分地、實質性地注意到這一哲學根基及其革命性指向,尤其是對蔣孔陽美學的基礎性、決定性影響和作用,造成了對蔣孔陽美學的一些本質性誤讀和誤解。在這里,我們著重從如下幾個方面展開簡要辨析和評論,以期達成更確切的理解和把握。
首先,我們需要弄清唯物史觀如何決定性地關涉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蔣孔陽美學作為對現當代中國美學諸流派以及德國古典美學的一個重要的批判性總結、反思以及在此基礎上的重鑄,可以說在最關本質的方面業已達到或實現實質性突破和推進,顯示出非同一般美學的境界和高度。這種境界和高度,如前所言奠基于唯物史觀,切實而內在鞏固地構成并定格了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如此一來,我們對蔣孔陽美學的性質和意義的透視與估價,就必須而且應當首要由此哲學根基及其定向來展開。這里將結合前面的論斷扼要探討三點:第一,馬克思“存在論革命”打通了通向和切入美學現象、美學現實、美學世界的真正道路,蔣孔陽由此而展開了極具啟發和革新意義的美學探索。這集中體現在“審美關系”這一最根本、最核心概念之創構上。在蔣孔陽美學里,“審美關系”是一個唯物史觀基礎上的概念,或者說“實踐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概念。①朱立元編:《當代中國美學新學派》,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9頁。那么,這應當如何理解或者說到底意味著什么呢?(1)人對現實(包括自然)的審美關系既是人類社會長期實踐和發展的必然產物,同時又仍在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審美關系扎根于豐富而復雜的人類社會,是一種歷史的、現實的社會關系或現象。之所以如此,這歸根到底是由人的復雜本質決定的,而這種復雜本質,就其現實性而言就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56頁。(2)審美關系絕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說明和規定,而是表征著作為對美學現象、美學現實、美學世界的現實規定性,它徑直就是一種特殊的實踐,即特殊的“感性的活動”或“對象性的活動”。③朱立元先生在《蔣孔陽審美關系說的現代解讀》中認為,審美活動是審美關系的歷史的、現實的展開,審美關系大致來講就是審美活動。因此,審美關系絕非看不見、摸不著、感覺不到的,而是歷史地、現實地發生著。蔣孔陽關于審美關系之“感性的形象性和直覺性”、“外在的自由性”和“內在的自由性”,人作為整體與現實發生關系并由此能夠全面展開“人的本質力量”以及人對現實的“感情關系”之凸顯等①蔣孔陽:《蔣孔陽美學藝術論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0、12、13頁。特性的判定就有力地說明了這一點。(3)審美關系表征了人對現實,尤其是人對自然的原初的、全面的、整體的關系,從而由存在論根基處滌除了人與自然對立、對抗的諸因素或可能,破除了囿于認識論哲學或主體哲學的人類中心論,蘊含了一定的生態美學元素,甚至可以說孕育了生態美學的潛在學術生長點。這或可為當下學界盛行的生態美學提供某種歷史的參照和啟示。
第二,蔣孔陽美學在基本建制上本質地瓦解和摒棄了“我思”即“意識的內在性”這一形而上學建制,而這種瓦解和摒棄是由“存在論革命”及其所進行的美學探索來決定的。誠如海德格爾所言:“只要人們從Ego cogito(我思)出發, 便根本無法再來貫穿對象領域;因為根據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據萊布尼茨的單子基本建制) , 它根本沒有某物得以進出的窗戶。就此而言, 我思是一個封閉的區域。”②海德格爾:《晚期海德格爾的三天討論班紀要》,丁耘譯,《哲學譯叢》2001年第3期。進一步,具體到形而上學美學來講,由“意識的內在性”來展開美學探索和建構,本質上鎖閉和封存了面向、介入以及通向鮮活的美學現象、美學現實和美學世界的道路,造成主客二元隔絕和對立,美學探索淪為主觀反思和想象等,從而根本上也就不可能“貫穿對象領域”或“感性領域”,而頗具意味的是,美學的全部秘密卻就蘊藏在這里,即蔣孔陽所說的“審美關系”。如韋爾施在《重構美學》中所提示的,美學要直面和介入現實生活,而且要實質地考慮并囊括現實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非儼然一種學科,即純粹知識反思或范疇建構游戲。③沃爾夫岡·韋爾施:《重構美學》,陸揚、張巖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頁。或許這與美學“貫穿對象性領域”之本質訴求形成了某種層面的應和與契合。這正是蔣孔陽美學何以要擊穿、克服和超越“意識的內在性”的奧秘所在。
第三,在上述兩點基礎上,就要求蔣孔陽美學直接揭示和訴諸人與現實(包括自然)的活潑潑的,而非實在(實體)的、現成的審美關系。④朱立元:《蔣孔陽審美關系說的現代解讀》,《文藝研究》2005年第2期。“實在”、“現成”,本質上是形而上學性質的,而且是形而上學想象和反思現實世界的必然產物,具有封閉性、單質性等特質。因此,這種揭示和訴求,實質是生存論性質的,而且內在鞏固地行進在“生存論路向”之上,故本質上已然突破形而上學美學傳統路數。而且在一定意義上講,這種揭示和訴求,“撩開”了覆蓋在這種關系之上的形而上學面紗,引向、掘開并激活了審美關系諸種復雜歷史、現實條件,復雜面相及其多樣可能性。
上述三個方面共同構成了蔣孔陽美學的基本性質與意義。這是蔣孔陽堅持“以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作為出發點”,并以此為美學研究對象⑤蔣孔陽:《美學新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3頁。周來祥先生在《美學問題論稿》和《論美是和諧》等專著中提出了“審美關系”是美學對象的觀點,雖然蔣先生對此有所繼承,但在基本性質和意義上卻存在本質差異。的根本原委所在。學界某些學者對“審美關系說”之所謂“同義反復”、“自相矛盾”等指責和詰難,我們認為本質上是無視或至少未能充分、徹底參透這一性質和意義,而仍然囿于形而上學那套框架和建制進行批駁和評判的必然結果。在此意義上講,朱立元先生把蔣孔陽美學精辟地稱為“審美關系說”,無疑是深得其精髓的。
下面,我們將站在這一基本性質與意義的高度上來辨析和評判閻國忠先生對蔣孔陽美學的解讀和評價,希冀將其中與此相關涉的問題進一步推向深入。這里,我們主要依據閻先生撰寫的文獻《蔣孔陽的美學——還原為審美現象的美學》、《誰在接著朱光潛講?——“主客觀統一說”的邏輯展開》、《美學為什么要奠立在哲學一元論之上》等,還有就是閻先生與其學生合寫的《美學建構中的嘗試與問題》中所涉及的相關部分。①閻國忠、黃玉安、徐輝等:《美學建構中的嘗試與問題》,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年。閻先生在《美學建構中的嘗試與問題》的“后記”中說,關于蔣孔陽美學這一部分由張玉安負責。
在閻先生撰寫的篇什中,蔣孔陽美學的價值和意義及貢獻獲得了積極肯定,②參見閻國忠:《蔣孔陽的美學——還原為審美現象的美學》,《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肯定并未徹底深達蔣孔陽美學之本質的重要層面,即其唯物史觀這一哲學根基處,從而使蔣孔陽美學的基本性質和意義陷于晦暗不明之中。這種晦暗不明往往造成對蔣孔陽美學理解和闡釋的不徹底和歧義性。第一,閻先生認為,蔣孔陽從馬克思經典文獻中為自己的美學找到并確立了“兩個基本的出發點”,即“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以及“美學革命化”、“審美教育社會功能”等馬克思經典論斷。③閻國忠:《蔣孔陽的美學——還原為審美現象的美學》,《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由此可以發現,閻先生深刻注意到了馬克思經典論斷在蔣孔陽美學中的重要影響以及重要位置,而且《美學建構中的嘗試與問題》把蔣孔陽連同李澤厚、朱光潛一并歸在以“實踐”為基礎概念的美學建構之下等,④閻國忠、徐輝、張玉安等:《美學建構中的嘗試與問題》,第130頁。也佐證了這一點。眾所周知,這些經典論斷與唯物史觀(“實踐唯物主義”)是內在鞏固的、一體的,而非矛盾的、分裂的。也就是說,如前所言蔣孔陽美學建立在唯物史觀之上。但問題是,綜觀閻先生的相關研究,如此這般的馬克思經典論斷之唯物史觀性質和意義,或者說其背后的唯物史觀,以及其對蔣孔陽美學的革命性影響,并未徹底達至實質一貫地、內在鞏固地、本質重要地闡明、展開和貫徹。這種有意無意地懸置和忽視,導致了蔣孔陽美學基本性質和意義得不到應然判定和昭示。
第二,正因對蔣孔陽美學哲學基礎及其革命性新變領會和把握不充分、不徹底,而造成了對“審美關系”的一些認識上的不充分、不徹底。這集中體現在:在閻先生看來,審美關系對蔣孔陽美學而言具有存在著深刻矛盾的雙重含義,即“無自己定性的派生性概念”和“有自己定性的本原性概念”,并認為其精華之處是從“將審美關系當作一種方法論”的后一概念出發而展開的美學探索,擺脫了“二元論困境”。⑤閻國忠:《蔣孔陽的美學——還原為審美現象的美學》,《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大致說來,這仍然囿于形而上學陰影之中,試圖訴諸概念、邏輯、反思的世界來領會和把握審美關系,并將其領會和把握為一種“方法論”,由此而有意無意“漏過”了對其哲學根基處悄然變動和革新的捕捉和透視,而這種捕捉和透視又必將決定性地指向其美學基本性質和意義。事實上,如前所言,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審美關系說”,首先揭示并呈現的是存在論根基處的革命,即作為“感性活動”或“對象性活動”的審美關系,或者說就是“審美活動”,就此而言審美關系不僅與實踐本質相通,而且意味著對“純粹活動”或“自我活動”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央編譯局編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4頁。的擊穿和瓦解,意味著與“我思”根本不同的出發點的決定性奠立。由此而言,審美關系必須且應當首先被本質地領會和把握為“存在論”,而非“方法論”,而且只有如蔣孔陽所言“以人對現實的審美關系作為出發點”,才能真正而有效地擺脫二元對立困境,而不僅限于方法論。②朱立元:《超越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文藝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
第三,正是源于上述理論態度和立場,閻先生認為審美關系的說法混淆了兩種主體和客體,即“介入審美活動前抽象的主體和客體,與介入審美活動后具體的主體和客體”,也即是說,閻先生認為審美關系的說法意味著人與對象天然是審美主體和客體,并且處在審美關系之中,不管是否介入審美活動。③閻國忠:《美學為什么要奠立在哲學一元論之上》,《上海文化》2015年第8期。就此而言,不得不說,這種指責和批評,實質是把審美關系先行地領會和把握為“方法論”,并懸置其哲學根基而將其視為與審美活動截然相對立的、分離的一種抽象的“客觀存在”或“現成者”,由此出發當然就可得出所謂“混淆”之結論。但我們詳細研讀蔣孔陽美學著述之后卻發現并不然,事實是:審美關系既是歷史的、現實的,同時也是生成性的、開放性的,既是人類性的,也是個體性的。④參見蔣孔陽《美學新論》、《美在創造中》等著述,以及朱立元、張玉能等先生關于蔣孔陽美學的系列研究。無疑,這再一次深刻揭示并確證了閻先生何以將審美關系領會和把握為“方法論”了。
特別值得反思的是,閻先生在《誰在接著朱光潛講?》中仍繼續重述與此相近或變異性的論調,斷定蔣孔陽“將美的本質和本原結構歸結為‘審美關系’,學理上與邏輯上還存在著明顯的紕漏”,重要理由之一是在蔣孔陽美學中,至少還存在“通過勞動實踐改造過的自然的美是純然客觀的”這樣一種自相矛盾的狀況。⑤閻國忠:《誰在接著朱光潛講?——“主客統一”說的邏輯展開》,《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11年第1期。在這里,姑且不論“將美的本質和本原結構歸結為‘審美關系’”這一表述和概括是否妥當、真確,是否內在鞏固地揭示和呈現了蔣孔陽美學的基本性質和意義,單就“通過勞動實踐改造過的自然的美是純然客觀的”而言,我們認為建立在唯物史觀這一哲學根基上的蔣孔陽美學,不論從學理還是從邏輯上講都不存在“純然客觀的美”孕育和誕生的可能性。這是由蔣孔陽美學的哲學根基及其基本性質和意義決定的。此外,閻先生還認為,蔣孔陽美學并未真正擺脫實踐美學的“悖論”或“矛盾”,譬如“美是勞動的產物,美的本質是勞動”與“美在創造中,美是多層壘的突創”的矛盾,“因為有了客觀的美,才形成了人與現實的審美關系”與“因為審美關系的存在才造就了美的對象”的矛盾等。⑥閻國忠:《蔣孔陽的美學——還原為審美現象的美學》,《學術月刊》2006年第6期。我們以為這種批評本質上仍然落于形而上學窠臼,是悖逆蔣孔陽美學的基本性質和意義的。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只有真正領會和把握了唯物史觀,并本質一貫地、內在鞏固地領會和把握了建基于唯物史觀之上的蔣孔陽美學之基本性質和意義,才能達成對蔣孔陽美學的本質洞悉和真確闡釋,而不致滑入歧路。
三、一個延續:“實踐存在論美學”
在文獻收集、閱讀和研究過程中筆者注意到,不少關于蔣孔陽美學的解讀、評論、闡釋,以及質疑、指責和批評等,由于自覺或不自覺地囿于形而上學哲學、美學,以及庸俗化馬克思主義等既定框架、觀念、前見及偏見,往往難以徹底、實質、真確地深入其哲學根基,并揭示和把握此根基之于蔣孔陽美學的決定性作用和意義,從而也就難以抵達和透視蔣孔陽美學的真正內核。由此而言,這構成的不是真正的解讀和批判,實質是一種懸置和遮蔽。于是,越是如此,蔣孔陽美學之基本性質和意義就越是晦暗不明。
不過,蔣孔陽美學由于諸種原因雖然遭到誤解和批判,但同時更值得注意的是,學界也對它進行了豐富的、堅實的、建設性的重大闡發和推進。這其中產生過重要影響并具有廣闊發展前景的,當首推“實踐存在論美學”。①“實踐存在論美學”,由以朱立元先生為代表的諸學者提出并進行了詳實的闡發。關于“實踐存在論美學”,以朱立元先生為代表的諸學者與董學文、李志宏等學者展開了較長時間的論爭。“實踐存在論美學”,在根本上講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也是對蔣孔陽美學,特別是其基本性質和意義的本質一貫地、內在鞏固地領會和把握。誠如朱立元先生自己所言,馬克思唯物史觀,以及實踐論與存在論相結合思想,以及蔣孔陽“審美關系說”等,共同構成了“實踐存在論美學”提出的核心根據。②參見朱立元:《簡論實踐存在論美學》,《人文雜志》2006年第3期。由此而言,“實踐存在論美學”既一脈相通地、原則高度地承繼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美學,也本質深刻地拓展和推進了蔣孔陽“審美關系說”。
在此意義上講,一些學者對“實踐存在論美學”的“海德格爾化”、“取消認識論”等指責和非議,③董學文、陳誠等學者指責和批評“實踐存在論美學”把馬克思“海德格爾化”等,李志宏、劉兆武等指責和批評其“取消認識論”等。這一方面新近文章發表在《學習與探索》、《文藝爭鳴》等雜志上。本質上都是難以站住腳的。因為他們根本沒有徹底真確地、本質一貫地、內在鞏固地領會和把握馬克思唯物史觀的革命性及其實踐定向,因而不能真正領會和把握“實踐存在論美學”的哲學根基和原則高度,而實質上仍然限于形而上學框架和建制來加以框定和評價,故而形成的不是客觀“了解之同情”(陳寅恪語)基礎上的真正學術對話和批評,而是未真正切入“實踐存在論美學”思想地基、內核,以及這種思想所面向并通向的鮮活的、豐富的現實感性活動或對象性活動本身的外部(或主觀)批評和反思。由此看來,這無疑是需要我們保持高度警惕和清醒認識,并實質地加以檢討和反思的。
責任編輯:沈潔
*劉陽軍,男,1984年生,貴州銅仁人。復旦大學中文系文藝學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法蘭克福學派文學、美學及文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