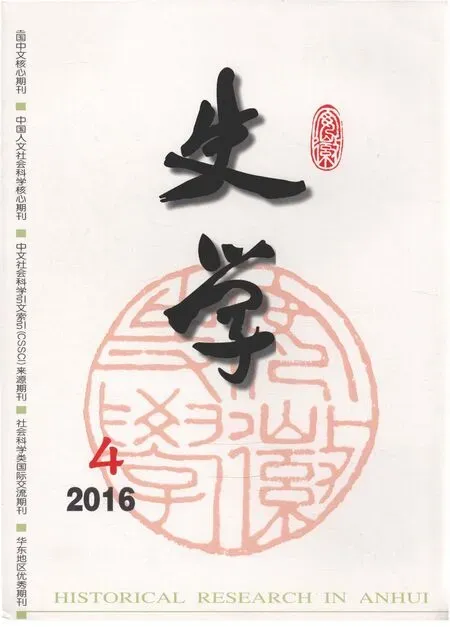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話語體系建構中的“圣人之道”
李 燕
(北京教育學院 教師教育人文學院,北京 100120)
?
由“周孔”而“孔孟”:儒家話語體系建構中的“圣人之道”
李燕
(北京教育學院教師教育人文學院,北京100120)
摘要: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化為“孔孟之道”,是儒家基于特定歷史語境建構話語體系的產物。隨著周、孔形象漸趨圣化,漢唐時人多以周、孔并舉,包含政治教化與人倫道德兩方面內涵的“周孔之道”得以生成。繼韓愈“道統論”之后,宋儒建構“性與天道”理論和道統譜系,“孔孟之道”逐漸成為儒學的代名詞。統治者藉由教育、祭祀等參與此過程,也彰顯出道統與治統的復雜關聯。
關鍵詞:周孔之道;孔孟之道;圣人;道統;治統
今人言及“儒學”,多以“孔孟之道”代之。而事實上,正如錢穆所言:“自宋以下,始以孔孟并稱,與漢唐儒之并稱周公孔子者,大異其趣。此乃中國儒學傳統及整個學術思想史上一絕大轉變。”*錢穆:《朱子學提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12頁。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人們對于儒家思想更普遍的理解乃是“周孔之道”。“孔孟”取“周孔”而代之,“周孔之道”演變為“孔孟之道”,實與儒家話語體系的建構密切相關。而歷代統治者亦藉由教育、祭祀等參與其間,彰顯出道統與治統在此問題上的錯綜復雜關系*“道統”在廣義上指整個中華文化的大傳統,狹義上則指儒學的傳承統緒,本文所言是就其狹義層面而言。“治統”又稱“政統”,多指帝王政權或政治形態發展的統緒。此外又有學者提及“學統”與“道統”,前者主要是就學術的傳承統緒而言,后者則特指居于正統地位的某一學說的傳承統緒。參見潘志峰:《近年來關于“道統”問題的研究綜述》,《廣西社會科學》2008年第11期。。當然,上述結論的獲得,必須建立在對歷史深刻省察的基礎之上。
一、周、孔圣化與“周孔之道”的生成
在中國學術思想史上,周公、孔子備受矚目。孔子弟子稱其為“圣人”,繼孟子提出“周公、仲尼之道”*(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1,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93頁。后,隋朝王通宣稱:“卓哉,周孔之道!”*張沛:《中說校注》卷1,中華書局2013年版,第13頁。然而孔子卻稱:“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頁。然則周、孔是如何圣化,而“周孔之道”又是如何生成的?有必要從歷史的角度進行梳理。
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曾先后輔佐文、武、成王,為鞏固統治和創建禮樂制度立下卓越功績。在他卒后,成王充分肯定其功,并特準魯國行天子禮樂以褒獎其德。《左傳》昭公二年,晉大夫韓宣子聘魯,見到《易象》與《魯春秋》,也感嘆魯國保存周禮完備,認為從中可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第2版,第1226—1227頁。。春秋中后期以來,王權衰落,禮崩樂壞,甚至出現“八佾舞于庭”的亂象*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頁。。孔子洞見周公形象對于恢復禮制的重要意義,因而推崇“周公之才之美”*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頁。,晚年更感慨:“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頁。在他眼中,周公實為王道教化的象征。因此,周公形象漸趨圣化。至戰國時期,孟子明確稱周公為“古圣人”“古之君子”*(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9,第292、295頁。,認為他具有既仁且智、不懼有過而又善于改過的德行。
與之相應,孔子的形象也在悄然變化。孔子本不以“圣人”自居,他自認只是好學多能的學者和不受重用的政治家。甚至當與弟子走散而被形容為“喪家之犬”時,他也是欣然接受*《史記》卷47《孔子世家》,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2328頁。。然而子貢卻稱頌他“天縱之將圣,又多能也”*楊樹達:《論語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5、61、196、155、217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6,第213、217頁。;宰我也認為,夫子“賢于堯舜遠矣”*(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6,第213、217頁。。故而,仁且智、賢而多能成為孔子之“圣”的主要特征。
此后,思孟學派從道、德、性等方面對“圣”“圣人”進行論證*郭店楚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世紀中期至公元前3世紀初,對于墓中竹簡《五行》《成之聞之》,學界多認為屬子思一系作品。王永平:《郭店楚簡研究綜述》,《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第3期;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文物天地》1998年第2期。本文所引簡文俱以通行字替代,遇有爭議,則酌情改定并擇要注明。,從而為周、孔并舉打通了關節。郭店楚簡《五行》篇曰:“德之行五,和謂之德,四行和謂之善。善,人道也。德,天道也……聞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也。”*荊門市博物館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頁。仁、義、禮、智、圣五種德行的和諧稱為“德”,是天道;前四行和諧稱為善,屬于人道。君子之道即人道,聽聞它并且知曉其何以為君子之道的是圣,圣人知曉天道,意即圣人溝通天人之道。《成之聞之》引古君子之言,認為天德是圣人內化天道、天常而形成的圣人之德,圣人之性發揮博大時,圣人便不是中人所能追隨效仿的了*《郭店楚墓竹簡》,第168頁。此處句讀及釋義參李學勤先生說,詳見《試說郭店簡〈成之聞之〉兩章》,《煙臺大學學報》2000年第4期。。這種鼓勵中人通過自覺實踐而盡性的思想傾向,大大淡化了圣人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神秘性。
在此前提下,孟子稱“圣人”為“百世之師”“人倫之至”*(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28、14,第976、490頁。,他稱贊楚人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1,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93頁。,又說:“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3,第459頁。。夷夏之辨在于禮樂制度,周、孔以文治武功維護社會秩序,因此這里的“周公、仲尼之道”實謂禮樂教化之道。荀子則將圣人與大儒相結合,認為周公輔佐成王安定天下,“非圣人莫之能為”,此即“大儒之效”*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840頁。;孔子“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并”*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840頁。。殆至兩漢,周、孔并舉漸為人所接受,如《漢書》記班嗣語云:“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漢書》卷100上《敘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205—4206頁。《三國志》亦載崔琰之言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三國志》卷12《魏書》,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368頁。
由此可見,“周孔之道”實與周、孔形象的圣化密切相關。在總結三代文化特別是西周禮樂傳統的基礎上,孔子承揚周公“以德配天”的思想,形成以仁釋禮的王道教化思想。孔門后學繼承其注重德、能的價值傾向,兼顧“圣人”的外在事功與內在修養,提出包含政治教化與人倫道德兩方面內涵的“周孔之道”。但孔子畢竟有德無位,出于儒家話語建構的需要,漢代以來的學者在闡揚“周孔之道”時,多強調它以六藝為載體、興禮樂而備王道的意蘊,如司馬遷以紹繼“周孔之道”為己任,將《禮》《樂》置于《史記》“八書”之首,在《孔子世家》中更直言孔子追修經術以備王道,“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史記》卷47《孔子世家》,第2356頁。
二、孟子“升格”與“孔孟之道”的提出
東漢明帝永平二年(59年),“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圣師周公、孔子。”*《后漢書》卷90《禮儀志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3108頁。周、孔被納入國家教化系統,實與古代興學設教傳統有關。《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圣、先師。”鄭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孔疏:“以周公、孔子皆為先圣;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94頁。可見,釋奠禮的對象最初并無一定之規。然而唐代以來,“周、孔何者為圣”這一問題卻屢起爭議。隨著孟子地位的躋升,“周孔之道”漸被“孔孟之道”所取代。
唐武德二年(619年),高祖詔令有司為“二圣”在國子學各立廟一所,“四時致祭”;武德七年(624年),又以周公為先圣、孔子配享。然而,貞觀二年(628年),左仆射房玄齡、博士朱子奢據史提出,釋奠禮應以孔子為先圣、顏回為先師*武德二年事見《舊唐書》卷189上《儒學列傳》,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4940頁;武德七年、貞觀二年事俱見《新唐書》卷15《禮樂志》,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373頁。。太宗接受了這一建議。高宗永徽年間一度又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但顯慶二年(657年)七月,禮部尚書許敬宗等人奏請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圣*詳見《舊唐書》卷24《禮儀志》,第918頁。此條《通典·孔子祠》亦作“禮部尚書許敬宗等奏曰”,《唐會要·褒崇先圣》《新唐書·禮樂志五》《冊府元龜·奏議三》則以之為太尉長孫無忌等言,待考。。此后,周、孔分祀,國學專以“先圣”祀孔子遂成定制。
此時,孟子地位并無特別變化。事實上,孟子與孔子在最初不僅被分而視之,地位也有云泥之別。荀子曾以孟子、子思聯稱而對其五行說大加批駁。《史記》中,孔子入“世家”,而孟、荀并入“列傳”。直至漢昭帝時,孟子的名字才與孔子聯系起來*《鹽鐵論·相刺》載大夫論曰:“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軻見賤于諸侯也。”王利器:《鹽鐵論校注》卷5,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255頁。。此后,儒者多以孔、孟聯稱,如東漢王充曰:“或以賢圣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圣人,孟子賢者。”*(漢)王充著、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卷1《逢遇篇》《命祿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14頁。細繹其論不難看出,在王充看來,圣、賢還是存在區別的,具體來說,“圣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圣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漢)王充著,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卷26《實知篇》,第522頁。也就是,圣賢之別并非性質的根本不同,而僅在于才智、“入道”程度等方面的差異。馬融《長笛賦》“溫直擾毅,孔孟之方”*(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卷18《長笛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817頁。,則徑以孔孟并提而贊其溫和正直、柔順堅毅的品行。
唐代宗寶應二年(763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孟子》入“兼經”,事雖不成,而啟《孟子》由“子”升“經”之先聲*事見《唐會要》卷76,第1396頁。漢文帝時,《孟子》曾被列為傳記博士,后被罷。開元年間,洋州刺史趙匡上《舉選議》,后附《舉人體例》請以《孟子》入策問范圍,唯趙氏以《孟子》入諸子之列。參見(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第13頁;(唐)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卷17,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422頁。。此后,韓愈在《原道》中以仁和義規定道、德,認為儒家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至孔子、孟子后失傳,并提出:“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唐)韓愈著,劉真倫、岳珍校注:《韓愈文集彙校箋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4頁。即自周公以上,道統的擔當者是君,所以通過事功來推行;周公以下,道統的擔當者是臣,所以通過學說來弘揚。韓愈此論正式揭開了“孟子升格運動”的大幕*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9頁。,使孔、孟由“道統”而相關聯。唐懿宗咸通四年(863年),皮日休再上《請〈孟子〉為學科書》,以《孟子》雖屬子學而不偏離“圣人之道”,其文粲若經傳,實為“圣人之微旨”*(唐)皮日休著,蕭滌非、鄭慶篤整理:《皮子文藪》卷9,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頁。,請求將其列入明經科目。至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孟子》終入“兼經”,后又于徽宗宣和年間被補刻入“石經”*熙寧四年事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20,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5334頁。關于《孟子》入“石經”問題,參見舒大剛:《“蜀石經”與〈十三經〉的結集》,《周易研究》2007年第6期。,它在經部中的地位也更加鞏固。與此同時,孟子也屢獲詔封,元豐六年(1083年)首次被封為鄒國公,次年配享孔廟*《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40、345,第8186、8291頁。,元文宗至順元年(1330年)又獲封“鄒國亞圣公”*《元史》卷76《祭祀志》,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893頁。,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被封為“亞圣”*《明史》卷50《禮志》,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299頁。。至此,孟子的地位與影響遠超顏回、曾子、子思,得與孔子聯稱。
從文獻來看,孔、孟聯稱的說法至遲在南朝就已出現。如永明末年,齊世祖欲北伐,王融上疏稱:“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南齊書》卷47《王融列傳》,中華書局1972年版,第820頁。南宋以來,“孔孟之道”這一術語漸趨常見。如宋高宗紹興五年(1135年),胡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后知其可學而至。”*《宋史》卷435《儒林列傳》,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2914頁。朱熹論《論語·子張篇》云:“孔孟之道規模大,若有理會得者,其致治又當如何!”*(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卷49,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200頁。
應當指出,作為儒家話語體系中的歷史范疇,“孔孟之道”的內涵與外延是不斷豐富拓展的,它在狹義上特指孔、孟二人的思想,在廣義上則泛指以孔孟“仁學”為核心、強調“親親尊尊”的儒家思想學說或主流意識形態。孟子曾學于子思門人,他在繼承孔子思想的基礎上提出“四端”說,以性善論為邏輯起點,將仁心落實到仁政,并提倡養氣尚志。宋儒著眼于孔、孟思想的一致性與相繼性,通過仁義功利、心性理氣之辨闡發“圣人之道”,朱熹更以“四書”為載體,圍繞“中庸之道”對心性論、宇宙論及道統論詳加闡發,從而建構起儒家“性與天道”理論和道統譜系。經此一變,“孔孟之道”遂逐漸成為儒學的代名詞。
三、道統、治統與“圣人之道”的衍化
從周、孔并舉到孔、孟聯稱,從“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實為儒家爭取參與社會話語權的需要。通過塑造“圣人”形象、選擇經典文本并維護其權威,歷代儒者致力于構建自身話語體系,而統治者亦得以參與其中。在道統與治統的相互影響下,儒家“圣人之道”不斷衍化并被表達出來。
自先秦時期,儒家面對社會失序即表現出強烈的弘道意識。他們意識到六經等經典文本的重要性,并通過“圣人”這一主體形象,致力于論證“圣人”與“道”“經”的內在貫通。不惟儒家,為爭取重建社會秩序的話語權,其余諸子也紛紛提出各自的“圣人”觀念,尊稱本派研習典籍為“經”,并對其宗師多加推崇,從而推動了“圣人崇拜思潮”的發生。因此,對于孔門后學并舉周、孔的做法,他們并不認同。例如,公孟子提出,孔子博學多識、明察禮樂,符合上圣標準時,墨子明確表示反對*(清)孫詒讓撰、孫啟治點校:《墨子間詁》,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454頁。。在墨子的認知中,圣人應當兼具才智、德行,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包括有名有位者(即三代圣王)和有名無位者兩類。因此,他雖然視周公為“圣人”,卻不贊成孔子之“圣”。
當然,由于時勢變遷與認知差異,儒家對于“圣人之道”的詮釋也多有變動與反復。例如,孔門后學曾提出“禪而不傳”的“唐虞之道”,主張“愛親尊賢”,認為這是“圣之盛”“仁之至”*《郭店楚墓竹簡》,第157頁。。但對處于劇烈轉型期的社會而言,這一不合時宜的理想藍圖不可能獲得當政者的青睞,注定無法實現。韓愈雖以孔、孟入儒家之道統,而其關注重心已由禮樂轉向仁義。當“孔孟之道”漸為人所共識后,明清時期又有儒者倡言回歸“周孔”。如黃道周曰:“凡學問自羲、文、周、孔而外,皆無復意味。”*(明)黃道周撰、(清)黃壽祺整理:《明漳浦黃忠端公全集》卷30,清道光十年刊本。章學誠更進一步指出,孔子有德無位,學而盡周公之道以明其教,因此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清)章學誠著、葉瑛校注:《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143頁。,體現出對宋儒道統觀的反動。
不僅如此,由科舉考試與釋奠禮的發展演變來看,在儒家構建“圣人之道”話語體系的過程中,道統與治統也呈現出既緊密結合又彼此抗衡的復雜關系。一方面,正如《禮記·中庸》所言:“雖有其位,茍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茍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53,第896頁。儒家以“治道合一”為政治理想,孔子深以為然,對于自己以布衣垂教而修《春秋》之舉,自謂后世“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3、16,第452、546頁。自孔子開“治道分離”之先河后,歷代儒者深入思考道統、治統的關系,并力圖通過道統所賦予的話語權對治統施加影響。孟子主張君臣權利與義務對等,聲稱“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清)焦循撰、沈文倬點校:《孟子正義》卷13、16,第452、546頁。;荀子則提出“從道不從君”的命題*王天海校釋:《荀子校釋》,第573頁。,強調道統對于治統的約束。明代呂坤認為,天地間以“理”與“勢”地位最高,兩相比較,象征圣人之權的“理”又高于象征帝王之權的“勢”,帝王無圣人之“理”,則其權“有時而屈”,“勢”賴于“理”而存亡*(明)呂坤:《呻吟語》卷1,王國軒、王秀梅整理:《呂坤全集》,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646頁。。對于道統維系治統的重要意義,統治者多有認同,清康熙帝即說:“萬世道統之傳,即萬世治統之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初集》卷1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頁。漢代以來官方尊儒崇經的種種舉措也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然而,統治者又往往基于現實政治的考量,藉由教育、祭祀等干預儒家話語體系的建構。古代尊儒崇經政治文化傳統的形成,固然與儒者不斷強化的道統觀念及其現實努力有關,而從實踐層面看,實為統治者與儒家通過政治對話達成一致的結果。無論是儒學官學地位、儒家經典權威、儒者神圣形象的確立,還是孔廟在國子學及州、縣學普遍設立,抑或是釋奠禮作為天下通祀制度化,莫不最終取決于統治者的決策。道統的權威性實有賴于治統的支持與認可,這在周、孔“先圣”地位之爭中已表露無疑。而諸如明嘉靖九年(1530年)又啟孔廟改制,謚孔子為“至圣先師”而不稱王;毀塑像而用木主,去章服,祭減殺;更定從祀制,改“大成殿”為“孔子廟”,內增“啟圣祠”等舉動,更明顯是統治者對“制度化”道統的挑釁。對此學者已有詳論,茲不贅述*參見黃進興:《優入圣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07—137頁。。
要之,由“周孔”而“孔孟”,由“周孔之道”到“孔孟之道”,歷代儒者對自身話語體系不斷進行整合與加工,而統治者亦參與其中,體現出道統與治統的互動。經由周、孔形象的圣化,周、孔由分說到并舉,“周孔之道”得以生成。而隨著周、孔由并舉到分祀,儒家“道統論”日益豐富與發展,孟子地位不斷躋升,“孔孟之道”也終于取“周孔之道”而代之。
責任編輯:郝紅暖
中圖分類號:K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16)04-0053-04
作者簡介:李燕(1982- ) ,女,山東濟南人,北京教育學院教師教育人文學院講師,歷史學博士。
From the Duke of Zhou-Confucius to Confucius-Mencius:Confucianism Discourse System Construction of the Doctrine of Sage
LI Yan
(Faculty of Education for Teacher of Liberal Arts,Beij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Beijing 100120,China)
Abstract:The term of “Confucius-Mencius” had eventually taken “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place and the doctrine of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 had developed into Confucius-Mencius in Chinese traditional ideology history.It was the result of Confucianism constructing their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It had been affected by rulers’system of education and sacrifice,which highligh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ule and Confucian orthodoxy.
Key words:doctrine of the Duke of Zhou and Confucius;doctrine of Confucius-Mencius;sage;Confucian orthodoxy;Rule orthodo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