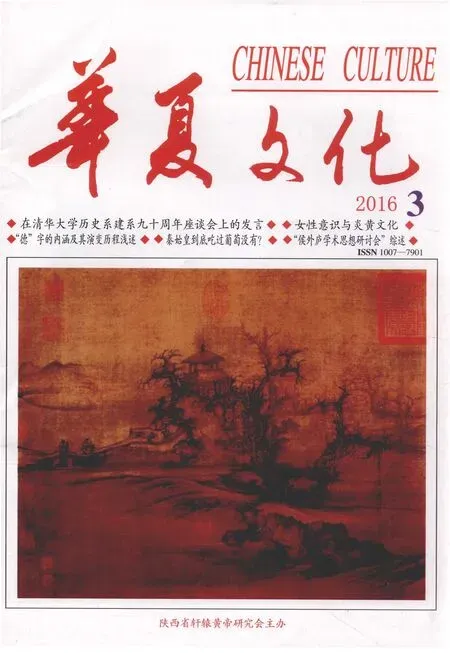黃帝與古代中國的政治文明
□ 李禹階
黃帝與古代中國的政治文明
□李禹階
黃帝作為華夏民族“圣王同祖”“華夷共祖”的理想型人物,是由古代中國文明進程的特征所決定的。以黃帝起始的中原地區部落聯盟制度中以“禮”為標志的政治文化與世俗性特征,體現了華夏民族的社會生活與政治文化的鮮明特點。人們往往將黃帝及其部族所開創的政治文明及世俗化禮儀制度作為華夏民族文化與國家、文化認同的標志,而將黃帝作為華夏民族始祖及政治文明的開創者。
一、文明與國家
文明與國家是兩個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的概念。文明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社會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它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社會在物質與精神創造上的進步狀態。國家則是指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它是在社會階級分層基礎上所形成的具有政治自治權和管理權的特定范圍內的區域。一般而言,文明又具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從廣義看,文明標志著人類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發展程度;而從狹義看,文明又與國家起源的諸要素(城市、文字、宗教、生產工具等)緊密結合,是國家產生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基礎。但是,一定階段的文明進程是國家賴以產生的基礎,而國家是在一定的文明水平上出現的。因此,如果我們綜合考察世界上的文明古國,可以看到,國家并不是與文明同時產生的,它是文明諸要素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結果,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標志。從人類社會普遍的史前歷史看,在一些大洲及地區,當國家還沒有出現時,就產生了較高程度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國家的出現,則標志了這一地區、民族的社會與政治發展的水平及階段性。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國如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埃及、古代中國均是如此。例如在我國,人們普遍認為古代中國國家是從夏開始形成。但是在夏建立國家之前,我國黃河流域與長江流域,以及北方地區的內蒙古、東北、西南及珠江流域等,都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發展。在一些地區,這種發展甚至有較高的水平。地中海文明亦是如此。早在公元前2000年,便出現了愛琴文明,其后又產生了輝煌的克里特與邁錫尼文明。其初期國家即是在這種燦爛文明基礎上產生的。尤其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典希臘城邦國家等雖然是鐵器時代的產物,但是在它之前,古希臘半島已經走過了漫長的文明旅程。所以,從廣義上看,在國家之前,人類文明已經開始起步。正是在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上,在有著較多可支配的剩余產品及財富分配基礎上,才能夠形成社會的分層,政治的等級,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性國家。
國家不僅是文明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且也是在文明諸要素例如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的合力作用下形成的。正是這些要素的聚合,才能使社會存在階級、階層的分化。這種社會階級、階層的分化,在各個古文明形態中各有不同。但是有一點是共同的,即它都是在諸多有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乃至行政、管理要素的集聚和合力中蛻變而出的。而這些不同的要素所產生的不同合力及其結果,又構成不同的文明進程與國家起源之路。它由此使世界各區域文化呈現千姿百態的特色。因此,在原始社會漫長漸進過程中,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各種社會要素的集聚而形成的合力,既奠定了早期國家產生的基礎,又規定了早期國家不同的發展方向。世界幾大文明古國以及其后的各區域國家的產生,大致即沿著這一規定性而起源、發展、壯大,并且有著自己鮮明的發展特點。在研究中國古代文明進程與早期國家起源問題上,我們既需要關注文明與國家的關系,又必須注重古代華夏大地上文明進程中產生國家的諸種條件與要素。
二、中國史前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古代中國文明進程與早期國家的產生也遵循了這一規律。從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考古材料來看,在新石器時代,我國的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北方的內蒙古、東北地區,南方的珠江流域,以及遠在西南部的四川盆地與云貴高原,都形成過方式各異、或高或低、程度不同的文明形態。對于大量遺址的發掘資料表明,這些地區文明的產生,并不是某一核心地區文明單純的衍生或其擴展的產物,而是在各個不同地區自發產生、形成,并帶有自己鮮明區域性文化特點的形態。因此,在距今約4000—5000年前后的中國大地上,各個區域性文明呈現百花齊放的狀態。例如其時除了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文化以外,東北地區的紅山文化,長江中下游的良渚文化等,都具有相當高的發展水平。
對于史前中國文明起源與發展問題,早在20世紀20-70年代,就有過中國文明西來說、中西文明對立說以及文明起源一元論等不同觀念。20世紀80年代以后,隨著大量考古新材料的出現,我國考古學界多數學者根據各個地域不同的新材料而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說。例如蘇秉琦先生的六大區域說,佟柱臣先生的“三個接觸地帶”理論,石興邦先生主張的以西北腹地半坡系統和以東南沿海的青蓮崗系統為代表的兩大集團系統說,嚴文明先生的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江浙文化區、燕遼文化區和甘青文化區等幾大文化起源區論。這些先生的認識不論有怎樣的差異,但基本點是一致的,即“不同地區的文化,都特征明確,源遠流長,但彼此的淵源、特征、發展道路存在差異,發展水平不平衡,階段性也不盡相同”(蘇秉琦語) 。
從這個意義上說,古代中國文明的發展是多元的。在早期華夏大地上文明發展的進程中,是沒有所謂核心地域或者由一地而衍生、擴展開來的文明起源一元論。這種史前中國文明的發展具有的多元狀態,是目前考古學界對于古代中國文明發展的基本判斷。
這種多元性不僅指地域發展的不同,亦指各個地域在其文化發展的階段性與高低程度上。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大地上一些地區的文化形態已經呈現高低不一的發展水平,例如當時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晚期等。相對而言,地處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以及東北的紅山文化等,在當時已具有較高的物質與精神文化,并且其發展水平已在中原地區之上。近日考古學者在良渚文化遺址發現距今已經有4700至5100年的古城外圍水利系統,該水利系統位于良渚古城的北面和西面,共由11條堤壩組成,這些堤壩根據形態和位置的不同可分為長堤和連接兩山的短壩,其中短壩又可分為建于山谷的高壩和連接平原孤丘的低壩。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最早的水壩,比傳說中的“大禹治水”還要早1000年。據報道:“該水利系統的確認證實良渚古城具有完整的都城結構,由內而外依次為宮城、王城、外郭城和外圍水利系統,其價值可與同時期的其他世界文明媲美。”良渚水利工程的規劃視野之闊、技術水平之高、動員能力之強令人刮目相看。同時,重要的是,根據考古資料看,在史前中國各種文化類型中,不同的社會發展形態亦是不一樣的。這些史前社會發展形態,根據其神權與王權的比重、內涵的差異,又具有不同的發展模式。這些模式大致可以分為三種,即以陶寺類型龍山文化為代表的以王權形態及崇尚軍權的政治威權模式;以東北紅山文化和長江下游的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為代表的以宗教形態為主的神權、祭司威權模式;以大汶口文化晚期、屈家嶺文化等為代表的夾雜政治威權與神權、祭司威權的混合模式。在早期文明中,由于原始宗教神權與酋長行政權力往往混合在一起,而形成社會發展的諸要素。因此這些模式的劃分并非絕對的,而僅僅是以其中某一占主導地位,并成為其核心要素作為根據的。李伯謙先生曾說到在陶寺文化時期,當時中國大地上出現了兩種不同性質的社會發展模式,這就是以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為代表的具有宗教神學特征的神權模式,以及以陶寺文化為代表的軍事與王權模式。李先生所說應該就是指這幾種不同的社會發展模式,其說應是具有合理性的。
所以,從中國古代文明起源看,由于其孳生的多地域性、文化形態的多樣性、社會發展的相異性,使中國文明起源既不存在一個核心區域,也不存在由某一區域向其他區域文明的衍生、擴展過程。但是我們也不能不承認,這些地區文化也在其發展進程中相互影響、相互融合,并由此促進各區域文化的不斷發展。正是這種文明發展的多樣性、融合性特點,才使我國史前文化形態豐富多樣,百花爭艷。中國史前文化發展,既是在各個區系中獨立發展起來,又是在各區系的獨立發展中通過相互影響、相互融合而不斷進步提高的。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不論是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是我們的母親河;不論我國東、西、南、北各區域,都是我國史前文明發展的生長點。
三、黃帝與史前中原政治文明的發展
史前中國東、西、南、北各區域文明發展樣式盡管是多樣、多元的,但是它們仍具有一些共同特點:
1. 自生性與融合性。這些文化并非由某一個文化形態孳生出來,都是在各個區系中自己獨立發展、成長。同時在成長過程中與其他地區有著或多或少的相互交流、滲透。因此,其基礎是獨立的、多點的,但是又有著一些共同特點。
2. 以原始農業為主,并且處于極低的生產力水平上。在我國史前社會中,各個地域文化主要是以原始農業為主兼采集、漁獵的生產、生活方式,同時由于它們均處于木石器工具時代,其生產力極其低下,剩余產品也極其稀少。它與世界其他古老文明,尤其是和鐵器時代進入國家階段的古典希臘文明有著十分重要的區別。
3. 都有著較為強大的社會動員與管理能力。
大約距今5000年—4000年左右,還處于木石器工具時代的幾個重要區域文明,出現了較大規模的城市遺址、大型水壩、大型祭壇、大型墓地,以及精美器具等物質產品。尤其是像紅山文化的大型祭壇及其精美玉器,以及在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宮城、王城、外郭城和能夠與同時期其他世界文明媲美的大型外圍水利系統等。這些大型建筑以及精美器物的生產,不僅需要較多的人力、物力,而且也需要專門的分工。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在這個社會中,已經具備較大規模的對于周圍氏族、部落人口的動員與聚合能力,通過這種動員來從事大型的宗教祭祀或政治、軍事活動。同時,它也反映出這個社會已經具有與動員能力相適應的專門的組織者以及較高的組織、管理水平。
4. 有著一定的社會階層分層。從這些文化形態看,大型的城墻遺址、祭祀建筑、眾多精致禮器及祭祀物品,說明社會已經具有了較為清晰的社會分層,以及與其動員、管理能力相適應的明確的社會分工,包括統治者及有著一定知識水平的社會人群,如專門的祭司等群體的出現。例如,在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中,玉器呈現系統化和禮儀化規模,其墓葬的大小形制及隨葬品的不同,反映社會等級分化日益明顯,階層分化日益矚目。而在陶寺為代表的史前文化中,已經出現了大型的城市、城墻、宮廷遺址,以及代表政治等級和權力的諸多禮器及眾多軍事用途的器具等。它說明當時的政權管理體制已經出現,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社會分工。正是這些社會分工及社會管理力量說明社會的等級分層達到一個較高程度。
但是,在史前華夏大地上諸多文明即將進入國家的前夜,卻出現了一個值得十分關注的現象,即以紅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等為代表的,以神權、祭祀威權模式為主的區域文化突然衰弱下去,而以陶寺龍山文化為主的政治威權模式一枝獨秀,成為史前中國文化發展的主流。正是這不同凡響的一起一落,使古代中國文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它使中原地區的文化形態(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文化)保存下來,并成為古代中國史前文明發展的主流。
目前關于紅山文化、良渚文化的衰微,學術界有著種種看法與認識。例如天災論、外敵入侵論、宗教致使人們生產、生活資料不足論等。這些問題尚需要進行進一步探討與研究。但是有一點需要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在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木石器時代,集中這么大的人力、物力去從事浩大的工程,與當時的經濟條件是有著很大差異的,也是當時社會產品所很難承擔的。它既說明當時文化的發展已經超過我們的想象限度,也說明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道路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比較,確實有著重要的區別。
嚴格地說,當時的中原文化在物質與精神發展上并沒有高于其他重要史前文化的水平。它的異軍突起,最為重要的原因在于在周邊文化紛紛凋零后,而展現出其獨具特征的一面。即一方面,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在其物質與精神文化的發展程度上,具有耀眼的閃光點。它的城市發展、社會生活方式的進步,是當時這一區域范圍內文明發展的亮點。另一方面,則是以該區域的龍山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顯現出其獨具的特征,這就是它的政治文化及社會管理方式的發展,以及相關聯的對于其時社會組織的有效整合與動員,可能是適應了當時生產力低下的該地區史前農業社會的情況。至于其具體的一些問題,還需要經過進一步深入研究。但是,不論怎樣,主要分布在豫西、豫北和豫東一帶的龍山文化,發展為中原地區中國文明初期的青銅文化是無疑義的,并且在該地區產生出下承夏、商、周三代的中國古代國家起源的社會組織模式,亦是無疑義的。這樣,地處中原的龍山文化在史前中國面臨國家產生以前的黎明階段,就成為中國文明進程的主流以及早期國家起源的源頭。它作為中國神話與傳說時代三皇五帝的重要活動范圍以及社會組織的早期模式,奠定了古代中國的基本版圖及政治文明的模式。
目前從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來看,地處中原的龍山文化之所以能夠延續下來并開創古代中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模式,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著現實依據的。這個時代,正是史前先民大遷徙、大融合的時期,而這種遷徙、融合是在激烈的戰爭以及部落的聚合過程中實現的。史前中國的許多神話傳說,例如炎黃之戰,黃帝與蚩尤的戰爭,黃炎部族的東漸,東夷族的西向擴張,苗蠻部落的北上,使中原成為各氏族、部落血緣融合的漩渦。《尚書》中《堯典》、《舜典》稱堯、舜、禹時曾“流共工于幽州,放
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分北三苗”“黜陟幽明”。所謂流、放、竄、殛、分、黜陟,實際上是通過暴力方式處置戰敗部落,也是當時戰敗氏族集群的境況的寫照。現在尚存的史前傳說帝王系統中混淆不清的數十個“帝”“王”,當是在中原大戰中曾一度處于優勢的各血緣氏族、部落群體的首領。中國史前三皇五帝的傳說,本質上是部落酋長個人權威上升的歷史性再現。在這種口碑化的歷史中,黃帝是70余戰保持不敗的“戰神”,炎帝、太皞、少皞、顓頊、共工、堯、舜、禹都有轟轟烈烈的戰績。即使像共工這種失敗的英雄,也有“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的神力。正是在戰爭中,公共權力發展起來。古史有“黃帝四面”之說,說明至少在5000年前酋長的權威及手握的公共權力就已經很大了。1973年在長沙馬王堆二號漢墓中出土戰國佚書4種,其中《十六經·立命》有以“黃帝為天下宗”的說法。“昔者黃宗(帝)質始好信,作自為象,方四面,傅一心。四達自中,前參后參,左參右參,踐五(位)履參,是以能為天下宗。”黃宗,即黃帝。從這段傳說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黃帝時代仍然還保留著濃厚的原始民主制遺風,凡有所為,須征求上下左右的意見;另一方面,這種民主正在朝著它的相反方向發展,個人權威開始上升,而像黃帝這樣的首領的威信則達到為“天下宗”的地步。
目前我們在黃河中下游地區所發掘的史前聚落遺址,都特別鮮明地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戰爭特征,以及在戰爭、遷徙中部落的聚合、分層與發展。正是在激烈的部族戰爭中,這一崇尚軍事與王權,并且在原始農業生產力十分低下的條件下崇尚務實的部落社會組織才能迅速發展起來,并直接導致其組織的精細化與等級化。目前我們從《尚書》等文獻及考古材料中所能夠看到的官僚階層、刑法、專業祭司等的出現,大都與中原地區三皇五帝并直承堯、舜、禹的傳說有關。
因此,中原地區部落文化成為古代中國文明進程與國家起源的一個核心區域文化。而這種核心區域文化則是以崇尚務實與王權的政治文明為基礎的。這種文化模式加快了當時該地區社會組織的分層化與行政化,大大縮短了史前部落及部落聯盟向中國古代國家發展的進程。由于國家起源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絕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中國古代國家的出現,實際上是由黃帝至堯、舜而夏禹建立夏王朝的一個漫長而又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實際上已經被秦漢時人所看到。早在先秦諸子百家中,就有關于黃帝等三皇五帝的傳說。司馬遷的《史記》正式列了《五帝本紀》,作為夏以前中國政治進程的歷史。漢以后,其傳說越益發展。20世紀初期的疑古派曾經對于三皇五帝的傳說加以懷疑、抨擊。但是考古材料證明,早在夏以前,中原大地上已經有著相當發達的政治與文化制度,以及相關物質及精神文化的顯現。因此,以五帝——三王的帝王世系為代表的中國文明演變體系,以及以五帝之首的黃帝作為華夏政治文明起源的代表和華夏民族始祖的代表面目出現,是具有一定歷史真實性的。它反映了人們對當時歷史的一種記憶,以及人們對當時中原地區部落聚合的核心部落及其首領炎、黃的崇拜情結。正是這種崇拜情結使炎、黃,尤其是黃帝成為了我國古代國家起源的偶像,民族緣起的始祖。
四、禮與中國史前政治文化
在中國古代文獻記載中,自五帝后,史前中國便走上了一條與其他文明古國都具有相當差異性的發展道路,這就是世俗化的軍事性部落聯盟以及與此相關的政治、行政分層組織,而非宗教性的祭祀威權的部落聯盟占據了歷史發展的主流地位,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模式而開始一路走下去。這種世俗化的軍事性部落聯盟的行政規則,并不是完全脫離宗教性的信仰及其禮儀,反而是以世俗性王權為中心,對原始宗教進行了改造,將原始宗教與世俗化的分層制度、部落血緣體制相結合,并且以這種血緣和政治等級制的融合為基礎,建立了一套中國最早的禮制。
早在距今5000年左右,史前中國大地上的各個文化遺址就出現了大量禮器。而在龍山文化時期,中原地區也出現了大量禮器。這些禮器既包括祭祀用的器物,也包括區別貴賤等級的社會生活的各種禮儀性用品。例如在陶寺墓葬中,處在塔尖位置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致,已經有鼉鼓、特磬等重要禮器,推測墓主應是掌握祭祀和軍事大權的部落首領人物。這些原始宗教與世俗化政治等級,以及部落血緣制相結合的體制,構成了最早的宗法血緣禮儀制度。
研究中國歷史,都知道早期華夏國家、民族之間的區別,最重要的是文化認同而非血緣認同。中國文化的傳承,時間越久,文化就越是作為其核心因素。尤其到了春秋時期,當時的華、夷之別,既不是純粹的民族血緣性,也不是諸侯邦國的政治向背,而是看其是否遵循華夏禮儀原則,即“習夏禮而夏族,習夷俗則為夷狄”。而華夏民族這一傳統,經春秋至秦漢,則越演越烈。在這種民族的文化識別與認同中,華夏之“禮”則是其中至關重要的要素。
過去我們在民族的文化認同中對于華夏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因素及“禮儀”的政治性傳統講得較少。其實,作為華夏文明核心的禮,其內容包括了我們民族文化的兩個大層面:1.作為華夏這一農業民族社會生活的起居住行、生產交換、風氣民俗、社會交往;2.作為區分貴賤等級層次的政治性禮儀制度,即不同政治層級的人群其身份、祭祀、衣食、住行、服飾、車馬的不同標志。這種政治分層性的禮儀標志是不能夠僭越及隨意使用的,否則就是神人共誅的對象。在傳統民族與政治文化中,這兩個方面都起著重要作用。例如早在黃帝時期,就有了各種等級制度的禮。例如祭祀制度。《史記·五帝本紀》記黃帝在位時,“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莢”。《管子·封禪》則云當時的封禪情形:“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伏羲、神農、黃帝封泰山未必實有其事,但它說明這些酋長兼巫師循守泛靈禁忌這一傳統規則以趨福避兇的情形。而隨著公共職能的發展,酋長與部民權力距離拉大。生時為天代言的巫覡,死后又成為在冥冥上天保佑下民的祖先神。先民古樸的互滲思維方式又把許多自然神忌加在他們身上,將他們上升為最高的神,成為人們的祭祀對象。這樣,原先各部落的圖騰逐漸為偶象化的掌握有世俗權力的酋長所替代,這些酋長既是軍事首長,又是為天代言的巫師。他們死后又作為神化偶象,與泛靈禁忌融合,成為呼風喚雨、降魔伏怪、居住天宮的統一的眾神之神。《山海經·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黃)帝之下都。”《韓非子·十過》載師曠言:“昔者黃帝合鬼神于西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并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騰蛇伏地,鳳凰覆上,大合鬼神……”秦簡《日書》簡1028“四月上旬五月上旬戌 ……凡是日赤啻恒以開臨下民而降其決不可具為……”簡857:“毋直赤啻臨日……”赤啻即炎帝。王符《潛夫論·五德志》云:“有神龍首出常羊,感任姒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農,代伏羲氏。其德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班固《白虎通·五行》“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太陽即火神,其色尚赤,說明炎帝驅魔效應在秦仍有表現。
正如上述,以黃帝起始的中原政治文化的層級制度與世俗性社會生活特征,共同組成了禮這個貫穿古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宗族活動的各個方面。而這正是由活動在中原一帶的三皇五帝創造并起始的,黃帝正是其最早的代表人物。如果我們這樣看問題,就可以知道,為什么古人將黃帝尊為華夏民族的始祖,為什么要將黃帝的活動時代作為中國五千年文化和歷史的起點。這是因為中國文化是以世俗性禮儀制度為核心和起點的,正是這種禮儀制度體現了華夏民族、文化、早期國家的特征。所以,以黃帝為華夏民族的始祖及中國文明的起始,是以黃帝部族所開創的世俗化禮儀制度及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為起始標志。這種世俗化禮儀制度及華夏民族的文化認同是當時政治等級(行政)分層、原始宗教的多神崇拜、宗法血緣體制共同融合而成。正是這種世俗化禮儀制度,決定了古代文明發展的方向,使中國古代文明向著這一與世界其他古老文明不同的,排斥統一的、人格的宗教神的方向發展,由此使中國文化始終處于世俗化狀態中。《國語·魯語上》有一段關于祖先崇拜的記載:
“故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在這個祀典中,黃帝作為華夏族祖先神,成為祭祀對象。這種由人轉化的族神是華夏共同的祖先神崇拜主體,也代表了中國古代的民族與文化認同。
中國“禮”的這種屬性,既是以政治文化為核心的,也是以形而上的“天命”“天道”為保障的。《大戴禮記·禮三本》記:“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說明世俗化的禮與形而上的“天道”保障宗教有內在有機聯系。從目前考古材料及文獻資料看,禮與宗教的關系應追溯到中原地區的新石器時代中后期。在這一時期里,原始宗教內孕育著禮的胚芽,并決定了禮的內涵、構架、基本特征。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六千年前的蚌塑龍虎圖墓葬,在遺址45號大墓中,葬一壯年男性,仰身直肢,頭南足北,其東側置龍,西側置虎,可以說是迄今為止“左青龍右白虎”的最早實物例證。從墓中精心擺置的龍虎圖案和墓室內非正常死亡的殉葬者看,墓主人既是部落酋長,又兼有巫覡的職能。部落族眾用當時十分稀少的貝殼擺置墓室圖案,可能還有死者死后駕龍虎而在神界保佑活人的意義。從這些考古材料證明遠在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人為偶象的一神崇拜已從多神崇拜分化出來,成為中原宗教祭祀的中心。隨著歷史的發展,禮雖然在不斷成熟,但并未脫離它的原初狀態。因此,研究中原地區禮與形而上“天命”“天道”的特定關系,對中國政治文化及社會生活史都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中國古代人在世俗化的社會生活中,有著超越感性的形而上信仰。殷商時期對血緣性祖先神及天、地、山、川神靈的多神崇拜與信仰;西周時代對于以“德”為核心的”天道”“天命”“天”的崇拜與篤信;秦時對于諸神,包括五岳、河流等的山川多神祇崇拜,都是這種形而上本體保障與信仰的產物。同時,這種世俗化禮儀亦以宗教形式而將人間社會的政治等級和君主專制作為最終歸宿。它們往往是以本體保障來說明形而下的世俗性社會生活,尤其是政治性的社會分層的等級制度的“天道”認同的合理性,而其最終目的是以獲得形而上保障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力量來保障現實中的君主專制政治以及社會政治等級制度。
五、黃帝與“圣王同祖”“華夷共祖”社會理想
由于中國文明是一種世俗性文明,因此從國家產生之初,它就以世俗化的禮制代替了世界古代文明通常所具有的以統一神為主的宗教威權模式,而形成以世俗性政治威權為核心的禮制模式。這種政治威權與文化認同模式不僅在國家建立之初就成為中國古代國家的基本模式,而且在華夏民族形成過程中也貫穿其中,成為貫穿我們民族文化的精神要素。尤其是在春秋時期及以后夷夏民族關系的緊張,華夏民族由諸夏逐漸形成統一的民族,而華夏各個諸侯國家也在不斷的兼并戰爭中逐漸凝合為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的時候,具有民族與國家內涵的華夏禮儀文化也在這種情況下成為民族與國家的精神內涵。于是自春秋戰國以后,隨著民族與國家的逐漸統一化,這種文化的始祖黃帝也被作為中華民族的始祖而受到社會的高度重視。在漢代人的歷史觀念中,“圣王同祖”是人們一個較為普遍的認識。不論是文明的開端,還是國家、民族的起源,均上溯到炎黃的歷史。司馬遷在其歷史巨著《史記》中,以其開闊的國家與民族視野,闡釋了“圣王同祖”“華夷共祖”的社會理想,將東西南北的“五方”之民,將秦、楚、越,以及包括中國四邊的匈奴族、南越族、東越族、西南夷等的祖先一同納入到華夏的同祖共源的世系中去。《史記·五帝本紀》以黃帝為華夏第一帝,由此構建了由五帝三王起始的中國人五千年的政治與民族、文明的歷史,并成為古代中國人“同源同祖”及政治上國家治統的淵源。
因此,由史前中原政治性世俗化的文化模式為基礎而奠定的古代中國政治文明,由于其成為中國文明模式發展的核心要素,它使這種文化模式的創造者黃帝及其部族,既作為華夏民族淵源的人格化偶像,也作為中國古代國家政治文明的開創者,而受到華夏族眾的景仰,并成為“圣王同祖”“華夷共祖”的社會理想人物。從這個意義上看,黃帝與中國古代的世俗性政治文明的起始與發展,具有重要聯系。當這種世俗性政治文明成為史前中國的民族、文化、國家認同的核心要素時,黃帝的歷史意義與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作者:重慶市重慶師范大學教授,郵編40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