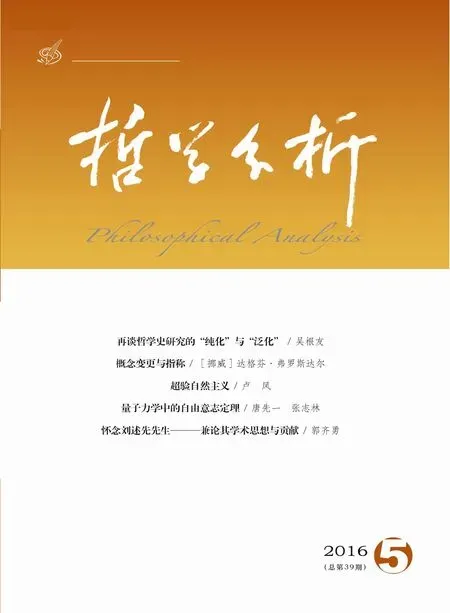重估“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范式意義——評點先剛博士的《柏拉圖的本原學說》
李 偉
重估“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范式意義——評點先剛博士的《柏拉圖的本原學說》
李 偉
在寫出以下的評論和拙見之前,得先提及先剛君關于學術創新和批評的一個重要“表態”:
真正的“創新”毋寧在于潛心領會哲學家的豐富而深刻的思想,把哲學家的認識消化為自己的認識……當“柏拉圖的”認識成為“我的”認識,它就已經是一個“新的”東西……如果有人隨意批評柏拉圖這里不對那里有錯,進而指責我“盲從”柏拉圖等等,我想借用西塞羅的一句話答復道:“你們別管我,我寧愿和蘇格拉底及柏拉圖一起犯錯誤!”①先剛:《柏拉圖的本原學說——基于未成文學說和對話錄的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前言”第5—6頁。以下凡引此著皆以夾注方式標出頁碼。這里,且不說先剛君對“創新”的理解精當與否,只就所謂“隨意批評柏拉圖”言明以下幾點。其一,真正嚴肅的學術討論,都不是“隨意的”,但都是“有意的”;其二,批評的對象可以有兩種——柏拉圖及柏拉圖研究,任何人也沒有資格把自己的研究等同于被研究對象,否則就有“隨意”和“獨斷”之嫌。也即是說,先剛君斷不能以其“柏拉圖研究”來自居“柏拉圖”,不能把自己的柏拉圖研究等同于柏拉圖本身,以為對前者的批評就是對后者的不遜。就此,我也明確一下本文的言說對象:不是柏拉圖,而是先剛君的柏拉圖研究,具體說就是這本《柏拉圖的本原學說——基于未成文學說和對話錄的研究》。毫無疑問,這是一本卓越的學術著作,雅需嚴肅待之。以下擬從學術立場、詮釋策略、核心議題和哲學術語諸方面談些不同的理解。
先說學術立場和詮釋策略。先著始終站在“護衛”柏拉圖的立場上,盡量讓柏拉圖自圓其說,如果現存的對話錄不敷用,就會以此著重點發揮和深化的“未成文學說”來接濟。對柏拉圖著作中涉及的一切問題,都盡量予以“同情式”和“圓場式”的讀解。這種策略和思路,對研究思想史領域中的經典作家和原典來說,是最最要得之舉。那種動不動就以某種官家哲學來對經典作家和作品橫加指責和批評的做法,著實令人反感,此乃政治對學術的不法僭越。①這里可能會有人反駁說:你以經典作家和作品為權威,我以某家為準的,不是一樣嗎?不一樣,你的標準只有一家,我這兒是一種姿態和態度,可以是任何一個經典作家或作品。一家獨大,是學術進展的大忌。
然而,學術“護衛”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在中國古代典籍的詮釋中,就存在這樣的傾向,叫“增字解經”。即是說,把某段令人費解的材料解釋清楚是通過增加額外的材料才獲得的,那這種釋讀就可能是不諦的。現代詮釋學意識已明確,一切人文解釋,都是視域之融合的結果,今人當下之所有,斷不能在解經過程中被排除殆盡,實際上也無法做到想象中的那種凈化,詮釋總是循環的。只是需要辨明一點,伽達默爾他們并未對“前理解”做出進一步的類型上的區分。其實,所謂“前理解”需要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基礎性的、前提性的、常識性的,比如要能認字,要對相應文化有相當之了解,有最起碼的思維能力等等;一類是導向性的,先入為主,也就是那種“主題先行”甚至“上綱上線”和“遵命奉迎”的把戲。前者可稱作“前見”即“前提性理解”,后者則可名為偏于一角的“偏見”即“強制性理解”。或許可以這樣說,伽達默爾他們所強調的“前理解”主要是就“前見”而非“偏見”來立論的,對后者,他們覺得實在不值一駁。然而,即使就第一類“前理解”而言,它是否就一定沒有“導向性”,不是我們的“一偏之見”?那又不能一概而論,因為這類基礎性的“具有”,其間多少都是有價值判斷滲透其中的,絕非純粹的事實因素,可以把這類理解因素從中分離出來而名之為“融匯性理解”,以與純粹事實性的“前提性理解”相區別;當然,它和那種鐵了心地“拉郎配式”的“強制性理解”還是有根本不同的。對于“前提性理解”我們需要自覺,對于“融匯性理解”必須作“前提性批判”,掘出其中的價值判斷,以自覺持論的潛在因素,對于“強制性理解”則必須堅決予以抵制。而且最終,一切經典詮釋都必須經得起文本自身和歷代接受者的重驗。
一如著者自言,此著之最終學術意圖是為柏拉圖哲學提供一個“整體論述”。但細讀來,其重點發揮者,還是圖賓根學派的“基本立場”和“基本精神”,即強調“柏拉圖口傳的未成文學說”和“對話錄與未成文學說的結合”(參見“前言”第1頁)。更明確地說,此著是以“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為最終解釋依據的,作為標題的“本原學說”即是來自這一“未成文學說”。再進一步說,它所提供的“整體論述”實質上是以“未成文學說”為統率和取舍標準的。一如作者所言:“未成文學說是整個柏拉圖哲學的指導綱領和基本架構……它是對話錄的根基和前提。”(第127頁)取舍標準和整體立場的改變,必然使得整個解釋格局發生大震動,使之不可能如著者所言的那樣——“重點不在于討論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的內容”(“前言”第1頁)。因此,“未成文學說”無疑是理解此著的鑰匙和關鍵。這一解釋柏拉圖哲學的致思策略,經圖賓根學派幾代學人的卓越開拓,已被伽達默爾斷定為柏拉圖解釋中的“顯要問題和中心問題”(“附錄”第415頁)。圖賓根學派“未成文學說”即“以存在的最高本原及結構為對象的學說”(第416頁)的邏輯前提,則主要建立在柏拉圖《斐德若》中對“書寫著述”的嚴厲批判上。這派認為,正是柏拉圖嚴厲的“書寫批判”最終導致他不愿或不能在“成文”的對話錄中,暢快直接且毫無顧忌地表達和論證自己的全部學說,尤其是柏拉圖自認最有心得和獨創的那部分理論。故而,對柏拉圖哲學整體而言,現有的“對話錄”不僅不完整,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也因之并不具有傳統賦予的那種絕對權威性。
邏輯地看,柏拉圖之不愿“直說”(因而例之成為“對話錄”)而只訴諸“口傳”之“未成文學說”,若恰能代表其哲學之真諦,根由無非有四:作為“媒介”的書寫之先天缺陷,作為“內容”的學說本身之深奧難解,作為“受者”的聽眾之層次不夠——此三者為“客觀上不能”——和作為“授者”的柏拉圖之對自家學說的珍視護愛——此為“主觀上不愿”。圖賓根學派釋讀策略的基本邏輯前提,則主要建立在《斐德若》中對“書寫著述”的嚴厲批判上。也就是說,只有承認這個前提的“無可置疑性”,才能由此推定“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優先地位和主導意義。這無疑是一個悖論:圖賓根學派立論之基,恰恰是其決意要消除其“權威性”的“成文著述”即“對話錄”——這里主要指《斐德若》中對“書寫著述”的嚴厲批判。也就是說,圖賓根“未成文學說”之“有效性”的根基即是“成文學說”的“權威性”,否則就得面對這樣一個詰問:憑什么單單相信“對話錄”中關于“書寫批判”這一部分的“根本性”和“權威性”(第42頁),而不是像以施萊爾馬赫代表的“以對話為權威的柏拉圖詮釋模式”(第74頁)那樣照單全收?這就需要對柏拉圖現有對話錄做出內容上的分判,指出哪些可信,哪些是戲言。因此,“成文學說”恰恰是“未成文學說”得以成立的邏輯前提,推開來就是,圖賓根學派不構成對“施萊爾馬赫派”的“范式轉換”或“革命爆破”(第74頁),毋寧說是對后者的延伸和補充。
我這樣理解所可能遭受到的最大質疑,無非就是圖賓根學派特別看重并被視為重要學術創見的“善即是一,才是存在的最終本原”(第122頁),并自豪可憑此顛覆以“理念”為柏拉圖哲學核心范疇的傳統認識。其實,這一點,也不像圖賓根學派們所認為的那樣具有“范式轉換”的“革命性”。
關于最終本原的問題,如果從希臘哲學的一般特征及柏拉圖現有對話錄看,世界的最終本原是“一”,根本不是什么聽眾無以理解且解釋起來如何困難的問題。《巴門尼德斯篇》整個對話就是從少年蘇格拉底向芝諾請教“一”與“多”的關系引發的,最終是巴門尼德與少年亞里士多德關于“一”與“多”這兩個概念的辯證法演練。再一個,就“善一”作為柏拉圖哲學最高本原而言,它其實就是“理念”,目前沒有任何足夠且可信的理由不把“善一”理解成“理念”。這也是柏拉圖自己招認的:在《理想國》中,他把“善的理念”亦稱作“理念之理念”。這種稱法,也完全符合柏拉圖的致思模式,就易于接受的角度說,可以這樣表達:最具體的現實對象來自其對應的概念(最低層次的理念,基本是“個名”),這些有現實意指對象的理念又來自更高一級的理念(比如共名)……以此類推,這過程結束于作為最高的也是最終的那個理念,其基本特征是“唯一”(“統一性”的最高體現,即后世所謂“絕對者”或“無條件者”),其基本功能是“可生”(同于老子所謂“可為天下母”),至于給這個“唯一”命名為“善”還是其他什么說法,那都無關緊要。它與世界萬物之間的根本關系,無非就是古希臘思想家殫精竭慮的“多樣性”與“統一性”即“多”與“一”的關系問題罷了。先著就柏拉圖把“善一”仍訴說為“理念之理念”(肯定是從極力彰顯“圖根賓學派”創新性的考慮)曲為辯解道:
盡管就其名稱而言還掛著“理念”一詞,但嚴格說來已經不能再被理解為一個理念。因為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理念本身作為統一性原則卻還處于多樣性的規定之下,這說明在它們之上還存在著更高的乃至最高的統一性原則。(第270頁)
只是先著所謂的“嚴格說來”,一點也不嚴格:柏拉圖何時把理念可能具有的“最高統一性”剝奪了?先著對柏拉圖理念的多層次性倒是有明確認知,既然理念是多層次的,那么,這個層次要不要結束于一個最高的范疇?把所有理念最終統一起來的居然不再是理念?我看,柏拉圖真正的意思,恰恰是要把作為流變現實背后根據的一切,都名之曰理念,只是層次、地位和功能不同罷了。這樣也更能顯示柏拉圖思考的一致性,也更能標明諸理念不僅具有相應的層次性,更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上面這段引文,倒應該這樣說:
盡管就其名稱而言還掛著“善”一詞,但嚴格說來還是那個“理念”,只不過是最高層次的理念罷了。
這大概就是先著在隨后的論述中(比如第361頁),也總是說“善的理念”如何如何的潛在根由。
再就作為“內容”的學說之深奧難解來說。先著所概“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基本內容”包括五個方面:最終本原是善其本質是一(可簡稱為“善一”)、存在階次、走向本原和從本原出發的解釋路向等(第113—125頁)。而就“柏拉圖未成文學說”這些具體內涵而言,實在說來,并不比柏拉圖在《蒂邁歐篇》等對話錄中解釋“一”與“不定的二”如何通過“混合”而產生出諸多個別理念和具體事物的部分更神秘、更難以為一般聽眾所理解,這讓我們不得不這樣想:柏拉圖用這種云里霧里的解釋,夾帶著纏繞的例證,到底是為了說明自己的哲學呢還是根本就沒找到最佳的表達方式呢?如果他柏拉圖認為,自己這樣的解說都是可以被人們理解的,那么,把世界的本原追溯至“一”和“不定的二”,這有什么難以被理解的呢?除非他根本就不想把這一部分透露予外人,這就是“主觀上不愿”。那么,柏拉圖為何在主觀上不愿傳授自家學說的精義呢?看來根由只能是作為“受者”的聽眾之層次不夠——這一點倒是實實在在的。
對柏拉圖對話錄的解讀,最最緊要但又無法確知的問題是,這些對話究竟是“實錄”還是“代擬”。如果是前者,上述的推論,尤其是圖賓根學派立論之根基,就是堅固的,如若是后者,也就是說,這些對話完全是或者基本是“個人創作”,柏拉圖不過是那不出場的“導演”罷了——那就非常糟糕了。因為,顯然地,既然是自己導演,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聽眾之層次不夠”的問題,如果不夠,那也是“導演”的“故意為之”,那他自然就可以設置“高層次的聽眾”,否則,他或者故弄玄虛,或者無法表達自己,或者不想以之示人進而流布后世,這些都不太可能。更糟糕的是,從目前對話錄的實情看,其間諸多人物決不能與歷史上真正存在過的那些對應者等同。連圖賓根學派的主要代表斯勒扎克(Thomas A.Szlezák)也極力主張其“戲劇性”①斯勒扎克:《讀柏拉圖》,程煒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110頁。。在這一點上,先著亦承認這些參與對話的角色及其所傳達的思想“究竟是否符合客觀事實,還是僅僅是柏拉圖的杜撰,這是不易斷定的”(第147頁)②先著在對柏拉圖“對話錄”究竟是“實錄”還是“杜撰”這一點上是非常游移的,他之認同于哪一方,則要看對其先天看法是否有利而定。比如第192—193頁對希臘智者的評論,就主要依據“對話錄”中以他們的名義出現的那些人的言行來評定,就極不合適。既然作者無法斷定“對話錄”是“事實”還是“杜撰”,那怎么能不加證明地以“如實”作前提來推證呢?;并認為,“對于那些至關重要的學說,柏拉圖并不是客觀上‘不能’,而只是主觀上‘不愿’將其托付給文字。”(第88頁)這同樣必須進一步追問,柏拉圖為何“主觀上不愿”?如果真的“不愿”,那又為何要在學院中講給自己的學生聽?
有一個證據可以明確回答這個疑問,這個證據給出的結論則是:柏拉圖決沒有“主觀上不愿”的意思。請看先著從其立論之主要文獻依據即蓋瑟爾所編《柏拉圖學說記述》中選錄的出自阿里斯托色諾斯的一段文字:
亞里士多德曾經一再說道,那些來聽柏拉圖的講課《論善》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這樣的情形:在此之前,每個人都以為會聽到通常關于人的福祉(比如財富、健康、體能或其他值得驚嘆的幸福)的指導,但是,他們聽到的卻是關于數學,關于數、幾何、天文學的討論,最終竟然是這樣一個命題:“善是一。”我覺得,對他們來說這是一些完全意想不到的,很奇怪的東西,所以他們中的有些人對這些內容不屑一顧,有些則分開地拒絕它們。(第97頁)
請您仔細琢磨其中“那些來聽柏拉圖的講課《論善》的人,絕大多數都是這樣的情形”這個句子,不是明擺著柏拉圖的“講課”是不擇聽眾,而且似乎還有課前預告之類的情況嘛。“這些來聽課的人”,斷然不會全是柏拉圖的學生,否則,不可能會出現“絕大多數都是這樣的”這種情形。“完全意想不到”不也說明這些人不可能就是學院的學生嘛。既然有那么多的外來客,那為何還要講述自己那被圖賓根學派指認為與“成文學說”相比更形緊要曾的“未成文學說”呢?因此,這足以說明,柏拉圖并非“主觀上‘不愿’”。
進一步的問題是,在有關柏拉圖“未成文學說”的諸多論爭中,最核心且最緊要的一個問題是,這些從別人,不論是亞里士多德還是其他人的著述中,勾稽出來的所謂柏拉圖的“未成文學說”與“對話錄”的關系若何?邏輯地看,無非四種:兩者相合,前有后無,前無后有,相互矛盾。第一種情形相對簡單,但又是最基礎的,可以作為討論和裁定分歧的基本依據;第二、三種情形,亦不復雜,以之互補即可,只要它們與第一種情形不相矛盾即可。關鍵是第四種情形,遇之則以誰為準?還有就是,柏拉圖對“書寫”的批判,是一貫還是一時的?他是對著述“形式”的不信任,還是對構成著述之“文字”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是絕對的還是有所保留的?
再柏拉圖所用術語的角度看。柏拉圖對話錄中,賦予“本原”以截然不同的諸種術語,先著本應對此類術語作一個系統集中的梳理和總結,尤其是“造物主”與“必然性”、“始終存在著”與“始終流變著”、“一”與“不定的二”、“存在”與“非存在”等范疇。
比如在論證“存在”與“非存在”的關系時,就應當明確,這種關系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是存在本身就包含著非存在,還是存在只有相對于非存在才能被稱為存在?就像《斐多篇》(97a-b)里所說“二”是如何形成的一樣(是“分的”還是“合的”)。這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論證理路。此著對此,未加措意。
柏拉圖二元本原之一的“物質”即“不定的二”,這個“無規定性的物質”,這個又被稱為“必然性”,同時又被稱為“偶然”,到底是一種可以實指的存在呢,還是僅僅是一種純粹觀念上的推定?如果是后者,我們就能理解謝林所謂的“‘不得不存在’這一必然乃是最大的偶然性”的要義,即是說,“不得不存在”是邏輯上推定的,推理到了這個地步所不得不設定為存在的東西,而“偶然性”則是說它的來源是無法再追究的和我們對之所無解的。
因此,就實質意義來看,“圖賓根學派”的價值并不是像先著所說的那樣巨大,而倒是在于一種“眼光”和“提醒”,讓我們注意到柏拉圖對話錄中已然涉及的某些重要理論命題和思想罷了。
最后,就先著中出現的一些細節問題列舉如下:(1)第11章“柏拉圖政治哲學中的本原學說:哲學王與民眾”在邏輯與全書不洽,或可移到第10章前,或并入前面“本原論”各章節中;而且,此部分的思考,與前相比,亦不夠成熟,對柏拉圖“哲學王”的理解本人以為不夠通透,根源在于,論者缺乏相應的“事實與價值分野”的視野①筆者對此有較為細致的分析,參見《詩中有史不是史,史蘊詩心終非詩——事實與價值視域下文史關系的哲學辨證》,載《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3年第5期,又載于人大復印報刊資料《文藝理論》2014年第1期。。(2)“先著”未對國內柏拉圖研究的前輩學者如嚴群先生相關重要著述作出必要的吸收和借鑒。(3)文中有不少特別“噱頭”的語句和表達,讀來倍覺多余,且不夠尊重對手。(4)康德引文,只字不提今已較為成熟的漢譯本,對本民族之哲學研究不夠尊重;引第一批評時只注明A版頁碼,亦不合于國際慣例。(5)先著中多次提及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概念外延關系的“種、屬、類”等概念(如第121、267頁),這里必須解釋,尤其是亞氏所言種、屬,與今日之含義正相反對。(6)文字上的問題:先著中多次(如第91頁)用到“蓋言之”,聯系其上下文,此“蓋”當是“概括”之“概”,而非“大概”之“概”(通“蓋”);第120頁,段二第二行小括號內的“影響”顯系“影像”之誤,第304頁段二第一行亦是;第150頁倒數第一段倒數第三行的“則是全都是”,第一個“是”是衍文;第224頁頁下第一、二個注所引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不是“V”卷,而是“Δ”。(7)著中諸如“每一個認真讀過柏拉圖的著作并且尊重柏拉圖的人都必定會承認這一點”此類的話,須刪去。這根本不是學術用語,也不是有效的論證,而是“詭辯”:如果你說你讀了柏拉圖,但不承認這一點,那是你不尊重柏拉圖;如果你尊重柏拉圖,也讀過,但也不承認這一點,那是因為你讀得不“認真”。一句話,我“總是在理”。
(責任編輯:肖志珂)
李偉,安徽師范大學副教授,臺灣東吳大學客座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