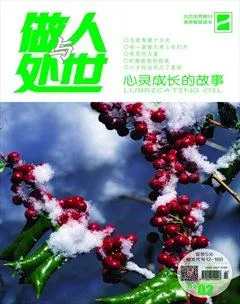看些讀不懂的書
孫君飛
我有一個壞習慣叫躲避,包括思維上和行動上的躲避。
譬如我喜歡看書,但是只看讀得懂的書,讀不懂的書一概不看,被我用思維的篩子漏掉了。這好像沒有問題。是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我可能一輩子都讀不懂,還有大量理科書我都讀不懂,舍棄這些書不是很正常嗎?
而作家畢飛宇講他讀《時間簡史》的一些情況,深深地觸動了我。畢飛宇坦陳自己也讀不懂這本書,然而他并沒有放棄,一直堅持讀。“我讀得極其慢,有時候,為了一頁,我會耗費幾十分鐘”,即使這樣,他還是讀不懂,沒有什么收獲,但是讀不懂偏要讀下去,沒收獲也視之為珍寶。換作我,起碼不會這樣浪費時間,讓讀書的信心受挫,因為我認為這不值得、沒意義。畢飛宇卻恰恰相反,首先他沒有偏見,不會畫地為牢,在喜愛文學語言的同時,也喜愛科學語言,他說科學語言散發著鬼魅般的光芒,對他雖有障礙,卻在背后隱藏著求真的渴望,“它的語法結構里有上帝模糊的背影”。
這樣看待科學語言確實令人耳目一新,而對于不懂的東西,我向來不會如此正面看待,甚至腹誹,而這正是心胸狹窄、認識片面的表現。大概是畢飛宇謙虛,他讀懂了不少科學上難解的語言,才捕捉到這種“鬼魅般的光芒”,于是繼續讀,想看清楚上帝的背影。我是壓根兒對難解的語言不感興趣,哪怕是文學上的語言,我唯一的選擇就是放棄、忘掉,再也不去接觸。這種內在的躲避不叫怯懦又叫什么呢?我只選擇輕松的,不敢挑戰有難度的讀物,會不會帶來精神上的營養不良,會不會形成一種智力上的不良慣性?我沒有考慮過,也意識不到。
我是一個特別容易自我滿足的人,讀懂一頁《百科全書》就覺得夠用幾日了,從來沒有勇氣去讀愛因斯坦,讀霍金,甚至愛慕虛榮,見專家們推薦《時間簡史》,也去買一本放到書架上,卻始終沒有翻過。其實虛榮也是一種怯懦和自以為是,對書這樣,對其他東西恐怕也是如此。然而真實情況是,我讀一百本名著改編的漫畫書,也根本不能跟認認真真地讀完一本全譯本名著畫等號,前者是朝肚子里塞快餐,后者才是滋養心靈的好習慣。
畢飛宇還說了一句讓我臉紅的話,讓我清醒地意識到專挑輕松的書看,或者往深處說,專朝輕松的地方生活,本身也是壞習慣。畢飛宇是這樣說的:“讀讀不懂的書不愚蠢,回避讀不懂的書才愚蠢。”剛開始,這句話確實讓我感到不服氣,我的理由是:既然讀不懂,就不妨回避一下,去讀讀得懂的書,難道不是一種聰明的選擇嗎?接著畢飛宇解釋說,像《時間簡史》這樣的書就如陡峭、圣潔、距離遙遠的雪山,他這輩子都不可能登上去,但是為什么一定要登上去呢?隔窗望著它們,知道它們“在那兒”,不也是很好的嗎?這兩句問話使我明白自己還是太現實,缺乏浪漫情懷,表現在讀書上就是只看容易的、輕松的、有趣的,那些難懂的、嚴肅的、厚重的,在我的心目中就好像不存在,“小橋流水人家”嘛,沒有勇氣去走近雪峰皚皚的圣山。既然人生是悲喜交集的,就應該達到精神生活的深淺平衡,我不應該避難趨易。難怪我讀了那么多的書,仍然庸俗膚淺。
沒有見過氣象萬千的世界,就很難養成浪漫的情懷,浪漫絕不是一種小資情調,它來自壯闊、深邃和勇敢。越躲避,距離浪漫越遠;距離浪漫越遠,就越要選擇現實中觸手可及的東西。雖然還沒有讀完一頁《時間簡史》,我也猜想它一定是一本極其浪漫的科學著作。
對于難度閱讀,畢飛宇這樣安慰像我這樣的讀者:“難度會帶來特殊的快感,這快感首先是一種調動,你被調動起來了。”問題是人們現在滿足快感有很多方式,不一定會選擇難度閱讀。畢飛宇又說“一個人所謂的精神歷練,一定和難度閱讀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句話讓我在為難度閱讀猶豫的時候終于變得慎重起來,我也愿意像畢加索那樣:“當我讀愛因斯坦寫的一本物理書時,我啥也沒弄明白,不過沒關系,它讓我明白了別的東西。”所以 “一個沒有經歷過難度閱讀的人,很難得到‘別的快樂”。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