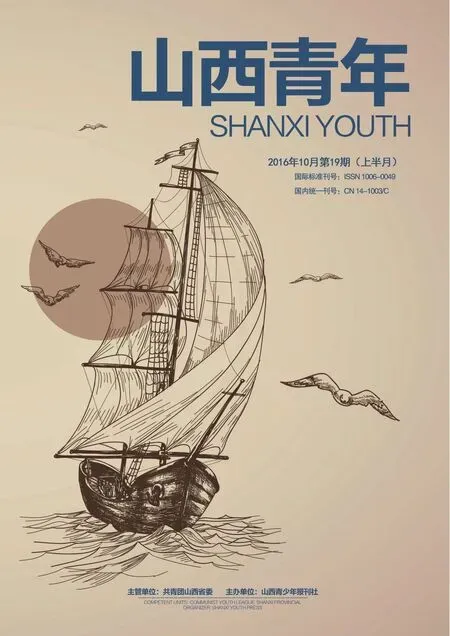安樂死立法的倫理依據
杜 宇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安樂死立法的倫理依據
杜宇*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保定071000
安樂死問題是世界性的問題,并且是多領域問題:涉及到醫學、法學、倫理學等多個方面。之所以讓人們有如此高的關注度,是因為安樂死問題直接關系到人的本質——生命。而要使安樂死走向立法則更是慎之又慎。本文旨在為安樂死立法尋找最本質的倫理依據。
安樂死;倫理
一、安樂死的界定
“安樂死”一詞最早源自希臘文euthanasia,原意為“好死”。自1605年由弗蘭西斯·培根在其著作《學問之深化》中首次用以指現代意義上的“安樂死”后,其意義便被固定下來并被人們廣泛沿用。[1]拉墨頓大夫在1975年4月貝克斯菲爾德學院發表演說時指出,盡管安樂死曾經意味著“好死”,如今也不再有這樣的意義了,而意味著仁慈殺死或謀殺。安樂死一詞在詞義上存在著模棱兩可和混亂,基于這種原因,后人將其細分為聽任死亡、仁慈助死和仁慈殺死三類。[2]
(一)聽任死亡
聽任死亡包含兩層意思:當不可能治愈之時拒絕開始治療;當治療已不再有助于臨終患者之時主動停止治療。換言之,晚期病患不在接受醫療干預而自然死亡,但不意味著是對患者可以不作為更不意味著醫生對病患的放棄。從倫理角度出發,聽任死亡首先是對患者個人生命選擇權利的尊重和保護,其次醫生對患者醫療救助的預判認為,醫療干預在不會有任何治療效果的情況下,還可能會造成患者更為痛苦的后果,而選擇聽任死亡,是對患者權利的最大保障,也是醫務工作者醫德的體現。
(二)仁慈助死
仁慈助死是根據患者主動提出要求,他人采取行動,行動使患者生命結束。晚期病患多數處于受盡病痛折磨,卻無力自殺,只能選擇求助他人,幫助自己結束生命,從倫理角度出發仁慈助死同樣是對患者個人生命選擇權利的保障,并且通過行動,幫助患者消除病痛折磨,使患者得以解脫,雖然結果是結束生命,但其行為是包含人道主義情懷的。
(三)仁慈殺死
仁慈殺死是在未經患者允許情況下,他人采取行動,行動導致患者生命終結。這一行動的前提是患者的生命不再“有意義”。這里的“有意義”是指社會、醫療等層面的意義,醫助不再有效;晚期病患單純的耗損醫療資源,不再具備社會層面的意義。但不意味著失去生命本身的意義,生命本身意義應該是生命個體的存活。生命的選擇權應該由生命個體本身來掌控,其他任何人的干預都應該視為對個體權利的侵犯。但不意味著可以隨意剝奪自己的生命(自殺),前提條件是生命受到不可抗力侵害,病痛的折磨難以忍受且不具有治愈前提下可以選擇生命終止。
二、安樂死的立法思考
(一)權利保障
“法律總是以規定權利為主要任務,權利總是法律的主要內容。”[3]叔本華在《悲觀論集卷》自殺論中這樣寫道“人生在世,具有把握自己生命與肉體的權力,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因此,重病患者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同意結束自己的生命,而不對他人構成侵害和威脅時,這種權利應該被尊重,應該得到保障,而法律法規的保障是最行之有效的。任何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都想努力的活下去,但當遭受病痛災難時,不到萬不得已誰都不愿意選擇死亡,做出安樂死的決定必定是沉痛而堅定的,選擇生命的結束方式,同樣是對人權利尊重和保護。
(二)立法合理性
《憲法》中規定公民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公民個人有選擇生存的方式,同樣在特定情況下也具有選擇死亡的方式。病痛的折磨侵蝕著人們的身體,同時瓦解著內心,治愈無望的陰影一直籠罩著病患直至生命終結,此情況下尊重病患安樂死的意愿,才是對他人格的尊重和尊嚴的維護。安樂死并不與憲法相違背,且不超越其權限范圍。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符合法定形式,安樂死立法是具備可行性的。
(三)立法必要性
安樂死的具體實施涉及到的不僅僅是患者本身,還會涉及到醫生、親屬,涉及生命終結須慎重考慮。醫生、患者家屬甚至患者不可隨意決定是否實施,必須依靠相關的法律法規,具體的實施細則,法律就必須制定出行之有效,責任明確,符合實際的相關條文,進而規范和約束安樂死。通過明確的法律條文調節醫患及患者家屬三方的關系,使得安樂死能夠得到法律的真正保障和真正可行。
三、安樂死立法的倫理依據
(一)個人權利的尊重與保障
“自愿”安樂死并非患者的真實意愿,而是迫于治療無效且病痛折磨被迫做出的“自愿”選擇。尊重生命、保護生命是人道主義的基本準則。對于這些治病無望卻又要飽受病痛折磨的人安樂死等同于解脫與自救,而實施安樂死則是對病患自我選擇權利的尊重,并且幫助患者脫離病痛折磨是基于人道主義的行為。
(二)醫療資源的合理分配
晚期患者醫療對其已經無效,但其家人和主治醫院明知無效卻迫于社會壓力,仍然為患者進行醫療,無異于將醫療用藥像丟垃圾一樣丟掉,不僅浪費了醫療資源,而且占用了他人的醫療資源,造成資源浪費的同時也造成了資源分配的不合理。而安樂死則解決了這一難題,將不必要浪費的醫療資源用在可以治愈的人身上,才是做到了醫療資源合理分配。
(三)減輕患者親屬的負擔
重癥醫療必定帶來的是沉重的醫藥費,而對一般家庭來說,家中有位醫治無望的患者無異于鈔票焚燒爐,將拉低家庭的生活質量,甚至難以維持生計。安樂死的實施解脫的不僅僅是患者本身,同樣解脫的是其家庭。解脫的不僅僅是親屬的經濟負擔,還有親屬們時刻準備親人離開自己的難過害怕的心。擁有正常關系的親屬家庭都不希望親人離去,當面對病患持續痛苦并無治愈可能時,患者少受罪則是對親人莫大的安慰。經濟的負擔是可怕的,但內心的痛苦才是最煎熬的。安樂死的實施不僅成全了患者自己同樣成全了親人。
四、結語
安樂死立法問題同樣也是符合功利論,安樂死立法不僅保障了患者的權利,同時確保了醫生醫院方面的責任義務,并且在對待親屬家庭成員經濟負擔方面進行解放。安樂死立法不僅具有合理性、必要性,最重要的是擁有倫理道德支撐,人們常說法律是道德的底線,倫理道德可以寬容的看待安樂死,法律也必將接受。
[l] 張毅.安樂死論爭與第三條路線的法律評價[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2.
[2]雅格·蒂洛,基思·克拉斯曼.程立顯,劉建譯.倫理學與生活(第9版)[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2.
[3]公丕祥.法理學[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
杜宇(1991-),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學政法大學,倫理學專業碩士研究生在讀。
D924.11
A
1006-0049-(2016)19-0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