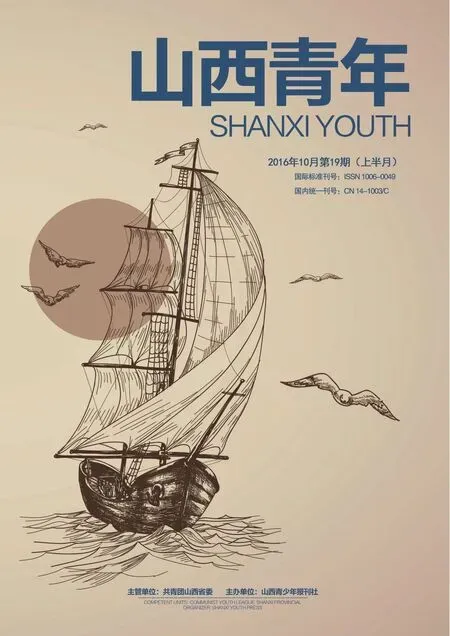不作為侵權(quán)中作為義務產(chǎn)生的理論基礎(chǔ)研究
劉 杰 劉襄楠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 保定 071000
?
不作為侵權(quán)中作為義務產(chǎn)生的理論基礎(chǔ)研究
劉杰*劉襄楠*
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河北保定071000
不作為侵權(quán)與作為侵權(quán)是侵權(quán)責任法上侵權(quán)行為的兩個重要的表現(xiàn)形式,在我國現(xiàn)有的侵權(quán)法規(guī)范意義語境下,作為侵權(quán)是侵權(quán)行為的主要表現(xiàn)形式,但是伴隨社會的發(fā)展,不作為侵權(quán)的表現(xiàn)形式愈趨多樣化。由于我國在立法上對于不作為侵權(quán)的規(guī)范相對比較少以及司法實務中面臨的不作為侵權(quán)的案例頻發(fā),那么就需要通過對不作為侵權(quán)做進一步的理論研究,從而擴大侵權(quán)法的適用范圍并為不作為侵權(quán)中侵權(quán)人的責任承擔提供理論基礎(chǔ)。本文試圖從自由理論、社會共同體理論和成本理論這三個方面來闡釋作為義務產(chǎn)生的理論依據(jù)。
作為義務;自由主義;社會共同體;成本理論
不作為侵權(quán)中責任人承擔責任的基礎(chǔ)是有積極作為的義務,這種作為義務來源于法律規(guī)定、合同關(guān)系、先前行為和公序良俗等等,這些義務的來源可從以下理論中找出合理性基礎(chǔ)。
一、自由理論
自由主義理論間接地為不作為侵權(quán)責任的承擔提供了充分的論證基礎(chǔ)。可能會有人認為讓一個沒有做出任何積極行為的人去承擔損害責任是對人自由的不合理限制,其實這只是對自由的誤解。在不同的社會環(huán)境下對自由有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即使是自由主義法哲學家也認為,在特定情境下承擔作為義務,通過積極作為來避免可預期損害的發(fā)生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一)積極作為的要求或者義務的設(shè)定并非是對自由的侵犯,相反兩者是內(nèi)在統(tǒng)一的
古典自由理論并不反對人們負有積極作為的義務,相反它要求人們在特定環(huán)境下要積極的作為以避免損害結(jié)果的發(fā)生,因此在討論行為人是否應該救助受害人時,不可避免的需要對自由的實質(zhì)性內(nèi)涵作出分析。在自然的狀態(tài)下每個人是一個不受侵害的個體,人們在自由的界限范圍內(nèi)行使權(quán)利享受利益并履行相應的義務。這個自由的邊界為阻止非合法暴力提供的權(quán)利行使的理論依據(jù),即在自然狀態(tài)下,每個人都有權(quán)利通過阻止不合法行為來保護自己的自由權(quán)利。在新自由主義理論下,不作為侵權(quán)也獲得了該理論的支持。新自由主義理論強調(diào)人不僅僅是個體語境下的人,更是社會性的人。
(二)積極的作為義務要求是基于對個人自由合理限制的必然結(jié)果
自由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每個人都不受任何拘束,社會必將無序,每個人的個人權(quán)益必將受到侵犯。
但是,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即“應當根據(jù)什么或者運用什么樣的手段來界分每個人的這種私域。”自由理論本身并無法做出回答,這就需要法律做出規(guī)定,通過法律來規(guī)定救助義務,在適用上遵守形式平等,這本身是就符合自由的實質(zhì)內(nèi)涵。在現(xiàn)有的社會環(huán)境下,人們普遍所接受的規(guī)則是在他人人身受到危險的時候,旁觀者應給予救濟,雖然“碰瓷”社會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對人們內(nèi)心固有的舍己救人觀念有所沖擊,但這并不能推倒人們心中形成的固有的道德觀念。因此通過法律的形式,將違反作為義務的行為規(guī)定為侵權(quán)行為,能獲得自由理論的支持。
二、社會共同體理論
社會是由一個個鮮活的個體組成,為了能使共同體協(xié)調(diào)統(tǒng)一的存續(xù)下去,需要每個人放棄一部分自由,承擔相應的作為和不作為的義務。因此,共同體理論為作為義務的來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論基礎(chǔ)。
為獲得安寧、和平與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和生命財產(chǎn)的不受侵犯,需要大家相互協(xié)作、互相幫助,因此這就需要人們積極的去作為以實現(xiàn)這種目的。一方面,共同體理論強調(diào)個人權(quán)利的保護和福利的增進,認為這一目的的實現(xiàn)必須通過共同體這一渠道,只有賦予共同體內(nèi)的每一個個體在他人危難環(huán)境下積極作為的義務,才能實現(xiàn)達到共同體存續(xù)目的的實現(xiàn)。另一方面,共同體理論認為,只有在道德義務通過立法轉(zhuǎn)化為法律義務或者社會義務時,它才能被貫徹執(zhí)行。
三、成本理論
從經(jīng)濟學的角度考慮,法律的規(guī)定對于行為人行為的選擇有重要的引導作用,通過法律賦予作為義務,能促使人們在損害發(fā)生或有擴大可能的情況下采取積極的預防措施,能夠使損害降到最低,從社會整體上來講,能夠節(jié)約社會成本。
首先,在預防損害成本很低的情況下,通過設(shè)定作為義務,可以有效防止損害的發(fā)生。比如,店主在濕滑的地面上設(shè)置警示牌,或者在大霧天的道路上,開啟霧燈或者危險報警閃光燈,這些積極的作為義務盡管微不足道,但能避免極大的損失,從而也就減少不必要的成本付出。
其次,由危險源的控制者或者引起者來承擔相應的作為義務,符合責任理論的基本要求。相較于受害人或者其他旁觀者來講,他們具有先天的“優(yōu)勢”。店主或者經(jīng)營者對于本店地面濕滑的基本情況是最清楚的,讓他們設(shè)立警示標志成本最低,效果最好。如果不賦予經(jīng)營者這種作為義務,那么顧客必將處處小心,時時留意,這樣防止損害發(fā)生的成本將很高。
隨著社會的不斷發(fā)展,基于公共秩序和受害人利益最大程度的保護要求,不作為侵權(quán)責任理論必將不斷獲得充實和全面闡述,同時不作為侵權(quán)的適用范圍將不斷擴大。但不作為侵權(quán)責任的承擔必須以作為義務的產(chǎn)生為基礎(chǔ),因此作為義務是不作為侵權(quán)責任研究的理論核心,只有作為義務的理論基礎(chǔ)獲得充分論證,才能為責任的承擔獲得合理性基礎(chǔ)。
[1]王振東.《自由主義法學》[M].法律出版社,2005.87.
[2]盧梭.《社會契約論》[M].李平漚譯.商務印書館,2011.1.
[3]鄧正來.《哈耶克法律哲學的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20.
[4][美]史蒂文·J·海曼.《民事救助義務的理論基礎(chǔ)》[M].王迎春譯.張民安主編.《民商法學家》.第2卷.中山大學出版社,2006.
[5]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6]王成.位權(quán)損害賠償?shù)慕?jīng)濟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7]蔡唱.不作為侵權(quán)行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8]蔡唱.不作為侵權(quán)行為的法哲學基礎(chǔ)[J].法學雜志,2009.02.
劉杰(1990-),男,漢族,山西長治人,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民商法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在讀;劉襄楠(1988-),女,漢族,河北邢臺人,河北大學政法學院,民商法學專業(yè)碩士研究生在讀。
D923
A
1006-0049-(2016)19-011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