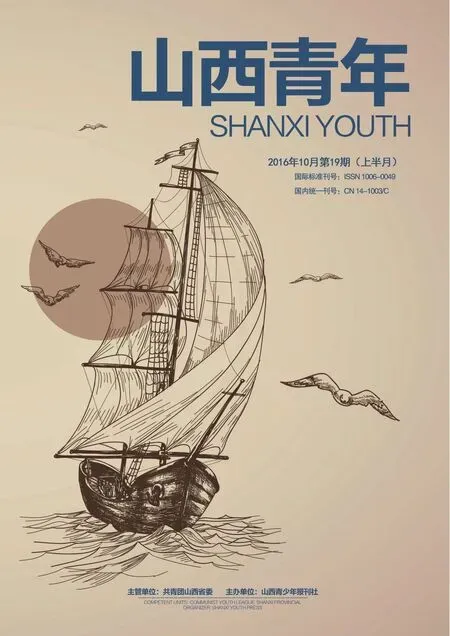基于知識形態變革的大學管理創新
謝 瀑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 三門峽 472000
?
基于知識形態變革的大學管理創新
謝瀑*
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河南三門峽472000
大學是以知識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組織,知識活動和知識創新是其存在與發展的關鍵所在,知識活動形態和知識組織形態的變革,要求大學重新審視管理的“合法性”,緊緊抓住知識創造價值這一關鍵因素,加強管理創新,不斷提高知識創新的有效性。
管理創新;知識形態;組織形態
大學是以知識為基礎建構起來的組織,知識活動和知識創新是其存在與發展的關鍵所在,隨著知識形態的變革,唯有知識的活動形態與組織形態協調統一,才能夠有效促進知識活動與知識創新,唯有通過管理層面的組織結構創新,才能夠為知識活動形態與組織形態的協調統一提供有效保障。正是由于我國大學長期存在的金字塔形的科層管理,不能夠適應知識活動形態與組織形態的發展變化,從而影響了知識創新活動的有效性,基于組織結構層面的大學管理創新才顯得尤為迫切。
一、知識活動形態變革要求大學管理創新
大學以知識為基礎的稟性,決定了“教學—知識的傳播或獲得,科研—知識生產,社會服務—知識的應用與轉化,文化傳承—知識的繼承與傳播”的基本功能,而在這種基本功能的實現過程中,“知識—人—組織”的知識活動形態的變化,決定了大學功能實現的成色。
大學知識的獲取是在一定知識形態內進行的,這些知識既包括學科知識、教學知識、學科教學知識與教學相關的社會與政治環境知識等信息,即包含了對外顯知識的獲取和對諸如教學經驗、科研方式與思維等默會知識,傳統意義上是圍繞靜態學科知識核心而呈現的知識活動形態。
知識活動形態是以知識為活動基礎,以人為活動核心,以組織為活動載體的,“知識本身要經過保存、傳播、創新、轉化、生產等基本活動,這是知識的活動形態;知識的活動離不開人的活動,即教學、科研、生產、服務等基本活動,這是人的活動形態;當人的知識活動日益復雜化后,就要依附于學科、專業、產業等組織,即形成知識的組織活動形態”。[1]人作為知識活動的核心,首先應當緊緊把握知識形態發展變化趨勢,才能不囿于知識保存、傳播的狹隘活動,才能夠貢獻于知識創新、生產、轉化等活動之中。
傳統意義上的知識是一種靜態的、局部的、受學科分類嚴格限制的知識,而這種靜態的學科知識,從本質上講是最適宜保存和傳播的,所以在傳統大學教育中,其知識流動的表現形態一直是以保存、傳播為主的。然而,在當今社會,“正在從一個商品生產社會轉變為一個信息社會或知識社會”[2],“知識是唯一有意義的資源”[3],知識作為一種無形要素,其經濟價值越來越體現出生產性,而生產性知識與傳統意義上的學科知識的靜態性相比,其動態、活躍的特質,決定了知識的生產性愈明顯,其活動方式愈易于發生變化;由于生產性知識重在應用,重在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和利潤,必然要求加快理解、傳播、創新、轉化、固化、更新的速度。知識形態的變化,需要大學的知識活動形態與之相適應。
以靜態學科知識為基礎,以保存、傳播靜態知識為主要知識活動形態,自然形成了與之對應的金字塔形的垂直集權管理體制,這種管理體制的結構主要體現為科層建制、行政集權,以學科為基礎的組織依附于科層行政集權,自上而下的行政科層,集權掌握對于學科組織的資源分配,大學的知識活動便局限在對靜態學科知識的保存和傳播之中,長期形成了固守象牙塔式的“閑逸好奇”,在束縛教師、科研人員跨學科開展教學、研究、創新的積極性,也束縛了知識生產、創新活動與產業、新的商業模式發展的密切結合。因此,大學的管理體制必須以知識管理為核心,緊跟知識活動形態的發展趨勢,創新管理體制機制,形成適于知識形態變化的服務化、網絡化、扁平化管理結構。
二、知識組織形態變革要求大學管理創新
大學的知識活動形態不僅體現為保存、傳播、創新、轉化等關系之中,而且也體現為知識的存在方式上。知識的存在方式主要依附于人的基本活動方式,大學的知識存在方式所依附的是以教師和學生為主體的教與學的活動方式,教與學的活動方式包含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服務社會和文化傳承,聯結的中介是知識,如果只是為了保存、傳播靜態的學科知識,教與學的活動自然依靠于以學科劃分的專業及其教學組織,如果以知識的生產性為追求,傳統的學科知識體系就難以適應跨學科生產知識的需要,不僅知識的保存、傳播方式會因此而發生變化,而且知識的組織形態也必然隨之而改變。
大學作為以知識為核心資源的知識組織,其傳統的知識組織形態主要以學科、專業為依托,知識的組織邊界以學科知識與方法、專業領域與方向的劃分為依據,其邊界十分清晰,人員、資金、物質條件等配置習慣,都是圍繞學科、專業展開的,很難形成跨學科跨專業的知識組織,即便遇到跨學科跨專業的研究項目,也是通過行政手段調配資源、組成臨時團隊,知識的組織形態并沒有脫離學科、專業的匡扶。
問題在于,這樣的大學知識組織形態與經濟社會發展格格不入,一方面培養出的人才由于缺乏多學科融合的視野,難以成為創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學科象牙塔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缺乏與產業的融合,直接影響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和快速實現最大利潤。社會的各個產業并不是以學科、專業進行劃分和建設的,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生產技術升級,往往需要跨學科跨專業解決,無論是調整產業結構或提升技術水平,都需要同時考慮與之相適應的商業模式選擇。知識經濟社會中,知識的生產性特征不僅決定諸如政府、企業、科研等組織之間的邊界更加模糊,而且要求大學在追求知識的生產性價值的過程中,也應當隨之模糊知識組織邊界。
就大學而言,模糊組織邊界,首先要打破學科、專業等組織壁壘,促進知識組織之間的有效融合和組織、活動、人員的相互滲透,建立保證知識信息共享、交流的平臺和機制。21世紀是平臺創造價值的世紀,[4]圍繞知識的生產性特征及其需要,建立與產業企業合作的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技術孵化中心、協同創新中心、創業中心、技術轉化交易中心等平臺,跨學科跨專業組建團隊,形成新的知識組織形態和與之相適應的管理體制。
由于組織邊界模糊的知識組織及其平臺的建立,要求大學管理體制必須創新。新的知識組織打破了原有的學科、專業壁壘,以學科、專業為依據所進行的大學資源配置和科層制垂直管理體制,無論選擇增加管理層次縮小管理幅度,或者減少管理層次擴大管理幅度,都難以適應自下而上的新型知識組織結構的發展需要,要求大學管理隨著知識組織形態變革不斷創新,以有力促進生產性知識向現實生產力的順利轉化。
三、大學管理的合法性與創新
合法性存在于由命令和服從構成的系統之中,取決于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養對其存在意義的普遍信念,[5]意味著某種秩序被認可的價值[6]。大學管理的合法性,其實也就是指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系統中構成的管理的意義所被認可的價值,當這種被認可的價值在管理關系中建立起了被認同的普遍信念,大學管理便被認為具有合法性。
大學管理系統中存在著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這兩種不同類型的權力。大學的“行政權力”是根據管理者的目的去影響教職工行為的能力,其作用方式是強制推行管理規范和措施。學術權力則是因“學術”而產生的“權力”,其作用方式是通過擁有系統性高深知識和探索高深知識而影響他人,體現為一種學術影響力。大學行政權力的合法性,一方面通過行使國家權力的延伸,形成與教育行政機構相銜接的組織機構和管理職能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是通過操縱與分配通過特定的強制手段,在進行組織、控制、協調、監督等管理時,以內部制度規范為表征的管理職能所形成的正當性。大學學術權力的合法性之所以被確認為正當性而得到普遍認同,是通過探索與傳播高深知識、扮演著知識權威的角色而形成的。
當然,大學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合法性還在于其價值“有效性”,無論是存在于“命令—服從”關系中的行政權力的“正當性”,還是存在于“影響—服從”關系中的學術權力的“正當性”,只有被認同為價值“有效性”,才能夠成為大學的普遍信念。在知識的存在形態、活動形態、組織形態,都簡單依托學科、專業進行結構和管理的情況下,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在管理系統中,由于學術協調機構和行政決策咨詢結構的疊加,雖然協調了知識資源及其其他資源的分配關系,但卻制約了學科交叉背景下的知識探索、傳播的資源整合,尤其不能適應創造生產性知識的需要,其管理“正當性”的價值“有效性”不能得到更好發揮。
按照系統論的原理,系統的結構決定功能,由此延展的系統組織管理理論認為,一定的功能需要特定的管理結構來實現。我國大學目前的內部管理系統結構模式大多都采取的是矩陣式,縱向是由校長、職能處室構成的,橫向是由學術協調機構、行政科層結構、院系構成的,行政管理機構和學術協調機構共同與下層的各個項目組和院系形成交叉。在這種管理結構中,雖然加強了各個項目組和院系的橫向聯系,但項目組織的臨時性和院系劃分的學科化及其資源分配的集權垂直化,仍然不能適應知識組織形態的變革。
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下屬的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在對包括大學在內的教育部門、高新技術組織、醫院等在知識創新、轉換和使用等各個方面開展比較研究中發現,大學在各個方面的效益都處在較低程度,匱乏知識管理卻使大學成為知識型組織的“軟肋”。[7]不僅由于缺乏對知識的系統、有效管理,直接影響了大學真正成為知識型組織的成色,而且在大學管理系統中,由于行政系統與學術系統“彈性”關系的斷裂和新的知識組織獨立性的“缺位”,直接影響著建立在管理“正當性”和秩序的“有效性”基礎上的大學權力的合法性。
大學不同于企業組織、政府部門和非營利性機構,高等教育是圍繞特殊的理智材料—知識組織起來的,學術工作是圍繞知識資源展開的,知識是大學創造價值的關鍵所在,學術工作不僅需要尋找方式方法擴大和傳播知識,而且需要尋找方式方法生產、創造、轉化直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生產性知識。大學的管理創新必須回到以知識資源這個關鍵點上來,在分權管理已成為普遍趨勢的當今時代,不僅大學各層級之間的聯系應當相對減少,各基層組織之間應相對獨立,而且新形態的知識組織之間及其與各基層組織之間,更應當建立一種緊湊的橫向關系,強化知識信息共享,強化知識組織與產業、企業等在創造生產性知識過程中的直接的密切的聯系,在破除知識資源、科研項目資源等自上而下集權分配的束縛同時,加強知識資源、科研項目資源的橫向聯系,提高知識管理的有效性,促進大學管理全面創新。
[1]胡赤弟,黃志兵.知識形態視角下高校學科—專業—產業鏈的組織化治理[J].教育研究,2013(1).
[2]丹尼爾.貝爾.后工業社會[M].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85:152.
[3]彼得.德魯克.后資本主義社會[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45.
[4]鄢一龍,白鋼,章永樂,歐樹軍,何建宇.大道之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社會主義[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201.
[5]馬克斯.韋伯著,林榮遠譯.經濟與社會[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239.
[6]哈貝馬斯著,張博樹譯.交往與社會進化[M].重慶:重慶出版社,1989:184.
[7]Centre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lnnovation:Knowledge managenent in learning society chpt2,OECD,2000.
謝瀑(1986-),女,河南洛陽人,管理學碩士,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教師,主要從事教育政策與法規、家庭文化學教學與研究工作。
G647.1
A
1006-0049-(2016)19-017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