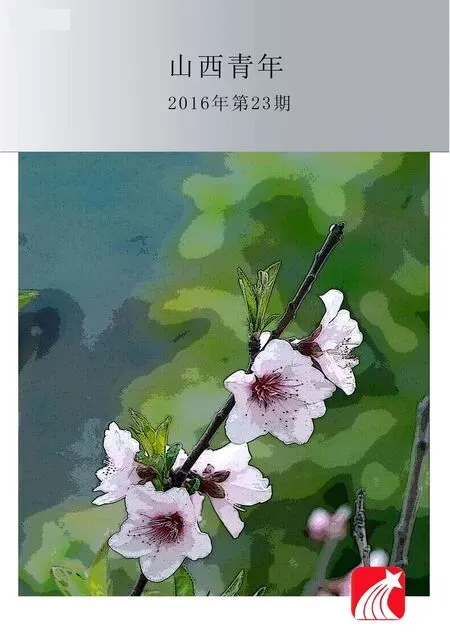淺談犯罪的社會(huì)責(zé)任
王奧然
遼寧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81
?
淺談犯罪的社會(huì)責(zé)任
王奧然*
遼寧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遼寧 大連 116081
每當(dāng)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公眾多將責(zé)任歸咎于犯罪分子的個(gè)人因素,相反社會(huì)責(zé)任意識(shí)淡薄,國家在處理犯罪案件時(shí),也往往對(duì)犯罪的社會(huì)因素視而不見,而國家的不當(dāng)履職、不良的社會(huì)環(huán)境、激化的社會(huì)矛盾等社會(huì)因素乃是引發(fā)犯罪的更深層次原因。隨著司法寬緩化的發(fā)展,國家逐漸認(rèn)識(shí)到了其在刑事責(zé)任承擔(dān)中的重要作用,而“社會(huì)責(zé)任觀”的逐步樹立,也推動(dòng)了司法寬容趨勢的深入。
犯罪;社會(huì)責(zé)任;寬容司法;社會(huì)責(zé)任觀
犯罪是一種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象,其產(chǎn)生有多方面原因,在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時(shí),除了分析犯罪人的個(gè)人因素,更為重要的是剖析犯罪深層次的社會(huì)因素,如不良的家庭環(huán)境、學(xué)校教育的缺失、社會(huì)矛盾的凸顯、社會(huì)輿論的消極引導(dǎo)等。正視犯罪中的社會(huì)責(zé)任,給予犯罪人更多的人文關(guān)懷,無疑有利刑法正義、符合刑罰人道。犯罪中單一的個(gè)人責(zé)任觀逐步轉(zhuǎn)向社會(huì)責(zé)任觀,強(qiáng)調(diào)國家在刑事責(zé)任中的重要作用,也是分配正義的內(nèi)在要求,刑法謙抑、刑罰輕緩化的題中之義。
為了深刻剖析犯罪的社會(huì)根源,本文將犯罪的社會(huì)責(zé)任按照時(shí)間順序,分為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前的社會(huì)責(zé)任(罪前責(zé)任)和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后的社會(huì)責(zé)任(罪后責(zé)任)。
一、罪前責(zé)任
(一)國家的立法活動(dòng)可能制造犯罪
法律可以懲治犯罪,同時(shí)也通過立法條文制造犯罪。立法機(jī)關(guān),甚至執(zhí)法機(jī)關(guān)可以將普通的違法行為評(píng)價(jià)為應(yīng)受刑事處罰的行為,可以臆造犯罪。問題的關(guān)鍵只在于立法者這種自由的限度。
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中闡述了惡法對(duì)犯罪的影響,“賞罰上的分配不當(dāng)就會(huì)引起一種越普遍反而越被人忽略的矛盾,即:刑罰的對(duì)象正是它自己造成的犯罪。”“擴(kuò)大犯罪的范圍就等于提高犯罪的可能性。”國家有時(shí)將本不應(yīng)該納入犯罪范疇的行為以法律的形式評(píng)價(jià)為犯罪行為,法律自身創(chuàng)造出其本該遏制的行為。過重或過輕的不當(dāng)立法,引導(dǎo)人們的犯罪傾向變?yōu)楝F(xiàn)實(shí)。國家的此種不當(dāng)行為,可能出于統(tǒng)治需要的考慮,也可能是認(rèn)識(shí)錯(cuò)誤所致。
(二)不良社會(huì)環(huán)境乃誘因
對(duì)人的理性選擇起決定作用的是人格,人格的形成受社會(huì)化過程中的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影響。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所以惡,是因?yàn)樯鐣?huì)制度自身還不夠完善,社會(huì)環(huán)境還不夠良好,給人以釋放惡的可乘之機(jī)。
在社會(huì)化進(jìn)程中,良好的家庭環(huán)境、優(yōu)質(zhì)的學(xué)校教育、和諧的社會(huì)氛圍,是每個(gè)公民都應(yīng)享受到的權(quán)利。然而,我國的家庭教育仍未擺脫讀書至上的傳統(tǒng)窠臼,學(xué)校在過分重視成績時(shí)忽視了思想品格培養(yǎng),社會(huì)中權(quán)錢至上、追求享樂、沖動(dòng)報(bào)復(fù)等不良文化氛圍誘使人們喪失人格、迷失自我。不良社會(huì)環(huán)境最終致使公民人格異常,社會(huì)環(huán)境又誘使人格異常的人走上犯罪不歸路。近些年來,大學(xué)生違法犯罪現(xiàn)象嚴(yán)重,從窮兇極惡的馬加爵,到視法律如敝履的“藥八刀”,再到復(fù)旦大學(xué)宿舍投毒殺人的林某,都是當(dāng)代大學(xué)生人格異化的血淚教訓(xùn)。
人格異常的犯罪人也是不良社會(huì)環(huán)境的受害者,馬加爵缺少必要的社會(huì)關(guān)懷,藥家鑫面對(duì)壓迫窒息的家庭教育。國家有責(zé)任為公民提供良好的社會(huì)環(huán)境、創(chuàng)造積極的社會(huì)氛圍,保障人們擁有健康積極的品格,避免公民淪為犯罪人。
(三)社會(huì)矛盾的無形轉(zhuǎn)嫁
長期以來國家一直認(rèn)為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的迅猛發(fā)展、物質(zhì)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對(duì)人民最大的福祉,而對(duì)人民個(gè)體的權(quán)益卻無暇他顧,片面追求經(jīng)濟(jì)發(fā)展中的“快”字,公平與效率失衡,社會(huì)公平失落,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趨勢明顯。而社會(huì)矛盾深層次的根源便在于社會(huì)分配不公,貧富兩極分化。長此以往,民眾負(fù)面情緒堆積,便只好通過犯罪的途徑來紓解。
我國正處于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同其他發(fā)達(dá)國家所經(jīng)歷的一樣,在此期間社會(huì)矛盾突出,犯罪率持續(xù)高漲,社會(huì)分配不均的弊病日益顯現(xiàn),迪爾凱姆曾指出:“犯罪有時(shí)是社會(huì)緊張和壓力的‘活塞’,社會(huì)有時(shí)會(huì)將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轉(zhuǎn)嫁’于犯罪人,使之成為‘替罪羊’,以發(fā)泄、緩和社會(huì)內(nèi)部的壓力。”
在犯罪問題上國家對(duì)經(jīng)濟(jì)原因決定論的認(rèn)同,認(rèn)為一個(g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必將伴隨犯罪率的增長。科技的進(jìn)步必定會(huì)促使新的犯罪類型出現(xiàn)、豐富犯罪的手段,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犯罪有刺激增長的一面,國家看到了這一點(diǎn),也往往以此為推脫國家責(zé)任的理由,卻對(d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也可抑制犯罪的一面有意回避。國家作為社會(huì)管理的主體,應(yīng)充分掌握經(jīng)濟(jì)發(fā)展規(guī)律,采取有效的宏觀調(diào)控措施和手段,充分發(fā)揮經(jīng)濟(jì)發(fā)展對(duì)犯罪的抑制作用,克服社會(huì)發(fā)展對(duì)犯罪的消極影響。
二、罪后責(zé)任
(一)國家的司法活動(dòng)可能制造犯罪
司法活動(dòng)本身存在變形走樣、腐化的危險(xiǎn),司法過程中法官對(duì)罪行的擅斷也是產(chǎn)生犯罪的原因,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罪行擅斷往往使案件結(jié)果難以捉摸,同案不同判,同等的情形往往得不到同樣的處遇。司法的不確定性損害了法律的尊嚴(yán)、司法的權(quán)威,更重要的是公民守法的自覺性因此大打折扣。
任何人都有通過司法程序獲得公正的處遇和充分賠償?shù)臋?quán)利,如被害人在遭遇犯罪的侵害后,司法機(jī)關(guān)未能恰當(dāng)?shù)淖肪糠缸锶素?zé)任、被害人沒有獲得應(yīng)有的經(jīng)濟(jì)賠償,受害人就會(huì)加深對(duì)犯罪人的仇恨,失去對(duì)司法權(quán)威的信賴,進(jìn)而產(chǎn)生對(duì)司法機(jī)關(guān)的怨恨及對(duì)國家的不滿情緒。此種情緒往往促使被害人采取私力救濟(jì)方式,以報(bào)復(fù)行為來實(shí)現(xiàn)自我與他人的再一次“平等”。刑事被害人有可能與加害人互換角色,產(chǎn)生新的犯罪。
(二)社會(huì)輿論的消極影響
社會(huì)輿論可以發(fā)揮積極的監(jiān)督作用,是維護(hù)司法正義的一股重要力量。然而,輿論也可能引發(fā)輿論審判,即輿論、媒體通過預(yù)測性報(bào)道,代替法院進(jìn)行審判。輿論審判往往有違無罪推定原則,給犯罪嫌疑人法外定罪,對(duì)法院審判施加了巨大壓力,影響司法獨(dú)立。
藥家鑫案發(fā)生后,媒體給予了廣泛關(guān)注,輿論幾乎一面倒地譴責(zé)聲討肇事者,判決前發(fā)起的關(guān)于藥家鑫案量刑的民意調(diào)查結(jié)果顯示,97%的網(wǎng)友認(rèn)為法院應(yīng)當(dāng)判處藥家鑫“死刑立即執(zhí)行”。輿論除了在量刑方面給予了巨大的壓力外,對(duì)于“激情殺人”、“自首”、“民事賠償”等具體的法律問題也予以高度關(guān)注。對(duì)于藥家鑫等此種輿情案件而言,大眾媒體應(yīng)保持理性客觀,合理引導(dǎo)輿論、疏導(dǎo)民意,切莫為博人眼球、吸引關(guān)注,發(fā)表不負(fù)責(zé)任的言論,使情緒化的輿論彌漫,對(duì)事件本身造成不利影響。
(三)監(jiān)獄制度的缺陷
監(jiān)獄具有懲罰、改造罪犯,預(yù)防、減少犯罪的法定職責(zé),而監(jiān)獄的功效是有限的,犯罪人的重新犯罪率高達(dá)50%,各國皆是。經(jīng)過監(jiān)獄改造過的犯罪人被貼上“惡人”的標(biāo)簽,不被社會(huì)接受,成為社會(huì)的遺棄者。面對(duì)公眾的譴責(zé)和惡人的標(biāo)簽,犯罪人很難保持一種積極的自我形象,他們會(huì)對(duì)社會(huì)的拋棄和壞人的標(biāo)簽產(chǎn)生消極的認(rèn)同,自暴自棄,為謀生只好再次作惡。
犯罪標(biāo)簽理論讓我們看到了監(jiān)獄制度對(duì)犯罪人的副作用,對(duì)于越軌者,特別是初犯、偶犯、過失犯、未成年犯,呼吁社會(huì)應(yīng)更加包容,不能因?yàn)榉缸锶说囊淮问ё憔蛷拇吮簧鐣?huì)拋棄,貼上永久不良的標(biāo)簽,對(duì)犯罪人的改造、教育,幫助其重新回歸社會(huì),成為守法的良好公民是社會(huì)義不容辭的責(zé)任。
總之犯罪不僅是一種法律現(xiàn)象,也是一種復(fù)雜的社會(huì)現(xiàn)象,犯罪現(xiàn)象的發(fā)生具有多重原因。長時(shí)間以來,國家面對(duì)犯罪現(xiàn)象時(shí)大多只關(guān)注犯罪人的個(gè)人因素,于其他因素?zé)o暇顧及或有意回避。“犯罪中的社會(huì)責(zé)任”是一個(gè)嚴(yán)肅的命題,也是一個(gè)相對(duì)嶄新的命題,筆者試圖在犯罪的個(gè)人責(zé)任以外,層層論證、深刻剖析了:國家的不當(dāng)履責(zé)、突出的社會(huì)矛盾、不良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不完備的社會(huì)制度等社會(huì)因素乃是犯罪更深層次的原因,筆墨至此,寫作的目的基本實(shí)現(xiàn)了。
隨著刑法人道與人文關(guān)懷的倡導(dǎo)、刑法謙抑和刑罰輕緩化理念的深入、司法寬緩化趨勢的發(fā)展,犯罪時(shí)單一的個(gè)人責(zé)任觀開始逐步轉(zhuǎn)向社會(huì)責(zé)任,強(qiáng)調(diào)社會(huì)在刑事責(zé)任中應(yīng)承擔(dān)部分責(zé)任。國家也逐漸認(rèn)識(shí)到犯罪現(xiàn)象發(fā)生時(shí)除分析犯罪人的個(gè)人責(zé)任,還有更深層次的社會(huì)因素的影響,然而,國家認(rèn)識(shí)社會(huì)責(zé)任到承擔(dān)起社會(huì)責(zé)任之間還有很長的距離,何況這種認(rèn)識(shí)還只是初步階段,理念上的進(jìn)步更需要在實(shí)踐中落實(shí),國家應(yīng)真正承擔(dān)起預(yù)防和控制犯罪、緩解社會(huì)矛盾、改善社會(huì)環(huán)境、完善社會(huì)制度的法定職責(zé),使理念到實(shí)踐不再是理想到現(xiàn)實(shí)般難以逾越的距離。
[1]何清漣.現(xiàn)代化的陷阱——當(dāng)代中國的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問題[M].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2]王牧,主編.新犯罪學(xu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吳宗憲.西方犯罪學(xué)(第二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4]周東平.犯罪學(xué)新論[M].廈門:廈門大學(xué)出版社,2006.
[5]盧建平,主編.刑事政策評(píng)論[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7.
[6][法]盧梭.社會(huì)契約論[M].何兆龍譯.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63.
[7]郭道輝.社會(huì)公平與國家責(zé)任[J].法治研究,2007(l).
[8]周紅鏘.國家契約與國家責(zé)任[J].杭州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1(5).
[9]斯超.從刑事政策角度看犯罪產(chǎn)生的社會(huì)責(zé)任[C].中國犯罪學(xué)學(xué)會(huì)第十八屆學(xué)術(shù)研討會(huì)論文集(上冊(cè)),2009.
王奧然(1990-),女,遼寧大連人,遼寧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法學(xué)理論專業(yè)碩士研究生。
G212;D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