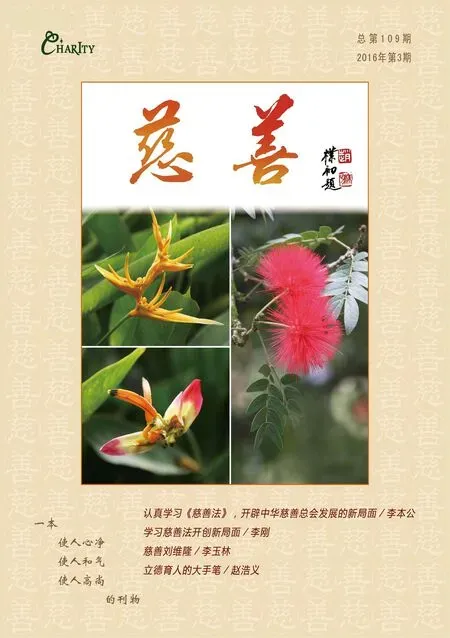學習和弘揚“萬物一體·生態和諧·同體大悲”為理念的慈善文化
● 陸鏡生
?
學習和弘揚“萬物一體·生態和諧·同體大悲”為理念的慈善文化
● 陸鏡生
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數千年的歷史中一直沃灌著中華民族的心靈,熔鑄著中國人的文化精神。中國古圣先賢傳下的歷史文化典籍,其豐富完整,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相比。這些文化遺產閃爍著思想的光芒,凝聚著智慧的力量,蘊藏著道德、慈善的精髓,形成了強大的生命力。我們黨抓住時機,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中華民族的文化越來越成為中國人民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中國民族文化的突出作用是其思想力,它有著高尚的理想理念和價值取向。它是一種激勵我們不斷前進的前導性力量。
我國的慈善事業起步較晚,但發展較快。文化先行是世界上歷來改革的常軌。優秀的文化能激勵社會上的善,批評和舍棄不善,待到善的部分壯大了,就會形成向善的社會風氣。我國的慈善事業要有大的發展,需要有慈善文化的勃興,提升對慈善文化價值的認知。文化缺位的發展,不可能是健康的、全面的、可持續的發展。慈善家群體的涌現,也絕不會來自膚淺的心靈。
現代社會極需慈善文化大張旗鼓地弘揚和普及。現代社會以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為特征,是“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賺錢成為許多人畢生追求的奮斗目標。亞當·斯密曾期望市場發揮公平作用,然而市場上,競爭者有利他念頭的人究竟不多,市場造成弱肉強食,優勝劣汰。市場不是公平可靠,市場導致過度競爭,有時被壟斷或操縱,造成“潘多拉魔盒”的無序,乃至混亂。
在市場經濟主宰的社會中,個人主義廣為盛行。個人主義奉行自主性原則,強調只有個人是一個獨斷的價值源泉,自己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反對任何人的批評和別的價值觀念。這種極端的個人取向對社會就很危險。很多人道德迷失,心靈失落,缺少生命的終極目標和價值取向,對什么都沒有敬畏感,只追求個體對名利、物欲的滿足。企業家為了利益最大化,采用廣告,制造消費者的“虛假需求”,誤導消費者在追求風尚中耗盡了自己的錢包。當很多人把人的價值簡單地定位于物質財富的享用和高消費時,就演變成一種“商品崇拜”,成為“拜物教”,消費成為自我價值實現的表征,獲得社會性身份建構的意義。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寫道:“商品崇拜是人的異化的主要因素。人類被他們自己的商品奴役了,即使休閑時間自由和親密關系的共享也被物化為一種占有與消費的精神狀態。”“在古代社會中,人是矗立著的,財富不過是一個有用物。而今天,物矗立起來了,人卻全面異化和虛空了。”《日本經濟新聞網站2015年12月24日》報道:中國巨額消費支出流向海外。日本2015年度十大流行語揭曉,第一名選中形容中國赴日游客狂熱的“爆買”。赴日本的中國游客人均購物超過17萬日元(約8900人民幣)。日本人譏諷地以“爆買”一詞形容這種消費景觀。“奢侈”如同傳染病流行,將許多淳樸的心靈污染了。我們的媒體也驚呼:“精神荒漠化了。”為什么?因為在消費者的視野中已經沒有了理想、莊嚴、神圣的事物。即使古代文化經典也被一些編導拿來惡搞,造成“黃鐘毀棄,瓦釜雷鳴”的狀態。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一書中指出,有兩種方法可以讓精神枯萎:一種是讓文化成為一個個監獄;另一種就是把文化變成一場娛樂至死的舞臺。從世界范圍來看,許多國家共同的教訓是:真正的貧困不是資源,缺少的也不是財產的匱乏,而是人的素質的滑坡。黑格爾說:“一個民族要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如果只關注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對此,有良知的人們已經警覺。曾經以世界霸主心態傲慢地宣稱“歐洲中心論”和“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地方,其統治地位已經被打破,越來越多的學者批判這種“中心論”的偏頗、缺陷和重物質、輕精神,重科技、輕人文,重個人、輕群體等等的負面作用。越來越多的民眾認同學者們的這種看法。歐美不少學者發現和贊賞古老東方的文化精神和思維方式,呼吁要“從古老東方智慧中尋找靈感”。
西方人下決心,要“從古老東方智慧中尋找靈感”,那么我們中國人應持什么態度呢?我們要從我們古圣先賢留傳下來的典籍中尋找智慧。但這樣做,必須要有動力。在人的本性中,天生具有超越現實的內在沖動。比如,一般來說,當一個人或一家人的衣、食、住無虞的時候,會感到自己或一家人的幸福度還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非財產因素,從而產生一種提升自己文化意識的需求。但這時候,有沒有師、友的引領是不一樣的。筆者的經驗是:在美國當訪問學者時,閱讀英國大史學家湯因比的著作和對話錄時,被他的一句話深深地觸動了。這句話是“解決二十一世紀的社會問題,只有靠孔孟學說和大乘佛教。”湯因比史學大師是學貫東西的。筆者深信他的這句話是他畢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結果。筆者是一個研究西方的普通學子,心悅誠服地把自己看作他的私淑弟子,開始讀儒釋道的經典,并證悟了他的話確實有道理。一個人在思想上有了對自己祖國的文化的理解,就會有強烈的認同。筆者更深信黨中央提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這個中國夢的涌現,其重要因素之一是源自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整體性理解,并從高的層面上把握了中華民族文化及其發展的基本態勢。馬克思說:“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黨中央正是對歷史和現實的深入體悟,達到了對現實背后的本質的把握。在這把握中有中國人對真善美的敬意,對神圣的向往,對生命品質圓滿的渴望。
這里,我們專談的是慈善文化。筆者在曾寫過的文章中談到中華慈善文化有一個靈魂,即“宇宙萬物與我同體”的理念,即“全人類和宇宙不同維度空間的所有形式的生命和物是一個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并從這一理念生發出“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大愛精神”。一個人對這個問題有越深的認識,他的責任意識就越深刻,越持久。儒家學說感悟到“萬物一體”的宇宙真相,而與其同時,在實際運作上,“仁”是從自然的“親親之愛”輻射出去的倫常之情,始則以血緣關系為基礎,表現為父子關系即孝和兄弟關系即悌,繼則向外延伸到非血緣關系,推己及人,于是由“親親”而“仁民”,由孝悌而“泛愛眾”。這是借助理性的實踐過程來不斷提升“愛”的境界和高度。西方人受大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的影響。該書說,“我們能用晚餐,并非屠宰商、制酒者和面包師傅的恩惠,而是由于他們認為對他們有利。這是簡單有效的機制。”然而,在我們看來,這是一種利害關系。不過,按儒釋道的理念,食物生產者和食物享用者相互都感恩的話,社會就會和諧美好,因為“同體大悲,無緣大慈”會喚醒雙方的溫情,會復蘇雙方的良知。
學術界幾乎都認為,文化要“以人為本”。然而在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提倡“以人為本”已經有局限性了。中國的古圣先賢自古以來最敏感的問題,最關注的問題是天、地、人的關系問題。中國的儒釋道感悟了“天地萬物為一體”“萬物與我為一”和“人與天地一物也”。佛教更明確地講“依正不二”(人與人的生存環境是一體)。以王弼為代表的魏晉玄學主張把人文主義思想與自然質樸的自然主義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提出“以自然為本”的思想。儒釋道提倡處理好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和人自身的是靈與肉的關系,與其同時,不破壞自然,而是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這正是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所需要的指導思想。生態文明建設所需要的就是從對人類的愛擴展到對動物、植物、礦物,乃至宇宙不同維度空間各種形式的生命的愛。因此,建設生態文明的時代的文化應該彰顯中華慈善文化的“萬物一體為本”的理念。
中國慈善文化本質上是視“萬物為一體”,善待自然,培育現代生態文明,摒除人類對自然的狹隘功利態度,把大自然視為人類生存的母體和生命的家園,養成一種向自然萬物認同和回歸的態度。中國慈善文化是“生態和諧”的文化。慈善文化的“萬物同體”的大愛理念,是我們慈善事業活動中所追求的、所把握的價值觀點、方向和尺度。慈善文化最終是“為了誰,為了什么?”然后向外展現為慈善事業制度和規范體系的制定,并經過長期反復的實踐,最終形成人們認同的慈善風尚和慈善習慣。這樣,慈善事業就會健康和諧地發展,給人類和宇宙萬物帶來福祉。
“天人之學”是中國思想文化和中國慈善文化的最高主題。司馬遷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變,成一家之言。”這是說,只有研究天人之間的關系,才能在做學問上有所建樹。長期以來,在西方學術界,沒有“天人之學”,是一個空白點。18世紀德國大哲學家康德雖然對星空和道德表示敬畏,但他并沒有思索兩者之間是否存在如中華文化所彰顯的“天人合一”問題。西方思想家只是在面臨現代生態危機時,才開始注意中國的“天人合一”和“萬物與我是一生命共同體”的“理論和實踐”,并從中尋找到靈感,提出了生態文明的主題。美國學者羅伊·莫里森在1995年出版的《生態民主》一書中明確提出了“生態文明”的概念。此后,西方學者越來越多地就生態文明的內涵、理論基礎、方法論模式、實現機制、實現路徑等做了討論。
我們中國人在黨的領導下,用短短的30年、40年的時間,全方位地推進工業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幾乎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100年、200年所走過的歷史進程,與其同時,注意到工業化、市場化引起的生態問題。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的戰略,2007年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奮斗目標。2012年黨的十八大確立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融入其中的生態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格局,提出從優化國土空間開發格局、全面促進資源節約、加大自然生態環境系統和環境保護力度、加強生態文明制度建設等四個方面,對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作了戰略部署;列出盡快消除生態環境危機,推進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大的進展,建設天藍、地綠、水凈為主要標志的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貢獻,就是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提出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作為生態文明建設的內涵,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途徑和方式;提出節約優先、保護優先、自然恢復優先為主的方針,體現生態文明建設規律的內在要求;提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觀念和主流價值觀。這是中國進行生態文明建設的綱領,同時這也是從當代角度,詮釋了“萬物一體”和“同體大悲,無緣大慈”的中華慈善理念。美國著名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想家大衛·格里芬對美國政府很失望,寄希望于中國來引領生態文明建設,為世界樹立榜樣。他撰寫的《生態文明:拯救人類文明的必由之路》一文中寫道:“美國被財閥和軍事力量嚴重控制,我對美國將引領走向一種后現代世界不抱希望。但我確實有理由相信中國可能會引領這一條道路。”建設生態文明是這個世界中最大的善。我們大家應當把“萬物一體、生態和諧、同體大悲和無緣大慈”的慈善理念作為我們的信仰,作為我們每個人生命的最高自我價值和自我實現。
慈善信仰首先是作為一種慈善價值來理解。慈善信仰具有價值性,而且與其他事物的價值相比,它是人類的最高價值。它會提升人的生命質量,促進社會和諧和人與自然的和諧,力爭達到建設生態文明的目標。我們可以斷言:中華慈善理念會解決國家和世界的整體性問題;慈善事業會解決局部性問題。
中華慈善文化的“萬物一體·生態文明·同體大悲”理念作為大家認同的價值,一種休戚與共的真情,一種對他人和其他形式的生命的感應溝通,將他者的感受視為自己的感受,見他者的痛苦視為自己的痛苦,消融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宇宙不同維度空間中的生命之間的冷漠和對立,并生起無盡的關愛和扶持,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形成多元不同中的共同的榮辱,共同的喜與憂,在愛人中愛己,在利他中利己,在使眾人快樂中獲得自己的快樂。一個人對這個道理有越深的認識,他的責任意識就越堅定不移,堅韌不拔,并形成自己的“知行合一”的文化自覺。慈善事業的大發展恰恰是社會上無數個人自我全面發展和自我完善的結果。
在中華精神發育史上,始終伴隨著慈善理念的神奇力量,穿透千秋歲月,在祖國蒼茫大地上高揚仁愛、博愛、慈悲的旗幟,凈化世道人心,健全人格國魂,也照亮慈善事業前行之路。春天來了。春風化雨。愿我們大家一起學習和弘揚“萬物一體·生態和諧·同體大悲”為理念的慈善文化,大力改善社會風氣。在物質享受和感官享受的喧囂之后,應該進入一個理性回歸的家園,回歸到真善美的追求上來,活出人生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