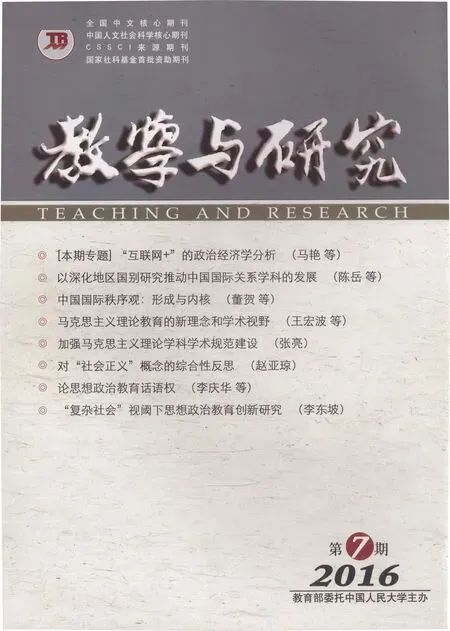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與社會進步*
速繼明
?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與社會進步*
速繼明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社會分工;社會進步
在一個“數(shù)據(jù)重構世界、流量決定未來”的“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成為撬動傳統(tǒng)社會向現(xiàn)代社會轉型的“杠桿”,成為政府轉型、企業(yè)創(chuàng)新、社會變革的加速劑。回顧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思想邏輯和實踐軌跡,我們可以看到以電腦和網(wǎng)絡廣泛運用的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的產(chǎn)生,猶如原子裂變產(chǎn)生的沖擊波,不但裂化和改造了人們的思想,推動著整個社會的發(fā)展和經(jīng)濟持續(xù)增長,也引起了社會分工的再次深化與整合,從而推動了社會進步與發(fā)展。這是因為社會分工既是市場意志、市場精神的歷史沉積,又與科學技術的變革節(jié)律相鏈接。為此,本文從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角度梳理了人類的數(shù)字化生存圖景的歷史變遷過程,考察了“互聯(lián)網(wǎng)+”的顛覆性革命,從馬克思的歷史哲學分析范式來探析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變遷與社會分工的歷史嬗變之間的深層邏輯,乃至對于社會進步的作用力。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的實質就是信息技術革命,是一場人們對“信息技術”的關注從信息的收集、儲存、傳輸?shù)取凹夹g”轉向“信息”本身的觀念性革命。這一革命時代被尼葛洛龐帝稱之為“比特時代”、馬克·波斯特叫“電子媒介時代”,而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命名為“大數(shù)據(jù)時代”。這場關于“數(shù)據(jù)”(也即信息)的研究、開發(fā)、利用在給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注入新的動力的同時,以原子裂變沖擊波般的方式席卷了整個經(jīng)濟生活,顛覆了人們探索世界的方法,引起了社會分工的深刻變化和社會結構、社會秩序的變遷。
一、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的緣起:人類的數(shù)字(化)生存圖景
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核心就是信息數(shù)據(jù),而數(shù)據(jù)就是數(shù)值,是人們通過觀察、實驗或計算得出的結果。作為描述事物關系的參數(shù),數(shù)據(jù)有多種表現(xiàn),最簡單也最基本的就是數(shù)字。從最初的誤差極大的粗糙的測量以及簡單的計算到如今的精確測量、浩繁計算和前瞻預測,人類的數(shù)字化生存圖景經(jīng)過了歷史的發(fā)展與演化過程。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提出“數(shù)是萬物的本原”,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也提出“世界的本質就是數(shù)據(jù)”,[1](P125)人們測量、記錄和分析世界的渴望以及對確定性的不懈追求催生了關于數(shù)的理論及其應用技術的發(fā)展。人們用數(shù)據(jù)來表征世界的一切關系,用數(shù)據(jù)化的方式來記錄人類的活動軌跡。數(shù)據(jù)科學的發(fā)展,使人們在定量描述客觀世界的同時,也深入到人類精神以及社會行為等主觀世界領域,以“量化一切”的方式為整個世界貼上數(shù)據(jù)的標簽,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人類認知、理解和改造世界的方式。
人類的社會實踐總是在一定科學技術條件下開展的。因此,測量、記錄與計算能力總與依據(jù)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改造自然與改造自身的能力而展開。
1.在原始社會中后期,產(chǎn)生了粗糙的信息獲取能力與方式。
隨著抽象能力與計算能力的增強,原始社會晚期人類就開始探索長度和重量等最為簡單的測量與記錄,并在簡單抽象的基礎上進行基本的計算。這種測量、記錄能力也成為原始社會與“文明社會”的分水嶺之一。這種測量、記錄能力促成了數(shù)據(jù)的誕生,它們是數(shù)據(jù)化的最早根基。這一時期的數(shù)據(jù)知識有三個特點:(1)借助于原始的測量工具,較為簡陋、粗糙,測量結果誤差較大;(2)測量方式、記錄方式具有較大的地域性,人類的活動空間所決定的活動范圍決定了不可能有統(tǒng)一的度量衡;(3)測量的動力來源于處理生產(chǎn)生活中的土地丈量、重量測定、偶然的交易記錄等的需要。
2.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印度、中國等文明的數(shù)字系統(tǒng)誕生并且得以完善,提高了人類計量、記錄和再現(xiàn)人類活動的能力。
在公元1世紀左右,后來被世界普遍運用的阿拉伯數(shù)字系統(tǒng)產(chǎn)生于印度,在波斯得以改善,在阿拉伯得到巨大改進并最終完善。而在遙遠的中國,《周易》等重要文獻中還蘊含了極為豐富的二進制思想。雖然這一時期的數(shù)字系統(tǒng)還不是很適合計算,但也基本準備就緒。到了13世紀中葉,自然科學“測量現(xiàn)實”的需要促進了測量、計算的精確度。該時期的數(shù)據(jù)特點有三個:(1)測量方式與能力有所改進,使精確度進一步提高、誤差不斷縮小;(2)人類活動初步突破了地域限制,使度量衡的統(tǒng)一在時間上趨于同步、空間上逐漸拓展,逐漸打破地域的阻隔與限制;(3)測量的動力來源于對變化的量度以及人類生產(chǎn)活動的記錄、計算和交流的需要。
3.資本主義以降,新工具的發(fā)明、新思維范式的發(fā)展、新生產(chǎn)生活的需要共同促進了測量技術與計算科學的繁榮,推進了數(shù)字向數(shù)據(jù)化的轉變。
歷史上很多時候,人們會把測量世界作為征服世界的最大成就。伴隨近代物理學、數(shù)學、地理學、化學的發(fā)展,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人類探索世界的意志持續(xù)膨脹,開爾文“測量就是認知”成為了各個學科的共識,改造自然、改造社會的渴求推動人們必須以必要的技術手段來測度和記錄時間、空間和重量等。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也使得這種渴望逐漸變?yōu)榱爽F(xiàn)實。不斷完善和發(fā)展的測量方法逐漸運用到社會實踐中,同時也在科學觀察、解釋方法中得以廣泛運用并作為研究對象本身,形成專門的學科。在19世紀,測量科學以其獨立性、系統(tǒng)性,根據(jù)世界歷史交往的需要,衍生出各國普遍采用的標準體系。這樣,人類社會就發(fā)展到了一個任何事物都需要數(shù)據(jù)來記錄和分析的時代。
二、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的實踐張力
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預言,計算機的誕生與運用,數(shù)字存儲與傳輸、計算能力的提升,正在帶來一場意義深遠的信息革命。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中,他闡明了大數(shù)據(jù)的Volume(大量)、Velocity(高速)、Variety(多樣)、Veracity(真實)這四大特點。上海求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platoguo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我們需要這樣的思考方式》一文里,也非常精辟地概括了大數(shù)據(jù)的顛覆性影響,非常具有代表性。他從研究方法、研究對象等幾個方面對小數(shù)據(jù)時代與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特點和轉化做了闡述。
1.就研究方法來看,從“基于預設的結構化數(shù)據(jù)庫”到“無需預設的非關系型數(shù)據(jù)庫”。
過去,對數(shù)據(jù)的存儲與檢索依賴于能有效展示數(shù)據(jù)的整齊排列與準確存儲的分類法和索引法。然而,數(shù)據(jù)的海量、混雜等特征無疑與預設的數(shù)據(jù)庫系統(tǒng)相悖,如何從紛繁雜亂充滿復雜性與不確定性的數(shù)據(jù)中發(fā)現(xiàn)價值,需要新的策略。微軟的數(shù)據(jù)庫設計專家派特·何蘭德(Pat Helland)在題為《如果你有足夠多的數(shù)據(jù),那么“足夠好”真的足夠好》的文章中,把大數(shù)據(jù)思維稱為一個重大的轉變,“我們再也不能假裝活在一個齊整的世界里”。[1](P62)
2.就研究對象來看,從“隨機樣本”的調查統(tǒng)計到“全量數(shù)據(jù)”的全景分析。
人們發(fā)現(xiàn),采樣分析的精確性是統(tǒng)計學中的一個重要目標,也是重要的衡量指標,而這種精確度同向變化于采樣隨機性,這是剔除主觀因素的必然結果。該結果與樣本的大小關聯(lián)不大。無疑,這很好說明了隨機采樣的必然性與成功性。但是,人們也隨之認識到,采樣的隨機性很難實現(xiàn),主觀因素或多或少會影響采樣過程,這就必然導致結果對真相的背離。在大數(shù)據(jù)時代,全量數(shù)據(jù)成為可能,這就是我們能夠站在更高的層級更為全貌地看待和分析問題,就能夠發(fā)現(xiàn)過去難以獲得的數(shù)據(jù)價值。
3.就研究結果來看,人們從追求“數(shù)據(jù)的精確性和結果的準確性”逐漸過渡到“數(shù)據(jù)的混雜性和結果的容錯性”。
從絕對主義、絕對觀到相對主義,人們對結果精確性的認識經(jīng)歷了一個轉變階段。在前者的影響下,人們普遍追求通過那些排列整齊如士兵的數(shù)據(jù)序列得出確定無疑的唯一結果,難以容忍非精確;而大數(shù)據(jù)時代,海量數(shù)據(jù)必然帶來數(shù)據(jù)的混亂性,結果也未必那么準確。事實上,“執(zhí)迷于精確性是信息缺乏時代和模擬時代的產(chǎn)物。在那個信息貧乏的時代,任意一個數(shù)據(jù)點的測量情況都對結果至關重要。所以,我們需要確保每個數(shù)據(jù)的精確性,才不會導致分析結果的偏差。”[1](P55)而大數(shù)據(jù)時代的到來,數(shù)據(jù)量的擴張帶來了新洞察、新趨勢和新價值,“除了一開始會與我們的直覺相矛盾之外,接受數(shù)據(jù)的不精確和不完美,我們反而能夠更好地進行預測,也能夠更好地理解這個世界”。[1](P56)
4.就研究內容來看,從分析因果關系的“為什么”到分析相關關系的“是什么”。
小數(shù)據(jù)時代,人們獲得數(shù)據(jù)和分析、計算的能力有限,人們無法就研究對象的全景來分析和做出決策,這就使探究隱藏在現(xiàn)象背后的邏輯——“為什么”成為不得不遵從的必然選擇。然而,大數(shù)據(jù)技術的發(fā)展,海量數(shù)據(jù)的獲取、存儲、傳輸以及處理等技術群的發(fā)展,人們會發(fā)現(xiàn)過去不被關注或被忽視的聯(lián)系,從而提供了新的問題研究視野和有價值的預測指南,這就使探究“是什么”成為我們發(fā)現(xiàn)和了解世界的便捷途徑,且能減少主觀因素的干擾。此外,大數(shù)據(jù)的發(fā)展也導致了從“因果關系”到“相關關系”以及從“審慎的決策與行動”到“快速的決策與行動”的變化。在信息匱乏的小數(shù)據(jù)時代,人們熱衷于采用因果關系范式來快速理解和解決問題。大數(shù)據(jù)時代,人們傾向于量化數(shù)據(jù)值之間的數(shù)理關系,去發(fā)現(xiàn)表面不相關的事物之間的內在關聯(lián)度。
總之,大數(shù)據(jù)的目的就是讓數(shù)據(jù)自己發(fā)聲。“大數(shù)據(jù)時代開啟了一場尋寶游戲,而人們對于數(shù)據(jù)的看法以及對于由因果關系向相關關系轉化時釋放出的潛在價值的態(tài)度,正是主宰這場游戲的關鍵”。[1]電腦、網(wǎng)絡等技術工具的使用使這一切成為可能,“寶貝不止一件,每個數(shù)據(jù)集內部都隱藏著某些未被發(fā)掘的價值。這場發(fā)掘和利用數(shù)據(jù)價值的競賽正開始在全球上演”。[1](P20)
三、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變遷與社會分工的歷史演變
馬克思在《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中尋解“歷史之謎”時,不但意識到“考察分工和交換是很有意思的”,[2](P138)并且還意識到社會分工對社會進步的巨大推動作用,并認為它是“大工業(yè)建立以前的最強有力的生產(chǎn)杠桿”。[3](P642)從“人猿相揖別”時的手足分工,到性別、年齡等因素引起的自然分工;從早期人類社會三次大分工,到人類社會的普遍分工。社會分工水平伴隨社會結構、生產(chǎn)力水平以及社會功能的改變而變化,下文從社會系統(tǒng)*德國社會學家盧曼在其社會系統(tǒng)理論中所提出三種社會類型:“分支式分化 (segmentary differ-entiation)”、“層級式分化(strat-ification differentiation)”和“功能式分化 (functional differentiation)”。參見 G.Kneer, A,Nassehi:《盧曼社會系統(tǒng)理論導引》,魯貴顯譯,第181頁,臺北巨流圖書公司,1998年。的演變與測量、記錄、計算能力即數(shù)據(jù)科學的發(fā)展來考察人類歷史上的幾次社會分工。
1.原始社會中后期的“分支型社會”三大社會分工。
原始社會是由家庭、部落等小型社會構成單位的社會模式。在該社會中,粗糙的信息獲取能力能夠支持人們對長度和重量等最為簡單的測量與記錄,進行初步的社會探索和社會改造。但簡陋、粗糙,測量結果誤差大以及測量技術的屬地性等因素沒有也不能夠孕育更多更精巧的社會功能,因此也不存在更深程度和更廣范圍的社會分工。這一時期的分工有三個基本特征:第一,自給自足,社會成員通過原始的采集和畜牧而滿足生存和發(fā)展的需要。這種需要可以說是一種由模糊的數(shù)的認識和淺陋的對應關系即可匹配,沒有交換,也不需要精確的量的關系與比例。第二,原始的“差序格局”,根據(jù)血緣親疏遠近來確定系統(tǒng)內部結構,這種自然的血脈延續(xù)顯然不需要經(jīng)過計算,也不需要DNA的識別技術,其活動范圍也是囿于地域的局限。第三,根據(jù)血緣、身體的自然稟賦和德行來確立原始的“權威”體系,但該體系既不成熟、也不穩(wěn)定,更沒有體系性的心智模型來維持該秩序結構。無論是觀念意識、技術手段,還是社會制度,都不足以產(chǎn)生成熟的社會分工體系。當然,歷史上的三次社會大分工,還是成為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演進的助推器:畜牧業(yè)的分離、手工業(yè)和農(nóng)業(yè)的分離以及商業(yè)和其他產(chǎn)業(yè)的分離,產(chǎn)生了人類社會歷史上的四大產(chǎn)業(yè)。
2.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時期的層級式社會分工。
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社會分工得到國家制度架構的支撐,以血緣、業(yè)緣等因素為鏈接的家庭、行會等社會單位為依托,在一定層面上社會分工進一步細化和深化。某種程度上,相較于原始社會粗糙測量計算能力的進步是支撐這種深化的重要因素。不斷完善并廣泛運用的數(shù)字系統(tǒng)的誕生,提高了人類計量、記錄和再現(xiàn)人類活動的能力。相對成熟的測量、計算技術使“測量現(xiàn)實”成為可能,這無疑為自然科學的誕生、為跨地域的社會實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的“數(shù)字技術”支持了如下的生產(chǎn)力結構:第一,社會分工模式和程度與社會層級體系相匹配,受生產(chǎn)力制約,與之對應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相匹配。第二,社會分工的深化和擴展有限,難以打破團體、組織或個人一身多職,一職多能的局面。在思想史上,人們已經(jīng)開始較為系統(tǒng)和深入地反思經(jīng)濟社會分工等現(xiàn)象,并熟練運用概念對經(jīng)濟現(xiàn)實進行理性的把握與反思。如色諾芬在《經(jīng)濟論》里闡述社會分工思想:“社會分工的發(fā)展程度受市場規(guī)模制約。[4](P405腳注)柏拉圖也試圖從人的多樣化需求來分析社會分工產(chǎn)生的根源,他認為社會分工是人的稟賦才能發(fā)展的結果。但馬克思卻認為柏拉圖沒有看到社會分工的決定因素和影響因素,認為其分析具有片面性。
3.工業(yè)社會的功能式社會分工。
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以市場意識的多元和市場法則的契約化為支撐,由功能各異的社會領域、且領域間有明確界限和規(guī)則來構筑網(wǎng)絡型的社會結構,領域間界限清晰、規(guī)則鮮明、獨立自治、進出自主;領域內部具有自治和獨立發(fā)展能力,這就拆除了阻礙社會分工發(fā)展的藩籬,為社會分工的無限擴展奠定了基礎。眾所周知,必要的測度和記錄時間、空間和重量的技術手段催生了具有獨立性、系統(tǒng)性的測量科學,進而為物理學、數(shù)學、地理學、化學的發(fā)展,為地理大發(fā)現(xiàn)以及大航海時代的到來提供了記錄技術、測算技術,更為重要的是,提供了強大的邏輯思維能力,也為這種思維能力提供了最為豐盛的經(jīng)驗素材。從而使這一時期成為人類歷史上生產(chǎn)力發(fā)展最為迅猛的第一個時期,馬克思曾對此評價:“資產(chǎn)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chǎn)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chǎn)力還要多,還要大。”[5](P405)譬如亞當·斯密的“制針”例子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認為,互通有無的交換傾向是分工的根源,而市場規(guī)模限制分工的程度和大小。穆勒則認為發(fā)達的交換是分工的結果。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從“社會關系和社會結構演變”的角度對現(xiàn)代社會中分工不斷深化的現(xiàn)象進行了探討。涂爾干認為,分工是一種普遍存在的現(xiàn)象。分工不僅僅只出現(xiàn)在生產(chǎn)領域,還存在于整個世界(包括人類社會與自然界),“我們了解到勞動分工的規(guī)律不但適用于社會,而且還適用于有機體。”[6](P3-4)而馬克思在認可斯密等思想家把社會分工視為交換發(fā)展和人類需求多樣化的結果的同時,也看到了斯密等經(jīng)濟學家的局限性。在他看來,古典政治經(jīng)濟學的誕生,標志著人類從古代社會單純的感性需要及其滿足方式,過渡到有思想地認知人類“需要體系”并自覺地組織生產(chǎn)與交換形式。這種有意識的思想體系,初步構建了人類的經(jīng)濟學大廈,對作為大廈之基的社會分工有了較為系統(tǒng)而深入的認識。有兩個方面的認識是比較深刻的:一是對現(xiàn)代社會分工的基礎的分析。現(xiàn)代社會分工的基礎是個人概念的發(fā)育以及“個人權利”的產(chǎn)生。雖然人類在進化過程中,一開始就是以“社會性群體”的形態(tài)出現(xiàn)的。但吊詭的是,在人類的演進歷史過程中,個人主義獲得優(yōu)先發(fā)展,社會性卻逐漸缺位。一旦“理性化的個人從具有統(tǒng)一信仰的社會有機體中脫出”,就產(chǎn)生了現(xiàn)代的個人觀念和個人權利,從而個人追求自身發(fā)展、追求個人財富、追求個人價值的體現(xiàn)就變得理所當然,這樣,市場制度的建立獲得了來自于心靈的支撐。二是從發(fā)端于人類本能的“生物基因”到歷史進程中沉淀下來的“文化基因”的形成及影響,使人類的分化與合作機制逐漸成熟起來。在生物個體和族群里天然地蘊含了合作關系,這是支配人類社會的重要因素。在長期交往中形成的合作行為,會逐漸演變?yōu)榱曀住⒌赖履酥列叛觯饾u沉淀出類似于“生物基因”的“文化基因”。該基因能使人類群體在規(guī)模擴張的同時保持合作的傾向與可能。
4.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革命下的社會分工。
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的發(fā)展,導致了信息化、網(wǎng)絡化、符號化和專業(yè)化,在產(chǎn)生吉登斯意義上的符號系統(tǒng)和專家系統(tǒng)的同時,又以新技術來“摧毀”和“替代”這樣的系統(tǒng)。
首先,就深度和廣度而言,社會生活領域間的壁壘被電子化的交流方式擊穿,由此帶來社會分工的大整合,表現(xiàn)為分工越來越細,分化越來越復雜,表現(xiàn)為越來越專業(yè)化的專家系統(tǒng)。該系統(tǒng)打碎了人們生活、工作的區(qū)域環(huán)境的限制,把人們牽引出來,并向廣闊的外界空間延伸,導致吉登斯所謂的“脫域現(xiàn)象”。傳統(tǒng)社會的生產(chǎn)力水平和生活方式?jīng)Q定了人們社會交往必然被地域所限制,這種在具體條件中展開并受諸多限制的交往方式限制了分工的范圍和程度。現(xiàn)代性的萌育,當?shù)厥录h方事件的形塑,擺脫了時間、空間的束縛,使跨距離的交往成為可能。也就是說,掌握各種專業(yè)知識和信息的“專家”突破地域壁壘,超越地域限制,打破傳統(tǒng)社會架構制約,他們是現(xiàn)代教育和技術革新引起的復雜分化和高度專業(yè)化的產(chǎn)物。而他們的存在,站在各自專業(yè)領域的高地,在專業(yè)知識的催化下,使專業(yè)領域的分工的深化達到了歷史的頂點;在新領域上的突破,又催生了新的職業(yè)和工種。
其次,現(xiàn)代信息傳播技術使“專業(yè)知識”不再被行業(yè)壁壘所保護,逐漸成為整個社會的“默會知識”,這對吉登斯意義上的“專家系統(tǒng)”形成形式上的挑戰(zhàn)。現(xiàn)代信息技術迫使行業(yè)專家面對更加透明的行業(yè)知識,使之與網(wǎng)絡等信息平臺的知識信息進行博弈。這將改變和調整人們在管理、決策等方面的理念。數(shù)字化和數(shù)據(jù)化使過去難以計量、存儲、分析和共享的知識為所有人敞開了大門。這就好比為每一位能接觸信息平臺的人都發(fā)放了一本“操作手冊”,可以按章操作,人們可以自己查驗得了什么病,如何做菜,如何修理家電(當然,這樣一種方式并不能替代行業(yè)專家);另外,爆炸式的信息使人們無暇消化知識,并依據(jù)因果關系的傳統(tǒng)偏好做出決策,而是從海量信息中發(fā)掘相關關系來做出決策。
再次,經(jīng)驗的作用和影響權重降低,轉而依靠數(shù)據(jù)做出決策與反應,也就是說,人類從依靠自身判斷做決定到依靠數(shù)據(jù)做決定的轉變。社會繁榮和人類歷史的進步基石是建立在因果推理基礎之上的,如果沒有尋求因果的動力,人們就無法探尋物質現(xiàn)象之間、社會現(xiàn)象之間,包括法律現(xiàn)象之間的關系,他也就無法獲得社會進步的不竭動力。然后,伴隨信息技術的發(fā)展,行業(yè)專家和技術專家的光芒都被統(tǒng)計學家和數(shù)據(jù)分析家的光芒所掩蓋。統(tǒng)計學家和數(shù)據(jù)分析家能夠聆聽數(shù)據(jù)發(fā)出的聲音,其判斷建立在相關關系的基礎上,可以較為快速地做出判斷和行為決策,從“審慎對的行為決策”轉變?yōu)椤翱焖俚男袆印薄?/p>
最后,改變了知識的價值,從而引起了社會分工中在下一代的教育投入和工作技能的培訓內容與方式。大數(shù)據(jù)正在重構我們的生活、學習、科研、工作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因為“過去確定無疑的事情正在受到質疑。大數(shù)據(jù)需要人們重新討論決策、命運和正義的性質。我們的世界觀正受到相關性優(yōu)勢的挑戰(zhàn)。擁有知識曾意味著掌握過去,現(xiàn)在則更意味著能夠預測未來”。[1](P239)一是數(shù)學知識、統(tǒng)計學知識、甚至是有少許編程和網(wǎng)絡科學的知識由于在數(shù)據(jù)價值的發(fā)現(xiàn)方面的特殊作用,將導致這些學科門類傳統(tǒng)社會地位的改變。二是非專業(yè)的“專業(yè)化”,即通過統(tǒng)計學等知識的運用,打破學科分界,呈現(xiàn)出學科之間的“跨界”現(xiàn)象。在2015年5月4日的“互聯(lián)網(wǎng)大爆料”公眾微信號中,有一篇題為“文科生終于可以被‘消滅’了”的文章*參見人人網(wǎng),韓曉的日志鏈接:http://blog.renren.com/blog/239211924/791482704.。文章開篇就問“你羨慕那些出口就會吟詩的文人嗎?現(xiàn)在可以不用再羨慕他們了!”甚至有位網(wǎng)友“yixuan” 算出《全宋詞》的99個高頻詞匯,“熟記這些高頻詞,你就可以隨心所欲進行創(chuàng)作了!”根據(jù)詞頻,得出了最流行的宋詞就是“東風何處在人間”!
四、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與社會的進步
總的來說,社會分工的發(fā)展歷程與信息技術的發(fā)展具有密不可分的內在關系。如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所言,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人們理解“IT”時,關注點是有所不同的,過去,人們普遍關注“T”——技術,而現(xiàn)在,人們把注意力轉移到“I”——信息上來。在以前,一旦完成收集工作,數(shù)據(jù)就只是作為存儲或備份而存在,大數(shù)據(jù)使人們重新挖掘,從而獲得新的認知、創(chuàng)造新的價值。他非常清醒地看到信息與技術在當下的權重關系,并進而指出,“為了得到可量化的信息,我們要知道如何計量;為了數(shù)據(jù)化量化了的信息,我們要知道怎么記錄計量的結果。”[1](P105)
1.數(shù)據(jù)不再是靜止和陳舊的,在過去的數(shù)據(jù)中,隱含了當下與未來的選擇項。
據(jù)考證,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記賬人員發(fā)明了書寫來有效地記錄信息;在古代中國也很早就產(chǎn)生了類似于結繩記事之類的信息記錄范式。而計算機的發(fā)明,使記錄方式各異、進制不同的書面語言,轉化為電腦可以輕松讀取和處理的通用語言。這一技術使數(shù)據(jù)的存儲和處理變得簡潔易行,且成本節(jié)約,這就使數(shù)據(jù)的管理效率大幅提升,從“陳舊”數(shù)據(jù)中攫取“新信息”能力也得以提高,人們逐漸學會了從一切太陽底下的事物中汲取信息,比如從手機的地理位置、鼠標點擊和停留時間、就醫(yī)的醫(yī)生診斷書等獲取。通過量化的方法把這些內容轉化為數(shù)據(jù),激發(fā)這些數(shù)據(jù)此前未被挖掘的潛在價值。
2.數(shù)字不再只是數(shù)字,人類的經(jīng)濟生活逐漸從數(shù)字化向數(shù)據(jù)化轉變。
數(shù)據(jù)化和數(shù)字化不是一回事,數(shù)字化指的是把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描述以數(shù)據(jù)的方式表現(xiàn),并能通過編碼的方式用0和1表示出來,既用數(shù)字來標識,也可以用數(shù)字來計算和處理。正如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數(shù)字化生存》中所預言的:人類的生活是“從原子到比特”。從20世紀90年代起,從文本的數(shù)字化,到現(xiàn)如今的菜譜、道路信息、圖像、視頻、音樂等都以數(shù)字化的方式呈現(xiàn)出來,“數(shù)字時代,比特超越了原子,成為世界的主角;今天,物聯(lián)網(wǎng)又讓比特與原子緊密地結合到了一起。實現(xiàn)了比特和原子的無縫連接。此時,重返舞臺的原子已經(jīng)不再是傳統(tǒng)概念的原子,而是一個用比特武裝起來的原子”。[7](引言)這里面有三層隱含信息:(1)雖然數(shù)字化帶來了數(shù)據(jù)化,但是數(shù)字化與數(shù)據(jù)化是兩回事情。數(shù)字化是通過編碼實現(xiàn)對實物的文字描述或數(shù)字描述進行編碼的過程,依據(jù)采樣定理,在一定條件下,用離散的序列來代表一個連續(xù)函數(shù),其實質是用“比特”來描述“原子”;而數(shù)據(jù)化則包括數(shù)據(jù)的采集和數(shù)據(jù)的處理過程。(2)數(shù)據(jù)化表征著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根本性轉變。數(shù)據(jù)化使人們在意識到世界是由信息構成的同時,信息還起到了生產(chǎn)力增長乘數(shù)的作用。(3)通過數(shù)據(jù)化,人們就能對對象世界進行采集、存貯、加工、檢索以及計算等處理。人們學會從數(shù)據(jù)的海洋里檢索出過去未曾注意到的現(xiàn)象和關系,并且學會以一種新的、全景觀察的視角來審視現(xiàn)實。
3.數(shù)據(jù)價值的再發(fā)現(xiàn)。
大數(shù)據(jù)科學的產(chǎn)生始于人類最大規(guī)模的單位時間數(shù)據(jù)的捕獲能力,即樣本選擇的全數(shù)據(jù)模式使“樣本=總體”成為可能,數(shù)據(jù)價值的挖掘使“數(shù)據(jù)發(fā)聲音”。[1](P27)所謂大數(shù)據(jù)思維,“是指一種意識,認為公開的數(shù)據(jù)一旦處理得當就能為千百萬人急需解決的問題提供答案”。[1](P167)2009年甲型H1N1流感爆發(fā)時,谷歌在醫(yī)療系統(tǒng)統(tǒng)計結果前使公共衛(wèi)生機構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數(shù)據(jù)信息,他們通過海量數(shù)據(jù)進行分析以取代“沒有分發(fā)口腔試紙和聯(lián)系醫(yī)生”,從而準確預測疾病的傳播趨勢。近年來,作為集統(tǒng)計學家、圖形設計師、軟件程序員于一體的“數(shù)據(jù)科學家”這一新的職業(yè)出現(xiàn)了,通過挖掘潛在數(shù)據(jù)庫中的信息,來發(fā)現(xiàn)過去沒有注意到的東西,讓數(shù)據(jù)來“澄明”真實情況,讓數(shù)據(jù)自己說話來揭示隱藏在數(shù)據(jù)中的秘密。
五、結 語
應當說,社會分工通過資本擴張的哲學教條與政治譜系的歷史同構,獲得堅實的物質基礎、牢靠的政治制度保障和深厚的資本主義精神支撐。馬歇爾在《經(jīng)濟學原理》中,把社會分工稱為社會機能“微分”,而把社會有機性、密切性、穩(wěn)固性的增加稱之為“積分”,由此分析經(jīng)濟社會“分化—整合”的兩個向度,“社會機能的再分之增加,或稱為‘微分法’,在工業(yè)上表現(xiàn)為分工、專門技能、知識和機械的發(fā)展等形式;而‘積分法’——就是工業(yè)有機體的各部分之間的關系的密切性和穩(wěn)固性的增加。”[8](P288)科學技術的進步,使社會在分化與整合的兩個向度上,分別獲得深化與強化。而信息技術的飛躍,又使這種變化得以往前邁出一大步。
一方面,無可否認,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正改變著原來的社會分工格局,為實現(xiàn)自覺分工提供了物質基礎。人類的社會分工總是在一定科學技術條件下展開的,它是依據(jù)以科學技術為核心的生產(chǎn)資料狀況、對勞動過程的合理分割以及勞動者的優(yōu)化組合而展開的。科學技術的發(fā)展樣態(tài),生產(chǎn)力水平的發(fā)展階段,都決定了分工形態(tài)。因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變化,也引起了生產(chǎn)部門的結構變化,在消滅一部分生產(chǎn)部門的同時又催生出新的生產(chǎn)部門。科學技術體系及其開發(fā)過程的復雜化、精確化趨勢,使研究開發(fā)領域不斷消滅或派生出新的分工。
另一方面,不要神化信息技術革命——尤其是大數(shù)據(jù)的神奇力量,也不要神話社會分工的偉力。在通常情況下,人們并不需要弄清楚“為什么”,而只要知道“是什么”就行了,“大數(shù)據(jù)的相關性將人們指向了比探討因果關系更有前景的領域”,[1](P240)能夠幫助我們以更優(yōu)惠的價格買到東西,能以更快捷的方式預測輿情,能以更有效的方式教導人們,等等。但問題是,僅僅知道這些顯然不夠,科學的發(fā)展、知識的進步,更需要知道使“彼此不關聯(lián)的事物”鏈接在一起,并具有某種關系的背后的邏輯。
[1] [美]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等.大數(shù)據(jù)時代[M].盛楊燕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2] 馬克思. 1844年經(jīng)濟學哲學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3]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法]涂爾干.社會分工論[M] .渠東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0.
[7] 項有建.沖出數(shù)字化:物聯(lián)網(wǎng)引爆新一輪技術革命[M] .北京:機械工業(yè)出版社,2010.
[8] [英]馬歇爾.經(jīng)濟學原理(上卷)[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
[責任編輯 陳翔云]
The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Social Progress of Internet
Su Jim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Shanghai 200090)
internet technology; division of labor; social progress
In a “data reconstruction world, flow decide the future” era of “internet plus”.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leverage which “transforms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society” and can be “the accelerator of government transformati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social change.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thinking and practice path of internet technology, we can see the genera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revolution which is the widely used of computers and the internet, not only crack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thinking,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ocial and economic sustained growth, but also deepening the social division and integration of labor again, so as to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It is like atomic fission produced by shock wave. This is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market will,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market spirit, but also links wit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rhythm. To this end, the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igital human survival picture from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point of view, the subversive revolution effects of “internet plus”, deepening the logic paradigm of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from Marxist philosophy.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互聯(lián)網(wǎng)背景下的財富革命研究”(項目號:13CZX009)的階段性成果。
速繼明,上海電力學院黨委辦公室副教授(上海200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