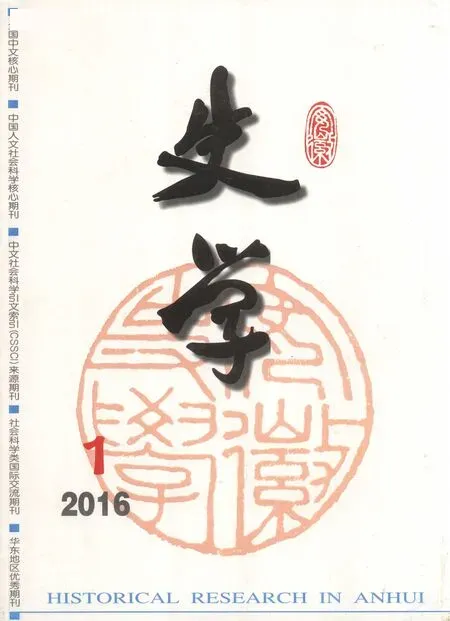民主的悖論:20世紀40年代甘肅鄉鎮保長民選及其異化
柳德軍
(山西大學 近代中國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
民主的悖論:20世紀40年代甘肅鄉鎮保長民選及其異化
柳德軍
(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山西太原030006)
摘要:抗戰后國民政府迫于輿論壓力,開始沿承總理遺教,實施“憲政”統治。為了使其憲政之治初備民主色彩,國民政府決定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委派制轉變為選舉制。甘肅鄉鎮保長民選亦在國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開始實施,然因其地僻處西陲,財力、人力均極缺乏,民眾思想陳陋痼弊,鄉鎮保長民選一開始便舉步艱難。加之內戰的爆發和田賦兵役的持續加重進一步加劇了村民與鄉鎮保長的矛盾,鄉鎮保長職位不再成為鄉村精英競逐的對象,隨選即辭或被迫就任者屢見不鮮,本欲借助選舉以提高鄉鎮保長素質的民選制度卻進一步加劇了鄉村權力結構的失衡。面對鄉鎮保長群體性劣化和鄉村秩序的紊亂,甘肅省政府在內戰尾歇之際被迫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再次由選舉回溯為委派。鄉鎮保長民選的異化及最終失敗的結局,宣告了國民政府在天時、地利、人和均處不利的時境下試圖通過民主的幻象來挽救日趨消亡的政治聲譽,其結果只能是一場民主的濫觴。
關鍵詞:國民政府時期;鄉鎮保長;民主選舉;甘肅省政府
抗戰后的中國政局風雨飄搖,國共內戰一觸即發。抗戰的勝利并未給中國人民帶來一個和平安定的生活環境,相反,新一輪的戰爭將再一次考驗著中國人民的承受力和忍耐度。面對戰后全國人民對和平的殷切期望,重返南京的國民政府為了贏取輿論民心,開始沿承總理遺教,實施“憲政”統治。然憲政之基在于地方自治,如何在基層社會貫徹自治精神并使其初具“民主色彩”,國民政府將目光集中在鄉鎮保長的選舉上。因為在時人眼里“民主就是選舉,選舉就是民主。有了選舉就有了民主,沒有選舉就沒有民主”*王振民:《關于民主與憲政關系的再思考》,《中國法學》2009年第5期。。然而,戰后的中國社會艱難困窘,戰爭與貧窮始終困擾著這個遼闊的國家,國民政府推行基層政制民主化的努力,無論基于何種理由,都難以找到一片適宜于生存的土壤。而鄉鎮保長民選的異化及最終失敗的結局,宣告了國民政府在天時、地利、人和均處不利的環境下試圖通過民主的幻象來挽救日漸消亡的政治聲譽,其結果只能是一場民主的濫觴。以往研究者對于民國時期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本身及社會層面的影響*對于這一問題的主要研究成果有:朱德新:《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冀東保甲制度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冉綿惠:《民國時期四川保甲制度與基層政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張濟順:《淪陷時期上海的保甲制度》,《歷史研究》1996年第1期;王先明:《從自治到保甲:鄉治重構中的歷史回歸問題——以20世紀三四十年代兩湖鄉村社會為范圍》,《史學月刊》2008年第2期,等。,而對鄉鎮保長群體的研究缺乏應有關注,對鄉鎮保長民選制度的研究則更為少見。有鑒于此,筆者以甘肅省檔案館館藏之鄉鎮保長資料為中心,以鄉鎮保長民選為契點,系統梳理20世紀40年代甘肅鄉鎮保長由委派轉變為選舉,再由選舉回溯為委派的歷史進程,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分析國民政府推行基層政制民主化的努力及其限度。
一
在國民政府的行政體系中,國家權力的末梢不再是王權時代的縣政府,而是國民政府在保甲制度推行中設立的鄉鎮公所。鄉鎮保長作為國家行政體系的組織細胞,成為執行各種政令不可或缺的一份子。在國民政府的政制視閾內,無論鄉鎮公所抑或保甲公所,他們都是保甲制度的有效組織,而國民政府正是憑借這些組織將國家權力滲透于基層社會,從而加強對基層社會迅捷有效的管理與控制。
回溯20世紀三四十年代保甲制度的發展軌跡,不難發現,南京國民政府推行的保甲制度不再是中國傳統保甲制度的翻版,而是當中國被卷入國際化的巨潮之后,面對西方政治制度與思想文化的強烈沖擊而產生的一種自覺式的反應:即試圖將西方基層民主模式之自治與中國傳統基層控制模式之保甲融為一爐。雖然國民政府的這一政治理想看似完美,然任何一項政治制度的改革歸根結底均將以人為本。“普通常有以‘人治’和‘法治’相對稱,而且認為西洋是法治的社會,我們是‘人治’的社會。其實這個對稱的說法并不很清楚的。法治的意思并不是說法律本身能統治,能維持社會秩序,而是說社會上人和人的關系是根據法律來維持的。法律還得靠權力的支持,還得靠人來執行,法治其實是‘人依法而治’,并非沒有人的因素。”*費孝通:《鄉土中國》,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版,第48頁。正所謂“法由人立”,“法賴人行”,“所謂王安石治法雖善,終為無治法之人而歸敗績”*⑤⑥宰時:《新縣制之研究與人事之關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9-7。。因此“有合理之制度,尚須有健全之人事,茍所用非人,則不啻交利器與拙匠之手,不徒無益,反收僨事。”⑤蔣介石對此亦有感觸:“為政之道,首在得人,人事之成否,即效能之高下與政治之成敗所連。”⑥可見制度執行者素質之良寙,對于一項政治制度的改革和推行影響甚巨。正是鑒于人事問題的重要性,國民政府在推行保甲制度的過程中,一方面通過各種法令制度對鄉鎮保長的行為進行規范約束,另一方面則以轉變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來對其群體加以改良。
1932年南京國民政府重置保甲時規定,鄉鎮長的產生主要由縣政府委派,并呈報該省民政廳備案;保甲長的產生雖表面上由當地民眾選舉,但事實上仍由鄉鎮公所推薦,由當地素孚聲望且家道殷實之人擔任,并呈報縣政府備案。至于鄉鎮保長賢與不肖,“當縣長的多半是照例不管,隨便委任。還有些縣長甚至專找些壞蟲去充任,因此才可以上下呼應,狼狽為奸,當鄉鎮長的,只要一張委狀在手,于是在鄉壩里,就可以作威作福,刮盡地皮。”*保自春:《關于人民選舉鄉鎮長》,《現代農民》1944年第9卷第13期,第13頁。對此情形,時任甘青寧監察使的戴槐生亦有感觸:“洮河隴南各縣吏治,亟待整頓,蓋縣長對省府政令,例多敷衍,無切實奉行者。而縣以下之區長,多不識字,對政令不但多不了解,且挾勢橫行鄉里,民受其殃。”*戴槐生:《巡視隴南公畢返蘭》,《申報》1936年4月24日,第7版。為了推進基層政治改革,增加行政效率,1939年9月19日《縣各級組織綱要》對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進行了如下修訂:(1)保設保民大會,選舉保長,鄉鎮設鄉鎮民代表會,選舉鄉鎮長。(2)保民大會的出席人員以戶為單位,每戶出席1人;鄉鎮代表會的代表由保民大會直接產生,每保選舉代表2人。國民政府稱,這種規定只是為了適應我國目前農業社會的實際情形,求其簡便易行的初步規定,如果將來自治事業行有成效,則將依據《綱要》第六條之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論男女,在縣區域內屆往六個月以上,或有住所達一年以上,年滿二十歲者,為縣公民,有依法行使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之權。”到那時鄉鎮保甲的民意機關一定將以個別的公民為單位,行使直接民權*高清岳:《新縣制下鄉鎮保甲組織之檢討》,《地方自治半月刊》1940年第1卷第12—13期合刊,第12頁。。國民政府之所以如此改制,則是鑒于過去鄉鎮保長的人選困難,往往賢者不為,為者不賢,基層政權機構往往被土劣把持操縱,違法舞弊,殘害人民,而上級機關又不易糾察。如果設立民意機關,就可以運用民主方法,采取民主監督制,使直接發生利害關系的全體人民公開選舉,以此產生出優良盡職的鄉鎮保長。然而,民意機關的設立并未改變鄉鎮保長對一切事務的執行仍然只以上級命令為依據,并未通過鄉鎮民代表會和保民大會。究其原因,一則因地方行政基層人員唯恐鄉鎮民代表會和保民大會的健全,使他們不能假借政令,殃民自肥。二則民眾對于鄉鎮民代表會和保民大會的認識只停留在聽報告、簽受命令而已,并沒有給他們更多可以發揮權力的機會*秦柳方:《鄉村長實行民選問題》,《國民公論》1940年第4卷第8期,第272頁。。盡管如此,鄉鎮民代表會和保民大會的成立標志著國民政府的保甲制度開始在自治精神的規約下朝著民主的方向發展,雖然這種民主意象的背后蘊藏著諸多的政治目的。
新縣制實施后,國民政府即要求各省辦理鄉鎮保長之民選工作,然由于受諸多因素的影響,甘肅省政府直至1944年底才開始著手此項事宜。1944年11月10日國民政府內政部函詢甘肅省政府:“查鄉鎮組織暫行條例規定,鄉鎮長、副鄉鎮長及保長、副保長分別由鄉鎮民代表會及保民大會選舉,貴省此項選舉已否開始辦理,利弊得失如何?又關于辦理此項工作,除鄉鎮組織暫行條例已規定者外,是否有由中央另頒補充法規之必要。”*④內政部公函:《函請將貴省辦理鄉鎮保長選舉情形見示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對于內政部的詢問,甘肅省政府回函稱:“查三十三年度本省正趕辦縣各級民意機構之建立,尚未辦理鄉鎮保長選舉事宜,擬于三十四年由各縣市擇條件優越之鄉鎮先行試辦,如有成效,再推廣其他地區,并定于上半年現行試辦民選保長副,下半年再試辦民選鄉鎮長副,經將實施限度及實施方法厘訂編入本府三十四年度工作計劃。至補充法規似應有中央頒布之必要,俾各級辦理人員有所遵循步驟。惟本省教育尚未普及,人才缺乏,鄉鎮保長資格不宜過高,以免選舉時發生困難,所以選舉程序及方式亦宜力求簡便易行,而予以彈性之規定,俾地方有權力伸縮之余地,不致為法所拘。”④由此可見,雖然國民政府從1940年起就要求各省辦理鄉鎮保長民選事宜,但在異常艱難的抗戰年代,各省對于此項政制變革不得不一拖再拖,直至抗戰勝利在望,國民政府才將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這一基層政制的改革上。
在內政部的督促下,甘肅省政府決定于1945年開始辦理鄉鎮保長選舉事宜,并制定了《甘肅省政府三十四年度工作計劃關于民選鄉鎮保長條文》,從3個層面對甘肅鄉鎮保長民選事宜作出說明。一、創辦緣起。“查本省各縣市鄉鎮民代表會、保民大會三十三年內均已辦成,主為訓練人民行使人權、提高參政興趣及健全鄉鎮保基層干部起見,所有鄉鎮保長副亟應依法實行民選,以符規定。”二、實施限度。“查民選鄉鎮保長副事屬創舉,深恐辦理稍有不善,致滋流弊,為慎重起見,應由各縣市擇條件優越之鄉鎮先行試辦,如有成效,再推廣其他地區,并于上半年各縣市先行試辦民選保長副,下半年再試辦民選鄉鎮長副。”三、實施方法。“選舉保長副、保長方面:1.各保保民大會舉行達六次以上,經縣政府考核完畢者,得選舉保長、副保長。2.就本保公民中經已任公職候選人檢覆及格者選舉之,本保公民中如符此項及格人時,應依照鄉鎮組織暫行條例第五十四條之規定辦理。3.保民大會應加倍選出保長、副保長各兩人,由鄉鎮公所呈請縣政府圈定委任之。選舉鄉鎮長副方面:1.各縣民選保長、副保長辦理確有成效,各鄉鎮民代表會舉行四次以上,甲種公職候選人檢覆及格完竣,經縣政府考核優異,呈由省政府核準者,得實行民選鄉鎮長副。2.鄉鎮民代表會選舉鄉鎮長副時,應就本鄉鎮公民中經甲種公職候選人檢覆及格者選舉之。3.鄉鎮民代表會應加倍選出鄉鎮長副各二人,繕具各種履歷表,由各縣市政府呈請省政府圈定委任之。”*《甘肅省政府三十四年度工作計劃關于民選鄉鎮保長條文》,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
由上可知,初辦選舉的甘肅省政府為了穩妥起見,在不違背原則的前提下首先擇區試辦,同時為了保證鄉鎮保長的質量,要求鄉鎮保長當選人數加倍而有所選擇。然而,擇區試辦卻遭到了內政部的反對,而當選人數的加倍亦為此后的鄉鎮保長選舉增添了諸多困惑。1945年9月內政部再次函電甘肅省政府稱:“查抗戰已告結束,今后地方工作,應以完成自治為先務,而舉辦鄉鎮長副及保長民選,實為推進自治之主要過程。貴省各縣市雖以文化水準不甚齊一,人民政治興趣有欠濃厚,對于此項事務,開始辦理時,限于事勢,自難望悉符理想。然國策所關,似不便先擇少數鄉鎮試辦,候著有成,效及各地,教育發達然后普遍舉辦,致稽地方自治之進行。所有缺點盡可于辦理過程中隨時督導,加以改進,以期憲政基礎早日奠定。”*《內政部快郵代電渝民字3917號》,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在內政部的催促下,1946年3月,甘肅省政府決定在全省各縣普遍推行鄉鎮保長民選制度。正如甘肅省政府主席谷正倫所說:“現值憲政伊始,還政于民之際,鄉鎮公所為自治領導機關,而鄉鎮長之產生似應由人民選舉賢能素孚眾望者擔任為宜。”但本省各縣除一部分鄉鎮“業經試辦,成效頗佳外,而其他各鄉鎮長仍屬委派,以致意見紛岐,工作難達時代之要求。茲為健全人事組織,亟宜普遍民選鄉鎮長,方能促進地方自治,完成建國工作。”*③《準蘭州市參議會函請普遍實行民選鄉鎮長以符民治一案請鑒核示遵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因此甘肅省政府決定“本府本年度工作計劃內亦訂定全省各市縣局鄉鎮保長一律普遍實施民選”,并分令各市縣局遵照,切實辦理③。同年7月,甘肅省政府頒發了《甘肅省各縣市局辦理區鄉鎮長選舉應行注意事項》25條,決定將1945年試辦民選的鄉鎮保長一律改選。并通令各縣稱:“案查本省各縣市局上年試辦民選鄉鎮長辦法,規定鄉鎮長選二人呈由本府核定一人,保長選二人由縣市府核定一人,與民選鄉鎮長辦法不合。刻各縣市已普遍實施民選鄉鎮長,所有上年試辦之民選鄉鎮保長似應通飭一律另行改選,以符規定。”*《為簽呈上年試辦之民選鄉鎮保長應通飭一律另行改選以符規定請核示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
就在甘肅省政府積極籌備民選鄉鎮保長之時,內政部再次特電催促甘肅省政府稱:“奉主席手諭,將各省實施鄉鎮保長民選情形迅速呈核,貴省實施情形如何,請依下列各項:一、已成立鄉鎮民代表會及已舉辦鄉鎮保長民選之鄉鎮數字;二、全省所有鄉鎮保長,預計須在何時始可完全出自民選;三、已否訂有鄉鎮保長選舉單行規章;四、各縣舉辦鄉鎮保長民選之年月;五、各地舉辦鄉鎮保長民選之實施情形;六、各地實施鄉鎮保長民選有何困難及流弊;七、地方公正士紳及優秀青年,是否踴躍競選;八、各候選人有無利用不當及非法方法競選情事;九、民選鄉鎮保長素質是否較未民選前為高;十、各縣政府及人民對鄉鎮保長民選之觀念如何。請迅速分別縣市查報,并請將一、二、五三項提前電復。”*《南京內政部致甘肅省政府函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0。
二
國民政府為何要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委派轉變為選舉,而且辦理得如此迫切呢?事實上,這與戰后中國國內政治的劇烈變動緊密相連。因為抗日戰爭的爆發“完全改變了國共兩黨政治斗爭的條件。問題變成了那個黨能在這個國家的農業比較重要而現代化程度較差的地區,最充分地動員民眾,建立軍事力量,戰爭使這種競爭從官僚政治的現代化轉向社會革命。”*[美]費正清、費維愷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頁。
自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后,蔣介石便將注意力由對外轉向對內,如何在中國取得合法有效的領導地位成為其考慮的首要問題。1939年9月9日國民黨參政會一屆四次會議召開,蔣介石在開幕詞中為此次會議設置了三個議題:集中人力,建設后方;加強軍事,爭取勝利;注意國際形勢,推進戰時外交。盡管蔣介石閉口不談結束黨治與實行憲政,但參議員提交的眾多提案還是將會議的主題拉到結束黨治與實施憲政上。為了使憲政之路在預設的軌道中運行,在蔣介石的允諾下,由國民黨籍的參政員孔庚等59人聯署提交了《請政府遵照中國國民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案定期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憲法開始憲政案》。內稱:“抗戰兩年,所流者全國國民之赤血,所竭者全國國民之脂膏,在現在黨治之下,政府僅能對黨負責,對全國國民幾無責任之可言。”為此國民政府必須重視民意,珍重民力,實施如下措施:“一、由政府授權國民參政會本屆大會,推選若干人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以制定一可使全國共同遵守之憲法。二、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行政院暫時對國民參政會負責,省市縣政府分別暫對各級臨時民意機關負責。三、于最短期內頒布憲法,結束黨治,全國各黨各派一律公開活動,平流并進,永杜糾紛,共維國命。”*孟廣涵主編:《國民參政會紀實》上卷,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第596頁。然此時抗戰正酣,憲政之議只能成為文牘案卷。
太平洋戰爭爆發和美國參戰進一步堅定了蔣介石抗戰必勝的信念,也加速了其對戰后國內政治的安排。蔣認為隨著抗戰的勝利,由“訓政”進入“憲政”無疑是國民政府贏取民心、奠定統治的不二選擇。然如何才能實現憲政之治?完成地方自治無疑是其通向成功的康莊大道,因為地方自治是“憲政制度的最重要的成分,沒有地方自治,憲政制度只是徒具其表的形式”*Min Tu-ki,NationalPolityandLocalPower:theTransformationofLateImperialChina,Cambridge,Mass,1989,P.159.。對于憲政與地方自治的關系,孫中山在《建國大綱》中早有論述。“凡一省過半數以上之縣皆達成完全自治者,則為憲政開始時期”及“全國有過半數省份達至憲政開始時期,則開國民大會決定憲法而頒布之”*高經:《推行憲政促進地方自治平議》,《新中華》(復刊)1944年第2卷第11期,第5、7頁。。胡漢民在1929年國民黨三大開幕詞中也稱:“所謂訓政,是以黨來訓政,是以國民黨來訓政。在訓政時期中,國民大會的政權乃由本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代行。”為了將來實現憲政,訓政期間“最重要的就是要靠實現總理所詳細規定的地方自治了。地方自治實在是人民的一種基本團結、基本組織。有了這個組織以后,眾人才能變成人民,才能談到一切民權的行使。”*榮孟源主編:《中國國民黨歷次代表大會及中央全會資料》上冊,光明日報出版社1985年版,第617—618頁。由此可見,地方自治與憲政實同為民權運動之產物,憲政之基礎。“人民政治興趣、政治能力及政治道德,固有賴地方自治之培養訓練,而地方自治又必借憲政為之領導促進與保障,二者實相輔相成,互為表里,無先后之可爭。而以地方自治充實憲政,以憲政促進地方自治,乃今后中國政治建設的必由之路。”③高經:《推行憲政促進地方自治平議》,《新中華》(復刊)1944年第2卷第11期,第5、7頁。
然而,自20世紀30年代初南京國民政府推行保甲以來,地方自治被遺落于歷史的角落。雖然國民政府表面上為遵循總理遺教而不得不對地方自治時加提及,但事實上地方自治在基層社會中已失去了往昔的光彩。在抗日戰爭還未結束而國共競逐日趨激烈的特殊年代,如何借用保甲制度來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有效控制,充實與中國共產黨最后攤牌的力量,同時又使這一傳統制度披上民主的外衣,保甲制度與地方自治的融合便成為國民政府解決這一難題的理想選擇。正如梁漱溟所說,在消極散漫的中國鄉村社會步入近代以來,隨著交通的發達和歐風美雨的浸潤,已經很難維持原來的模樣,“要求中國復興,必定要轉到一個新的方向去,什么新的方向呢,就是要由消極的境界轉到積極的境界,由散漫的狀態轉到組織的狀態,這樣新生活的轉變,才是實行地方自治的精義所在。”*梁漱溟:《中國地方自治問題》,《蘇聲月刊》1934年第1卷第5期,第91頁。
雖然國民政府曾致力于保甲與自治的融合,但僅僅理論層面的融合并不能解決面臨的現實困局。為了能使現有的基層政制確具民主色彩,國民政府便將希望寄托在鄉鎮保長的民主選舉上。盡管這一單調的民主模式不能盡顯國民政府改革基層政制之本意,但即使這樣簡單的民主表達在遼闊封閉的中國農村也不見得能夠順利推行。因為“形諸法制如歐洲所有者,始終不見于中國”,“權利自由這類觀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陳序經:《選舉,憲政與東西文化》(二),《現實文摘》1948年第1卷第9期,第9頁。,何況鄉鎮保長民選制度在理論上亦遭到了時人的質疑。他們認為軍政時期及訓政時期最先注重者“在以縣為自治單位,蓋必如是,然后民權有所讬始,主權在民之規定便不至成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勝言。”第一,“以縣為自治單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則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狀態,專制舊習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莫如縣以內之事,縣自治尚未經訓練,對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味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戶籍厘定,皆縣自治最先之務,此事已辦,然后可言選舉。今先后顛倒,則所謂選舉,適為劣紳土劣之求官捷徑,無怪選舉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縣自治以為憑借,則進而參與國事可綽綽然有余裕,與份子構成團體學理乃不相違,茍不如是,則人民失其參與國事根據,無怪國事操縱于武人及官僚之手。”*鄭拔駕:《憲政與地方自治》,《臺灣訓練》1947年第5卷第5期,第20頁。雖然上述說法不無道理,但事實上則是以短視的目光誤讀孫中山的思想。在孫中山看來,如果想讓中國的政治達到民有、民治、民享的地步,即須從最下層做起。實行地方自治,使人民有參與本地地方政治事務的機會,直接選舉地方的官吏,自由制定地方的法令,獨立經營地方的特種事業,人民并得運用四個政權(選舉、罷免、創制、復決)以監督促進地方的政治效率。以其本人話來說:“地方自治者,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石不固。觀五年來之現象,可以知之。今后當注全力于地方自治。”*莊心在:《中國政治建設與地方自治》,《新聲月刊》1931年第3卷第3期,第3頁。可見,孫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并非僅僅局限在縣一級,相反,培育鄉民四權意識,選舉鄉鎮保長才是其自治思想的核心內容。
事實上,國民政府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委派制轉變為選舉制,除了迎合國民黨即將由“訓政”邁向“憲政”的政治因素外,也隱含了國民政府對鄉鎮保甲人員素質的深切關懷。在近代中國推行的各種政制改革中均會遇到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人才的選拔與任用。觀諸民國鄉鎮保長之現狀,誠如時人所稱:“沿至今日,去古愈遠,人心愈壞,而地方保甲愈趨愈下,其弱者頂名充數,一無能為;其強者則交結官差,私通胥吏,或曰縣中某頭腦其親戚也,衙前某先生其好友也,鄉愚無知,以為與官府聲氣相通,不敢稍有觸犯,以罹咎戾,于是乎擅作威福,魚肉鄉間。每節須送節規者有之,做壽分帖苛派禮物者有之,稍有事端,便生枝葉,肆其貪狼之性,逞其狡兔之謀。其在名鄉望族,或尚斂跡而不敢恣肆,倘在窮鄉僻壤,去城較遠,官府耳目有所不及,則若輩更肆無忌憚,無所不為矣。”*《舊報新抄:地保》,《申報》1940年8月1日,第12版。這種不良現象之存在,“大之足以妨得國策的貫徹,小之亦使地方有志人士不屑置身于地方政治,人才既不肯到鄉鎮,于是基層政治永無起色。”*《社評:改進地方基層政治》,《申報》1943年3月14日,第2版 。
國民政府推行地方自治,其目的就是要求地方人民處理地方事務,以避免上述問題的再度發生。然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如果想讓如此眾多的民眾處理自己的事務顯然不切實際,這就需要“少數思想清楚、精力強健的現代化人物”為之代表。但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民眾智識水準“普通低淺,知識青年競向城市活動,鄉村社會的文化和經濟都操縱在土豪劣紳的手里,人民自身對自治漠不關心,一切舊勢力的活躍足以窒息這萌芽的自治運動而有余。所以過去推行自治,其結果不出二途:或是成立了機關,但無實際活動,所謂自治,名存實亡;或是自治機關由土豪劣紳支持,使得土豪劣紳的統治合法化、衙門化。在老百姓看來,根據自治條則產生的鄉長、區長,仍不過是昔日之保正、團總等等的化身而已。”*陳柏心:《完成地方自治的途徑》,《現代讀物》1939年第4卷第4期,第40—41頁。同時上級委派的鄉保長,“常以政府一員的姿態出現,一切政令設施,都是自上而下,一味以命令為主,而不問民情的是否適合,只求功令的敷衍,而不顧民眾的要求如何,因是要想動員而不能徹底,即令努力推行,亦無法獲得置效。”*秦柳方:《鄉村長實行民選問題》,《國民公論》1940年第4卷第8期,第271頁。加之“近年以來,差傜繁興,鄉務特忙,支應軍差,尤為難事。稍有不周,便遭凌辱,因之對鄉長一職,率多裹足不前,視為畏途。”*郭昌齡:《關于鄉鎮長》,《鄉村工作》1937年第6期,第18—19頁。“稍有資產或稍有知識者,皆逃避一空,不肯承乏。而夤緣得此者,又擅作威福,以土皇帝自居,一保或一甲之人,皆不得聊生。”*成駿:《湖北農村雜寫》,《申報》1936年4月8日,第8版。有見于此,國民政府決心借用民選模式以改良已處劣化的鄉鎮保長,并認為民選的鄉鎮保長或能“充分代表民意,深知民間疾苦,為民眾所擁護,受民眾的愛戴,動員工作固能順利進行,民力也易于發揮”⑦秦柳方:《鄉村長實行民選問題》,《國民公論》1940年第4卷第8期,第271頁。。
三
綜上所述,國民政府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委派轉變為選舉,其目的固然是為了爭取輿論民心、迎合憲政之需;但同時亦想借用民選的方式徹底清除原有委派之鄉鎮保長的種種弊病,為鄉村社會治理添加一種新的領導力量,并在此基礎上緩解民眾與鄉鎮保長之間的緊張關系。然而,國民政府的這一政治理想能否實現,面對國民政府功利激進之態度,時人評論稱:“選舉的意義在求才,而不在騖名,粗制濫造的選舉,只在騖名,而非求才。欲速則不達,這句話固然可以作為故意拖延選舉的借口,但無計劃、無步驟的選舉,適足以僨事。”*王蘊卿:《論民選保甲長之重要性》,《民治》1945年第1卷第3—4期,第7—8、7頁。事實證明,上述說法實非危言聳聽。自1946年實施鄉鎮保長民選以來,“曾經造成許多使人啼笑皆非的場面。假造民意的選舉票一大把一大把塞進選舉柜,兩個集團因為勢均力敵,竟因此造成團毆的場面。”之所以會出現如此怪現象,是因為“中國人民一向不習慣民主國家人民應享受的權利,對于民意選舉向來更漠不關心。因此,雖然政府已經把選舉權交給人民,但人民大多都沒有好好地運用這個基本權利。”*十郎:《談“選舉”》,《申報》1947年7月12日,第2版。正是源于上述問題的諸多制約,甘肅省政府在內政部的不斷催促下倉促實行普遍民選,一開始便遇到了諸多困難。
第一,民選鄉鎮保長對于偏僻閉塞的甘肅鄉村來說簡直是“千年未有之巨變”,毋庸說普通鄉民,即使縣政府行政人員對于民選之事亦聞所未聞,試辦之初,未免疑慮重重。加之民選初行之時,制度本身的不健全及朝令夕改,更使執行者茫然若失。時人評論稱:“十年以來,許多人感覺盡管鄉、鎮、村、閭、鄰等編制已經改名為鄉、鎮、保、甲,但是據行政當局的報告,除了廣西省已普遍實行保長民選,安徽省已開始試行民選保長而外,其余各省縣市的保長,不免大多數仍由政府委派,即使有的省份實行民選鄉鎮保長,仍不過是選出加倍人數呈送政府擇委。”⑩王蘊卿:《論民選保甲長之重要性》,《民治》1945年第1卷第3—4期,第7—8、7頁。甘肅省在試行民選鄉鎮保長時情形亦是如此。
第二,甘肅地處西北邊陲,地瘠民貧,教育文化極為落后,要想在這一鄉村區域選拔出一批品能兼優的鄉鎮保長,無疑于水中望月。因此甘肅各縣之民選鄉鎮保長雖然表面上實行民主選舉,但實際上卻是“換湯不換藥”,民選的鄉鎮保長仍大多由原來的鄉鎮保長充任。例如1946年莊浪縣政府代電稱:“本縣民選鄉鎮長于奉令辦理后,即發動黨團各學校力量,宣傳鼓勵地方公正士紳及具有革命性之有為青年踴躍競選,同時一面通告登記候選人并公布選舉日程,一面根據頒發注意事項訂定各鄉鎮應行注意事項、選舉日程表,并制發各項應用表冊、選舉票等分飭各鄉鎮公所遵照,積極準備,擴大舉行。自八月十六日開始選舉,由縣長并派員會同黨團參議會負責人依照日程表親赴各鄉鎮監選,及函請各鄉縣參議員就地參加指導選舉,截止本月二十日,本縣維新、臥龍、寧陽、安東等四鄉鎮長副已依法選出。經核當選人均為青年黨團員,悉曾任公教人員多年,資歷多佳,尚屬合法。至選舉時會場秩序嚴整,并因擴大宣傳,人民情緒頗為興奮。”*《莊浪縣政府快郵代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4-113。不難看出莊浪縣政府對于此次民選鄉鎮長贊譽有加。然而,莊浪縣民選的鄉鎮長果真是當地有為青年?莊浪縣長陳永康在隨后的呈電中道出了實情:“本縣定于八月無法開始選舉鄉鎮長,據臥龍等鄉鎮民代表會呈請,以鄉鎮長責繁任重,本鄉人才缺乏,稍不勝任,貽誤實深,為利公便民計,擬懇仍選舉現任鄉長連任。”*《莊浪縣呈甘肅省政府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4-113。對此甘肅省政府認為,“查籍隸本鄉鎮之現任鄉鎮長原有被選權,如果當選,自可連任”*《甘肅省政府代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4-113。。由此觀之,迫于政治、經費、人才等諸多因素困擾,20世紀40年代甘肅各縣所謂的鄉鎮保長民選其實仍不過是新瓶裝舊酒,名異而實同。
第三,甘肅各縣鄉鎮保長民選的主動權和決定權始終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由于民國時期的甘肅鄉村社會仍然延承著封建時代的鄉村治理模式,士紳階層與知識份子掌控著鄉村社會的政治、經濟命脈,在中國鄉村社會的等級體系中,無論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是委派還是選舉,其結果均將代表少數精英的利益。但事實上,鄉村精英的利益并非與普通民眾的利益完全相悖。首先讓我們看一看當時民選的鄉鎮保長是何許人?1946年4月據皋蘭縣北辰鄉民稱:該鄉“第五保第八甲民戶張子述者,出身軍人,前在國民革命第五路軍總司令部屬充軍,做事勇敢,忠誠樸實,為長官素所贊許者也,時賜獎章,以資其功。后因作戰代傷,下伍旋里,自該張某到吾鄉之后,仗義疏財,專為慈善,親老扶幼,言辭和悅,拯危救困,本鄉長幼男女勿不欽敬感懷,誠吾鄉公正之偉人也。曾在趙老灣募緣化布,修建廟宇,又在溝中募建佛堂,見義勇為,雖死不辭。吾鄉去歲大旱,餓殍盈野,張某即以身作則,辦理荒旱,親至鄰華堂處,不非口舌,不辭勞苦,敦請鄰君施舍白米百石,每人分散二斗,此情此德,不啻再造。所作之善,不能盡述,張某一身清白熱心,赴湯蹈火,亦所不避,誠吾鄉貧民之救星也,是以公舉。”*《呈為公舉得人忠誠樸實服務熱心公眾選舉得專委任事》,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4。可見該鄉所舉之張某不僅擁有充軍的經歷,殷實的家資,而且在當地也有一定的聲望。這種鄉村精英不僅能夠得到鄉民的普遍認同,同時也能得到鄉村士紳和政府的信任。透過甘肅鄉村社會的政治實景,我們仍能看到這樣一種場景:雖然歐風美雨飄蕩在中國社會已近百年,但地處西陲的甘肅鄉村仍然延續著傳統的經濟形態和生產方式,制度的變革僅僅改變著基層政制機構的名稱,卻未真正觸及到鄉村社會治理的內核和本質。在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形態下,普通鄉民與鄉村精英的利益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吻合的,這種利益的吻合亦決定了民選鄉鎮保長應有的標準。
相反,如果當選的鄉鎮保長不能符合鄉村社會的這一標準時,無論是鄉村士紳、知識階層,還是普通民眾均會伸出彈劾之手。1946年8月當隴西縣云田鄉民得知該鄉民選鄉長為雷虎卿時,即聯名呈請甘肅省政府稱:“竊查云田鄉奉令選舉鄉長,結果雷虎卿為鄉長,究其原因,地方劣紳李馪勾結趙鳳翔及雷虎卿三人大花金錢,設擺酒宴,邀本保鄉民代表活動鄉長。唯查該代表多系先年保長,劣紳李馪任意挑撥,故不以民眾意見,而以狼狽為奸,漁利自肥,失了民意主旨,誤了選舉規則。又查趙鳳翔、雷虎卿皆先年鄉長,種種貪污案件民等告發縣府及專署者不勝枚舉,即被勒令停職,縣府有卷可考,迄今懸案未結,依法不宜當選。再查李棟、李馥品學兼優,秉公正直,人地相宜,按照當選法規,李棟為正鄉長,李馥為副鄉長。”*《為呈報隴西縣云田鄉選舉鄉長雷虎卿懸案未結依法不宜充任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51。云田鄉中心國民學校校長唐仲藩,教員雷霖、李彬、李馥、王俊杰等亦呈報甘肅省政府:“竊查隴西云田鄉選舉鄉長,結果雷虎卿為正鄉長,李棟為副鄉長。唯查雷虎卿曾任過云田鄉鄉長,民眾多不滿意,言舊案未結不應當選,但舊案是否結束,職等不明,邇來本鄉一般民眾情形風潮迭起,大不安寧。職等因雷虎卿人地不宜,上恐誤公,下怕累民,依照地方實際情形與民眾意念,李棟為正鄉長,李馥為副鄉長,方可上不誤公,下不累民。”*《為懇請隴西云田鄉選舉鄉長實情伏乞核準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51。從雷虎卿個人簡歷看,雷雖然擔任過鄉長、聯保主任,并取得了甲乙兩種公職候選人資格*《甘肅省隴西縣鄉鎮長選舉當選人名簿》,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51。,其職位亦得到上級行政部門的庇護,但由于其行為已經背離了該鄉士紳及民眾的普遍認同,最終仍逃脫不了“并案核辦”,改選下課的政治命運。
第四,國共內戰爆發后,田賦兵役日趨加重,鄉鎮保長開始在上級命令與民眾抵觸間艱難斡旋,一些深得民望的鄉鎮保長鑒于形勢險惡,均紛紛請辭。就以隴西縣鄉鎮長更迭為例。1947年5月21日隴西縣萊子鎮鎮長伍昌麟辭函稱:“查本鎮鎮長一職,前由第一期代表會選昌麟接充,現已將近二載之久,任勞任怨,奉公守法,未能有益于桑梓,亦未貽害于地方。昌麟本應用全力暫將應付,但近月內身得惡疾,精神錯亂,認事不清,反輕反重,若不及早辭卸,不免上誤下累,貽害終身,相應函請,查照轉報縣府另選賢達接替,推進一切,則昌麟感德無涯矣。”*《呈轉本縣萊子鎮長伍昌麟辭職請核示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51。9月16日隴西縣政府稱:“查四月份本縣鄉鎮長副動態情形計,紫來鄉副鄉長顏希賢被選為鄉民代表,首陽鎮長原祥麟病故,復興鄉副鄉長汪啟齊因事他往,昌谷鄉長羅錦山因推動工作困難,碧巖鄉副鄉長張希漢因就學深造,鄉長包廷選被選為鄉民代表,均經先后辭職。”*《電復紫來鄉副鄉長顏希賢等辭職案情形請核示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51。事實上,這種情形不惟甘肅獨有。1946年1月張曉崧在談論上海整編保甲意義時稱:“本市整編保甲工作自本月15日開始以來,已歷數日,一般情形,堪稱良好,惟有一部分市民被任為甲長或保長時,頗多不愿就職。”*《張曉崧談整編保甲意義》,《申報》1946年1月19日,第2版。鄉鎮長的頻繁更迭不僅加劇了資金的浪費和社會的紊亂,同時也造成了鄉鎮保甲機構的運轉不良,鄉村社會陷于權力的真空狀態。
鄉鎮保甲機構是國民政府行政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權力深入鄉村社會的重要一級,也是國民政府加強基層社會控制的橋梁和紐帶。如果說20世紀40年代鄉鎮長的處境艱難,那么保長的處境則更如水火。因此在鄉鎮長紛紛請辭的同時,無人應選保長遂成為保長選舉的瓶頸。1949年4月28日皋蘭縣中正鄉鄉長王子豐報稱:“該鄉第十保保長管意,自本年二月十六日當選,迄今抗不接辦,致政令無法推行,附送管意一名,請予法辦。”但管意稱自己“目不識丁,恐有貽誤”,因而請求辭退。經縣政府派員調查稱“中正鄉第十保前次選舉保長實欠合法,茲為解決該保糾紛,免誤要公計,當會同該鄉長于十九日前往該保,召集保民代表管如、劉竹軒及紳耆民眾等七十五人”,重新選舉,“結果仍將管意以六十二票當選為該保保長”。為了能使該保長順心就職,皋蘭縣政府決定“管意第一次被選為保長,因系前任鄉長陳森章主持監選,確實不合選舉保長法令手續,該鄉長王子豐不查明原委,竟勒令管意接充保長,如此處理,殊屬失當。除將該鄉長王子豐記大過一次,以示懲戒外,已令飭該新任保長管意即日接辦。”*《據本縣中正鄉長王子豐報以新任保長管意抗不接充一案處理經過情形電請核備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6。從上述材料中不難看出,無論選舉手續是否合法,管意當選保長并非心甘情愿,然迫于上級政令及行政處罰,管意就職也只能是無奈之舉。
既然民選保長已經成為一種形式,那么被選的鄉鎮保長素質則不言而喻。1947年1月,據靖遠縣大廟鄉鄉長杜興泰稱:“查上年本鄉當選之保長副確能得到民眾信仰,辦事穩練,成績較好者固多,而有少數之保長副以近來對保政之不能推行而致落后者有之,因無辦事能力已失保民素望,經保民大會開會罷免者有之,此種情形實由于初次選舉,民眾尚不明瞭選舉意義,以致當選者未得其人。經查應予更換之保長副,需要另行選舉精干者接充,以期推行保政效率之易速,以故擬據保民大會之要求,飭即另選。”*《為呈未屆期滿之民選保長副如遇辦事不力或失民望時如何辦理請鑒核示遵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6。然而,這種稍現規則的民選制度在1947年以后開始發生質的改變。內戰爆發和田賦兵役的持續加重將普通民眾逼到了生死邊緣,淪落為國民政府征兵納稅的鄉鎮保甲機構開始成為民眾發泄仇恨的對象,鄉鎮保長不再成為鄉村精英競逐的對象,即使普通鄉民對于競選該職亦避猶不及。然而,為了完成上級政令,各縣政府不得不按照規定選舉出足夠數量的鄉鎮保長。正是在這一特殊的時境交替中,各地土劣分子乘虛而入,鳩占鵲巢。據稱貴州某縣長甚至“大批出售鄉鎮長,以三堂鄉長而言,包張爭贖,竟出資達六百萬元;勝龍鎮鎮長出資四百萬元;其余二三百萬不等,最低亦需百萬元。”*《某縣長大賣鄉鎮長》,《貴州民意》1945年第1卷第4期,第18頁。本欲改善鄉鎮保長素質的民選制度此時卻成了各地土豪劣紳發財致富、爭權奪利的護身符。
面對鄉鎮保長素質的嚴重劣化和欺壓民眾之情事接連發生,鄉鎮保長與民眾之間的矛盾開始加劇,甘肅省政府在無力提高待遇、加強培訓的情境下,唯有一途便是加重對不稱職之鄉鎮保長的懲處。1947年1月21日甘肅省政府規定:“民選保長副如有辦事不力或已失民望情事時,除所處保民大會得自動提議予以罷免外,該管鄉鎮長并得依‘修正各縣市辦理地方自治人員考核及獎懲暫行條例’第三條及第六條之規定,按其情節酌予懲處。”*甘肅省政府代電:《電釋民選保長副懲處辦法》,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6。然而,正可謂“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甘肅省政府對于鄉鎮保長的懲處既不能制止保長的頻繁辭職和拒不就任,亦無法提高當選保長的個人素質,鄉鎮保長的民選模式并未給國民政府的鄉村社會治理帶來更高的效率。
隨著戰爭的持續進行和田賦兵役負擔的不斷加重,鄉鎮保長與普通鄉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詆毀、呈訟鄉鎮保長的案卷多如牛毛。如皋蘭縣八堡鄉民眾匿名控訴該鄉鄉長施子寅,稱其“本無鄉長之資格,更非民眾之悅服,不過此次經選鄉長者,純系一種運動手段。況我八堡鄉共分七保,心悅誠服之人不過三四人也,其余民眾均在敢怒不言。政府此次民選鄉長,一為地方治安,二要減輕民眾負擔,方合政府法令與地方治安之條例。此人做事心似狼毒,視財如命,與地方不為無益,反而害之。”因此請求甘肅省府“戀念苦情,以救民命,速派賢員接替”*《呈為減輕民眾負擔更換棘手鄉長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6。。靖遠縣大廟鄉民匿名控訴該鄉鄉長楊興泰,稱其“為人狡詐,武斷鄉曲,吸食鴉片,蔑視法紀,種種劣跡,筆難盡述。前于民選鄉長時,曾以磕索人民血汗之資——前為本鄉副鄉長,賄買各保之鄉民代表,大肆活動,選伊為鄉長,強奸民意,把持鄉政,殊失‘民主’之至意。所可痛者,該鄉長身為公務人員,而竟吸食鴉片,誅求人民之血汗,供一己之享樂,每至各保巡查,各保長深以大煙之無法供應為苦。”因而要求甘肅省府將其徹查究辦,以維法紀,而維憲政*《為吸食鴉片賄選鄉長把持鄉政魚肉人民祈鑒核徹查究辦以肅法紀而維憲政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15-15-666。。面對鄉鎮保長與鄉民矛盾的不斷加劇,為了維持鄉村社會的穩定,完成戰亂年代地方自衛及征兵征糧等工作,甘肅省政府對于上述民眾之訴訟,一般采取“匿名稟告,應予不理”的態度而匆匆收場。這一方面表明隨著中國國內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動,甘肅省政府已無暇處理鄉鎮保長的優良寡窳,維持現狀成為這一時期甘肅省政府的最佳選擇;另一方面甘肅省政府也認識到戰爭年代鄉鎮保長的特殊使命與普通民眾利益之間的尖銳矛盾,處于夾縫中的鄉鎮保長成為民眾控訴攻擊的對象已成見怪不怪的平常事。
四
面對鄉鎮保長民選而引發的諸多問題,1947年7月甘肅省鎮遠縣縣長崔汝峻呈報稱:“查現值剿匪緊張之際,軍差供應日益浩繁,本縣現任民選鄉鎮人員多不理事,遇事敷衍諉卸,貽誤匪輕,為求政令運用靈活配合軍事之需要,計擬請在綏靖期間,凡鄉鎮人員因故去職或開缺時,準由縣府暫派干員代理,一俟軍事平定再行補行民選。”*《據鎮遠縣政府電請綏靖期間鄉鎮人員去職開缺準由縣暫派員代理一案請核示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對于崔的建議,內政部認為“與規定不合,未便準行。如民選鄉鎮長因故去職或開缺時,得由原選舉之民意機關依法改選或選補,并報民政廳查核,以免藉口情形特殊,任意由縣遴員派任,滋生流弊。”*《內政部復甘肅省政府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可見在內戰初始,民選鄉鎮保長雖給國民政府控制鄉村社會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但基于對憲政和地方自治的長遠考慮,國民政府仍然不想在此時脫掉為其鄉村社會控制披上的民主外衣。
然而,國民政府的這種堅持并未延續多久,隨著國共內戰的全方位展開和國民黨軍隊的不斷失利,使得國民政府對基層社會的汲取愈來愈多,而民選鄉鎮保長在諸多因素的困擾下已無法完成戰爭年代對人力、物力和財力的大規模征運。1948年6月甘肅省政府電呈內政部稱:“1.本省各縣市局鄉鎮長系三十五年七月起辦理民選,依照縣各級組織綱要第三十三條、市組織法第三十四條之規定,區鄉鎮長任期定為二年,瞬將屆滿,自應分別改選。為行憲政府業已成立,省縣自治通則即將頒布,此項通則公布后,縣以下各級自治機構均將全部改組,預計時日至多當不出一年。區鄉鎮長如在此時改選,將來自治通則頒行后,在新選之鄉鎮長任期未滿前又須改選。值茲動員戰亂時期,安定為先,人事變更頻繁,不特影響業務之推行,尤恐因選舉之爭競滋生事端,似應重加考慮,酌予變通,以期法令事實,兼籌并顧。2.在此過渡期間,各縣市局鄉鎮長任期屆滿者,擬援照省縣參議員延長任期例,一律延長至自治通則頒布后,區鄉鎮自治機關改組成立后,正式區鄉鎮長選出之日為止。”*《民政廳長馬繼周致甘肅省政府代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對于甘肅省政府的這一提議,內政部認為不可,令其“于期滿后依法改選,不得延長”*《內政部函甘肅省政府代電》,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但此時的甘肅省政府迫于形勢之嚴峻,已不再遵循內政部的意見,而于同年7月訓令各縣市局長、專員稱:“各區鄉鎮長任期已再電內政部準予延長在案,在未奉令前,各區鄉鎮長任期屆滿者一律暫緩改選,仰飭遵照。”*甘肅省政府:《區鄉鎮長任期屆滿者暫緩改選》,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
雖然甘肅省政府已對內政部的政令進行了變通處理,但戰爭年代鄉鎮保長的馭重角色已不容其朝選夕辭,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選舉轉變為委派再一次成為這一時期甘肅省縣政府的共同意愿。1949年5月,甘肅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高增級、天水縣縣長高德卿、秦安縣縣長杜凌云、清水縣縣長楊貽書、禮縣縣長閻廣、通渭縣縣長李志謨、甘谷縣縣長陳永康、武山縣縣長柴慶榮、西和縣縣長張孝友、兩當縣縣長劉世英、徽縣縣長胡晉一聯名提議“鄉鎮保甲長暫時采用派任辦法”。其理由是“民選鄉鎮保甲長施行以來,利弊互見,如選賢與能、推行政令、維護桑梓、不負民望者固多,其有文化閉塞、知識水準低落之區域,礙于法令,限于人才,以削足適履之拙策,奉行民選之功令,非特不堪稱職,且足以誤國誤民。值茲非常時期,為應付萬一,配合上級政府之要求,對民選鄉鎮保甲長亟應予以調整。”*《鄉鎮保甲長暫時采用派任辦法案》,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其調整辦法為:“1.民選鄉鎮長經縣府考核如有才不勝任,貽誤要公者,準由縣長撤換,報請省府核備。2.如本鄉無適當人選,準由縣長另派其他鄉鎮人員充任。3.各鄉鎮保甲長由各鄉鎮保長切實考核,其不稱職者由各鄉鎮長另派其他公正精干富有熱情人士充任。”②《鄉鎮保甲長暫時采用派任辦法案》,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
對于上述提議,其他各縣亦隨之附和。如西和縣政府呈電稱:“查本鄉鎮長實行民選以來,固有選舉得人,工作順利者,而因選舉造成地方派系意見分裂,糾紛迭出者亦復不少。鄉鎮長當選后應付人事足感困難,每一工作輒有人出而反對,藉端攻擊,希圖再選,且有鄉鎮長希求人民之所好,不顧國家之大計者,以致影響工作效率甚大。值此軍事時期,地方事務繁多,實有改選為派之必要。”*西和縣政府:《鄉鎮長之選舉改由縣政府委派任用案》,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通渭縣縣長李志謨稱:“鄉鎮保長實施民選以來,所有地方自治及政府委派事項無形降低效率,揆厥原因,多由代表會代表偏重情感,所選出之鄉鎮保長間有不合政府選賢與能之意旨,以致能者退藏,庸碌當道,對一切政令之推動,率多遲誤。值茲非常時期,似應權衡本省實際需要,將鄉鎮組織予以變通,以求切合。”*《各縣鄉鎮保長擬將民選改由政府遴派以增效率而利政令案》,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莊浪縣縣長嚴德駿稱:“本省文化落后,人民水準、文化水準較低,一般下級工作干部選任困難,尤自民選鄉鎮長以來,常因人事不宜或因辦事能力太差,對工作不明緩急,屢有遺誤。茲當戒嚴期間,鄉鎮工作應以精強干練者充任,故民選鄉鎮長有酌改由政府委派之必要。”*《為戒嚴期間民選鄉鎮長酌量改由政府委派以利工作由》,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華亭縣縣長李曉白稱:“本縣系接戰地區,軍差繁重,工作緊張,選任之鄉鎮長礙于情面,辦事敷衍,工作推進至感困難,亟應由縣府遴派干員暫行接辦,以利事功。”*《接戰地區鄉鎮長擬請一律派任以利行政案》,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面對各縣之提案,甘肅省政府認為:“1.民選鄉鎮保長在現行法令未變更前未便遽行廢止,惟有不能勝任情事,為適應當前非常情勢,便利縣政之推行,自應于法令事實兼籌并顧之下,酌予變通辦理。2.民選鄉鎮保長如確有不能勝任情事,得予免職另選,報府核備,但在接戰地域各縣得由各該縣府暫行遴派妥員代理,仍將代理人員姓名、資歷報府備查。”*甘肅省政府:《核飭行政院會議有關民選鄉鎮保長改由縣政府委派》,甘肅省檔案館藏,檔號:4-8-622。
由上可知,近代中國連綿不絕的戰爭使得鄉村社會青壯年勞力極度缺乏,而勞力的缺乏和社會的動蕩進一步加劇了鄉村社會的貧困。在這個人力、物力極度缺乏的年代,國民黨政權為了維持戰爭機器的運行,只能任由鄉鎮保長對鄉村社會進行無休止的索取。然而,這種索取遭到了鄉民們的拼死抵制,而鄉鎮保長的頻繁更迭更使國民政府的征運計劃屢受挫折。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基層社會的控制與索取,同時避免因鄉鎮保長頻繁更迭而引發的諸多問題,甘肅省政府在內戰行將結束之時最終決定將鄉鎮保長的產生模式由選舉回溯到委派。鄉鎮保長產生模式的回流,在一定程度上隱現出國民黨政府推行基層民主的限度,盡管這種限度的背后隱藏著諸多無奈。誠如蔣廷黻在談論改革地方行政時所言:“健全行政不外組織緊湊、運用靈活、職權相當;人才得宜、才盡其用;經費充足、支配合理。我國地方政府對此三方面殊欠健全。”*《蔣廷黻談改革地方行政》,《申報》1936年4月30日,第6版。正是在政治、經濟、人才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下,國民政府所實施之“地方民選,既無民選制度之前提條件存在,又無民選制度之真正內容,一切還是以一黨包辦作中心,其結果,當然是包辦、操縱、賄選、劫持等怪象也就層出不窮,而牛波馬勃,敗鼓之皮也都成為人民代表,即使有一二正紳,也不外是點綴而已。”*黃道庸:《現行地方民選制度平議》,《民主星期刊》1945年第8期,第2頁。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南京國民政府甘肅保甲制度與基層社會控制研究”(13BZS061)的階段性成果。]
責任編輯:汪謙干
A Paradox of Democratization:the Democratic Elections of Town-chief in Gansu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0s
LIU De-jun
(School of Modern China Research,Shanxi University,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herited the triple demise of Sun Yat-sen and began to impl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under the public pressure.In order to make the preparation of constitutionalism democracy,National Government decided to turn the appointment system into election system for finding qualified town-chief.In 1945,Gansu also started to elect town-chief because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s repeatedly urged.Gansu’s ground is remote in the northwest China,economic situation and rural elite are extremely lacking,people’s thinking was backward,therefore town-chief was hardly elected in these small towns and villages.Coupled with the outbreak of civil war and increasing land tax for military service,it further exacerbated the conflict between villagers and town-chief.The position of town-chief was no longer contested objects for the rural elite.It was not uncommon town-chief resigned the position or was forced to work.They had wanted to use this elec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own-chief,but it became imbalance of rural power structure.Facing with unqualified of town-chief and disordered in the towns,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was forced to appoint the leader again at the end of the civil war.With the failure of election system for town-chief in town,it declared that it was just the democratic illusion at last for the Government which were in the adverse circumstances trying to save the reputation of nationalist party.
Key words:The period of National Government;town-chief;democratic elections;Gansu Provincial Government
作者簡介:柳德軍(1979-),男,甘肅靜寧人,山西大學近代中國研究所講師,歷史學博士后。
中圖分類號:K265.9;K26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05X(2016)01-008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