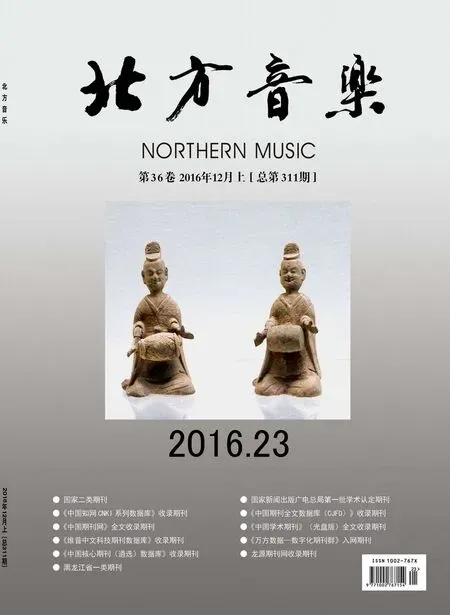用舞蹈生態學理論分析舞蹈劇目《走西口》的編創
魏亞男
(山西大學音樂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用舞蹈生態學理論分析舞蹈劇目《走西口》的編創
魏亞男
(山西大學音樂學院,山西 太原 030006)
舞蹈劇目《走西口》作為有深厚文化歷史背景鋪墊下的產物,其舞蹈編排的素材,技法與藝術表達,無一不運用對民族舞蹈文化發展規律的探索。它巧妙的結合舞蹈生態學中社會學、心理學、美學、生態學、藝術學等多種門類的相關學科,通過對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并利用各種舞蹈生態因子和舞蹈生態項,創造意象,達成舞意,成為優秀的舞臺舞蹈作品。
舞蹈生態學;舞蹈編創
一、《走西口》中的舞蹈生態學
在舞蹈生態學的理論當中,舞蹈被認為是一種在特定環境中存在的人類有目的的行為。“走西口”的歷史故事為舞蹈劇目的編創背景提供了一個具有社會性的角度,換句話來說,就是舞蹈的編排設計依靠著這個獨有的文化背景作為表情達意的大環境。劇目《走西口》的舞蹈情節是通過簡單的兩個舞蹈形象反映其背后強大的藝術生長環境和當時歷史時期的文化藝術內涵。所以說,此舞蹈劇目很大程度上是從舞蹈生態學角度來展現其藝術美感的,他的文化背景也成為了舞蹈編創的主心骨。
“走西口”的歷史起自明朝初年的獨特歷史環境,邊塞軍需吃緊,運費昂貴,明政府鼓勵商人向邊塞運糧,這也是晉商興起的歷史背景。走西口的根源在于內地人口激增導致的人地矛盾激烈,已經超過當時生產力所能承受的水平,這也造就了舞蹈故事情節當中的妹妹幾次心想留下哥哥,但出于無奈哥哥不得不離家求生存的緣故。一個好故事情節的編排一般建立在一個強大的戲劇沖突之上,也就是舞蹈生態學所說的在特定的環境中。人的形體動作作為媒介為的是表達其內心的目的意圖,走西口作為政治家“借地養民”政策的政治手段,將當時大多數的百姓推入這個無奈出走求生的潮流中,其間各種故事的發生發展,使得舞目的歷史沖突達到一個制高點。當然,舞臺作為一個表現歷史片段的媒介,只能以小見大,即簡單又具體的表達一個歷史的點,既能表情達意,又能被大眾接受認同。劇目《走西口》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舞蹈功能而言,《走西口》屬于表演性質的舞蹈。舞蹈表現的是普通百姓生活中的故事場景,具體在一種濃縮與升華的人類情感,不僅具有節奏性,在體態上卻也是動態與穩態的交替,以穩態作為每一個動作的起點與終點,飽含山西民間舞酸﹑嗲﹑扭捏的藝術特點,那種男女主人公之間表情,眼神的變化,加之動作的酣暢淋漓展現二人情誼深厚,不僅很好的刻畫了人物間的情感糾葛,也從側面反映當時的社會背景對百姓生活的負面影響。
二、用舞蹈生態學分析劇目《走西口》
劇目《走西口》可以按照情感線分成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情感鋪墊
舞蹈出場的形態設立在沒有伴奏的背景下,男女主人公在安靜的畫面下牽手上場,妹妹緊隨哥哥的步伐緊扣十指,無一不透露著戀人不舍的真切情誼。簡單的畫面布置,真實質樸的表達著兩人的情感。這里沒有夸張的舞動因子,而是利用了呼吸節奏,將內在情韻快節奏的表達出來,給觀眾一種情結暗示,是對故事情節發展的一種巧妙鋪墊。
這一部分的雙人動作配合多為互相拖拉式等近似于推抱的相對力量的互動。例如,哥哥推著妹妹前行,妹妹用后靠的體態表示不愿分離的場景,其中銜接著跳,轉,翻等雙人技巧串,這樣兩個人互動的情節,正是牽引兩個人關系的線索,動作在依靠間行進,線索不停,關系不斷,且每一段舞動序列都不盡相同,各顯其彰,這里的動作編創利用最基礎的舞動元素,通過間接的敘事與抒情,達到舞動與舞情的形神兼備,身心一致。隨著音樂節奏的不斷加快,兩個人的情感表達不僅限于簡單的相互依賴,此時妹妹動作多使用折,轉等二維舞動,不單是處于同一緯度,利用跳轉與地面的結合,將舞動復雜度提升,從而表現一種內心的復雜情緒和糾結心情。當然,作為山西民間舞的一支,那種全身心的動作線條,夸張大咧的舞蹈序列,穿插以擁抱﹑依靠為線索,展現出一種溫和舒緩的的舞境,也自然而然的生成了“意”與“美”的結合體。
第二部分:情節深化
第二部分開端于舞蹈場面由安靜轉向歡悅的氣氛,音樂節奏由柔美變為靈活多變,其中雙人的技巧展示更快速復雜,花樣多彩,是第一部分的升華,同時也是舞情的升華,是舞蹈劇目的高潮部分,兩個人配合默契,以快節奏的舞動表現這一部分舞疇序列的基本節奏型。其典型性顯要動作部位多為腰﹑胯部的扭動,旋轉,其基本步伐多山西民間舞中的踩﹑踏,特點鮮明突出。
這一部分的編創多以男女主人公的情緒為主線,利用雙人技巧的牽引,加之面部表情的真實再現,入情入景。男主人公的體貼與呵護,以雙臂的開合與各種跳的技巧體現;女主人公的嬌羞與依戀,多以含蓄的手遮﹑擋,身體的三道彎這樣的小舞動展現。舞情展現的合理得當,也為后面結局的突變做好了鮮明對比與鋪墊。
第三部分:情感延伸
高漲的情緒到達頂點后,一般都會呈現下降趨勢的舞臺情感表現。舞目的結束段音樂由歡快變為急促,利用舞動風火輪和涮腰,將肢體大開大合作為情感表現,兩人將舞情線索延伸到極致,運用一切肢體的能動性展現兩人難舍難分的故事情節。這一部分不同于第二部分,它是悲傷到達頂點,合理利用三維空間,將肢體的無盡延展取代舞具的作用,更具說服力,運用肢體協調一切舞意。
三、《走西口》編創中的舞蹈生態學理論
通過對舞目《走西口》的情節分析,可以得出《走西口》的編創是以歷史背景為為宏觀框架,以情節中男女主人公的舞情為主線的山西民間舞類群。我們通過舞蹈生態學中的四大核心元素“形,功,源,域”分析其編創技巧。
(一)形:《走西口》中舞蹈形態分析
舞蹈形態由多種舞蹈因子構成其舞動﹑舞序,進而形成完整的舞目。《走西口》中的舞動及舞序,不僅是由單一的山西民間舞動律而構成形象資料的。直觀而言,作為雙人舞的范例,其“形”大多通過內心的舞情借助肢體的延伸來完成的,編創寫實性強,情節性突出;通過獨特的音樂節奏型烘托舞境,以渲染氣氛,從而突出兩個演員的舞臺表現力,使得其形的藝術內涵不單限于肢體舞動。
(二)功:《走西口》中語言系統功能的構建
一部優秀舞目的完成,一是要看舞體的出色表現,二是要看舞蹈語言在舞臺上的完美詮釋。
舞蹈編創者作為舞體的一部分,他們運用社會文化背景的啟示作用,搜集﹑組合﹑整理﹑編排,以一個突出的舞詞(舞動的外部表現)落實于一系列舞蹈形態,再將其注入舞情,是舞目具有傳情達意的審美作用,并給予它一種特殊的功能——舞蹈語言的表達。《走西口》在舞蹈語言的表達中運用到位,準確。由于它的發生背景具有其歷史獨特性,所以其舞蹈語匯地域性特點較突出,這也為《走西口》的語言系統定了方向,以男女主人公情感深厚卻因現實因素不得不分離的情節為主要情感線,建立了屬于《走西口》的舞疇范圍。
(三)源、域:《走西口》中生態環境的確立
舞目《走西口》中的生態環境,或者說生態系統,有時是決定舞目立意的主要因素,它體現在舞蹈生態學中的“源”與“域”當中,奠定了舞蹈編創的基調。一部優秀的藝術作品,要憑借其表現的生活內涵來彰顯其藝術價值,最關鍵的便是編創的形式與內容。《走西口》作為發生在獨特歷史時期的現實故事,通過史料得出這是政治改革史上的一次重大沖突。舞目的編創正是利用這一沖突,并且對其范圍進行限定,取材自最普通的百姓生活與情感故事,以小見大反映更深遠的社會內涵,使藝術大眾化﹑生活化,審美化,這也成為了形式與內容結合的精妙成品。
四、綜述
《走西口》的編創是舞蹈生態學理論發展的一個良好體現,其中所運用的舞蹈語匯,編創技巧,都是生態學的學術理論延伸與實踐的結合體。舞蹈生態學的不斷發展,再次給每一個新興舞目的素材提取,情節編創以及典型藝術形象塑造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論基礎,為舞者找尋自身內在修養也有一定啟發,也為今后的舞蹈教學提供了豐富的技術性指導。舞蹈生態學將會引領一個新型的藝術創作熱潮。
魏亞男(1993—),女,山西太原,碩士研究生,山西大學,音樂與舞蹈學,研究方向:舞蹈表演與教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