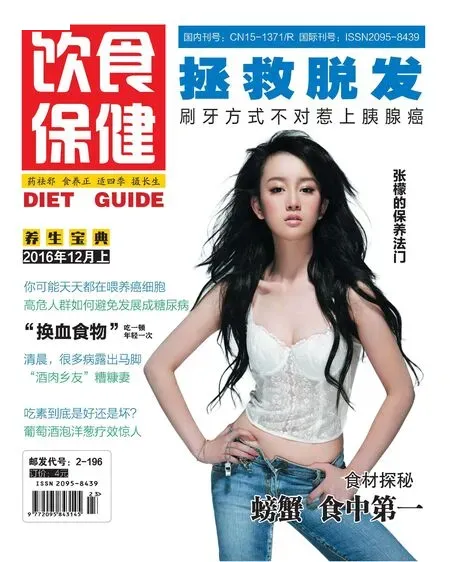晚清餐飲業(yè)的新格局
文/佚名
晚清餐飲業(yè)的新格局
文/佚名
晚清以來隨著商品經(jīng)濟(jì)的活躍,各地區(qū)交往日益頻繁,大量人口流向城市,生活需求趨向多樣化,這給各種菜系的交流和競(jìng)爭(zhēng)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環(huán)境和機(jī)遇。現(xiàn)代廣告、包裝手段的引進(jìn),一批批新式酒樓茶舍的開辦,促進(jìn)了飲食業(yè)的興旺。

老北京前門全聚德烤鴨店老照片
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和經(jīng)濟(jì)繁榮的上海等地薈萃了蘇、川、魯、粵四大菜系,爭(zhēng)奇斗艷,在飯館、酒樓、茶舍密集的大都市首先突破單一的經(jīng)營(yíng)模式,吸收西餐的長(zhǎng)處,對(duì)中餐進(jìn)行改良,開創(chuàng)了飲食經(jīng)營(yíng)的新格局,這一新格局又?jǐn)U大了人際交往和新風(fēng)尚的傳播。
海派菜的興起與上海大都市的形成相得益彰。海派,本是指上海藝術(shù)界新流派,它以吸收融會(huì)其他藝術(shù)形式豐富京劇的表演而見長(zhǎng)。由于京派長(zhǎng)期居于正統(tǒng)的地位,所以把這新流派稱為海派,最初還含有某種貶意。其實(shí)海派并不局限文藝界,也是一代新興城市的社會(huì)風(fēng)貌,在廣大居民的物質(zhì)生活中有生動(dòng)的表現(xiàn)。海派菜系是海派文化滲入民眾的生活方式,并構(gòu)成海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海開埠后,中外商人云集,飲食業(yè)迅速發(fā)展,有上海菜館一二百家,到20世紀(jì)初已是遍地開花。
海派菜的特點(diǎn)是善于吸收各家之長(zhǎng),它以水鄉(xiāng)的蘇式菜和海濱的寧波菜為主,兼融本邦菜與風(fēng)味菜于一爐,創(chuàng)造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品種,在操作方式和調(diào)味用料方面都有改進(jìn),例如用西式方法烹制昌魚、吉利明蝦,既保持了西式菜的鮮嫩,又有中國(guó)菜的入味,這比一般的西餐更適合中國(guó)人的口味。別具一格的“和菜”更是上海餐館的獨(dú)創(chuàng),它把冷盤、熱菜、大菜和湯水組合在一起,按檔次分組配套供應(yīng),價(jià)位可高可低,既有實(shí)惠又不少花樣,從而滿足了各種層次的市民需要。
快餐式的便飯經(jīng)營(yíng)有多種形式,如三餐可外送的包飯作、露天的飯攤、串街走巷的飯籃等。在大眾消費(fèi)中出現(xiàn)一批物美價(jià)廉的海派風(fēng)味菜如肉炒百葉絲、清炒鱔糊、腌篤鮮、草魚粉皮等,還有一種蓋澆飯,在飯上澆上帶湯汁的時(shí)菜,按份出售,貧富皆宜,還有各式炒飯、炒面、生煎饅頭等等。中餐、西餐、名菜、家常菜異彩紛呈,平民百姓的應(yīng)季時(shí)菜月月翻新,上海因此被譽(yù)為是“吃的世界”。
中國(guó)人本是善于吃、精于吃的民族,但在這吃的世界里從明代以來就有一股為了滿足口腹之欲而不擇手段虐待動(dòng)物的現(xiàn)象,古人稱為“虐吃”,如炙甲魚、啖猴腦、烙鵝掌等,間有反對(duì)的,也很微弱。難能可貴的是,在清末民初的上海民謠中就有善待動(dòng)物的呼聲,一首《田雞怨》道盡了田雞的哀愁。
與上海鄰近的南京菜、淮揚(yáng)菜也受此影響,南京的金陵春模仿上海老一枝春,淮揚(yáng)菜,融匯南方的鮮脆甜嫩和北方的色濃、偏咸,在不同程度上做到中西兼味,南北相宜。尤其是時(shí)令水鮮的烹調(diào)鮮嫩清醇,淮揚(yáng)菜肴用料的規(guī)矩是,醉蟹、風(fēng)雞不過燈(節(jié)),刀魚不過清明,鰣魚不過端午。取料精良,刀工細(xì)密,一條魚可以整用、也可以切成塊、片、絲,剁成茸,頭、尾、中段、肚、腸、肝、舌、皮無不可烹制成佳肴。配菜講究色調(diào),春季多秀色,夏季主清淡,秋季多絢麗,冬季主濃彩,美味還配以栩栩如生的花卉、魚蟲、人物的鏤刻,色香味俱備,著名的蟹粉獅子頭、拆燴鰱魚頭、菊花青魚、翠珠魚花、清煮干絲等等都膾炙人口。這些上品菜肴不論在大館子還是小館子,都有檔次不同的制作,所以海派菜并非都為富人享有,它在制作上的精致化和大眾化這兩方面都有相應(yīng)的發(fā)展,這是晚清市民飲食的一大變化。
北京菜的制作素以老字號(hào)著稱,六必居的醬園創(chuàng)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王致和在康熙十七年(1678),烤肉宛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天福號(hào)的肘子始于乾隆三年(1738),月盛齋在乾隆四十年,鴻賓樓建于咸豐三年(1853),全聚德在同治三年(1864)。著名的飯館有八大居,八大樓,如廣和居、同和居、和順居、恩承居、福興居、春華樓、安福樓、正陽(yáng)樓、致美樓等。這16家飯館中魯菜館就有13家之多,魯菜中又分膠東(東派)和濟(jì)南(西派)兩派,東派注重本味,西派專長(zhǎng)厚味,兩派都以湯鮮味美見長(zhǎng),在爆、炸、扒、燒、熘中兼有脆嫩清香的特色。京味菜中清真菜別有風(fēng)味,其以回民菜為主,兼收其他菜系的制作方法,推出清真和菜系列,有八大菜、八小碗、十六碟之說,高中低檔俱全。但是與南味食品北上相比,京味菜南下而成功的并不多,這與經(jīng)濟(jì)中心南移不無關(guān)系。
京味菜的改良也具有平民食品精致化的特點(diǎn),以炒肝為例,它本是白煮的豬下水,這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家常菜,后經(jīng)《北京新報(bào)》負(fù)責(zé)人、美食家楊曼青的改進(jìn),精心烹制,用醬色勾芡,并請(qǐng)著名藝人捧場(chǎng),打造了一個(gè)全新品種的小吃。北京平民飯館有一個(gè)特殊的名稱,叫“二葷鋪”,即只售兩種葷菜:豬肉或羊肉;或是肉與下水。
京城是首善之地,傳統(tǒng)的飲食風(fēng)俗有根深蒂固的基礎(chǔ),民間專操紅白喜事的“大棚廚子”,在民眾中的名聲不在大飯店、洋酒樓之下。為了保持與同行的競(jìng)爭(zhēng),廚師中形成地域性的組織和一些特殊的幫規(guī)行話,如油稱“漫”,香油即香漫;糖稱“勤”,紅糖即紅勤;醬油稱“沫字”,黑醬油即“黑沫字”;鹽稱“海潮字”;即使簡(jiǎn)單的數(shù)字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也用“日、月、南、蘇、中、隆、星、華、彎”來代替,如要買35條魚,就說成“混水字南中著”。廚師進(jìn)了大棚,眼觀六路,耳聽八方,隨時(shí)用行話與伙伴傳遞信息,如說一句“漫大聯(lián)兒浪蕩著點(diǎn)兒”,就是“炒這個(gè)菜油加大著點(diǎn)兒”;說一句“漫大聯(lián)沫著點(diǎn)兒”,就是要“這個(gè)菜油小著點(diǎn)兒”;如說“這個(gè)人可婁”,就是說“這個(gè)人狗狗松松”,意思對(duì)這人要小心點(diǎn)兒;廚師若要大便了,說成“吊橋”,小便說成“碎呼碎呼兒”,據(jù)說這是為避開主人的刁難和趨吉避兇。還有什么祭灶吃會(huì),拜師儀式,茶館人市(勞務(wù)),都有成套的幫規(guī)行話,簡(jiǎn)直是一個(gè)小小的獨(dú)立王國(guó),由于缺少文字記載,早已鮮為人知。(參見唐濟(jì)泉:《老北京的大棚廚子》,徐昌義編:《名家談吃》,第285~286頁(yè),成都出版社,1996)
與京城相鄰的天津津菜得益于商業(yè)大都會(huì)的地利,在清末民初發(fā)展到鼎盛,甚至超過北京。大型飯莊有30多家,高樓大廈,陳設(shè)華麗,遠(yuǎn)勝京師。津菜精于調(diào)味,百菜百味,各有千秋,尤其擅長(zhǎng)煮湯,如用雞鴨肉調(diào)制的三合湯;烹調(diào)白色菜品用燜白湯;清亮如水,濃郁鮮醇的高湯等等。
京派、海派飯店、酒樓經(jīng)營(yíng)的新格局,對(duì)全國(guó)的飲食業(yè)起了示范的作用,對(duì)蘇、川、魯、粵四大菜系的制作、服務(wù)和銷售都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