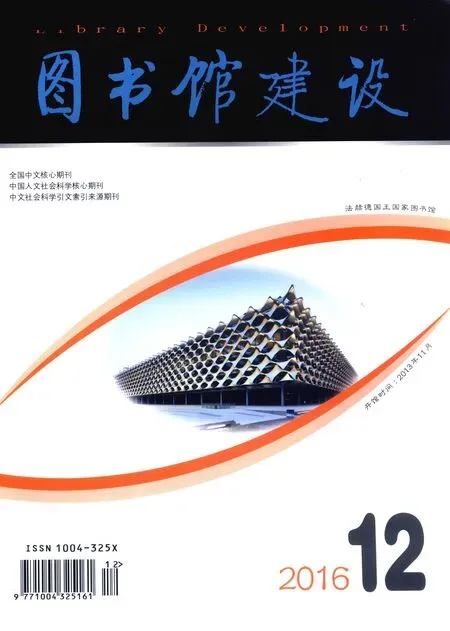基于關鍵詞共現聚類的深閱讀研究熱點分析*
吳 健 李子運 王洪梅
(江蘇師范大學智慧教育學院 江蘇 徐州 221116)
基于關鍵詞共現聚類的深閱讀研究熱點分析*
吳 健 李子運 王洪梅
(江蘇師范大學智慧教育學院 江蘇 徐州 221116)
以CNKI中127篇關于深閱讀的有效文獻為數據來源,利用BICOMB和SPSS軟件對其關鍵詞進行共現分析和聚類分析,可發現:我國目前研究深閱讀的3個主要領域是圖書館界、出版界和教育界;其熱點主要聚焦于“新媒體環境下的語文教學”“全民閱讀的策略研究”“淺閱讀是非之爭及圖書館應對策略”“大學生深閱讀的實證研究”“學術期刊應對淺閱讀的措施”,但存在缺乏針對深閱讀的系統研究、針對大學生深閱讀的研究較少等不足。我國應利用技術優勢促進深閱讀、提高深閱讀實證研究的科學性,研究焦點應轉向促進人們深閱讀的具體方法,從而更加科學化地進行深閱讀研究。
深閱讀 關鍵詞共現 聚類分析 研究熱點
閱讀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是聯系歷史與未來、實現現實價值的最好路徑,是人類一直不斷探索的古老而永恒的話題。知識、視野、涵養、理性、智慧是閱讀給予個人成長和發展的瑰寶。數字閱讀媒介的出現和迅速發展沖擊著傳統閱讀,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報告顯示,2015年的數字化閱讀率為64.0%,已經超過了紙質閱讀[1]。數字閱讀隊伍不斷壯大,帶來的問題也尤為凸顯:數字設備易造成視覺疲勞,導致閱讀持續性和專注力下降;數字媒介下的淺閱讀趨向導致讀者思想鈍化、缺少思考的深度[2]。正因如此,“深閱讀”成為閱讀研究的重要內容。深閱讀是一系列促進理解的過程,包括推論、演繹推理、批判分析、反思和洞察[3],其基本價值取向和最終目標是實現創新,發生的先決條件是閱讀超越頭腦理解范圍的內容。
本文對CNKI期刊數據庫中有關深閱讀的文獻進行研究,通過文獻的外部特征分析和共現聚類分析,揭示深閱讀的發展趨勢和研究熱點,為我國深閱讀未來的研究方向提供理論依據和參考。
1 深閱讀研究文獻概況
筆者通過對文獻的發表年份、來源分布進行分析,了解國內研究深閱讀的基本情況,從文獻的外部特征著手,揭示、探索出深閱讀研究發展的趨勢和空間以及研究深閱讀的主要領域。
1.1 數據來源
核心期刊基本占據本領域絕大多數的信息資源[4],并且CNKI的核心期刊收全率達到99%[5];加之,關鍵詞能體現文章的核心思想、研究方法等,是文章的精髓,對關鍵詞進行統計分析可以把握一個領域的研究熱點和前沿,因此,為了更權威、更全面、更深入地分析國內深閱讀研究的熱點和現狀,筆者以CNKI期刊數據庫作為本文的數據來源,來源類別選擇“中文核心期刊”&“CSSCI源期刊”,時間不限,檢索日期為2016年7月30日,并以“深閱讀”“深度閱讀”“深層閱讀”“深層次閱讀”為關鍵詞進行檢索,排除征稿啟事、書訊等非學術文獻以及剔除無關文獻和重復的文獻后,共得到有效文獻129篇。
從文獻的年份分布可知,2006—2016年學界對深閱讀的研究是連續的,而2006年之前關于深閱讀的研究只有兩篇(1999年和2004年各1篇),且時間間隔長,所以本文對2006—2016年的文獻進行研究,有效文獻數是127篇。
1.2 發表年份及數量
從近11年深閱讀文獻發表數量可看出(見圖1),在“中文核心期刊”和“CSSCI源期刊”上發表的深閱讀文獻呈上升趨勢。從圖1可看出,2006—2010年每年發表的篇數在10篇左右,處于研究初期;2011年最多,有20篇,深閱讀研究量突增;2012年有所下降,但是接下來的幾年波動較小,呈穩步發展。2016年上半年就已經有10篇,所以深閱讀研究的熱度整體呈上升趨勢,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圖1 2006-2016年深閱讀文獻數
1.3 研究深閱讀的主要領域
對文獻來源出版物進行分析不僅能夠了解每個期刊載文量的多少,重要的是能看清研究該課題的主要領域的分布情況,從而進一步探索深閱讀研究發展的規律。從圖2可知,研究深閱讀的主要領域是圖書館界、出版界和教育界。
1.3.1 圖書館界
由圖2可知,圖書館界發表的關于深閱讀的文章最多。圖書館始終是文化傳承和知識傳播的圣地,并且閱讀一直是圖書館不斷探索的經典話題,加之新媒體使淺閱讀成為大眾主要的閱讀方式,一時間關于深閱讀與淺閱讀的是非好壞以及如何辯證地看待兩者的關系成為人們爭辯的焦點,因此圖書館不可避免地加入了這場熱議的潮流。

圖2 文獻來源分布圖
1.3.2 出版界
出版界發表的關于深閱讀的文章也較多,初步分析其原因是:傳統閱讀向數字閱讀過渡,傳統出版與數字出版并存,數字出版物的風行使淺閱讀大行其道,而深度閱讀是對于出版物精神內容的直接訴求[6],深閱讀需求的應然與淺閱讀風行的實然已經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數字出版物作為如今的主流閱讀客體,如何通過創新來完善其功能和優化文字的具象化設計以促進讀者的深閱讀已經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更是出版商應面對的挑戰。
1.3.3 教育界
閱讀是一切學習的基礎,提高學習效果始終是教育界所關注的,此外閱讀過程也是信息加工的過程,而大腦如何加工信息、建構知識是教育界研究的內容,所以閱讀自然而然地成為教育界研究的內容。相對圖書館界和出版界,教育界對深閱讀的研究較少,初步分析是學科性質所致。淺閱讀行為盛行,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如何促使人們利用新媒體技術進行深度閱讀和深度學習應是教育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教育界不能忽視這方面的研究。
2 深閱讀的高頻關鍵詞共現聚類分析
仍以127篇有效文獻為數據源,筆者使用書目共現分析系統BICOMB提取文獻中的關鍵詞并建構共現矩陣,通過Excel 2003將共現矩陣轉換成高頻關鍵詞的相似矩陣和相異矩陣,再將相異矩陣導入到SPSS中,進行聚類分析,最后歸納分析得出研究熱點。
2.1 關鍵詞提取
筆者用BICOMB系統提取127篇文獻的關鍵詞,共得到516個,其中有255個不同的關鍵詞,為避免同義關鍵詞影響分析結果,合并同義關鍵詞,如“網絡閱讀和網上閱讀”“深閱讀和深層次閱讀”“策略和路徑”等,再參考1973年Donohue提出的高頻低頻詞界分公式[7]和1992年國內學者孫清蘭推導出的高頻低頻詞詞頻臨界值計算公式[8],并結合統計結果的代表性,最終確定高頻詞與低頻詞的閾值為4次,共得到20個高頻關鍵詞(見表1),其總的出現次數是267次,占關鍵詞總數的51.7%。這20個高頻關鍵詞基本能夠代表國內深閱讀領域的研究熱點。

表1 核心期刊高頻關鍵詞表
2.2 高頻關鍵詞共現矩陣建構
高頻關鍵詞共現矩陣的建構是進行聚類分析的基礎。筆者用BICOMB系統對除“深閱讀”之外的19個詞進行兩兩配對,建構出19x19的高頻關鍵詞共現矩陣(見表2),對角線上的數值表示該關鍵詞在檢索到的有效文獻中出現的總次數,其余的數字表示兩個關鍵詞同時出現在同一篇文獻中的頻次,頻次越高,說明兩者關系越緊密,關聯程度越強,如“網絡閱讀”在127篇文獻中共出現13次,與“淺閱讀”出現在同一篇文章中的頻次是8次,與“圖書館”同時出現的頻次是4次。

表2 高頻關鍵詞共現矩陣(局部)
2.3 高頻關鍵詞相似矩陣和相異矩陣的建構
兩個不同的關鍵詞共現頻次易受到詞本身出現頻次的影響,不能反映真正的相依程度,故筆者引入Ochiia系數進行處理,消除出現頻次懸殊的影響。處理方法是將共現矩陣導入到Excel中,調用Visual Basic編輯器,將Ochiia系數的計算公式編寫成代碼,運行即可得到高頻詞相似矩陣(見表3),矩陣中的數值越大,表明兩者的關系越緊密,相似度越大。

表3 深閱讀高頻關鍵詞相似矩陣(局部)
因為相似矩陣中的0值很多,統計時容易引起誤差過大,所以筆者將相似矩陣轉換成相異矩陣,處理方法是用數值1減去相似矩陣中的各數值,結果如表4所示。與相似矩陣相反,相異矩陣中的數值越小,說明兩者之間的關系越緊密、關聯性越強、相依強度越高。

表4 深閱讀高頻關鍵詞標準化后的共現相異矩陣(局部)
2.4 高頻關鍵詞聚類分析
筆者將相異矩陣導入到SPSS中進行系統聚類分析,結果如下頁圖3所示。結合SPSS的因子分析結果,符合條件的因子個數是5,為研究熱點的分類提供了依據。結合共現分析、聚類分析和研讀相關文獻,筆者將深閱讀研究熱點分為5類,分別是:新媒體環境下的語文教學、全民閱讀的策略研究、淺閱讀是非之爭及圖書館應對策略、大學生深閱讀的實證研究、學術期刊應對淺閱讀的措施。
3 深閱讀的研究熱點分析
基于共現矩陣的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并研讀、分析相關文獻可知,目前深閱讀的研究熱點聚焦于新媒體環境下的語文教學、全民閱讀的策略研究、淺閱讀是非之爭及圖書館應對策略、大學生深閱讀的實證研究、學術期刊應對淺閱讀的措施研究這5個方面(見圖4)。

圖3 高頻關鍵詞的聚類分析圖

圖4 深閱讀研究熱點示意圖
3.1 新媒體環境下的語文教學
此熱點由“紙質媒介、電子媒介、經典閱讀、語文教學”等關鍵詞組成,主要探討了新媒體環境下語文閱讀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和出現的淺閱讀現象。語文是發掘人文底蘊、培育人文素質、提高語言表達能力的一門學科。技術的動態發展給語文教學帶來了新的問題、提出了新的挑戰。偏離審美、感悟、思考的淺閱讀不僅在社會上成為潮流,而且在語文教學中也普遍存在。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學科教學與多媒體融合的提出加快了教育信息化,但是由于教師對這種“融合”的錯誤理解和對多媒體的不恰當使用,導致語文閱讀教學出現嚴重的淺閱讀問題,表現為:閱讀感官化、閱讀淺顯化、閱讀平庸化、閱讀資源復雜化,使學生被動接受。語文教學中閱讀的淺層化問題出現的原因和解決路徑已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李玉英認為,教師對新課程概念缺乏正確理解和社會“淺閱讀”的影響是語文教學存在閱讀碎片化、隨意化、浮于表層并背離閱讀和教學宗旨的主要原因[9]。袁華莉等人對網絡環境下的語文深度閱讀教學進行了研究,通過建構閱讀教學層級模型,以此為基礎和指引,并結合教學目標提出了課堂網絡環境下提高深度閱讀教學的5個策略[10]。楊現民等人以布魯姆的認知目標為依據,劃分出小學生的閱讀層次,并通過實證研究探討出SURF(共享獨特的閱讀體驗的網絡閱讀工具)能夠幫助小學生實現深層次閱讀[11]。萊州一中通過建立“生態”課堂,配套“套餐”課程,重視以活動帶動學生深度閱讀,構建“悅讀”文化[12]。但于翠玲指出,警惕媒介文本的娛樂本質,以引導學生親近印刷文本作為提高深閱讀能力的途徑[13]。其他研究還包括語文教學的實踐性研究、針對某具體課文的教學設計等。
3.2 全民閱讀的策略研究
此熱點由“策略、全民閱讀”等關鍵詞組成,主要探討了全民閱讀的現狀、遇到的問題及策略。全民閱讀是建設學習型社會的重要戰略。2006年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總局提出全民閱讀活動理念,全力打造全民閱讀的國家品牌,開展了各種各樣的活動,如書香中國全民閱讀電視晚會、全國書香之家。從理念提出到如今已有10年,全民閱讀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荼,各地相繼開展了北京閱讀季、書香中國上海周、書香江蘇、海南書香節等一大批活動,同時各地也出現了24小時書店,全面支持讀者閱讀。從2014年開始,“全民閱讀”已經連續3年被寫入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全民閱讀在傳承民族文化、建設學習型社會以及和諧社會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受到國家的重視,但是在積極推廣和服務的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人文閱讀缺失、網絡閱讀導致淺閱讀、閱讀功利化、圖書品質降低等[14]。針對存在的問題以及營造的深閱讀氛圍,學者提出的應對策略是:融合傳統閱讀的“深”與數字閱讀的“廣”;提高個人的參與意識,發揮政府的職能[15];充分利用公共圖書館[16]等。
需要指出的是,新媒體的出現加快了淺閱讀現象的普遍化[17],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數字閱讀不能實現深閱讀,并且不加思索地認為網絡閱讀就是淺閱讀,是對新媒體技術功能的扼殺,也是對深閱讀認識的扭曲。改變的是形式,不變的是閱讀[18],深閱讀的發生與閱讀內容的呈現方式無關,而是與讀者的思考程度有關。
3.3 淺閱讀是非之爭及圖書館應對策略
此熱點由“網絡閱讀、閱讀率、淺閱讀、圖書館”等關鍵詞組成,主要探討了在媒介改變閱讀方式和閱讀態度的背景下,對“淺閱讀普遍化”現象持何種態度以及圖書館采取何種措施。由于學者的學習經歷、學習感悟和研究視角不同,對淺閱讀普遍化的現象持不同的態度,從而引發了關于淺閱讀是非之爭:淺閱讀應該被視為這個時代的洪水猛獸還是人們必不可少的閱讀方式?不同聲音此起彼伏,褒貶不一,被推到社會輿論的風口浪尖。不少學者對淺閱讀成為閱讀常態表示擔憂,認為淺閱讀過程中隨意、不思考,會降低語文表達能力,使文化靈蘊消失,其消遣娛樂的閱讀目的容易使人內心浮躁,急于求成[19-21]……許多學者為圖書館推廣深閱讀諫言獻策:在閱讀資源建設上,建立圖書館聯盟,實現資源共享;在閱讀工具上,構建多元化的導讀模式和基于Web2.0的導讀平臺,即圖書館和用戶的共同協作的平臺[22];在閱讀方法上,用表征邏輯結構的思維導圖引導深層次的經典閱讀[23];在閱讀活動上,開展書評交流,以接受美學為理論,開展深層次的閱讀推廣活動,以讀者創新、個體解讀和閱讀交流為推廣重點[24],培養讀者的閱讀興趣……可見已有3 000多年歷史的圖書館仍然在人類知識傳播、文化交流方面一直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雖然抨擊淺閱讀的學者給淺閱讀貼上了“隨意”“碎片化”“輕松閱讀”“淺嘗輒止”等標簽,“抨擊”之聲也一直在繼續,但學術界仍不缺乏對淺閱讀的“追捧”:淺閱讀不代表沒有思考,淺閱讀與深閱讀并不矛盾,淺閱讀是深閱讀的基礎;淺閱讀降低閱讀門檻,意味著閱讀走向大眾化;閱讀本身包含著、實現著一種價值,我們又何必去指責“淺層次”“格調不高”呢[25]。沈迪飛先生甚至說:“淺閱讀是人類第二次閱讀革命的主力軍。”[26]
閱讀始終肩負著傳承文明的重任,是人類追求至善至美的認知行為,在追求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今天必然會引起更多人的關注,淺閱讀的是非爭辯實質是人們為了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滿足自身的需求對有效閱讀方式的不斷探索。
3.4 大學生深閱讀的實證研究
此熱點由“大學生、實證研究、移動閱讀、碎片化”等關鍵詞組成,通過實證研究探討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深閱讀的情況以及閱讀工具能否支持深閱讀。新媒體的出現和發展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和思維方式,大學生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主力軍和新技術的前沿群體,其閱讀方式、學習方式、社交方式更是受到新媒體技術的強烈沖擊和影響。在此背景下,從實證的角度客觀地探討大學生閱讀行為特征的變化以及淺閱讀對深閱讀的影響成為眾多學者研究的重點。柴陽麗以托尼·巴贊的閱讀環節為理論依據,通過實證研究探究閱讀工具中的社會化批注功能對深閱讀的應用效果并提出促進深閱讀的方法。研究表明社會化批注有利于提高閱讀思考的投入度,能夠支持深閱讀的各個環節[27]。邱相彬以浙江6所大學的大學生為研究對象,通過專家咨詢和問卷調查探究出移動網絡環境下大學生淺閱讀對深閱讀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28]。胡兆芹以圖書是否借出圖書館作為劃分深閱讀和淺閱讀的依據,統計30天的數據并分析出不同類別圖書的深淺閱讀量存在顯著差異[29]。
3.5 學術期刊應對淺閱讀的措施研究
此熱點由“數字化閱讀、新媒體、期刊”等關鍵詞組成,探討在互聯網和新媒介改變閱讀載體、閱讀行為和方式的情況下,學術期刊界為迎合讀者需求所做的研究。面對數字信息超載負重和數據庫的急劇擴張,學術期刊界一致認為逐一閱讀海量信息是很不經濟的,而且也沒有必要,讀者應各取所需以滿足自身的發展需求。所以,尊重讀者多樣化的閱讀選擇,對淺閱讀不抱有偏見,對深閱讀不抱有敬畏之心,雖然深閱讀與淺閱讀涇渭分明,但兩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優劣互補。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應將淺閱讀與深閱讀結合,首先利用快速高效的淺閱讀查找、瀏覽、過濾信息,以發現有價值的、值得深入閱讀的文獻,其次通過題目、摘要、關鍵詞等做一個整體的價值判斷,決定是否深入閱讀,最后潛心研讀感興趣的相關文獻,進行創新創作。溫優華指出,數字時代兩手抓深閱讀和淺閱讀是學術期刊適應閱讀方式變化的應有作為,充分利用深閱讀和淺閱讀優勢互補的特點,尋找兩者之間的契合點,讓“小眾學術”走進“大眾視野”,引導讀者深閱讀,發現學術成果的多維價值和挖掘創新性選題[30]。謝文亮提出實現淺閱讀與深閱讀對接的兩種途徑:微博+博客,把博客的全文鏈接地址添加到微博的后面,讀者根據自身的閱讀需求判斷是否閱讀全文;使用期刊APP和微信公眾平臺提供的摘要性信息和鏈接全文的功能以及內容推送功能,實現個性化服務[31]。仲明指出,數字化環境下學術研究依然提倡深閱讀,只有通過不斷的閱讀、思考和感悟,才能達到思維深度,提高學術水平[32]。由此看出,做好淺閱讀和深閱讀的對接以及引導讀者閱讀向縱深發展是學術期刊界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他研究包括自出版對編輯存在價值影響的思考以及編輯如何轉型[33]。
4 對目前深閱讀研究熱點的思考
4.1 不 足
(1)缺乏針對深閱讀的系統研究
目前沒有對深閱讀做出嚴格明確的概念化定義,而是以描述性定義居多,如深閱讀是指對圖書心懷敬畏,細細品讀,把讀書學習當成一種人生態度[34]。這樣的定義不僅缺乏學術性,而且其抽象、朦朧的特性不利于對深閱讀開展研究以及探索其發展規律,反而容易使人們對深閱讀的理解越來越模糊。此外,有學者不加思索地認為深閱讀就是傳統閱讀、經典閱讀;網絡閱讀和數字閱讀就是淺閱讀。閱讀載體確實會影響閱讀行為,但是這些學者已完全忽視閱讀主體的能動作用和閱讀本體的內在機制,所以這種劃分是不可靠的。另外,不少學者為促進讀者深閱讀出謀劃策,卻沒有理清深閱讀本身的概念,犯了舍本逐末、本末倒置的錯誤,所提的策略缺乏可信的依據。
(2)針對大學生深閱讀的研究較少
目前現有的深閱讀研究中針對大學生的研究很少。但是,而今已經進入智慧教育時代,大學生是國家發展的中心力量,要想加速國家發展的步伐和提高全民族的智慧,就要先提高大學生的智慧和創新能力。而且,目前大學生陷入“閱讀危機”,大學生閱讀不是出于個人的興趣和需要,而是為了考試而閱讀,為了娛樂而閱讀,這種功利性、娛樂性、淺層次的閱讀,阻礙了大學生的健康和諧發展,也不利于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此外,數字閱讀成為大學生主要的閱讀方式和閱讀選擇,所以,針對大學生進行關于如何利用數字媒體促進深閱讀方面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4.2 建 議
(1)“宜疏不宜堵”,利用技術優勢促進深閱讀。
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直接改變了人們的學習方式和生活方式,新型閱讀媒介催生了新的閱讀方式和閱讀習慣,數字閱讀成為讀者獲取信息的首選閱讀模式,改變了閱讀文化的品質與格局,從而重新構造人們的精神世界。不停地刷微博、瀏覽各種娛樂新聞、無節制地觀看視頻,人們毫無知覺地跨進淺閱讀的行列,顯然淺閱讀已經成為我們這個時代閱讀生活的趨勢和常態。目前,國內教育界、出版界、圖書館界仍在譴責互聯網技術分散人們的注意力、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思維,呼吁回歸紙質經典閱讀。但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技術支持的數字閱讀首次超過紙質閱讀[1]。信息技術的出現和流行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既然存在,我們就要正視它存在的必然性。既然我們已經身處互聯網時代,技術時刻陪伴在我們的身邊,越來越多的人離不開技術,“宜疏不宜堵”,我們要正視技術對閱讀的影響,學者們也應該將研究的焦點從技術對閱讀的不利影響轉向挖掘新技術對深閱讀的支持以及如何提高個人的修養和品質來抵御網絡給人們帶來的不良影響。
(2)提高深閱讀實證研究的科學性
實證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便是結果的客觀性,客觀性是提高研究科學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希望有更多的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的方法來研究深閱讀,將內隱的閱讀行為外顯化。但目前關于深閱讀的實證研究中存在實質性的錯誤——錯誤劃分深淺閱讀的標準。有學者通過實證方法研究大學生深閱讀的現狀,出發角度很好,但劃分深淺閱讀的依據卻弄錯了。該學者認為深閱讀圖書是讀者辦理借閱手續后的圖書,淺閱讀圖書是在圖書館內翻閱等形式的圖書,這種劃分依據存在缺陷。深閱讀不應該以閱讀時間的長短來劃分,有些讀者雖然借了很多書但是不看,而有些人閱讀效率較高,能夠在短時間內領會內容的含義。所以筆者認為,實證研究時要合理設計實驗,應以注意力、深入性、思考程度來劃分閱讀的深淺,并結合研究的兩種范式——認知實驗和非知識測驗,使用腦波儀和眼動儀等技術,從微觀和宏觀的角度探索閱讀行為,提高深閱度研究的科學性和說明力。
(3)研究焦點應轉向促進人們深閱讀的具體方法
淺閱讀的是與非不是閱讀生活中最該爭論的問題,如何激發讀者由“淺”入“深”的閱讀欲望,培養讀者由“淺”入“深”的閱讀習慣,才是當今我們最該深思的問題。國內有不少文獻從學科教學、政府、個人、出版商等角度研究了深閱讀策略,但是學者大多從宏觀角度出發,提出的做法大而廣,不夠聚焦。筆者認為,應該策略細化,在資源上,圖書館建立數字化學科原典文獻數據庫,將高品質資源推送給讀者,降低海量、平等和簡易闡釋的信息對讀者閱讀的消極影響;在知識管理上,幫助讀者培養管理知識的意識,使用圖形組織工具,提高聯接知識的敏感度,增強閱讀情境和合理的呈現方式,減少閱讀過程中的認知負荷。
5 結 語
本文通過對127篇文獻的外部特征分析和聚類分析,直觀形象地揭示了國內深閱讀的研究現狀和研究熱點,具有現實意義,對后續的研究具有參考價值。目前我國對深閱讀研究還處于探索初期,研究上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我們不斷探索,以科學的態度重新審視深閱讀,總結其特征、分辨與其他概念的區別以及弄清深閱讀可能發生的階段等。
[1]第十二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成果發布[EB/OL].[2016-05-14]. http://www.chuban.cc/yw/201504/t20150420_165698.html.
[2]胡 凱. 媒介形態變遷視野下閱讀行為嬗變:以印刷媒介和數字媒介為例[J].中國出版, 2014(14):10-13.
[3]Wolf M,Barzillai M.The Importance of Deep Reading[J].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9,66(6):32-37.
[4]劉振華. 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利用存在的問題及對策:基于哈爾濱市高校圖書館數字資源利用情況調查的實證研究[J]. 高校圖書館工作, 2009(5):68-69.
[5]徐以鴻, 朱 濤. 機構知識庫內容快速建設方法[J]. 現代情報, 2011(4):148-151.
[6]徐正芳. 深度閱讀——深度出版的深度選擇[J]. 出版科學, 2009 (5):56-60.
[7]Donohue J C.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Literatures:A Bibliometric Approach[M].Cambridge:The MIT Press, 1973:49-50.
[8]孫清蘭. 高頻、低頻詞的界分及詞頻估計方法[J]. 情報科學, 1992(2):28-32.
[9]李玉英. 語文教學中的“淺閱讀”現象解析[J]. 教育探索, 2008 (9):70-72.
[10]袁華莉, 余勝泉. 網絡環境下語文深度閱讀教學研究[J]. 中國電化教育, 2010(7):13-22.
[11]楊現民, 孫 眾, 邢蓓蓓,等. SURF工具對小學生閱讀層次的影響研究[J].電化教育研究, 2010(4):103-108.
[12]蔡潤圃, 張建梅. 高中語文深度閱讀的探索與實踐[J].當代教育科學, 2015(4):52-55.
[13]于翠玲. 媒介素養教育融入中學語文教學的思路[J].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 2010(12):44-47.
[14]楊 嵐. 文化傳承視角下全民閱讀現狀與對策研究[J]. 編輯之友, 2014(5):22-25.
[15]曾絢琦. 全民閱讀的時代意義與實現途徑[J]. 現代出版, 2014(1):21-23.
[16]李 貞. 公共圖書館推動全民閱讀的策略研究[J]. 出版廣角, 2015(2):105-106.
[17]王子舟, 周 亞, 巫 倩,等“.淺閱讀”爭辯的文化內涵是什么[J].圖書情報知識, 2013(5):15-21.
[18]達恩頓. 閱讀的未來[M].熊 祥,譯.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1:1.
[19]李 勁. 論淺閱讀時代圖書館對大眾閱讀的深度引導[J]. 圖書館學研究, 2008(4):79-81,75.
[20]蔡 紅. 唐秀瑜. 淺閱讀時代圖書館的深度選擇[J]. 圖書館, 2007 (3):41-43,46.
[21]董一凡. 對近兩年圖書館界關于“淺閱讀”問題研究的述評[J].圖書館論壇, 2009(3):11-13,2.
[22]徐洪升. Web2.0環境下的深閱讀及圖書館導讀策略[J]. 圖書館論壇, 2008(4):124-127.
[23]陶文萍. 數字化時代經典閱讀的思維導圖推廣策略:以湖北師范學院圖書館為例[J]. 現代情報, 2013(2):152-154.
[24]趙慶玲. 接受美學與深閱讀:圖書館可以做的[J]. 高校圖書館工作,2016(2):3-6.
[25]楊 紅“.淺閱讀”時代圖書館的應對策略[J]. 圖書館, 2008(2):93-94.
[26]沈迪飛. 請不要貶低淺閱讀[J]. 公共圖書館, 2012(2):73-80.
[27]柴陽麗. 社會化批注對大學生數字化深閱讀影響的實證研究[J].現代遠程教育研究, 2016(2):107-112.
[28]邱相彬, 沈書生, 徐曉拉. 移動網絡環境下“淺閱讀”對“深閱讀”的影響分析:基于對浙江六所高校大學生的實證研究[J]. 圖書館學研究, 2016(1):71-75.
[29]胡兆芹. 大學圖書館“圖書深、淺閱讀”的實證研究[J]. 現代情報, 2011(8):126-129.
[30]溫優華. 數字時代學術期刊淺閱讀和深閱讀的“兩手抓”[J]. 編輯之友, 2015(9):43-46.
[31]謝文亮, 楊小川. 移動互聯網時代學術期刊的淺閱讀與深閱讀[J].中國科技期刊研究, 2014(1):152-154.
[32]仲 明. 數字化閱讀對學術研究的正負效應[J]. 圖書館工作與研究, 2010,(10):4-7.
[33]趙明霞. 互聯網環境下編輯的價值思考[J]. 出版廣角, 2016(5):8-10.
[34]張亞軍. 從深閱讀到淺閱讀的變遷[J]. 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6):144-148.
Analysis on Hotspots of Deep Reading Research Based on Keywords Co-Occurrence Clustering
Using the keyword ''deep reading'' to retrieve documents in the platform CNKI, by co-occurrence analysis and clustering analysis with software BICOMB and SPSS, it is found that three major fields researching on deep reading are library, publication, and education; hotspots mainly focus on ''Chinese teaching in circumstance of new media'', ''strategic research on nationwide reading'', ''argument on superficial reading and libraries' countermeasur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deep reading'', and ''academic journals' countermeasures on superficial reading'', while there lacks system reserch on deep reading, and has rare research on college students' deep reading. Technology should be used to promote deep reading, improve scientific empirical research on deep reading, and the research focus should transform to specific methods on how to promote deep reading, so as to research deep reading more scienficially.
Deep reading; Key words co-occurrence analysis; Clustering analysis; Research hotspot
G252.7
A
吳 健 女,1991年生,江蘇師范大學智慧教育學院教育技術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
李子運 男,1973年生,副教授,現工作于江蘇師范大學智慧教育學院。
王洪梅 女,1990年生,江蘇師范大學智慧教育學院教育技術專業2014級碩士研究生。
2016-07-0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大學生數字化閱讀的眼動研究”,項目編號:12YJC880050;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資助項目“江蘇師范大學教育學省優勢學科建設”,項目編號:蘇政辦發〔2014〕37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