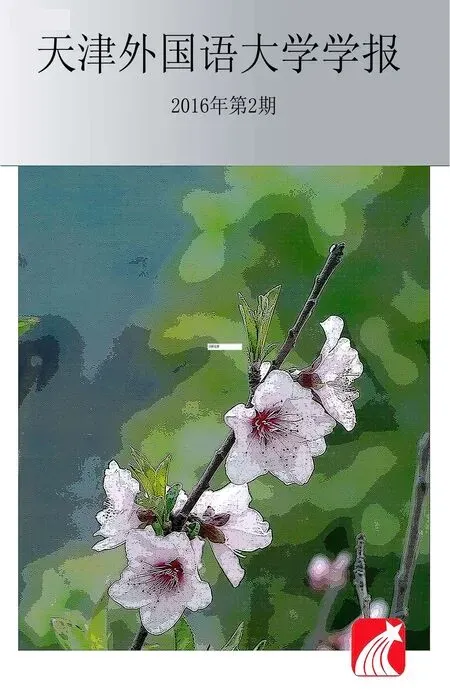死亡話語研究綜述
王景云
(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北京 100871)
死亡話語研究綜述
王景云
(北京大學 外國語學院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北京 100871)
本文是語言學視角下死亡話語的研究綜述。文章梳理了國內外死亡話語的語言學諸視角分析,總結了各研究視角的主要內容和特點,并探討了死亡話語研究的未來前景。語言學研究視角涉及語用學分析、敘事研究、語類研究、多模態話語分析、及話語心理學等領域;研究內容既包括現實情境中的死亡話語闡釋,也涉及死亡主題的文本呈現,主要涵蓋死亡的意義建構和意義傳遞兩個維度。最后,文章簡要討論了國內死亡話語研究面臨的挑戰和未來發展。
死亡話語;語用學分析;敘事研究;語類研究;多模態話語分析;委婉語;話語心理學
一、引言
死亡是自然界最普遍的現象,也是無法回避的事實。因此,死亡成為人類一直探索的問題,對死亡話語的研究也見諸于文學、心理學、社會學、醫學、語言學等各領域。文學作品中的死亡話語研究是文學分析的熱點之一。心理學角度的研究探究過人類對于死亡或死亡過程的心理反應,并通過考察人們對死亡的態度對重病患者進行心理治療干預。死亡也成為社會學研究關注的問題,如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干對“自殺”的分析和研究開創了社會學角度研究自殺的新視角。醫學技術的進步使得人類能夠對死亡進行干預,延長生命期限;同時人文醫學的發展也促使臨終關懷、安樂死等問題的討論。
近些年來,語言學領域對死亡話語的研究也在不斷發展。從語言學視角對死亡話語進行分析,透過語言解讀死亡,能夠更加深入地解釋此類具有深刻現實意義的話語。那么,語言學視角對死亡話語的研究有哪些?死亡話語研究涉及哪些研究內容?死亡話語分析的現狀和發展前景又將如何?基于上述問題,本文將對語言學視角下的死亡話語研究做一個系統的梳理分析,并嘗試為未來死亡話語研究提出一些建議。
目前筆者還沒有在語言學領域看到“死亡話語”這種提法,因此這并不是一個專門的概念。鑒于此,本文將首先對這一提法進行界定。Fairclough較早對話語的概念做出界定,指出話語是“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是語言口頭和書面形式的運用(Fairclough,1996:22)。因此,本文所考察的死亡話語出現在死亡這一特定的情境中,指談論“死亡或瀕死”(death or dying)事件的話語。此處,死亡話語既包括口語會話對死亡事件的敘事,也包括死亡的書面文本。
Carpentier和Van Brussel(2012)曾分析過西方死亡話語的核心元素;從語言發生學的視角(對死亡和好的死亡的表述隨時間而變化)探究了死亡的條件性;通過對臨終關懷和死亡權利運動的分析,討論了死亡話語的政治特性。本文對于死亡話語未做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的區分,把涉及死亡和瀕死事件的話語都包括在內。同時,文中所提到的死亡是指生物學意義上的死亡,指喪失生命,生命終止,不繼續生存。
二、死亡話語分析
本節將主要介紹國內外近 10年對死亡話語的語言學視角研究,主要涉及語用學分析、敘事研究、語類研究、多模態話語分析、社會語言學的委婉語、及話語心理學等。
1 語用學分析
語用學分析涉及言語行為、禮貌和面子理論,這些理論視角可以用于探究特定語境中的死亡話語。死亡話語的語用學分析關注醫生和患者交流情境中的語言使用情況,包括對“死亡”話題的處理、告知病情以及死亡預期等,其中涉及到禮貌原則、面子理論、語用策略的使用等。
Tsai(2010)分析了醫患交流中對“出生”和“死亡”話題的處理,考察了臺灣醫生和老年患者之間的49個即時交談案例,其主要目的是收集病人的家族病史。研究發現醫生使用的話語策略主要是通過只含主語的問句,如“您丈夫呢?”,或是對家庭成員還健在的肯定推測,如“您的父母多大年紀了?”。家庭成員死亡的信息表現為非顯性和間接的信息。通過提供一個模糊的問題或假定家庭成員還健在,醫生為病人提供了較大的空間,這樣有助于平衡與死亡有關的面子威脅影響。Tsai指出其團隊2008年的類似研究發現,醫患溝通中老年患者和醫生對死亡的詞匯選擇也表現出差異:老年患者會采用更直接的表達,如“死”(die),而醫生會選擇更委婉的說法,如離開(pass away)。這說明說話者的詞匯選擇與他們的職業以及其所接受的教育有關系,醫生選擇更正式的間接表達,反映了他們的職業角色以及對患者的尊重和關心;同時也反映出他們相比患者擁有更好的教育背景。
Anderson et al.(2013)考察了美國醫院情境中重癥患者和住院醫師之間有關死亡和瀕死事件的溝通,研究了39位病人和23位住院醫師的對話錄音。研究發現告知病人死亡的可能性是一個關鍵環節。一般情況下,直接向病人交代病情的情況較少,但這也取決于患者和醫生之間的合作溝通情況。有利于溝通的情況包括病人表露自己的情緒;醫生獲知病人對自身疾病的理解和情緒困擾。公開告知患者病情后,伴隨的臨終事宜討論包括:目標和價值觀、對死亡和診斷的恐懼,緩和醫療的選擇等。告知病情的過程可以作為及時和誠實探討臨終事宜的前期指導。
禮貌原則、面子理論等語用學理論為醫患話語溝通研究提供了理論框架。真實醫患溝通情境中的死亡話語分析,不僅能夠描述和展現“死亡”話題的具體處理過程,也可以為醫護人員提供工作指導,幫助患者家屬和患者更好地面對死亡。告知病情和生存期、討論死亡等一些敏感話題,對于醫護人員來說,是巨大的挑戰,其中也會涉及一些文化和社會問題。另一方面,這類醫患溝通研究需要大量的真實語料,涉及研究倫理,需要通過醫學理論倫理委員會的批準,也需要征得患者家屬和患者的同意。同時,目前國內醫療糾紛比較嚴重,醫患矛盾也比較突出,這也為語料收集提出了挑戰。另外,數據分析的過程中也需要增加社會和文化因素的考量。因此,由于涉及隱私、醫院環境的特殊性以及一些社會因素,數據收集困難較大,所以死亡話語研究在這一領域的研究還有待進一步的發展。
2 敘事分析
敘事研究又稱“故事研究”,關注人類體驗世界的方式。它從講述者的故事開始,以詮釋故事為其主要任務,重在敘事材料和意義分析(Lieblich et al.,1998)。死亡話語的敘事分析主要包括醫護人員職業經歷的敘事、以及病人患病的經歷和對死亡的闡釋和解讀。醫護人員的敘事反映了這一經常和死亡進行近距離接觸的特殊群體對死亡的認識、生命意義的反思以及對自身職業認同的理解;臨終病人或重癥患者則更多是從自身出發,闡述他們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的認識和感受。
Borbasi等(2005)分析了澳大利亞社區和醫院情境中醫院護士對于提供給末期心衰患者的照顧和服務的解讀。護理人員認為應該讓病人經歷“好的”死亡(good death),呼吁放棄毫無希望的治療,讓病人安靜離去。病人后期治療的選擇,緩和醫療還是積極治療,將影響病人及其家屬的心理變化軌跡,因此緩和醫療團隊的早期干預具有重要意義。
?sterlind et al.(2011)對瑞典4家養老院的護理人員進行了研究,數據收集來自 28位護理人員的 5次焦點小組談論。研究結果發現:在談論將要面臨的死亡時,護理人員往往是沉默的;情感被壓抑,成為談話的背景;對死亡的關注在老人死后才出現。此類話語的結構表現為規避死亡和面對死亡之間的移動,而其主要表現為規避死亡。這種對死亡的沉默需要引起人們對死亡的關注以及對護理人員培訓的思考。
Davis-Berman(2011)收集了17次與居住于養老院的老年人的面對面半結構化訪談數據,采用質性研究方法,讓老年人講述自己與死亡相關的故事。數據分析呈現的主題包括:接受死亡、對來世的談論、目前生活條件的影響以及對自殺的談論。受訪者并不害怕死亡,能夠平靜接受死亡,但對未來世界有不同的理解,強調目前生活條件的重要性,同時自殺也成為一個凸顯問題。
Candrian(2014)采用了民族志研究方法,對經常接觸死亡的臨終關懷和急診科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跟蹤研究。研究者采用“駕馭/馴服”(taming)來形容醫護人員對死亡的描述,分析了醫護人員談論其工作和工作環境的方式,以及這些認識和感受對他們自身以及對臨終病人護理產生的影響,如醫護人員如何以特定的方式解讀工作的意義,以及這些意義如何維持特定的關系,話語如何影響臨終護理的決定。
Semino et al.(2014)研究了13位英國的臨終關懷機構管理者對好的死亡和壞的死亡干預的敘事,并對這些敘事的形式特點和功能特點進行了分析。受訪者的回答包括各種有關“成功的和不成功的死亡干預”的敘事,其話語行為的起始點和核心、人稱和隱喻的選擇、積極和消極評價的表達等方面都表現出鮮明的形式特點。同時,他們的敘事也在表現和建構其職業觀點、挑戰和認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是敘事的功能特點。
敘事研究是目前死亡話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醫護人員的死亡話語敘事研究,幫助醫護人員梳理其接觸重癥患者或瀕死病人的工作經歷,分析其工作中的困難和挑戰,反思未來工作實踐。老年人、臨終或重癥患者對死亡的認識和態度也促使人們對臨終關懷、尊嚴死問題的關注。不同群體的敘事和他們的身份認同息息相關,對死亡敘事的關注,能夠讓我們在別人的故事中更好地認識和解讀死亡。
3 語類研究
語言學中“語類”的概念由genre(通常譯為“語類”或“體裁”,本文采用語類的概念) 這個詞而來。不同的語言學家對genre也有不同的定義。系統功能語言學家 Hasan(1985)認為語類是指語篇的類型,由結構的必要成分來定義。Martin和Rose(2008)將語類定義為“分階段的、有目標取向的社會性過程”以及“不斷重現的可促成特定文化中社會實踐的意義構型”。美國新修辭學以 Miller(1984,1994)和Bazerman(2003)為代表,將語類定義為是一種社會行為,側重研究語類生成、流通和接受過程中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語境所承載的社會目的。應用語言學領域的研究,如Swales(1990)和Bhatia(1993),重視交際目的,強調話語社團的概念。本文將語類定義為實現不同的社會目的和作用的各種語篇類型,死亡話語的語類研究涵蓋涉及死亡話語的各種語類,如與死亡相關的新聞報道、個人故事、以及訃告等。
Duncan(2011)研究了“突發死亡新聞故事”這類個人故事的敘事類型,并采用Labov和Waletzky的個人敘事模型,分析了失去親人的人如何講述他們的悲傷以及報道者如何解讀他們的經歷。研究發現在報道家庭悲劇時,盡管后期會采用較為積極的情緒,但是整個敘事過程呈現的是一種極度的悲痛和永遠的失去。
Krishnatray和Gadekar(2014)分析了2009年《印度時報》中的69篇H1N1死亡報道。研究發現了四個主要框架:害怕-恐慌、責任歸屬、行動和人情味。報紙將H1N1塑造為一種致命疾病,新聞報道以這種方式呈現死亡,讓讀者產生了害怕和恐慌的情緒。
Al-Ali(2005)從約旦的兩大主流報紙中隨機選取了200篇訃告,將訃告進行分類,通過訃告的九個“話步”來考察阿拉伯社會中訃告的結構成分,并分析各個語類成分傳達的交際功能。Askildson(2007)則考察了美國軍隊訃告這一語類,對其語體特征和語言功能進行了分析。Berns(2009)討論了死刑修辭中的終結陳詞和情感。Rizza(2015)從儀式情境中的嬉戲語言(ludic language)的視角分析了死刑判決聲明。判刑可以被視為一種社區儀式,具有儀式的特點;同時運用Cook語言游戲(Language Play)概念,分析了處決聲明嬉戲語言的形式、語義和語用特征。
國內對訃告的研究既有對語篇特征的分析,也有對社會因素的考察。張菊芬、魏躍衡(2008)分析了訃告的語篇特征,探討了其及物系統、組篇、功能結構等方面的語篇特征,并分析了所選語篇的語類結構潛勢(GSP),討論了訃告語篇的必要成分和任意成分。批評話語分析也是訃告研究的一種分析視角,傅恒(2011)根據Fairclough的話語三維分析模式,對《紐約時報》關于本拉登的訃聞報道從描述、闡釋、解釋三個維度進行批評話語分析,同時與其他三家媒體的訃聞作相關對比,挖掘了其隱含意識形態。
語類研究對語篇特征的概括,為在不同的語境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死亡話語提供了一種描述和研究的方法,能夠從細致的語言學角度對死亡話語進行呈現。但是我們也需要注意到,部分研究關注語言結構,但對話語的意義和力量重視不夠。
4 多模態話語分析
Kress和Van Leeuween(1996)認為,多模態語篇是一種融合多種交流模態(如聲音、文字、形象等)來傳遞信息的語篇。多模態話語分析將話語分析的研究范圍從單模式的語篇分析法擴展到多模態分析,涵蓋文字、圖像、顏色、音樂等符號系統。多模態話語分析吸收了符號學理論,其主要理論基礎是 Halliday創立的系統功能語言學。死亡話語的多模態話語分析涵蓋傳遞文字、圖片和網絡短片視頻等,涉及了傳達死亡信息的多種形式。
Ayodeji(2013)運用多模態話語分析的方法,對《基督教婦女鏡報》涉及審判和死亡的文章進行了批判性分析,對文章主題所涉及的語義指示語、以及視覺元素進行了討論,研究發現基督徒認為死亡是在天堂或地域的另一種生活的繼續。
Wildfeuer et al.(2015)運用批評話和多模態話語分析的方法,分析了青年志愿者與臨終病人和其家屬進行交流的短片和志愿者在網絡上有關個人經歷的分享。該研究通過從短片中截取的反映年輕人與臨終病人及家屬交流的圖片,以及他們在網絡上的文字文本,探究了死亡過程和死亡的概念在這些語篇中如何被重新和多樣化建構,以及語義內容如何產出、新的社會文化實踐如何變得可見。
將語言和其他相關的意義資源整合起來,不僅可以發現語言系統在意義交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 而且可以看到諸如圖像、音樂、顏色等其他符號系統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效果, 從而使話語意義的解讀更加全面。對死亡話語的多模態話語分析將更直觀的呈現死亡的景象納入分析,關注了語言文字和圖像的聯系和互動,為死亡話語研究開拓了更寬闊的道路。但是,多模態話語分析通常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同時各種模態之間的互動關系比較復雜,加之多模態涉及多學科的結合,多模態的綜合分析也為研究者提出了更多的挑戰。
5 社會語言學中的委婉語
委婉語源于語言禁忌,是指對一些敏感話題、禁忌之事如死亡、疾病等,采用模糊或間接的方式表達。委婉語是社會語言學中一種特有的語言現象,帶有鮮明的社會文化特征。由于“死亡”是禁忌話題,這就催生了大量和死亡相關的委婉語和隱喻表達,委婉語分析也成為了死亡話語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Holder(2007)編纂的《牛津委婉語詞典》中列舉的和死亡相關的委婉語就有七百多個,其中包括死亡、瀕死和殺死。
Weisman(1984)的研究發現晚期癌癥患者在談到他們的病情時,會避免直接提及“癌癥”這個詞,而是采用“腫塊”或“生長”,這些詞語暗含疾病可以被治愈的意思。Allan和 Burridge(1991)認為否認死亡是醫生和患者的典型心理反應。相比患者,醫生可能具有更大的恐懼,一方面承認死亡意味著他們專業能力的失敗,另一方面與臨終患者的溝通也存在挑戰。因此死亡委婉語和醫學術語成為醫生這一群體否認死亡以及隔斷具有壓力和使人痛苦的事情的一種方式;同時對于病人來說,死亡委婉語也是一種否認工具。
Fernandez(2006)分析了 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訃告中的委婉語,并通過概念隱喻理論探究訃告委婉語的形成機制。Camus(2009)分析了新聞報道中癌癥的隱喻,通過對《英國衛報》中37篇文章的分析,發現了15個概念隱喻,其中“癌癥是一場戰爭”是最明顯的概念隱喻,隱喻也成為人類認識死亡以及與死亡作斗爭的一種語言手段。Stadler (2006)研究了恐怖主義條件下對死亡的解讀,在此情況下,死亡已經變成一種公眾關注,打破原來的私人話語范疇,因此死亡禁忌在一定程度上也被打破。Lee(2008)對現代社會中的死亡禁忌語進行了再探究,并從現代性的角度重新考察了死亡。
國內對死亡委婉語的討論也比較多,既有中西文化的對比,也有對死亡委婉語形成機制的探索研究。田貴森(1989)從社會語言學角度分析了中外禁忌語和避諱語,提到在漢語中,人們提到“死”,一般都會采用比較委婉的表達。不同的階層、不同信仰者、不同年齡、以及死的場所不同,對死的表述都有不同。“對死采用描述、引申、比喻、隱諱的方法來表述,使得死的同義形式增至200多個”,這也說明語言形成和發展受到語言使用者的社會心理的影響。在漢語中,與“死”相關的委婉語達200 多個。(孫汝建,1996)
李思國和姜焱(2001)對英漢“死亡”代用語進行了跨文化分析,探討了“死亡”代用語的起源,以及英漢“死亡”代用語與中西方文化的聯系。黎昌抱和吳鋒針(2005)從社會地位、年齡和性別特征、宗教信仰、價值取向以及發展變化五個方面對英漢“死亡”委婉語作了對比分析,發現兩者的差異是由兩種語言民族各自不同的社會制度、價值觀、宗教信仰以及風俗習慣所決定的。張妍妍(2009)從文化角度出發,分析了中英死亡委婉表達在宗教信仰、等級觀念和社會因素三個方面的不同。
包麗虹(2000)從語言的靈物崇拜、漢民族傳統價值觀、宗教、喪葬習俗、一定歷史時期獨特的人文景觀五個方面入手,探討了語言與文化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力圖揭示出漢語死亡委婉語的文化成因。馬雯(2013)以認知語言學為理論框架,探討了漢語死亡委婉語的生成機制及本質,分析發現轉喻模型及隱喻模型為委婉語的生成提供了認知基礎。
死亡委婉語是社會語言學領域的一個研究視角,死亡話語的特殊性也促使中外學者對該分析視角的關注。但是這種傳統的分析,不論是對某種文化中的死亡委婉語的考察,還是死亡話語的跨文化分析,都不能停留在過去單一的分析角度,與其他分析視角的結合能夠開拓新的視角,如隱喻理論為研究死亡委婉語背后的形成機制提供了理論支撐。另外,在現代社會中,這種社會禁忌是否仍舊維持還是被打破,或許也能夠成為頗具意義的分析角度。
6 話語心理學
話語心理學是話語分析在心理學領域的應用,也是心理學話語轉向的標志。話語心理學以話語分析為分析方法,關注人們的溝通、互動和爭論,以及這些實踐在不同場景中的組織(Edwards & Potter,1992)。話語心理學認為許多心理現象可以被解釋成話語的特性,話語現象也不是隱匿的主體性心理現象的顯現,話語現象就是心理現象(邵迎生,2000)。死亡話語分析的實踐價值可以體現在話語心理學方面。通過分析人們在談論死亡時的語言,探究面對死亡時的心理,可以用于分析臨終患者的心理問題。
O’ Leary和Nieuwstraten(2001)通過分析老年病人談論死亡的語言,發現了死亡認識的三個階段以及在談論死亡時會出現的心理變化。死亡認識的三個階段包括:否認、沮喪(消沉)、接受三個階段,老年患者面臨的心理問題涉及:害怕被忘記、沮喪、能夠討論死亡的應對機制(情感偏移、利用歌曲、禱告和幽默等)。話語心理學以話語分析為基礎,能夠用于心理治療,特別是對于那些正在經歷死亡的人們。
話語分析與其他學科的整合借鑒,催生了跨學科的研究。作為死亡話語分析和心理學的結合界面,話語心理學能夠通過文本和言談的結構來考察人們的認知和心理,通過對現實世界中的自然語言進行分析能夠觀察到人類的內心世界,可以實現對“人”的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此類研究在未來具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三、結語:死亡話語研究的現狀、挑戰和未來發展
通過上述死亡話語研究的回顧,我們發現此類研究的話題涉及醫療情境中的死亡話語,如醫患溝通、醫護人員的敘事話語和患者的話語;以及和死亡相關的文本,即死亡是如何以文字的形式被呈現。內容主要涵蓋死亡的意義建構和死亡的意義傳遞兩個維度,即如何通過話語建構死亡的意義,以及如何向他人傳遞死亡的意義。從話語分析角度研究死亡話語,“死亡”更多的是一種話語建構,一種意義建構。
雖然死亡是人們規避談論的話題,但是受到網絡、電視等各種媒介的影響,這一問題卻變得日益公眾化,直接呈現在大眾面前。對死亡話語的分析也逐漸從文學作品的神壇,走向社會現實,人們開始關注現實中的死亡話語,如自殺、癌癥等,并催生了更多實證性研究。醫學的發展,特別生物醫學的人文和社會轉向,也促使人們關注死亡以及對死亡話語的分析。
而目前國內對死亡話語的研究仍主要集中于文學作品分析以及社會學研究,如人們對死亡的整體認識和態度;醫學領域對死亡相關的問題的討論,如目前緩和醫療、尊嚴死等,以及對死亡委婉語的分析等。國內對實際情境中的死亡話語研究仍舊比較少,這或許和國內整體的醫療環境和氛圍有關系,醫療糾紛和醫患溝通依然比較敏感,收集數據比較困難,加之中國目前的醫療環境的復雜性,也對我們客觀分析這種特殊的機構話語提出了挑戰。
語言學分析為死亡話語研究提供了一種細致的描述工具,透過話語去關注“人”和人的生死;死亡話語的語言學視角分析深入到此類話語在宏大敘事中的微觀層面,進行了細致入微和深刻的考察。不同的話語分析研究方法和視角也為死亡話語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語用分析、多模態話語分析、語類分析等,推動了話語分析研究的發展和理論建設。
死亡話語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社會意義,提供了社會生活特定領域的語言描述,豐富了對“人”的理解和研究,通過對死亡話語的研究,加深對死亡的認識,從“死”中解讀和理解“生”,能夠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生命價值。此類話語分析的意義也體現在其應用價值和實踐操作上。探究醫患交流中存在的問題或許能夠為建構更加和諧的醫患溝通模式提供參考;死亡話語分析的研究結果應用于臨床實踐能夠為醫護人員臨床工作提供指導,幫助醫護人員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
跨學科的發展催生了交叉學科領域研究,話語分析和心理學結合發展了話語心理學,醫學和語言學的結合或將催生醫學語言學,或臨床語言學,學科之間相互借鑒,促進共同發展。死亡話語未來研究不僅需要跨學科的整合,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也需要加強對語言社會生活中特定領域的關注,用語言學研究方法去分析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使語言學更多地干預現實問題,用于解決與語言相關的問題和任務。通過各種現代技術手段對真實口語文本語料進行分析,或許可以對某些問題進行深入分析,如關注語用的情感方面等,對語言學理論提供補充。死亡話語研究有待在未來獲得更大發展,其中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也包括語言與身份認同的建構。人們在死亡話語溝通和死亡話語的敘事中,通過話語建構其身份認同。對于國內的學者來說,我們也需要加強對具體情境中的死亡話語的研究,增加更多實證性研究。死亡是一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命題,相信死亡話語研究在未來也將獲得較大發展,出現更多跨學科、超學科研究,這也需要語言學者、醫護工作者和其他社會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北京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所高一虹教授和兩位匿名評審專家對本文提出了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1] Al-Ali, M. 2005. Communicating Messages of Solidarity, Promotion and Pride in Death Announcements Genre in Jordanian Newspapers[J]. Discourse and Society, 16(1): 5-31.
[2] Allan, K. & K. Burridge.1991. Euphemism & Dysphemism: Language Used As Shield and Weapon[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Anderson, W., S. Kools & A. Lyndon. 2013. Dancing around Death: Hospitalist-patient Communication about Serious Illness[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3(1): 3-13.
[4] Askildson, L. 2007. Discourse and Generic Features of US Army Obituaries: A Mini-corpus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Military Death Announcements[J]. Language, Meaning and Society, (1): 108-121.
[5] Ayodeji, O. 2013. Christians’ Perception of the Concepts of Death and Judgment: A Multimodal Discourse Analytical Study of Selected Editions of Christian Women Mirror Magazine International[J]. Journal of English and Literature,(10): 508-515.
[6] Bazerman, C. 2003. Speech Acts, Genre, and Activity Systems: How Texts Organize Activity and People[A]. In Bazerman, C. & P. Prior (eds.) What Writing Does and How It Does It [C]. London: Erlbaum.
[7] Berns, N. 2009. Contesting the Victim Card: Closure Discourse and Emotion in Death Penalty Rhetoric[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50): 383-406.
[8] Bhatia, V. 1993. Analysing Genre: Language Use in Professional Setting[M]. London: Longman.
[9] Borbasi, S. et al. 2005. Letting Go: A Qualitative Study of Acute Care and Community Nurses’ Perceptions of a“Good” versus a “Bad” Death[J]. Austrilian Critical Care, (18): 104-113
[10] Camus, J. 2009. Metaphors of Cancer in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Articles in the British Press[J]. Discourse Studies,(4): 465-495.
[11] Candrian, C. 2014. Taming Death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Discourse[J]. Human Relations, (1): 53-69.
[12] Carpentier, N. & L. Van Brussel. 2012. On the Contingency of Death: ADiscourse-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Death[J].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2): 99-115.
[13] Davis-Berman, J. 2011. Conversations about Death: Talking to Residents in Independent Assistedand Long-term Care Settings[J].Journal of Applied Gerontology, (3): 353-369.
[14] Duncan, S. 2011. Sadly Missed: The Death Knock News Story as a Personal Narrative of Grief[J]. Journalism, (5): 589-603.
[15] Edwards, D. & J. Potter. 1992.Discursive Psychology[M]. London: Sage.
[16] Fairclough, N. 1996. Language and Power[M]. New York: Longman.
[17] Fernandez, E. 2006. The Language of Death: Euphemism and Conceptual Metaphorization in Victorian Obituaries[J]. SKY Journal of Linguistics,(19): 101-130.
[18] Hasan, R. 1985. The Structure of a Text[A]. In M. A. K. Halliday & R. Hasan (eds.) Language, Context and Text: 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C]. Australia: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19] Holder, R. 2007. Oxford Dictionary of Euphemism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 Kress G. & T. Van Leeuwen. 1996.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M]. London: Edward Arnold.
[21] Krishnatray, P. & R. Gadekar. 2014. Construction of Death in H1N1 News in The Times of India[J]. Journalism, (6): 731-753.
[22] Lee, R. 2008. Modernity, Mortality and Re-enchantment: The Death Taboo Revisited[J]. Sociology, (4): 745-759.
[23] Lieblich, A., R. Tuval-Mashiach & T. Zilber. 1998. Narrative Research: Reading,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M].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24] Martin, J. & D. Rose. 2008. Genre Relations: Mapping Culture[M].Londres: Equinox.
[25] Miller, C. 1984. Genre as Social Action[J]. Quarterly Journal of Speech, (70): 151-167.
[26] Miller, C. 1994. Rhetorical Community: The Cultural Basis of Genre[A]. In A. Freedman & P. Medway (eds.) Genre and the New Rhetoric[C].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27] O’Leary, E. & I. Nieuwstraten. 2001. Emerging Psychological Issues in Talking about Death and Dying:A Discourse Analytic Stud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unselling, (23): 179-199.
[28] ?sterlind, J. et al. 2011. A Discourse of Silence: Professional Carers Reasoning about Death and Dying in Nursing Homes[J].Ageing & Society, (31): 529-544.
[29] Rizza, C. 2015. Death Row Statements: A Discourse of Play[J].Discourse Society, 26(1): 95-112.
[30] Semino, E., Z. Demjen & V. Koller. 2014. “Good” and “Bad” Deaths: Narratives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Interviewswith Hospice Managers[J].Discourse Studies, (5): 667-685.
[31] Stadler, N. 2006. Terror, Corpse Symbolism, and Taboo Violation: The Haredi Disaster Victim Identification Team in Israel (Zaka) [J].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 837-858.
[32] Swales, J. 1990. Genre analys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3] Tsai, M. 2010. Managing Topics of Birth and Death in Doctor-patient Communic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42):1350-1363.
[34] Weisman, A. 1984. Denial and Middle Knowledge[A]. In E. Schneidman (ed.) Death: Current Perspectives[C]. London: Mayfield Publication.
[35] Wildfeuer, J., M. Schnell & C. Schulz. 2015. Talking about Dying and Death: On New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a Formerly Postulated Taboo[J]. Discourse and Society, (3): 366-390.
[36] 包麗虹. 2000. 漢語死亡委婉語之文化成因探[J].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S1): 77-80.
[37] 傅恒. 2011. 英文訃聞的意識形態——《紐約時報》及其他三英文媒體中本拉登訃聞的批評話語分析[J].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4): 137-139.
[38] 黎昌抱, 吳鋒針. 2005. 英漢“死亡”委婉語對比研究[J]. 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1): 16-19.
[39] 李思國, 姜焱. 2001. 英漢“死亡”代用語跨文化對比分析[J]. 外語與外語教學, (11): 52-54.
[40] 馬雯. 2013. 漢語死亡委婉語的生成機制: 轉喻與隱喻視角[D]. 西南大學碩士論文.
[41] 邵迎生. 2000. 話語心理學的發生及基本視域[J]. 南京大學學報, (5): 109-115.
[42] 孫汝建. 1996. 委婉的社會心理分析[J]. 修辭學習, (5): 17-19.
[43] 田貴森. 1989. 從社會語言學角度看中外禁忌語和避諱語[J].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 (2): 108-112.
[44] 張菊芬, 魏躍衡. 2008. 訃告的語篇特征: 從話語分析角度探討[J]. 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 (3): 18-21.
[45] 張妍妍. 2009. 關于中英“死亡”委婉語的對比分析[J]. 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 (2): 144-145.
(責任編輯:呂紅周)
H030
A
1008-665X(2016)2-0001-07
2015-12-19;
2016-02-17
王景云,女,博士生,研究方向:社會語言學、話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