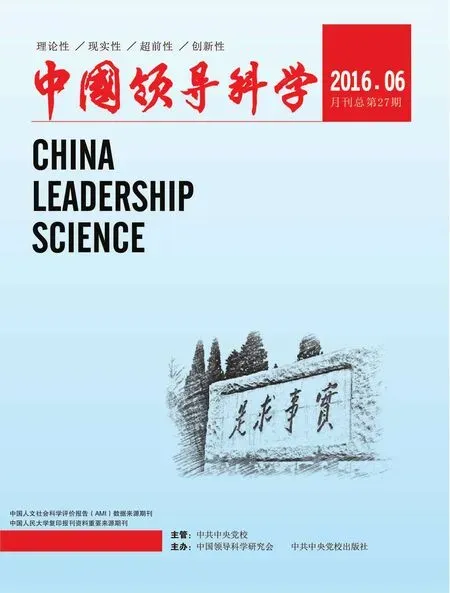李慶霖告“御狀”
黃志雄
?
李慶霖告“御狀”
黃志雄
文章摘自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的《知青家長李慶霖》。該書出版后受到有關專家高度肯定與社會的廣泛關注,《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藝術報》、《文藝報》、《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中華讀書報》等新聞媒體先后做了相關報道。該書為長篇紀實文學,不僅具有文學價值,還有很高的社會價值與文獻價值,對于研究中國當代史,尤其是研究“文革”、研究知青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填補了知青上山下鄉歷史中的部分重要空白。
1972年12月中旬,李慶霖每天吃完晚飯后,便坐在家中廳堂方形竹桌邊,鋪開信紙,一遍又一遍地寫了又改,改了又寫,然后又一遍遍地將信謄清抄正,哪怕是一個筆畫不端正,也要重抄一遍。他已經連續七八天,一吃完飯就坐在這兒。他忘記了一切,只是堅韌地一遍遍地重復著自己心中的訴說。他相信這封信語氣得體用詞恰當沒有錯別字,但就是不放心,就是情不自禁地要一遍遍閱讀檢查。當他再一次用手指按著字,一個字、一個字地讀了三遍后,確信沒有什么出入,已經講了所要講的話時,終于滿意了。他伸了伸懶腰,長長地噓了口氣。
他站起身來,先是在室內行走,后來又推門出去,站在院子里讓寒風吹拂自己。小城已經進入深睡,一片漆黑,只有天上的星星還在眨著眼睛。他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仰望天空。隨后,他轉身進屋關好門后,再一次拿過信來,作最后審定:
尊敬的毛主席:
首先,我向您老人家問好。
我是個農村小學教員,家住在福建莆田縣城廂鎮。家庭成分貧農。我的教員生涯已有二十多個寒暑了。
我有個孩子,叫李良模,是個一九六八年的初中畢業生。一九六九年,他聽從您老人家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毅然報名上山下鄉。經政府分配在莆田縣山區——萩蘆公社水辦大隊插隊落戶務農。
在孩子上山下鄉后的頭十一月里,他的口糧是由國家供應的(每個月定量三十七斤),生活費是由國家發給的(每個月八塊錢),除了醫藥費和日常生活中下飯需要的菜金是由知青掏腰包外,這個生活待遇在當時,對維持個人在山區的最低限度的費用,是可以過得去的。
當國家對上山下鄉知識青年的口糧供應和生活費發給斷絕,孩子在山區勞動,和貧下中農一起分糧后,一連串的困難問題便產生了:
首先是分得的口糧年年不夠吃,每一個年頭里都要有半年或更多一些日子跑回家吃黑市糧過日子。在最好的年景里,一年早晚兩季總共能分到濕雜稻谷兩百來斤,外加兩三百斤鮮地瓜和十斤左右的小麥,除此之外,就別無他糧了。那兩百來斤的濕雜稻谷,經曬干揚凈后,只能有一百多斤。這么少的口糧要孩子在重體力勞動中細水長流地過日子,無論如何是無法辦到的。況且孩子在年輕力壯時期,更是會吃飯的。
在山區,孩子經常參加農業勞動,不但口糧不夠吃,而且從來不允許分紅,沒有一分錢的勞動收入。下飯菜吃光了,沒有錢去再買;衣褲在勞動中磨破了,也沒有錢去添置新的;病倒了,連個錢請醫生看病都沒有。其他日常生活需要的開銷,更是沒錢支付。從一九六九年起直迄于今,孩子在山區務農以來,他生活中的一些花費都得依靠家里支持;說來見笑,他風里來,雨里去辛勞種地,頭發長了,連個理發的錢都掙不到。此外,他從上山下鄉的第一天起,直到現在,一直沒有房子住宿,一直是借住當地貧下中農的房子。目前,房東正準備給自己的孩子辦喜事,早已露出口音,要借房住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另找住所。看來,孩子在山區,不僅生活上困難成問題,而且連個歇息的地方也成問題。
毛主席:您老人家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我完全擁護;叫我把孩子送到山區去務農,我沒意見。可是,當孩子上山下鄉后的口糧問題,生活中的吃油用菜問題,穿衣問題,疾病問題,住房問題,學習問題,以及一切日常生活問題,黨和國家應當給予一定的照顧,好讓孩子在山區得以安心務農。
現在,如上述的許多實際困難,有關單位都不去過問,完全置之不理,都要由我這當家長的自行解決,這怎么能行呀?有朝一日,當我見閻王去,孩子失去家庭支持后,那他將要如何活下去?我真擔心!
今年冬,我的又一個孩子將要初中畢業了,如果過不了明春的升學關,是否再打發他去上山下鄉呢?前車可鑒,我真不敢去想它!
在我們這里已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中,一部分人并不好好勞動,并不認真磨煉自己,并不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卻倚仗他們的親友在社會上的政治勢力,拉關系,走后門,都先后優先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完成了貨真價實的下鄉鍍金的歷史過程。有不少我們地方上執掌大權的革命干部的子女和親友,縱使是地富家庭出身,他們趕時髦上山下鄉才沒幾天,就被“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發展的需要”調用出去,說是革命干部的子女優先安排工作,國家早有明文規定。這么一來,單剩下我這樣農村小學教員的子女,在政治舞臺上沒有靠山,又完全舉目無親,就自然得不到“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需要”而加以調用了。唯一的資格是一輩子在農村滾一身泥巴,干一輩子革命而已。
面對我們這里當今社會走后門成風,任人唯親的現實,我并不怨天,也不憂人,只怪我自己不爭氣。我認為:我的孩子走上山下鄉務農的道路是走對了。我們小城鎮的孩子,平常少和農村社會接觸,長大了讓其到農村去經風雨見世面,以增長做人的才干,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當孩子在務農實踐中碰到的許多個人能力解決不了的實際困難問題,我要求國家能盡快給一條自食其力的路子走,我想,該不至于無理取鬧和苛刻要求吧。
毛主席:我深知您老人家的工作是夠忙的,是沒有時間來處理我所說的事。可是,我在呼天不應,叫地不靈的艱難窘境中,只好大膽地冒昧寫信來北京“告御狀”了,真是不該之至!
謹此敬頌
大安!
福建省莆田縣城郊公社下林小學
李慶霖敬上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李慶霖這封信如何遞送到毛澤東主席處,傳說有多種多樣。
晚年毛澤東只能仰視,很難接近。據說,“文革”期間被關押在上海的毛岸英之妻,也即毛澤東前兒媳婦、義女劉松林(劉思齊)給毛主席連寄5封信,竟無下落。他又是如何收到了李慶霖的“御狀”?
有的說李慶霖為了避開福建省的審查,趁在省體工隊的女兒李良培進京參加全國田徑比賽時,帶往北京郵寄;也有的說李慶霖在中辦有親戚,往后親戚又演變成了同學、朋友;還有的說信是托一個去北京辦事的朋友捎去的。
其實,李慶霖送走那封信,并沒有外人想象的那么復雜,但也不是那么簡單。毛澤東能夠收到他的信,是因為李慶霖當時突然來了靈感。
那天,李慶霖懷里揣著剛剛寫好的信件,沿著小城巷道前往縣郵電局。郵電局離家不過十來分鐘的路程,李慶霖走走停停,心里一直打鼓,他怕毛澤東收不到他的信。突然,他腦子里靈光一現,想到外交部部長助理王海容經常陪同毛澤東接見外賓。他興奮地踅回家中。
李慶霖瞬間閃現出來的靈感,不僅為數以千萬計面臨絕境的知青帶來了希望與福音,也徹底改變了他自己一生的命運。這剎那間閃現出來的靈感,是打開歷史大門的鑰匙,它讓李慶霖走進了歷史。
(本文摘自《知青家長李慶霖》一書,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黃志雄著)
責任編輯:張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