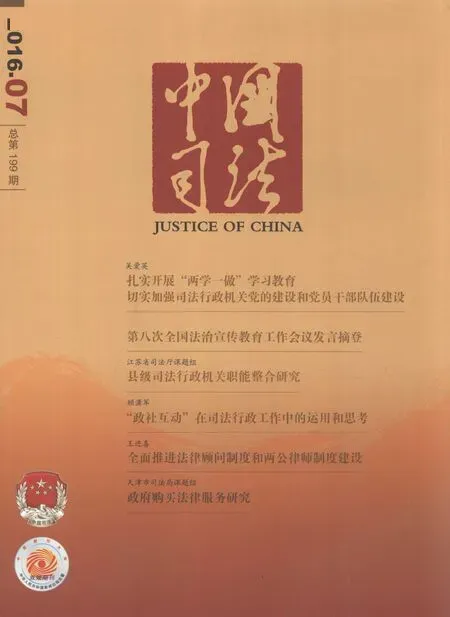言論廣角
卷首語
言論廣角
陳光中:嚴格司法應“準”字當頭
嚴格司法要求司法制度設計做到“三符合”,即事實認定符合客觀真相,辦案結果符合實體公正,辦案過程符合程序公正。“三符合”是高標準要求,核心是“準”。要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就必須在辦理所有案件中做到“準”字當頭,力求運用證據認定的事實符合客觀真相,運用法律正確適當。“準”字當頭,還要求有各種配套措施來保證。例如,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的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就是要讓領導干部尊重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保障審判權、檢察權依法獨立正確行使;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發揮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的決定性作用。司法案件有偵查、起訴、審判、執行等環節,涉及司法機關分工負責、互相監督,但最終靠審判解決核心問題,這是司法規律的反映。庭審不能虛置,不能走過場,要落實直接言詞原則,實現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制度,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發揮庭審質證、認證在認定案件事實中的核心作用。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庭審為中心,這是訴訟制度改革的方向,也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標志。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陳光中如是說,《人民日報》,2016年5月23日)
李 林:中國特色法學理論體系必須堅持人民性
我國憲法和法律是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相統一的體現,是通過立法程序上升為國家意志的人民共同意志。這種本質特征,決定了中國特色法學理論體系必然具有鮮明的人民性。這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要求法學理論必須始終堅持人民主權原則和人民至上的主體地位,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和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二是堅持法學研究和法治建設以保障人民根本權益、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三是堅持立法為民和民主立法,努力使每一項立法都符合憲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擁護;四是堅持執法為民和執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五是堅持司法為民和司法體制改革,依法公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決不能讓不公正的審判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群眾權益;六是堅持政法為民和“保障人民安居樂業”,從讓人民群眾滿意的事情做起,從人民群眾不滿意的問題改起,為人民群眾安居樂業提供有力法律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所長李林如是說,《北京日報》,2016年5月30日)
馬懷德:“放管服”改革促進法治政府建設
“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既是當下行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法治政府建設的基本要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在大刀闊斧推進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同時,提出了“放管服”改革思路,取得了積極進展。與以往改革不同,此次“放管服”改革注重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改革,將各項改革全面納入法治軌道,彰顯了法治政府品格。各級政府全面清理并公開行政審批事項,建立權力清單、負面清單和責任清單,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進一步下放審批權限,對轉變政府職能,優化公共服務,激發社會活力,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放管服”改革注重政府職能法定化,也有力地促進了法治政府建設。“放管服”改革的本質是全面清理政府現有職能,從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出發,厘清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將政府職能定位于宏觀調控、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生態保護,實現政府職能的法定化。只有實現政府職能的法定化,才能夠有效推進“放管服”改革,保障改革成果,也才能真正促進法治政府建設。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如是說,《光明日報》,2016年6月20日)
王 旭:律師應是法治理想的“流動運送者”
實現“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還必須更加充分發掘律師群體的多重功能。律師的法律服務不能僅停留在訴訟與糾紛解決的層面,也不能僅是“社會律師”這樣的職業定位,還應該在國家與社會兩個層面,以及在法律職業共同體之間,成為法律知識、價值與技術的“流動運送者”。律師和立法工作者、法官、檢察官等法律職業群體一樣,有著共同的法治理想。律師的活動舞臺也不應該局限于法庭和社會領域,而必須作為一種法律人力資本,連綴立法、司法與行政,最終通過個體身份的靈活轉化,實現法律知識、技術在不同領域的統一理解與運用。推動優秀律師進入立法和司法的職業序列,不僅是優化立法和司法領域自身的人才結構,還有助于實現傳統立法司法職業與廣闊社會的有機聯系與自由流動,使法治國家與法治社會的價值觀更加趨同。而設立公職律師與公司律師的舉措,更是直接形成了“社會、政府與國有企業”三元的律師隊伍,進一步促進了律師群體內部的專業分工,按照不同領域的具體法律需求和特征,提供不同的法律人力資源。這種分工必然會提高法律服務和公共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質量,也將統一的法律體系貫穿和實踐到不同的領域。更重要的是,“兩公”律師群體的出現,將使得法律風險預防和全程法律監管的理念牢固確立,對律師功能的理解不再停留在事后糾紛處理的層次,進而形成“全過程的法律風險預防”機制。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王旭如是說,《人民日報》,2016年6月20日)
高晉康 王 方 朱乾燦:大數據轉變普法模式 塑造公民新的守法思維
人們學習、主動運用法律多在事后,如果利用大數據實現了裁判尺度的統一,律師、當事人都可以運用大數據來預測判決結果,那么事前人們就可以預測到自己行為若引起訴訟的勝訴概率,對訴訟風險建立合理預期,從而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調整。人們主動接觸和運用法律的時間被提前,從事后遇到糾紛時才訴諸法律,轉變為在事前就先運用法律對自己的行為進行一次法律審查,以法律作為自己行為的重要參照依據。人們還可以根據大數據對案件的判決結果進行預估,決定是否將爭端訴諸法院。人們遇到法律糾紛時,可以先行利用大數據預估勝訴率,若己方勝訴率很低,會更傾向于采用其他方式解決。這樣便鼓勵了爭議雙方采取非訴訟的糾紛解決方式,不僅可以節約當事人雙方的訴訟成本,也可能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節約司法資源。人們對法律的使用從一個低頻率事件變成了一個高頻率事件,普法模式從受眾被動接受,轉變為主動查找法律、運用法律來調整自己的行為。實際上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已經開始自覺運用法律來指導自己的行為,該行為的長此以往的不斷重復便會固化為一種習慣,進而建立起一種尊法、遵法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高晉康、王方、朱乾燦如是說,《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6月21日)
游 偉:公開透明:司法“供給側”還需深化改革
司法權是國家事權,司法機關雖然地處地方,但執行的是全國的法律,它的依據必須是統一的“國標”,一些地方存在和內部掌握的“紀要”“意見”,即便針對同一法律適用問題也極不統一,形成司法實際依據的“地方化”“差異性”。又由于這些“紀要”“意見”不公開,不向上一級司法機關報備、審核,因此,也缺乏必要的統籌協調與監督。堅持司法公開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本前提,沒有公開,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公信。這既是真理,更是常識。但真理或者常識要轉化成司法操作的規范和實踐,有時卻并不那么簡單和容易,還需要社會各界廣泛予以關注,尤其需要司法機關做出更多的不懈努力。實踐證明,司法公開是法治現代化和司法民主化的重要環節,當然也是我國民主與法治建設事業的迫切需要。由此,各級司法機關應當站在不斷推進司法民主和維護執法公開、統一的高度,樹立司法為民的理念,不斷規范自身行為,通過切實努力,使司法公開這一憲法原則真正落地,成為人們能夠切身感受的司法行動。
(華東政法大學教授游偉如是說,《人民法院報》,2016年6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