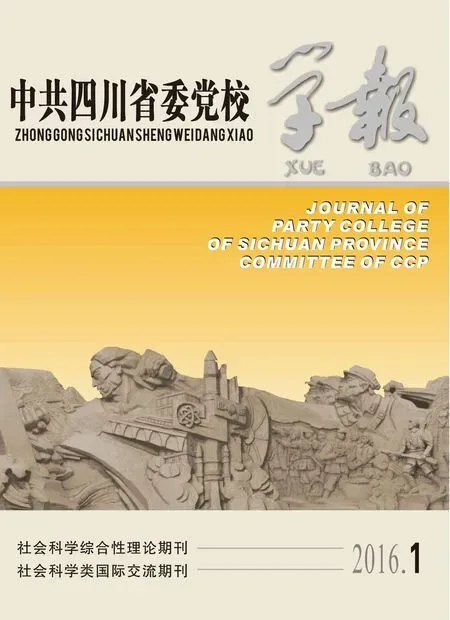論萊斯對消費主義狀態下人的存在方式批判
劉 楊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上海 200433)
?
論萊斯對消費主義狀態下人的存在方式批判
劉楊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上海200433)
[關鍵詞]威廉·萊斯;消費主義;異化;存在方式
[摘要]人的存在問題是當今時代的重大主題。對消費社會人的異化存在方式的批判是萊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獨具特色的思想。萊斯從商品與需求問題出發,追溯消費主義狀態下個體陷入異化存在的根源。他批判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異化的需求觀、拜物教思想和幸福觀,準確判定人的異化存在從生產領域轉向消費領域,開啟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新的理論批判視閾。盡管萊斯所構建的生態社會主義理想極具浪漫主義色彩,但他準確判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未曾改變,主張通過自然解放、勞動解放和構建穩態社會制度模式,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影響深遠。
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催生了消費主義的蔓延。從某種意義上,消費主義是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保持資本主義繁榮穩定的圭臬。西方國家推行“高生產、高消費”的社會生存模式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為資本主義統治合法性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人們帶來極大的物質生活享受。然而,“豐裕社會”也引發了人通過對物的占有并以物的形式而存在的現象,現代人的異化程度不僅沒有減輕,反而徹底“喪失了人性”。作為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奠基人,威廉·萊斯針對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消費主義盛行的現象,從解析商品與需求的關系路徑出發,激烈地抨擊了資本主義異化的“需求觀”、“拜物教”和“幸福觀”,準確判定人的異化存在從生產領域轉移到了消費領域,并斷言人應從生產中而不是消費中尋找滿足。鑒于當前學界偏重從生態危機根源視域解讀萊斯思想的研究范式,本文將立足人的存在方式這一獨特視角,尋找萊斯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中所蘊含的對于現代人的生存境遇的關懷。
一、萊斯對消費主義狀態下異化“需求觀”的批判
對于萊斯而言,消費主義創造了一種獨特的社會文化,它以市場為紐帶,通過控制“需要( need)、欲望(want)、內驅力(drives)或者偏好”等非理性因素,來服從資本主義制度這部龐大的機器。萊斯的需求理論以人與自然控制與服從的辯證法為哲學基礎,融合了自然與文化、理性與非理性、需要與商品關系等多重層面,橫跨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和人類學等多學科研究領域,深刻剖析了消費主義存在狀態下造成人的異化存在的直接原因與表現形式,其突出特征表現在:
第一,以人的需求問題作為批判始基,著力從需求異化向度追溯人在消費主義狀態下陷入異化存在的困境。“人與自然控制與服從的辯證法”是萊斯構建人的存在方式問題的邏輯基礎。這一思想澄明了人與自然內在統一原則,并將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內在需求與外在需求、控制自然與服從自然作為批判研究的理論對象。正緣于人與自然這一辯證統一關系,萊斯繼控制自然的意識形態批判之后,反求人內在的人欲向度,通過深刻分析需求結構本身、需求與商品內在關聯以及需求與幸福關系,進而廓清消費主義狀態下人何以遭遇異化的存在問題。在萊斯那里,控制自然的人本身被其內在心理所奴役,“對自然和人的控制在社會統治階級的引導下,內化為個人的心理過程;它是自我毀滅的,因為消費和行為的強制性特征破壞了人的自由”[1](序言P8)。萊斯建構人的存在方式問題的出發點十分獨特,他并未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作為批判對象,從資源供應的有限性問題來探討消費主義對人與自然產生的雙重危機,而是從主體人的需求問題出發對現代工業社會消費主義存在方式展開激烈批判。萊斯批判“高集約度市場布局”預設了一種不斷提高消費水平的生活方式,并將此作為個體最高價值標準。這種經濟形式通過曲解需求本性以及需求與滿足間的內在關聯,將主體的社會與經濟行為定位于依賴高消費的生活方式。實際上,這只不過是對在生產領域所遭遇到異化存在的補償。然而,正如阿格爾的“期望破滅了的辯證法”一般,萊斯指明個體期望的挫折與物質財富增長之間的錯位,使得人們必須重新定位需求的真正內涵。萊斯立足于需求碎片化與模糊性特征,表征消費主義存在方式產生的直接原因。他認為個體需求趨于碎片化特征,進而表現為不確定、模糊、隨機與臨時性。同韋伯批判理性資本主義精神一樣,萊斯也抨擊需求碎片化要求人遵從市場經濟的理性原則。他批判資本主義條件下人的需求被簡單拆分為瑣碎的部分,“個體身份成為每天被各種混雜信息重塑的順從的模具”[2](P18)。需求的碎片化瓦解了主體的豐富與完整,人自身、人際間關系以物的形式得以呈現。因此,個體尋找自身完整性則必須在不斷的商品消費中尋找需求碎片的滿足,這也直接導致了人們陷入消費主義的境遇中。
第二,駁斥傳統需求理論的抽象原則,堅持以具體的社會經濟形式作為理論分析的基本前提。在盧卡奇那里,馬克思超越了康德、黑格爾與費爾巴哈,因為他看到了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人是社會的存在物,同時是社會歷史過程的主體和客體[3](P71)。深受馬克思主義傳統影響的萊斯,也將現實的經濟生活作為分析需求問題的理論前提。在萊斯看來,前現代社會是建立在以親緣關系與等級秩序基礎上的社會結構,正基于相對穩固的社會等級秩序與統治權威的社會文化,商品流通才依據社會規范而非市場行為加以調節,同時,傳統手工藝技巧偏向于將生產原料與個體目標直接關聯,能夠直接獲得滿足自身需求的產品。萊斯認為,前工業社會交換活動十分單純,并未混雜著“欲望與恐懼情緒”[2] (P71)。在傳統社會文化統治形式下,需求的表達在特定時期會保持相對穩定性,這也為前工業社會人們未能陷入消費主義提供了有力依據。畢竟前資本主義“對于資本的理性使用,以及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形式,尚未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支配力量的狀態”[4](P53)。而現代社會摒棄了傳統所奉行的特權世襲形式,經濟理性原則主導全部生活,個體在直接的經濟生產和需求滿足中尋找穩定與權威,“主要的社會關系是個人自我興趣的認同,以最大限度的滿足自我需求為目標”[2](P4)。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隨著新技術發明、個性表達以及社會文化中介變化,主體必須不斷詮釋自身需求,在工業社會中滿足需求的形式隨著商品市場交換的擴展而不斷變化,同時,眾多商品與服務對象使個體陷入商品選擇的困境。
第三,拒斥傳統二元性需求理論,依托“物質-符號”需求二元結構追溯消費主義存在方式的理論依據。萊斯將傳統需求理論規約為生物與文化意義一般性結構、等級制度或優先權、行為主義者和批判主義三種需求結構類型[2](P53)。1萊斯批判傳統需求理論共性在于脫離現實社會生活以嚴格標準將需求進行簡單二元劃分,以確定與抽象的范疇作為理論構建基礎,淹沒個體需求的獨特特征。萊斯認為現實需求結構卻無法超越具體的社會歷史形式。在萊斯看來,人類的需求結構實質上就是一種物質與文化關聯的二元結構,即“物質-符號”需求二元性結構,“需求的每種表達或陳述都同時與物質和符號或文化關聯”[2](P64)。如果將鮑德里亞關于現代工業社會的符號消費批判看作以物質與符號分離為前提條件,那么萊斯則與之截然相反。盡管這種結構從外在形式上具有二元性特征,然而這是一種無法獨立運行的需求結構,也即物質與文化是彼此無法割裂的統一體,主體在經文化中介的現代工業社會必然在這種二元結構范圍內不斷詮釋自身需求。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二元結構是連續性的客觀存在,寓于社會經濟制度所有階段,只是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這種二元性結構更為深入。在前工業社會這種二元結構更明顯地表現為物質層面,而在工業社會則更多表現為文化的層面。必須指出的是,在萊斯那里,商品不僅是“特性的集合體”,也是物質-符號二元結構形式的載體,萊斯所要批判的是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需求與商品日益趨同,“商品增加造成經文化中介的需求從非物質領域(神話,傳說,禁忌)轉移到物質領域(物品)”[2](P66)。人們的需求被固定在商品領域,人的需求觀被扭曲為異化的需求觀,將商品消費作為人的唯一需要。
第四,基于需求模糊性特征與作為“特性集合體”商品尋找需求與商品內在關聯。萊斯深刻指出,現代工業社會人們在自身需求與商品消費之間建立密切而復雜的關系。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需求具有模糊性特征,表現為需求復雜性特征隨著外在社會條件而變動、滿足需求的標準無法確定、連接需求與滿足之間的紐帶-商品,其本質及其運轉模式十分模糊。萊斯把需求和滿足看作一種“復雜活動的基本指標”[2](P49),認為需求的滿足本身具有不可測、非穩定性特征。需求作為潛在心理意識與滿足需求的判斷之間是一種不斷形成、消解的動態心理過程。萊斯批判商品被理解為滿足欲望的手段,作為將沖動與目標連接在一起的紐帶[2](P24)。在萊斯看來,商品“不只是物質性的東西而是‘物質-符號實體’,也就是那些體現復雜信息與特征的東西”[2](P74)。萊斯認為早期邊際效用理論家并未在商品特性與需求之間建立單一對應關系,但卻承認商品具有自身特性。僅就早期的社會經濟特點而言,消費者憑借常識即可對商品進行準確評估。而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消費者可以從任意商品中獲得具體特點,人們喪失了對于商品特性的準確判斷,陷入異化消費的狀態之中。萊斯斷言現代工業社會條件下,商品具有復雜性特征,人們偏愛“特性集合”而非商品本身,“生產者最后賣掉的是特性的集合而不是商品”[2](P80)。商品并非以物的形式存在,而是被植入各種非穩定性、暫時性特征的“物質-符號”存在。因此,作為特性的集合體,同需求一樣商品也具有先天的模糊性特征。“商品自身分裂成一系列特性并失去了他們獨有的‘統一’”[2]〗(P80),“物體特性的分解代表了與需求碎片化的相互關系”[2](P82)。
二、萊斯對消費主義狀態下“拜物教”的批判
針對消費主義狀態下商品拜物教形式,萊斯通過批判吸收馬克思的“拜物教”思想、盧卡奇“物化”理論、馬爾庫塞的“技術理性”原則以及薩特的“惰性實踐”理論,揭示消費主義狀態下人全面陷入消費異化的境遇中。
萊斯認為“被工業化大生產和普遍商品交換所推動,當今市場經濟總體趨勢是,在物質產品中專門嵌入了形成人類需求特征的符號中介網。(或者更準確地說,將需求完全以商品為目標)這個過程馬克思稱作商品拜物教”[2](P67)。在萊斯看來,馬克思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是二十世紀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石,也是現代工業社會激進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無產階級喪失革命意識的重要理論根據。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神秘性:“商品的神秘性質不是來源于商品的使用價值。這種神秘性也不是來源于價值規定的內容。……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總勞動的社會關系反映成存在于生產者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由于這種轉換,勞動產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覺而又超感覺的物或社會的物”[5](P89)。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將商品類比為宗教體系,通過勞動將自身創造力表現為對象物,商品似乎獨具生命力,并與需求無關,看似具有謎一般性質。然而,在萊斯看來,馬克思卻揭示商品形式并不存在這種神秘性,“決定實際人類事物的并不是非人的市場力量,而是資本的擁有者”[6](P61)。萊斯批判人們被這種神秘性現象所愚弄,商品拜物教其實與馬爾庫塞的“虛假意識”異曲同工,商品生產成為安慰自我幻覺的舞臺。
萊斯高度贊揚了馬克思關于拜物教的深刻分析,認為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商品的全部神秘性。萊斯認為“工業主義擁有驚人的能力去創造具有各種新的特征的商品。可以說所有這些都是具有神秘性的”[6](P61)。但他反對馬克思從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二元劃分來解剖商品本質屬性。萊斯的物質-符號需求二元結構完全摒棄了這種思維邏輯。在他看來,商品生產與消費行為之間有著漫長的距離容易讓人產生錯覺。無論以何種目的進行的生產都必須經文化形式中介。事實是,“物質-符號二元性在商品生產和消費活動之間擺動,商品交換越多,擺動頻率越高”[2](P67)。只是早期社會人們參與產品生產每個環節,生產與消費主體十分明晰,商品特性作為自身內在自然屬性得以呈現;而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分工精細,個體只從事某一部分生產活動,必須通過購買其它產品滿足自身需求,生產者與消費者通過物的形式而存在,商品也便帶有了某種神秘性。
相對于馬克思的拜物教理論,萊斯認為盧卡奇的“物化”概念、薩特的“惰性實踐”和馬爾庫塞的“工具理性”具有相似的意義。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對商品形式占統治地位的人的存在方式展開深刻批判。通過對“物化”概念的考察,他揭示了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產階級何以喪失了革命的意識。在萊斯看來,盧卡奇的物化理論融合了馬克思、齊美爾和韋伯思想,將商品問題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最緊要的問題。盧卡奇強調商品結構本質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獲得物的性質”[3](P149),吸取并利用馬克思拜物教理論、韋伯的合理化原則以及官僚政治統治批判,揭示物化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普遍的命運使人成為一種非人的存在。在萊斯那里,如果說馬克思是借中世紀實物交換與現代社會貨幣交換形式作對比,指明人與人之間關系由個人關系轉變為產品這種物之間的關系,盧卡奇物化理論則是抓住了“理性主義成為工業主義的本質特征”,準確判明工業社會人類勞動經歷了理性化過程,勞動專門化、機械化、同質化、工資與時間量化等打破了勞動作為有機的整體。“生產過程機械地分解成部分破壞了個人與生產有機化的社會連接”[6](P149)。萊斯質疑盧卡奇對于前資本主義完全處于非物化存在狀態的假設前提,并且認為對于商品經濟下人的物化存在的論證尚不具充分性。但萊斯也批判這種勞動碎片化、機械化打破了原始勞動的有機與整體,而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勞動領域所遭遇的異化存在已經轉移到了消費領域,理性主義所設定的合理化牢籠使得人性普遍異化。
同物化一樣,技術理性也是人們難以逃離的普遍命運。針對馬爾庫塞對技術理性原則的批判,萊斯則認為技術理性“通過社會機構操控社會-在現代,政府與大公司彼此聯合-沒有給個體留下任何‘合理的’理由來反對這些制度的不公”[6](P67)。而技術理性的這種統治并非來自外在強制,而是人們當下生活的合理性。萊斯認為現代組織機構偽造技術會不斷進步假象是統治與合理性相結合的結果[6](P67-68)。事實上,盧卡奇、馬爾庫塞均反對通過激烈的社會政治變革來反對這種異化的人的存在方式,萊斯也同樣如此。萊斯批判現代工業社會商品“拜物教”形式,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商品作為物質-符號二元結構體現了偶像崇拜、象征主義、自我陶醉與圖騰崇拜,將人自身、人際間關系變成一種物的存在形式。相對于其師馬爾庫塞那種溫和的激進派,萊斯更是一個保守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他主張建立一種穩態的經濟制度—“較易于生存的社會”,實現勞動解放、自然解放以及人的最終解放,構建一種更加符合人性的人的存在方式。
物化可以被視為“惰性實踐現象的形式”[6](P72)。商品是自我實現的機會,“使得人類行為自身外在化并以物的形式而存在”[6](P69)。事實上,人們必須面對的現實是,主體必然通過勞動客體化的過程認識物的惰性存在,人類存在一個“外在于自身的存在”(being-outside-itself)。某種意義上,萊斯似乎更傾向于薩特惰性實踐理論的解釋原則,被人類需求驅動下生產的物品,也有自發表達人類目的相關的它自己的生活,只是這種惰性實踐的結果不是人規定物,而是物體系對人的需求的設定,為人通達自由王國設置阻力,在物與物關系背后隱藏著人與人之間的內在關系。正如萊斯援引愛默生的名言:“事物在掌控之中,卻駕馭著人類。”寓意理性看似掌控著自然,最終卻落入非理性之網中。針對消費主義狀態下看似具有消費選擇的主體自由,卻難以逃避以商品消費滿足自身需求的唯一選擇。需求的碎片化、模糊性使人構成完整的主體存在成為幻想。因此,在萊斯那里,拜物教的結果就在于,“工業經濟擴張,越來越多的自然環境和人的才能被卷入商品交換的軌道,卷入商品領域。萬物皆有用,同樣,萬物皆有價”[7](P323)。
三、萊斯對消費主義狀態下虛假“幸福觀”的批判
現存資本主義制度鼓勵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試圖在消費與幸福之間建立某種必然性聯結,將消費過程中個體需求的滿足作為自身幸福的源泉。資本主義這種虛假的幸福觀,鼓勵個體將幸福標準等價于消費商品欲望的滿足程度,遵從量的標準而非質的標準作為衡量個體滿足依據,把消費選擇自由作為生產中異化存在的補償。然而,正如阿格爾所言,異化的人并無幸福可言,這種異化消費的結果必然是一種異化的幸福觀。
首先,商品流變特性與需求碎片化特征造成滿足與幸福模糊性。“不論在前現代、非市場社會還是在現代市場經濟的早期階段,都有規定個人表達相應需求種類的高度結構化的社會模式”[2](P88)。在這種經濟模式下,社會文化形式相對穩定,盡管個體體驗經歷少許不同,但在這種高結構化社會模式下,社會整體文化形式塑造了個人關于物品與需求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而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作為特性集合體的商品,商品特性不斷改變繼而引發個體對商品需求種類處于流動狀態,個人關于特定物品適合特定需求的判斷也處于變動之中。商品特性依據個體需求、感官經驗、對象種類而重新劃分,需求碎片化為更小的組成部分,并依據市場信息重新組合、集聚、形成新的形式,只是這是一種臨時的、易變的、不穩定形式。居于流動、重組中的需求碎片化,阻礙個體形成需求連貫目標,從而使個體無法有效判定適合自身的特定商品,這也是萊斯所解釋現代人陷入消費主義之中而滿足感與幸福感卻變得模糊的重要原因。
其次,需求碎片化與特性集合的商品無法與滿足、幸福建立有效連接。萊斯抨擊現代文化傳媒傳達一種將商品消費與幸福聯系起來的錯誤觀念,以日漸消弭的原始性日常生活背景作為激發人們消費欲望的導引,進而將消費欲望的實現與幸福形象緊密關聯起來。萊斯批判文化工業將商品與業已消失的日常生活相連,其悖論恰在于正是工業化市場經濟的擴張導致了這種結果的產生。在萊斯看來,正是“需求碎片化和不斷改變的商品特性破壞了傳統更穩固的幸福感”[2](P89)。在前工業社會生產條件下,幸福建立在需求與商品特性直接對應基礎上,而在高集約度市場布局下,需求完全脫離與某種單一商品特性關聯。“個體消費選擇只代表對復雜而變動的需求碎片化和商品特性的暫時解決”[2](P90)。馬爾庫塞就反對將幸福與滿足需求直接關聯,“人的幸福應該是個人滿足以外的某種東西”[8](P316)。萊斯同樣反對從消費選擇中獲得成就感就判定商品特性有助于實現個體需求從而獲得滿足與幸福。事實上,正是這種變動不居的需求碎片化和商品特性集合形式,使得在滿足與幸福也具有模糊性特征。正像鮑曼所批判指出消費社會將人的需求不斷置于新的誘惑下,“對滿足的承諾和期許會優先于需要,且總大于既有的需要”,進而永遠“保持在一種懷疑和不滿足的狀態中”[9](P67)。
第三,以幸福模糊性特征推動個體從消費中尋找滿足具有不合理性。萊斯強調滿足與幸福的這種模糊性特征激發個體從商品消費中尋找存在感。他批判當下消費主義存在就是在個體的幸福滿足感與商品消費之間進行了一種實驗。個體自身的需求與感覺是“實驗對象”,而市場便成為個體尋找幸福感源泉的“實驗室”。然而,萊斯認為,由于個體時間的相對有限性以及產品信息的不充分特點,人們盲目追求消費商品的數量而犧牲了對其他需求體驗,也將阻礙個體關注質的需求以及產品自身結構與特質[2](P90)。同時,個體對對象的冷漠必然導致自身需求瑣碎與淺薄。“個體必然對想要和尋求滿足需求產品的細微差別變得越來越冷漠。需求內在特點要求個體必須在無限可能的商品特性中進行廣泛尋找以適應需求的碎片化”[2](P90)。進而,萊斯主張以質的標準而非量的標準作為消費行為的原則。
第四,消費主義導致生態失衡危及人類未來幸福。科學技術普遍應用于商品生產帶來主要副作用在于對環境危害的風險,而現有科技水平無法對潛在危機做出有效評估。就長期的風險評估而言,目前尚且無法確定高生產、高消費的生活模式對于環境的潛在危害程度。并且,針對復雜的生產與消費形式,個體與社會無法提供合理、健全的有效管控環境危機的解決方案,這也為科學技術在商品生產與消費過程中埋下的潛在風險帶來不確定性。在萊斯看來,從消費中尋找需求滿足幸福感這一現存實踐是一種“工業社會大規模自動實驗”,但是這一過程卻帶來了危及人類未來與其它生物的環境風險。然而,人們追求需求的短暫滿足卻掩蓋了這種長期潛在的環境風險。萊斯主張放緩技術創新和生產應用速度,對于技術的應用結果對復雜的生態系統的負面作用采取審慎態度,將可能存在的技術風險降低到最低水平,而最直接的有效手段便是“在數量上和種類上大幅度減少人造物”[2](P91)。
四、萊斯批判理論的特征與現實意義
法蘭克福學派基于抽象的人本主義原則,對于現代工業社會消費主義狀態下人的異化存在做出激烈批判。馬爾庫塞抨擊現代人已經成為單向度的人,“人和物以扭曲、限制或否定其本質(實質)的形式而存在”[10](P101)。弗洛姆將對物的占有的生存方式歸因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批駁“我就是我所占有和我所消費的一切”[11](P25)。“我就是我的占有物”,“我擁有它”,“它亦擁有我”[11](P68)。萊斯繼承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傳統,從商品與需求關系出發,以人與自然控制與服從的辯證法為邏輯基礎,從控制自然與控制人欲兩重向度開辟出解讀人由生產異化向消費異化存在方式轉變的根源。同時,萊斯以馬克思主義視域透視現代工業社會人的存在,開啟了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人的存在方式問題新的理論范式。萊斯關于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極具特色。
一是他開創性提出需求的“物質-符號”二元結構,并將其安置于特定的社會經濟關系中。萊斯的需求二元結構與鮑德里亞完全不同。鮑德里亞在《物自體》與《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中仍糾纏使用價值與符號的交換價值如何演變為倒轉的邏輯關系。在鮑德里亞那里,這種物與符號結構具有不平衡性,“物遠不僅是一種實用的東西,它具有一種符號的社會價值,正是這種符號的交換價值才是更為根本的-使用價值常常只不過是一種對物的操持的保證”[12](P2)。萊斯則完全脫離了這種傳統的兩分考察路徑,將需求二元結構視為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整體。這種二元結構從未分離過,它生成于社會經濟所有階段,只是每個階段表現的形式側重不同。從某種意義上說,萊斯的需求二元結構將鮑德里亞意義上的物與符號關系推向了彼岸。
二是萊斯預言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人的存在方式由生產異化向消費異化的轉向,突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并未改變”這一重要判斷[2](P87)。這種轉向并非是異化程度的減輕,而是雙重壓迫的開始。“消費過程異化的程度同生產過程一樣”[13](P106)。在萊斯看來,生產資料所有權與控制權仍被統治階級占有,世襲遺傳財富、權利的先天不平等、等級階層權利差異、生產領域遭受的剝削與壓迫仍是人們生存面臨的現實存在狀態。這種改變不過是通過文化統治在消費領域開辟新的維持資本主義統治合法性的領地。這種文化統治“不會永久性地改變任何生產領域的特征;并且像‘消費社會’和‘消費者主權’這種蒙昧主義觀念,暗示了消費者手中擁有重要的社會權利”[2](P87)。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統治形式,消費在大眾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不僅保留了生產關系基本結構,并且在大眾文化領域發生了決定性改變。萊斯抨擊現代工業社會“把受外界支配的需要內在化,擴大社會對于人內心生活的控制”[14](P154)。消費社會這種文化統治是新的極權統治形式,理性同一性原則不僅支配著生產領域,也主導了消費領域。
第三,萊斯強調這種由生產異化向消費異化的轉向,并非主張消費領域變得比生產領域更為重要,抑或在兩個領域中異化程度的不同,而是在消費主義這種經濟結構模式下探討此種改變對表達需求與滿足感、幸福感之間關系。萊斯批判消費社會中“完全以消費領域為目標來滿足需求”[2](P87)。更為嚴峻的問題是,這種消費主義存在方式已經彌漫于全球的經濟運作模式下,不僅發生在資本主義社會,同樣產生于官僚統治的社會主義國家。在此,萊斯給人類敲響了警鐘,提醒人們消費主義存在方式已經成為全球性選擇的人類整體生存模式,主張人們當從創造性的生產勞動中獲得真正的滿足。
第四,萊斯以需求與商品關系為理論突破口,但不以此作為判定消費異化的理論根據。萊斯的批判模式并非內在自然與外在自然、或控制人欲與控制自然兩個方面,萊斯對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貢獻恰在于以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為基本批判對象。這種批判范式對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具有重要意義,深刻影響了阿格爾、奧康納、福斯特等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批判范式具有一定的徹底性,盡管他所構建的“較易于生存社會”是一種浪漫主義的烏托邦,他的穩態經濟模式、技術分散化思想在經濟與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是如此脫離現實的社會生活,然而,他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批判作為最終落腳點突顯其對馬克思主義思想衣缽的繼承。萊斯提倡通過勞動解放、自然解放、構建穩態社會制度模式來重建人的存在方式,特別強調從創造性的生產勞動中尋找最終滿足,以量的標準而非質的標準重塑合理的消費方式,對于重新審視當下沉浸于消費主義的現實社會生活人的存在狀態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參考文獻〕
[1]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M].岳長齡,李建華,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93.
[2]Leiss W.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M].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6.
[3]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任立,燕宏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
[4]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馬奇炎,陳婧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6]Leiss W.Under Technology’s Thumb[M].Canad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0.
[7]Leiss W.Social Communication in Advertising[M].London:Routledge,1990.
[8]馬爾庫塞.現代文明與人的困境[M].李小兵等譯.上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1989.
[9]齊格蒙特·鮑曼.工作、消費、新窮人[M].仇子明,李蘭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0.
[10]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M].劉繼,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
[11]弗洛姆.占有或存在[M].楊慧,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9.
[12]鮑德里亞.符號政治經濟學批判[M].夏瑩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9.
[13]弗洛姆.健全的社會[M].孫愷祥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14]Leiss W.The Domination of Nature[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
(責任編輯:吳兵)
[中圖分類號]F713.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5955(2016)01-0093-06
[作者簡介]劉楊(1979-),女,遼寧大連人,復旦大學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資助項目《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人的存在方式的研究》(11JJD710001)。
[收稿日期]2015-1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