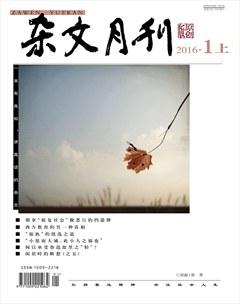被折騰的鰣魚
茅家梁
鰣魚味美,連魚鱗都得細細地嚼,不然,純粹是上海人嘲笑的暴殄天物的“洋盤”。
《萬歷野獲編·卷十七》里說,明代有皇帝好這一口,于是,大熱天從長江里好不容易覓得新鮮鰣魚“晉京”,就成了有關官員的頭等大事。“晉京”的鰣魚走水路,即使一帆風順,也得半月以上,所以其船晝夜兼程,急如星火,每到一站,便“求冰易換”,否則,魚兒腐爛,誰也擔當不起。那個季節,要弄一船讓鰣魚“完璧”如初的冰塊,談何容易!而實際上,底下接受指令的人倒沒有幾個驚慌失措的,“實不用冰,惟折乾(以錢代替實物)而行”。冰沒有,“冰炭銀”(如今天的“灰色收入”)可以有,以孝敬欽差——有錢能使鬼推磨,何況活生生的人了,所以,肩負重任的欽差慢慢吞吞,擺足架子,停靠的碼頭越多,勒索的機會就越多,故而,沒有哪個想一下子長上翅膀飛回金鑾殿復命的。
這么一路折騰過來,長官自然將消災的真金白銀頂破了大錢匣,而“其魚皆臭穢不可向邇(靠近)”,不幸而嗅之者,“幾欲嘔死”。“其魚到京,始洗刷進充玉食”。“洗刷”的過程中,烹制的過程中,難道沒有敢道破“天機”的御廚嗎?估計多半也是得了白花花的好處,緘口不語罷了。朝廷上,好多有見識的官員從別個“忠而獲咎”的遭遇中,吸取了反面的教訓,也就集體搗糨糊,單只蒙著皇帝一個人。
鰣魚以清蒸為美。臭得離奇、魚刺都突凸的鰣魚,如何敢上籠“裸蒸”?于是,掌勺的“雜調雞豕筍俎,以亂其氣”,再加上許多調料,哪兒還有絲毫的原味?反正“高貴者最愚蠢”,皇帝的味蕾早已逐漸異化了,筷子一夾:“嗯,鮮得眉毛都要掉下來!”而在一旁侍候兼窺測動向的家伙、“一條龍”服務的負責人,表面上沉穩從容,心下卻暗暗慶幸又一次“得手”或歪打正著。
聽喜歡吃臭魚的人說,這臭鰣魚鮮得野,鮮得邪惡,鮮得像K粉。不敢茍同。這世界上除了嗜痂成癖的怪物,有些“侈為珍味”的東西,實際上普通人都不堪下箸。有人說,物極必反,保不準這臭得驚人的鰣魚和徽州的名菜臭鱖魚差不多?沒有比較過。還有人說,這是對統治者的反叛和嘲弄。這“拔高”得有點牽強附會了。既鬧得盆滿缶盈,又可以賺頂“反封建反權貴的英雄”的桂冠戴戴,左右逢源,自然有更多的人接踵而至,學習、取經。算卦的說:“相互信任輕盈的擊缶而歌,后來必有別的吉祥。”怎么看,這都是極不正常的現象,卻偏偏有掌聲雷動。黠者瞎來來,他們一“吉祥”,老百姓就該遭殃了。
還是講那些臭鰣魚。據說當時有個從宮里派出到南方當“守備”的太監,“夏月忽呼庖人,責以饌無鮮鰣魚。庖人以每頓必進為言”,太監生氣不相信,“我每餐下肚的竟然是鰣魚?”下令拿來,仔細審查驗明“正身”后,才將信將疑地說,“其狀頗似,但何以不臭腐耶?”聞聽此事,人皆捧腹大笑。
現實中,這樣的“太監”不少。明明是好東西,只因為不“臭腐”,就招來無端的懷疑,十足的“洋盤”,反而混充吃遍天下無敵手的“美食家”。這些沒有喪失器官的“太監”卻喪失了立場,就只欣賞其“內核”早已軟噗噗的東西,而他們還一頭扎進去,盡管“幾欲嘔死”,卻聞其“臭腐”即食指大動矣。
要真正認識鰣魚,得誠懇地請教行家;想嘗一嘗鰣魚之鮮,不妨放下身段,讓高明的廚師做一條“清蒸”的,不放喧賓奪主的“花花綠綠”,吃“原汁原味”;如果能不辭辛勞地到產地去,調查研究兼追根溯源,親歷親為,逮一條鮮蹦活跳絲毫不經折騰的鰣魚來,肯定其樂無窮。
【小黑孩/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