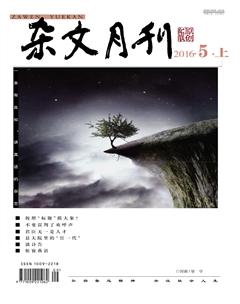期待新的制度供給
李泉佃
“供給側改革,很多人理解的光是經濟學意義上的供給,我的理解則是要提供新的制度供給,要提供新的制度體系。”
提出這個觀點的,是鄭永年先生。
鄭永年無疑是近年來在中國最具公共影響力的政治學學者之一。他的很多觀點,往往能超越各種政治化的紛爭,保持獨立的批判精神,給予公允和有說服力的解讀和分析。
鄭永年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還是諾丁漢大學中國政治研究所主任。我讀他的文章,以前更多的是通過新加坡早報網;后來,發現《參考消息》也開始高頻率地轉載他的文章了。對此,他頗為自豪地說,希望自己能活到100歲,好好地做學問,把中國解釋清楚。
鄭永年做學術的價值,在于他的獨立而深入的思考。比如,他提出,制度創新比技術創新更重要,要提供新的制度體系。
這個觀點,在他的新著《未來三十年》(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1月出版)中,有具體的闡述。
他說,中國的改革,從鄧小平開始,都是通過培養新的利益,來對既得利益構成壓力。在沒有新利益的情況下,要改革既得利益,突破舊利益的阻礙,是很難的。因為,你要改革老的利益,是需要成本的,而這個成本,誰來承擔?所以,就要在體制外培養新的體制,培養新的利益,對舊的利益和舊的體制構成壓力了,這些舊的利益、舊的體制,就不得不去改變自己。同時,新的利益也可以消化因為改變老的利益而帶來的成本。
那么,當下,有哪些舊體制,需要去改變,或需要去破除?換言之,有哪些新體制需要去創新?
鄭永年認為,中國三十多年改革的成功,動力在于五個角色的良性互動,即中央政府加上“四條腿”——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外資。
而當下最嚴峻的問題,是“四條腿”的作為問題。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這兩條腿基本上沒有什么大的動作;民營企業,除了互聯網這一塊外,其他方面也不怎么作為;外資看似平穩,但難以突破。
所以,鄭永年呼吁,中國要順利實施“十三五”規劃,就得提供新的制度供給,提供新的制度體系。
主要是三大領域。
一是,要化解反腐敗和改革動力之間的矛盾。
他不認為反腐敗會影響經濟發展。從長遠看,反腐敗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非常有利。但是,從短期看,反腐敗對經濟是有些成本的,即“整頓成本”。
所以,反腐敗要盡量減少對企業運作的負面影響,要建立健全新的政商關系,要大量起用新人。
鄭永年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的情況是,一旦一家企業的老總出事了,整個企業就完了;要整治政商關系了,就對商人避而遠之了;清除了腐敗者,起用的新人,則大多或沒有能力作為,或不敢作為。諸如此類的情形,已嚴重影響著企業和政府的運作。
其實,中央也已看到這些問題,并開始著手改進。比如,今年全國兩會,習近平總書記在與全國工商聯代表、委員座談時,就提出要建立新型的政商關系,要做到“親”與“清”。另外,習總書記也多次強調,也要對不作為官員零容忍。
二是,要處理好法律與改革之間的矛盾。
鄭永年建議,要清理舊的法律,加快分權,保護改革者。
他認為,中國在立法方面,往往重視加法,忽視了減法,而很多法律,已不合時宜,嚴重約束了改革。還有,法律要保護改革者。改革者得不到保護,官員就肯定不敢作為。
三是,要節制民粹主義,加快吏治改革。
鄭永年認為,中央政策除了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外,政策的落地,還有賴于官僚體系的執行力。
改革一定是有風險的,沒有風險,哪談得上改革?不容許改革者犯任何錯誤,將犯錯誤和腐敗之間畫等號,就沒有哪個官員敢于承擔風險。
還有,政務官的選拔、任用,還是墨守成規,一成不變,就必然會影響官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總之,鄭永年一再強調,一定要有新的制度供給。
今天,中國已處于“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發展仍然是要務,是硬道理。如果發展是可以持續的,則所有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但如果發展一旦出現重大問題,問題的性質就會變化。
良藥苦口,忠言逆耳。這種時候,鄭永年先生走出象牙塔、“國事家事事事關心”的做法,就顯得尤為必要且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