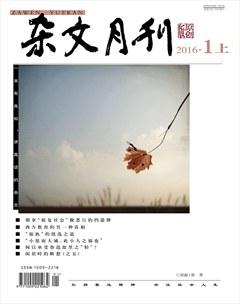割不斷那縷文化情結
李偉明
我較早的一個理想,是當上鄉文化站站長。那時候,在農村讀書,學校里通過考試出去改變農民身份的學生是百里選一,而我這人自信心一向不咋地,在參加高考之前,從來就沒想過讀大學的事。那時鄉里的文化站長,當然也不是大學生,他是“泥腿子文化人”轉正過來的。那年代,靠著半耕半讀而最終甩掉“牛糧”吃“馬糧”的人,基本上在每個鄉里都有,他們多數干的是文化活兒。這誘惑力,對于課余也喜歡舞文弄墨的“農N代”來說,該有多大!
說起來,老家所在的鄉鎮,還是有些文化味的。全地區第一家農民文化宮在我們鄉建成;時任文化站長是小有名氣的農民詩人;連續兩任鄉黨委書記都是作家型官員,一個出版了幾部長篇小說,一個是功底深厚的詩人。每逢元旦、國慶等節日,鄉里還經常舉辦征文比賽,農民文化宮墻上的宣傳欄,也專門開辟了“文學副刊”,發表本鄉作者的作品,而這些事,主要是文化站長具體操辦。所以,在我看來,做個文化站長,坐擁圖書室幾百冊藏書,籌辦各種主題的文化活動,還主持著宣傳欄這個重要陣地,定然是件幸福的事。
沒想到,后來自己還是擠過高考“獨木橋”進城讀大學了。讀的是當時最沒地位的師范學院,估計以后要回歸到農村中學當個語文老師。如果是這樣,在教學之余寫點東西甚至中長篇小說,也挺有意思的,說不定在某些方面會有些收獲呢!——那時,我已開始陸續在報刊發表些小豆腐塊,這個想法,并非全無現實基礎。
沒想到,命運軌跡再次出現意外,當了一個多月的實習老師后,畢業了居然沒有成為真正的教師,倒是滿懷欣喜進了市里的報社。其實,我并不想當新聞記者,只希望做一名副刊編輯。入職不久,總編派我參加一個活動的報道,我不情愿以記者身份寫這種稿件,把一位同事拉上,寫稿任務也轉讓給了他。稿子交上后,總編說是兩個人同去的,應當一起署名(看來這個行業挺講究協作),同事補上我的名字,其中一個字寫錯了,我看在眼里卻不吭聲,因為我正希望通過這個錯誤的名字表明那不是我。
多干了幾年就知道了,報社是新聞單位,在這里上班,不可能回避寫報道之事,尤其是年輕編輯,本身就兼有記者身份,說不定哪天就安排你做專職記者了。果然,后來便離開了副刊編輯崗位,日報記者、晚報記者、新聞編輯,采編口的什么活兒幾乎都干過了。我的職業,本來就叫“新聞人”嘛。
還好,不管是干哪個崗位,每年都能堅持讀點自己想讀的書,寫點自己想寫的文字,業余生活始終不會和“文化”離得太遠。從讀中學以來,沒有哪一年中斷過自發地寫點小東西,盡管收成少的年份只寫了寥寥數篇,但畢竟是堅持下來了。尤其是2007年以后,從零星發表“升格”為結集出書,對文化的興趣不減反增。
后來,我離開了工作15年的報社,到機關單位任職。工作性質變化后,真正檢驗出了自己的所思所想所追求,體會到了失去“歸屬感”的滋味。看看自己的處境,愈發感到自己的“境界”還是太低了,就像吃慣了鄉下土菜,總覺得城里大賓館的菜肴太沒味。那是一種味覺記憶使然。而我呢,囿于眼界、格局,顯然不是雄心壯志的人,也不是希望叱咤風云的人,我只適合做一些具體的小事,而且是自己有興趣的事,最好當然是和文化有關的事。因為在我的職業“味覺”中,留下最深印象的正是文化的味道,因此總是割不斷那縷文化情結。
當然,充當業余寫手至今,我也逐漸清醒地認識到,文化之于我,也只是“情結”而已,也可以說只是一種“單相思”。這么多年來的堅持,收獲的仍不過是些價值不大的小文章,現實和理想的距離太遙遠了。特別是最近這些年,我做的事和“文化”越來越遠,跳出圈子細思量,自己根本不是個文化人,也可以說本來就沒多少文化。只不過因為那縷情結,我潛意識里喜歡和文化人打交道,喜歡做和文化有關的事情,甚至,多年來還陸續寫下了一些和“文化”沾點邊的隨想文字。
現在,我將若干年來寫的和“文化”帶點關系的文字結集成《文化不是哈哈鏡》,盤點這一百多篇小文章,寫作時間跨度太大,內容東拉西扯,并無一個集中的主題。一本無主題的集子出版,沒個序言作交代似乎更為不妥。思來想去,有感而發,信馬由韁,寫下了上述這段同樣無主題的文字,權充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