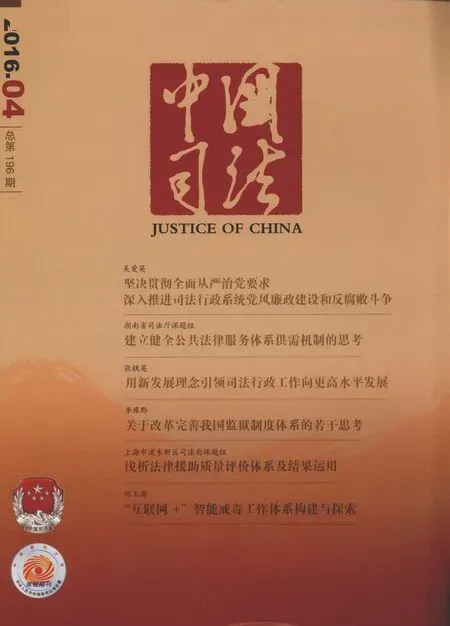律師法律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山西律師法律服務為例
郭 強(山西省司法廳)
?
律師法律服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以山西律師法律服務為例
郭 強(山西省司法廳)
當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提高供給質量出發,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成為必然選擇。談及此,筆者不由地想到律師法律服務的供給側問題。
以山西為例。15.6萬平方公里,3600萬人口。律師事務所和執業律師兩個數值,僅2015年,就分別增加28家、977名,“十二五”期間,分別增加了40%和100%,目前,分別達到640家、7200名;全行業業務收入約8億元。山西萬分之二的律師比重與發達國家相比、與法治建設的步伐相比,仍顯單薄,故增加絕對數值仍然是未來趨勢。但筆者亦覺,單從數值上看,基本是全國平均水平,在目前需求遠未及發達國家旺盛的情況下,供需關系相對還是基本適應的,究其最大的問題,就在于“質量”上的供需關系嚴重不適應。
有據可證。山西占北京的數值比例,律師事務所約為1/3,執業律師約為1/4,業務總收入僅約為7%。山西律師業務水平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高端、高收費業務長期被北、上、廣等地律師占領,本土律師基本上在一些中低端、中低收費業務上爭奪市場。山西律師綜合素質總體不高,既懂法律又懂外語、懂金融、懂貿易的復合型人才嚴重短缺。山西律師事務所規模不大,至今沒有百人所,近年增加的80%是個人所,合伙所盡管還占有半壁江山,但總體比重正在逐年下劃;專業化程度不高,基本上是什么都會干、什么都干不精的“萬金油”;品牌效應不大,放眼國內幾乎沒有什么知名度,影響力微弱;管理方式簡單粗放,律師凝聚力差,大多單兵作戰,缺乏歸屬感,“租賃柜臺”現象較為普遍;至于國際化等更高層次更是無從談起。這些都是山西律師法律服務市場的供給側問題,亦或在全國有一定的代表性。
山西律師也在苦苦探索自強之路。一些律師事務所重組為全國知名律所的分所模式、與省內外多家律所的聯盟模式、加盟大型律師機構的連鎖店模式、改制為特殊普通合伙所模式、律所合并模式,如此等等,都是山西律師知恥而后勇的有益嘗試。我們也深深為之歡欣鼓舞。
如何做大、做強、做優律師法律服務業?推進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乃必由之路。我們不妨從全要素生產率的“生產要素構成”來分析。普通生產要素構成主要是勞動力、資金、土地等,而律師法律服務生產要素構成應當是包括理念、人才、業務、質量、管理、供給方式等多方面的綜合體。這些生產要素的改革正是律師法律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內容。
——理念先行。理念是行動的先導。創新、開放、協調、規范的發展理念必不可少。要把創新的理念融入律所管理、業務建設、隊伍建設等方方面面,讓創新成為常態風尚、形成深厚氛圍、產生不竭動力;要以開放的理念與外界在人才、信息、業務、管理等方面打通關隘、沖破藩籬,敢于引進來、走出去,切勿固步自封、閉門造車;要以協調共進的理念實現城鄉、區域以及不同律師事務所和律師業務的協調發展,先進帶動落后、強項帶動弱項,實現共同進步;要以規范發展的理念保障律師業的推進發展在法律、法規、規章框架體系之內,不做出格越界之事。
——推進律師業務轉型升級。律師業務轉型升級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要鞏固充實傳統訴訟、仲裁和非訴訟業務,使其常做常新、煥發生機。在此基礎上,要立足職能,發揮好律師熟悉現行法律規定的專業優勢、相對客觀處理法律事務的職業優勢、立足經濟社會生活的實踐優勢,緊緊圍繞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以及安全廉潔發展,圍繞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圍繞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圍繞參與化解代理涉法涉訴信訪案件、參與矛盾糾紛調解、參與公共突發事件處置等,找準切入點、著力點,發揮作用、彰顯優勢,在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和民主法治建設的同時,完成律師業務的轉型升級。
——提高律師業務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靈活性和適應性。靈活性和適應性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必然要求,前提是預見性和超前性。要加強調查研究,及時洞察中央和地方的大政方針,捕捉信息前兆,增強對經濟社會和民主法治建設走向的預見,引導律師業務未來預期,使律師業務導向適當超前至少同步于需求變化。當前在中央實施“三去一降一補”政策形勢下,化解產能過剩成為重要任務,必然要依法實施市場化破產程序,隨之兼并重組、破產清算以及相關衍生業務將成為未來幾年重要的市場預期,律師業務亟待超前謀劃、調整方向、跟進服務,從而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贏。
——改進律師法律服務供給方式。供給方式是溝通聯系供需雙方的橋梁媒介,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環節。“互聯網+”上升為國家戰略的今天,在利用新一代信息技術優化和集成生產要素,改變生產要素的使用結構,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從而創造出嶄新業態的生動場景下,“互聯網+法律服務”的供給方式,不僅會帶來律師法律服務供給方式的一場革命,而且會極大地促進律師業務分工與細化,產生律師業務的規模化效應,解決法律服務市場拓展的瓶頸問題,形成更多的特色服務品牌,帶動律師法律服務供給側的全面改革。
——提高律師隊伍素質。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沒有一支高素質的律師隊伍一切皆空。政治素質、業務素質、職業道德素質一樣都不可少。要形成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主導的繼續教育培訓、實習培訓、崗前培訓、業務骨干培訓、專題培訓、交流培訓與律師事務所自發組織的日常集中學習培訓、律師個人自主學習培訓相結合的立體式人才培養體系,打造若干業務和管理領域的領軍人才;要請進來、送出去,通過多種渠道方式加強人才培養;要在高端、緊缺領域和復合型方向加強人才培養;要建立社會律師與“兩公”律師、老中青梯次結構合理的律師隊伍;要關心律師的政治進步、個人成長,為他們發揮作用提供更多機會、搭建更好平臺。
——加強律師事務所科學管理。管理也是生產力,管理也是效益。科學有效的律所管理,應當是能使律師業務分工更加有利于體現高端專業性、薪酬制度更加有利于激發創業積極性、內部運行更加有利于保障高效性和協調性。以此為標準,來衡量目前律師事務所所謂團隊制和分散制、提成制和薪金制、簡約制和公司制、所有權經營權統一制和分離制等各種形式的律所內部管理結構,才更有價值和意義。一句話,律師事務所管理要以提高勞動生產率、鼓勵價值創造為核心。
——建立律師業務質量評估體系。法律服務質量是律師的立業之本、執業之基。建立律師業務質量評估體系,既是律師增強責任心、提升服務水平的需要,也是確認律師服務成效、保護律師合法權益的需要。要建立起科學合理的質量評估機制,按照不同律師業務類別的特點,遵循其內在規律,建立包括委托人滿意度、律師自身工作量、律所管理監督、社會公眾和管理機關認可度等內容的指標體系;建立專業權威的評估機構;建立客觀公允的評估方法;評估的結論得到及時的公布和充分有效的運用。
——防范律師執業風險。執業風險是律師必須面對的“伴生品”,是始終懸在律師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有些律師倒在《刑法》306條的“絆馬索”下,有些律師事務所和律師被證監會的巨額罰單命中,難怪有人嘆曰“螳螂捕蟬黃雀在后”。律師事務所要建立嚴密的風險防控體系,加強對從接案到結案全過程的研判、審核、監督,構筑起堅固的“防火墻”。律師要加強自身素質和修養,樹防線、守底線,提高抵御風險和誘惑的能力,建立與委托人之間充分的理解、尊重、信任與合作,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盡職盡責地提供服務。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要加強風險防控的教育引導,建立統一的執業保險機制,最大限度地解除律師的后顧之憂。
——鼓勵建設區域性大所、強所。律所的規模是衡量律師業水平的重要標尺。四川明炬合并33家律所,捍衛本土榮耀,打造成西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所、強所之路,值得學習借鑒。作為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要鼓勵支持律所搞合并,實現人合、資合、理念合、業務合、信息資源合,大家抱團取暖,互信、互聯、互助、互補,產生“1+1>2”的效果,產生規模效應,降低運行成本,應對大宗業務、大數據時代的挑戰。
全面依法治國正在深入推進,“十三五”規劃的大幕已經開啟,律師法律服務伴隨經濟社會前進的腳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重道遠!
(責任編輯 張文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