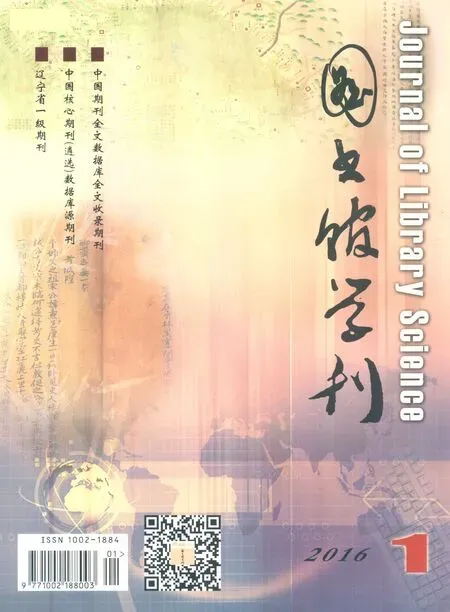唐代秘書省校勘工作探幽*
郭偉玲(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
唐代秘書省校勘工作探幽*
郭偉玲
(浙江傳媒學院文學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秘書省作為國家圖籍機構,在保存、傳遞、校勘、刊印古籍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以唐秘書少監顏師古及其著作《匡謬正俗》為基礎,探討了唐代秘書省內的圖書勘正工作的內容、流程及其參與人員。
[關鍵詞]唐朝秘書省校勘
[分類號]G256.1
*本文系浙江省社科聯科研項目“唐代文館及其藏書研究”(課題編號:2014N087)成果。
魏晉以來,國家圖籍機構進行了多次藏書的校勘工作,并設立了秘書郎、校書郎、正字等專掌國家圖書保藏、勘校工作的職官,至隋唐時期,校勘成為圖籍機構的日常工作之一。以學術論,圖書校勘“或是正其文字,或厘定其句讀,或疏證其義例”[1],因此唐代秘書省內的校勘工作可以分為兩類:由秘書監、秘書少監帶領校書郎、正字所完成初步的文字刊正工作,即文字和句讀的厘定;或由秘書省引進專業學者進行的學術勘校工作,即從音韻、訓詁的角度對圖書進行深層次的義例勘校。筆者即以唐秘書少監顏師古及其著作《匡謬正俗》為基礎,初步還原唐代秘書省內的圖書勘正工作。
1 顏師古與《匡謬正俗》
1.1顏師古
顏師古(581~645),名籀,字師古,以字行于世,雍州萬年(今陜西西安)人,著名經學家、史學家,仕唐27年,秘書省任職16年,歷任直秘書內省、秘書少監、秘書監等職位,為唐朝貞觀年間的秘書省建設做出了突出貢獻。
1.2《匡謬正俗》
顏師古有文集60卷,亡佚;編撰圖書有顏師古注《急就章》一卷、注《漢書》120卷、《安興貴家傳》卷亡、顏師古《王會圖》卷亡;參與編纂圖書有《周易正義》16卷、《大唐儀禮》100卷、《武德律》12卷又《式》14卷《令》31卷、《隋書》85卷《志》30卷;其中“所注《漢書》及《急就章》,大行于世”[2]。
另,顏師古還有一部類似于秘書省工作日志的圖書,即《匡謬正俗》。與其他著作不同,該書乃未竟之作,是由其子符璽郎顏揚庭于其身后整理而成,總為8卷,于永徽二年(651)呈上。《全唐文》載有其《上匡謬正俗表》:
“臣揚庭言:臣亡父先臣師古,嘗撰《匡謬正俗》,稿草才半,部帙未終。……臣敬奉遺文,謹遵先范,分為八卷,勒成一部。……謹赍詣闕,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深震悚。永微二年十二月八日,符璽郎臣顏揚庭上。”[3]
由引文可知,顏師古在生前對《匡謬正俗》曾有規劃,但僅完成了一半,其依據當為顏師古生前所制定的圖書凡例、篇章目錄等內容;而圖書定稿則是顏揚庭按照其父所擬定好的編撰凡例整理而成。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匡謬正俗》的撰寫者依然是顏師古,而其子揚庭只是后期編輯者,重新界定了卷的劃分,形成圖籍,于此之外無所增刪,對此書的內容依然保持尊重,主要內容依舊是訂正圖書的謬誤和典制的錯位。此書表上之后,唐高宗給予了高度評價,于永徽三年三月十五日,由中書侍郎來濟擬詔表彰:
顏師古業綜書林,譽高詞苑,討論經史,多所匡正。前件書發明故事,諒為博洽。宜令所司錄一本付秘書閣,仍賜其子符璽郎揚庭絹五十匹。[3]
唐廷對顏師古秘書省16年的任職高度認可,夸贊其史學、經學才能卓著,于訓詁、校勘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匡謬正俗》的體例內容融洽廣博,適合入藏秘書省,進行官方的推廣。雖然《匡謬正俗》屬于非完整著作,但由于其特殊體例,書內具體條目引證豐富,論述中肯,援引了眾多唐之前的古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其評價極高:
考據極為精審。……古人考辨小學之書,今皆失傳,自顏之推《家訓·音證篇》,實莫古于是書。其邱區禹宇之論,韓愈《諱辨》即引之,知唐人已絕重之矣。戒山堂《讀史漫筆》,解都鄙二字,詫為獨解,不知為此書所已駁。毛延齡引《書序》俘厥寶玉,解《春秋》衛俘,詫為特見,不知為此書所已引。洵后人證據,終不及古人有根柢也。[4]
2 秘書省校勘工作
2.1《匡謬正俗》凡例
《匡謬正俗》全書分8卷,計182條,“前4卷55條,主要論諸經訓詁音釋,后4卷凡127條,皆論諸書字義、字音及俗語相承之異”[4],從該書的內容來看,其宗旨主要體現在糾正圖書中讀音、注釋的錯誤,并對出錯的原因進行考據,進而指出合理的解決方法。顏師古之所以編撰此書,其原因多種。
其一,顏師古出身于顏氏,精通訓詁。顏氏家族以學術傳家,門內多為文字音義方面的專家,父顏思魯在訓詁方面也有專長,欲注釋《急就篇》而未成;叔父愍楚著《證俗音略》、游秦著《漢書決疑》。
其二,顏師古“于貞觀中,與國子祭酒孔沖遠同定《五經正義》,師古更承其叔父游秦之業,注《漢書》100卷,當時被稱為班氏功臣;又以世俗之言多謬誤,質諸經史匡而正之,謂之《匡謬正俗》”[5]。顏師古多次參與唐廷關于圖書的校勘和注疏,并負責了《五經》的考訂和《五經正義》的編纂,獨著了注《急就篇》和注《漢書》,其文字讀音、含義等方面的知識堪稱舉世無雙,因此其晚年整理編撰《匡謬正俗》具有充分的個人主觀條件。
其三,顏師古本人在秘書省負責圖書文字刊正長達10年,負責校書正字進行圖書典校時候的釋難答疑,“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2],見多識廣,積累了豐富的實例經驗,有編纂此書的可能性。筆者討論焦點主要放在《匡謬正俗》后3卷的問答內容,分析其考證內容和問答方式,進而考證唐秘書省內校勘工作的具體表現形式。
2.2《匡謬正俗》的校勘內容分析
以中華書局出版的1985年版《匡謬正俗》的卷六、卷七、卷八為基礎材料進行問題內容的分析,可以看出3卷內容主要集中在文字的意義、讀音、訓詁、典故等方面,主要提問方式有以下幾種:
①問文字的含義,或問曰:“俗呼檢察探試謂之覆坼,坼者,何也?”[5]這就是從文字本身的含義來提問,之后的回答也主要圍繞著該字的讀音、使用、典故來進行說明。
②提問特定文字的使用原因,主要集中在正俗字和古今字的區別,這樣的問題占最后三章近一半的篇章,其提問方式主要是“俗呼……謂之……,何也?”“俗謂……為……,何也?”“今謂之……,古號……,何也?”主要提問正字、俗字的使用與古字和今字的使用原因,而其回答主要集中在文字的使用范圍和形成這種使用方式的原因。
③提問文字古今意義的區別,主要提問方式是:“謂……為……,有舊義否?”“于義何取?”“別有異義乎?”而回答內容也主要集中在文字意義的演變,通過不同時代圖書的引用,說明隨著時代變遷,文字意義所發生的變化。
④提問文字訓詁方面的疑惑,問曰:“俗謂何物為底,底義何訓?”[5]另外還有這樣提問,“其義定何訓解?”
⑤提問文字讀音方面的問題,主要集中在古今音和南北音的區別,如“今人讀……謂……,得通否?”“……北人讀……,南人讀……,何者為是?”另外還有關于讀某種音的原因,“呼……為……音,有何依據?”
⑥關于事實性和典故性質的提問,如“……謂之……,……是何物?”這是關于事實性的問題;“人或有復名,單稱者于理云何?”這是關于事理性的問題;“俗謂……為……,此語有何典故?”這是關于典故和歷史的提問。
綜合以上對《匡謬正俗》卷六至卷八中問答式條文的總結,可以看出,這些問題涉及面廣,專業性強,有字義方面的,有字音方面的,有字形方面的,也有三者交織在一起的,而回答則是考證精確審要,引證豐富,是顏師古考釋古籍、校正古注、解說俗語、刊正文字的結晶。
2.3《匡謬正俗》與唐秘書省校勘工作
劉曉東《〈匡謬正俗〉平議·自序》說:
顏籀學承家訓,志規前典。審音考文,(圭石)然中理;訂經注史,展也大成。季年復撰《匡謬正俗》,雖未能卒業,然梗槩已具,倫脊可尋。觀其審諦如帝,密察足以有別;推十合一,發揮足以旁通。辨故籍之失解,考屬文者用事之誤,摘發凡數十事,率能是正前修,徐申新羲。齡俗言之遷嬗偽溷者,莫不振葉沿波,探究本始。[6]
可以認為,這是一本關于顏師古在進行其他圖書典校和注釋時候,所產生的問題的集錦,那么從圖書的內容、撰寫體例來看,聯系顏師古的學術和仕途經歷,就可推測出,《匡謬正俗》此書后3卷內容應該是顏師古在秘書省任職期間,于工作中遇到的關于圖書疑難問題的總結和記錄,其原因如下:
①從圖書本身的內容來看,前4章與后4章的內容存在明顯區別,前面4章討論儒家諸多經典的訓詁、音釋,其靶向對象為儒學經典,這與顏師古的學術經歷相符合,顏師古從貞觀初就開始著手《五經》《漢書》《急就篇》的校勘、注疏,前4章的內容當為在這個過程中所產生的疑難問題,而且是顏師古認為有必要進行特殊強調的條目,而且諸多學者都有關于《匡謬正俗》與《漢書注》之間內容的聯系,其中內容詳略相輔,指向明確,中間雖然有相悖的結論,也是出于顏師古在不同時期所產生的不同認識;后4章主要涉及諸類圖書中的文字的讀音、意義、典故、正俗字形的使用等方面,其靶向不單單局限于儒家經典,而擴大到了諸類圖書,這與其秘書省的任職背景完全相符。貞觀七年,顏師古被任命為秘書少監,主掌秘書省內圖書的勘校典正工作,《舊唐書》有言:“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2]這樣的職責結合該書的后4卷內容,不難看出,其中諸多條目當產生于秘書省校勘過程中的疑難問題,而顏師古則是負責答惑解疑的少監,其中的回答應該引證豐富,有理有據,也正如書中所記載的那樣。
②從圖書的體例上來看,前4章的條目開篇指出問題所在,然后羅列史料,進行說明,屬于注疏式的撰寫方法;而后4章則與前面迥然不同,采用問答式的方式,具體條目開始由某人提出具體的問題,關于音義典故等,然后進行回答,其形式主要是:“或問曰……答曰……”“問曰……答曰……”“……問曰……答曰……”或者“某問曰……某答曰……”,可見這是一種雙向的交流,不是單方面在文獻勘校中出現的問題,而是一種為對方答疑的行為的記載,這樣結合顏師古長達十數年的秘書省生涯,結論不言而喻。
③從具體的條目來看,尤其是卷八中所出現的兩個人名,引證于下:
禽或問曰:“易云:失前禽唯謂鳥耶?及其獸耶?”董勛答曰:“凡鳥未孕者為禽,鳥獸通耳。……”[5]
關雎蔡南問:“詩關雎尸鳩,今何鳥?”董勛答曰:“……”[5]
殊死或問曰:“每見敕書,或云殊死以下,或云死罪以下,為有異否?何謂殊死?”董勛答曰:“……”[5]
從引文中可以看出,這3個條目中出現了兩個人名,其中蔡南為其中一個問題的提出者,而董勛解答了這3個問題,從常理上推斷,顏師古個人著述中收錄他人的論述的條目,值得商榷。而筆者以為,這種記載他人論述的行為更能進一步說明《匡謬正俗》后4卷的內容屬于顏師古秘書省中刊正圖書的工作記錄。之所以這樣推斷是因為從常理上說,秘書省人才濟濟,從令狐德棻、魏征至虞世南,多為博學之士,除了世人共知的鴻學大儒之外,當時秘書省還“多引后進之士為讎校”[2],注意吸收新鮮血液,而當時顏師古擔任少監一職,負責圖書刊正工作,但并不意味著所有的問題必須由其本人解答,而董勛則是其中擅長解答事實性問題的學者,顏師古于工作之時,認為其解答精辟審要,信手記之,而后收錄進《匡謬正俗》,卷八的這3個條目更加有力地支持了筆者的猜想——《匡謬正俗》后4卷為顏師古秘書省職責履行的工作記錄。
3 秘書省校勘工作流程
綜上所論,筆者嘗試勾勒出唐秘書少監顏師古在秘書省內的校勘工作狀態。唐制,秘書少監為秘書省的副長官,武德四年改秘書少令為秘書少監,置一人,“(秘書)監掌經籍圖書之事,領著作局,少監為之貳。”[7]可以說秘書少監職責是負責輔佐秘書監管理秘書省內的日常庶務,為秘書省第二長官。唐代,秘書省擁有自己的校書地點,“門侵校書廳”[8],而顏師古作為省內副長官,當有自己單獨的辦公地點,因此校書廳與顏師古所在是相互獨立的,而當校書郎在典校圖書過程中出現了疑難問題時,應該不會隨時就去問詢顏師古,應當是當時進行記錄,而后在一定的時間段內,面對眾人提出問題,類似于現代的答疑會,《舊唐書·顏師古傳》有載:“所有奇書難字,眾所共惑者,隨疑剖析,曲盡其源。”[2]其中“眾”和“共”字體現了顏師古工作內容,由顏少監親自解答的問題必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是眾校書郎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超出了校書郎的能力之外,才由顏師古進行當眾釋疑,追溯其文字淵源,進行詳細的剖析答疑。
除了集體圖書校勘活動,結合顏師古的學術生涯,其中從貞觀四年至貞觀十九年去世,近16年都在秘書省度過,在這期間,《隋書》的編撰、《五禮》參編、《五經》校訂、《五經正義》的撰修、《漢書》注疏、《急就篇》注釋等著作一一完成,在時間上可以說存在很多重疊,如《隋書》和《五禮》、《五經正義》和《漢書注》,兩者在實踐上存在重合,可以說顏師古在秘書省的編撰任務幾乎沒有停息,顏師古作為秘書少監不僅僅要負責省內圖書勘校的答疑工作,還要負責眾多圖書的編撰,甚至還在聽令于東宮太子,為其文治功績添磚加瓦,可以說顏師古的秘書省生涯是非常繁忙的,而這種繁忙也是顏師古在無意于仕途之后的選擇,自貞觀七年太宗斥責后,顏師古就“乃闔門謝賓客,巾褐裙帔,放情蕭散,為林墟之適。多藏古圖畫、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7]。在這樣的心態下,顏師古依托于秘書省豐富的收藏,潛心學術,著力著述,終成一代鴻儒,可以說秘書省的任職生涯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顏師古的學術地位,而顏師古憑借其穩固扎實的家學淵源、豐富的小學和訓詁修養,指導秘書省內的圖書勘校工作,使得秘書省內圖書在博學之士的指導下,其校勘和抄寫行為更加科學和規范,從而減少了圖書的錯誤,樹立了秘書省圖書在唐朝的權威性,更好地發揮了秘書省作為國家圖籍中心的作用。
參考文獻:
[1]梁啟超著;夏曉虹點校.清代學術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劉昫,等.舊唐書·顏師古傳[M].二十四史簡體字版.北京:中華書局,2000.
[3]董誥,等.全唐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4]紀昀,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M].整理本.北京:中華書局,1997.
[5]顏師古.匡謬正俗[M].北京:中華書局,1985:盧見曾序.
[6]劉曉東.匡謬正俗評議[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
[7]歐陽修,宋祁.新唐書[M].二十四史簡體字版.北京:中華書局,2000.
[8]王溥.唐會要[M].北京:中華書局,1955.
郭偉玲女,1983年生,講師。研究方向:圖書史。
·研究綜述·
收稿日期:(2015-07-28;責編:姚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