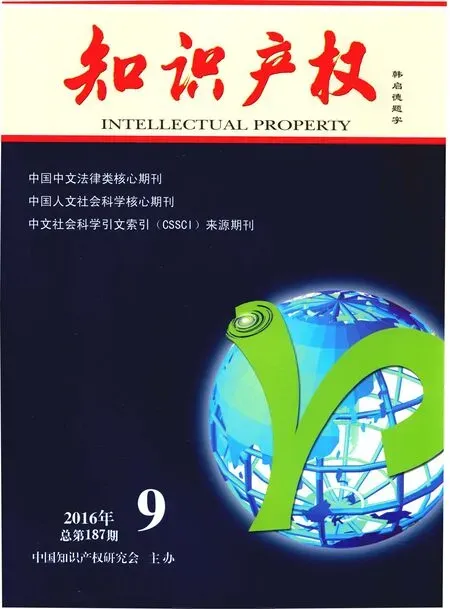等同原則對功能性特征的適用
——評法釋[2016]1號第8條
李春暉
等同原則對功能性特征的適用
——評法釋[2016]1號第8條
李春暉
內容提要:最新司法解釋法釋[2016]1號第8條對功能性特征提出了定義和不同于傳統等同原則的等同標準。這種對功能性特征和普通技術特征的區分在技術層面是困難的,在權利層面會導致權利要求保護范圍因技術特征是否被認定為功能性特征而產生極大不同,從而推動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爭議,影響權利人行使權利。事實上,美國司法實踐以及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在權利要求中的目的、在語言學上的關聯、在司法實踐中的解釋方式、等同原則與功能性特征的根源與目的等,均表明功能性特征應與普通技術特征一樣適用傳統的等同原則。即,對功能性特征等同侵權的標準,應為“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功能性特征 等同原則 反向等同原則 權利要求的解釋
一、問題的提出:功能性特征不再適用等同原則?
(一)等同原則的引入和適用
在我國專利實踐中,《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法釋[2001]21號,以下簡稱《規定》)第17條正式引入了等同原則:“專利法第五十六條第一款(即現《專利法》第59條第1款a《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專利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若干規定〉的決定》(法釋[2015]4號)已修正。)所稱的‘發明或者實用新型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以其權利要求的內容為準,說明書及附圖可以用于解釋權利要求’,是指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應當以權利要求書中明確記載的必要技術特征所確定的范圍為準,也包括與該必要技術特征相等同的特征所確定的范圍。”“等同特征是指與所記載的技術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領域的普通技術人員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征。”其中,“必要技術特征”的措辭與終被否定的“多余指定原則”b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01年9月29日向北京市第一、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發的《專利侵權判定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47條:“多余指定原則,是指在專利侵權判定中,在解釋專利獨立權利要求和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時,將記載在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中的明顯附加技術特征(即多余特征)略去,僅以專利獨立權利要求中的必要技術特征來確定專利權保護范圍,判定被控侵權物(產品或方法)是否覆蓋專利權保護范圍的原則。”有某種程度上的呼應,司法實踐已經以全部技術特征原則取代之c法釋[2009]21號第7條。另,法釋[2015]4號已對《規定》的措辭進行了修正,將“必要技術特征”修改為“全部技術特征”。。該《規定》所確立的等同原則的基本標準,即手段、功能、效果的基本相同,則一直延續下來d在法釋[2015]4號對《規定》修正之后,“等同特征,是指與所記載的技術特征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并且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特征。”但本文不討論判斷是否等同的時間節點和“創造性勞動”的問題。。
(二)功能性特征的解釋
審查指南提及了“功能或者效果特征”及“功能性限定的技術特征”e《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二章3.2.1節第7段。,但未直接定義。《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09]21號,以下簡稱《解釋》)第4條涉及“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術特征”,《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法釋[2016]1號,以下簡稱《解釋二》)則定義了“功能性特征,是指對于結構、組分、步驟、條件或其之間的關系等,通過其在發明創造中所起的功能或者效果進行限定的技術特征,但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僅通過閱讀權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確地確定實現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的除外。”f法釋[2016]1號,第8條第1款。如何識別功能性特征的問題,筆者將另文討論。三者所指為同一對象。
在侵權救濟程序中,《解釋》第4條規定,“對于權利要求中以功能或者效果表述的技術特征,人民法院應當結合說明書和附圖描述的該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及其等同的實施方式,確定該技術特征的內容。”若被控產品與說明書及附圖(以下簡稱說明書)記載的具體實施方式不相同也不等同,即使其落入功能性特征g當涉及“等同”時,指的是技術特征。當涉及侵權判定或新穎性創造性、支持問題等審查基準時,指的是權利要求(技術方案)。為行文簡潔,本文不作特意區分。的語義范圍也不構成侵權。
該第4條涉及了“等同”。從其措辭來看,這里的“等同”非指傳統的等同原則,而是功能性特征的解釋所使用的一種手段。它與等同原則的標準有何異同?在這一點上存在分歧。“基本相同的手段”這一要素似無太多爭議,分歧主要在于對功能和效果這兩個要素,是“相同”還是“基本相同”。若考慮到該第4條的目的是“確定技術特征的內容”,亦即解釋權利要求的技術特征,而非進行侵權判定,認為該“等同”的標準是“基本相同的手段、相同的功能和效果”是有道理的,畢竟功能性特征就是用功能或效果來限定該技術特征本身h國家知識產權局2013年9月26日發布的《專利侵權判定標準和假冒專利行為認定標準指引(征求意見稿)》中,提出了“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的標準。但是在國家知識產權局2016年5月通過國知發管字[2016]31號印發給各地知識產權局的《專利侵權行為認定指南(試行)》中,完全未涉及權利要求保護范圍的確定。。相對于傳統的由三個“基本相同”構成的“標配”等同原則而言,我們不妨將只有一個“基本相同”的“等同”稱為“低配等同”。
(三)功能性特征不再適用等同原則?
基于前兩節,可自然推知,對于經說明書和附圖解釋的功能性特征仍可適用等同原則。即,經過《解釋》第4條的解釋,功能性特征的內容包括與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以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和效果的實施方式。這是判定字面侵權(相同侵權)的基礎。進一步,在等同原則之下,與該功能性特征相比,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和效果的技術特征,為等同技術特征,構成等同侵權的基礎。
然而,最新頒布的《解釋二》第8條規定:“與說明書及附圖記載的實現前款所稱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術特征i法釋[2016]1號第8條采用了“實現……功能或者效果不可缺少的技術特征”的說法,與法釋[2009]21號第4條的“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的說法有所不同。為簡潔起見,本文仍采用“具體實施方式及其等同實施方式”的說法。即使在法釋[2016]1號之前,法釋[2009]21號第4條采用的“具體實施方式”的說法也并不意味著包含所有不相關的細節。換個角度,即便包含這樣的細節,其等同的范圍必然是很寬廣的,寬廣到跟不考慮該細節一樣。相比,被訴侵權技術方案的相應技術特征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且……j為行文簡潔,本文均略去了“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這樣的用語,除非有特別強調之需。在被訴侵權行為發生時無需經過創造性勞動就能夠聯想到的k參見注釋d,本文不討論判斷是否等同的時間節點和“創造性勞動”的問題。,……與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其中,“與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這樣的措辭使得該第8條的邏輯比較凌亂。如果說第8條的目的在于直接規定如何判定功能性特征的相同或等同的標準的話,則相當于廢除了《解釋》第4條。而如果說《解釋二》第8條的目的在于進一步細化《解釋》第4條的話,則“與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這樣的措辭又與該第4條確定功能性特征的內容的目的不符。
事實上,按權威解釋,《解釋二》第8條即功能性特征的最終保護范圍,不應再對功能或效果進行“二次等同”l宋曉明、王闖、李劍:《〈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的理解與適用》,載《人民司法·應用》2016年第10期,第28、31頁。,這就是為什么使用了“與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這樣的措辭。即,雖然最高人民法院聲稱《解釋二》不與《規定》和《解釋》相抵觸,不存在取代它們的問題m同注釋l,第36頁。,事實上《解釋二》第8條有兩個功能:一是對依據《解釋》第4條對功能性特征進行解釋的方式進行進一步明確,二是對功能性特征的等同原則進行特殊規定。
進一步,從《解釋二》第8條的措辭“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對應于“與功能性特征相同或者等同”兩種情況來看,唯一合理的理解為:“與功能性特征相同” 對應于手段、功能、效果均相同的情況,是對技術特征內容的確定,對應于《解釋》第4條,但相當于取消了其中的“等同”;“與功能性特征等同”則不屬于《解釋》第4條中所確定的“技術特征的內容”,而是對《規定》中等同原則的修正,即舍“標配”等同原則而采“低配等同”標準n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2013年9月4日下發至北京市屬中級法院和基層法院的《專利侵權判定指南》中,第39條和第54條即已分別體現了與《解釋二》類似的相同侵權和等同侵權判定規則,但從字面上并未排除二次等同。。
如此,則兩個方面均存在疑問:《解釋》第4條所確立的對功能性特征內容的確定方式真的不再包含任何“等同”手段了嗎?對功能性特征本身的等同標準有必要不同于普通技術特征嗎?即使假設《解釋二》第8條中的“等同”肩挑雙重角色,既作為確定功能性特征的內容的手段的一部分(以免出現與《解釋》第4條的矛盾),又作為對功能性特征本身的等同原則的新規定,則前述第二個問題仍然存在。甚或假設《解釋二》第8條不是對等同原則的修改而是對功能性特征斷絕了適用傳統等同原則的可能性,問題則是:功能性特征不再適用等同原則嗎?
無論上述諸問題如何提出,其實質是一樣的。為避免邏輯混亂,并鑒于《解釋二》第8條事實上包含了對功能性特征的“低配等同”(無論出于何種意義),本文將把該第8條視為延續了《解釋》第4條對功能性特征的解釋,即,作為相同侵權(字面侵權)的標準,功能性特征的保護范圍覆蓋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因此本文的問題是:對功能性特征本身,應與普通技術特征一樣適用傳統的等同原則。
二、等同原則與功能性特征的美國實踐
事實上,無論等同原則,還是對功能性特征的解釋,除《解釋二》第8條之外,我國均借鑒了美國的實踐。
美國專利實踐中的等同原則發端于Winans v. Denmead案(1853年)o56 U.S. 330 (1853).,而在Graver Tank & Mfg Co. v. Line Air Products Co.案(1950年)p339 U.S. 605 (1950).中明確了如今通行的“三個基本相同”的等同標準。
我國《解釋》第4條則類似于《美國專利法》第112條f款:“組合方案權利要求中的特征可以被表達為執行指定功能的手段或步驟,而不記載支持該功能的結構、材料或動作。這樣的權利要求應被解釋為覆蓋說明書中所描述的相應結構、材料或動作,以及其等同方案”。該條款是發源于Westing-House v. Boyden Power Brake, Co.案q170 U.S. 537 (1898).的衡平法原則“反向等同原則”(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或稱逆等同原則)針對功能性特征的具體化r閆文軍著:《專利權的保護范圍》,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0-151頁。。該原則的含義是即使被控方案在權利要求字面含義范圍內,但與體現于具體實施例的真正發明相比是以實質上不同的方式實現相同或相似的作用,則不構成侵權s同注釋r,150頁。。可見,《解釋》第4條和美國專利法系從正面陳述如何解釋功能性特征,而作為侵權抗辯原則的反向等同原則系從反面涉及何種技術方案不構成侵權。為論述方便,本文將兩方面均稱為“反向等同原則”,并在提及該原則時僅指代上述解釋方式,并不意味著相關機構或文獻明確提出了“反向等同原則”這個概念。
關于等同原則與第112條的“等同”之間的關系問題,美國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在Pennwalt Co. v. Durand-Wayland, Inc.案(1987年)t4 USPQ 2d 1737.中,認為第112條中的“等同”涉及的是相同侵權的判斷,而非等同侵權的判斷;并進一步認為等同原則針對的是每一個技術特征,而非權利要求技術方案的整體。1997年,美國最高法院在Warner-Jenkinson案uWarner-Jenkinson Company, Inc. v. Hilton Davis Chemical Co., 520 U.S. 17 (1997).中進一步確認,1952年《美國專利法》第112條并未取消等同原則。
這樣,在經反向等同原則“解釋”(法律問題)之后的權利要求基礎上可再施加作為侵權判定原則的等同原則(事實問題),即“三個基本相同”的標準vSee Kimberly A. Moore, Timothy R. Holbrook, John F. Murphy, Patent Litigation And Strategy, 4th edition, p532.。
三、功能性特征仍應適用等同原則
可見,關于等同原則和功能性特征,我國很大程度上借鑒了美國的專利實踐。然而《解釋二》第8條也對美國實踐進行了一些修改。這到底是因為中國特色的專利實踐所必需呢,還是因為我們簡單地置美國多少年的司法經驗于不顧呢?
(一)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沒有實質性區別
首先,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在權利要求中具有相同的目的,即概括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有一些文獻在論及技術特征的解釋時,區分概括性的技術特征和非概括性的技術特征,意指前者在說明書中是有記載具體實施方式的,而后者沒有。這種區分沒有太大意義,因為無論對什么技術特征的解釋,最終都要歸結到對構成技術特征的“元概念”的理解。對于所謂的非概括性技術特征也就是說明書中沒有更下位的具體實施方式的技術特征,其本身可視為一個元概念,需要結合內部證據和外部證據來解釋其含義。對于所謂的概括性技術特征包括功能性特征,當將其基于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進行解釋之后,為理解方便可認為按照具體實施方式的內容對技術特征進行了改寫,那么改寫后的技術特征將是由非概括性的技術特征也就是“元概念”組成的。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所謂非概括性的技術特征,可以認為其在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就是其自身。故本文僅作功能性特征以及非功能性特征的普通技術特征這樣的二元劃分。
其次,二者在語言學上是相關聯的,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功能性特征的使用多因技術發展和語言局限導致找不到恰當的已有術語。很多普通術語的淵源正是對其指稱的事物所完成的功能或任務的表述,例如“濾波器”、“剎車”、“夾具”等wGreenberg v. Ethicon Endo-Surgery, Inc., 91 F.3d 1580, 1583-84, 39 USPQ2d 1783, 178-87 (Fed.Cir.1996).。《解釋二》第8條將“……僅通過閱讀權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確地確定其實現……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的”限定功能或效果的技術特征(例如“變壓器”、“放大器”)排除在功能性特征之外x《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及說明(征求意見稿)》(第十三稿),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2月發布:第8條第1款及其說明。,部分目的即在于區分功能性特征與成熟普通術語所構成的普通技術特征y另一部分目的在于排除下面這種情況:不涉及成熟的普通術語,仍然是對功能和效果的描述,但是對于功能和效果的描述足以確定權利要求的保護范圍,例如,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九章涉及的軟件領域的所謂功能性限定,很多情況下實為對軟件模塊所欲完成的操作的描述,就有可能符合《解釋二》該但書的規定。信息來源: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庭審判長、《解釋二》執筆人李劍:《最新專利法司法解釋全文解讀》,在中國知識產權研究會“《侵犯專利權糾紛案件司法解釋(二)》與專利訴訟證據運用培訓班”上的講課,北京京燕飯店,2016年4月24日。,這正是基于對上述淵源的正確認知。
與美國實踐相似,上述對適用反向等同原則的排除是因為認為已經普通術語化的功能性語言的內涵、外延是清楚明確的z同注釋w,“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simply that a ‘detent’ or ‘detent mechanism’ is defined in terms of what it does, but that the term,as the name for structure, has reasonably well understood meaning in the art.”。但這種清楚明確至多是語言學意義上的,而非專利法意義上的。因為使用任何術語進行的概括,都應在專利文件上下文中獲得其含義。比如,對特定技術方案可能并非所有變壓器均適用,而只能依據該專利申請的技術背景、發明點來確定滿足特定條件的變壓器具體實施方式。因此,即便被排除的術語不明確適用反向等同原則,其仍然難逃依據說明書和附圖來解釋的命運。
(二)對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沒有實質性區別
基于上述,對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也不應有任何實質性區別,而事實正是如此。
中外專利法都認同申請文件可對術語另有定義。對說明書有明確定義的情況當然沒有任何爭議@7例如《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二章3.3.3節第8段。。但在說明書中沒有明確定義時何種情況可視為“另有定義”,有多種不同理解。一種認為,若從說明書來看所用術語明顯不是其常規字面含義,則應按說明書限定其含義。另一種認為,所用術語基本上都要基于說明書進行解釋,因為其含義必在申請文件之上下文中形成。我國司法實踐采后一理解。據《解釋》第2條、第3條,法院依據內部證據(說明書、附圖、相關權利要求、專利審查檔案)對權利要求的理解和解釋無任何前提條件,且內部證據優先于外部證據(公知文獻及通常理解)。這意味著法院認為權利要求的術語其實不存在獨立于所有內部證據、處于真空之中的“字面含義”。相反,其含義總是依據內部證據確定的,所謂的字面含義其實決定于外部證據,只有在沒有內部定義時才出場。確實,該《解釋》第2、3、4條均為對折中解釋原則@8《專利法》第59條第1款。的細化,且為層層遞進的關系,第4條(反向等同原則)只是在第2、3條的規則下,針對功能性特征這種特殊情況作出的具體規定,并不意味著功能性特征之外的技術特征的解釋就與功能性特征相反。
換言之,針對功能性特征的反向等同原則是語言的特點、權利要求技術方案的概括的性質和方法以及利益平衡原則所導致的利用說明書和附圖解釋權利要求的一種自然的方式,并非對解釋方式的實質性改變,仍然與對權利要求的折中解釋原則是一致的。只不過從實際效果來看,非功能性特征的普通術語往往具有相對成熟、明確的含義(或為本領域通用術語,或由申請人進行了明確定義),故適用反向等同原則的必要性和幾率較低,但這并不意味著所有用普通術語進行的概括永遠不必適用反向等同原則。例如,對于形式上非功能性特征、又非本領域通用術語而是自造的新術語,或者表面上是通用術語而事實上是申請人自己的新用法,若沒有明確定義而需借助于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來解釋,則其地位本質上與功能性特征應無任何區別。
從另一角度來看,對普通技術特征基于說明書和附圖進行的解釋也就是基于說明書所記載的具體實施方式的解釋,與侵權判定階段的等同原則相結合,則基本覆蓋了反向等同原則的效果(除了本文要討論的“等同”標準是否一致之外),或者說相當于反向等同原則(其中的“等同”為“低配等同”)加上等同原則(“標配等同”)的效果。例如,在程潤昌訴桂林合鑫案@9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粵高法審監民再字第44號民事判決書。中,“翻卷式密封套”這一技術特征在權利要求中沒有明確的界定,法院認為應借助說明書及附圖進行解釋。法院具體考察了說明書及附圖記載的具體實施方式,之后認為被控侵權產品的密封套與專利權人的翻卷式密封套相比較,二者的翻卷方式、功能及技術效果均相同,故屬于相同技術特征#0鄧艷輝編寫:《程潤昌訴桂林合鑫實業有限責任公司、龔舉東侵犯實用新型專利權糾紛案》,載《中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評注(第三輯)》,中國法制出版社2012年1月第1版,第166、171-172頁。。又例如,在東莞富增泡棉塑膠訴福建富增鞋材案#1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2008)閩民終字第391號民事判決書。中,根據說明書具體實施方式將甲苯二異氰酸脂(TB1)解釋為TDI-90。TDI-90的性能優于被告使用的TDI-80,也就是功能、效果不同也不基本相同,因此被告使用的TDI-80不構成等同替換,不侵權。#2黃從珍編:《東莞富增泡棉塑膠有限公司訴福建富增鞋材發展有限公司侵犯專利權糾紛案》,載《中國知識產權指導案例評注(上下卷)》,中國法制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第155、163-164頁。可以看出,上述兩案中,對非功能性特征的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和侵權判定方式與《解釋》第4條的解釋方式加上等同原則是類似的。
若說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有何區別的話,那就是,對于普通技術特征,可能要從說明書中去尋找其功能和/或效果;而對于功能性特征,其本身已經陳述了要達到的功能和/或效果。不過即便對于后者,并不排除其本身所陳述的功能和/或效果仍然不夠明確或有偏差,從而也需要借助于說明書進一步明確和解釋的情況——這也是本文主張對功能性特征也應適用傳統等同原則的理由之一。
(三)功能性特征對等同原則有同樣的需求
既然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沒有實質性區別,對它們的解釋也沒有實質性區別,即可認為,二者對等同原則也存在同樣的需求。對功能性特征完全可能存在功能和/或效果基本相同的等同侵權#3同注釋t。。
首先,適用等同原則的根本原因在于語言無法精確。功能性特征本身產生的根源也在于語言無法精確:尚無可用的普通術語可用。但功能性特征的“不得不用”并不意味著功能性特征“更”精確從而更不需要等同原則。相反,功能性特征本身從語言上看仍然是由普通術語(元概念)組成的描述語言構成的,這些描述中的任何詞語,包括所使用的功能/效果用語,應與普通技術特征處于同樣的地位。
適用等同原則的另一原因在于我在明、敵在暗,申請人無法預見到侵權者有可能采用的所有侵權方式#4尹新天著:《專利權的保護》,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第374頁。。功能性特征未必比普通技術特征更為寬泛#5同注釋l。該文指出之所以沒有二次等同,主要是考慮到功能性特征字面含義較為寬泛。筆者認為該邏輯并不必然成立。,因此沒有理由認為功能性特征比普通技術特征更能預見和覆蓋住可能的侵權方式。況且,無論是功能性特征還是普通技術特征,是否過于寬泛要與說明書所公開的內容相比較,而非僅僅取決于該功能性特征或普通技術特征的用語自身。若權利要求中的功能性特征對功能/效果的概括事實上小于說明書中具體實施方式所能支持的范圍,或者在例如涉及計算機程序的發明中功能性特征本身事實上是限定某種操作的情況下,功能、效果或操作層面的等同完全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
固然,審查指南對功能性特征是一種不提倡的態度#6《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二部分第二章3.2.1節第7段。“通常,對產品權利要求來說,應當盡量避免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來限定發明。只有在某一技術特征無法用結構特征來限定,或者技術特征用結構特征限定不如用功能或效果特征來限定更為恰當,而且該功能或者效果能通過說明書中規定的實驗或者操作或者所屬技術領域的慣用手段直接和肯定地驗證的情況下,使用功能或者效果特征來限定發明才可能是允許的。”。但是,在對保護范圍的貢獻上,所有技術特征都是平等的,不能歧視某一種技術特征,就像不能相對于發明專利來說歧視未經實質審查的實用新型一樣,或者就如《解釋二》第5、9、18條對前序特征、使用環境特征和產品權利要求中的制備方法特征一視同仁一樣。如前所述,《解釋》第4條的反向等同原則其實只是折中解釋原則的具體體現,與對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沒有實質性區別,不算對功能性特征的歧視;而《解釋二》第8條對功能性特征設定不同的等同標準(或取消傳統等同原則),則沒有合理的理由。即使假設使用功能性特征的申請人懷有不當擴大保護范圍的“不良”意圖的話,嚴格的專利審查,以及反向等同原則的適用,也已經縮小了范圍,讓功能性特征重新回到了與普通技術特征相同的起跑線上,更何況普通技術特征的范圍未必就不寬泛,使用普通技術特征的申請人未必就沒有(而是肯定有!)擴大保護的意圖。另外,無論使用何種技術特征,申請人都有權作出合理擴大保護范圍的嘗試,此種嘗試與意圖無好壞之分,不該因此得到懲罰。
當然,在適用等同原則時,對于不同的技術特征,例如必要技術特征、非必要技術特征、構成功能性特征的各種術語(元概念)、構成功能性特征在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的必要和非必要技術特征,以及說明書中對具體實施方式的描述所使用的各種術語(元概念), 何謂“基本相同”會有不同的彈性。然而決定這種彈性的是該特征(術語)與技術方案的發明點的關聯度,而與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的二元劃分無關。這種彈性也沒有理由導致對某類特征(例如功能性特征)完全取消“基本相同”的標準而要求嚴格相同。
對大量未經實質審查的實用新型的考量也是《解釋二》第8條對功能性特征采用不同的等同標準(或取消傳統等同原則)的因素之一#7同注釋l。該文還指出,“加之大量的實用新型專利授權未經實質審查,如果對于功能、效果適用基本相同,則會不適當地擴張了專利權的保護范圍”。,但是該理由并不成立。首先,實用新型制度的缺陷與功能性特征完全是兩個方向的問題,不存在任何內在的關聯性;其次,實用新型中未經審查的不僅包括功能性特征,也包括起概括作用、可能同樣范圍寬泛的普通技術特征,沒有必要區別對待;第三,對實用新型的明顯缺陷的審查會排除部分功能性特征#8《專利審查指南2010》第一部分第二章7.4節之(9)。,而且涉及實用新型的侵權訴訟毫無疑問會有無效程序介入以完成所缺失的“實質審查”。
功能性特征甚至對等同原則有更多的需要。如前所述,功能性特征的使用往往是因為技術的發展碰到了語言的局限。申請人不得不使用功能性特征這一事實(當然,是否確實“不得不”要經過審查)就意味著相關技術方案具有一定的開拓性。業內已公認創造性更高的發明應享有更寬的保護范圍#9例如3.2.1節第2段,“開拓性發明可以比改進性發明有更寬的概括范圍。”,因此從理論上說,功能性特征理應具有更寬的保護范圍。那么,功能性特征的“不得不”,以及其至少在形式上的更為寬泛,所導致的更寬保護范圍也就有內在的合理性。《解釋》第4條的反向等同原則表面上看是對功能性特征的一種限制(如前所述,與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方法其實并無實質性區別),但這種限制并非否認上述更寬保護范圍的合理性,而是防止產生并非“不得不”而系蓄意謀求不合理保護范圍的情況。而當保護范圍按照反向等同原則已經收縮至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的時候,其至少已經取得了與普通技術特征相同的地位(如前所述,普通技術特征的范圍在某些情況下同樣需要向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收縮),應同樣適用等同原則。而若考慮到前述開拓性,甚至可以有更寬松而非相同或更嚴格的等同標準。
四、區別對待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的弊端
上面詳細討論了功能性特征與普通術語的淵源和關聯,顯示它們并無實質性區別。如此的話,若強行區分二者反而會帶來問題。
首先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何為功能性特征將非常難以區分,從而為司法機關和當事人帶來負擔。在美國,紛繁復雜的案例形成了復雜的規則以幫助區分何時適用針對功能性特征的反向等同原則$0MPEP§2181.,這種情況已經證明了如何區分功能性特征的難度。然而美國案例形成的規則尚屬相對客觀,相對照而言,《解釋二》第8條的排除對象,“本領域普通技術人員僅通過閱讀權利要求即可直接、明確地確定實現上述功能或者效果的具體實施方式”,其判斷標準就極具主觀性。加上前述功能性特征和普通術語之間的漸變性(從而——界限的模糊性),將導致實踐中非常難以操作。
當然,規則是否必要未必以其難度為準;然而也不能創立沒有必要或者必要性不那么高、卻難以實施的規則。若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的區分僅僅在于是否適用反向等同原則即是否將技術特征收縮至說明書中的具體實施方式(及其低配等同),則如第三部分所述,由于對普通技術特征的解釋方式與功能性特征沒有實質性區別,在這個方面對權利人并無太大影響,則前述技術層面的困難不會構成嚴重問題。然而,若這種區分導致了是否二次等同(即是否對功能性特征本身的功能/效果適用等同原則)的問題,或者說是否對功能性特征采用相同的等同標準的問題,則前述技術層面的困難對權利人的影響極大。
即,在權利層面,《解釋二》第8條的規定將導致功能性特征的認定不僅涉及是否適用反向等同原則的問題,而且涉及是否可以適用等同原則的問題。這樣,是否將一個技術特征認定為功能性特征將極為重要。考慮到上述技術層面的復雜性和難度,可以預見功能性特征的認定將是侵權糾紛當事人角力的重要場所:是否會有非功能性特征被認定為功能性特征?或者反之?功能性特征的客觀認定標準到底為何?有沒有灰色地帶?社會公眾,甚至是權利人自身,都有可能無法準確區分功能性特征的界限,從而無法穩定預期保護范圍。良善的法律應當消弭分歧,而非制造分歧。而《解釋二》第8條正是制造了這樣的分歧,其必要性卻是可疑的:如第三部分所述,并沒有合理的理由導致區別對待功能性特征和普通技術特征的保護范圍。
最后,舍棄“基本相同”,而采“相同”的標準來判定是否侵權,將十分不利于權利人。首先,眾所周知,語言無法精準,權利人對功能/效果的概括和描述未必完善$1例如注釋l,第30頁。。其次,同樣眾所周知,世間絕無完全相同的兩件事物,除非涉嫌侵權人是百分百抄襲。第三,基本不存在沒有用的技術特征,只要技術方案存在不同,一般而言定有功能/效果的差異。以上三點的結合將令權利人難以證明侵權者構成侵權。當然,如前節所述,凡權利要求中的用語,皆存在按說明書和附圖解釋的問題,那么,這種解釋過程中,對功能/效果用語的含義寬窄的掌握,或許可以彌補上述問題,尤其是第一個問題。然而,若如此,豈不只是拆東墻補西墻?從最終效果來看,只起到了浪費當事人和司法資源的效果:先要在用語的解釋層面角力,然后要在功能/效果是否相同的層面角力。而如果直接允許“基本相同”的判定標準,則可以將解釋階段和等同階段的爭議一攬子解決,節約當事人和司法資源,雖然解釋階段和等同階段解決的分別是法律問題和事實問題。中國與美國專利實踐不同,至少對專利侵權判定這種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高度混合的領域而言,法律或事實問題之分在中國不會導致侵權救濟程序和救濟結果的實質性差異。
結 論
綜上,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在權利要求中的目的、在語言學上的關聯、在司法實踐中的解釋方式、等同原則與功能性特征的根源與目的等,均顯示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對等同原則有同樣的需求,甚至更多的需求。若人為區分功能性特征與普通技術特征,并限制前者適用等同原則,在技術層面是困難的,在權利層面會導致專利權的保護范圍因技術特征是否被認定為功能性特征而產生很大的不同,從而推動產生一些不必要的爭議,影響權利人行使權利。
因此,《解釋二》第8條的征求意見稿(例如第十三稿)有其合理性。在該征求意見稿中,作為對功能性特征的解釋,亦即對功能性特征字面侵權(相同侵權)的標準,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相同的功能,達到相同的效果”;作為針對功能性特征本身的等同原則,亦即對功能性特征等同侵權的標準,是“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實現基本相同的功能,達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Art. 8 of judicial explanation No.1, 2016 puts forward a definition for functionality features,also a criteria measuring equivalence different from the current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It is technically diffi cult to distinguish functionality features from general technical features; and the protection scope of claim may vary dramatically depending on whether a technical feature is regarded as a functionality feature. The confusion can lead to unnecessary disputes and impact on the exercise of patent rights. The US judicial practices, the roles of both functionality features and general technical features in the claims, the lingual relationship there between,their similar construing manner, and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th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and functionality features are all indicating that the conventional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should equally apply to functionality features and general technical features. To sum it up, the equivalent infringement of functionality features should be measured according to the following criteria, “substantially the same means, functions and effects”.
functionality featur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reverse doctrine of equivalents; claim construction
李春暉,北京集佳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專利代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