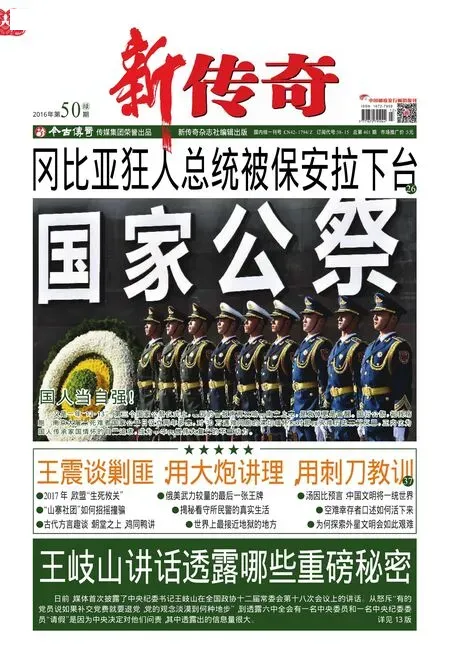朱德孫女:這一代“紅后代”特別能吃苦
朱德孫女:這一代“紅后代”特別能吃苦
“小時候沒有感到什么光環(huán)。我覺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樣。我在學校從來不說我是誰的后代。現(xiàn)在參加聚會,我都不允許別人說我的出身。因為從小就養(yǎng)成了這樣的一個習慣。”

今年62歲的朱新華長著一張國字臉,眉毛很濃,說話語速很快,行事干凈利落,英氣十足。鄧穎超第一次見到她時,笑著說:“一看就是朱家人。”圖為朱新華
朱德一生戎馬倥傯,大半生在戰(zhàn)爭中度過,只育有兒子朱琦和女兒朱敏兩個孩子,兒子朱琦與兒媳趙力平生有四兒一女,朱新華是朱德唯一的孫女。朱新華的名字就是爺爺給取的,寓意“新中華”。
從廣州解放軍第一軍醫(yī)大學畢業(yè)后,朱新華一直在解放軍301總醫(yī)院工作,任急診科副主任,之后調(diào)任金溝河干休所衛(wèi)生所所長直到退休,現(xiàn)在仍任顧問一職。
家風:“炊事員是為我服務(wù)的,不是為你們服務(wù)的”
1969年,朱新華15歲。她說,當時一個大的背景是我們國家和蘇聯(lián)的關(guān)系比較緊張,同時國內(nèi)形勢也很緊張。于是中央做了一個決定,把在京退居二線的老同志和部隊上的老領(lǐng)導(dǎo)疏散出去。
當時有七八個人去了廣東,跟我爺爺一起去的有董必武、滕代遠、李富春、蔡暢夫婦。我小時候一直在父母身邊長大,只在節(jié)假日、寒暑假到中南海和爺爺奶奶住。1967年中南海出了個規(guī)定,家屬不能進中南海,這樣即使寒暑假我也不能回爺爺奶奶身邊。所以,在廣東從化的那段時間,是我和爺爺奶奶接觸最密切的時候。
1970年我去廣州上學,五一放假我去從化看他們。那時我已經(jīng)當兵了,一回家就向爺爺敬了個禮,我爺爺特別高興,說:“你真是長大了,軍禮敬得也不錯,挺標準。”
我們一起散步,門口有站崗的哨兵,哨兵給他敬禮,他每次都回禮,我沒有這個習慣,跟在后邊走過去了。他看了我一眼,對我說:“這個小同志剛才給我敬禮,你為什么不給他回禮。”我說:“他不是給您敬的禮嗎?”“但是我們在一起走,我們都走過去后他才把手放下來,人和人之間要互相尊重。”這樣我就懂了,以后都會回禮。
這就讓我想起,在戰(zhàn)爭期間他幫戰(zhàn)士扛槍、站崗;長征途中,他帶頭抽出了一匹牲口供傷員使用,要求“把傷員全部帶走,一個都不能丟。”雖然他職位很高,但愛兵。
我們在一起,爺爺很少講自己的過去,也不講什么大道理,就是從這些平常的生活小事中,潛移默化影響著我們的為人做事。
當時我和他們住在一棟樓里,我既然是家人,就應(yīng)該和他們一起吃飯吧。但當時不是這樣,只有爺爺奶奶在家里吃飯,家屬需要到大食堂吃飯。爺爺說:“炊事員是為我服務(wù)的,不是為你們服務(wù)的,你應(yīng)該和工作人員一起到大食堂吃飯。”到了廣東第二天,奶奶給我買了飯票,讓我跟著工作人員到食堂吃飯。
對后代規(guī)劃:“長大了要學一門技術(shù)”
我在廣東呆了將近8年時間,先是在那邊當兵,然后在解放軍第一軍醫(yī)大學上學,畢業(yè)以后才回北京。
當時在那邊很多人都帶著孩子,孩子們年齡也都差不多,閑著也不是事兒,所以就跟廣州軍區(qū)商量,能不能把這些孩子送到部隊里去鍛煉。正好趕上那年廣州軍區(qū)招兵。新兵訓練結(jié)束以后,我被分配到廣東興寧解放軍第179醫(yī)院工作,工作兩個月后調(diào)回來,我和陳小玫就分到了廣州軍區(qū)總醫(yī)院,其他人分到了其他醫(yī)院。
放假的時候,爺爺說:“雖然你放假回來,但這個規(guī)矩不能變。”“你也不能天天在家這么呆著,除了看書、學習就是出去玩,總得干點事。”干什么事呢?他說:“幫工作人員干事,打掃院子。”所以我一大早就拿笤帚掃院子,慢慢習慣了。
到部隊以后,我給他們寫信,我是有什么說什么,有時候會訴苦。他們就寫信教育我,讓我想想勞動人民的孩子是怎么過來的。“別人能吃苦,為什么你就不能?”
一開始我是做護理員,相當于現(xiàn)在醫(yī)院的護工。剛開始不是不想干,是不會干。比如挑水,我不會,根本就沒扛過扁擔。成天讓我搞衛(wèi)生、掃廁所、端屎端尿,我說當兵怎么干這事。爺爺奶奶就批評我:“不要見異思遷,要向勞動人民學習,為什么別人能干,你不能干?”
爺爺對后輩沒有具體的規(guī)劃,但有一條要求:“你們是我的后代,可以說你們是紅色的接班人。但是我所要的接班人,不是接官、接地位,是要接革命的班。不是說你出生在紅色的家庭里,就理所當然是紅色接班人,接班人要有理想、有志向、有專業(yè)。你們長大了要學一門技術(shù),要為祖國建設(shè)做貢獻。”
“紅后代”的壓力:“不要到處彰顯自己的出身”
作為“紅后代”,我覺得我和普通孩子一樣。我在學校從來不說我是誰的后代。現(xiàn)在參加聚會,我都不允許別人說我的出身。因為從小就養(yǎng)成了這樣的一個習慣。
我在家里受的教育就是這樣:不要到處彰顯自己的出身,出身和你自己沒什么關(guān)系,出生在什么樣的家庭是天生的,但未來的路是自己走的。不過我很榮幸出生在這樣的家庭。
要說壓力,也沒什么。參加勞動、參加訓練,大家都是一視同仁。不過我要求自己干得比別人多一點。不能讓別人說我壞話,不能給自己家抹黑。
參軍以后,我是拼命吃苦。別人干的活我要想辦法做到。一開始我不會挑擔子,但是后來我挑得比誰都好。上世紀70年代的醫(yī)院條件比較差,病房里沒有熱水,病人喝的熱水需要我們一桶一桶從從鍋爐房挑上樓。我上樓的時候一桶一桶挑,走平路的時候我能一下挑4個桶,別人都很驚奇。
爺爺對我爸媽要求也很嚴格。我媽媽生完孩子休56天產(chǎn)假,產(chǎn)假一結(jié)束就去上班。為了讓我爸爸媽媽安心上班,爺爺奶奶就說:“等孩子斷奶之后,就送到北京來,我們給你帶孩子。”所以我哥哥10個月就被送到了中南海。
我們這樣的家庭,不上班、在家里游手好閑,老人肯定是看不慣。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物質(zhì)的豐富,很多人都會變。但是我們那個年代成長起來的人思想就是這樣,你去看看這個年代出生的其他“紅后代”,也大多是這樣的想法。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特別賣力,特別能吃苦。我們的想法很單純:我是這樣家庭出來的,我要做表率,不能表現(xiàn)得比別人差。當然也有個別人例外。
(《上海觀察》2016.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