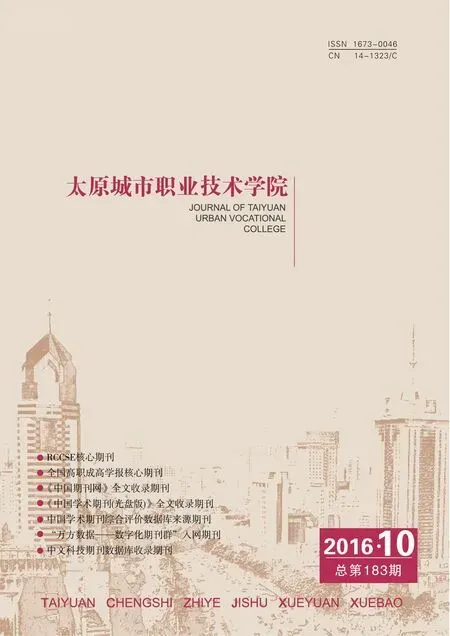淺論劉體仁《七頌堂詞繹》中“境界說”的內涵
劉崇建
(中南大學,湖南長沙410000)
淺論劉體仁《七頌堂詞繹》中“境界說”的內涵
劉崇建
(中南大學,湖南長沙410000)
劉體仁是明末清初時期詞學發展中一個重要人物,其《七頌堂詞繹》中“境界說”的提出,首次將“境界”這一術語引入詞學批評范疇,對清代中后期的詞學發展和研究,尤其是對王國維“境界說”的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劉體仁“境界說”核心內容散布于《七頌堂詞繹》中,主要體現在“詞之體式論”、“詞中警句”與“詞之神理”三個方面,其直接影響了王國維“境界說”的相關理論,“境界說”在詞學領域有首創之功,其對于清代詞學發展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劉體仁;“境界說”;《七頌堂詞繹》
劉體仁(1617-1676),字公勇,河南潁川衛(今安徽阜陽)人,崇禎十二年(1639)“領前己卯鄉薦”,順治十二年(1655)進士,與王士、汪碗同榜,在京師以詩文唱和為主,曾從孫奇逢、傅青主等高士問學,工詩文,善作畫,喜收藏,精鑒別。因平生慕連成、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王績、韋應物七人之為人,各自為頌,故以“七頌”為其堂,亦名其詞集,著有《七頌堂集》、《七頌堂詞繹》、《七頌堂識小錄》等。
《七頌堂詞繹》一卷,共三十三則,涵蓋詞學理論、詞學批評兩大方面,涉及“境界說”、“詞史分期”、“詩詞分疆”等重要的詞學思想,尤其是其核心思想“境界說”的提出,影響深遠。
劉體仁最早將“境界”的概念引入詞學研究的范疇中,其《七頌堂詞繹》的核心理論價值在于“境界說”的提出,全篇圍繞“境界”這一核心理論展開闡述,為“詞中境界”的范疇建立和體系健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境界”的提出,預示著詞學研究領域翻開了新的一頁,啟迪后代研究者從“境界”方面去探尋詞學思想與詞體本身的發展。劉體仁“境界說”就內涵及范疇而言,在全篇《七頌堂詞繹》中主要包含以下三個部分。
一、“境界說”與詞之體式論
劉體仁定“詞之體式”之論,為其“境界說”定下了基調。“境界”一詞,本意取“邊界,疆界”之意:
詞中境界,有非詩之能至者,體限之也。大約自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等句來。
此處的“體限”,乃詞與詩之別,有“體式受限”之意。古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選自《樂府詩集》北朝民歌《木蘭詩》,相比傳統的詩歌,民歌《木蘭詩》在體式方面有著較大的靈活性,保留著民歌的形式和風格。連鎖、問答、排比、重疊等形式的運用,都與民歌大致相同。單就韻而言,民歌不講求嚴格的對仗和押韻,篇幅較長的樂府詩歌大都是隔幾句換一個韻,很少一韻到底,這樣才能使演唱的歌曲音節復雜而有變化,從而使得情感的表達更加自由,更加細膩豐富。《木蘭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等句的表達方式相比于《木蘭詩》“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更多地突出了閨房之中情節的細膩的描寫,這在詩歌中是不常見的。從“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到“當窗理云鬢,對鏡貼花黃”的過渡正映襯出了詩詞之間的過渡,“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等句的細膩的閨情描寫有了詞的影子,后世詞家將部分詞的源頭定位于樂府詩,不無道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道出的“詩之境闊,詞之言長”,正是對此種過渡最合理的詮釋。
劉體仁此處所論境界之本意,大致如此。結合詞體本身易于言情、表現細膩的等特點可知,在詩歌中作家不愿意表達或不易表達好的內容,在詞中卻能充分地被表現出來,尤其是人的情感世界以及細微的心理活動,“詩莊詞媚”,不無道理,作家筆下那些深邃婉妙的抒情,正是構造了詞中獨特的“境界”之美。能創造詞中獨特的“境界”,劉體仁在《七頌堂詞繹》中將其定位為“作手”:
詞須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乃稱作手。
劉體仁“境界說”的提出,有一個大的前提,那便是對詞體本身的明確定位以及對于詞作為一種文學體式與其他文體的區別性的分析和論述。劉體仁道詞須“上脫香奩”,實則是對“詞情”的一種限定和憧憬,其雖尚婉約,但并不癡迷女性閨幃之作;韓身處晚唐,當時詞體本身還不夠成熟,《香奩集》中多為細膩描寫,這種表現方式無疑在詞中更易展現,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詞體的發展。然而,劉體仁所謂“詞須上脫香奩”,實則是寄希望于詞能回歸到“詩情”本身,還是能寫出“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的氣勢與境界,而不僅僅局限于描寫閨中細膩、溫柔之情,其從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詞為小道”的觀念,希望詞也能與詩有同樣的文學地位,能夠言志傳情。
“上脫香奩”規避詞流于小道,“下不落元曲”則凸顯詞的地位。元曲原本來自所謂的“蕃曲”、“胡樂”,首先在民間流傳,被稱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調”,其后有嚴密的格律定式,每一曲牌的句式、字數、平仄等都有固定的格式要求。劉體仁勒令詞“下不落元曲”,乃是對詞體本身所傳達情感與所起作用的高度定位,其還是寄望于詞能上升到傳統經典的高度,能言悲情,能托物言志,而不是街頭巷陌之作,毫無意義可言。
若能做到“上脫香奩,下不落元曲”,則詞正矣,詞家本色當行矣。劉體仁此論總結前人對于詞體的定位及開啟后人對于詞體的認識,促進了清代文人對詞的研究。
二、境界說之“詞中警句”與“妙境”
劉體仁“境界說”的提出,除了確定詞體基本體式及其與詩、曲的分疆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準確把握并提出了“詞中妙境”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境界說”中“警句”的提出,一定程度上直接啟發了后代王國維“境界說”。劉體仁在《七頌堂詞繹》中談到:
惟“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詞有警句,則全首俱動。
其圍繞“警句”一詞展開,闡釋“警句”對于詞的重要性,暗示了“詞中境界”在一定程度上由詞句本身所凸顯。陸機《文賦并序》記載:“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眾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在前人陸機的基礎之上,劉體仁認為“詞中警句”對于詞體境界的形成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詞中警句”的提出也為其“境界說”的完善提供了重要的依據。“詞中警句”的提出,同時也為劉體仁“詞中妙境”的提出埋下伏筆,有警句則妙境自然而生。
其在《七頌堂詞繹》中談到:
文長論詩曰: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興觀群怨,應是為傭言借貌一流人說法。“溫柔敦厚”,詩教也。“陡然一驚”,正是詞中妙境。
“詞中警句”使得詞體本身表現出“陡然一驚”之妙,從中突出了詞體“奇”的特質;強調“陡然一驚”之效,可理解為詩詞創作在不經意間的凸顯與觸動,而這種不經意的凸顯和觸動,恰恰正是詞中警句最好的顯現;正如其在《七頌堂詞繹》第二十七則所道:“紅杏枝頭春意鬧”,一鬧字卓絕千古。王國維也在《人間詞話》中談道:“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此觀點顯然直接受到劉體仁所論“詞中警句”對于“詞中妙境”凸顯的影響。
另一方面,此論中“興觀群怨”是孔子論詩的社會功能最基本的概括,也是儒家詩學的基本觀念,前人徐渭則認為如果詩能夠使人讀之如“冷水澆背”那樣“陡然一驚”,也就達到了“興觀群怨之品”。實際上,徐渭是把“陡然一驚”作為詩歌藝術價值的最高標準。劉體仁繼承了徐渭的說法,以“詞中妙境”概述“陡然一驚”之奇效,有其獨到之處;其在“詞中警句”的基礎之上,引申提出詞中妙境“陡然一驚”之說,也體現出劉體仁“境界說”既有宏觀的體式之論,亦有微觀上通過特殊的藝術手法達到奇妙的藝術效果的意識。這種宏觀與微觀并重的詞學分析理論在明末清初時期無疑起到了“先導”之用,為后代詞學研究者提供了參照。
三、“境界說”之“神理備具”——詞境與詩境之離合
劉體仁“境界說”的提出,除了限定其體式、基調,道出詞體本身的妙處之外,“境界說”之中所蘊含的“詞之神理”為重中之重;無“格之卑,體之靡,境之離,辭之枝”,這便是清初鴻儒徐乾學對于劉體仁作品的評價,用此四短句來界定劉體仁“境界說”之“神理”亦為得當。與此同時,詩境到詞境的轉換過渡,在劉體仁詞論中也有所彰顯,這在一定程度上突顯了劉體仁詞論的尊體之說。
詩之不得不為詞也,非獨《寒夜怨》之類,以句之長短擬也。老杜《風雨見舟前落花》一首,詞之神理備具,蓋氣運所至,杜老亦忍俊不禁耳。觀其標題曰新句,曰戲,為其不敢背大雅如是。古人真自喜。
劉體仁敏銳地從杜甫詩中發現出一首“別調”——《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認為杜甫在標題上標注“戲為新作”是有道理的,此詩具有詞的特征,以此實例來論證“詞之神理備據”;劉體仁對于這首別調的定位,可謂慧眼識珠;其認為,詩之不得不為詞并非獨《寒夜怨》等僅從句式長短上進行區別,而是以杜甫《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等為代表的唐詩中已經凸顯出詞體所具備的因素。其將此種現象上升到了“詞之神理”的高度,道出了詞之精妙之處;也道出了“詩之不得不為詞,乃氣運所至”,可謂高論,影響深遠。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是杜甫晚年的作品,大歷五年作于潭州,整首詩精致細膩,構造出細雨飛花的幽微之境,此境界詩中的確少有;其次,內容上以言情為主,多用比興,以桃花之悲映襯自身命運之多舛,不經意讓人聯想到蘇軾的千古名篇《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一詩一詞,二者有異曲同工之妙;表現虛實相間,語言婉約綺麗,正印證了“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學術界普遍認為,唐詩的發展歷經初、盛、中、晚四個階段。盛唐詩與中唐詩呈現出截然不同的審美趣味和精神氣韻。盛唐詩歌籠罩在“盛唐氣象”中,而受“大歷詩風”的影響,中唐詩歌相對于盛唐詩歌多偏重于情感細膩的描寫與表達,少了盛唐詩歌的大氣與恢弘,這種情感的轉變使得詩歌本身也經歷著轉型,一種由詩向詞轉變的契機應運而生;章炳麟說“:中國廢興之際,樞于中唐,詩賦亦由是不竟。”把中唐視為古典詩歌演變的一大關鍵,是有眼光的。經過歷時八年的安史之亂,唐王朝從盛世走向衰世,文人的心理狀態、精神面貌也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因此,中唐素被認為是詞體形成的關鍵時期。劉體仁認為中唐時期,詞體“氣運所至”,正是對安史之亂后,文人心態、詩風轉變的一種合理的揣測。杜甫對這種帶有詞體意味的風格難免“忍俊不禁”,故雖以詩歌的體式來創作,但已悖離了此前的創作方式。又因為其詩學觀念的成熟,杜甫“不敢背大雅”,所以特地冠以“戲為新句”以示區別,劉體仁這種對杜甫創作的心境的揣測,有一定合理之處。“古人真自喜”,此處評價得體卻又不失風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詞的衍變與產生與詩歌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詞境與詩境存在一定聯系,但是詞的作法與抒發的情感又有著與詩歌的不同之處;因此,簡單地將詞定位為“詩余”是片面的,也是不完善的,這也與劉體仁的詞學思想是一致的。
總而言之,從詞學理論發展演變的角度著眼,相對而言,宋、元、明時期相對較弱,仍處于草創階段,詞學研究發展至清,開啟了其繁榮興盛的時期;劉體仁《七頌堂詞繹》屬于清代前期少有的詞學研究作品,道其為清代詞學研究的“先導”,并不為過。其“境界說”的提出,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直接或間接為清代末期王國維的詞學思想中“境界說”的提出與體系的形成埋下伏筆。
劉體仁在詞學領域最早提出了“境界說”,其對于詞學研究在于清朝中后期的發展中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雖然劉體仁并未對“境界說”的核心理論展開系統全面的論述,只是將其散布于《七頌堂詞繹》的評說之中,但不能因此否定劉體仁在詞學理論方面獨特敏銳的眼光和深入的思辨性。其大膽而獨到的見解,為后人在其基礎之上的完善提供了方向和延展性,為“清詞中興”的完成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其關于詞學理論的論說直接影響了王國維“境界說”的提出與核心理論的建構,真正創造了“境界說”在詞學批評領域的價值,奠定了其在詞學批評領域的地位。
[1][清]劉體仁.七頌堂集[M].王秋生,校點.安徽:黃山書社, 2008.
[2][明]楊慎.詞品[M].岳淑珍,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王國維.人間詞話[M].徐調孚,注.北京:中華書局,2011.
[4]王國維.人間詞話疏證[M].彭玉平,疏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
[5]唐圭璋.詞話叢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6.
[6]沈雄.古今詞話·詞品上卷[M].孫克強,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7]葉嘉瑩.《人間詞話》之基本理論——境界說[M].北京:中華書局,2009.
[8]彭玉平.杜詩變體與詞體內質——以《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三首為考察中心[J].閱江學刊,2010(4).
I206
A
1673-0046(2016)10-01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