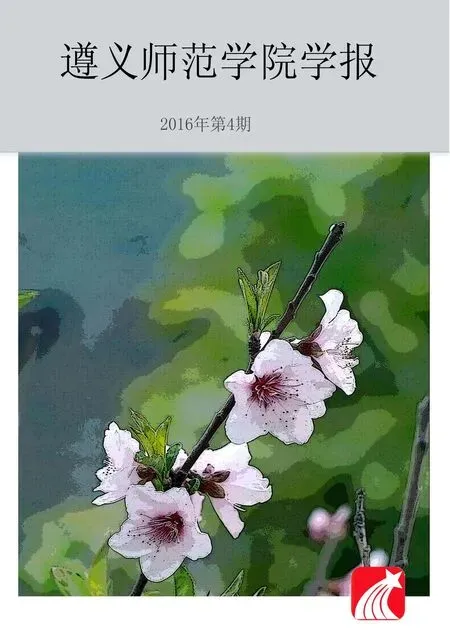共產國際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關系研究
汪學平
(遵義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遵義563002)
共產國際和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決策關系研究
汪學平
(遵義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貴州遵義563002)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是共產國際及其軍事代表在第五次反“圍剿”過程中執行錯誤的軍事戰略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在請示共產國際同意后才執行的戰略轉移,期間工農紅軍關于戰略轉移必要的理論、物質和輿論準備也是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進行的。
長征;共產國際;黨的建設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路線、組織人事、軍事策略以及財政經濟等方面都深受蘇聯主導下的共產國際的控制和影響,這種局面直至1943年5月15日共產國際決定“予以解散”時為止。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此種關系的影響,正如周恩來同志曾經指出的那樣:“中國黨在這個時期犯了那么多錯誤,使中國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損失,我們中國人當然要負責,但與共產國際有很大的關系”[1],這種指導錯誤最嚴重的后果就是中國工農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被迫退出中央蘇區進行的戰略轉移。
一、共產國際與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關系
1933年9月25日,國民黨第三路軍第八縱隊周渾元部偷襲中央蘇區和贛東北蘇區的最主要通道——黎川,中央蘇區和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拉開序幕。此次“圍剿”,蔣介石吸取以往失敗的教訓,以“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為反共方針,動員64個師7個旅6個團,另加航空隊11個,飛機105架,兵力合計約80萬人[2],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統一指揮下,采用以碉堡和封鎖線為中心的新式戰術,從北、西、南三個方向對中央蘇區封鎖圍攻。
歷經前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中央蘇區范圍擴展至江西、福建和廣東三省60個縣[3],核心區域人口達200萬以上[4],工農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
增至約10萬余人[2],紅色革命政權日益鞏固。1933年初,以博古(秦邦憲)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從上海遷到中央蘇區,“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央蘇區的危害日益嚴重,紅軍的軍事戰略、訓練以及部隊和后勤的組織問題則由共產國際軍事代表李德實施。雖然李德在《中國紀事》里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自辯時表示:“我對政治領導不進行完全任何干涉”[5],但是他承認“博古以及后來的周恩來,總是習慣地把一切軍事問題事先同我討論一下,然后在軍事委員會上代表我的意見”[5],而他是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的命令行事,“他(指曼·弗雷德)要我負責在中央蘇區嚴格執行他的一切指示,其根據是,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軍事代表”[5],這些表明第五次反“圍剿”的軍事決策者是李德以及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軍事總顧問曼·弗雷德、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
“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與殘酷的階級決戰”[6],中共中央充分估計到第五次反“圍剿”的嚴峻形勢,要求“必須立即戰斗地動員群眾在‘粉碎敵人新的五次圍剿’,‘保衛與擴大蘇區’,‘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等口號的周圍……保衛蘇維埃”[6]。李德完全照搬蘇聯軍事學院教科書的教條和蘇聯軍事條令,以“御敵于國門之外”為口號、實施“兩個拳頭打人”戰略,企圖以“短促突擊”戰術應對國民黨“圍剿”軍的堡壘戰術。所謂“短促突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1933年9月12日給中央蘇區的電報指示:“我們應該讓敵第一梯隊部隊向前推進幾里。在這時我們將迅速在兩翼運動,以便出人意料地迎擊敵主力部隊。在先殲滅敵第二梯隊之后,再以小股部隊擊潰其第一梯隊”[7],初步表述“短促突擊”理論雛形,而李德在1934年4月《革命戰爭的迫切問題》和《論紅軍在堡壘主義下的戰術》里集中闡述這一戰術原則,即工農紅軍以防御支撐點誘引敵人遠離堡壘,以主力部隊對被吸引來的敵人進行突然、集中地打擊,以便于在己方堡壘前殲滅敵人。
至1934年4月,國民黨軍在江西省構筑碉堡5300個[4],修筑鏈接碉堡的公路6000余里[2],蔣介石嚴格要求貫徹穩扎穩打戰略,“匪區縱橫不過五百里,如我軍每日能進展二里,則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領匪區”[8],此戰略戰術致使紅軍傳統運動戰受到遏制。李德的“短促突擊”戰術理論針對第五次反“圍剿”國民黨軍“堡壘主義”的戰術變化,同時表面上看符合工農紅軍此前創造的游擊戰、運動戰戰略戰術關于“迅速”、“突然”、“機動”、“集中兵力”基本原則的總結,起初得到朱德、項英、林彪、彭德懷和聶榮臻等軍事將領的支持,成為工農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運用的戰術。但是在國民黨軍“穩扎穩打”、“以靜制動”、“注重工事”、“集中優勢兵力”背景下難以達到殲滅戰的目的。聶榮臻在1934年2月16日與林彪向朱德總結經驗教訓時表示“短促突擊”戰術“結果仍變成堡壘戰”[9],而指揮體系、戰術訓練和武器裝備方面的嚴重問題致使工農紅軍在堡壘陣地戰中存在著攻堅能力不足的致命缺陷。1934年4月28日,在博古、李德和朱德親自督戰且調集紅軍精銳第一、三、五軍團9個主力師參戰的情況下,中央蘇區北部門戶——廣昌保衛戰失利,國民黨軍傷亡2600余人,紅軍主力傷亡5000余人,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形勢急轉直下。
二、共產國際與“湖南計劃”
日益嚴峻的軍事形勢導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始考慮撤離中央蘇區問題。其實溯及到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曾建議中央蘇區紅軍在保衛中央蘇區時,應該特別參考前四次反“圍剿”運動戰和游擊戰關于紅軍“機動性”的成功經驗原則,同時:“應該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卻的路線,做好準備”[7]。同年7月2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負責人埃韋特給上級皮亞特尼茨基報告中表示:“盡管我們竭盡全力,最終還是未能擺脫僵局。而敵人的工事和數量反而有了增加。……我們沒有理由悲觀,但是我認為,近期我們擺脫中央蘇區所處困境的希望不大”[7]。可見,第五次反“圍剿”尚未開始,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就已經在考慮是否放棄中央蘇區根據地問題。
同年11月27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上海軍事顧問團總顧問曼·弗雷德提出“湖南計劃”[10],要求中央蘇區紅軍主力跳出中央蘇區核心區域分別向贛北和湖南西北部地區突破,打擊北面進攻中央蘇區的國民黨部隊側翼和后方。“湖南計劃”遭到中共中央的拒絕和共產國際執委員會的否定。李德1933年12月23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遠東局復電表示:“盡管計劃被否定了……總計劃的原則被采納了。在(中共)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會議上,強調(有必要)指出,我們將來的策略也應該是
把西面作為進攻的方向”[7]。共產國際執委會1934年1月2日致電中共中央表示中央蘇區軍事行動根本上應該由中共中央來決定,而且“我們認為,在目前形勢下,11月27日的計劃是不利的”[10]。
1934年4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屢戰失利,中央蘇區南線門戶筠門嶺、北線門戶廣昌等戰略要地相繼失守,雖然博古在《紅色中華》社論堅稱:“我們要保衛土地、自由、蘇維埃,直至最后一個人,最后一滴血,最后一口氣”[11],但是撤離中央蘇區的計劃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高層的理性選擇。1934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書記處瑞金會議決定實施紅軍主力的戰略轉移。《博古文選·年譜》記述:“主力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12],并將這一會議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埃韋特(即李德《中國紀事》中的阿瑟·尤爾特)1943年6月2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皮亞特尼茨基的報告說中共中央“準備將我們的主力撤到另一個戰場……”[10],他建議共產國際執委會考慮在中央蘇區反“圍剿”各種可能性窮盡的情況下:“保存著我們大部分有生力量的情況下才應使用”[10]。1934年6月16日,共產國際執委會反復研究討論后做出決定,并復電中共中央和埃韋特:“如果說主力部隊可能需要暫時撤離中央蘇區,為其做準備是適宜的”[10],這是中央紅軍此后進行戰略轉移行動的決策根據。
三、共產國際與長征的準備
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1934年6月16日電報及此后的指示,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一系列戰略轉移的準備措施,包括擴紅運動、糧食儲備、福建戰役、輿論宣傳、轉移偵察和探路這些準備措施都是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的部署指示下進行的。
1934年5月12日,中共中央發出公開指示信,指出“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了五六七三個月擴大紅軍五萬的計劃”[13],為長征進行兵員的補充,要求各級動員機關無論如何要在規定期限內完成該計劃。根據紅星報報道,工農紅軍1934年5月擴大23025人,6月擴大29688人,7月(至15日止)擴大2457人[14],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把10多個新兵團、140萬發子彈、7.6萬多枚手榴彈和大批物資補充到紅軍各主力軍團[15]。
為配合紅軍的戰略行動,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書記處政治委員會1934年6月17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建議“發動福建戰役,將其作為預防和吸引敵人”的措施[10]。1934年7月,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以尋淮洲、樂少華、粟裕等人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途經福建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后,分成兩路向浙皖邊和皖南行動。關于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意圖,朱德后來表示:“是準備退卻,先派先遣隊去做個引子,不是要北上,而是要南下。”[16]
1934年7月15日,中共中央領導機關發表《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企圖“把全中國變成他的殖民地,把全中國的民眾變為亡國奴”的野心,抨擊國民黨政府不僅“出賣了東三省,出賣了熱河內蒙”,而且向“全中國唯一反日反帝的工農的蘇維埃政府與工農紅軍進行不斷的‘圍剿’”[6]。《宣言》在日本帝國主義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并不斷向華北蠶食,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情況下,既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向日本宣戰,又起到掩護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作用。
1934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決定:“舉行秋收六十萬擔借谷運功,并決定立即征收今年的土地稅,隨著武裝保護秋收的運動迅速切實的完成,以供給各個戰線上紅軍部隊的需要”、而且“這一任務,一般的要在九月十五日前完成”[6],從時間節點來看,此舉目的并非一般意義上的保證紅軍糧食供給,而是為工農紅軍進行長征準備糧食必需品,而是對共產國際關于“成立運糧隊和為紅軍建立糧食儲備”的應對措施[10]。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和中革軍委發布《關于紅六軍團向湖南中部轉移給六軍團及湘贛軍區的訓令》,命令任弼時等組建紅六軍團后“離開現在的湘贛蘇區轉移到湖南中部去發展廣大游擊戰爭,及創立新的蘇區”,其目的在于與活動在貴州、湖南和四川范圍內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取得聯系,“以造成江西四川兩蘇區聯結的前提”[6],此訓令拉開紅軍長征的序幕。時任六軍團軍團長的蕭克回憶指出紅六軍團突圍西征“實際上起到了為中央紅軍長征進行偵察、探路的先遣隊作用”[17]。
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準備工作全部就緒后,1934年9月17日,博古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確定此前“湖南計劃”既定的湖南西部為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的目標,“全部準備工作將于10月1日
前完成,我們的力量將在這之前轉移并部署在計劃實施戰役的地方”[10]。9月26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在《紅色中華》發表社論《一切為了保衛蘇維埃》,為即將實施的中央紅軍主力戰略轉移進行政治動員。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率紅軍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共五個主力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組成的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共約8.6萬人,分別自瑞金、雩都地區出發,實施戰略轉移向預定的湖南西部出發,自此開始漫長艱苦的“長征”歷程。盡管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問題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領導下經過周密的籌劃和準備,但是基于李德“突圍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的考慮,因而關于工農紅軍戰略轉移部署僅限于政治局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知情,“其他人,包括政治領導干部和部分高級干部,只知道他們職權范圍內需要執行的必要措施”[5]。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博古、李德為首的最高“三人團”“沒有依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在干部與紅色指戰員中進行解釋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會議上也沒有提出討論”,而且“我們突圍的行動,在華夫同志(即李德)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堅決的與戰斗的,而是一種驚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動”[6],導致工農紅軍在長征初期一味退卻逃跑消極避戰,攜帶大量輜重和甬道式行軍嚴重削弱紅軍機動性能,在突破敵人四道封鎖包圍線,尤其是湘江戰役時遭遇嚴重的損失。
[1]周恩來.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M](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熊尚厚.對蔣介石第五次“圍剿”中央蘇區的準備之考察[J].民國檔案,1992,(1):101-105.
[3]凌步機.中央蘇區區域范圍考察[J].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2,(3):50.
[4]黃道炫.張力與限界:中央蘇區的革命:1933-1934[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5]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M].北京: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
[6]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4-1935)(第9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7]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3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8]王多年.反共戡亂(上篇第四卷)[M].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
[9]周均倫.聶榮臻年譜(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4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11]博古.我們的位置在那邊,在前線上,站在戰線的最前面[A].李志英.秦邦憲(博古)文集(下卷)[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12]吳葆樸,李志英,朱昱鵬.博古文選·年譜[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13]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冊)(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14]一年來擴大紅軍的統計[N].紅星報,1934-07-22.
[15]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16]粟裕.回顧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A].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紅軍長征史料[C].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17]蕭克.開路先鋒:紅六軍團的先遣西征[J].軍事歷史,2006,(6):8.
(責任編輯:婁 剛)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intern and the decision of Long March by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WANG Xue-pi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Long March made by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resulted from the wrong military strategies carried out by Comintern and its military advisor in the counterattack on the“fifth encirclement and extermination campaign”;it was also a kind of strategic shift implemented by CCP after it was agreed on by Comintern;and the necessary theory,materials and preparations for public opinion about strategic shift were conducted under the guide of Comintern as well.
Long March;Comtern;Party’s construction
D231
A
1009-3583(2016)-0009-04
2016-03-16
2013年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長征視域下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關系研究(13SZK004)”的階段性成果;中國共產黨革命精神與文化資源研究中心2015年項目“毛澤東、張聞天和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期間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15KRIZY10)的階段性成果
汪學平,男,河南洛陽人,遵義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共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