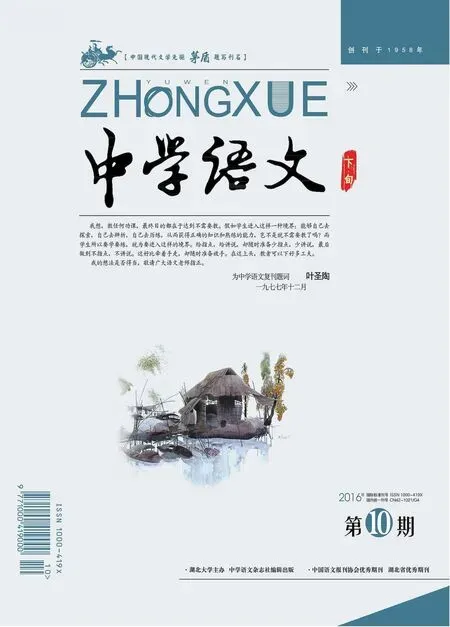對中學語文的一點思考
孫玉霞
對中學語文的一點思考
孫玉霞
在中學語文(母語)課程當中,或能夠將其劃分為兩門課程:語言課(包括寫作)與文學課;或能夠將其合并作為一門課程,并將語文的每一冊課本都劃分為具有相對具有獨立性的語言(包括寫作)與文學兩大類體系;而無論是采用劃分法或是合并法,都將會以文學為主、語言為輔。
語文按照字面意思來進行解析即為語言和文學,其正確性較早即已經被大量研究實踐所證明,已成為定論,無人會再對此進行置疑。當前,在全球教育領先的國家與地區當中,如歐美、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十分重視本國的母語文學教育,并作為一門重要的學科來進行學習。而在我國中學階段的教育當中,語文即為語言和文學,作為一種常識性的理念,也同樣為社會所普遍接受。培養中學語文教師的師范大學中文系,即為中國語言文學系。
但是,在我國教育界長期以來對于中小學語文的認知方面,并不認可語文即為語言和文學此一常識性認知,并將此認知視為違背傳統理念的片面看法,而“什么才是語文”這一常識性問題,竟然成為了困惑了我國教育界50余年的難題。眾多的語文教育方面的專家與學者所詮釋的“什么才是語文”,大多背離于人們的常識性的認知,并不乏失實之處。
中華民族具有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學傳統,但是,由于在歷代封建王朝,出于穩固自身統治的需要,將儒學置于社會教育的最高地位,而無一例外的都會對文學進行邊緣化,而《詩經》作為自西漢以來至清代末期,一直是我國2000余年的儒學重要教材,《詩經》僅僅是自隋唐“開科取士”以后古代科舉的入仕之書、以及進行封建倫理道德教育之書,其自身作為文學作品的知識性與藝術性,大都被封建社會的主流思想所歪曲。《詩經》之所以被奉為我國長期的儒學教育教材,正是佐證了我國在古代缺乏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教育傳統。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洋務運動發展的影響下,廢止“以儒入仕”的科舉制度,由“效法西洋教育”的現代學校取代了私塾教育,意味著我國開始了教育現代化的進程。而在當時,源自于西方近現代教育的現代學校教育模式,正是完全學習西方教育的產物。由于傳統的封建教育當中,多只是注重于儒學的學習,近現代教育課程當中的化學、美術、生物、音樂等多元化的課程,都是古代封建教育所不具備的。因此由西方引進現代化的教育,從編定教學大綱,學科設置、教材內容,都有著學習西方教育的厚重痕跡,所以在當時能夠較快的使得我國教育與世界接軌,并且取得了顯著的成效。傳統儒學教育的核心內容是以封建倫理綱常為核心道德,其目標為科舉入仕,所設置的是近似于文科綜合課。現今,在“國學”教育興起的背景下,許多學者提倡以《弟子規》《千字文》等古代“蒙學”知識作為當代語文教育的基礎教材。
其次,是基于現實的原因。上個世紀曾進行過兩個階段的語文教學改革:50—70年代初期為第一階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為,語文應具有宣傳教育的使命,是傳播思想政治的主陣地之一。因此當時的語文課也異變成為了政治教育課。例如在60—70年代初期的中學語文課程當中有魯迅的多篇短篇小說,名義上是文學課,但是由于當時的時代特征決定了其實質是政治教育課,《吶喊》當中的人物都被政治化的劃分成不同的政治面貌,泛政治化下的文學作品,也異變成政治文章,從而與作為文學作品的《吶喊》的思想意識相去甚遠。這是由于在當時“階級斗爭生活化”的特殊的年代所造成的問題。
70年代末期—當代為第二階段,其主流的教育理念為:確定了語文的工具性作用,當時教育界提出了語文教育的工具論。而在70年代早期及之前更早的時代,將語文泛政治化,其中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其存續了語言教育。當工具論開始發展起來時,由于文革的開始,工具論被廢止。因此在60年代—70年代初,工具論的主流理念地位并未能完全樹立起來。直至70年代末,語文教育開始蓬勃發展,才將工具論正式確立為語文教育的主流理念。當時的語文教育專家學者倡導開展“人文性的語文教育”的思想意識發展大討論,對于語文教育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語言作為一門科學,也有其整體性的系統。其自身具有的特質,完全不同于理科學科所具有的特質。當然作為一門科學,其也會有自身的科學規律性。中文作為中國及全球華人共同的母語,同時也是全球應用人數最為廣泛的語種,不容置疑的是其所具有的科學規律性。而對于當代的公民而言,應用母語不能僅依據自身的感覺,應該客觀的來認知母語所存在的科學規律性,明確如何應用母語才能體現出其正確性。
葉圣陶先生曾言:“語文為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的一致性。”構建起正確的語文理念,有助于構建正確的語文教育理念。之所以會出現各種差異性的語文教育理念,大部分都是由于對語文概念產生的多元化理解而形成的。例如現今廣泛流行的語言教育理念和文學教育理念,是與將“語文”詮釋為語言的文學具有關聯性。有怎么樣大語文理念即會產生怎么樣的語文教育理念。
★作者單位:甘肅平涼市莊浪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