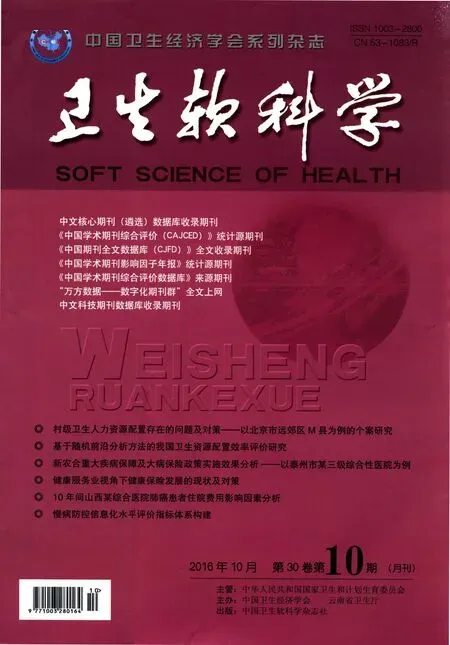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以北京市遠郊區M縣為例的個案研究
劉婷婷,于魯明,王曉燕,張溪婷,程文兵,齊韶涵
(1.首都醫科大學,北京 100069;2.北京市醫院管理局,北京 100053)
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以北京市遠郊區M縣為例的個案研究
劉婷婷1,于魯明2,王曉燕1,張溪婷1,程文兵1,齊韶涵1
(1.首都醫科大學,北京 100069;2.北京市醫院管理局,北京 100053)
[目的]了解北京市M縣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現狀,分析目前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關建議。[方法]采用目的抽樣的方法,對M縣3個鄉鎮的21位村干部、21位村醫以及42位村民進行實地觀察并訪談,對訪談結果進行定性分析。[結果]M縣在數量上配有鄉村醫生473人,平均每千人數為1.68人,基本達到政策文件的要求;分布上仍有41個空白村;平均年齡高達56歲;80.95%的鄉村醫生的從業年限高于20年;85.71%的鄉村醫生的初始文化程度為初中及以上水平。同時,鄉村醫生準入門檻過高、待遇水平低、后續保障不足等對其配置產生一定的影響。[結論]鄉村醫生年齡偏大,文化程度偏低,醫療技術水平不高,應通過提升鄉村醫生的待遇,加強后續保障,拓寬鄉村醫生培養的途徑等措施改善村級衛生人力資源的配置。
村級衛生室;衛生人力資源;配置
村級衛生室作為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的“網底”,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健康穩定發展以及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有著重要的作用[1]。根據全國第三次衛生信息普查發現,農村三級醫療衛生服務網絡提供的服務,鄉村醫生占到了60%~70%,農村53.5%的患者在村級醫療機構就診[2]。在村衛生室各種衛生資源配置過程中,村級衛生人力資源處于核心位置,也是村衛生室發展的決定性資源,無論是在村衛生室硬件設施的完善中,還是在具體制度的執行中,各類資源作用的發揮都離不開人力資源這一行為主體能動作用的發揮。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課題組采取目的抽樣的方法,綜合考慮村落地理位置、經濟及文化發展水平,選取M縣3個鄉鎮,每個鄉鎮選取7個行政村,共選取21個行政村作為實地觀察現場,每個村觀察村民2名,村干部1名,鄉村醫生1名,累計觀察84人。
1.2 研究方法
于2015年7月20日至8月3日在北京市M縣進行實地觀察,對3個鄉鎮的3類人群進行深入訪談,訪談內容主要包括各類人群基本情況、村莊生活、衛生服務利用情況、村衛生室舉辦情況以及對未來村衛生室舉辦的建議等。
1.3 質量控制方法
為保證研究的質量,課題組采取專家會議法,在問卷設計階段就其科學性和可行性進行了多輪論證。并在實地觀察和深入訪談前進行預觀察,并對反饋的訪談提綱進行及時的調整。在訪談的過程中,及時對提綱的完整性及回答的質量進行檢查,如有未答或回答不明確的問題及時進行補充完善,提高信息質量。
1.4 調查時間
為深入了解村級衛生人力資源配置現狀及存在問題,首都醫科大學“村民自治”環境下村衛生室服務能力研究課題組于2015年6月至12月對M縣進行了問卷調查、實地觀察及結果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鄉村醫生數量與質量的雙重考驗
2.1.1 鄉村醫生數量上“差強人意”與分布上的“重疊設置”并存
在鄉村醫生數量上,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指導意見》中規定:“原則上每千人應有1名鄉村醫生,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適當增加;每所村衛生室至少有1名鄉村醫生執業”[3]。根據課題組前期兜底資料顯示,M縣17個鄉鎮共332個行政村,其中282個(84.94%)行政村配備有村衛生室,另外有11個村(3.31%)既設有村衛生室又有社區衛生服務站。目前全縣常住人口28.15萬,配有鄉村醫生473人,平均每千人鄉村醫生數為1.68人,在數量上已達到政策文件的要求。
在鄉村醫生分布上,雖然總體平均水平達到文件對鄉村醫生配置的數量要求,但M縣仍存在41個醫療空白村。同時政府在政策上對每千農業人口配置的鄉村醫生數量做出了要求,但并未考慮行政村實際情況,如部分小型村由于未達到政策規定的配置標準而成為鄉村醫生配備的空白村。另外有的行政村由于歷史和地理等的原因,存在自然村落較多、且相距較遠但人口較少的情況,如TST鎮LHY村村民表示由于其村衛生室與他不在同一自然村內,兩個自然村落相距3000m,而村中目前以老年人居多,因此看病就醫非常不便。因此,對于這部分村民的就醫問題必須納入政府政策的考慮。在空白村存在的同時,又有重復設置的情況,如G鎮TH村戶籍人口970人,村中卻配備有3所村衛生室,而戶籍人口370人的T鎮NG村的村衛生室卻至今空置,衛生人力資源上分布的不均衡導致了數量上本就差強人意的村級衛生人力資源更加捉襟見肘。
2.1.2 鄉村醫生質量上“年老體衰”與“資質困頓”并存
在從業年齡上,本次實地觀察的21名村醫中,年齡最小者35歲,年齡最大者79歲。近半數(10人,47.62%)村醫年齡集中在50~59歲。21名村醫的平均年齡為56歲。M縣衛生局《關于〔M縣關于鄉村醫生聘用的實施意見〕的補充意見(試行)》中規定,M縣10個山區鄉鎮中2008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定點村衛生室的鄉村醫生聘用年齡可以放寬到男性63周歲,女性58周歲。實地觀察中發現,所觀察的21名鄉村醫生中,60周歲鄉村醫生7人(33.33%),但由于后續鄉村醫生補充不足,因此政府對鄉村醫生超齡執業的現象持默許態度,詳見表1。

表1 所觀察村醫的年齡結構分布情況 n(%)
在從業年限上,本次實地觀察的21名村醫從醫時間均比較早,其中15名(71.43%)村醫從醫時間早于1983年。其中從業開始最早的為1965年,現從醫年限達到50年。實地訪談中17名(80.95%)鄉村醫生的從業年限高于20年,年輕鄉村醫生較為缺乏,提示鄉村醫生隊伍較長時間無“新鮮血液”的補充,詳見表2。

表2 所觀察村醫的從醫年限分布情況 n(%)
在文化程度上,本次實地觀察的21名鄉村醫生中3名(14.29%)鄉村醫生的初始文化程度在小學及以下;18名(85.71%)鄉村醫生初中及以上水平。其中,2名村醫的文化程度為中專;3名村醫的文化程度為大專,可以看出其鄉村醫生的初始文化主要以初、高中為主,文化程度普遍偏低。
在從業資質上,目前執業的鄉村醫生多數是從以前的赤腳醫生轉化而來。本次觀察的21名村醫中20名村醫持有《鄉村醫生執業證書》;1名村醫持有《執業醫師證書》。而在《2001-2010年全國鄉村醫生教育規劃》[4]中政府提出了鄉村醫生逐步向執業助理醫師轉化的要求,但本次走訪的3個鄉鎮的21名鄉村醫生中僅有1人達標。20年過去了,鄉村醫生向執業助理醫師轉化的進行依然非常緩慢,需要我們重新審視鄉村醫生在執業資質轉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原因。目前鄉村醫生平均年齡較大、知識老化,一方面其學習能力確實已經較低,考取執業助理醫師證書的積極性較小;另一方面,執業資格考試的內容大多脫離農村診療常見病多發病的實際情況,考試難度相對較大,在客觀上阻礙了鄉村醫生鄉執業助理醫師的轉化。
2.2 鄉村醫生服務處于“基本醫療服務”與“公共衛生服務”的兩難處境
2.2.1 村級基本醫療服務日漸萎縮
在實地觀察中發現,村衛生室提供的基本醫療項目與鄉村醫生技術本身有密切關系,有部分村衛生室因技術水平較低無法得到村民認可,已淪為村落藥房,頻臨歇業狀態。在前期的問卷調查中,村民到村衛生室日常尋求的服務類型中排第一順位的是“買藥”,第二順位的是“量血壓和查體”,常見病的診療則僅排在第三順位,而輸液、打針等醫療服務項目則因技術、風險、政策等原因逐漸被摒棄,村衛生室的醫療服務項目較赤腳醫生時期大大萎縮,詳見表3。

表3 村民日常尋求服務排序分布情況
鄉村醫生的醫療技術水平問題是影響農村衛生工作的另一重要因素。目前的鄉村醫生多數是從以前的赤腳醫生轉化而來,大多未受過正規系統的醫學教育,鄉村醫生隊伍知識層次不高,缺乏醫學新知識、新技術的更新升級,診療方法老化。近年來M縣啟動了各項鄉村醫生的在崗業務培訓和繼續教育培養。從培訓的形式和內容看,確實促進了鄉村醫生業務知識水平的提升,但是由于鄉村醫生年齡比較大,主觀上缺乏學習的主動性,客觀上鄉村醫生對新知識的接受程度較低,更習慣于用老方法看病治病,造成了實際效果不理想,知識老化現象沒有改變,鄉村醫生的實踐技能不高。另外在培訓方式上,各鄉鎮主要采取每月村醫例會上“以會代訓”的方式為鄉村醫生播放視頻等方式來進行,形式較為枯燥,學習內容未貼近農村診療的實際需求,鄉村醫生普遍對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如GBK鎮TH村的鄉村醫生就表示:“培訓沒啥用,還耽誤我半天活呢。”而對于培訓考核,目前的考核也日漸形式化和過程化,考核過程較為寬松,考核結果水份較大,無法起到該有的激勵作用。
2.2.2 村級公共衛生服務在夾縫中生存
2014年《村衛生室管理辦法》第八條規定:村衛生室承擔行政村的健康教育、預防保健等公共衛生服務,主要包括:(1)承擔、參與或協助開展基本公共衛生服務;(2)參與或協助專業公共衛生機構落實重大公共衛生服務;(3)縣級以上衛生計生行政部門布置的其他公共衛生任務[5]。對于上述12種公共衛生服務,在M縣觀察的15所政府購買服務的村衛生室中,有5種公共衛生服務是能開展的,分別是村民健康檔案管理、健康教育、高血壓患者健康管理、Ⅱ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和傳染病及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報告和處理。而在村民對村醫提供的公共衛生服務的滿意性評價上,仍有110位(44.00%)村民表示鄉村醫生提供的公共衛生服務不能滿足其日常需求,或感到滿足情況一般,詳見表4。

表4 村民對鄉村醫生提供的公共衛生服務的滿意性評價
實地觀察中了解到,目前村衛生室所提供的大部分公共衛生服務均是村衛生室協助鄉鎮衛生院開展,根據文件規定,鄉鎮衛生院承擔60%,鄉村醫生承擔40%[6]。但訪談中發現,相比于可以帶來利潤的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多數鄉村醫生對公共衛生服務感到興趣寥寥,依然停留在被動應對階段。一方面由于利益等方面的驅動,導致鄉村醫生“重醫療輕公衛”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另一方面,鄉村醫生目前的配置不足、年齡較大、技術素質較低、思想認識不到位,無法承擔好繁重的公共衛生工作也是另一不可忽視的因素。
2.3 鄉村醫生準入條件上的“不習地土”
2003年8月5日國務院令第386號公布《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規定自2004年1月1日起進入村醫療衛生機構從事預防、保健和醫療服務的人員,應當具備執業醫師資格或者執業助理醫師資格[7]。
對于這一要求,本次觀察的21位鄉村醫生中有12人(57.14%)認為門檻適宜,有7人(33.33%)認為門檻過高,不適應當前的現狀。實地觀察發現,多數在崗村醫對于提高準入門檻這一情況,因其與自身利益關系不大,所闡述的觀點多為認可提高資質要求的規定。但這一要求卻讓有意進入村醫隊伍的人員望而卻步。根據農村的實際情況,若要求鄉村醫生必須達到執業助理醫師的水平,則必須要提高鄉村醫生的待遇,解決其房屋、戶口、職業發展、養老等各項待遇。但現實情況是鄉村醫生的執業地點主要在農村,執業環境較差,其服務也定位為常見病、多發病的診斷和治療,身處醫療衛生體制外,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同時準入門檻卻與縣醫院和鄉鎮衛生院執業的醫務人員等同,通過難度較大,必然導致本就吸引力不夠的鄉村醫生更加雪上加霜。因此,盡管我國《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的制定初衷之一是提高鄉村醫生的服務質量,但這種執業資質的偏高設定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將一部分人拒之門外[8]。
3 討論與分析
3.1 衛生政策的制定要與農村“村民自治”的實際環境相適應
政府衛生政策的制定必須與農村“村民自治”的實際環境相適應,要引導鄉鎮政府和村委會公共服務職能的發展,使其明確“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與公共服務的公平供給是推動社會全面發展的制度平臺,也是解決三農問題和農村醫療衛生服務的機制引擎”[9]。雖然政府出臺的各項政策明確規定“村民委員會要積極辦理本村各項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但實際情況是村衛生室和村委會的關系只是形式上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有條件的村委會對村衛生室的發展支持也僅停留在水電暖等資金支持。因此,政府在制定衛生政策時,必須捋順村級衛生人力資源的管理主體,解決目前村衛生室“人人可管卻又無人愿管”的尷尬境地。同時必須規范鄉鎮政府對村委會的具體指導權,以“鄉政村治”的制度安排為準則,嚴格劃分政務和村務的界限[10],要明確誰指揮、誰執行、誰監管,打破原有的僅限于原則性的規定,確定具體的指向和范圍,加強對村級衛生工作及人力資源配置上的重視程度,否則政府的各類衛生政策在實際執行中不過是“雨過地皮濕”。
3.2 改善鄉村醫生的后續保障,實現在體制內共發展
相比于赤腳醫生時代,目前鄉村醫生依然處于“政策內、體制外”的無奈境地。具體表現在執業環境上,鄉村醫生執業環境地處農村,交通較不便利,硬件設施滯后,執業環境較差且身處“熟人社會”背景較為復雜。目前政府的各類補助政策相對于鄉村醫生的工作和生活來說依然杯水車薪。在晉升機制上,鄉村醫生身處醫療衛生體制外,缺乏順暢的晉升機制,導致沒有有效的職業發展規劃,工作積極性較低。在外部保障上,鄉村醫生目前行醫中依然存在風險,缺乏明確的第三方風險共擔機制,同時養老保險水平較低,無法滿足日常需求,導致其職業吸引力較低。
因此,針對這些情況,必須在動態中繼續逐步改善鄉村醫生的待遇。首先要進一步完善政府的財政投入機制。明確政府在農村衛生工作中的主體地位,將村衛生室的醫療設備、人員培訓、公共衛生服務等各項經費納入預算;同時要將投入結構逐漸轉變為以衛生人才的培養等軟環境為主,硬件投入為輔的可持續發展模式,注重對村級衛生人才培養和培訓的財政支持,為村衛生室的平穩運行提供資金保障,并需制定一整套有效的績效考核制度,鼓勵鄉村醫生多勞多得,培養競爭意識。可將運營和發展較好的村衛生室樹為典型予以獎勵,提升鄉村醫生的工作積極性。鄉村醫生工資可參照當地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平均工資,或者借鑒參考城鄉義務教育階段教師實行“同城同薪”制度的薪酬體系改革,為城鄉同級別的醫務人員提供同等待遇,以吸引人才[11]。
其次,建立鄉村醫生第三方風險共擔機制,由政府、衛生局和鄉村醫生個人共建鄉村醫生專項風險保障金,成立專門機構管理基金的使用和運行,保證款項的專款專用。另外,要逐步將鄉村醫生納入醫療衛生體制內,建立有資質的鄉村醫生在鄉鎮衛生院的人才流動機制,為鄉村醫生提供較為順暢的上升渠道。同時,鼓勵有資格的鄉村醫生積極參加國家執業醫師資格考試[12],通過制度和機制的安排,將其嵌入到我國農村“鄉政村治”的客觀實際中。最后,要適當降低鄉村醫生的準入條件,建立鄉村醫生執業考試制度,考試內容與農村工作實際相適用,如常見病、多發病和地方病的診斷與治療等,保障后備人員的補充。
3.3 創新培養模式,促進村級衛生人力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鄉村醫生的技術水平問題,是農村衛生工作的關鍵。對于在崗鄉村醫生的培養,應以實效為重點,改善目前“以會代訓”的培養模式,建立一套完整系統的繼續教育培養規則。首先在培訓內容上應有針對性地制定鄉村醫生培訓規劃,培訓內容貼近鄉村醫療的實際需求,以常見病、多發病及地方病為主,適當補充中醫診療的知識和手法。其次培訓手段上更加靈活多樣,避免“重理論輕實踐”,采取臨床進修、集中面授、實踐實訓和城鄉對口支援等多種方式,激發鄉村醫生對畢業后教育及學歷教育的積極性,使鄉村醫生對疾病診療和預防等知識的掌握更加系統全面。最后,在培訓費用上應繼續貫徹落實免費培訓的原則,并對鄉村醫生培訓所產生的誤工、交通、餐飲等進行適當的補助。
對于鄉村醫生后續人員的補充問題,應聯合醫學院校,創新鄉村醫生的培養模式,應本著“適宜適用”的原則,結合農村衛生工作的實際情況和需求,研究面向農村的衛生人才培養模式,以“定向招生、定向培養、定向分配”的形式[13],從本村選取高中學歷以上,有志成為鄉村醫生的青年,通過相應的考試后進入大學或醫學職業院校進行專業培養,簽訂協議,在培養合格后,本著“鄉來鄉去”的原則,回到本村落或就近村落為農民群眾提供較為優質的醫療衛生服務工作。在鄉村醫生的課程設置上,要區別于普通醫學專業教育,根據農村衛生工作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常見病、多發病和地方病的預防、治療和康復等專業培訓,同時要提高鄉村醫生公共衛生方面的服務能力,并進行農村相關衛生法律法規等的教育,保證其“學得會”,在未來能“用得上”。總之,建設一支留得住、用得上,掌握農村常見病預防與急救、婦幼保健與計劃生育等為重點的衛生適宜技術,并具有良好醫德醫風,能為農村居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保健服務的村醫隊伍才是農村工作的重中之重[14]。另外要加強對鄉村醫生醫風醫德的教育,樹立奉獻精神,增強其對鄉村醫生職業的熱情,從而保障鄉村醫生隊伍后續的穩定性。
[1] 李長明,王 斌.我國村醫存在的歷史意義和發展的現實局限[J].中國村醫雜志,2010,(1):3-4.
[2] 衛生生部統計信息中心.2008年我國衛生事業發展統計公報[EB/OL].(2009-4-29).http://www.gov.cn/gzdt/2009-04/29/content_1299547.htm.
[3]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意見[EB/OL].(2015-3-2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3/23/content_9546.htm.
[4] 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印發2001—2010年全國鄉村醫生教育規劃的通知[EB/OL].(201-2-27).http://www. 34law.com/lawfg/law/6/1187/print_251734098916.shtml.
[5] 國家衛生計生委等.關于印發村衛生室管理辦法(試行)的通知[EB/OL].(2014-6-27).http://www.nhfpc.gov.cn/jws/s3581/201406/55de13fd597a4918bfc42e3a5b7ff2b8.shtml.
[6] 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鞏固完善基本藥物制度和基層運行新機制[EB/OL].(2013-2-10).http://www.gov.cn/xxgk/pub/govpublic/mrlm/201302/t20130220_65940.html.
[7] 國務院辦公廳.鄉村醫生從業管理條例.國辦發[EB/OL].(2003-8-05).http://www.moh.gov.cn/mohzcfgs/pfg/200804/30766.shtml.
[8] 呂兆豐,王曉燕,線福華.雨潤圓荷—醫改背景下農村衛生實地觀察手記[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2.
[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841.
[10] 盧福營.沖突與協調:鄉村治理中的博弈[M].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83-86.
[11] 蔡惠州.新農合背景下的鄉鎮衛生院人力資源狀況研究[J].中國社會醫學雜志,2010,27(1):23-25.
[12] 王 玉,王曉燕,韓優莉,等.鄉村醫生執業資質轉化難的原因及對策[J].醫學與社會,2013,26(4):7-10.
[13] 陳烈平,賴愛華,黃淵清.新農合的實施對農村衛生人力資源的挑戰[J].中國農村衛生事業管理,2008,28(11):819-821.
[14] 楊淑艷,鐘秀宏,張以忠,等.明確目標培養高素質鄉村醫生[J].衛生職業教育,2011(9):24-25.
(本文編輯:鄒 楊)
Analysis 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village level health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Take M county as an example
LIU Ting-ting1,YU Lu-ming2,WANG Xiao-yan1,ZHANG Xi-ting1,CHENG Wen-bing,QI Shao- han1
(1.CapitalMedicalUniversity,Beijing100069,China;2.BeijingHospitalAuthority,Beijing100053,China)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status of health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 in M county of Beijing suburb,analyze the problems and causes of village health human resources allocation,and put forward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Methods Used the method of Objective sampling,observed and interviewed 21 village cadres,21 village doctors and 42 villagers in 3 townships,and the Results were analyzed qualitatively. Results M county in number with 473 rural doctors,the average per thousand people was 1.68,basically reached the requirement of policy documents. The distribution still had 41 blank villages,the average age was 56 years old. 80.95% of rural doctors’ working years was higher than 20 years. 85.71% of the village doctors’ cultural degree were junior high school level and above. At the same time,rural doctors access threshold was too high,low level of treatment,the follow-up to ensure the lack of its configuration had a certain impact. Conclusions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reatment of rural doctors,strengthen the follow-up protection. Broaden the ways of rural doctors training and other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allocation of village health human resources.
village clinics,health human resources,allocation
2016-05-30
10.3969/j.issn.1003-2800.2016.10.001
首都衛生管理與政策研究基地重大項目(2015JD01)
劉婷婷(1991-),女,山東青島人,在讀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衛生政策方面的研究。
于魯明(1961-),男,北京人,學士,北京市醫院管理局局長,主要從事衛生政策改革方面的研究。
R195
A
1003-2800(2016)10-0003-05
?本期關注:衛生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