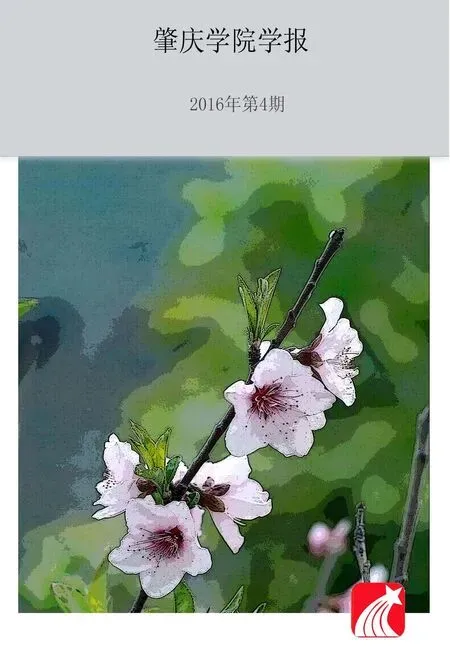《己卯年雨雪》與抗戰文學的新敘事
顏同林,王麗婷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新世紀嶺南文學研究】(欄目主持人:黎保榮)
《己卯年雨雪》與抗戰文學的新敘事
顏同林,王麗婷
(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貴州貴陽550001)
主持人語:熊育群是廣東文壇也是中國當代文壇的知名作家,以散文名世,其散文集《路上的祖先》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后轉攻小說創作。《連爾居》《己卯年雨雪》為其至今的長篇小說代表作。他系同濟大學建筑工程系畢業,從事過建筑設計、新聞、出版等工作,后棄工從文。其作品既顯工科人的細致,又兼記者的敏銳以及學院派的靈氣與厚重。長篇小說《己卯年雨雪》2016年1月出版。古語云“十年磨一劍”,他是“十四年磨一劍”,用了14年的時間來調研、采訪、閱讀與寫作。可見這是一部用心用力的大作、杰作。
主持人:黎保榮
熊育群的小說《己卯年雨雪》是一部“和平之書”,小說從作者家鄉汩羅江兩岸1939年8月的抗日史實出發,從日本人與中國人交錯互動的視角來寫當地抗日戰爭,考察軍人與平民在戰場中的特定狀態和心理,追根溯源地探究了侵略戰爭的罪惡本質,并建構了自己獨特而鮮明的新敘事模式。其中包括采用了雙線并行與交叉錯綜的敘事結構,以此來突圍傳統戰爭文學較為單一的敘事視角;借鑒了復調的敘述方式,將對戰爭的反省,人性的復雜放置在一個獨特而豐富的審美空間之中。小說具有可讀性、傳奇性,頗見作者的用心與用力之處。
《己卯年雨雪》;新敘事;雙向視角;復調敘述;傳奇性
當代知名作家熊育群的家鄉是湖南岳陽,在日夜流淌的汩羅江兩岸,大小村莊遍布于這片湖區。春夏秋冬,四季輪回會有不同;風電雨雪,看似平常卻見異色。當人們把目光回溯到1939年農歷己卯年的八月,雖然同樣是在秋季,雖然也是常見的風雨天氣,但是這年八月卻格外的特別和血腥。以營田、推山咀、大灣楊、馬頭曹、南渡橋、新市、河夾塘等為具體地名的村莊或集鎮,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區域,經歷了一次次無比慘烈的大型戰役。作為長沙會戰的前沿之一,中日兩個國家的軍隊屯集于汩羅江兩岸,雙方敵對的軍人、平民,以及這些人物背后的萬千家庭,都聚焦于此。在戰爭地所發生的硝煙與故事,并沒有隨著歷史的推移而失去了記憶,相反,它會因為摧殘人性的酷烈、因為鄉土的熟悉而永遠定格了下來。——熊育群的童年記憶,雖然沒有戰爭,但更多的是這些戰爭遠去后留下來的村莊與市鎮,以及年長的親人與鄉民,因此,油然而生的是一份銘記痛苦記憶的勇氣與擔當。十多年之間,熊育群一直醞釀與構思著這部紀實性作品,一步一步地進行著扎實的史料搜集和實地調研工作。記述地方抗戰史實,反思戰爭本性,便有了這部沉甸甸的力作——《己卯年雨雪》。
故事的梗概并不復雜:1939年中秋前后,一名叫武田千鶴子的日本女人踏上了中國國土,目的之一是慰問自己新婚之后便辭別家鄉、遠赴中國打仗的丈夫武田修宏,在岳陽營田戰地終于與丈夫短暫團聚。兩人隨后在隨軍行進過程中遭遇了埋伏,武田重傷生死未卜,千鶴子則被中國軍民俘虜。俘獲押送她的核心人物是祝奕典,因其與祝氏關愛之人王旻如相貌十分相像,僥幸得以活了下來。千鶴子先是受到祝奕典等人仇視,隨著雙方了解不斷深入,她后來得到祝奕典、左坤葦夫婦,以及左太乙等一家人的救助與關懷。期間千鶴子誕下了與武田修宏的孩子,而武田修宏死里逃生,歷經千辛萬苦尋找妻兒,最后孩子找到了,自己卻難逃命運的安排而被擊斃。故事最后以千鶴子被押送至戰俘營,祝奕典則因窩藏日本人而被判了十年監禁而告終。
《己卯年雨雪》立足于特定地域,以抗戰新敘事見長,其引人入勝之處,不僅僅在于塑造了武田千鶴子、武田修宏、祝奕典、左坤葦和左太乙等一批血肉豐滿的軍民人物形象,展現了戰爭下人性的善與惡、恩與怨、仇恨與寬恕等主題,更重要的是,作家用獨具匠心的敘事技巧,為我們怎樣講述這一個故事做出了可貴的探索。
一、雙線并行、新穎多樣的敘述結構
與大多數文學作品的單一結構線索不同,《己卯年雨雪》為了追求故事內容的豐富新穎和情節結構的跌宕起伏,強化陌生化,設計的是雙線甚至是多線條的敘述結構,中間還用明暗結合互補的方式加以縫合。“小說家詹姆斯曾略帶夸張地說:‘講述一個故事至少有五百萬種方式。’每一種講述方式都會在讀者身上喚起獨特的閱讀反應和情感效果,因此如何講述直接決定著這種效果能否得到實現。”[1]敘事學理論告訴我們,同一個故事可以有不同的敘述方式,研究敘事文學作品應該研究故事是如何被敘述的,如何敘述對于作品來說十分重要。熊育群在《己卯年雨雪》的新敘事形式無疑體現出了作家的個人化思考。
首先,從小說的故事情節可以看出,作者有意以中日兩對不同戀人的遭遇與命運為主線,即以武田修宏與武田千鶴子,祝奕典與左坤葦為中心開展故事情節。兩條線索并非是平行不相交的,兩對戀人之間的故事也不是彼此孤立的,他們之間有著密切而錯綜的聯系,這就涉及到了隱藏于其中的橋梁——曾經喜歡祝奕典并差一點與之結合的王旻如,是王旻如被日軍殘暴殺害之后,報仇心切的祝奕典俘虜了千鶴子,故事一下子就進入了恩怨分明的膠著狀態。千鶴子和王旻如之間冥冥中注定有著某種聯系,祝奕典“第一次看到一個人與另一個人長相如此酷似……日本女人與中國女人原來是一樣的”。在后續情節中,這種似曾相識得到了擴大。譬如,千鶴子還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左坤葦還跟著千鶴子學日本禮儀,千鶴子喜歡莊子,收藏《史記》,自幼背誦《論語》,崇拜諸葛亮,迷戀《紅樓夢》……甚至連武田修宏也推崇中國古代文人墨客的典故“雪夜訪戴”“竹林七賢”和“蘭亭雅集”;中國與日本的很多節日也是相通的,中國的清明節和日本的盂蘭盆節都是祭祀祖先的日子,武田夫婦的家鄉日出町也時興過中秋節;中國的陌生面孔能讓他們想起自己家鄉的親人,武田修宏看到的那個像自己舅舅的老人,他給老人煙抽,并想營救老人,雖然老人最終還是慘遭殺害;左太乙也讓千鶴子聯想到自己家鄉的老人,“在她的印象里,這個老人似曾相識,她想不起來在哪里見過,在志高湖還是經冢山?反正是日出町遠處的什么地方”;甚至中國村莊土墻上的牽牛花和日出町的也一模一樣。關鍵的一點是,千鶴子還會講漢語,大體聽得懂一些當地方言,使得她與祝奕典等人之間的溝通消除了語言上的障礙,拉近了來自兩個不同國家的完全陌生者之間的距離。在雙線并行中,正是這些情節與感情上的許多支架,像血管一樣密切相通,讓兩條并行線索較好地交融在一起,相互之間產生豐富的關聯。
其次,作者在小說中還采用了新穎多樣的敘述方式。一般來講,小說的敘事順序主要分為順敘、插敘、倒敘和補敘之類。順敘是最簡單、最基本的一種敘述方法,它是按照時間的先后順序來反映人物事件的經過與原委,使用順敘便于確定文章的中心和布局,方便安排材料,寫作起來也相對順手,使得文章條理清晰、層次分明。這也符合人們認識事物的發展規律,是敘述性文學作品常用的敘述方式。但是,如果單純使用順敘又會給文章帶來平淡無奇的感覺,難以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小說的結構涉及人物的配備,情節的處理,環境的布置,章節段落的劃分,以及它們之間的聯系和結合,等等,這些都要通過作家艱苦的創造性的勞動,加以巧妙的編織,形成為一個生氣貫注的有機整體。”[2]好的小說必然離不開好的敘述方式,倒敘、插敘和補敘的使用則彌補了順敘結構的不足,使得文章跌宕起伏,懸念叢生,無形中豐富了文本的閱讀內容,從而引起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
《己卯年雨雪》對這種復雜結構的運用,使得作品的情節有了波濤起伏般的變化,有助于增強作品的層次感,深化作品內涵。小說以千鶴子訪親被俘為開端,以其被送往戰俘營告終,故事敘事時間長度為一年多。在這一年多的時間內,除了祝奕典的故事與其并行發展外,故事中大量穿插了千鶴子的人生回憶,武田修宏的戰爭體驗和變化;以及左太平、左太乙、左坤葦、王旻如等人悲歡離合的小故事。小說主體以現實發展為主,插敘了大量回憶性片斷或情節,比如千鶴子在昏迷時回憶起母親在少女時代教她如何伺候未來的丈夫,以及她和武田修宏結婚時的場景,他們在日本作為普通人生活的一幕幕展現在讀者面前;祝奕典也在故事的發展與推進中,回想起與左坤葦的美好愛情,他和王旻如的陰差陽錯……諸如此類,都是這部小說吸引讀者的匠心之處。
二、雙向視角、多種聲音的復調模式
小說是一種敘事的藝術,敘事文本中整個錯綜復雜的方法問題,“都要受角度問題——敘述者所站位置對故事的關系問題——調節。”[3]不同的視角會有不同的效果,而所謂視角,是指“敘述者或人物與敘事文中的事件相對應的位置或狀態,或者說,敘述者或人物從什么角度觀察故事。”[4]可見,視角作為敘事要素之一,與敘事作品的整體風格互相應和,共同體現創作者獨特的創新思維與能力。敘事視角的意義還在于它是建構敘事文本的基點,是作者與文本的心靈結合,作者把他體驗到的不論是現實的還是歷史的世界,轉化為語言敘事的虛擬世界;同時,幫助讀者進入敘事虛構世界當中,找到打開作者心靈的鑰匙。總之,敘事角度選取的成功與否,直接關系著小說藝術成就的高低,同樣會在較大程度上影響小說的風格設定和技巧、節奏,等等。
熊育群在小說《己卯年雨雪》中,敘事視角上有意將日本人作為主角,并站在他者的立場展開敘述,與以前同類題材的抗日作品截然不同。作者在長篇“后記”中就曾提到“我要寫一對日本戀人和一對家鄉的戀人”的故事,“中國作家寫抗戰題材小說鮮有以日本人為主角的”,作家的理由是“一場戰爭是兩個國家間的交戰……任何撇開對方自己寫自己的行為,總是有遺憾的,很難全面,容易淪為自說自話”。作者覺得“要真實地呈現這場戰爭,離不開日本人”,“我想,超越雙方的立場,從仇恨中抬起頭來,不僅僅是從自己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出發,從受害者的立場出發,而是要看到戰爭的本質,看到戰爭對人類的傷害,尋找根本的緣由與真正的罪惡,寫出和平的寶貴,這對一個作家不僅是良知,也是責任。”正如優秀的敘事作品“以小說特有的方式,以小說特有的邏輯,發現了存在的不同方面”[5]一樣,作家發現的側面不同,體現出來的精神也是不同質的。這種以日本人為主角進行敘事的創作手法,無疑成了此書中的一個亮點,為作者打開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敘事空間。知名學者孟繁華在其著作《敘事的藝術》中提到,“視角的變化極大地改變了敘事藝術的結構,對于提高敘事藝術的表現力提供了眾多的方式。我們大概都會承認,同一個故事會由于敘述方式的不同而產生完全不同的藝術效果。”[6]75在論述敘事視角的選擇意義時,他認為視角選擇的多樣性表明“眾多的作家是在促進創作多樣化的發展,是在探尋‘怎么寫’才有可能接近真實的。比起一種敘事視角來說,多種視角畢竟能滿足更多的審美消費需求”[6]36。無疑,這一說法有的放矢,是小說敘事研究的一種深刻見解。敘事視角的選擇和設定,對于小說《己卯年雨雪》創作的成功有著積極意義。另一方面,小說《己卯年雨雪》在敘事模式上還借鑒了復調小說的發展模式。復調小說理論是蘇聯著名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研究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的基礎上提出的,認為“有著眾多各自獨立而不相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由具有充分價值的不同聲音組成真正的復調”[7]。而小說《己卯年雨雪》在人物描寫、內部聲音上,尤為注重人物心理活動和想象描寫,這是“復調小說”的一個重要特征。
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盡力從敵我雙方的自然轉換、不同聲音的對話與沖突來展示雙方人性的丑惡與美好,凸現人物思想上的不斷變化與矛盾。其中,我們認為這一“復調”思想主要體現在對戰爭與和平的反省,以及對敵國態度的換位思考上。千鶴子由最初仇恨中國人,隨著與中國人的深入接觸,慢慢地理解和接受了祝奕典等人,并最終與他們達到了心靈上的融合。她認識到“說支那人奴性十足是錯誤的。這里的人看不到一點奴性”,千鶴子不再為“圣戰”辯護,典型的如“祝奕典殺侵略自己國土的人,殺殺死自己心愛女人的人,又有什么不對”,她最終選擇了完全站在中國一方,站在正義一方。在被俘期間,她不斷反思戰爭的意義,作者有意讓我們從一個日本女人的視角來認識和解讀戰爭,即由最初所認為的“我們日本人有責任把支那從白人手中解放出來”,指責中國“是一個不爭氣的鄰國,它過去太自大了,從不向外面學習,搞洋務運動只是學些堅船利炮的東西”;到質疑“那里真的是日本人的希望嗎?中國人真的需要我們去為他們做事?為什么還要打仗呢”;再到徹底否定“‘太可怕了,簡直是地獄!’國內的報紙把戰場描繪的那么壯觀、美妙,英雄都是那么勇敢、高尚,這里看到的無非就是殺人,那些報導多么無知”。
與千鶴子相似,武田修宏的心路歷程同等重要,他讓我們從一個日本士兵的角度更徹底地認識到了戰爭的本質。武田修宏首先是認同戰爭,不傷及無辜,但逐漸把槍對準了中國平民,在習慣了殺戮的同時也在慢慢思考:“這種行為是否恰當?我們是為了和平才破壞和平嗎?和平真的離不開戰爭?為什么所有的戰爭都在說捍衛和平?”這本身就是悖論,“為了和平而破壞和平”,這種軍國主義者灌輸的荒誕邏輯在小說中大量存在,在相當一段時間內蒙蔽了像武田修宏這樣的軍人。最后,他開始不斷反思戰爭中的士兵,和鼓動戰爭的領導人,希特勒鼓舞人心的話,讓他感到反感,他覺得“人這種動物真是盲目”。“為何戰爭就能使人發瘋?這真是正義的‘圣戰’嗎?日本是優秀民族,希特勒也稱德意志為優秀民族,他們在歐洲大陸開了一個個‘舞場’,為什么全世界都在殺人?”“既然是為亞洲人的自衛自存,理應受到支那人的歡迎,但為何看到的全是仇恨和恐慌?這兩年的經歷,武田修宏遇到的全是反抗和戰斗。強迫別人就是應該的嗎?好東西為什么他們不接受?支那人真的那么愚蠢,連好歹都不分了”“靠殺人來實現的主義會是好的主義嗎”。小說中類似的句子、段落有很多,從中不難發現,不論是千鶴子,還是武田修宏,都有其內心不同聲音的對話,在本真的猶疑與怯懦之間,在自詡的正義與真理之間,在殘忍的屠戮與傷害之間,這些飄蕩在人生歧路上的各種聲音,總是突然而至,處處讓人產生一種不信任感、不真實感,并從內部否定了這場曠日持久的戰爭。
同樣道理,站在身份斑駁的“抗日英雄”祝奕典的角度來看,雖然他無法放下對日本人的仇恨,但隨著與千鶴子的深入接觸和對她的了解,也覺得“她溫順、禮貌、善解人意,她完全是她自己了”“他觀察日本女人一段時間后,心里就開始糾結,越是糾結越是仔細的觀察,越是仔細的觀察越發現她不同于她的同類”,慢慢地祝奕典也對千鶴子產生了愧疚心理,“他覺得自己對她太狠了。他把她的一生毀得干干凈凈”,而人與人之間的諒解,是建立在互相理解和信任的基礎上的。至于左太乙、左坤葦等人,超越了簡單的冤家路窄的復仇心理,他們與普通民眾不同的地方,同樣存在于他們能在具體的人與事中進行獨立思考,同樣存在于他們對人性普遍真善的常識以上的判斷。所以,在小說的情節推進過程中,越到后來,中日軍民在中國血與火的戰場上相逢,漸漸消泯了各自國籍的標簽,和平共存的主題也得到了凸現。
三、傳統戰爭文學敘事技巧的借鑒與創新
《己卯年雨雪》具有鮮明的傳奇色彩和浪漫主義特征。小說從開頭到結尾,所穿插的命運預言、奇幻情境和離奇的情節,等等,都是十分普遍的。類似“比較典型的運用了通過幻想反映現實的表現方法”[8]一樣,傳統戰爭文學的敘事元素,給小說作品帶來了強烈的可讀性,一定程度上滿足了讀者的想象訴求。
以小說人物而論,中心人物之一的祝奕典是作者筆下的抗日英雄,但“他一會兒是篾匠,一會兒是跑江湖的船幫,一會兒殺日本梁子,一會兒又與土匪糾纏不清,隱身江湖,任性而為,從無約束”;同時又有著脆弱柔情的一面,他對王旻如用情至深,對左坤葦和孩子都是體貼關懷、充滿愛意,甚至對千鶴子后來的態度也轉變為關懷和憐憫,內心充滿愧疚。與祝奕典形影不離的是他充滿傳奇色彩的響刀,其來歷十分罕見:“打成一把五行刀,師徒倆都會病一場。師傅知道他們的病除了累,還有神靈的懲罰,當那刀兀自鳴響的時候,師徒倆就開始頭昏腦脹,師傅聽到了靈的哭泣。他知道打出這樣的寶刀是一種罪孽”,這把奪命的五行刀甚至會“自言自語”,它有著嗜血的本性,“它在指揮自己殺那個日本兵”,祝奕典沒能來得及思考“刀自己就在行動了”“響刀開始成為傳奇。它注定不凡。”一把寶刀的出世,仿佛是吸取了天地的精華,帶著殺戮和罪孽,這種寫法頗具傳統武俠小說的風韻,讓人讀來嘆為觀止。佩刀之人自然也是非凡之人,祝奕典“一直貼身帶著這把響刀,母親手中的一根線他不用剪而用刀斷開,他用刀給人剃光頭、刮胡子,用刀把筍切得紙一樣薄……他眼到刀到,不差分毫”。在迷魂一樣的楊仙湖上,祝奕典能夠出入自如,“人們談論他就像談論神靈一樣充滿敬意”。顯然,如此種種關于冷兵器及其主人的描述,大體延續了傳統戰爭文學中對英雄人物的神性化塑造,雖帶有明顯的夸張和浪漫主義傾向,但并沒有影響小說事件真實性的曲折反映,作者通過這種文學書寫的方式凸現出人物的英勇和傳奇,相對于概念化敘述更能激起讀者的閱讀興趣。
而另一個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就是左太乙。左太乙是小說中最親近自然和回歸本真的人,他通曉老子、莊子和《周易》,從不帶著世俗的眼光和心境來看待外界。他“一步步沉浸到了老子、莊子和《周易》的世界,從陶淵明、王維、柳宗元的詩中尋找著慰藉,最終心皈道教”。左太乙愛鳥、護鳥,為了遠離亂世,他躲到大灣楊“上到荒洲,與鳥為伍,更無人世的糾葛了”,世界在發生著變化,但他在鳥的世界里,看到“純凈、自在、悠然、輕盈、忘我……”。在戰爭年代里他堅持尋找內心的回歸,“一個人長期在湖中生活,沉思默想,迷戀孤獨,漸漸地他開始生活在自己的幻想中了,時間卻在為他慢慢打開”。與仇恨日本女人相反,他視千鶴子為國人、親人,在戰爭中,無辜的女人需要的是保護,而不是無情的屠戮。試想,如果沒有左太乙,千鶴子能存活下來么?最令人稱奇的是,最后他的死也成為了一個不朽的傳奇,老人消失后蹤跡無處可尋,等找到他時,已經有一個月的時間了,而“他的尸體竟然沒有腐爛”,他的相貌“一天一變,好像許多個人的模樣”,就連左坤葦甚至都不能確定這是自己的“爺”,而這個神奇的老人仿佛還永遠存在于天地之間。左太乙的死又成為了大灣楊人們口里的怪事——“死的怪”,村民以七大怪來總結他的人生。總之,作者在左太乙身上,展現了他對自然,對道,對人性的終極追求,其目的之一便是與戰爭的發動者、漁利者、嗜血者進行鮮明的多維對比,人性的美丑、善惡自然也昭然若揭!
對于戰爭中普通人物命運捉摸不定的安排,也成為了小說中的創新之處,作者以此來體現出人在戰爭中無法掌控自己命運的荒誕感和無力感。這種命運的安排在對武田修宏的描述中體現得最為明顯。“自踏上支那國土開始,他就越來越相信命運了”,他認為“戰場上誰會死,什么時候死,其實命運早已做出了安排”。比如,戰場上井上被安排在后面最安全的地方,死的卻是他,讓武田修宏“覺得生命真是無常,命運似乎早就注定了一切,人的努力也許都是徒勞的”“戰場上誰會死,什么時候死,其實命運早已做出了安排。有人置身槍林彈雨毫發無傷,有人躲在戰壕卻被打死。只有命運才能決定一個人的生死”。當我們讀到這些故事細節時,莫不感慨萬千:桑野想方設法躲避死亡,但他卻死了,被流彈擊中;井上總是調侃大家會幫他們把骨灰帶回去,但井上卻死了,自己連骨灰都沒能留下。幸存下來的人也像是命運的安排,如村民黎哲秋的家人慘遭殺害,自己為家人去白水親戚家找食物卻逃過一劫……這些都體現了戰爭的荒誕性和命運的不確定性,既像夢魘一樣帶有傳奇色彩,也對戰爭本身的特質進行了徹底的解剖。
四、結語
熊育群的小說《己卯年雨雪》,采用了雙線并行與交叉錯綜的敘事結構,以此來突圍傳統戰爭文學較為單一的敘事結構;同時借鑒了復調的敘述模式,將戰爭的反省、人性的復雜放置在一個獨特而豐富的審美空間之中。作為一部難得的“和平之書”,小說從日本人的視角來寫戰爭,考察日本人在戰爭中的特定狀態和心理,追根溯源地探究與否定了戰爭的本質,而不只是以單向的視角,僅僅提出控訴和指責。這樣在反思中大力向前推進,既建構了自己獨特而鮮明的敘事模式,也在主題上進行了新的嘗試。作家這一努力,使得小說作品具有可讀性、傳奇性,也足以見出作者用心與用力之處。
[1]羅鋼.敘事學導論[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58-159.
[2]孫子威.文學原理[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201.
[3]盧伯克.小說技巧[M]//方土人,譯.小說美學經典三種,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180.
[4]胡亞敏.敘事學[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19.
[5]米蘭·昆德拉.小說的藝術[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5.
[6]孟繁華.敘事的藝術[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
[7]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M].北京:三聯書店,1988:29.
[8]游國恩.中國文學史(二)[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200.
(責任編輯:盧妙清)
The Rain and the Snow in 1939 and New Narrative of Literature of Anti-Japanes War
YAN Tonglin,WANG Liting
(Collegeof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University,Guizhou,Guiyang 550001,China)
ract:The Rain and the Snow in 1939 is one of Xiong Yuqun’s novels,which can be called“the Book of Peace”.The novel,starting from the anti-Japanese historical facts in August1939 thathappened in M iluo River on both sides of the author'shometown,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Japanese and Chinese people,w rites about the Anti-JapaneseWar of the local,investigates them ilitary and civilians'certain status and psychology in battle fields and explores the evil nature of invasion w ith trace to the source,and then constructs new narrativemodesw ith unique and distinctive style himself.These include:narrative structure of parallelmodel and cross-complex,which is a reform of the simple narration of the conventionalwar literature;the narration mode of polyphony,placing the introspection of war and the complex of humanity in an aesthetic,specific and rich space.The novelpossesses readability and legendary show ing the author’sgood intentions.
ords new narrative;dualperspectives;polyphonic narration;legendary
I207.425
A
1009-8445(2016)04-0001-06
2016-04-09
顏同林(1975-),男,湖南漣源人,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